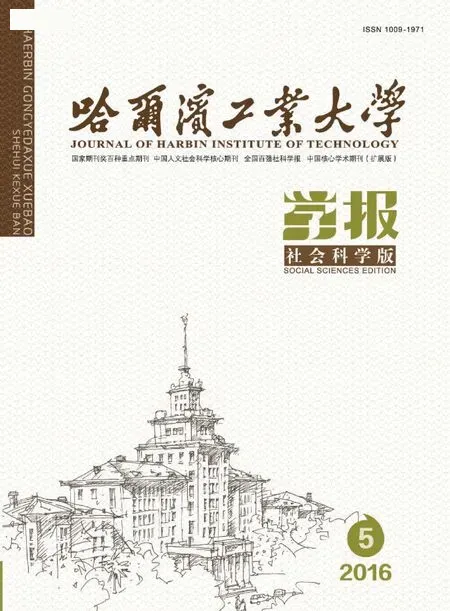启蒙: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复杂性理解
——评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启蒙与现代性的研究
郑 飞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100026)
·哲学研究·
启蒙: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复杂性理解
——评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启蒙与现代性的研究
郑 飞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100026)
新世纪以来,启蒙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这一时期,学界关于启蒙的讨论日趋深化,从思想层面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学者们看来,启蒙不仅意味着个体认识方式的改变,更意味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值得关注的是,对启蒙与现代性问题的检视与反思逐步成为这一时期的热门话题,有的学者把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弊端的根源寻溯到启蒙。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关于启蒙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一幅纷繁复杂的理论图景。虽说学者们观点各异,但都承认启蒙以来的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所具有的某种复杂性。在某种意义上,启蒙意味着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复杂性理解。
马克思;启蒙;现代性;复杂性
新世纪以来,启蒙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参考当下“时兴”的大数据研究手段,笔者在知网、百度和谷歌上,分别以“启蒙”、“革命”为关键词,限定时间段为1949年—1977年、1978年—1989年、1990年—1999年、2000年以来进行检索。其检索出的文献数量显示:“启蒙”呈递增趋势,“革命”呈递减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革命”数量高于启蒙;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启蒙”数量高于革命;二者数量变化的临界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然,以知网、百度和谷歌为代表的网络平台收集数据的完整性并不完备,所收集的数据也并非全部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性,甚至其中夹杂着大量的冗余和重复,但这一检索结果大致反映出国内学界对启蒙问题与日俱增的关注热情。
在上述比较的基础上,笔者在知网上以启蒙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按照1949年—1977年、1978年—1989年、1990年—1999年、2000年以来四个时间段对检索得到的文献进行整理。笔者发现,2000年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启蒙研究的学术文献呈现出井喷的趋势,新世纪以来这一研究的文献数量超过之前的总和。其中,大部分文献的主题围绕启蒙与现代性的研究展开。
一、深化:从思想层面拓展到社会生活诸领域
新世纪以来,学界关于启蒙的讨论日趋深化,从思想层面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学者们看来,启蒙不仅意味着个体认识方式的改变,更意味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一变迁过程不仅涉及器物和制度,而且深入到思想、历史、文化、艺术等精神理念层面。
诚如张光芒等在《论新世纪的启蒙话语及其思想谱系》中所指出的那样,新世纪启蒙思想谱系的新变化表现在社会、阶层、个体、心灵由表及里的四个层面。张光芒回顾并梳理新世纪的启蒙话语方式:“其一是社会层面,着重探讨社会、文化结构模式的重新取径;其二是阶层层面,表现为‘底层’话语以及卢梭意义上的平等意识凸显;其三是个体层面,体现为对自由命题的重新探究;其四在心灵层面,表现为信仰意义上的人性价值突入。”[1]。
启蒙不再是大而化之的研究对象,在宏大叙事背景下寻求深入细致的学理分析成为新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趋势。当然,这也体现出不同学科背景的差异。但无论在哪个学科中,较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热”而言,在新世纪以来关于启蒙的研究中,思想退场、学术登场都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中,既有叶秀山、韩水法、周晓亮、张慎、赵林、尚新建等从哲学思想层面深入分析欧洲启蒙思想的哲学根源,也有卢钟峰、姜义华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启蒙背景下的中西文化变迁,还有马德普、丁耘等研究启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叶秀山认为,“康德关于‘启蒙’的观念,不是孤立地对一个问题的见解,而是和他的整个哲学的观念密不可分的”,“‘启蒙’作为一种思想潮流或运动,它的旗帜上写着‘理性’。这是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进入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2]。
韩水法强调,“康德的第一批判和第二批判是理性自我发现、认识乃至构造的典范作品,它展现了同一理性在经验世界的不同层面所营造的两种不同秩序”。然而,“理性不仅展现为不同的能力、原理和层面,而且这些领域及其现象可以分别予以探讨;不同的理性原理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在理论上或是不清楚的,但它们在现象之中却确实地建立起来了,所留下的只是理论难题”。“理性在今天依然占据首要的地位,但相比于启蒙时代人们对它的展望和憧憬,情形则远没有那么理想和完美。理性非但没有形成内在一致的统一体系,反而更趋多样化,呈现更多的内在矛盾”[3]。
周晓亮提出,“中国与西方的交往有悠久的历史,尽管那时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是表面的、浮浅的、抽象的,但它为思辨层面的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思想进入西方的视野做了现实和物质方面的准备”,“鉴于中国的国情,来华传教士采取了尊儒、附儒的策略,促进了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传播”,“欧洲的启蒙运动成为西方了解和接受中华文化的内在动力”[4]。
张慎主张,“虽然德国启蒙运动在时间上要晚于英国和法国,但它在追求目标和表现形式方面与英国和法国有很大不同,尤其在思想理论深度方面要超过它们”,“由启蒙运动留下来、并对现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个最重要思想遗产,就是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概念。人性、人道主义是启蒙运动的核心”[5]。
赵林指出,“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虽然在哲学上导致了一种理性主义独断论,但是这个体系同时也是对当时在德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虔敬主义神学或信仰主义独断论的猛烈冲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德国启蒙运动的发展”。在他看来,“与慷慨激昂的法国启蒙运动不同,德国启蒙运动始终保持着一种理性的审慎态度,它对基督教的批判远远不如法国启蒙运动那样激烈,但是却比后者更加深刻。德国启蒙运动最初表现为对圣经的历史考证和理性批判,当法国启蒙主义者以一种嬉笑怒骂的方式将圣经斥为一堆无稽之谈的大杂烩时,德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却以德国人特有的严肃认真态度对圣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历史考据”[6]。
尚新建提出,“西方近代发生的启蒙,并非一场简单的运动或一股短暂的思潮,而是整个西方文化的重新塑造,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关注人性”。在他看来,“启蒙思想家注重人性,是为了改变传统人性,尤其是中世纪残留的基督教人性,从而塑造新人,建立新的文化制度,以适应新的时代”,“自爱(自利)与理性,是启蒙人性的两个重要因素或主要根源”,“启蒙人性的这两个因素反映出启蒙思想家的某种一致倾向,即用自然的、甚至物质的机制解释人性,解释人的道德情操,解释人类社会和文化制度,从而切断了人与上帝的神秘联系,让人从天上回到地面”[7]。
针对“在中国历史上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卢钟峰认为这种“萌芽史观”是“把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套用于中国历史的产物,是用‘假如理论’编造而成的‘假历史’”。他进而指出,“18世纪的中国已经出现了社会思潮的异动,形成了多种文化形式并存互争的局面。其中,传统与启蒙之争贯穿于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始终,决定着社会思潮的走向,从而构成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基本特点。正如封建社会晚期在生产方式上所发生的新变化已经无法从封建社会的传统性质中得到解释,而只能从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因素中找到答案一样,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异动也已经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而另辟新径,只有从思想启蒙的意义上才能作出科学的说明”[8]。
姜义华分析“启蒙复兴”的世界历史背景,他指出,“启蒙的复兴,其国际背景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重新高速启动,其国内背景则是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重新高速启动,得力于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及在生产过程中被广泛使用,还得力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努力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欧美及大洋洲等许多国家取得明显成效,缓解了这些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越来越多的民众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实现了他们的价值。亚洲众多新兴国家与地区的崛起及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新秩序、政治新秩序的建设,加上苏东体制的瓦解,使重新高速启动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一体化所没有的一系列新特点。这一环境无疑有利于启蒙在中国的复兴,有利于启蒙核心观念为人们所认同”[9]。
“启蒙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命运”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在马德普看来,“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虽然发端于清末的维新运动,但真正意义的启蒙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该说,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两大价值体现了西方启蒙思想的基本精神,也反映了现代性的一些基本要求。当然,五四运动虽然在促进思想解放、传播科学知识和现代理念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是由此造成的科学崇拜及其导致的科学主义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端”。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启蒙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它所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本身就是批判的”,“反思和批判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人类活动,启蒙也是一项不断破除迷信和教条的未竟事业”[10]。
丁耘重点分析启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他认为,“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讨论语境中,‘中国式启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已如此紧密,以至于被当作同义语使用。这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某个面相,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五四运动与启蒙观念本身的复杂性。无论是舒衡哲—李泽厚以及汪晖的启蒙论叙事,还是冯友兰—沟口雄三那样避免直接提及启蒙的叙事,都不言而喻地将启蒙置于和传统的对立之中”[11]。
二、反思:对启蒙的反省与批判
世纪之交,随着哈贝马斯、福柯等人的大量著作被译介到国内,现代与后现代之争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启蒙与现代性”、“现代性是一项未竞的事业”、“现代性与大屠杀”成为热门话题。值得关注的是,对启蒙与现代性问题的检视与反思逐步成为这一时期的热门话题,受西方反启蒙思想家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的影响,一些学者把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弊端的根源寻溯到启蒙,认为启蒙唤醒的人类理性自觉以及人类对启蒙理想的追求,并不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却导致了当今社会的种种灾难,启蒙走向自己的反面。在这些研究者眼中,启蒙不再是文明的代名词,而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此外,在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之际,关于启蒙的再评价和再反思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在《启蒙的悖论及其出路》一文中,莫伟民等提出,“启蒙在为西方社会带来物质进步和思想进步的同时却又把西方人拉回到了未被启蒙的原始社会,这就是启蒙的悖论”。他分析道,“人类对理性力量的近乎宗教式的盲目崇拜,又使理性变成了彻底的非理性,理性取代了上帝信仰在人心中曾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性从软弱无力的极端走向了无限膨胀的另一个极端。理性变得鲁莽、狡诈、狂暴、血腥、堕落甚至邪恶,理性发生了危机,理性病入膏肓,理性需要诊断、思考、挽救”。例如,“福柯断然拒绝启蒙运动设定的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作出非此即彼选择的‘敲诈’”;“德里达在去世前不久就‘启蒙的过去与未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既要继承和保存欧洲的启蒙遗产,又要充分意识到并悔恨过去的极权主义、种族大屠杀和殖民主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12]。
于奇智分析了从康德到福柯关于“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回答。他提出,“康德解答启蒙运动问题的短文成为18世纪征文中的代表作,它在康德全部著作中也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尽管启蒙运动带来了消极而危险的后果,诸如欺诈、人道主义与启蒙运动的混淆、借启蒙运动之名提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和建立的相关制度等,但福柯并没有全盘否定启蒙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积极性哲学品性——‘关于我们的历史存在的永恒批判’”。“福柯扬弃了康德的启蒙运动观,认为欧洲人远未成熟,也远未摆脱奴役,一个成熟而令人满意的欧洲尚未出现,但是我们能够在这一过程中认识和理解我们自身,反思我们自身的身份”[13]。
谢永康等探讨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中的“启蒙”问题,发现“进入20世纪后,人们普遍认为,启蒙运动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启蒙问题的焦点便逐渐转移到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上”,《启蒙辩证法》将这一残酷现实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在这部书中,他们提供了一种他们认为能够让启蒙去反思自身局限性的批判方式:展现出它是如何与其目的相背离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实现‘启蒙自身的启蒙’”,“‘启蒙自身的启蒙’实际上包含了看似相互矛盾却缺一不可的两重含义:首先,深入地批判启蒙;其次,在深入批判的基础上拯救启蒙”。他认为,“阿多尔诺提出的‘星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来重新考察被认为是已经过时了的形而上学问题,以及这个所谓‘启蒙了的’现代社会。它固然并没有为我们如何拯救启蒙提供具体的指导,但它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反思启蒙的方式,昭示了启蒙的可能走向,也为拘禁于现代统治中的人们提供了解放的希望”[14]。
李慧娟在介绍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基础上,剖析和揭示“启蒙怎样由于自身的发展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更多地关注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达并没有带来他们所预想的人类的大踏步前进,反而给人类的文明生活带来了一系列致命的打击。在人们以为启蒙完成之时,他们指出,启蒙导致的并不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是人类文明的倒退,他们从整个的社会发展出发,在人类进步的大环境下看到了人类退步的因素,并把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了启蒙批判上。”她认为,“启蒙理性本应具有批判性、超越性和形上的维度,但工具理性对于启蒙理性的取代,使启蒙完全丧失了本身所应包含的内容和实质,退化为了‘同一性’的思维”[15]。
百年之后,学界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仍然众说纷纭,这些争论折射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不同文化路向之间的思想分歧,这种情况恰恰说明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远。如何对待传统,如何看待启蒙?新文化运动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仍具有当代价值。新文化运动喊出了反传统、反礼教的口号,打倒“孔家店”,这种主张被一些人冠以“激进主义”而受到批评,甚至有学者提出这是“思想启蒙的光辉篇章,还是错乱妄为的历史灾难”?陈卫平认为,“指出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的片面性有其历史正当性,意在对它的反传统有同情的理解,而决不是要无视这些片面性。只有将肯定其历史正当性和揭示其片面性结合起来,才能作出公允的评价”,“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以科学取代经学,打开了研究传统文化的现代新天地,而并非妖鬼化传统文化。”[16]谢地坤主张,“就是在启蒙运动原发的欧洲诸国,启蒙实际上也从未停止过”,否则,“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就发出的‘启蒙辩证法’,福柯也不会产生‘启蒙’并未让人们成熟起来的遗憾”,“我们要看到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新文化运动的永恒意义:在背负如此沉重传统的中国,启蒙不能有休止符,启蒙将永远进行下去!”[17]。
三、启蒙:不同学科和学派关注的焦点
在新世纪以来关于启蒙研究的热潮中,不仅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且在各学科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团队、形成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等高校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团队,把研究重点集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辩证法”的批判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问题。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是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该学术团队组织出版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译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撰写和发布每年一度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追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动态;编辑学术集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刊载国内外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文;20世纪80年代末编著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是第一部立足外文第一手资料全面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诸流派的著作,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物研究上形成系统性,尤其是俞吾金教授主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研究”对深化启蒙与现代性的探讨具有重要价值。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是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该学术团队组织出版了“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翻译和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献和专著;编辑学术集刊《社会批判理论纪事》,刊载国内外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的论文;在卢卡奇、阿多诺、阿尔都塞、布洛赫、列斐伏尔、鲍德里亚、哈维、普兰查斯、高兹、德勒兹、德里克、拉康、齐泽克、广松涉等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上取得了一批成果,提出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新概念,引起了学界关注。
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以东欧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哲学研究为特色。在该学术团队看来,“文化哲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哲学学科或研究领域,而是内在于众多现代哲学流派和学说之中的哲学主流精神或哲学发展趋势”,他们“明确反对把文化哲学理解为一种具体的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的做法,而主张把文化哲学理解为渗透到众多哲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在近现代哲学演进中,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的历史哲学理论、本尼迪克特等人的文化模式理论、以韦伯和帕森斯等人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理论、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潮、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以德里达和福柯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等等,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自觉或不自觉地逼近和揭示了文化哲学的主题”。该学术团队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解读为“以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深刻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为背景的深刻的文化批判理论”[18]。有学者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进一步上升为一般性的‘法理’,却成为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普适的文化批判理论方法论的基本理论诉求。一定意义上讲,近20年的国内文化哲学研究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伙伴’而同行的”[19]。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方克立的倡导下,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现代新儒家研究,南开大学中国哲学专业还形成特色。其中,新世纪以来,第三代新儒家关于“启蒙反思”、“启蒙心态”等问题的思考,引起中国哲学研究界的关注,杜维明等试图“在肯定启蒙精神积极意义的同时”,正视启蒙精神的“盲点”,在此基础上通过“调动包括非西方文明与原初传统在内的多方资源”,“在对话中超越启蒙心态”,成就“多元现代性”[20]。
在萧萐父的带领下,武汉大学中国哲学专业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研究为特色。新世纪以来,对“早期启蒙说”的探讨重新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界关注的话题。“早期启蒙说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派文化观,是20世纪中国思想家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背景下探寻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及思想资源的产物。近90年来,以梁启超为开端,经过张岱年、范寿康、吕振羽、侯外庐等人的阐发,早期启蒙说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诸多的研究成果”。“从这一文化观出发,早期启蒙说的主张者们对明清之际中国哲学与思想的开展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探讨,使早期启蒙思潮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凸现出来。这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包括对于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研究,都是一个重要的开辟。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一种重要形态”[21]。“中国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哲学’的论述方式,则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积极努力下,通过合理地扬弃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逐步完善的,并逐渐成为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思想界有关明清以降中国社会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论述形式之一”[22]。
在学术会议方面,“启蒙与现代性”也是讨论的重点。“马克思哲学论坛”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联合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点举办的一个年度学术论坛。论坛自创设至今,几乎每一届论坛的主题都成为一个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第四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第十五届论坛主题是“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现代性问题”。其中,启蒙是现代性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考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创新,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和后现代性的各种理论,必须以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现代性思想为指导”[23]。“中美学术高层论坛”是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维思里安大学联合举办的小规模、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举行一届,在中国和美国轮流举办,第二届主题为“比较视阈下的启蒙”,第三届主题为“现代化:中西比较的视野”。其中,启蒙与现代性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与会学者看来,“今天我们讨论启蒙,并不是要否定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而是要在当今世界,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站在人类文明和世界发展的制高点,对启蒙本身进行历史性的、批判性的反思,对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进行重新审视和清理,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总结和归纳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成果,在对话中求同存异,在互惠中取长补短,最终建构起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合乎人类发展趋势的现代思想体系”,“启蒙运动提倡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抽象原则,必须结合每个国家的特殊国情,才能生发出适合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不能穷尽现代性的所有方案,不能代替非西方世界对自身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而非西方世界结合本土文化资源所进行的现代转型,又在不断丰富着现代性的内涵。面对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不同文明之间没有优劣高下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潜藏着孕育现代性的文化因子”[24]。
四、启蒙意味着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复杂性理解
总之,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启蒙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一幅纷繁复杂的理论图景。虽说学者们观点各异,但都承认启蒙以来的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所具有的某种复杂性。在笔者看来,启蒙意味着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复杂性理解。
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刘小枫试图界定现代性的含义:“一种普世性的转换每一个体、每一民族、每种传统社会制度和理念形态之处身位置的现实性(社会化的和知识化的)力量,导致个体和社会的生活形态及品质发生持续性的不稳定的转变。”[25]这种界定揭示出现代社会相对于前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某种复杂性。根据韦伯的看法,现代社会的生成过程就是形式合理性的逐步扩展,实质合理性的日趋减缩,不仅现代性经济活动是一种精确的计算行为,社会劳动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官僚制、甚至思想文化领域的价值中立和意义丧失都是合理化的结果,“再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26]29。哈贝马斯描述合理化在现代社会生成过程中的作用:“韦伯使用‘合理性’或‘理性’这个概念是为了规定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形式,即资产阶级的私法所允许的交往形式和官僚统治形式。合理化或理性化的含义首先是指服从于合理决断标准的那些社会领域的扩大。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劳动的工业化,其结果是工具活动(劳动)的标准也渗透到生活的其他领域(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交通和交往的技术化)”[27]。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矛盾构成韦伯用以分析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架构。韦伯认为,西方现代性的兴起过程就是合理化的产物,表现为形式合理性在人的观念和行为中的体现与发展,同时也表现为形式合理性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其结果最终体现为世界“除魅”的过程,“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26]48。韦伯用“除魅”来描述启蒙以降的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过程。从本质上讲,“除魅”的过程就意味着启蒙。
在笔者看来,并不是由启蒙造成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而是启蒙改变社会理论家对社会生活的基本看法,带来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复杂性理解。社会生活是一种客观存在,并非由于启蒙而发生变化;作为思想观念的启蒙,却是对社会生活变迁的一种反映。思想家的遗产往往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所处时代问题的“诊断”。对于现代社会,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社会理论家的“诊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抑或是涂尔干的思想,都涉及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复杂性理解,也即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双重考量,而绝非是单一因素的考察。他们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认定,都是出于对现代性诸因素总体性的考量,这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统一,这在韦伯那里表现为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的统一,这在涂尔干那里表现为制度论与观念论的统一[28]。这种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决定了经典社会理论家对现代性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的考量,决非是一种经济决定论、或是文化决定论所能概括的,他们在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时却力求实现一种总体性的把握,兼顾到这一问题的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并在这种总体性的关照下来揭示现代社会的存在基础。然而,这种对现代社会的总体性考察,并不能消弥思想家之间的理论分歧,现代社会的存在基础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仍具有不同的含义,他们研究路径的分化,源于对现代社会生活中诸要素之不同地位的认定。
回顾和反思1949年以来我国启蒙问题研究,本身也同样是一个启蒙的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成为这一过程最重要的催化剂。新世纪以来,启蒙问题研究不仅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诸领域和学术研究的各学科,而且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维度,在学术研究逐步走向成熟的同时,充分体现出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复杂性理解的意蕴,在认识论上重演了启蒙的过程。
[1]张光芒,童娣.论新世纪的启蒙话语及其思想谱系[J].探索与争鸣,2009,(4).
[2]叶秀山.康德之“启蒙”观念及其批判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4,(5).
[3]韩水法.启蒙的第三要义:《判断力批判》中的启蒙思想[J].中国社会科学,2014,(2).
[4]周晓亮.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中华文化[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1).
[5]张慎.德国启蒙运动和启蒙哲学的再审视[J].浙江学刊,2004,(7).
[6]赵林.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与德国启蒙运动[J].同济大学学报,2005,(1).
[7]尚新建.启蒙与人性[J].云南大学学报,2005,(1).
[8]卢钟峰.由传统走向启蒙——论18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J].哲学研究,2002,(1).
[9]姜义华.人的尊严:启蒙运动的重新定位——世界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变迁[J].复旦学报,2003,(5).
[10]马德普.论启蒙及其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命运[J].中国社会科学,2014,(2).
[11]丁耘.启蒙视阈下中西“理性”观之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2014,(2).
[12]莫伟民,汪炜.启蒙的悖论及其出路[J].求是学刊,2009,(4).
[13]于奇智.从康德问题到福柯问题的变迁——以启蒙运动和人文科学考古学为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1,(5).
[14]谢永康,侯振武.实现启蒙自身的启蒙——形而上学批判视域下的启蒙辩证法[J].云南大学学报,2010,(5).
[15]李慧娟.启蒙的界限——兼及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J].社会科学战线,2010,(9).
[16]陈卫平.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之辨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5,(11).
[17]谢地坤.永恒的“五四”:启蒙与思想解放[J].中国社会科学,2015,(11).
[18]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简介[J].求是学刊,2003,(1).
[19]陈树林.当下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困境[J].思想战线,2010,(2).
[20]李翔海.杜维明“启蒙反思论”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5).
[21]李维武.早期启蒙说的历史演变与萧萐父老师的思想贡献[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1).
[22]吴根友.萧萐父的“早期启蒙学说”及其当代意义[J].哲学研究,2010,(6).
[23]王海锋.现代性问题的中国阐释[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0-29.
[24]褚国飞.启蒙与梦想——第二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侧记[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6-05.
[25]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2.
[26]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27]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38.
[28]郑飞.从经典社会理论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J].学习与探索,2012,(2).
Enlightenment:A Complex Comprehension of the Social Life—Review of the Domestic Scholars'Research 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Modernity Since the New Century
ZHENG Fei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ress,Beijing 100026,China)
Since the new century,the study 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modernity became the focus of domestic scholars.During this period,the academia discussions on enlightenment was deepening day by day and extended from the ideological field to all areas of social life.In the opinion of scholars,enlightenment not only means the change of the way of individual cognition,but also means social lifestyle changes.It is noteworthy that,the inspection and reflection of enlightenment and modernity gradually become a hot topic during this period.Some academicians consider enlightenment as the basic reason of the various social ill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Although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views,they all admitted modern society relative to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has a certain complexity.In a sense,enlightenment implies the complex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life.
Marx;enlightenment;modernity;complexity
B506
A
1009-1971(2016)05-0067-07
[责任编辑:郑红翠]
2016-07-03
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马克思与韦伯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重点课题“1949年以来我国启蒙问题研究专题论文集”
郑飞(1982—),男,河南平顶山人,副编审,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发展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