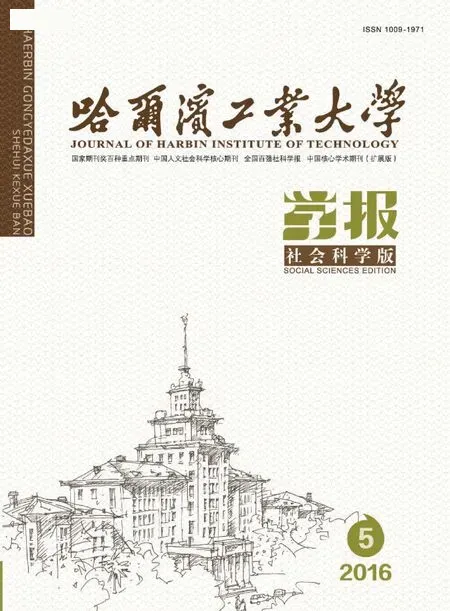《国家赔偿法》死亡赔偿金条款的合宪性分析
柳建龙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北京100089)
《国家赔偿法》死亡赔偿金条款的合宪性分析
柳建龙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北京100089)
《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对死亡赔偿金作了规定。通说认为,较民法之人身损害赔偿,其更合乎平等原则的规定和精神,可更有效地保障公民生命安全、促进依法行政;在个人生命权受到侵害的情形下,可以给予其亲属或者被扶养人更充分、有效的救济。经由文义解释可发现,系争规定纵向和横向上均有违反平等原则的嫌疑,且在比例原则之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四阶审查下,虽经受住目的正当性原则和适当性原则的审查,但未必能经受住实效性原则和均衡性原则的审查,应予违宪无效。
生命权;死亡赔偿金;平等原则;比例原则;禁止保护不足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个人不仅需要国家提供保障以对抗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及来自第三人和外国的各种威胁,也需要它提供保障以对抗来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本身的侵害[1]。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之下,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个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一般情形下,个人可经由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甚至信访等途径寻求救济(一次救济);因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人身、财产及精神等权利而遭受损失的,还可依照法律取得国家赔偿(二次救济)。①《宪法》(1982)第41条第2款、第3款。为履行上述保护义务,宪法将保护种类及范围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予以具体化。为此,它们先后通过了《民法通则》(1986)②《民法通则》第121条。、《行政诉讼法》(1989)③《行政诉讼法》第9章。不过,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业已删除有关国家赔偿的规定。、《国家赔偿法》(1995)、《行政处罚法》(1996)④《行政处罚法》第6条、第59条及第60条。、《行政监察法》(2010)⑤《行政监察法》第49条。、《行政强制法》(2011)⑥《行政强制法》第8条、第26条、第41条及第68条。等一般或者特别规定。其中1995年施行、并经2010年和2012年两次修改的《国家赔偿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生命权保障人的肉体存在,即生理和物理意义上人的存在。尽管宪法对生命权并未予以明文规定,然而作为其他权利存在和实现的前提条件,生命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有的学者所正确指出的:它是人类的最高权利,其他一切权利随它而生;是其他权利的基础,是人权不可克减的核心之一[2][3]。为保障公民人身和生命安全,《国家赔偿法》(2012年修订)第34条第1款第3项第1句①即《国家赔偿法》(1995)第27条第1款第3项第1句。(下文也称之为“死亡赔偿金条款”)对侵害生命权的赔偿标准②这一表述并不妥当,详见下文。作了规定:“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然而,就其理解而言,多数论著只是照搬法条,究其原因,或认为其字面含义甚为明白,无进一步解释的必要[4];有的虽然作了解释,但也只是将其重新表述为“在侵害公民生命权的情形下,国家赔偿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在内”[5]326[6]而已。③林鸿潮、赵鹏于《国家赔偿法司考读本》中认为二者总额不得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这与立法原意相违背。胡康生同志1993年10月22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所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的说明》明确指出:“有关部门建议对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残疾、死亡的,规定最高赔偿金额,考虑到最高赔偿金额暂时难以确定,拟进一步研究后另行规定。”换而言之,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第1句所确定并非国家赔偿的上限。其次,不符合现行法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7条、国家赔偿法第37条的规定,国家赔偿诉讼可以进行调解。这意味着,国家赔偿的标准和总额可以协商,而协商后所采的赔偿标准既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国家赔偿法所确定的一般标准。——不过,我认为,应当认为国家赔偿法所提供的是基本保护,即其所确定的为最低标准。为此,在调解的情形下,最后所确定的赔偿标准不应低于法定标准。——在双方无意进行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的情形下,则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应采用法定标准,即在此种情形下,若法院认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则其国家赔偿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二十倍,既不得高于也不得低于这一标准。不过,有疑问的是,在国家赔偿义务机关以高于法定赔偿标准诱使受害人的近亲属进行调解,但未能达成协议又继续诉讼的情形下,法院是否应依法定标准确定国家赔偿的金额,抑或是以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最初所建议的较高标准或者是调解过程中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所提出的最高标准确定国家赔偿的金额?从当下的资料来看,似无讨论;但此又非不可想象之事。那么在此种情形下,当事人能否主张信赖利益保护呢?个人以为,未来对于该问题进行探讨极有必要,因为其或能在一定程度防止赔偿义务机关以调解为借口,从而利用调解的时间联合法院对当事人施压,从而迫使其接受相对不利的条件的情形的出现,更好地保障受害人之继承人和被扶养人的利益。此外,除有关赔偿标准过低、赔偿金性质④就本条规定而言,学术界目前关于国家赔偿法的批评和检讨多集中于前两点。及“上年度”的不明确性[7]24[8][9]的批评和检讨外,一般很少予以展开。但是,其是否“明白”而无探讨的必要,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含义为何,倚赖何种法理,是否真的与存在违反平等原则嫌疑的侵权责任法规定有所不同、更合乎平等原则,是否比国家赔偿法其他规定更为“适当”……窃以为,当下学说对这些问题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故有重新检讨的必要;下文拟重新厘定该规定和死亡赔偿金的含义,证明其不仅违反法制统一性和平等原则,也违反比例原则之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故存在违宪嫌疑,应予以修改。
二、死亡赔偿金条款的含义
国家赔偿法上的死亡赔偿金,系指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行使职权行为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造成受害人死亡的情形下,由国家向受害人相关近亲属支付的赔偿费用。《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对此作了规定。
(一)死亡赔偿金条款的既有解释
依照当下学说和实务对《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的理解及适用情况,可归纳出如下两种见解:
其一,赔偿金总额=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20。绝大多数学者或认为,就其语义而言,第34条第1款第3项表述比较清楚、没有歧义,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造成公民死亡的,国家有义务对受害人的继承人和其他具有扶养关系的亲属给予赔偿。倘不考虑第34条第1款第3项后半段规定的“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的情形,则国家应支付赔偿总额为: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成赔偿决定时的上年度⑤此处采通说,然而关于何为“上年度”存在多种见解,详细讨论可见柳建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身损害国家赔偿计算标准之探讨——“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的“上年度”之意涵》,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24页以下。国家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维持原赔偿决定,则按原赔偿决定作成时的上年度执行。该赔偿金由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两部分组成;不过,与民法上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不同,它不单独赔偿丧葬费[10]。
其二,赔偿金总额=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20+丧葬费。该说认为,“在公民死亡的情况下,国家支付的丧葬费以及死者生前的医疗救治费应分别计算,死亡赔偿金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11][12]145-146
比照当下相关论著和判决,应认为第一种主张为通说,因为绝大多数学说和实务都采取该立场;①就实务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唐德华、黄松有、江必新、梁凤云、王晓滨等法官即持此种观点,也能从法院判决得到佐证,如:“陈为民、林金林申请平潭县公安局行政赔偿案”,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年5月22日行政赔偿判决书;“王会明、张文芳与潜江市公安局”,湖北省汉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汉行终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徐金林、张荷娣、徐治辉与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上海宝山区人民法院(2000)宝行初(赔)字第23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等等。学说上更是如此,可见本文所参引各著作。相对而言,本说则为极少数说,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即本文所援引的其他文献——而言,只有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的李飞、许安标及武增等所主编的释义及解读持此种观点。不过,至于其解释何以与法律的字面含义及通说迥异,他们并未进一步说明其理由,不宜妄加揣测,故此处先不予讨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完善国家赔偿法立法和实务的考虑,本文批评的对象仅限于通说。
(二)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必要性
就《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而言,有不少学者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之和表述为死亡赔偿金[13][12]146[14],这不仅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意旨,也易滋生误解。尽管也有人认为,国家赔偿法未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予以明确规定,仅规定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总额限制[15][5]326,还有待在实践中总结探索,通过制定相应实施细则的办法加以完善[16][17];况且在实践中,和民法上的人身损害赔偿不同,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既无实益,也无必要。
然而,从释义学的立场出发,有进一步明确其第34条第1款第3项规定前半段的内涵,分别厘定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各自在该赔偿金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的必要,因为:
首先,基于民主原则和法治国原则的要求,解释者在解释法律时不能假定法律某些语句或者语词是无意义的;除非法律规范本身要求如此,否则,此类假定是站不住脚的。②比照Marbury v.Madison(1803)。换言之,解释者应当对作为民意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表示充分尊重,除非国家赔偿法明确要求或者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立法者在立法时本身无意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或存在此种意向,否则,不应认为其中任何一条规定的某些语句或者语词本身是无意义或无价值的。就此而言,不能认为立法者意旨仅在规定侵害生命权时国家应支付的赔偿总额,无意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虽然《国家赔偿法》(1995)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1996)、《国家赔偿法》(2010修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011)都未对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概念和内涵做进一步的界定;否则,立法者只需要将其表述为“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赔偿金,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即可。何况从当时的立法材料——《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的说明》——看,立法者并未将所谓的“侵害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总额)”作为一项而予以列举,而是明确指出:“草案根据以上原则,对各种不同损害的赔偿标准和方式,分别作出规定:……对造成残疾、死亡的,还规定支付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向受害人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支付生活救济费。”③胡康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的说明——1993年10月22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即对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进行列举。
何况只要能够籍由相关法律的规定确定其中一项的标准,无论是死亡赔偿金抑或是丧葬费的标准,在国家赔偿总额确定的情形下,都可计算出另一项的标准(额度)。于此,认为前揭见解为我国对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未作规定的基础自然就土崩瓦解了。
其次,尽管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系同一致人死亡的行为导致的法律后果,但在制度设计上,二者各自所欲保护的法益和存立的法理基础迥异。虽然一般认为,无论是在私法意义抑或是公法意义上,作为人的最高利益的生命在侵权行为法上的意义甚小[18]72,因为一个被剥夺了生命的人不会遭受任何损害[18]70,其死亡后果通常是由死者以外的人,如近亲属、生活伴侣、雇佣人或交易伙伴等承担的,故而对他们中哪些人可以就哪些损失主张权利是从他们而非死者角度展开的[18]72。在这一维度下,死亡赔偿金通常被视为一种致人死亡时特有的财产损害赔偿项目,系以造成受害人死亡导致国家赔偿请求权人扶养费来源中断而受有财产损害或者导致可由作为法定继承人的国家赔偿请求权人继承的、受害人的余命收入的逸失为赔偿范围[19]1091-1093。这虽然颇具嘲讽味道,却是包括诸多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所普遍接受的事实[18]70。
相比之下,理论上认为,丧葬费实际不是由侵权行为所生损害,因为被害人将来必有一死,其费用或许也应由其继承人予以承担[20];为此,即便存在所谓损害,充其量也仅相当于比本来死期提早支出的费用的利息损害而已[18]72。不过,即便如此,也有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必要,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更加突出死亡赔偿金的地位以表示对受害人生命的尊重。
最后,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对处理因其分配而产生的争议而言,也具有实务上的价值。虽然通常情形下,基于道德和风俗习惯的自律或者约束,死者近亲属就丧葬费的承担发生异议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例外的情形下仍可能出现争议:一方面,在受害人有多个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的情形下,可能出现,其中一人或者数人垫付丧葬费,但其他人拒绝分担,或者虽然同意分担,却认为开支明显不合理,为此拒绝承担其所认为的不合理的部分;另一方面,在受害人的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以外的第三人垫付丧葬费的情形下,同样也可能出现前述争议。因此,为防止出现不必要的争议,有必要明确丧葬费的标准,以确保实际支付丧葬费者的合法权益,防止受害人的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或者第三人以丧葬费而侵害其他继承人和有扶养关系的亲属的利益。就此而言,《侵权责任法》第18条第2款“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规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在该法施行前,也可以通过《民法通则》第9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①1988年4月2日法(办)发〔1988〕6号。第123条的无因管理而予以解决。于此,在《国家赔偿法》未明确规定上述情形应如何解决的情形下,应有必要类推适用前述民法规定,而这无疑也是以明确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为前提的。
(三)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计算
虽然国家赔偿法对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计算标准未予明确界定,②张红和童航在其合著的文章指出:“《国家赔偿法》确定了丧葬费的计算标准,但是与死亡赔偿金一并计算,未突出丧葬费的独立性,且仅适用于国家赔偿的案件。”这一判断恐与实定法的规定和学界的见解多有龃龉。张红、童航《侵害生命权之丧葬费赔偿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3期第67页。但从现行法的整体秩序出发,或有籍由相关法律的规定予以厘清的可能。在一定意义上,应视国家赔偿法为民法(侵权责任法)特别法[21][22][23],为此,在国家赔偿法未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以相关民事法律规定作为切入点是较为妥当的做法,此一方面和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国家的国家赔偿制度的实务与学说发展轨迹相吻合,另一方面也和我国《民法通则》第121条和此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1991)第114条(已废止)的旨趣相合。③也可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之“一”,法复[1995]1号。
不过,就现行法制而言,虽然民事法律规范也对人身损害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标准做了规定,但其所采标准和国家赔偿法不同:前者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为计算标准,后者虽然未明确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但对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总额的计算标准均采取“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计算标准。就此而言,并不能凭借民法相关规定而直接确定国家赔偿法上死亡赔偿金的额度;但这也并非意味着,民法上的规定对其标准的确定毫无参考价值。易言之,能否确定丧葬费的标准成了能否厘清二者含义的关键:倘若其无法确定,则亦无法确定死亡赔偿金的含义;反之,则可确定死亡赔偿金的含义。
就丧葬费而言,学说上一般认为存在如下几种赔偿方法:定额赔偿,即按地方制定统一的赔偿数额予以赔偿;弹性赔偿,即按地方制定赔偿费用的额度,由法官选择确定赔偿数额;实际赔偿,即按实际支出的费用赔偿,但对支出的标准有限制[24][25]。与之相一致,在立法和人身损害赔偿实务中丧葬费标准亦呈现出一种诸法并存的混乱局面,直至《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施行才得以统一为: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其中“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系指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受诉法院所在地的上一年度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职工月平均工资[26][27]344。丧葬费标准不因受害人的职业、身份、工作、性别、年龄等情况有所不同,也不因受害人生活在城镇还是农村而有所不同[27]345。
相应地,伴随着《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丧葬费标准的统一,经由丧葬费而进一步确定国家赔偿法上的死亡赔偿金不仅是可能而且是确定的,其计算公式为:死亡赔偿金=(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0)-(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职工月平均工资×6)。
三、死亡赔偿金条款违反平等原则
合并《宪法》第41条第3款和第33条第2款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宪法保障所有公民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并规定国家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对于任何公民的保护或者惩罚都应当是平等的,不应因人而异。就此而言,一般认为,国家赔偿法上的死亡赔偿金与《侵权责任法》①学者多数认为《侵权责任法》第17条所以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是考虑到此前人身损害赔偿由于考虑年龄、户籍等不合理因素而有违反平等原则和人格尊严,以致有违宪的嫌疑;相较之下,第17条更能体现人格平等的精神。(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立法最新讨论的50个问题》,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12期,第5页)这显然忽略了一个问题,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看,第17条本身并非无争议的,因为就其文本而言,其使用的是“可以”而非“应当”,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授权性规定,即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也可以以不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另外,其显然也不能排除不同个案中以年龄和户籍等为依据而确定不同数额赔偿金的可能性;更何况在残疾赔偿金问题上,《侵权责任法》仍沿用之前的做法。就此而言,上述批评仍不能得以消解。及其施行前的《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9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中所隐含的(城乡)身份和地区差别从而导致“同命不同价”②关于“同命不同价”的学理争论,可见高圣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立法争点、立法例及经典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231页。有所不同,其计算必须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职工平均工资”为准,而不能以当地的经济生活发展水平下的地方统计数字为准,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死亡赔偿金不至于因为“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不同的行业岗位之间收入差别也大……”而在“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样的损害在不同地区得到不同数额的赔偿,这对受害人来说有欠公平”[28][29]103[30]442。而第34条第1款第3项所采用的是相对统一和固定的赔偿标准,并不因为受害人的职业、收入、年龄、地域、身份等因素而有差别[31]。这更能体现宪法和法律平等的保护精神[32][29]103[30]442、更合乎人格尊严的要求,具有“平等的导向性和进步性”[33]258。
然而,《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是否更符合平等原则呢?仔细审视,则可以发现,上述主张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死亡赔偿金条款不仅可能导致纵向的不平等,也可能导致横向的不平等。
(一)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在回答前述问题之前,必须明确人身损害赔偿的性质。就此而言,民法学中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扶养丧失说、继承丧失说、所得丧失说、劳动能力丧失说、③大陆学者似乎较少注意到劳动能力丧失说,可参见陈聪富“人身侵害之损害概念”、“劳动能力丧失与慰抚金的调整补充机能”,载陈聪富《侵权违法性与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125页以下及179页以下。精神抚慰金说、生活来源丧失说,此外,也有少数人主张应改采“物质生活水平维持”说[34]211;而专就死亡赔偿金而言,在学说及司法实务中居于通说地位的是扶养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也有部分学者主张精神抚慰金说[34]216-217。由于现行法规定与各学说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龃龉之处,为此有不少批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④法发(2010)23号。之“四”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8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易言之,侵权人如果承担了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则不再承担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消除这一乱象。不过,尽管同此前的《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8条相比,排除扶养费请求权虽然能够使得人身损害赔偿规定在法理上更为自洽,但它同时也缩小了人身损害赔偿范围,使得赔偿金总额大幅缩减,故颇受诟病。国家赔偿法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脱胎于民法,自然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就死亡赔偿金而言,国家赔偿法上也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扶养丧失说、继承丧失说以及精神抚慰金说。一般认为,居于通说地位的是继承丧失说。不过,2010年修法以前,也有学者对继承丧失说提出批评,认为,由于旧法第27条第1款第3项后半段对扶养费已有专门规定,并且采全国统一标准,不考虑受害人年龄、收入的地区和城乡差异,故而不同于继承丧失说,其在性质上为精神抚慰金。然而,2010年修法后,新法第35条后半段对精神损害赔偿特别作了规定,于此,动摇了上述批评的基础,故应以继承丧失说为宜。
(二)纵向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
在上述观念基础上,首先需要检讨的是作为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的“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上年度”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问题。
明确性要求是合法性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35],然而,第34条第1款第3项规定难谓符合该要求:其中“上年度”的意思究竟为何,在实务和理论上均存在较大的分歧,①详细讨论可见柳建龙,前引文;汪本雄、金俊银《赵仕英等诉秭归县公安局行政赔偿案》,李友信、金俊银《李伟珍诉钦州市公安局以殴打暴力行为致其子梁永成死亡请求行政赔偿案》,载祝铭山《行政赔偿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83,1-98页。形成了多种见解,如违法行为时上年度说、违法行为结束时上年度说、危害结果发生时上年度说以及赔偿决定作成时上年度说等[7]24。后经由两次司法解释才使得其含义得以进一步厘清:
一是199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其“六”第1款将“上年度”确定为: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决定时的上年度;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维持原赔偿决定的,按作出原赔偿决定时的上年度执行。
二是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作成的《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规定纠正原生效的赔偿委员会决定应如何适用人身自由赔偿标准问题的批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年度”的不明确性导致的分歧,如果将其“六”第1款后半句纳入考量,可以发现其并未明确:在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改变原赔偿决定的情形下是否应当采取变更决定作成时的上年度作为确定“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标准时间,是否应按变更决定是基于形式性或者实质性的原因作成的予以区别对待?[7]33本解释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指出:在此种情形下,原决定的错误系漏算部分侵犯人身自由天数的,应在维持原决定支付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的同时,就漏算天数按照重新审查或者直接审查后作出决定时的上年度国家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相应的人身自由赔偿金;原决定的错误系未支持人身自由赔偿请求的,按照重新审查或者直接审查后作出决定时的上年度国家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人身自由赔偿金。尽管此处仅提及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但似乎也可以类推适用于其他的纠正原生效的赔偿决定的情形,如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纠正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决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纠正复议机关的赔偿决定的情形。
然而,即便搁置最高法院对第34条第1款第3项的解释或者虚造本身可能引发的解释权限争议问题,也不意味着业已排除其可能存在的违宪嫌疑,这是因为:根据该条规定,赔偿标准和赔偿总额的确定可能因赔偿请求提出时间和赔偿决定作成时间不同而有差异。即,可能出现如下情形:在同一时间发生两起以上性质和结果皆相同案件,虽然同时提出赔偿请求,但由于有权机关作成的赔偿决定的时间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别,赔偿总额的差额可能高达数万甚至数十万,尤其是在各该赔偿作成时的“国家职工上年度平均工资”存在较大幅度增长或者下滑的情形更是如此[7]32。此种差别难谓合理。
另就法释(2014)7号所及的情形而言,即便是同一个案件在不时期也可发生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不同的问题。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规定纠正原生效的赔偿委员会决定应如何适用人身自由赔偿标准问题的批复》法释(2014)7号;关于此种处置措施,柳建龙前引文有所批评。就此而言,其和前段所及情形恐怕都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存在龃龉,并且也使得赔偿金总额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
(三)横向不平等与内在不统一性
正如此前所指出的,如果采取通行做法,不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将之视为一个整体,则较之民法上死亡赔偿金的规定而言,国家赔偿法的死亡赔偿金条款较合乎平等原则的规定,不会造成横向的差异——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然而,如果和民事法律规范一样将丧葬费排除在外,单独计算死亡赔偿金,则可以发现,《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不仅存在横向不平等的疑问,而且背离了死亡赔偿金的设计理念,特别是,一旦将之与国家赔偿法关于限制人身自由和侵害健康权的赔偿规定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国家赔偿法在制度设计上未能做到体系的自洽,从而存在内在不统一性。这是因为,正如此前所指出的,死亡赔偿金金额的确定只能经由扣减丧葬费而予以计算;而丧葬费金额应依2003年《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7条规定予以确定。
根据该规定,丧葬费的计算系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水平为基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发达水平,与之成正比。这一标准“既考虑到了地域差异,又兼顾了公平,是一种比较科学、合理的标准,还简单易行、标准明确、便于掌握”[19]1090[36]。而丧葬费一旦确定,则死亡赔偿金的金额和数额也随之确定。就此而言,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总额确定的情形下,在那些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较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通常为经济发达地区),国家赔偿中的死亡赔偿金水平要比那些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较低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区域内(通常为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死亡赔偿金要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这无疑与继承丧失说的基本立场不一致,因为:依照该说,死亡赔偿金就其性质而言为受害人余命年岁收入的逸失,与个人潜在收入成正比。换言之,即便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一样,退让以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死亡赔偿金的金额也应与受害人所属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成正比,而非成反比。就此而言,此种差别对待显然并无合理的根据,故其不仅违反平等原则,也违反法的统一性原则。
(四)小结
基于以上理由,可以发现系争第34条第1款第3项不仅因“上年度”一词含义不明确而存在违反法之明确性原则的要求,即便经由司法解释予以限定,其仍可能导致横向与纵向的不平等,并且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存在龃龉。为此,应认为其构成违宪。
四、死亡赔偿金条款违反比例原则
尊重和保障人权、尤其是生命权,是国家的基本义务。于此正如德国学者施密特-阿斯曼(Schmidt-Assmann)教授所说,国家行为具有“法治国双重委托”的特性:一方面,国家行为具有规制性,亦即国家负有不逾越法律的界限侵害公民生命权的消极义务;另一方面,其也具有积极性,即国家为实践个人权利而生的行为义务[37]18。而就立法者对生命权的保障的积极面而言,“立法机关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应建立在谨慎的事实调查和合理的评估基础上,并应当能够达成适当和有效的保障”。①BverfGE 88,203(254).至于《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能否适当和有效地保障公民的生命权或者填补其继承人或者其他扶养关系的亲属因其死亡而遭受的损失,应置于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框架下进行审查。
(一)保护不足禁止原则
对作为防卫权之基本权而言,禁止保护不足原则(Untermaßverbot)与禁止过度侵害原则(Übermaßverbot)密切相关[38]557。二者共同构成了德国法上比例原则的内容。其中,禁止过度侵害原则要求公权力干预个人自由权利不能过度,是上限,而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却是要求国家满足其保护义务的下限[39],即要求国家的保护措施应当有效,能够实现法律所要追求的目的,并合乎均衡性原则[40]。就国家采取的针对基本权侵害者的保护性干预(Schutzeingriff)而言,该原则要求应确保作为基本权之防卫功能的实现并满足受害人的保障需求,并给予其以最大程度的赔偿[38]557。
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是在基本权保护义务释义学这一法学上的“大发现”或者“大惊愕”[41]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贡纳尔·福尔克·舒佩特教授(Gunnar Folke Schuppert)。他在1980年德意志国家法学者联合会上所作的《宪法解释的功能-法律上界限》(Funktionell-rechtliche Grenzen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该概念[42]513[1]。之后由克劳斯-威廉·卡纳里斯(Claus-Wilhelm Canaris)、福尔克马尔·格尔茨教授(Volkmar Götz)以及约瑟夫·伊森泽教授(JosefIsensee)在学说上予以进一步阐发[42]961[43]。其中贡献较大的是卡纳里斯教授,1984年,他在私法学联合会(亚琛)上所作的题为《基本权与私法》②AcP 184(1984)202.对该原则进行了诠释[44],将之作为处理宪法与私法关系这一“百年问题(Jahrhundertproblematik)”(费策语)[45]的标准。之后,联邦宪法法院在堕胎第二案(Schwangerschaftsabbruch II)③BVerfGE 88,203.中首次采用了这一学说[42]513。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和基本权保护义务一样,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提出最初也是为解决民事争议[46],经过之后的理论发展也及于公法争议[47]764(765)[48]。其意义在于,它使得保护义务不至于流为“口号”,即借其控制规范的特性对宪法所要求的最低保障作了规定,限缩了立法的空间[49]。
就审查模式而言,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是对禁止过度侵害原则的审查模式适当调整发展而来的[50],不过,它是一个独立的审查标准,不是禁止过度侵害原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51]309。一般而言,禁止过度侵害原则的审查模式通常包括四个阶层:目的正当性原则、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均衡性原则;与此相似,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则包括以下四个阶层:目的正当性原则、适当性原则、实效性原则以及均衡性原则[52]11。下文将试着援引该原则检讨《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关于死亡赔偿金规定的合比例性问题。
(二)目的正当性原则
目的正当性原则,它要求系争规范之保护给付的目的在宪法上应当是正当的[51]310。在该阶层审查中,首先必须确定系争规范之保护给付所欲追求的目的,而后方能进一步审视该目的在宪法上是否具有正当性;其次,就目的是否正当的判断而言,禁止过度侵害原则与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不同。禁止过度侵害原则要求,法律所追求的目的应非宪法和法律明文禁止的,而禁止保护不足原则要求,所主张目的应是基本权所追求的。
就侵权法上的赔偿而言,一般系以赔偿受害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为重要目标,但是,显然这并非赔偿的唯一目标,事后赔偿的目标通常还与抑制不法行为的目标相关[53]。国家赔偿的目标也是如此。按照《国家赔偿法》第1条所明确宣告的目的,设定国家赔偿范围与标准应当服务于如下目的:一是保障公民生命权免受公权力侵害;二是在其受到损害时,给予适当的救济;三是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所设置的死亡赔偿金也服务于上述三个目的,一方面,作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害公民生命权国家所应支付的侵权成本,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阻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促进依法行政、保障个人的生命权免受侵害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公民生命权受到侵害的情形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受害人的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因此而遭受的损失,从而恢复法秩序的“和平”。于此可以认为它是《宪法》第33条第3款、第37条及第41条第3款的具体化,与宪法并无龃龉,故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
(三)适当性原则
适当性原则,又称妥当性原则、适合性原则或者合目的性原则。它要求国家为履行其保护义务而采取的措施应具有适当性,即,其至少应有可能促进基本权保护给付所欲追求的目的的达成[51]310。在对称的思考模式下,宜应考量国家保护措施作为对加害人的基本权干预行为,是否足以达到排除加害人行为的目的。申言之,保护措施可以排除加害人对被害人的干预行为时,方有保护受害人基本权利权益的可能[37]30。在实务中,就该阶层的审查而言,只要保护目的达成存在抽象的可能性就足矣,因为国家不仅无法确保在所有的个案中上述目标究竟能否实现[51]310,亦无法确保其实现的程度,即究竟是全部实现抑或是部分实现;一般而言,除非国家完全不作为,否则,则应认为立法机关采取的措施符合适当性原则的要求[54]。
就《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规定而言,其所设定的死亡赔偿金标准应有助于前述保障公民生命权免受公权力侵害;在公民的生命权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权行为的侵害时,它应能予受害人近亲属以适当的救济以及敦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下面逐项展开讨论:
首先,正如此前所指出的,死亡赔偿金的设置本身是具有抑制性目标和威慑作用的,尤其是合并《国家赔偿法》第31条对于追偿、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的规定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其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而这能够促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从而防止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和权利的结果的发生,也就能够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
其次,虽然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存在理论上的争论,但就其实质效果而言,死亡赔偿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受害人的死亡给其近亲属带来的经济损失,并且死亡赔偿金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抚慰功能,从而为受害人近亲属因此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提供一定的救济。
最后,死亡赔偿金除具有前述的威慑效果外,作为对被害人的“第二次救济”,它其实也表达了立法机关、行政复议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造成受害人死亡的职权行为的合法性的否定性评价,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促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依法行政。
综上,死亡赔偿金的设置有助于前述国家赔偿法立法目的的实现,故合乎适当性原则的要求。
(四)实效性原则
和禁止过度侵害原则一样,就禁止保护不足原则而言,在对适当性进行审查后也须对多个可供选择的选项进行权衡。不过,不同的是,在这里实效性原则(Effektivitaet)取代了必要性原则(Erforderlichkeit)[55]。所谓实效性原则,也称为最小保护原则(Schutzminimums)或者必要保护原则(Schutzerforderlichkeit)。实效性原则要求所采取的高权措施必须能够提供充分的保护[51]310。尽管一般认为,立法者在履行宪法赋予的职权时往往享有形成余地(Gestaltungsspielraum),可以依其意愿而在多个可供选择的选项中间进行选择,不过,由于负有保护特定法益的宪法义务,为此,在进行选择时立法者并非完全不受拘束,即其选择的措施必须能够实现有效保障[56]。有的学者由此作进一步延伸,认为根据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要求,如果存在着其他可用、更好或者更有效的保护措施,但却是一个(对相对人、第三人甚或公共利益的干预)“强度同样小”的手段,国家不采行该手段即构成违反比例原则[52]11。不过,该观点无疑将禁止过度侵害原则植入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中,这已然超越了后者的考察范围;一般认为,此处仅须考虑能否有效实现保护目的就足矣[47]764(765)。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作为控制标准,较禁止过度侵害原则,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关注点不是“如何(wie)”实现保护任务,而是保障任务在于是否实现及其实现的程度[57]。
就国家赔偿设置的实效性审查而言,可以援引法经济学理论予以探讨,从而将国家赔偿视为侵害公民基本权利而应支付的对价。则一般情形下,基本权受保护之效果和被害人或者其家属获得救济的程度与国家赔偿的金额和标准的高低成正比,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与之成反比。易言之,可能受侵害的法益价值越高、受侵害的程度和可能性越高,则国家赔偿标准和金额应越高。唯有如此,方能确实有效地实现法律保障个人生命权、对受害人或者其家属的救济以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目的。而就个人权利侵害而言,致人死亡无疑是最为严重的情形[58][59],与之相应,其赔偿标准和金额理应最高,唯有如此方能契合事理。那么,国家赔偿法上死亡赔偿金的设置是否符合上述原理呢?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检讨:
第一,系争死亡赔偿金规定能否发挥足够的威慑力,从而为生命权保障提供有效支持呢?对该问题可以作如下解答:首先,且不论法经济学理论如何,抽象而言,人身损害国家赔偿标准的设置一直以来就颇受诟病:人们普遍认为,赔偿标准过低,使生命权不仅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受到漠视,难以发挥国家赔偿法的威慑作用,也妨碍了其保障公民生命权受到侵害的立法目的的有效实现;而最近几年见诸报端的一些侵犯公民个人生命安全的例子,尤其是一些国家机关就公民非正常死亡所作的荒诞解释和说明,如洗澡死、洗脸死、躲猫猫死、喝水死、噩梦死,或多或少也能说明一点问题;其次,比较第34条1款第3项和第2项,可以发现,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负全责的情形下,造成公民死亡的,应支付的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之和与造成公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应支付的残疾赔偿金相当,易言之,死亡赔偿金低于残疾赔偿金。在这种情形下,不免引发如下担忧:基于赔偿金额多寡的考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更可能“两害相较取其轻”,进而铤而走险,致人死地。尽管这在国家赔偿实务上并无可为凭证的统计数据,不过,就一般生活经验而言,这种担忧并非毫无理由:由于死亡赔偿金标准过低,在相当一部分司机中流传着一种观念——“撞伤不如撞死”,以致在一些交通伤害事故中,肇事者为了避免致残后可能遭遇的巨额医疗费用和残疾赔偿金请求,在发生交通事故可能造成受害人严重伤残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期待或积极地实施可能致其死亡的行为[60][61][62]。近些年屡屡发生的“✕✕药家鑫”案等案件就是例证。——尽管严格而论,这种观念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此类行为可能引起的其他法律后果,不过,在表面上,它至少印证了法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正是基于此,有的人才呼吁提高人身损害的民事赔偿标准。就此而言,即便我们无法证明在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但在普遍认为死亡赔偿标准过低,以致难以有效实现其立法目的的情形下,适当提高死亡赔偿金的水平,无疑是必要的。
第二,系争死亡赔偿金规定能否有效填补受害人的近亲属遭受的损失?对这一问题,可回答如下:首先,正如此前所指出的,人们普遍承认,死亡赔偿金现有标准过低,应予提高[63][64][65],这应能反证,死亡赔偿金并不能有效填补受害人的近亲属因受害人死亡遭受的损失;其次,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时至今日国家赔偿法虽然已经作两次修改,但是在赔偿范围和标准上并无多少实质性变化。1993年起草国家赔偿法时,考虑到在当时我国同时爆发了外汇赤字、财政赤字和金融赤字三大赤字,有必要确保国家赔偿之支付能力与“国家的经济和财力能够负担的状况”相适应,①胡康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的说明——1993年10月22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故而依据抚慰性原则设置了较低的赔偿标准。虽然其后我国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保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对之并未作必要调整。在这种情形下,应难谓现有死亡赔偿金标准能够有效填补受害人近亲属遭受的损失。
第三,系争死亡赔偿金规定能否有效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从而促进依法行政?这一点应无须过多赘述,因为既然死亡赔偿金现有标准过低,难以发挥其威慑力,当然也难以有效地实现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从而促进依法行政的目的。
基于以上理由,恐怕难谓第34条第1款第3项能够经受住实效性原则审查。而生命权在宪法的价值体系中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毕竟,倘若连生命权得不到保障或者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则其他基本权利乃至整个立宪主义制度都将成为一纸空文[66]。
(五)均衡性原则
即便认为上述关于实效性的分析不具足够说服力,而退一步承认,系争第34条第1款第3项可以经受住前述各阶层的审查,也并非意味着系争条款就是合宪的,其仍应进一步接受均衡性原则的审查。所谓均衡性原则,又称相称性原则或者狭义之比例原则(Proportionalität);要求国家所采取的保护措施跟所要保护的法益和可能发生的危险的现实性和程度相适应[51]310。那么,《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规定是否符合该原则呢?
判断生命权是否得到了与其宪法上之地位和重要性相适应的尊重和保障,可适用“越如何则越如何公式”(“Je-desto-Formel”),即可能受到威胁的基本权价值越高或者受到损害的可能性越高或者越严重,则国家之保护义务的负担越重。简而言之,生命权作为最重要的法益应当得到比其他基本权更高的尊重和保障,而就国家赔偿的立法而言,则意味着,应为生命权侵害设定一个较之其他权利侵害更高的赔偿标准。然而,比较《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和第2款所确立的赔偿标准而言,无疑可能出现死亡赔偿金有可能比残疾赔偿金低的情形,于此显然不能认为,生命或者生命权得到了与其宪法上的地位和重要性相适应的尊重和保护。更何况,就其学说基础而言,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和金额至少也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赔偿金的标准和金额相当,即都应是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20倍,因为二者都是以受害人全部未来收入的损失为赔偿范围的[29]105[33]264。为此,难谓《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所设置赔偿标准与生命权在宪法上之地位和价值相适应并符合均衡性原则的要求。
(六)小结
综上,死亡赔偿金的设计未能满足比例原则之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要求,虽然其目的旨在保障公民生命权免受公权力侵害,并在其受到损害时,给予适当的救济以及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而且事实上也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达成,但由于其赔偿标准显然低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情形下的残疾赔偿金,而且本身赔偿标准也过低,为此,并不能有效地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在公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侵害时,也不能给其近亲属以充分的救济,并且由于赔偿标准过低,也可能导致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漠视公民生命而违法使用或者滥用职权。故而难谓其合乎比例原则之禁止保护之不足原则的要求。
结 语
综上所述,就通说而言,《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无疑违反平等原则和比例原则,从而违反《宪法》第33条第2款和第3款、第37条第1款的规定,有进一步检讨或修正的必要。不过,于此也可能存在一种主张,即可以对《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作合宪性解释,即将之置于前述宪法各项规定的框架内予以解释,从而达致一个符合宪法的解释。换言之,无须修改《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只要转而采行前述全国人大李飞、许安标及武增等人所主张的少数说,前文各种指摘或许可以迎刃而解。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合宪性解释并非不受限制:一方面,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就文义解释而言,该少数说无疑超越了文字的理解可能,对系争规定作语义解释显然并不能得出与少数说相一致的结论;另一方面,只要系争法律规范语义明确并明显抵触宪法,则解释者不能背离其语义而强行对之作合宪性解释,否则,就有僭越立法权的嫌疑。尽管采少数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系争规定之违反平等原则的横向不平等问题和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问题,不过,即便如此,仍存在违反纵向不平等的问题。就此而言,无疑也应认为《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违宪有进一步修改的必要。
[1]KLEIN Oliver.Das Untermaßverbot-Über die Justiziabilität grundrechtlicher Schutzpflichterfüllung[J].JuS,2006:960.
[2]JAYAWICKRAMA Nihal.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Human Rights Law:National,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Jurisprudenc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243.
[3]上官丕亮.论宪法上的生命权[J].当代法学,2007,(1):61.
[4]刘计划.法律帮助一点通——国家赔偿[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124.
[5]唐德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及相关法律适用指南[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6]林鸿潮,赵鹏.国家赔偿法司考读本[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95.
[7]柳建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身损害国家赔偿计算标准之探讨——“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的“上年度”之意涵[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1).
[8]王勇.对国家赔偿法中“上年度”的理解[J].人民司法,2001,(11).
[9]房绍坤,毕可志.国家赔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96.
[10]朱新力.新编国家赔偿法:要义与案例解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54.
[11]李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29.
[12]许安标,武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13]薛刚凌.国家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M]//薛刚凌.国家赔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105.
[14]姚天冲.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专论[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5:75.
[15]胡充寒,周雄文.中国国家赔偿法学[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225.
[16]皮纯协,冯军.国家赔偿法释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271.
[17]皮纯协,何寿生.比较国家赔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177.
[18][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M].焦美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9]杨立新.侵权法论: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
[20][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M].杜景林,卢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00.
[21]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234.
[22]尹飞.论国家赔偿责任与用人者责任、加害人个人责任之关系[J].法学杂志,2008,(2):79.
[23]江必新.国家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关系之再认识——兼论国家赔偿中侵权责任法的适用[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1):126.
[24]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355.
[25]杨立新.侵权行为法案例教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306.
[26]张新宝.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20号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370-372.
[27]黄松有.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28]应松年.国家赔偿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233.
[29]薛刚凌.国家赔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30]沈岿.国家赔偿法:原理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1]许崇德.中国宪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15.
[32]房绍坤,丁乐超,苗生明.国家赔偿法原理与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30.
[33]王晓滨.国家赔偿法实务指导[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34]高圣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立法争点、立法例及经典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5]FULLER Lon L.The Morality of Law[M].New Delhi:U-niversal Law Publishing Co.,2006:63.
[36]杨立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释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22.
[37]谢荣堂,周佳宥.论国家保护义务[J].军法专刊,1955,(3).
[38]ISENSEE/KIRCHHOF.HandbuchdesStaatsrechts,BandⅨ,Allgemeine Grundrechtslehre[M].Heidelberg:3 Aufl.C.F.Müller,2011,303ff.
[39]李震山.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0:153.
[40]JARASS/PIEROTH.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Kommentar[M].München:9.Aufl.C.H.Beck,2007,S.37.
[41]STERN KLAUS.基本权保护义务——法学上的一大发现[J].蔡宗珍,译.月旦法学杂志,2009,(12):50.
[42]LINDER Josef Franz.Theorie der Grundrechtsdogmatik[M].Tübingen:Mohr Siebeck,2005.
[43]RUFFERTMatthias.VorrangderVerfassungund Eigenständigkeit des Privatrechts[M].Tübingen:J.C.B.Mohr,2001:212.
[44]CANARIS Claus-Wilhelm.Grundrechte und Privatrecht:eine Zwischenbilanz[M].Berlin:Walter der Gruyter,1999:9.
[45]FEZER Karl-Heinz.Diskriminierende Werbung-Das Menschenbild der Verfassung im Wettbewerbsrecht[J].JZ,1998:267.
[46]Chrisitian Starck.基本权利之保护义务[M]//李建良,译.李建良.宪法理论与实践:一.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103.
[47]MICHAEL Lothar.Grundfälle zur Verhältnismäßigkeit[J].JUS,2001.
[48]STAHL Sandra.Schutzpflichten im Völkerrecht–Ansatz einer Dogmatik[M].Berlin:Springer,2012.
[49]FÖLLMER Johanna.Palliativversorgungin der Gesetzlichen Krankenversicherung:Zur Hospizversorgung Nach§39a SGB Vund zur Spezialisierten Ambulanten Palliativversorgung nach§37b SGB V[M].Berlin:Springer,2014:243.
[50]DOLDERER Anja Beatrice.Menschenwürde und Spätabbruch[M].Berlin:Springer,2012:135.
[51]LEE Chien-liang.Grundrechtsschutz unter Untermaßverbot?[M]//GROTE Rainer.Die Ordnung der Freiheit:Festschrift für Christian Starck zur siebzigste Geburtstag.Tübingen:Mohr Siebeck,2007.
[52]程明修.禁止过度侵害与禁止保护不足[J].月旦法学教室,2004,(17).
[53][荷]威廉·范博姆,[荷]米夏埃尔·富尔.在私法体系与公法体系之间的赔偿转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1.
[54]PARK Byungwoog.Wandel des klassischen Polizeisrechts zum neun Sicherheitsrecht[M].Berlin:Berliner Wissenschafts Verlag,2013:108.
[55]Michael/Morlok.Grundrechte[M].Baden-Baden:2.Aufl.Nomos,2010,S.309.
[56]PAUL Benjamin.Patentrecht und Umweltschutz[M].Berlin:LIT Verlag,2013,S.77.
[57]TSAI Tzung-Jen.Die Verfassungsrechtliche Umweltschutzpflicht des Staates[M].Berlin:Duncker und Humblot,1996:134.
[58]胡充寒,周雄文.中国国家赔偿法学[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
[59]胡锦光,余凌云.国家赔偿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61.
[60]吴萍.人身损害赔偿的理念与标准[J].法学,2003,(12):77.
[61]陈屹立,张帆.死亡赔偿制度的分层构建[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6):91.
[62]张潜伟.生命的价值学说的价值与死亡赔偿——兼论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公式[J].河北法学,2013,(3):142.
[63]江必新,梁凤云,梁清.国家赔偿法理论与实务: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739.
[64]林莉红,赵清林,黄启辉.刑讯逼供社会认知状况调查报告:上篇·民众卷[J].法学评论,2006,(4).
[65]林莉红,余涛,张超.刑讯逼供社会认知状况调查报告:下篇·警察卷[J].法学评论,2006,(6).
[66]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265.
On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Wrongful Death Clause of The State Liability Law
LIU Jian-long
(School of Law,China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tudies,Beijing 100089,China)
Section 34(1)item 3 of The State Liability Law prescribed a wrongful death.Compared with the wrongful death clauses in civil law,it is usually held that the very section is more equal and effective in guaranteeing individual's right to life and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especially,in case where a wrongful death exists,it can offer a more sufficient and effective remedy to the victim's immediate relatives.However,it is found to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in context of textual interpretation.Moreover,it is also found to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especially the principle of Untermassverbot.Though it may sustain the first two levels of review by the proportionality,it fails the last two levels,hereby it should be declared unconstitutional.
right to life;wrongful death;principle of equality;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untermassverbot
D922.11
A
1009-1971(2016)05-0020-12
[责任编辑:张莲英]
2016-05-04
北京市青年英才计划“合宪性解释论”(YETP1338);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教师基金项目(82050323)
柳建龙(1979—),男,福建惠安人,副教授,法学博士,从事比较宪法、国家赔偿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