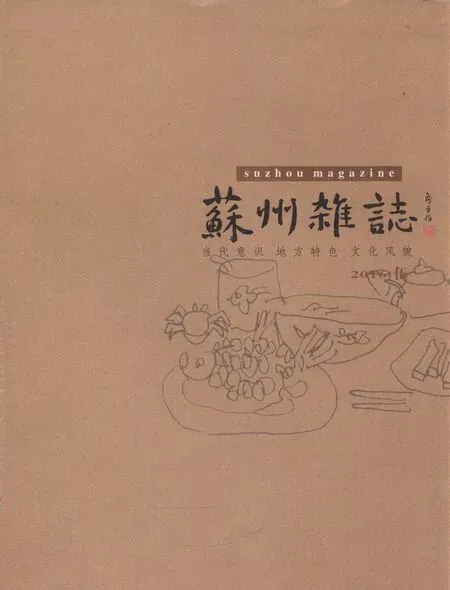评弹抗日轶事四则
朱寅全
评弹抗日轶事四则
朱寅全

一个新开篇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八路军新四军开展了游击战争。1939年5月,新四军一支队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抗日,在地方党和民抗、新六梯队团的配合下,坚决打击日伪顽各种反动势力,开辟苏常游击区积极宣传抗日。广大文艺工作者热烈响应,宣传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苏州评弹是苏常地区男女老少喜爱的说唱艺术,村镇桥浜皆有书场,是一种独特的宣传形式。为此,苏州县人民抗日自卫会,在1941年农历春节前,发布了一张关于评弹改革的通令:
元旦在即,各茶社向有邀请弹词之例。本系民间正当娱乐,惟内容缺乏革命精神,于抗日无助,要插进抗日材料,并广为宣传,以尽天职……
通令符合广大评弹艺人的心愿,一呼百应,他们以琵琶、三弦、醒木为武器,奔波于城乡茶室,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演唱抗日题材的作品。一时新创作的弹词作品有《送郎出征》、《讨汪逆》等。其中有一首《拥护新四军》的开篇,油印散发,处处演唱,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唱词如下:
芦沟七·七起风云,抗战原来全面动。(到如今)持久战局三年来,统一战线建大功。(幸亏得)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发扬着)优良传统好作风。八省健儿献身手,不怕饥寒霜雪风,(锻炼得)坚强钢铁一般同。北伐武昌初显绩,繁昌延陵更成功。转战江淮寒敌胆,大江南北显威风。革命必须抗日打鬼子,(故而是)到处民众拥护从,威信建立在战斗中。(可恨那)顽固分子亲日派,(眼看到)革命力大渐成功,心怀鬼胎眼睛红,反动政府昏冬冬,一道命令到华中,端出阴谋要反共,(分明是)一手遮天勿要面孔,仇者快,亲者痛,反对抗日罪难容。回头再看苏常太,皂白分明在胸中。江抗未来民众在活地狱,江抗一到匪顽逃得无影无踪。(到今朝)民主政权进入新阶段,光明进步大不同。自从“皖南事变”起,敌顽匪顽势更凶,一心联合来进攻,假名抗日真反共。我伲老百姓要过好日子,巩固政权不放松,参加游击自卫队,扩大主力革命便成功。要新民主社会得实现,(赶快将)敌伪匪顽一扫空,自由幸福乐融融。
通篇看来,开篇描写了苏南地区抗日历史片段,歌颂新四军,易唱好记,虽然个别唱句欠工整,大醇小疵,发挥了战斗作用。当时不仅有评弹艺人作开篇唱,街头艺人、戏剧演员、抗日宣传队都配上了各种调门四处唱开了。
一个老听客
1962年初春的一个夜晚,江苏省曲艺团金声伯、尤惠秋、朱雪吟三位著名评弹演员,由省委安排,坐轿车出中山门,在紫金山麓一处别墅,将为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作汇报演出。
三位演员携了乐器,走进大厅,正在揣摩为哪位首长演出,不想首长已迎了上来,啊,熟悉的,是谭震林同志。他操着一口湖南话,问长问短,谈笑风生,将几位演员原有的几分拘谨驱散干净,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开始了。
小客厅成了临时书场,演员和观众面对面近在咫尺。首先由尤惠秋和朱雪吟演唱了《王十朋·撕报单》。虽然谭震林先生不能全部听懂,幸好有位苏州籍的服务员充当临时翻译,倒也能懂十之八九。谭震林先生连连点头,大为赞赏。继而,评话名家金声伯上台表演《包公·断太后》,他神采飞扬,绘声绘色,妙语连珠,幽默动听。为了扫除语言上的障碍,金声伯不时将苏白改成京白,使谭谭震林先生听得更加入神,不时用掌声表示感谢。
演出之余,谭震林先生和演员们侃家常,谈往事,十分融洽。谭震林先生突然问道:“常熟梅李有家书场,你们去演出过吗?”金声伯立即回答:“是龙园书场。”“对”“我们都去演出过。”金声伯感到奇怪,旋转问道:“您怎么知道龙园书场?”
谭震林先生就介绍了自己过去战斗生涯中的一段往事。
原来,在1940年4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委派谭震林率一批团营干部抵达常熟,统一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抗日战争。当月25日,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兼政委。他几次化妆成听客,在龙园书场和战友秘密接线,部署反清乡反扫荡斗争,建立了苏常太抗日根据地,取得了一个个胜利。
金声伯听了问道:“您当时大约不用真名?”谭震林先生笑道:“化名林俊。”金声伯恍然:“大名鼎鼎的林司令就是您?”谭震林先生点点头:“就是鄙人。”金声伯接口:“您也是一个老听客了!”谭总理操着一口湖南话说:“当然啰!”
在场的听众、演员和工作人员听了,都笑得前仰后合。
一件冤假案
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罪恶昭彰,罄竹难书。
1940年秋,苏州光裕社有位评弹老艺人杜文奎,弹唱《描金凤》《大红袍》,书艺超群。那时,他在太仓县直塘镇畅乐园书场说书,演期即将结束,但书场里下一档书还未落实,老板委托杜先生介绍一档。杜文奎想到吴江有个艺友,立即去信联系。当时,写信一般就用明信片,三言两语,简简单单,告诉对方,约期进场。他在明信片上写道:“我还有两排,你家生不必带来,这里都有。”
这几句话,是当时评弹艺人的“行话”,“两排,一排是十天,二排是二十天;家生,是乐器,即琵琶、三弦。”哪里知道,就此闯了大祸,被一个日本翻译发现,告诉了日本鬼子小头目报功领赏。说:畅乐园书场是新四军联络站,说书先生林文奎是联络员,里面藏着二排人,还有家生,即武器。日寇小头目一听,立即出动武装,将书场团团包围,门口还架了机关枪。小头目和翻译拿着刺刀冲进杜文奎的宿舍,立即将他捆绑起来,严厉审问:新四军二排人在什么地方?“家生”放在何处?倘然不说,立即“撕拉撕拉”!
这突如其来的气势将杜文奎吓呆了,面色煞白,声音发抖,说自己是来说书的,没有新四军,没有“家生”,只有乐器。狗翻译眼睛一弹,出手就打了杜先生两个耳光,当场拿出一张明信片:“他娘的,这是什么?还赖,上面不是写着‘二排人’,还有‘家生’,你当我洋盘,快坦白!”又出手打了他一记耳光。
杜文奎开始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如梦初醒,又气又恨,这是普普通通的业务联系信,你们当成与新四军的联络信,你们害怕新四军到了这样的程度,真是可笑之极。书场老板毛桂生也站了出来,立即解说,这是评弹艺人的“行话”,杜先生说书到中秋节结束还有二十天,即二排。“家生”是乐器。私通新四军难道去用公开的明信片,你们弄错了。
狗翻译听了,自知没趣,一脸尴尬。鬼子小头目虽然听不懂他们的对话,也感觉到不是那么一回事,叽哩咕噜将翻译骂了几声,搬兵溜走了。
毛老板立即将杜文奎松绑,安慰了一下。但杜文奎吃了这么一个惊吓,瘫倒在床上,急火攻心,当夜就乘船回到苏州。后来越想越气,忧忧郁郁,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
一个大喜讯
常熟东乡的徐市镇,上世纪四十年代是个非常闭塞的僻壤。1945年8月,血气方刚的杨振雄在镇上新乐园书场弹唱《长生殿》。伪军班长红鼻子阿六依仗日军为虎作伥,欺压乡民,在书场门口耀武扬威,百姓敢怒不敢言,杨振雄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中旬的一天,杨振雄从一个在附近乡镇说书的道众那里获悉,日本鬼子要投降了,喜不自禁,翌日起了一个早身赶到太仓,证实了这个消息,立即返回徐市,在杂货店里买了一大包鞭炮,劈劈啪啪地放了起来。他一边放,一边高声宣讲:“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国人民胜利了!”老百姓欢喜若狂,奔走相告,小镇像煮沸了的开水欢腾起来。
“妈的,谁在放炮仗?谁在捣乱?”随着一阵靴声,传来了红鼻子阿六的吆喝声。他走到书场门口,看见杨振雄在放鞭炮,唬着一张马脸,“哦,原来是你,谁让你放的?”
杨振雄毫不畏惧:“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不做亡国奴了,庆祝胜利,何罪之有?”
“不要听信谣言,捣乱秩序!”红鼻子色厉内荏,掂了掂手中的驳壳枪威胁着说:“你再煽动闹事,我就不客气了!”
午后,书场里听众踊跃,个个喜形于色,借书场的一方乐土来表达胜利的喜悦。杨振雄心情欢畅,书说得格外起劲,还添了一段“外插花”:“杂货店鞭炮卖光,洋油桶当作大锣,铜面盆再凑热闹,太阳旗充当拖粪布!”有几个伪军开始时还在书场门口转来踱去,想寻找借口闹事,有几个听客在交头接耳议论,故意把声音放大:“听说新四军马上要进镇来了。”“真的,我家小二早上在梅李镇上看见了,都穿的灰布军装!”几个伪军听此议论,知道情况不妙,慌忙一溜烟走了。
果真,散书场时来了五个穿灰布军服的新四军战士。杨振雄和听众们急忙泡茶送水表示热烈欢迎。一个战士向群众宣布抗日胜利的消息,并警告日伪军立即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听候处理。群情激奋,人心大快。
当晚,新乐园书场场东兴冲冲走到后台房中告诉杨振雄:“红鼻子阿六格班赤佬到梅李交枪去哉。”夜场演出开始,杨振雄满心欢喜,上台时口占一首:“日寇投降,伪军跑光,新乐快乐,喜气洋洋!”
——苏州光裕书场现状调查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