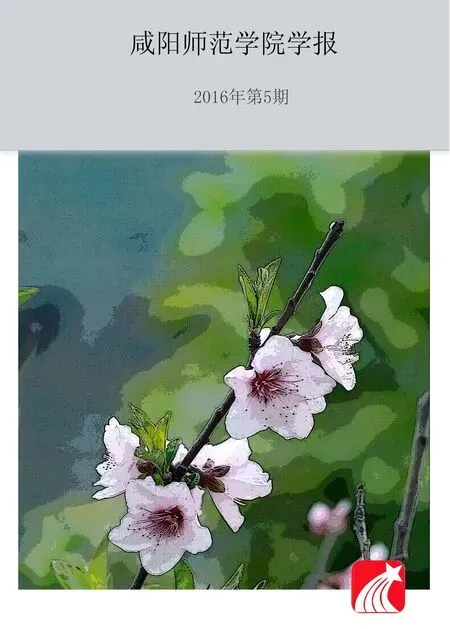论分户析产对汉代少年的影响
陶传祥,郭小楠
(1.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咸阳师范学院 资源环境与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论分户析产对汉代少年的影响
陶传祥1,郭小楠2
(1.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咸阳师范学院 资源环境与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汉代少年出身卑微,多依附豪强,违法犯禁多为财用,被视为恶少年。强制分户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措施之一,分户析产成为家庭延续的主要方式。从“分异之科”的角度剖析汉代少年活跃的社会经济根源:分户使得少年从父母的大家庭中游离出来,走向社会,取得独立的社会地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但析产后的少年不事劳作,多贫无产业,又缺乏家长有效的管教约束,肆意妄为,多违法犯禁,成为汉代不稳定的社会力量。
汉代;少年;恶少年;分异之科;分户析产
少年曾长期活跃于汉代的历史舞台,司马迁曰:“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1]3271寥寥数语概括出了汉代少年的特征。少年意气用事,血气方刚,固然与其年龄有关,《淮南子·诠言训》曰:“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暴强,老则好利。”[2]1012但汉代少年违法犯禁应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太史公曰“其实皆为财用耳”,《邓析子·无厚篇》亦云:“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3]1
王子今[4]、董平均[5]两位先生对秦汉少年做了深入的研究,涉及到了少年的界定、特征、少年的活动对社会的危害以及政府应对少年之策诸问题。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认为,少年是从里中父老控制下脱离出来者。[6]153沿着守屋氏的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出,少年在脱离父老管教之前就已经从父母大家庭中脱离出来了。大量少年离开父母而独自生存,“来去城郭,流亡,离本逐末,浮食”,[7]浮食者众不可避免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也考验了汉代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管子·治国》云:“民贫则难治也
……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8]924少年即混杂在这些浮食者中,对社会治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鉴于此,本文从分户析产的角度探究少年的出现并分析其活跃的原因,在有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略申己见,以期对汉代少年的研究有所助益。
1 汉代的分户析产
为了更好地观察汉代少年从家庭分离的过程,有必要对汉代的家庭制度进行梳理。汉代的家庭制度深受秦代影响,尤其商鞅的“分异令”影响巨大。商鞅在秦国进行了两次变法,首次变法内容有“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尔后再“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①对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李根蟠《从秦汉家庭论及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载于《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3-24页)一文认为,老百姓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成年儿子就必须分家,父亲与一个(或几个)儿子分居的同时,却往往与另一个儿子同居。杜正胜认为:“儿子或兄弟成年后就必须分家,只允许未成年子女与父母同居,塑造了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参见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载于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尽管杜、李两位先生对商鞅“分异令”的理解稍有不同,但汉代应普遍存在着分户析产。关于秦的“分异令”学界多有研究,商鞅变法对秦家庭制度的影响也有专文论述。[9]与分户相伴随的是对家产的析分,整个过程又称为“分户析产”,邢铁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分户析产有通论性的概述,[10]王彦辉对汉代的分户析产也有精深的研究。[11]96-128他们都提到,分户析产导致了农民家庭财产愈分愈贫。
汉承秦制,关于“异子之科”在汉代是否得以贯彻执行,学界普遍认为从文献记载来看,“异子之科”在汉代似乎因循未改。《汉书·刑法志》对汉初以来废除秦代酷法几乎做到了事无巨细的记载,但对“异子之科”只字未提。《晋书·刑法志》却记载了曹魏时“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12]925从而佐证了“异子之科”在汉代得以继续执行。葛剑雄推论,虽然没有发现西汉时期颁布的强制分户的法令,但可以肯定,实际存在着鼓励、促使以至强制百姓分户的措施或影响力。[13]360
分户析产在汉代还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汉书·地理志》载,河内“薄恩礼,好生分”,颜师古注“生分”曰:“生分,谓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财产。”[14]1647-1648又有颍川“好争讼分异”。[14]1654从出土的汉简也可看到汉代对分户的允许。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简337:“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15]55根据张家山汉简和相关文献,王彦辉认为,《晋书》的记载并不十分准确,汉代虽然没有颁布律令正式废除“异子之科”,并且允许兄弟之间别户分财,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当时仍在执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法令,而是本着不强迫也不禁止的原则,任由民间自行处置。[11]109-110
两汉虽然存在父母兄弟同居共财的现象,可是此种情况并不多见。②守屋美都雄对汉代兄弟同居的情况进行了罗列,有15例(参见守屋美都雄著,钱杭、杨晓芬译《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264页)。大多数是父母在世时,兄弟同居共财,一旦父母离世,旋即分家异财。分户析产是汉代普遍的社会现象。许倬云搜罗了汉代几世同堂的史料,有4例,数量是比较少的(参见许倬云《汉代家庭的大小》,载于氏著《求古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530-531页)。由于受“分异令”的影响,汉代的家庭规模较小,多为不到五口的核心家庭。[16-17]西汉家庭分异的情形至东汉并未有太大的改变。东汉全国的户口平均数与西汉相比有所提高,但增加得有限。到了东汉,风气渐变,分户析产的现象逐渐减少。[17]
2 汉代少年分户析产的个例分析
分户析产在汉代依然盛行,这是学界基本达成的共识。在此基础上,笔者拟选取三则案例,以观察汉代少年经过分户析产后,从家庭分离走向社会的过程。
第一则案例便是汉高祖刘邦与其父母兄弟分家后生活的情景。史书对刘邦的记载较为完备,虽不载其为具有特定含义的少年,但是刘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又好酒及色,[1]342-343观其言行皆是少年所为。高祖父亲认为刘邦为无赖,而少年又多称为无赖。《史记·高祖本纪》载未央宫落成时,刘邦曾对其父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1]386-387《汉书·昭帝纪》师古注“恶少年”曰:“恶少年谓无赖子弟也。”[14]231杜正胜对高祖刘邦兄弟分家的细节论述甚详,[17]20-23根据《史记》与《汉书》,刘邦父太公,母刘媪,上有二兄,下有一弟。长兄史籍无载,似已过世,遗有一妻一子;次兄名喜,生子濞;刘邦自己娶吕雉,生惠帝与鲁元公主,又置外室曹氏,生子肥;一弟名交,《汉书》云:“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14]1921刘邦一家四口,外室不同居,兄弟不同居,刘邦与父母也是分居异
财。《史记·楚元王传》曰:“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1]1987刘邦逃亡,不敢回家,求食于大嫂,可见他们是分户析产的。刘邦向其父敬酒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孰与仲多?”可见刘邦和其二哥的家产也是分开的,也当是异居别财。《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了“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并未见高祖父亲及兄弟的帮忙。刘邦系与其父、兄弟分户析产,而刘邦又不事田地劳作,不能治产业,其父认为刘邦是无赖,《史记集解》晋灼曰:“许慎曰‘赖,利也’。无利入于家也。或曰江淮之间谓小儿多诈狡猾为‘无赖’。”[1]386-387
第二例是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出土的元始五年(公元5年)《高都里朱凌先令券书》,记录了朱凌其家庭分户析产的诸多细节。
妪言:公文年十五去家自出为姓(生),遂居外,未尝持一钱来归。妪予子真、子方自为产业。子女仙君、弱君等贫毋产业。五年四月十日,妪以稻田一处、桑田二处分予弱君,波(陂)田一处分予仙君于至十二月。公文伤人为徒,贫无产业。于至十二月十一日,仙君、弱君各归田于妪,让予公文。妪即受田,以田分予公文,稻田二处,桑田二处,田界易如故。公文不得移卖予人。[18]
券书中的公文15岁的时候离开家庭自出为生,或是“分异令”影响使然,而公文又伤人为徒,贫无产业。公文应该不是特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少年从家庭中游离,走向社会进而违法犯禁的过程。
第三例是《隶释》之《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金季本有二子,金恭和雍直,后又收广延为后,季本在世时,曾分给雍直部分奴婢田地。分户析产后,雍直独自生活,不善劳作以致耗尽家财,负债逃亡。[19]162-163
从以上个案可以窥探,秦汉时期盛行的“分异令”导致了少年与父母分户析产。少年离开了父母所在大家庭后独自生活,多因不事生产、经营不善而贫困潦倒,为求生存铤而走险以至触犯法网。正如司马迁所指出的,少年“皆为财用”而违法犯禁。
3 汉代分户析产对少年的影响
《汉书·贾谊传》载贾谊批评秦人风俗鄙薄曰:
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14]2244
这段话一方面表明汉代袭秦,父子间仍然分户析产,另一方面也说明分户析产对秦汉家庭以及社会影响深远。笔者拟从家庭的经济、教育功能以及家庭成员间的法律连带责任等三个方面论述分户析产对少年的影响。
3.1 离开父母的庇护,少年生存困难
从上引贾谊的评论可知,父子兄弟分家异居后,互借生产工具尚且不可,共同劳动更是奢谈。分户后有一部分父子住在不同的里,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迁子”条有:“爰书:某里士伍甲告曰:‘谒鋈亲子同里士伍丙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敢告。’”[20]261-262同篇“告子”条亦有:“爰书:某里士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谒杀,敢告。’”[20]263简牍中提到“同里”,表明有一部分父子居住在不同的里中,甚至还不同郡县,如“迁子”条,咸阳某里人丙,迁到蜀边县,父子以及兄弟应当是各自治理产业。
王彦辉指出,分户析产造成农民的经营规模萎缩,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不仅体现在蒙受外力冲击时承受力有限,还在于经营规模始终处于一个自我分割的过程中。[11]127不善于料理家业的少年,其贫困情况更为严重。《汉书·卜式传》载卜式“以田畜为事。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而弟尽破其产,式辄复分与弟者数矣”。[14]2624《风俗通义·过誉》亦载:“(戴)幼起同辟有薛孟尝者,与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固乃听之,都与,奴婢引起老者。……田屋取其荒坏者……器物取其久者……外有共分之名,内实十三耳。子弟无几尽之,辄复更分,如此者数。”[21]200
《高都里朱凌先令券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少年从家庭分离后进而违法犯禁的过程:“公文年十五去家自出为生”,与史籍所载少年年龄相当;公文“居外,未尝持一钱来归”,可知公文在外生活艰辛,无生财之道;而后“公文伤人为徒,贫无产业”。公文的经历与少年类似,由于分户析产,使得诸如公文之属摆
脱了父母的管教,但又不善于稼穑,甚至将所分得田地移卖他人,以致贫无产业。
《荀子·修身》载:“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唐代杨倞注“偷儒惮事”曰:“皆谓懦弱、怠惰、畏劳苦之人也。”[22]34一般认为恶少者也即恶少年,恶少年具有怠惰、畏劳苦的性格,又不事劳作,坐吃山空,多耗尽家财,不得不背井离家,走向城郭,变为浮食者,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据前引《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载,金季本在世时,把一部分奴婢田地分给其子雍直,后雍直耗尽家财,负债逃亡。洪适认为,雍直似是季本庶孽不肖子孙,以訾产居之于外者。[19]162-163王子今认为,秦汉少年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无明确职业的所谓“浮游无事”之徒。[4]
3.2 父母长辈对少年的管教约束缺失
《汉书·循吏传》云:“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召信臣)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14]3642官吏子弟不事田作,游手好闲,由于召信臣的及时劝诫,一改前非,走向正途。如果是普通人家的子弟,未必会有长辈劝诫,《汉书·惠帝纪》载:“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14]85-86六百石以下官吏及普通基层民众仍是父母妻子别居的核心家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鞭长莫及。
张金光认为:“因为分户政策以及‘生分’、‘出赘’之俗,必使父家长对家庭的管理权力不能长期集中把握。”[9]颜师古注“少年恶子”曰:“恶子,不承父母教命者。”[14]3673-3674西汉的王吉批评了当时嫁娶过早的社会现象,他认为:“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14]3064与嫁娶过早相伴随的是子女婚后与父母分户析产,从而导致了父母对子女管教的缺失。
东汉时,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孝悌礼法思想日益得到强调,在一些上流社会官宦家庭开始形成了严整的家风。[23]393《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之兄去世后,马援承担起教育两个侄子的责任。针对侄子存在的“喜讥议而通轻侠客”的问题,马援诫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24]844-845《后汉书·王涣传》载王涣“父顺,安定太守。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24]2466生于官宦之家的王涣应是受父辈教化之故,方能向善好学。《后汉书·刘宽传》载刘宽“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24]877史书中多见东汉时期家中长辈及官吏以儒家文化教导子弟的例子,防微杜渐,对少年的人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而西汉时期的相关记载则不多。由于分户之风的盛行,汉代家庭教育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出身卑微的少年,与父母别居异财,衣食尚且无着,嘉言懿行岂非奢望!
3.3 无累少年之心,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少年犯罪
汉初法律疏阔,强调轻刑,刑罚大省,有刑错之风。《汉书·游侠传》:“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14]3698汉律疏阔,导致了社会上各类人员违法犯禁活动频繁,少年自然亦是如此。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收律》简174及简175规定:
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财、田宅。其子有妻、夫,若为户、有爵,及年十七以上,若为人妻而弃、寡者,皆勿收。[15]32
完城旦舂、鬼薪以上的罪犯如果其子女已完婚,与父母分户,有爵位,十七岁以上者,被抛弃之妻、寡妇,可免收,佐证了汉代有一部分人的结婚年龄在十七岁之下,也反映了连坐范围的缩小,避免了父母犯罪对子女的牵连。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分户可以限制连坐的范围,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又载:“‘盗及者(诸)它罪,同居所当坐。’可(何)谓‘同居’?户为‘同居’。”[20]160汉代多承秦法,对连坐的规定也应与此类似。今少年与父母兄弟分户析产,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少年犯罪对父母、妻、子以及同产的连累。
如果少年犯罪,多牵涉到其妻、子,而不涉及其父母。刘邦逃亡时,仅将吕后下狱,并未涉及刘邦父
母及其兄弟。①《史记·张丞相列传》曰:“高祖尝辟吏,吏系吕后,遇之不谨。任敖素善高祖,怒,击伤主吕后吏。”范阳少年欲杀其令,史载蒯通对范阳令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1]2574秦法严酷,范阳令虽然大肆杀戮,但并没有波及罪人之父或子。尹赏素称酷吏,严刑惩罚恶少年,也没有连带少年家人。[14]3673-3674公文伤人为徒,亦没有波及其兄弟姊妹及其母亲。再如《后汉书·刘盆子传》载吕母的儿子犯有小罪,宰论而杀之,并没有提到其子犯罪连及吕母。正是因为吕母未受到连坐,才得以密聚少年,执宰报仇。[24]477
汉文帝与诸大臣商议废除相坐之法,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文帝复曰:“朕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未见其便,宜熟计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14]1104-1105观诸史籍,确实只有谋反等大逆不道之罪,才施以族刑。对一般犯罪,多不牵连过广,无累其心,无形中纵容了少年的违法犯禁。
4 结语
活动频繁、能量巨大的汉代“少年”在波澜壮阔的秦汉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商鞅的“分异令”延续了五百年多年,[25]12而汉代少年也主要活跃在这一时期,这不可能不受当时分户政策的影响。商鞅的“分异令”使得少年在法律上拥有与父辈平等的地位,皆为编户民,纵然有利于增加徭役人口,推动以男耕女织为主的小农经济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分户析产具有一定的副作用,即脱离了家庭的汉代少年,无法受到父辈有效的管教和约束,得不到父辈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不善稼穑,甚至出卖田地、贫无产业,最终走上违法犯禁的道路。
从西汉中后期开始,世家大族得到发展,他们注重诗书传家,推崇察举入仕。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及察举制的兴起,数代同居共财逐渐得到推崇,“察孝廉、父别居”已遭到讽刺,以至到曹魏时乃“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此后,少年接受儒家文化的洗礼,沐浴长辈耳提面命般的教诲,日有所化。东汉以降,少年逐渐克服其戾气,“少年”一词更为主要的是用来指代年龄。具有特定含义的两汉少年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不复形成规模宏大的社会力量。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王恺銮.邓析子校正[M]//民国丛书:第5编:第9册,上海:上海书店,1996.
[4]王子今.说秦汉“少年”与“恶少年”[M]//秦汉社会史论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9-40.
[5]董平均.秦汉时期“少年”犯罪与政府防范措施[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9.
[6]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M].钱杭,杨晓芬,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居延简整理组.居延简《永始三年诏书》册释文[J].敦煌学辑刊,1984(2):171-172.
[8]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J].历史研究,1988(6):74-90.
[10]邢铁.我国古代的诸子平均析产问题[J].中国史研究,1995(4):3-15.
[11]王彦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5]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16]许倬云.汉代家庭的大小[M]//求古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515-541.
[17]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的家族与家庭[M]//中国式家庭与社会.合肥:黄山书社,2012:9-29.
[18]扬州博物馆.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J].文物,1987(1):4-13.
[19]洪适.隶释·隶续[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21]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2]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23]王利华.中国家庭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5]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The Analysis of Family-Separation’s Influence on Juveniles in the Han dynasty
TAO Chuanxiang1,GUO Xiaonan2
(1.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Gansu;2.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Culture,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anyang 712000,Shaanxi.China)
The juveniles in the Han Dynasty were from poor families.The bad juveniles committed illegal activities to break prohibition frequently.Shangyang took coercive family-separation measure in the Qin State,later named separation of families.Family-separation had become a primary process of family development.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easons for the activeness of juveniles in the view of family-separation.The juveniles broke away from parents’family,and then moved to the society.The juveniles were of independent social status,and took corresponding social responsibilities.The juveniles weren’t willing to work on tilling and planting,thus they were poor without family property.The juveniles became unruly and intractable for lack of parents’effective education.They committed illegal crimes and became unstable social power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e Han Dynasty;juveniles;bad juveniles;family-separation;dividing land
K234
A
1672-2914(2016)05-0023-05
2016-04-23
陶传祥(1992—),男,河南新蔡县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