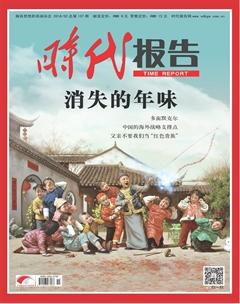回娘家
蔡怡


自从把父亲暂时安顿在我家之后,撒谎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是我每日必修的课题。
清晨,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还没清醒的我,知道又是父亲,睡眼惺忪地问:“爸,您找我有事啊?”“女儿啊,我要回家看看。”
过去两年多来,吵着要回家变成他的口头禅,他总一再地说。是语言被重复键入他的内存?还是在他混沌不清的脑子里,家的印象被埋得最深,永远忘不了?
我在被窝里翻了个身,问他:“你在我家吃得好,住得好,干吗要回北投呢?”这是我每天必跑的流程,口气已顺溜得像背书一般。“哎,我要去拿钱!我想起来了,在北投的家,还有我的存折、图章和钱哪。”
他不是失智了吗?怎么钱的事就是忘不了?我想着想着,心头好似有乱鼓一阵急敲,睡意全消,只好下床,再度从抽屉中找出自己替父亲开的新户头存折,及另外刻的新图章,开始编起亦真亦假的故事:“爸爸,您忘了,我把北投老家里的东西都搬过来了,干吗还要回去呢?您看,这不就是您的存折、图章吗?您的户头就在楼下银行,存着好多钱,花不完的。不信您数数看,个、十、百、千、万、十万,哇,好多钱。”
我的声调抑扬顿挫,演着每天要演好几遍的戏码,演技也因为一再磨炼而更加生动;父亲因我逼真的表演半信半疑,看着崭新但清清楚楚写着他名字的存折,又半信半疑地看着我。
为了证明这不是撒谎,我匆匆梳洗,牵着已穿戴整齐准备回家的父亲,到楼下银行ATM窗口,看清楚他户头里的数目字,还怕他印象不深刻,再具体地提出两千元,让他来回抚摸并回忆钞票的真实感后,放进他上衣口袋里。
以为靠撒谎,我的日子可以和他的糊涂一起度过,谁知多年在英国定居的儿子,突然要回来和我们长聚一段时间,这可搅乱了我们的一池混沌。
我忙着在客厅挪动家具,想再隔出一个空间,安顿多出的一个家人。但我既是父亲的女儿,亦是儿子的母亲,该怎样安排,才能摆平我心中那把天秤?该如何布局,才能布出我心中的团圆阵?
自从父亲搬进我家,丈夫就先关上他书房的门,除了吃饭几乎不再露面,似乎在这家中已分隔出另外一个天地,一个属于他私有的家。不知他是要把自己关在他的屋内?还是要把我关在他的家外?
这个家,还经得起重复的隔间吗?
父亲原有自己的家,在北投山边一个环境清幽的大厦中。八年前,嫂嫂和侄儿们移民加拿大,长兄不习惯一人住在自己冷清的房子,就搬进父母那不到30平的公寓去了。
当父母身体状况还好时,很乐于照顾到中年忽然变成单身的大儿子。三个人住在一起,虽然有些拥挤,但彼此间互相照应,相互取暖,仿佛时光倒流,三个中、老年人分别重拾过往回忆。
但随着父母的逐渐衰老,照顾长兄的能力减少,仰赖长兄的时间增多;原本享受亲情陪伴与天伦之乐的长兄,不堪肩上沉重的责任。尤其失智日趋明显、生活在自己时空中的父亲,已搭不上常人的列车。
父亲的问题尚未解决,我却在心理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听到医生惊人的宣判:你母亲,已是癌末!
消息来得太突然,我一时无法响应,呆滞地望向玻璃窗外,白云在天上走,风在吹,枝头鸟儿啁啾,树下孩童嬉闹,一个生意盎然的星期三下午。而主治医师面无表情地默坐在我对面,坐在一个红色的茶杯后面,等待我的答复:要告知病人吗?要作介入性治疗吗?你没有其他家人可商量吗?
家人当然是有,但长兄刚去加拿大探亲,弟弟外调大陆上海工作两年了,老公出差去了香港,儿子定居在英国……身边不知何时吹来一阵寒风,在这该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吹得我直打哆嗦,多少话哽在喉头。
等不到答案的医生站起身来,取滚水,泡新茶,我专注地凝视红色杯中的绿色叶片,正在滚水中上下翻腾、挣扎……
我失去了体温,也失去了感觉,全凭直觉反应将母亲安排住进病房,倚赖医生抽肺积水来减轻她的痛苦,同时帮父亲匆匆收拾简单衣物,接回我家,暂时安顿在空着的儿子房间里。每天,我带着父亲来回跑医院,陪母亲走完她人生最颠簸难行的一程。
母亲过世办丧事时,所有亲人由外地返台奔丧,看起来,浩浩荡荡一大家子,好不温暖。但丧事一办完,所有的亲人都作鸟兽散,没有一个人曾伫足停问:“失智的老爷爷、老父亲该如何照顾?”好像只要不触碰这问题,它就会消失不见;好像只要戴上一副墨镜,就可切断我眼神里的殷殷垂询。
我的心抖抖颤颤地下起小雨来,那滴滴答答的雨声像在呜咽,像是我的低诉:母亲走,家就散了。
一个多月后,天气转凉。斜风细雨吹得我心头更加冷飕飕,暗忖该回北投娘家替父亲拿些冬衣。未料,打开老家大门一看,除了客厅的沙发依旧,整个房子居然空无一物,剩下的,只是窗前几株母亲生前手植的兰草,在凄风苦雨中摇头晃脑,像是白头宫女细数前朝家变……
怎么母亲刚走,父亲失智,他们的人生就该被匆匆打包、清空,束之高阁?我该去何处借火取暖,温暖我那颗冰冷的心呢?
临走前,大厦管理员还特意追上来告诉我,手上的钥匙不能再用,因为父母的房子已经被兄弟处理好,租出去了。我的心一沉,钥匙变轻了。
怎么大家对凝聚爱与回忆的象征有这么不同的想法?太阳移位,绚烂彩虹会消失于空气中;一念之差,我们共营共生半辈子的家也就如蜃楼虚设,不见踪影?
才刚失去母亲,又失去娘家的我,瞬间魂魄飞散,不知该怎么回到自己家,更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暂住于儿子房间里的老父亲。但觉天地旋,山川走,景象崩。我失去所有依靠,成了天地间一孤雏,只剩个相貌神似父亲的躯壳,呆滞于身旁。我望着他,失智的、错乱的,岂止是他一人?第二天我病倒,发起高烧。在高烧不断中,我仿佛独自一人在狂风暴雨中奔跑,倾盆之雨,越下越大,积水也越来越深,即将没顶的我在苦水里泅泳,那又酸又苦的雨水,不断地被冲进喉咙里。但在昏沉模糊中,我觉察有个影子在我身边陪伴,有只温暖的大手,不断地在轻抚我滚烫的额头。
大病初愈的我,逐渐发现,留在身边的父亲绝不只是一具空壳,而是个依然有温度、有热度、有灵魂的亲人,他只不过灵魂有些缩水罢了。我喜出望外,享受和这神似我父亲的他一起唱儿歌、说数来宝,一起画图、折纸,过起身份颠倒的岁月。
两年多的时光,在不断的挫折与失望中摸索,在无数的泪水与欢笑中匍匐前进。好不容易才进入状况,那真实的儿子却远从英国回来了。我想从长计议,但父亲并不给我缓兵延宕的时间,一大清早又直接开我房门走了进来:“女儿,你母亲该回来了,我要跟她住。”我当场愣住,心里一阵抽痛,刚结疤的伤口被狠狠撕裂开来。谁不渴望往生已两年的母亲能如父亲所说,玩腻了天堂就回来了啊,我半天不知该如何作答。
昨天不是编了故事告诉他,长兄带母亲坐飞机,坐到“天的另一边”去了?而他自己不是也回答:“喔,天的另一边,是外国吗?美国?那太远了,我不跟她去了。”
显然,转眼他又忘了,今天对母亲的身在何处我又该编个什么说法呢?我曾经因为累了,词穷了,不想再说谎,不想再演戏,就直截了当回答:“妈妈不是已经去世了吗?您不是全程参与她的丧礼了吗?”结果他崩溃到无法收拾,好像这是两年来第一次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哭得不像失去配偶倒像失去母亲的小孩。但眼泪刚擦干,马上又转头问我:“你母亲该回来了吧?”
情绪无法无天,我选择永远撒谎,且要记得统一每天的谎言。
揣度老父因为看到身材高大,以前他很疼爱,现在却完全不认识的外孙,局促地蜷缩在沙发上睡觉,内心不安,无论我编什么故事,他都坚持要回家。眼看再不答应,父亲即将翻脸,我顾不得门外正是风横雨斜,打伞带他出门坐出租车。我笑嘻嘻地坐在车上,好像和他在玩游街的把戏;脑海却随着窗景一格一格地变化,十万火急地转动,想找出个喜剧脚本,演出皆大欢喜的版本。
回到了娘家大厦门外,父亲兴奋地指东指西:这是我和你母亲散步的院子,那是我成天张望你的窗口,这是……那是……好像我从来就不认识这块曾流着蜜汁的伤心地。管理员看到我们,立刻迎上前来,热心地告知,父母旧居的房客,前两个礼拜刚搬走;他手上有钥匙,可带我们进屋里去看看。我内心暗暗叫苦,拼命在父亲身后摇手,但手臂已被兴奋的父亲扯着直往里走。
父亲终于走进暌违两年没能回来的家,这个他朝思暮想、以为还有母亲身影、还有儿女欢笑、还有饭菜飘香的家;这个他还在里面做父亲,还是一家之主的温暖城堡。
父亲兴奋地推开门,跨着细碎的小步子,东进卧室,西转厨房,像蓄足力道,顿然旋开的陀螺,急速高转,呈现饱满的亮红。但我知道,也担心,陀螺碰东墙、触西壁,力道缓下,将会停顿、跌倒……
陀螺静止,色不再鲜,甚且瞧出它的苍白与斑驳。父亲晕了,也空了,像这空了的家。他双腿一抖一抖,吃力地走着,还回头望我。他的眼神也在发抖,如穷夜微火,闪着、烁着……然后,灭了……
他摸索着沙发坐下,像走失的五岁小孩,不拭脸,也不寻求我的协助,哇地大哭:“我的床铺、我的被子、我的家呢?家没有了,我怎么回——家——啊——?”
没有亲人的家,是个空屋,不回了;没有灵魂的人,是个空壳,不认了?
87岁老父的心,被敲出一个空洞,眼泪就从空洞中流出,其悲凉的哭声,和窗外那淅沥淅沥的雨声穿插交错,一声声、一叶叶地敲打在窗外芭蕉树上,更一针针、一线线地刺穿我的心头。我瞥见褪色的地板上,莫名其妙地流着一汪水,是窗缝渗进的雨水?还是……
母亲的眼泪?
我勇敢地擦干自己的泪水,决心不再犹豫,也不再撒谎,坚强地回过头,紧紧握住父亲温热的手掌,展开欢颜,像个撒娇的小女孩,说:“女儿的家,就是您永远的家。爸,咱们回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