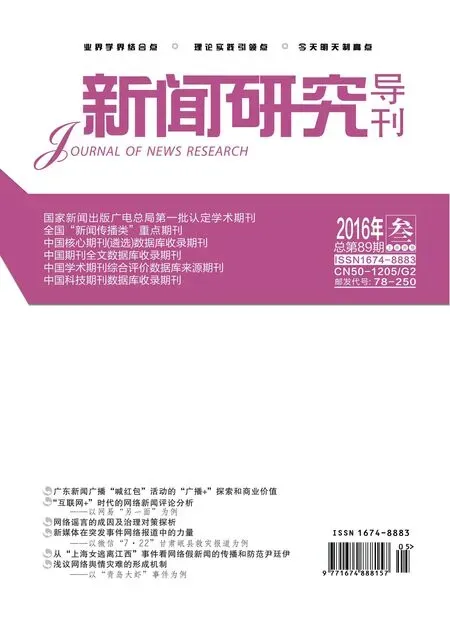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与生产的差异比较
杨嘉怡
(河南工业大学 科技处,河南 郑州 450001)
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与生产的差异比较
杨嘉怡
(河南工业大学科技处,河南郑州450001)
摘 要: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伴随着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央视纪录频道的正式开办,中国纪录片在央视纪录频道的推动下开启了新的篇章。中国电视剧纪录片从过去的完全艺术创作向商品化的生产转变。本文将结合中国纪录片产业的背景和产品属性来对其创作与生产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关键词:电视纪录片;生产;差异
中国电视纪录片在20世纪40年代被荷兰导演伊文思引入中国,当时是作为宣传动员的新闻电影。到80年代初,随着《丝绸之路》、《望长城》、《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大型纪录片的出现,纪录片具有了独立的艺术属性。90年代电视纪录片栏目化出现,1993年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开播,这是中国第一家以纪录片为主题的栏目。1993年《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开播,“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以平视的角度记录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全国掀起了第一场电视纪录片热潮。进入21世纪,面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娱乐之风盛行,中国电视纪录片遭到挫折,但是经历了短暂的停滞期后,伴随着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央视纪录频道的正式开办,标志着中国电视纪录片开始了真正意义的产业化试水。作为一项产业,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属性正在发生改变,电视纪录片被当作产品来对待,具有商品属性的纪录片决定了其生产过程有别于艺术品创作,下面笔者将结合中国纪录片产业的背景和产品属性来对纪录片创作与生产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一、导演属性的差异分析
从人的角度出发,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纪录片的导演是片子的灵魂,甚至可以说,纪录片就是导演的个人作品。作品中体现得更多的是导演自己的情怀、风格与认识。由于他们在美学上的造诣,纪录片学者往往把这类艺术纪录片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而这类纪录片在中国过去的几十年里也一直是其他纪录片学习的榜样。典型的代表有怀斯曼、麦克尔·摩尔等。他们拍摄的影片完全是个人化、个性化的艺术表达,版权归个人所有。他们的资金大多是个人投资或基金会,收入主要来自于录像带和DVD版权。
而反观纪录片生产,纪录片导演的地位就没有那么高了,如果说在记录片艺术创作中,导演是他自己创作国度里的国王,那么在纪录片生产过程中,导演只能算是国王的秘书。而真正的主导者是片子的出资方——制片人。导演与制片人是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导演在拍摄一部纪录片时常常受到制片人的监督和制约,他要在制片人的要求下去完成影片,版权往往归出资方所有。在这个过程中,导演要遵循标准化、产业化的生产模式,尽其所能地吸引观众,从而令制片人满意。此时,导演的诉求已经不再仅仅是艺术表达而更多的是商业市场。纪录片《索马里真相》导演吕建民在面对其片子太过商业化的批评时,表达了自己对纪录片的看法,“我完全不会在意别人说什么,只要观众满意就行。传统纪录片人有他们的圈子,他们的意见我考虑不了。我相信,一部成功的片子,不应该只是晚上在家里放着看,而更应该让更多观众看到。”[1]吕建民认为,如果说以前观众印象中的纪录片是那种一本正经、枯燥纯纪录的东西的话,他更希望做“商业元素强的纪录片”。著名纪录片导演周兵有着多年纪录片创作经历,从早期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栏目担任编导,再到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特别节目部主任,指导拍摄过《故宫》、《台北故宫》、《梅兰芳》、《敦煌》等一大批纪录片。周兵导演一直很注重纪录片的责任感,但同时他也坦言,他和他的团队目前正在尝试转型:“我们也需要团队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一些选题有了投资,人家找到我们承制,我们还在做一些商业的宣传片、广告等。我们也正在摸索,包括我的转型,不仅做导演。作为一个纪录片的运营者,我要转型做商务。”[2]可见纪录片导演在观念上逐渐在直面市场,生产出符合市场规律,令观众满意的纪录片成为未来纪录片创作者的目标。
二、运作周期和成本的差异分析
在纪录片创作中,起因可能是导演的灵光一闪,有可能今天你在街上听到某地有一个勾起你兴趣的事情,你就背上摄像机奔向那个陌生而又神秘的领域。可是当你千里迢迢赶过去,用了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拍摄了一堆散乱庞杂的素材后,回来却不知道如何把这些素材编辑在一起,更可能突然发现之前拍摄的东西也不过寥寥。创作的风险性很大,不可控的因素很多。纪录片《老头》的导演杨天乙,她的创作就颇为单纯和感性。杨天乙在北京租住的小区偶尔发现墙根儿坐了一排老头在聊天,她感到“看见了世间最好看的景象”。[3]于是决定拍摄这群老人。刚开始杨天乙请了摄像师、录音师、买了磁带、租了设备,结果录音师第二天就不来了,她就给老人带了麦克风。没过几天又和摄像师也闹翻了,杨天乙就买了DV数字机自己拍。中间停拍复拍了三次,拍摄就用了二年半的时间,素材长达9600分钟,后期剪辑用了半年的时间,最后完成片94分钟。她坦言面对庞大无序的素材,后期编辑过程中她也很困扰。张以庆导演的纪录片《幼儿园》在纪录片界是部佳作,导演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强调纪录片要表达自己的一种情怀。据说本片拍摄历时14个月,整个拍摄组是以导演为中心,总共就七八个人,拍摄下来的素材长达5000多分钟,而最终的成片只有70分钟,投资花费了一百多万。
上面提到的两部不计成本不考虑拍摄周期的纪录片,对于现在纪录片产业化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在纪录片生产中,为了保障成品有钱可赚,在生产前投资方要经过前期市场调研,判断哪个选题具有收视吸引力,哪些元素更能将观众稳在电视机前而不换台。于是,经过前期严密的调研,制定拍摄计划,并且规定生产标准之后,可以说前期的准备已经完成了纪录片生产的百分之六十。2012年7月央视“活力中国”的招标也进行了尝试,在第一季招标中以中短期现实类题材为主题,按照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的要求,参加投标的社会制作机构将在一个月内准备好详尽的投标文件,纪录频道组织专家评审确定中标名单并向社会公布。中标机构将获得由纪录片频道提供的制作经费,由于各选题的拍摄难度不同,纪录频道对各个选题的投资从8万元每集到15万元不等。[4]并在该频道的全程督导下进行相关纪录片的拍摄制作,有着严格的拍摄周期限制和质量要求。成品计划在2013年3月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目前已经在央视纪录频道完成了播出,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可见,央视纪录频道首次面向社会制作机构的招标过程,强调了纪录片制作的周期和成本运作。
三、注重商业价值的差异分析
纪录片由于受到商业化的影响,创作出来的成品,愈来愈带有商品化的属性。在纪录片的创作早期,纪录片的意义更多的是政治宣传、教育启迪。我国1989年版《电视词典》中对电视纪录片的定义是“对某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活或历史事件作系统、完整的纪录的电视新闻节目。”[5]由此可见,纪录片在刚开始进入中国时与电视新闻等同。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电视纪录片开始倡导将电视纪录片与电视新闻分开,与国际合作拍摄了很多大型纪录片,如《丝绸之路》、《望长城》、《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这一时期的电视纪录片规模比较大,或是国家投资,或是与国际合作的形式,反映出一种强烈的文化意识、审美意识,追求纪录片艺术价值。
纪录片走进了21世纪后,国家投资供给、自产自销的情况被打破。纪录片一方面面临着综艺娱乐节目竞争,另一方面又受到外国商业纪录片的冲击,中国电视纪录片必须开始转变。中国纪录片必须直面市场竞争,在竞争中努力调整自己,不仅要注重独特的艺术性,还更加注重商业价值。纪录片作为生产的商品,消费价值是它最重要的价值。纪录片能不能赚钱,才是纪录片生产者最关心的。纪录片《蓝色星球》是BBC的经典,它在策划开始就从商业价值出发,比如《蓝色星球》的音乐方面做得非常成功,BBC当时是请来专门的音乐大师为片子量身定做背景音乐。在配乐阶段,根据市场的需求,BBC做了各方面的调查,如法国版的配音,考虑如果请哪位演员来配会更加有魅力更加吸引观众,他们就会请哪位演员来配音。BBC一切以观众为中心,如何争取更多的观众就如何来做。
国内也如此,比如《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很大的原因在于它当时的收视率甚至超过了同时期播出的电视剧,从收视率上证明了中国电视纪录片是有观众群的,也是有市场的。在盈利方面,《舌尖》的海外发行收入是35万美元,创造了中国纪录片单集销售的最好成绩。尽管《舌尖》在艺术品质上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这些意义远远不如《舌尖》的商业价值带来的意义重要。关注收视率其实就是电视节目面向市场的一种表现。面对一个电视节目,作为投资者的最大诉求是商业价值,也就是获利,收视率就是衡量节目获利与否的重要标准。《舌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的收视率、它的盈利。可见进入产业化阶段的中国电视纪录片生产也在更加强调纪录片的商业价值。
四、生产标准和创作标准的差异分析
艺术家创作一件艺术品的时候,可以运用各种大胆的尝试,在创作过程中,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自由发挥。他们追随着自己的灵感,最终的作品对他们来说没有优劣之分,都是自己艺术的结晶。
但是纪录片的生产却不同。生产的商品是可复制的,在大批量流水线的工作环境中,商品的生产要遵循一定的工序进行。出来的成品如何评定,是否可以在屏幕上播出,也有一定的评判的标准。因此生产有方法论(生产模式)的指导,规定了产品一定要怎样做而不能怎样做。根据生产标准进而可以将产品分出优质品、合格品和残次品,这在创作中是没有的。
中国国内的纪录片产业尚不成熟,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在纪录片制作的项目流程管理方面,不少制作机构缺乏应有的经验。为了促进中国纪录片加速产业化发展,央视组织了CCTV-9纪录片频道“活力中国”招标活动。频道总监刘文说:“频道希望借此次招标,以‘命题作文、委托定制’的方式,催生一批关注中国当下社会现实、承接地气的优秀作品,发掘高水准纪录片的制作力量,锻炼具备国际化视野和市场营销意识的专业化团队,从而建立该频道与社会制作机构进行长效合作的机制,初步形成纪录片产业合作联盟,共同推动中国纪录片产业繁荣发展。”[6]相信在央视纪录频道的积极带动下,中国电视纪录片生产者们将会逐渐摸索出中国纪录片的行业生产标准。
讲到生产标准,对于中国纪录片创作者来说从模仿开始是难免的。纪录片《森林之歌》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记录森林版图的自然类纪录片,它填补了我国生态纪录片领域的空白。该片一共11集,每集50分钟,完全模仿外国商业纪录片模式来操作。主创者陈晓卿坦言:“《森林之歌》跟我的纪录片理想冲突太大,肯定不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但是,用国外的商业纪录片模式来操作,比较容易控制。这样拍最吸引观众,而且我的钱只够这么做。”[7]对比过去,我国以前也拍过这类动植物纪录片,比如中央电视台就拍过《丹顶鹤》,新疆台拍过《野马》、《回家的路有多远》。陈晓卿介绍当时的创作方法是你先拍到了,然后获得一点台里的资金支持,然后你再去接着拍下去,拍到实在没钱了,带回电视台剪辑。这种创作战线拉得非常长,周期不稳定,并不适合现在纪录片生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森林之歌》是一个长达11集的电视纪录片,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操作规范。“如果说投资方信任你把钱给你,你就去拍,这样做单集可能有的比现在做得好。但它可能就只能按时拍出两集,有两集播出了,而其他人还在山里边没拍完。”[7]可见,导演陈晓卿模仿国外纪录片生产模式制作《森林之歌》,是发现过去纪录片创作无法满足系列纪录片生产的必然选择。我国纪录片产业起步晚、经验少,唯一的方法就是学习,按照外国纪录片拍摄的模式进行模仿。但是模仿并不是目标,笔者认为,在模仿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吸取经验,从国内的价值观出发,形成自己的生产模式标准。这才是未来中国电视纪录片所真正需要的。
总之,中国电视纪录片在21世纪,由于电视发展环境的变化,正在从创作化走向生产化。这其中的转变是需要电视艺术研究者深入探讨的。分析二者差异有利于为以后的电视纪录片生产者进行标准化、批量化的产品生产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彭冀,朱美虹.导演坦诚拍纪录片既要冒险又要商业[N].新闻晨报,2012-03-12.
[2]张彬彬.导演周兵谈创作转型:纪录片要文化也要商业[N].半岛晨报,2012-05-29.
[3]杨天乙.导演杨天乙谈纪录片《老头》的创作过程[EB/ OL] . http://www.cnmhr.com/cnmhr/sxjyjmzz/2010/05/18/22233 76377.html , 2010-05-18.
[4]央视纪录频道首次面向社会制作机构招标[EB/OL] . http:// jishi.cntv.cn/20110715/100832.shtml ,2011-07-15.
[5]陈占慧.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策划研究[D].
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2:6-7.
[6]央视纪录频道首次面向社会制作机构招标[EB/OL] . http:// jishi.cntv.cn/20110715/100832.shtml , 2011-07-15.
[7]陈晓卿.商业纪录片假戏真做[N].北京青年报,2011-10-14.
[8]张同道,胡智锋,赵蓉,樊启鹏.2011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188(3):92-98.
[9]李婧.纪录片营销走入“定制时代”[N].中国文化报,2013-04-20.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05-0144-02
作者简介:杨嘉怡(1988—),女,河南郑州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广播电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