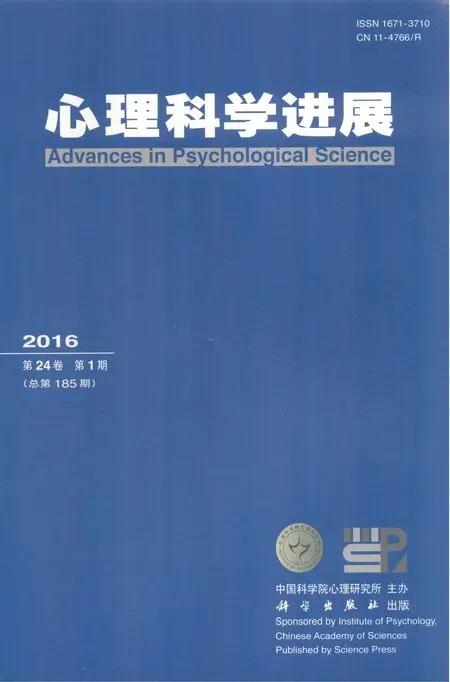情境对共情的影响
陈武英 刘连启
(1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2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 200235)
(3徐州工程学院宣传部,江苏徐州 221008)
1 引言
共情(empathy,也有人译作“移情”)是“个体基于对另一个人情绪状态或状况的理解所做出的情感反应,这种情感反应等同或类似于他人正在体验的感受或可能体验的感受”(Damon,Lerner, &Eisenberg,2006)。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是共情的两种主要成分,前者是指对他人情绪的情绪性反应,即产生和他人相似的情绪体验,后者指的是理解他人情绪状态产生的原因(陈武英,卢家楣,刘连启,林文毅,2014)。共情是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心理咨询与治疗等领域的热点话题,国内外已经有学者就共情的神经机制(Hétu,Taschereau-Dumouchel,&Jackson, 2012)、发展趋势(黄翯青,苏彦捷,2012)、性别差异(陈武英等,2014)等作了综述。与此不同的是,本文尝试梳理情境因素对共情的影响作用,并为未来的研究取向提供前瞻性的建议。
作为人际交往时的一种常见社会心理现象,“共情的发生不是单单有主体便会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共情是产生于特定的情境和关系下”(刘俊升,周颖,2008)。共情的情境效应可能代表着一种适应性的优势,这种优势使得个体的行为对不同的环境条件有更大的敏感性。为了做出灵活的应对行为,我们的大脑必须能够加工那些有社会意义预测性的情境信息,例如他人的身份、意图、感受和行为等。过去的经验和一些相关性可以帮助大脑完成这一过程。在每一次共情加工中,情境线索可以唤醒过去的经验,从而允许个体协调内部(过去经验)和外部(情境评价)的加工(Hein&Singer,2008)。
包括共情在内的许多社会认知加工,例如情绪加工以及决策大多都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Baez et al.,2013;Ibáñez&Manes,2012; Kennedy&Adolphs,2012)。事实上,人类的许多心理现象都存在情境依赖效应,例如视知觉(Zhang&von der Heydt,2010)、情绪(Ibáñez et al., 2011)和语言(Cardona et al.,2013)。
那么,情境对共情有着怎样的影响作用?情境对共情的影响是通过怎样的机制或方式实现的?情境对共情的影响又受到哪些因素的调节呢?
2 情境对共情的影响
关于什么是情境,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定义,即使是在心理学内部也有不同的观点(张文新,陈光辉,2009)。譬如有学者认为情境就是影响到各种感知特征被知觉的环境,包括感觉、行为和认知方面的各种信息(Albright&Stoner,2002)。更概括一点来说,情境就是在一个给定的时空场景中所展现出来的,能够影响到个体对目标刺激的意义理解的一切事物或信息。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刺激都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或解释,因为许多刺激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却可以在特定的情境中获得了恰当的意义,这就要求个体对情境具有敏感性(Vermeulen,2015)。个体对情境的敏感性其实就是情境效应的表现。许多社会认知加工中都有明显的情境效应,而且是在各种水平上都有所体现,从基本的感知觉到复杂的社会交往(de Gelder et al.,2006;Zibetti&Tijus,2005)。在社会认知加工的过程中,个体要聚焦于相关的社会线索,忽略掉无关的细节,将相关的情境信息与社会线索整合在一起,理解那些不完整或模糊的信息,最终产生对目标刺激的意义理解(Baez et al.,2013)。比如面部表情的识别。真实生活中的面部表情往往发生在信息丰富的具体情境之中,我们除了聚焦于他人面孔的表情以外,还要综合包括物理场景,声音,他人的肢体动作,甚至语言等相关的情境信息,最终准确地识别他人的面部表情(Barrett,Mesquita,&Gendron,2011)。
就共情而言,个体加工的目标刺激是他人的情绪情感体验,加工的结果是理解他人的情绪情感体验并产生与此类似的情绪体验。那么,为了达成对他人的情绪情感的准确理解,个体需要充分利用当前具体的情境线索。因为在真实生活中,社会信息的意义高度依赖于情境,而且有些社会要求或社会意义在具体情境中并不会被明确地表达出来(Kuzmanovic,Schilbach,Lehnhardt,Bente, &Vogeley,2011),这时往往就需要个体通过整合情境线索来进行内隐地推断(Klin,2000)。许多自闭症患者的社会认知水平不高,譬如心理理论和共情能力等有损伤,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他们缺乏正常人那样的情境敏感性,无法将情境信息有效地提取并整合到对当前目标刺激的理解中来(Vermeulen,2012)。
对一个具体情境中的社会信息(譬如他人的情绪情感)进行理解,通常包含三种基本的情境信息:时空框架、实体的集合以及实体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Wyer&Radvansky,1999)。其中,时空框架提供了事件发生在何时何地发生的信息。实体信息是事件中所涉及的个体,既可能是影响事件的人,也可能是受事件影响的人。在社会认知加工中,这个方面的信息是重点关注的。实体的生理特征、心理和情绪状态、姓名等信息都会用于这方面的表征。实体间的关系用于描述事件中所涉及的个体之间的关系。除此以外,事件的因果性以及实体的意图也属于情境信息。目前,共情的情境因素研究主要涉及的是实体及实体间的关系。
首先看一下对实体及实体间关系的研究。在一个具体情境中,共情的对象是他人的情绪情感,此时他人就是一个实体,若共情的对象是群体,那么群体就是实体的集合。对于一个特定的实体或实体集合,共情主体总有与之相应的关系。共情对象的社会身份以及因此与共情主体形成的群际关系是一种常见的情境因素,会影响到个体对他人的共情(Goubert et al.,2005)。譬如,当“他人”带有明显的“群体外(outgroup)或群体内(ingroup)”特征时,个体的共情反应可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类个体在社会中总是会归属于某些群体,或者说对某些群体产生认同感,重视自身群体的利益以及自己与群体成员的关系。与此相应的,我们更容易得到来自同一群体的其他成员的认同和支持,对不属于自己群体的人则通常更难产生共情,甚至会出现幸灾乐祸的情况(Cikara&van Bavel, 2014)。
种族就是一种常见的群体区分的标准。曾经有研究发现美国的大学生对于和自己同种族的人有更多的共情反应,显著强于对异种族个体的共情反应,研究者据此提出了群体内共情偏差的假设(the ingroup empathy hypothesis),认为归属于同一群体的成员之间可能发生更多、更强的共情反应(Brown,Bradley,&Lang,2006)。另一项研究(Westbury&Neumann,2008)证实了这一假设。在该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试观看一些描述人类、灵长类动物、鸟类等受到伤害的视频。结果表明,与其它动物相比,当电影内容与人类有关,即与个体的相似性更高,归属同一群体时,有更高的共情自评和更大的皮肤电阻。其次是灵长类,因为与人类更相似,明显比鸟类可以获得人类个体更多的共情反应。这一假设也得到了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支持(Avenanti,Sirigu,&Agiloit, 2010)。该研究选取白人和亚裔作为被试,要求被试对图片描述的同种族和异种族他人进行评定。除了操纵共情对象与共情主体的种族一致性以外,研究者还操纵了共情对象所处情境的效价,设计了积极的社会情境和消极的社会情境两种类型。结果表明,被试对于同种族的个体的共情反应显著高于对异种族个体的反应。但是,这种偏差只在共情对象处于消极情境时出现。而且,被试对图片内容的效价、唤醒度和忧伤程度的评定没有表现出种族偏差。这说明与种族归属有关的共情偏差受到了情境效价的调节作用,有可能仅限于消极情境中(Neumann,Boyle,&Chan,2013)。
除了种族这样的稳定的、不可选择的群体以外,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一些主动选择参与而形成的群体,例如支持同一球队的球迷。有一项研究设置了体育比赛作为实验情境,随机选取了两支棒球队的球迷观看比赛,实验操纵了比赛的结果(消极结果是自己支持的球队失败,对方球队胜利;积极结果是自己支持的球队胜利,对方球队失败),同时记录神经活动和主观感受。结果发现,消极结果激活扣带皮质前部和脑岛,而积极结果激活了腹侧纹状体。其中,腹侧纹状体的活动与主观愉悦有关,表明个体在看到“非本群体成员”的不良遭遇时感到开心,而不是产生共情(Cikara, Botvinick,&Fiske,2011)。由此可见,群体一旦形成,他人的群体归属性质就会对个体的共情反应产生影响。
当群体归属不明显时,共情对象与共情主体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亲密程度同样会影响共情反应。研究表明,当他人遭遇诸如疼痛、不幸等不良情形时往往容易引发我们的共情反应,即使他人与我们存在利益冲突,也不妨碍共情的发生(Singer et al.,2006)。也正因为如此,共情被认为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前提(寇彧,徐华女,2005)。但是,并非所有他人的不幸遭遇都会导致同样的共情反应。有研究发现,对于他人受到疼痛的刺激,“他人”是自己的恋人时要比“他人”是陌生人时有更为强烈的疼痛共情反应(Cheng,Chen,Lin,Chou, &Decety,2010)。可见,作为一种适应性的行为,个体对疼痛的共情受到个体与他人关系亲密性的影响。当他人处于疼痛情境时,个体迅速地推断自己与他人的亲密程度的结果会调节个体的所有情绪反应,这也有助于预测情境性的结果,并且指导个体的共情反应。这一现象甚至在自闭症患者身上也有体现。因为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在观察与自己存在社会关系或情感关系的个体时,可以表现出更加完好的社会性和共情性激活。但是,当观察的是与自己无关的或陌生的个体时,这种近乎自发的社会性和共情性激活则下降甚至消失(Gillespie,McCleery,&Oberman,2014)。
其次,情境中包含的事件的因果关系也会对共情产生影响。一些情境中的因果关系会比较明显,譬如序列事件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或其它来源的信息提示线索使得共情主体对他人情绪情感产生的原因和意义有所理解。以疼痛共情为例,通常看见他人疼痛都会引起个体的共情反应(Cheng,Chen,&Decety,2014;Novembre,Zanon,& Silani,2014),但是,有一项实验研究安排被试听到病患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因为疼痛刺激发出的声音(持续3秒钟),同时伴随视频上的一张面孔由中性表情转变为忍受疼痛的表情。在此之前,一半的被试得知病患接受的治疗是无效的,另一半的被试得知病患接受的治疗是有效的。实验同时收集了神经反应和主观评定两种指标。结果发现,无论是行为学数据还是认知神经数据都一致地表明在治疗无效的条件下被试对病患产生了更强烈的共情反应,当被试得知治疗有效时对病患的共情反应显著地更弱一些(Lamm,Batson,& Decety,2007)。这样的结果说明:当个体将疼痛解释为无效治疗的结果时,会认为这样的疼痛没有价值,更难忍受,而那些有效治疗伴随的疼痛则很有价值,应当承受。也就是说,因果关系的变化使得同样的刺激就有了不同的意义,于是个体的共情反应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在没有明显提示线索的情形下,个体也可以凭借自身的知识和经验提取情境中的因果关系。当然,因为个体的知识经验不同就可能会有不同的因果关系解释,这种差异也会使得个体的共情反应存在差异(Melloni,Lopez,&Ibanez,2014)。有两项研究对比了医生和普通人群对他人疼痛的共情反应。一项研究对比了医生和普通人对针刺疼痛的反应,结果表明医生的反应更弱(Cheng et al., 2007)。另一项相似的研究发现医生的脑电有延迟。这些结果表明医生对他人疼痛的情绪调节有早期效应,抑制了自下而上的负面唤醒过程,这样可以保持理智状态处理他人的疼痛(Decety, Yang,&Cheng,2010)。医生在从业过程中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他人疼痛的情境,相对而言,普通人对他人疼痛的情境接触远远少于医生。因此,医生对他人受到针刺的疼痛可能更倾向于解释为医务治疗的正常现象和必然结果,显得比普通人更为理性,故而负面唤醒体验要更少一些。
关于时空因素对共情的影响目前尚未有专门的研究进行考察,但是有研究者对情境的真实性和公开性的影响作用加以探究并获得了一些成果。例如,Gu和Han(2007)发现,对疼痛线索和刺激真实性的注意调节了与共情有关的神经活动。他们设计了4种情境,分别是真实的疼痛情境,卡通的疼痛情境,真实的中性情境和卡通的中性情境。另外,实验任务也有两种。一种任务要求被试判断疼痛的强度,这种判断要求注意聚焦于疼痛线索。还有一种任务是要求被试判断手或脚的数量是奇数还是偶数,这种判断要求注意远离疼痛线索。结果表明,同样是疼痛情境下判断疼痛强度的任务,卡通情境和真实情境都引发了包括前扣带回皮层以及右侧额中回在内的脑区的活动。但是,两类疼痛情境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前扣带回皮层的活动与疼痛共情的相关程度在真实疼痛情境条件下比卡通疼痛情境条件下更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卡通疼痛情境引发的脑电反应显著晚于真实疼痛情境,说明个体对情境真实性的加工弱化或延迟了额叶及中央脑区的疼痛共情早期加工。不仅如此,个体评定卡通疼痛情境引发的不愉快程度更少,对真实情境引发的不愉快则有更高的评定(Fan&Han,2008)。由此可见,情境的真实程度对共情反应的发生及强度都有所影响。
情境的公开性或私密性对共情反应同样存在影响。例如当有人受伤害时,多个人同时目睹和单独一人目睹,目击者的共情反应可能就是不一样的(Zaki,2014)。最近的一项研究以自编故事为实验材料,选取了1856名8~13岁儿童作为被试,考察儿童对不同群体的人的共情反应及助人意图。研究者设计的故事涉及到本国人和外国人两种群体,故事中的事件包括强烈需要帮助和比较需要帮助两种类型。儿童读完故事后在公开和不公开两种情境下对故事中的群体成员进行共情反应和助人意图的自评。研究结果发现了显著的交互作用:当他人所需的帮助不是非常强烈时,儿童在公开的情境下要比在不公开情境下对群体外成员有更多的共情反应和助人意图,对群体内成员的共情反应则不受情境公开性变化的影响;但是,当他人所需要的帮助非常强烈时,即使是在不公开情境下儿童对群体外成员也有更多的共情反应和助人意图(Sierksma,Thijs,&Verkuyten, 2014)。Sierksma等人(2014)对此结果的解释是:公开情境意味着公共场合,公共场合下社会规范更加明显,因此也促使儿童做出更多的自我表现的行为,比如富有爱心,公平,一视同仁等等。当群体外他人所需要的帮助不是特别强烈时,儿童会有更多的权衡,因此情境公开性与否就会影响到儿童的共情反应和随后的助人意图。当群体外成员强烈需要帮助时,即使是不公开的情境下儿童仍然对群体外成员有更多的共情反应和助人意图,可能是因为他人强烈需要帮助的情形激发了儿童的怜悯和同情,使得儿童不再考虑群体认同和情境公开性的问题。Sierksma等人(2014)对低需要帮助情形下结果的解释比较合乎逻辑,对高需要帮助情形下结果的解释则显得不够有力。在高需要帮助的情形下,如果儿童的同情被激发,而且这种同情被激发以后不再考虑情境公开性的问题,不需要表现某种姿态给别人看,那么为什么不是对群体外成员和群体内成员有着相似的共情反应,而偏偏对群体外成员有更强的共情反应呢?另外,该研究的被试是儿童群体,无法知道成人群体在相似的情境下是怎样的反应,假如儿童的行为确实受到自我表现的影响,成人是否会有更加强烈的自我表现行为呢?由于缺乏相关文献的对比和支持,作者对此缺乏很好的解释,反而认为有一种可能是在实验过程对主试对儿童有无意中的引导,即实验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尽管该研究的部分结果可能需要进一步检验,但是情境的公开性对个体的共情反应应该是存在影响的,只是这种影响不是绝对的,受到其它因素的调节作用,譬如个体遭遇的严重程度等。
3 情境影响共情的途径
根据上述分析,共情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心理活动,共情的产生是受到社会情境因素高度影响的。社会情境因素对共情的影响可能是通过自下而上(Ibáñez et al.,2011;Kveraga et al.,2011)和自上而下(Fogelson&Fernandez-del-Olmo,2013;Gu &Han,2007)两种途径影响共情的加工。
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极少的研究专门考察过社会情境因素对共情的影响是如何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产生作用的。在一项fMRI研究中,研究者呈现的是两种连续的手部医疗图片,一套是手部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注射的内容,另一套是手部在麻醉后进行组织活检的内容。被试只要观看图片即可。结果发现,看到被麻醉的手接受无疼痛注射时被试仍然出现了疼痛神经网络的活动增强,说明个体对假定的有害刺激有自动化的情绪反应。这种自动的反应受到一些与自我和他人区别有关的神经脑区的调节,包括颞项结合区和中部眶额皮层。这说明有些情境信息的加工是自下而上的影响共情反应的,因为图片上虽然提示了病患处于麻醉状态下,但注射的具体细节仍然自动化地激活了被试的疼痛神经网络(Lamm, Nusbaum,Meltzoff,&Decety,2007)。在视觉加工领域有研究考察过情景因素对视觉加工的自下而上的影响,可以作为一定的参考。Kveraga等人(2011)通过事先的评定选取了两类物体,一类是与某些特定情境有紧密联系的,称为SCA(strong contextual association),例如燃气灶。另一类则不与任何特定情境有紧密联系,称为WCA(weak contextual association),例如白纸。将两类物体分别放置在同样的情境中拍摄制作成彩色图片后供被试观看,实验任务分两种,一种要求被试报告图片中的物体是什么,另一种要求被试报告图片中物体的形状是什么。研究结果表明SCA比WCA在150~220毫秒时有更强的锁时,Kveraga等人(2011)对此的解释是在视觉识别的早期加工阶段就要对情境信息进行抽取分析,所以与特定情境有强烈联系的物体才会有更强的锁时。如果说Kveraga等人(2011)的研究与共情的关联不够密切,那么Ibáñez等人(2011)的研究则可以提供更进一步的推断。Ibáñez等人(2011)的研究采用了双重效价联想任务(DVAT),该任务模仿了内隐联想测验,选取愉快和愤怒两种面部表情以及正性和负性两类词汇作为刺激材料,通过按键反应的训练建立相容和不相容两类联想任务。该研究结果表明面孔表情的效价与情境(词汇的语义)之间的联想在早期的电位N170上有显著的差异,而N170在已有研究中已经被证明受到情境信息加工的调节影响(Righart&de Gelder,2008)。面部表情的识别加工是共情反应的重要基础,在许多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中都使用面部表情识别任务作为共情的测试指标(陈武英等,2014)。既然面部表情的识别加工在早期就受到情境信息的影响,说明情境信息可以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影响面部表情识别,包括共情。
最近,有学者从认知的角度指出,共情作为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情绪情感的理解和共鸣,依赖于两种输入:一是情境理解系统,二是情绪线索分类系统,所有的后期加工取决于这两个系统所输入的信息(Bird&Viding,2014)。
情境理解系统是一个领域普遍性的评价系统,提供了一个基础,用来估计他人的情绪状态是处于怎样的具体情境中。共情者并不需要直接体验到这个情境,但是可以根据一些线索对情境进行推断。这种推断依赖于共情者已有的知识经验,特别是社会情绪性知识经验。这一系统可以直接影响到共情者自身的情绪状态,使之向共情的方向靠近。
情绪线索分类系统执行的是较低水平的知觉分类任务,具体就是分析共情对象的各种线索从而形成某种类型的情绪结论。譬如综合分析对方的表情、语音或身体动作等线索。这一系统既可以直接影响到情绪表征系统导致情绪共情,也可以经由镜像神经系统间接导致情绪共情。
情境理解系统和情绪线索分类系统可以相互影响。我们如何知道他人的感受?可以根据个人线索进行分析,在个人线索缺乏的时候,可以根据情境进行推断分析。按照Bird和Viding(2014)的观点,情境理解在本质上是个体根据自身的知识经验结合有关的情境线索对他人所处的具体情境形成一定的认知和评价,从而准确理解他人当前的感受。因此,这里的情境理解是比较高水平的心理加工过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
已有研究也表明,情境因素对共情可以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产生影响。同样是前文提到的Lamm,Nusbaum等人(2007)的研究,还设计了另一个实验。他们使用了两种图片材料,一种图片显示的是使用注射器对人手的不同部位(如靠近指甲或靠近指关节)进行注射,即疼痛图片。另一种图片显示的包裹有黑色塑料针套的注射器贴近人手的不同部位,即非疼痛图片。两种图片在背景颜色、图片大小等方面都保持了一致。所有被试看完图片后要评定图片中人手的疼痛强度或者愉悦性质。两种不同的评定任务旨在操纵被试评价图片时的注意焦点。结果发现:在第一个实验中,与评价图片的愉快性质相比,评价图片内容的疼痛强度时躯体感觉运动区域有特殊的活动增强,即评价疼痛强度激活了被试自身与疼痛感受有关的脑区。评价任务的不同导致神经活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恰恰是共情所需要的,即产生与他人类似的体验。在第二个实验中,看到被麻醉的手接受无疼痛注射时被试仍然出现了疼痛神经网络的活动增强,说明个体对假定的有害刺激有自动化的情绪反应。这种自动的反应受到一些与自我和他人区别有关的神经脑区的调节,包括颞项结合区和中部眶额皮层。本研究说明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过程是如何交互作用并产生和调节他人导向的反应的。本研究的结果强调了认知加工在共情中的作用,并说明情绪和和身体的意识如何使得我们能够评价他人的感觉和情绪状态(Lamm,Nusbaum et al.,2007)。
在另一项fMRI研究中,研究者选取了57名年龄在7~40岁的(其中29人为男性)被试,以连续呈现图片的方式达到动态视觉效果,要求被试观看生活情境中的无疼痛、意外疼痛和蓄意致人疼痛等三种内容,结果表明,当被试看到他人偶然的疼痛时,激活了包括扣带中回前部、辅助运动区、脑岛和中央灰质以及躯体感觉皮层在内的区域。杏仁核、辅助运动区、脑岛后部出现了年龄差异。当被试看到他人被伤害的情境时,除上述区域以外还有另外一些脑区也被激活,包括与社会交往、情绪评价和道德推理有关的脑区,例如颞顶结合区、杏仁核、额区的中部和眶部(Decety &Michalska,2010)。这一结果说明在面对复杂的社会情境时,个体会运用包括与社会交往、情绪评价和道德推理等在内的知识和经验去分析他人面临的具体情况从而做出恰当的反应,这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作用方式。
4 情境影响共情的相关理论假说
假如把共情视作一种社会认知,那么可以参考以下几种理论来阐述情境对共情的影响。
首先,从认知的角度看,情境影响共情的前提是个体能够提取并理解情境中包含的相关信息。Wyer和Radvansky(1999)提出的情境模型对此有所解释。该模型认为个体在理解社会情境传达的信息过程中会自发的构建形成相应的情境模型。情境模型被假定可以代表真实世界中的情境的结构。但是,这些模型提供的信息并不是完整的,个体可以以此为最初的基础去理解新的信息并且判断新信息中有关的人和事件。情境模型通常有两种类型:一是事件模型,表征的特定的时空框架,对应于状态事件。因此,事件模型包含的信息有时空框架、实体以及实体间的关系。另一个是片断模型,指的是事件之间的关系,因此包含的信息有时间,因果性,意图,实体,实体关系。片断模型相当于多个事件模型的组合。个体在对他人共情时,根据当时情境所提供的信息可构建相应的情境模型,在信息较少的情况下构建事件模型,在信息丰富的情况下可构建片断模型。
弗里思等人曾经提出了弱中央统合理论(the weak central coherence,WCC)用于解释自闭症患者在共情、心理理论等社会认知能力上的缺陷。该理论认为中央统合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汇总各种信息并形成整体的意义理解,二是在特定背景下建构更高水平的意义。根据WCC理论,正常人经常以牺牲对细节和表面结构的关注为代价来处理信息以形成意义和整体结构。但自闭症患者缺乏这一构建倾向,即无法整合尽可能广泛的刺激,概括尽可能广泛的背景,而是倾向于将复杂的刺激理解为相互分离的部分,无法将之整合为有意义的整体。据此理论,个体要对他人产生共情,一方面要以他人的情绪情感为目标刺激搜集信息,另一方面则要以当前的具体情境信息构建情境模型,然后将两方面的信息汇总,最终建构对目标刺激的更高水平的意义,甚至还为个体的应对反应作出决策。其中,汇总各方面信息只是较低水平的统合,而在特定情境模型下建构对目标刺激的理解是高水平的统合。自闭症患者因为高水平的统合能力存在缺陷,所以只能加工一些细节和表面信息,却无法将情境信息统合起来形成完整的意义理解(Vermeulen,2015)。
那么,情境信息如何在高水平的统合中加入到共情的过程中并对共情产生影响呢?Melloni等人(2014)从认知神经加工的角度提出了社会情境网络模型(social context network model,SCNM)。这一网络可以更新情境线索并利用他们去构建快速的预测(额区),协调内部(机体)和外部(脑岛),巩固情境与目标刺激之间的联结学习(颞叶)。其中,脑岛起到关键作用,因为它的正常活动才能允许内部状态、感受、动机和特定的情境信息进行整合。而且,脑岛的前部与扣带回前部是很关键的节点,在知觉重要的依赖情境的信息时起关键作用,在个体对重要事件做出恰当的行为反应中也起关键作用。
5 未来研究趋向
情境对共情具有影响作用是毫无疑问的,明确这种影响作用是什么以及如何发生不仅有助于心理学者更好地理解共情的特点,而且也为后续的共情研究如何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提供了依据。但是已有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还不够深入,不少内容有待进一步挖掘。
第一,已有研究考察了包括人际关系、群际关系、情境意义性、真实性、公开性等对共情的影响作用,但情境因素的含义并不仅限于此,还有更多的情境因素值得研究者思考和关注。在当代发展心理学理论中,情境(context)的内涵有不同的观点,经历了由机械化到生物化再到人化的过程,通常包含物理环境,社会成员以及随时间推移的情境变量的变化等方面的内涵(张文新,陈光辉,2009)。其中,社会成员相当于前文所说的实体,已有的考察涉及到了社会成员,但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成员(共情对象)来说,除了与共情主体之间的群体关系和人际关系以外,共情对象的身份、性别、年龄、形象等许多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共情。譬如,有研究发现漂亮的孩子更容易得到他人的共情(Fisher &Ma,2014),这说明共情对象的外在形象对共情反应具有影响;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更容易得到他人(尤其是男性他人)的共情(Olweus& Endresen,1998),等等。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很零散,未来研究深入的空间还很大。除了共情对象的固有特征以外,共情对象的一些内在心理特点也可以作为情境因素纳入研究范畴,例如共情对象的情绪表达。以疼痛为例,有的人感到疼痛时会有明显的面部肌肉变化,甚至发出一些呻吟,有的人则是咬紧牙关。即使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中也可能对疼痛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些不同的表达会影响到他人对这种疼痛感受的感知理解,进而影响到共情的产生。另外,情境信息既包含了具体的信息,如刚刚提及的共情对象的形象、年龄等,也包含了更为抽象的信息,如情境的意义性、文化背景或某些语义线索等(徐强, 2014)。已有研究考察了情境的意义性对共情的影响,但是对文化背景以及语义线索的考察则乏人问津,可以在这一方向进行探索。
第二,情境对共情影响作用必然受到共情主体自身因素(比如年龄、经验、性别、动机、情绪状态等)的调节影响,这是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的另一个方向。以共情主体的性别为例,可以作如下思考。曾经有项研究以游戏任务的形式安排被试与对手(假想)进行竞争,设置了失败和胜利两种竞争结果,同时设置了公平竞争和不公平竞争两种竞争方式,考察被试对竞争对手的竞争结果有着怎样的共情反应。结果发现在公平竞争条件下,两性被试都对公平竞争的对手表现出了共情的神经反应,即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然而,在不公平竞争的条件下,男性的共情反应显著减少,并且同时伴随与奖励有关的区域的激活增强。这一研究说明对于男性来说,共情反应受到对他人的社会性行为的评价的影响,他们更容易对公平竞争的对手共情,对不公平的对手则希望对方受到惩罚(Singer et al.,2006)。这一研究与生活中的刻板印象相一致,即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对他人产生共情(Christov-Moore et al.,2014)。关于女性在共情上的性别优势,有观点认为这种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性别角色的社会期望(陈武英等,2014; Christov-Moore et al.,2014)。那么,就可以推论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情境的公开性或私密性发生变化将会对女性的共情反应有更大的影响,而男性则应有比较稳定如一的表现。因为无论社会情境是否公开,男性都不需要为了表现给他人看而做出某些不同的应对。也就是说,女性比男性可能更容易受到情境公开程度变化的影响。这一推断是否成立有待未来的研究验证。
第三,从认知加工的角度对情境影响共情的机制进行深入探索。虽然已有文献指出情境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影响共情,但是这种认识是比较笼统的。与一般的视觉加工中的场景效应不同,共情依赖的往往不是简单的自然环境,而是复杂的社交情境。理解复杂的社交情境是一种社会认知过程,因为个体对社交情境的理解取决于是否能有效提取相关的社交情境线索并将这些信息整合在一起产生社会意义(Baez et al., 2013)。未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继续借助包括fMRI、ERP以及眼动仪等在内的技术手段,从更加微观的层面揭示社交情境线索的提取和整合过程如何影响到共情反应的发生或强度,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对比不同特点的人群(如不同年龄群体的对比,不同认知风格的群体的对比,正常人与某些特殊疾病患者的对比等)探究情境影响共情的最本质的心理机制。
陈武英,卢家楣,刘连启,林文毅.(2014).共情的性别差异.心理科学进展,22(9),1423–1434.
黄翯青,苏彦捷.(2012).共情的毕生发展:一个双过程的视角.心理发展与教育,(4),434–441.
寇彧,徐华女.(2005).移情对亲社会行为决策的两种功能.心理学探新,(3),73–77.
刘俊升,周颖.(2008).移情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概述.心理科学,31(4),917–921.
徐强.(2014).场景对面部表情加工的影响(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
张文新,陈光辉.(2009).发展情境论——一种新的发展系统理论.心理科学进展,17(4),736–744.
Albright,T.D.,& Stoner,G.R.(2002).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visualprogressing.AnnualReviewof Neuroscience,25(1),339–379.
Avenanti,A.,Sirigu,A.,&Agiloit,S.M.(2010).Racial bias reduces empathic sensorimotor resonance with other-race pain.Current Biology,20,1018–1022.
Baez,S.,Herrera,E.,Villarin,L.,Theil,D.,Gonzalez-Gadea, M.L.,Gomez,P.,… Ibañez,A.M.(2013).Contextual social cognition impairments in schizophrenia and bipolar disorder.PLoS One,8(3),e57664.
Barrett,L.F.,Mesquita,B.,&Gendron,M.(2011).Context in emotion perception.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5),286–290.
Bird,G.,&Viding,E.(2014).The self to other model of empathy:Providing a new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empathy impairments in psychopathy, autism, and alexithymia.Neuroscience&Biobehavioral Reviews,47, 520–532.
Brown,L.M.,Bradley,M.M.,&Lang,P.J.(2006). Affective reactions to pictures of ingroup and outgroup members.Biological Psychology,71(3),303–311.
Cardona,J.F.,Gershanik,O.,Gelormini-Lezama,C.,Houck, A.L.,Cardona,S.,Kargieman,L.,...Ibáñez,A.(2013). Action-verb processing in Parkinson's disease:New pathways for motor-language coupling.Brain Structure& Function,218(6),1355–1373.
Cheng,Y.W.,Chen,C.Y.,Lin,C.P.,Chou,K.H.,& Decety,J.(2010).Love hurts:An fMRI study.NeuroImage, 51(2),923–929.
Cheng,Y.W.,Chen,C.Y.,&Decety,J.(2014).An EEG/ERP investig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empathy in early and middle childhood.Development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0,160–169.
Cheng,Y.W.,Lin,C.P.,Liu,H.L.,Hsu,Y.Y.,Lim,K.E., Hung,D.,&Decety,J.(2007).Expertise modulates the perception of pain in others.Current Biology,17(19), 1708–1713.
Christov-Moore,L.,Simpson,E.A.,Coudé,G.,Grigaityte, K.,Iacoboni,M.,& Ferrari,P.F.(2014).Empathy: Gender effects in brain and behavior.Neuroscience& Biobehavioral Reviews,46,604–627.
Cikara,M.,Botvinick,M.M.,&Fiske,S.T.(2011).Us versus them:Social identity shapes neural responses to intergroup competition and harm.Psychological Science, 22(3),306–313.
Cikara,M.,&van Bavel,J.J.(2014).The neuroscience of intergroup relations:An integrative review.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9(3),245–274.
Damon,W.,Lerner,R.M.,& Eisenberg,N.(2006).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Social,Emotional,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Vol.3,6th ed).New Jersey: John Wiley&Sons.
de Gelder,B.,Meeren,H.K.,Righart,R.,van den Stock,J., van de Riet,W.A.,&Tamietto,M.(2006).Beyond the face:Exploring rapid influencesofcontexton face processing.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155,37–48.
Decety,J.,Yang,C.Y.,&Cheng,Y.W.(2010).Physicians down-regulate their pain empathy response:An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 study.NeuroImage,50,1676–1682.
Decety,J.,&Michalska,K.J.(2010).Neuro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the circuits underlying empathy and sympathy from childhood to adulthood.Developmental Science, 13(6),886–899.
Fan,Y.,&Han,S.H.(2008).Temporal dynamic of neural mechanisms involved in empathy for pain:An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 study.Neuropsychologia,46(1), 160–173.
Fisher,R.J.,&Ma,Y.(2014).The price of being beautiful: Negative effects of attractiveness on empathy for children in need.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41(2),436–450.
Fogelson,N.,&Fernandez-del-Olmo,M.(2013).Implicit versus explicit local contextual processing.PLoS One, 8(6),e65914.
Gillespie,S.M.,McCleery,J.P.,&Oberman,L.M.(2014). Spontaneous versus deliberate vicarious representations: Different routes to empathy in psychopathy and autism.Brain,137(Pt 4),e272.
Goubert,L.,Craig,K.D.,Vervoort,T.,Morley,S.,Sullivan, M.J.L.,de C Williams,A.C.,...Crombez,G.(2005). Facing others in pain:The effects of empathy.Pain, 118(3),285–288.
Gu,X.S.,&Han,S.H.(2007).Attention and reality constraints on the neural processes of empathy for pain.NeuroImage,36,256–267.
Hein,G.,&Singer,T.(2008).I feel how you feel but not always:The empathic brain and its modulation.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18,153–158.
Hétu,S.,Taschereau-Dumouchel,V.,&Jackson,P.L. (2012).Stimulating the brain to study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empathy.Brain Stimulation,5(2),95–102.
Ibáñez,A.,Hurtado,E.,Riveros,R.,Urquina,H.,Cardona,J. F.,Petroni,A.,...Manes,F.(2011).Facial and semantic emotional interference:A pilot study on the behavioral and cortical responses to the Dual Valence Association Task.Behavioral and Brain Functions,7,8.
Ibáñez,A.,&Manes,F.(2012).Contextual 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behavioral variant of frontotemporal dementia.Neurology,78(17),1354–1362.
Kennedy,D.P.,&Adolphs,R.(2012).The social brain in psychiatric and neurological disorders.Trendsin Cognitive Sciences,16(11),559–572.
Klin,A.(2000).Attributing social meaning to ambiguous visual stimuli in higher-functioning autism and Asperger syndrome:The Social Attribution Task.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41(7),831–846.
Kuzmanovic,B.,Schilbach,L.,Lehnhardt,F.G.,Bente,G., &Vogeley,K.(2011).A matter of words:Impact of verbal and nonverbal information on impression formation in high-functioning autism.Research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5(1),604–613.
Kveraga,K.,Ghuman,A.S.,Kassam,K.S.,Aminoff,E.A., Hämäläinen,M.S.,Chaumon,M.,&Bar,M.(2011). Early onset of neural synchronization in the contextual associations network.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8(8), 3389–3394.
Lamm,C.,Batson,C.D.,&Decety,J.(2007).The neural substrate of human empathy:Effects of perspective-taking and cognitive appraisal.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9(1),42–58.
Lamm,C.,Nusbaum,H.C.,Meltzoff,A.N.,&Decety,J. (2007).What are you feeling?Using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o assess the modulation of sensory and affective responses during empathy for pain.PLoS One,2,e1292.
Melloni,M.,Lopez,V.,&Ibanez,A.(2014).Empathy and contextual social cognition.Cognitive,Affective,& Behavioral Neuroscience,14,407–425.
Neumann,D.L.,Boyle,G.J.,&Chan,R.C.K.(2013). Empathy towards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and different ethnicity when depicted in negative and positive contexts.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55,8–13.
Novembre,G.,Zanon,M.,&Silani,G.(2014).Empathy for social exclusion involves the sensory-discriminative component of pain:A within-subject fMRI study.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nsu038.
Olweus,D.,&Endresen,I.M.(1998).The importance of sex-of-stimulus object:Age trends and sex differences in empathic responsiveness.Social Development,7(3),370–388. Righart,R.,&De Gelder,B.(2008).Recognition of facial expressions is influenced by emotional scene gist.Cognitive,Affective,&Behavioral Neuroscience,8(3), 264–272.
Sierksma,J.,Thijs,J.,&Verkuyten,M.(2014).Children's intergroup helping:The role of empathy and peer group norm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126, 369–383.
Singer,T.,Seymour,B.,O'Doherty,J.P.,Stephan,K.E., Dolan,R.J.,&Frith,C.D.(2006).Empathic neural responses are modulated by the perceived fairness of others.Nature,439(7075),466–469.
Vermeulen,P.(2012).Autism as context blindness.Kansas City,MO:Autism Asperger Publishing.
Vermeulen,P.(2015).Context blindnes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Not using the forest to see the trees as trees.Hammill Institute on Disabilities,30,182–192.
Westbury,H.R.,&Neumann,D.L.(2008).Empathy-related responses to moving film stimuli depicting human and non-human animaltargetsin negative circumstances.Biological Psychology,78(1),66–74.
Wyer,R.S.Jr.,& Radvansky,G.A.(1999).The comprehension and validation ofsocialinform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106(1),89–118.
Zaki,J.(2014).Empathy:A motivated account.Psychological Bulletin,140(6),1608–1647.
Zhang,N.R.,&von der Heydt,R.(2010).Analysis of the context integration mechanisms underlying figure-ground organization in the visual cortex.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0(19),6482–6496.
Zibetti,E.,& Tijus,C.(2005).Understanding actions: Contextual dimensions and heuristics.In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Modeling and Using Context(Vol. 3554,pp.542–555).Berlin Heidelberg:Spr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