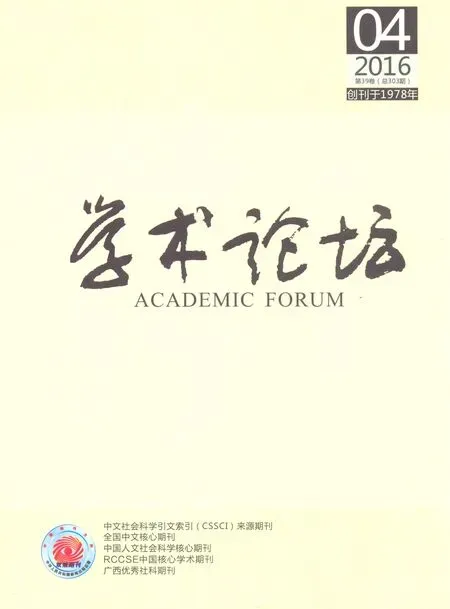从“共同文化”到“文化社会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解放之途
肖 琼,杨晓鸿
从“共同文化”到“文化社会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解放之途
肖琼,杨晓鸿
[摘要]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深入,产业工人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变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和理论还是否可行?英国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从文化层面上探讨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及其解放之途,从对“文化”的解析到“走向共同文化”再到“文化社会主义”的明确提出,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从文化的层面探讨进入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甚至提出可以摸索出一条从物质身体到共产主义的探索路径。文章选择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解放理论为研究对象,进而从文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方面探讨“文化社会主义”何以可能等问题,希望能够对当下马克思主义思潮低迷、社会主义应如何发展以及坚定社会主义的立场起到一定的理论借鉴作用。
[关键词]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共同文化;文化社会主义
早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社会发展运动的规律作出分析,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深入,产业工人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变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和理论还是否可行?英国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从文化层面上探讨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及其解放之途,从对“文化”的解析到“走向共同文化”再到“文化社会主义”的明确提出,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从文化的层面探讨进入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甚至提出可以摸索出一条从物质身体到共产主义的探索路径。2009年,伊格尔顿在《国际社会主义》第122期发表的《文化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从身体出发,如果能够改变我们躯体的感知,我们将会实现一个文化的社会主义。本文选择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解放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英国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社会主义”的理论合理性等问题,希望能够对当下马克思主义思潮低迷、社会主义应如何发展以及坚定社会主义的立场起到一定的理论借鉴作用。
一、文化的政治与文化政治:英国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概念的解析
正如张亮教授所强调的,关于“文化”这个概念,虽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概念,但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了巨大的扰动,成为其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1](P96)。英国悠久的文化研究传统使得他们阐述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严重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观念,并在重新阐释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的基础上,凸显出文化的整体性和政治性。
早在《关键词》中,威廉斯指出“文化”这个词是英文里两三个比较复杂的词之一。文化(culture)一词出自拉丁文cultura,原指农作物或动物等的耕种、培育、照料、练习、注意、敬神等,后被比喻性地反过来用于精神生活,转为培育、教养和修养等意涵。
“文化”成为一个问题并引发人们研究的兴趣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导致精神与物质、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双峰对峙的局面,对传统的社会心理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威廉斯通过考察发现,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进程,“文化”的概念大约经历过四个大的转变。第一个转化是通过类比形成的,“文化”(culture)从对自然生长的照管类推为对人类思维的训导过程;第二个转化,即“文化”是“整个社会智性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思即文化指“艺术的整体状况”;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文化”开始派生出第四个概念,即泛指一整套包括物质、智性和精神等各个层面的整体生活方式[2](P4)。威廉斯最看重最后一种,他摒弃了狭义的文化概念,认为文化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时代高级的精神和艺术产品。“文化是日常的,它就在每一个社会和每一个头脑中。”[1](P100)文化融入到看不见的日常行为和经验当中,而文化分析就是要将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及其或隐或显于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揭示出来。在将文化与各种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联结起来之后,威廉斯适时地提出了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观点,从而确立了“文化是普通的”这一典型的威廉斯式立论。威廉斯关于“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论点的提出,其目的在于要拯救人们的历史创造性,在肯定、高扬文化的创造性的同时,又不忽视文化生产的物质性基础。在威廉斯看来,文化不应该有高下贵贱之分,文化应该属于全体社会人,而不仅仅属于少数精英阶层。而且,威廉斯所强调的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记录了我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的这些变革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这“可以看作是一幅特殊的地图,借助它,我们可以对这种种历史变革的本质进行探索”[2](P5)。威廉斯关于“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提出,打破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机械性决定关系,恢复了文化的整体性和创造性。
汤普森进一步修正威廉斯“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定义,加强了其中的冲突性和斗争性,并提出了“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的文化概念。他说:“如果我们将威廉斯定义中的‘生活方式’换为‘发展方式’,那么,我们就从一个容易产生消极冷淡联想的定义转换到了一个能够提出活动性和主体问题的定义。如果我们再把词动一动,把隐含在‘发展’中的‘进步’联想删掉,那么,我们就得到‘整体冲突方式各要素间的关系研究’。冲突的方式也就是斗争的方式。”[3](P33)在汤普森看来,用冲突方式来修正生活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将文化定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传统重新连接到了一起[4](P34)。
然而,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和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双重影响,霍尔无情地批评了威廉斯、汤普森等为代表的“文化”不免带有主义的嫌疑。通过与结构主义的比较,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无情地指出了文化主义的局限性:首先,文化主义过分强调人的能动性而忽视了人的被限定性,从而变成一种“简单地肯定英雄主义”;其次,霍尔指出,文化主义强调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带有“某种复杂的简单性”;最后,霍尔批评文化主义过分注重经验,形成一种“经验的拔高”(experiential pull)[5](P47)。霍尔认为,在阶级和特定的文化形式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一对一关系,而往往是交叉重叠的。“大众文化就是文化霸权控制和反控制的场所,它使当代社会中,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相适应的新的对抗形式的建立成为可能。”[6](P149)由此,威廉斯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被霍尔改造为“文化作为一种斗争方式”,加强了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重要性,突出了文化的政治性及政治在文化领域的重要性。
伊格尔顿也是在与整个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框架中谈文化的观念。他认为文化一词的当代用法似乎主要有三个意义,并相互关联:(1)价值得到认同的具体的思想和艺术作品及其制作和分享过程;(2)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习俗、道德、价值观等组成的不断变迁但无法触摸的所谓“情感结构”;(3)制度意义上的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7](P129)。这些文化意义层面相互联系着,作为想象创造活动的文化与作为一般生活经验的文化,作为艺术、价值、风尚以及信念的文化与作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具体形式的文化,它们都是相互承转和相互结合,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伊格尔顿认为,当“文化与社会”论争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开始之时,关于这些文化意义的所有层面就开始得到承认并相互联系着。也就是说,在新的社会压力之下,以艺术、价值、风尚、信念之间的文化相互联系,同时在某些思想家的意识里以新的方式与另一方面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具体形式结合起来。这种文化观可以让我们看到个人的情感结构、社会的情感结构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制度综合体之间存在的相互承转关系。伊格尔顿暗示,文化内涵和艺术形式上的每一次变化都应该放在整个社会背景中才能体会到“文化”自身所包含的社会批判和变革力量。比如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从18世纪接过“文化修养”(cultivation)一词,却将词义的着重点由纯个人语境——有修养的个体,敏慧而高雅的行为规范——变为整个社会的生活品质。这一重心转移只有通过英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实际变革才能理解和道出这种变化所裹挟的文化内涵。而整个浪漫主义思潮不就是通过极力夸大理想生活方式和现实生活方式的分裂和价值张力,从而将文化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批判吗?所以,伊格尔顿总结,文化的意义正在于,“作为艺术,作为生活经验,作为社会结构——互相关联,交织为一种新的社会批判”[7](P132)。
当然,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分析方式”[1](P52),并不同于以往的文化批判。文化批判更注重对普遍意义的研究,表现为一种精英式的批判立场;而文化研究在于探究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之生产,不仅扩大了文化批判的范围,强化其社会性,还积极挑战了整个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并探索能够得以替代的权力形式,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向。
然而当代文化却被严重扭曲,偏离了它原来的位置,表现为“去政治化”和对集体、实际政治行动的严重失忆。伊格尔顿审视当前的文化理论时,发现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已被“性感”等“媚俗”的主题所取代。在《理论之后》中他写道:“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其他类似的思想,已经不再如过去般是个性感的题材。在今日,真正性感的主题是‘性’。在学院里,对法式亲吻的迷恋已经取代了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在某些文化圈子里,自慰的政治比中东的政治更令人沉迷。性虐待战胜了社会主义。”[9](P14)身体成了当下一个流行的话题,但伊格尔顿批判它们的焦点却是会感受情欲的身体,而不是会感到饥饿的身体;是交媾中的身体,而不是劳动中的身体。这种文化怕是早已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文化政治形式。伊格尔顿觉得很有必要对关于文化的政治和文化政治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他深刻地指出:“关于文化的政治强调的是文化只是进行政治的领地,而文化政治则强调文化作为政治替代物。其实在威廉斯他们一代那里,文化只是进行政治的领地,而现在却有可能要取代政治。”[10](P234)
二、共同文化与社会主义观念
伊格尔顿极力弘扬文化的政治性,对文化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认为,文化这个概念出现于文化本身在资本主义日趋重要的时代里,“是用以作为对中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而不是作为其盟友。文化是关于价值而非价格的,是关于道德而非物质的,是关于品格而非市侩的。文化是关于人类能力陶冶的,是为了让人类成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发自某种可鄙的功利动机”[9](P39)。正当粗鄙的工具理性日益牢固地掌控人类事物时,文化却仍然欢迎纯粹为自身而存在的事物,它不抱持任何目的性看法,只是为了赞颂事物自身丰饶的自我愉悦。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价值术语。它既沟通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同时又涉及一种关爱。伊格尔顿特别强调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爱的情怀,这正是人的身体之特殊性所在。
伊格尔顿从人的身体维度考察人的文化需求之必要性。我们天生就是缺失的。由于过早出生,身体的脆弱导致我们在极其漫长时期内都要依赖他人,这同时也产生了与他人非常密切的亲情关系。伊格尔顿写道,“所有的人在出生之际,都尚未发育完全、不能自立、有赖于他人帮助并且没有能力照料自己”。“只有依赖我们冠之以文化的这种外在力量,我们才得以逐渐自给自足”,“如果没有文化随之而来,我们就都会迅速死去”[11]。所以,我们的身体具有先天性的结构缺陷,需要文化的培植。人体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改造周围物体的过程中,也改造了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体先于那些物体,是高于它们、压过它们的“多余”之物。这个剩余物就是人的真我,非自我同一性,也是文化的身体。在伊格尔顿看来,这个作为人的剩余物的文化并不是当下流行的所谓的文化,而是应该走向一种共同的文化。
关于共同文化,在艾略特这里就早已意识到。艾略特相信可能有一种共同分享的文化修养,一个有着共同的信念、意义、价值和行为的社会。但艾略特又认为,一种共同文化绝不是一种平等主义的文化。如果少数人与大众享有共同的价值观,那么他们也是在不同的意识层面上拥有的。显然,艾略特既强调所有的人们都应该积极参加文化活动,同时也强调并非全都是相同的活动或者在相同的层面上。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培植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蒸馏并输入社会的无意识区域,而无意识区域也就在不经意之间、在习惯平常之中表现出这些价值。伊格尔顿认为艾略特的共同文化主张不无道理,但又认为,“艾略特保守地认定大部分人既没有能力掌握自觉的文化,也没有能力拥有自觉的信念,这似乎妨碍着他关于共同文化共享信念的设想”[7](P138)。
威廉斯则是从生活经验和情感结构出发,强调作为生活体验的文化无意识性。他说:“在体验某种文化的时候,它总是部分未知、部分未实现的。共同体的创造总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因为意识不可能先于创造,对于未知的体验没有公式可循。因此,一个好的共同体、一个鲜活的文化不仅会营造空间,而且也会积极鼓励所有人乃至所有个体,去协助推进公众所普遍需要的意识的发展。”[2](P345)文化永远不可能被完整地带到意识面前,因为文化永远敞开随时接受一切,因此永远都不会彻底地完成。
伊格尔顿将威廉斯的共同文化与艾略特的共同文化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发现威廉斯的共同文化较之艾略特的共同文化,既更自觉又不那么自觉:其之所以更自觉,是因为它包括所有成员的积极参与;其之所以不那么自觉,是因为这种合作将会产生的东西既不能事前设计,又不能在生产过程中完全得到了解。威廉斯明白,特定的价值观一旦被提供给新的社会集团后,结果就会变成非自我同一的,因为接受永远是对其进行再创造。而“艾略特的文化观却在这中间打进一个楔子:少数者培植意义和价值,然后传输给无意识的多数者。这样,艾略特眼中的价值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被事先设定:文化的基本要素已经存在于少数人的头脑,可以大致说出价值是什么样子”[7](P141)。伊格尔顿由此阐明了自己对共同文化的理解:“所谓共同文化,就是意义、行动以及描述等不断交换的过程,绝不是自我意识到的或可以总体化的整体,而是在所有文化成员的意识中、因而也是在充分的人性中不断长大推进。”[7](P140)共同文化意味着共同的责任、共同的参与和共同的掌握,所有成员都最充分地共同参与这些文化形式,包括艺术、政治、道德以及经济等,同时又要全力创造并维护它们。这种“充分的民主过程”要体现于文化的所有结构。这种共同文化的创造和形成,让全体人民参与并控制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生成过程,对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个运作过程就是革命政治。所以,伊格尔顿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共同文化的问题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问题”[7](P140)。
关于“社会主义”观念,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之前,英国和法国都有过社会主义的空想理论。马克思把实践唯物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从而使社会主义理论构想从空想变成必然。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认真地考察并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过程,指出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内在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最终将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制度。
社会主义社会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样的社会有过清晰的阐述: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伊格尔顿认为“这种自由作为人类可以充分发展天性的重要前提”意味着:“你可以自由地实现你的天性,不过,这里的天性并不是一种虚假的自然主义意义下的天性,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是表达出你所感受到的行动而已。……事实上,你是以一种同样允许他人实现天性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天性。而这意味着你尽其所能地实现自己的天性;因为他人的自我实现是你藉以发展天性的媒介,所以你并不享有暴力、宰制或自私的自由。”[9](P211)所以,伊格尔顿所理解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一种更广泛的文化革命。社会的每一个进程和整合变化都是无法抗拒或终止的,而每一种旧文化和意识在历史中的不愿意轻易撤退,每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形式的出现,都将社会引向进一步的整合和变化。这种整合和变化即是更为宽泛的革命,其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文化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文化观。
三、文化社会主义何以可能
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面世,掀起了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首先,他们认为,苏联解体只是标志着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苏联模式片面强调政治上的夺权,经济上的改制,而忽略思想文化革命;强调的是霸权和服从,而忽视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不是马克思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国家极权社会主义。其次,他们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基础已经发生变化,现代社会变革的动因不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工业社会对人本性的压制和摧残。所以当下的任务就是要摒弃人的异化状态,重新恢复人的自由本性。然而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是从科学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到科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于是纷纷从主观的、文化的、意识的、心理的等层面的革命来探讨社会主义变革的途径和必然性。他们用人道主义取代唯物史观,意图选择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价值,是将人从精神的、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消除人的自我异化,使人成为一个自由解放全面发展的人。而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
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依然从价值理性,从人道主义立场上去寻求问题的答案。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而强调一种“非暴力”形式。如葛兰西提出通过意识形态的革命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信仰和价值观念;马尔库塞则强调培养新感性,强调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恢复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变革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习俗和观念;列斐伏尔认为我们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他们所构想的未来社会确实美好,可是他们除了提供一种浪漫主义的心理学——美学救赎论之外,并没有为社会主义必然性进行科学的论证,也没有为人们指出一条关于人的解放的现实之路。正如张异宾教授所指出的:“可是,最重要的东西,即我们如何真实地从现实中找到革命的道路?解放是如何可能的?”[12](P173)等等这些最关键的问题,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似乎并不关心。
英国马克思主义试图开创一条从共同文化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解放之路。在对共同文化研究过程中,威廉斯提醒我们,如果想获得共同文化,首先需要在共同生活的每个层次上获得群体的生活资料,只有从这个根本原则出发,才能获得共同文化的经验。威廉斯开始刻意转向对共同经验的强调,对经验的相似性的强调。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强调:“文化的观念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状况所发生的普遍和重大变化所作出的一种普遍反应。其基本成分是努力进行整体性质的评估。我们共同生活的总体形态发生改变后,必然会产生了一种反应,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放在整体形态上。特定的变化会修改一种习惯法则,转变一种习惯行为。普遍的变化在完成以后,会促使我们回顾总体规划,使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总体进行重新审视。文化观念形成的过程即慢慢地重获掌控的过程。”[2](P311)而2009年伊格尔顿在《国际社会主义》上发表的《文化与社会主义》一文,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倡从文化的层面探讨进入社会主义的途径,甚至提出可以摸索出一条从物质身体到共产主义的路径。伊格尔顿认为,从身体出发,如果能够改变我们躯体的感知,我们将会实现一个文化的社会主义。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的是,伊格尔顿从身体维度去寻求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物质基础。他认为人的身体既是生理的身体,也是文化的身体。我们必须先要满足人的身体的基本要求,即满足需要维持身体基本生存和运转的基本生理性要求,同时当这些生理性的要求得到满足后,人的身体内部自然会产生更高层次的文化性的精神性的追求。这些转变在人的身体结构内部是自然过渡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过剩为文化生产的可能性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正如杜普雷所强调的:“经济过剩创造了文化生产的可能性,这种文化生产能够将自己从作为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支持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13](P465)在对文化生产分析和对文化剩余物的找寻中,伊格尔顿转向了悲剧。他通过对悲剧的分析,特别是对悲剧的情感反应效果分析,为我们所有的阶层找到了相似的经验领域,也为他的“文化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主义基础。
悲剧中的怜悯和恐惧情感效果分析源于亚里士多德,从此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基本上没有跳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框架。伊格尔顿大胆地质疑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怜悯和恐惧范畴的正确性,试图弥合对怜悯和恐惧机制分析的非理性和理性割裂状态。伊格尔顿首先对同情和移情进行了细微的区分。同情需要有一定的价值判断,而在纯移情的行为中不存在任何道德价值。移情强调对你的痛苦的感同身受,而同情你与感受你的悲痛是不同的。悲剧中的怜悯就是一种纯移情的行为,它不需要任何价值体系来帮助他们判断,是在意识判断之前的情感,强调共同的痛苦经验基础。所以在伊格尔顿看来,怜悯是先于自我反思前的情感,当我们见到人陷于困境茫然无助之时,或者遭受着灭顶之灾濒于死亡之时,我们马上会在情感上对这种行动的结果产生怜悯。这种怜悯情感产生将会为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共同体形式和主体化形式提供可能。这正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朗西埃所提出的重要概念——“感觉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朗西埃扩大了“美学”的含义,在“可感觉分配”的基础上,认为“审美”作为一种与可见、可说、可做的感性分配模式相关的感受性体系,能够为建构一种以共享意义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社会共同体形式和主体化形式提供可能,从而发挥艺术从积极的、建构性的面向重新介入生活的政治性意义。而悲剧艺术所激发人的怜悯和恐惧的情感反应,成为连结感情和意义,创设感觉共同体的重要力量,是“感觉分配”的具体实施。所以,伊格尔顿深入到内在的人格结构,挖掘出在人的怜悯情感中所蕴含的对人的道德价值的培养潜力以及介入生活的政治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才说,“悲剧是价值的源泉”。
在《文化与社会主义》一文中,伊格尔顿再一次明确指出,莎士比亚在《李尔王》剧中的某一处似乎指出了从剩余观念和良知发展到社会主义理念的路径。“当李尔目睹到衣不蔽体、孤弱无助的穷人时,他被这种非常陌生的景观所震撼,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啊,我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安享荣华富贵的人们啊,袒露着身体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痛苦吧,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李尔要表达的是,权力没有身体,也没有血肉。如果权力有了身体,有了感觉,它就会体会到身体所承受的痛苦,因而有可能停止这些行径。”[11]可是权力的身体性和感觉性在哪一个环节上被剥夺了呢?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丰富的感性被私有制异化为一种单一的冲动,即对占有的冲动。伊格尔顿深刻地指出,使权力的感觉钝化的是物质财富的剩余物,这些东西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身体,隔绝了人的恻隐之心。如果我们能够重新感知我们的身体,通过对审美感受性的改写而重新改写政治和生活,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必然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指出,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以类似方式寻求指出从物质身体到共产主义的路径。
四、结 语
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已经成功地探讨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逐步确立,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方面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社会伦理和道德方面还着实有待于发展和提高,存在着诸多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因于简单的发展主义所造成的经济和文化的不平衡发展,注重单纯的经济物质的发展和建设,对人的精神层面缺乏正当的引导。2013年习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的理论构想和目标要求是中国社会一个重大事件,既是对西方社会中的意义危机、价值危机和情感危机的回应,更是试图解决当下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伦理、理想价值重建以及社会共同体形成等问题的努力尝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显然,“中国梦”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共同文化观和共同理想观的最佳表现形式,它在国家层面上表现为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之梦,在个人层面上又表现为人民生活幸福、人生出彩之梦;既包含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宏伟目标,也包含着“共同享有梦想成真、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的个体希望;既描绘了国家、民族的宏伟蓝图,又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最大的共同文化结合点和共同希望凝聚。同时“梦”的形式又总是提醒着我们要意识到梦与现实的张力,追梦过程中的艰辛,作为理想形式的梦与实现过程之漫长,从而反对盲目乐观主义。“中国梦”同时也提请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在实现过程中的艰难、每个人梦想之间的冲突,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冲突,充分调动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个体的创造力,而不能在物质充裕繁华和盲目乐观中麻木了对痛苦的感知力和感受性,隔绝了人的恻隐之心。“中国梦”的提出其实就是政治与审美的完美结合。正如朗西埃所强调的,政治在根本上就是审美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从“共同文化”到“文化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解放策略,正是利用文化和审美对感觉的重新分布或划分而使政治发挥作用,而“中国梦”是“文化社会主义”的具体表达形式和实践尝试。
[参考文献]
[1]张亮.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3]Edward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I[J]. New Left Review,1961,(3).
[4]Edward Thompson.The Long Revolution II[J]. New Left Review,1961,(4).
[5]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A].陶东风,金元浦,等.文化研究第1辑[C].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6]李凤丹.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发展逻辑[A].刘伟民.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C].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7]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与爱欲[M].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弗朗西斯·穆尔赫恩.文化研究与政治,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等.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9]泰瑞·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李尚远,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5.
[10]特里·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M].王杰,贾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1]特里·伊格尔顿.文化与社会主义[J].强东红,译.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1).
[12]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3]杜普雷.评特里·伊格尔顿的《再论基础和上层建筑》,苏东晓,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M].第5辑,2002.
[责任编辑:戴庆瑄]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项目“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与现代性研究”(13BZW00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6)04- 0109 -06
[作者简介]肖琼,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杨晓鸿,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云南昆明65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