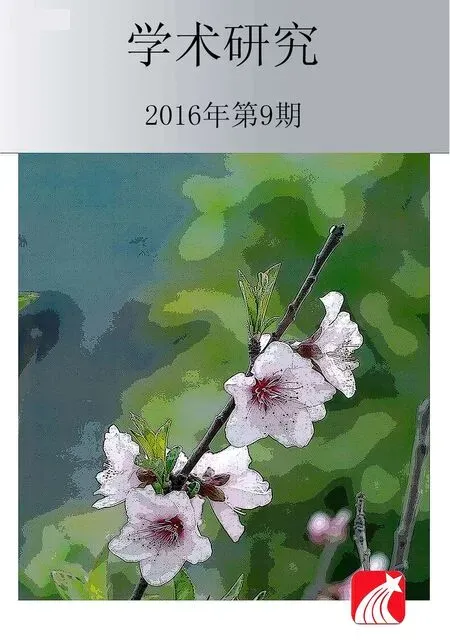“同情”与现代革命的催生机制*
黄 璇
“同情”与现代革命的催生机制*
黄 璇
同情,作为一种具有道德特质的人类情感,是现代革命的重要动力源。首先,同情能够将人们对非正义境况的感受,演变为一种追求独特性与超越性的激情,为革命提供巨大能量;其次,同情能够引发人们意欲改变平淡日常生活、唤起英雄主义的兴奋感,以此呈现出的政治美学张力,足以成为主导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动力;最后,同情通过激活公民个体之间、公民与政治共同体之间、公民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认同感,形成联合的力量,以成就现代革命。需要强调的是,合宜的同情,作为一种政治美德,不仅是一场审慎而正义的现代革命的巨大动力,同时也是避免极端暴力革命的重要的缓解剂。
同情革命独特性超越性认同感
革命,是一个有着众多争议的概念,也是一种具有不同性质和迥异现实结果的政治实践。有人把它视为社会转型与变迁的必要手段,有人把它视为破坏社会秩序的洪水猛兽;有人认为暴力必定与革命相随,因而革命具有毁灭性;有人认为革命是表达不满、释放愤怒、除旧布新的有效渠道,因而革命预示着希望与新生。像保守主义者柏克,分别以英国和法国为例,列举了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前者是一场睿智、审慎、严肃的、注重保留传承的革命;后者则是一场颠倒了人类同情心、极度鼓吹情感以至于使人们变得冷酷、失去人性而嗜血的革命。[1]这样的革命把国家置于危机之中。共和主义者阿伦特强调“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社会的根本性变化。”[2]民主主义者潘恩眼中的革命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是一场“敢于反抗暴政与暴君”、敢于“伸张正义”、捍卫人们建立自己的政府这一自然权利的伟大政治实践。[3]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把革命视为阶级斗争的积极形式,是阶级得以生存、自我更新与协调的重要方式,更是全世界联合起来的无产者通过暴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唯一途径。[4]
且勿论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实现方式及其造就的政治后果如何,我们有必要先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探讨革命,从源头上了解产生革命的动力机制,这样才能为勾画革命的全貌确定一个落笔点。同情,这一被视为人类天然美德的具有道德特质的情感,则是现代革命的重要动力来源。
一、寻求独特性与超越性
正如阿伦特所言,无论是被她定义为成功的美国革命,还是被她视为世界革命舞台之重要象征的法国革命,其主观上的动力都在于一种“非正义的感受”——即革命者目睹或听闻非正义境况时表达的感受。当然,尤其对于法国革命而言,这种非正义的感受已经演变为一种“追求独特性和超越性的激情”。[5]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注重暴力、崇拜狂热、向极端蜕变的革命形式中,这样的激情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与发展受到启蒙情感论思想的深刻影响,而在这场革命中起到重大催化作用的、追求独特性与超越性的激情,就是同情。
同情对独特性与超越性的追求,使之成为革命动力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在他人处于苦难境况、产生痛苦感受时,同情作为一种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情感,能够产生比起他人处在愉悦或者平淡处境中更为显著的体认作用。因此,同情的独特性就体现在它对苦难境况与痛苦感受的特定敏感性上。对于极端的暴力革命者而言,激起人们对苦难和痛苦的不正义境况的意识和体会,就是要通过强调人们所处环境的独特性——严格地说,即是由革命话语塑造的特别恶劣的情境,以显示出人们此时产生道德的同情感所具有的独特性,并赋予人们改变这一恶劣境况的举措以独特性,从而不断增强革命动机的正当性。
具体而言,对苦难境况与痛苦感受的体认,既可以是一种即时的感受,也可以是一种持续性的稳定认知。当困难与痛苦是由一次带给人们巨大身心冲击的突发事件造成的,那么它所激起的同情感主要是瞬时的,至少只是短时期内持续的同情感。在这种情况下,同情所展现出来的独特性,就在于引发了非常时期公民之间、同胞之间自然自发的凝聚力与联合力。这与人们处在相对和平的日常生活中重在自我保存的、以自爱为主导的情感区别开来。在独特境况中激起的独特的同情感所催生的公民互助行为,更是展现了政治共同体成员才具有的独特性:公民之间形成一条在非常时期能够暂时搁置自身利益、联合起来相互帮助、相互关心、从而克服难关的情感纽带。而这对于没有或者脱离政治共同体的人们而言,是难以具备的。这就是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强调的人只有处在社会中才真正具备人的价值的意义所在。
另一种情况,就是所谓的苦难与痛苦,并不是由产生瞬时强大冲击的突发事件造成,以至于人们难以对这一境况产生明确的感受,所产生的是人们在特定时期内对总体生活状态的相对认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苦难和痛苦的体认常常会发生分歧。就像某些革命者常常指出,苦于贫困、匮乏、专制与压迫的人们必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必定是极大的苦难与痛苦,是急需改变的不正义境况。然而,并不是革命话语所描述的身处这一境况的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处于苦难与痛苦之中。尤其在那些虽然物质贫困但精神并不匮乏、并有着根深蒂固宗教信仰的国家,更是如此。譬如,佛教国家不丹王国,作为一个其国民有着非常高的幸福指数而经济水平相对不高的国家,就曾被《世界幸福指数报告》视为特定案例进行全面分析。[6]此时,革命者对普罗大众的同情以及革命者试图唤起的人们相互之间的同情,是为了强化人们对特定状况的所谓“正确的认知”,是要促使人们对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做出突破。日常生活中的习以为常,在革命者看来就是一种得过且过的平庸,而改变这种想法就是在追求独特性。但是,这是一种为了实现革命目的而刻意凸显的独特性,同情在其中不免成为一种被扭曲的情感。其真正的道德蕴涵却在它被利用于刻意追求独特性以成为革命动力工具的同时,被销蚀掉了。
其次,由于同情是一种具有利他倾向的“天然美德”,是本身就能够体现出道德特质的情感,因此,同情对超越性的追求体现在它的正义诉求上。这样的超越性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凸显。一方面,同情超越了人们自我保存的自爱倾向,将情感关切与利益关注从自我转移至他人,甚至转移至共同体全体同胞以及全体人类。这种超越性的激情促使人们去体会并思考,当苦难不是降临在自己身上而是降临在他人、同胞,甚至是陌生人身上,自己应当有什么样的情感反应,才是身为社会共同体成员、政治共同体成员、人类大家庭成员所具备的合宜的道德情感。同情对道德超越性的追求,在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之间形成了恰当的利他关系。由此使人们对于人类社会中不平等、不正义的境况能够产生厌恶、痛恨与悲伤感,而不是冷漠、淡然和无所谓。在同情超越性的作用下,人们思考问题、感受现状的角度再也不是单一的个人视角,而是可以获得多元化、全局性的视角。这就为革命所需的一定程度的共性以及联合力量的形成提供了契机。但同时,同情所引起的对超越性追求,也极有可能陷入另一种危机:模糊了个人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私人与公共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必要界限。在这种情况下,超越性同时意味着对个性的抹杀;而原本有着正义的道德动机的革命,也极有可能演变为不惜牺牲个人以成就集体的以正义为名的革命。
另一方面,在启蒙运动年代被卢梭和苏格兰情感论者全面挖掘出其重要价值的同情,打破了只有理性才能作为现代政治基础的权威性规定,获得了超越理性成为现代政治之重要根基的支持条件。以同情超越理性,是卢梭的启蒙诉求。可见,同情对超越性的自信追求,根源就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利他倾向和道德蕴含上。且勿论这样的超越,其结果能否成功,其本质是否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但已经足以显示出同情所具有的力量感。这种力量感能够将马基雅维利试图区分开来的政治与道德、理性与情感又重新弥合起来。在同情的作用下,为政治寻求道德基础、为理性寻求情感支柱,就意味着要为现代政治指明一种正义的发展方向。从这种意义上看,同情对超越性追求是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的。但要注意的是,不能将超越等同于替代。换言之,同情不能在超越理性的过程中将理性对现代政治生活的作用全部抹杀。否则,原本一场有着正义诉求的思想变革将会因为这种情感的触底反弹,而成为一场诉诸极端与狂热的非正义革命。
同情从上述两方面共同体现出的超越性,意味着它能够产生动摇现代政治理性根基、扭转以人性自私为出发点的政治共同体建构模式的巨大力量。若要将这样的道德力量付诸实践,要使它最具冲击力、能造成最大范围的影响、获得最显著的效果,革命确实是一项简单易行、疾如雷电、不同凡响的实现方式。
二、实现正义与非凡的兴奋感
如果说作为一种追求独特性、超越性甚至是刺激性的激情,是对同情特质的描述,那么,要论证同情得以成为革命的动力,还需要从同情的功能入手分析。首先,一般而言,同情的产生,能为情感施动者及其对象同时带来兴奋感。就情感施动者而言,这种兴奋感体现在一种正义道德情感的油然而生,并以之为基础所构想出的、改变苦难现状并实现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图景之中。这就是罗尔斯所说的:“成员们有一种按照正义原则的要求行动的强烈的通常有效的欲望。”[7]当包含了正义感的正义观念在现代政治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时,它不仅能够克服人们破坏性的倾向,而且它的稳定性使得“所容许的制度产生着更弱的不公正行动的冲动和诱惑”。[8]就同情情感所指向的对象而言,得知他人对自身产生同情,也许会产生源于“自卑”的排斥心理,但也有可能会唤起某种程度的兴奋感。这种兴奋感则来自于一种在世界上发现“知音”的、感叹自身境况能引起他人共鸣与关注的安慰感。这种安慰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够缓解困境为受苦之人所造成的痛苦,至少在改善心理状况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情的这一特定功能也被视为一种特定道德情感在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的共通感。这样的共通感把道德规则与情感体察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人类普遍情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也反映出人们自身与生活中的他者之间的具体关联,并形成了康德所注重的联结知性、理性与感性的基于人类共同理智的判断力。[9]然而,也会有例外的状况。正如刚才所说,当人们对自尊的渴求强于受到关注的愿望时,来自他人的同情不仅不会带来兴奋感,有可能还会加重人们身处困境的痛苦感受。这也是为什么如尼采等思想家把同情视为一种恶,视为人性脆弱之根源的原因。
同情所引起的兴奋感能够为革命提供充足的动力,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第一个方面,在兴奋感的带动下,同情为日常生活带来新鲜与刺激。革命,要求对现状作出重要的形式上的改变,因而其内在具有将日常生活变为非日常生活的意图。但是在更激进的革命理论家看来,革命只有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显示出其真正的道德意义——“那些口口声声谈及革命与阶级斗争的人,如果不明确指向日常生活,如果不了解爱的颠覆性与拒绝压抑的积极性,那么他们的革命与斗争就是缺乏人性关怀的。”[10]一般来说,同情的产生及发挥作用,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只是偶尔发生的“小插曲”。然而,当同情成为一种持续发生与作用的情感现象,它带来的新鲜感、刺激感将使日常生活处于一种持续兴奋的状态,那么,日常生活的性质也将因此改变。
也许人们会将同情在政治生活中的泛滥归咎于某些个人、归咎于狂热革命者,但事实上,持续的同情并不是单纯依靠人为作用就能够轻易调动起来并长久保持的。尽管意图发动革命之人也许有强大的人格魅力与领导能力,但除了人的主观因素,同情得以持续引发兴奋感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体制。如果一个政治体制是非正义的,那么它将缺乏一种常规的渠道以助于释放同情及其引起的对非正义现象的不满感受。在这样的体制中,人们普遍对于公共问题与社会现象缺乏必要的敏感性,冷漠远多于同情。正因如此,当公共情感被长久压抑之后,一次对人们造成巨大冲击的偶发事件,或者一些显露锋芒的政治人物的煽动,就特别容易调动起人们的同情,并同时引发大规模的兴奋感。而此时迸发的公共情感,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价值指引、缺乏体制疏导,成为暴力革命的导火索也是意料中事了。如果人们习惯于在公共生活中表达对非正义的不满感受,习惯于合宜地表达同情而不是冷漠,人们的兴奋感也不会被随意调动至影响日常生活状态的程度。此时,相较于极端的革命,政治抗议与请愿成为人们在公共生活中表达同情与兴奋的重要实践方式。受法律保障与规定的政治抗议与请愿,在避免向暴力事件演变的前提下,鼓励人们自由地表达公共情感,实质上就是在鼓励思想与言论的自由。用密尔的话说,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关系到“人类精神福祉”,能够完善人的智性与德性。[11]在合宜政治情感与合理政治诉求的引导下,革命对于人们来说必定不是一种非做不可的唯一选择,也许还会被看作是一种最坏的选择。
第二个方面,同情能够以自身对正义的诉求唤起人们的英雄情结,以激起保护欲的方式来唤起人们的兴奋感。英雄情结,是相信自己能够有所作为、自己需要为不正义的社会贡献一份力量以拨乱反正的一种心理。人们为他人的苦难处境所触动而产生同情,甚至产生一种帮助他人脱离苦难的冲动与意图,这就是英雄情结的体现。英雄情结也许人人心中都会有,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它并不会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表现出来。若同情成为一种持续的情感经验,从而激化人们的英雄情结,使英雄情结深化为英雄主义情感,这就蕴含了直接的政治诉求。英雄主义情感还有一个作用——满足平凡人对伟大精神和伟大人格的想象。若将这样的想象付诸实践,平凡人自认的精英意识也会被激活。饱含英雄主义情感的革命,实质成了一种让平凡人发挥巨大力量、成为乱世中的精英、成就伟人心理的重要渠道。尤其在动荡变幻的现代转型社会时期,正如一切激情澎湃的革命理论家一样,人们特别有冲动去从看似平乏无味的日常与当下现实生活中发掘出史诗性精神与蕴含。同时,人们也试图为自己在变迁的时局中找到一个自己认可并为他人所认可的高尚人格定位。向他人、向同胞、向社会全体成员表达同情这种道德情感,必定是实现这一愿望的较为恰当的起点。但正是英雄主义情感赋予现代性史诗般的、必须通过革命来完成的宏大使命,往往让人们忽略了现实生活的平淡所反映出的可贵的真实性,也忽略了其中更值得珍惜和保存的重要价值。这就是现代生活中英雄主义的悖论。[12]
总的来说,无论是对生活的新鲜感与刺激感,还是史诗般的英雄主义情感,它们所包含的由同情引发的兴奋感呈现出一种政治美学层面的张力。这样的张力通过牵引人们对美的感受力来主导政治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尤其自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的理性与感性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人们对同情产生的兴奋感所蕴含的政治美感,有着更敏锐的感受力和更深刻的思考力。而这样的美感也逐渐由政治领域延展至非政治领域,从非日常生活延展至日常生活,充斥着人类行为与意识领域的方方面面。从而使得“政治领域中的各种行为活动逐渐被要求赋予美,其美感的强度甚至可以达到改变政治互动的结果”。[13]革命,这种足以产生强大现实冲击力与感官效果的政治实践,便造就了一种为人们的政治美感所期待的势不可挡的壮观景象。
三、革命认同感的三重造就
除了兴奋感,同情还能通过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共鸣来形成某种程度的认同感,从而使之成为革命的重要动力源。这样的认同感,可以包括个体间相互认同,对特定共同体的认同、对全体人类的认同。可以将认同感的三个具体涵项放置在现代政治语境中从以下三个视角来深入分析。
从公民—公民的视角来看,人们产生同情,是借由想象力的作用把自身与另一个或者另一些公民个体联系起来,从而双方能够获得情感与处境上某种程度的共同认知。这是一种浅层的、较为松散的认同感。尤其在强调个性与公私分化逐渐成型的成熟现代社会中,公民之间就对方的处境与痛苦表达特定的同情,很大程度上是实现某种自我价值的方式。所以,产生于公民个体之间的情感—处境认同感,实质上是一种以强调个体性、个体价值为原点的相互认同。它的特点在于,从情感共鸣发展至情感—处境认同的双方,尽管有深刻的情感触动并形成了特定的情感关联,但通常还是保持着个体间相互独立性。可见,这样的认同感所蕴含的差异性大于共同性。在这一视角中,基于认同感而形成的情感力量,也相对较弱。
总的来说,如果对他人特定处境表达的特定情感,被定位为基于公民个体性的情感—处境认同,其对政治现状的道德关注常常强于权力诉求,并且主要是偶发的行为而非持续的行为。由于关注个体独特性的显现,公民—公民视角中的情感认同并不注重促使个人联合起来表达对同一种价值的认同,只是强调以“人同此心”的方式来体会他人的情感与处境。实施这种情感认同方式,并不以僭越公民个体之间必要的界限、模糊双方的价值观差异性为代价。因而它足以引发革命的作用是相对微小的。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如果在某些媒介因素的刺激下,同情施动者将自我完全代入被同情对象的经历,或者把被同情对象的自我完全带入同情施动者自身的经历,那么此时的同情已经造成一种不太正常的、模糊了他者与自我之间必要界限的情感认同。这意味着公民—公民之间原本较为松散、浅层的情感—情境认知,在相互代入的过程中上升为对特定价值的一致认知。这就为革命所需的“联合起来的力量”提供了契机。
从公民—政治共同体的视角来看,公民对他人的痛感与困境表达特定的情感关切,常常能借由对各种公共活动、公共舆论的参与,上升到对整个政治共同体及全体成员的情感关切。此时,由同情形成的情感纽带已经突破基本的情感—处境认知,构成政治认同的重要内容。“在人民特有的风俗习惯中,在往往由于性质的特殊而成为排他的和民族的宗教仪式中,在使公民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的娱乐活动中,在增进他们的体质和自尊心的体育运动中,在舞台演出的戏剧中,找到了这种使公民们联合起来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他们彼此互相敬爱的纽带。”[14]这一纽带实质就是使政治共同体成员联系更紧密的政治认同。以同情为基础的政治认同强化了同情施动者身为共同体其中一份子的政治身份认知。这种同情是他对于与他具有同样公民身份的人的一种特殊情感,而这是他对外国人几乎没有的。在他看来,他所同情的对象不仅是另外一个个体,而且是与他一样从小生长在相同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环境之中,接受相近的教育方式、受相近风俗习惯影响的“同胞”。此外,以同情为基础的政治认同也蕴含着人们对国家的认同。这意味着,人们在同情并关爱政治共同体同胞的同时,饱含着对国家的特殊情感。这种对国家的“爱”通常演变为一种基于同情的爱国主义政治情感。
作为具有特定政治蕴含的爱的特殊形式,爱国主义情感并不仅仅包含简单的政治同意、政治承诺或对特定政治原则的遵循。它透露着把国家认为是公民“自己的”强烈情感。[15]但这也常常使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与表现形式上被随意混淆。必须强调的是,爱国主义并不是狭隘而偏执的激情,它所体现的基于情感的政治认同,是一种具有批判性、负责任的而不是盲从的认同。当公民在爱国主义政治情感的作用下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意味着他具有对整个共同体承担起必要公共责任、以公共理性精神来批判性地审视公共问题、以助于形成良序稳定的共同体政治生活的倾向与愿望。爱国主义情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美德,而不是政治激情。因而,它更注重为革命提供一种合宜的积极动力,而不是盲目的煽动力量。它在革命中承担着兼具批判性和支持性作用的角色。正如卢梭所强调的,以革命重获自由后公众所表现出的那股激情,虽很强烈,但往往是短暂的,是不可靠的。“应当把一个国家的人民的自由建立在他们的生活中,而不能建立在他们的激情上,因为激情是转瞬即逝并适时改变它追求的目标的。一个良好的体制的力量,是体制存在它就存在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是只有珍爱自由才能长久地享有自由的”。[16]爱国主义政治美德饱含的正是对公民的自由、同胞的自由、政治共同体的自由具有期望的真挚情感。可见,爱国主义政治情感不仅是推动变革的动力,它还能够成为保存而不是摧毁“革命果实”的重要动力。
从公民—人类共同体的视角来看,作为将同情引入现代政治理论的思想家,卢梭其实是反对公民将同情扩展至共同体之外的“异邦人”身上的。他认为这样的“博爱”使人们忽略了身边那些真正需要关怀的人。反讽的是,号召让所有底层人民联合起来形成兄弟般情感的“博爱”,却成了以卢梭为精神标榜的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口号。确实,博爱要比一般的同情、甚至比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感,能够产生波及更大范围的强大革命号召力。激发世界范围内的博爱情感并使之升华的那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19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政治宣言——《共产党宣言》中最激动人心的口号。其实,早在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就主张培养一种较为激进的世界主义情感:人们应当首要认同由人类的共同人性价值构成的人类道德共同体,而不是首先认同特定形式的政府与世俗的政治权力。[17]古罗马正是以这一世界主义主张作为基本治国理念,注重实施民族、文化、地域融合政策并成功地实现扩张。一个世界城邦的雏形在西方政治史上得以初次显现。当然,斯多葛派世界主义理念的激进特质被它本身所强调的冷静与理性诉求所缓和。而且,它也并没有像卢梭担心的那样,因为注重博爱而主张放弃爱身边的同胞。它强调,做一个世界公民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自我、对特定传统、对所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而是要为政治—情感认同拓宽范围,使认同的内容丰富化。[18]换言之,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实质上沿循着自爱—爱他人—爱同胞—爱国家的情感发展进路,并将这样的情感拓展至爱世界与爱人类的广度,同情的内涵也在此发展过程中得到丰富。而对人性与人类基本价值的关怀,和力求以理性矫正激情的理念,却又使得这样激进的博爱观并不会采取一些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屈从于偏执和狂热的方式来实践。公民对人类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升华至对人性价值的高度认同,是造就“世界公民”、实现政治正义的重要动力,它对于极端的政治革命而言,也是有效的缓解剂。
[1][英]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84-85、317页。
[2][5][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2页,第56-57、103页,
[3][美]托马斯•潘恩:《常识》,曾尔恕等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22页。
[4][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62-63页。
[6] Jonh Halliwell, Richard Layard, Jeffrey Sachs (edt.), World Happiness Repor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SDSN), 2012, pp. 109-111.
[7][8][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41页。
[9]卢春红:《情感与实践——康德共同感问题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9、31-32、88页。
[10] Raoul Vaneigen, 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 Donald Nicholson-Smith (trans.), Rebel Press, 2001, p.26.
[1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1、65页。
[12]Linda Nochlin, Realism, Penguin Books, 1990, p.179.
[13]林锡铨:《政治美学》,台北:时英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14][法]卢梭:《论波兰的治国之道及波兰政府的改革方略》,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9页。
[15] Martha C. Nussbaum, 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 Belknap Harvard, 2013, p. 208.
[16][法]卢梭:《科西嘉制宪意见书》,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3页。
[17][18] Martha C.,Nussbaum with Respondents,For the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 Joshua Cohen (edt.), Beacon Press, 1996, p.7, p.9.
责任编辑:王雨磊
D02
A
1000-7326(2016)09-0074-06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校级青年科学研究项目资助(16ZFQ81001)的阶段性成果。
黄璇,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北京,102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