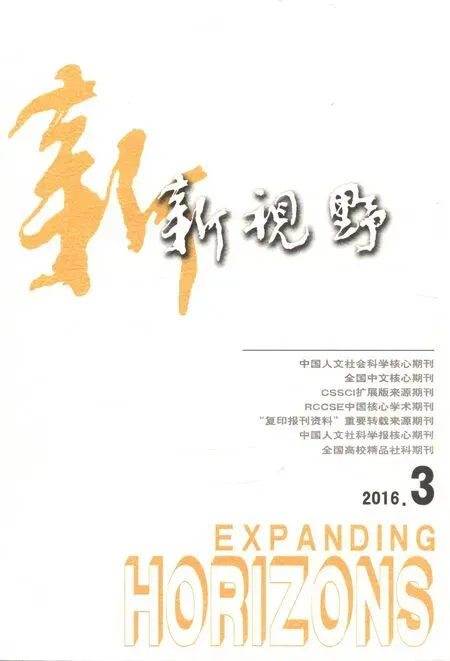社会组织进入村庄权力结构后的政治博弈分析
——以湖北G市“1+X”自治模式为例
文/贺海波 包雅钧
社会组织进入村庄权力结构后的政治博弈分析
——以湖北G市“1+X”自治模式为例
文/贺海波 包雅钧
摘要:当前,农村社会组织进入村庄权力结构、参与村庄政治博弈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事实。在湖北G市国家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村庄治理,建构起了“国家—村两委—农村社会组织—普通村民”四层主体的权力结构,每个权力主体都凭借各自的理性、利益预期和策略行动等参与村庄的政治博弈,但是农村社会组织成员的利益取向决定了各博弈主体预期利益的实现程度和新型村庄治理结构的存在状态。这种新型村庄权力结构中主体间的政治博弈是我国农村政治制度化和农村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
关键词:农村社会组织;村庄权力结构;权力主体;政治博弈
一 问题的提出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村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需要农村社会组织承担起相应的治理责任。农村社会组织近年来发展迅速,相关学术研究主要从以下几种理论视角进行解释:一是从“结构—功能”视角来看,农村社会组织内嵌于村庄结构内部,村庄结构的流变赋予农村社会组织功能,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创新对村庄结构也具有重塑作用。[1]二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从乡土社会中退场,但农村社会组织发育迟缓,难以规范和维护农民的利益,使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难以实现。[2]农村社会组织最为重要的是发挥自治功能,与其他一些基层组织形成共生合作局面,共同建构乡村社会的新公共性,从而再造乡土团结。[3]三是从治理视角来看,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是政府、村政权组织和农村社会组织共同努力的过程。当前在村级组织缺乏动员村民能力的语境中,尤其需要国家通过制度设计和资金支持来促进社会组织发挥积极治理作用。[4]但是当前农村社会组织呈现治理结构失衡的现象,可能会损害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5]因此,既要重视农村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正功能,又要预防其负功能。四是从社会组织化理论视角审视,当前农民的组织参与率非常低,主要是因为没有组织可依靠,但对于组织化有强烈的认同与期望。[6]因此,当下应积极探索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并扩大其组织效果,这关系到乡村社会秩序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发展战略问题。
综上可知,现有研究不断加深了对农村社会组织的认识,但是忽视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创新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向社会组织转移政府职能的大背景下,农村社会组织得到了大力建构,这些社会组织在承接了部分治理职能后就会拥有治理资源,在参与村庄治理中会与其它村庄权力主体展开政治博弈,从而会突破“乡政村治”背景下的权力配置与利益分配,进而会再造村庄权力结构。这一再造过程,可能是中国农村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二 政治博弈论:农村政治的一种分析框架
在长期的研究中,关于权力的定义经历了从“强力说”向“能力说”转移的过程,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接受了布劳的定义,即认为“权力是个人或群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7]在具体场域中,国家、集团、群体或个体等,只要能够依凭财富、地位、意志、价值观等物质与非物质资源控制别人就拥有了权力,就成为了一个权力主体。因此,村庄中的权力是指在村庄中某方面占据优势资源者在促成村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致行动中支配他人的能力。[8]国家、村庄精英、社会组织和普通村民等都可能会拥有这种支配能力,它们在互动中形成的稳定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或模式化关系就是村庄的权力结构。
村庄权力结构是理解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构件,是理解国家在村庄实施治理策略的关键。在研究传统乡村权力结构时,费孝通根据获得村庄认同的村庄权力所依凭资源的特点,区分了村庄中的同意权力、横暴权力和教化权力;杜赞奇提出了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国家、保护型经纪、赢利型经纪和普通村民在村庄舞台上依据各自拥有的权力进行博弈。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于现代村庄权力结构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一是从村庄内部各个权力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视角,有学者提出“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普通村民”的三层权力结构等;二是从国家与村庄关系视角,崔之元提出“上层—中层—下层”三层分析法、简·奥伊讨论了国家与农民的互动方式等;后来有学者将这两种分析视角进行整合,提出“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三层分析框架。[9]村庄权力结构的变迁体现了中国农村政治的发展进程。在一段时期内,村庄权力结构总会有相对稳定的主体,在博弈中各主体会获得各自的利益,也有可能实现村庄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这种为了村庄利益的分配或重新分配而不断博弈就是村庄政治发展变化的一种集中体现,这种现象可概括为村庄政治博弈。
结合博弈论自身的特点和在政治学领域的发展,政治博弈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应该主要包含如下要素:第一,局中人。实际参与政治博弈活动是辨识政治博弈者的唯一依据。换句话说,政治博弈者不仅是指实际参与政治博弈活动的人,而且还必须是正在参与的人,一旦退出博弈场域,就不再是政治博弈者了。政治博弈者均是理性人,是以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理性决策主体。第二,利益预期与策略行动。局中人的效用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利益,对于这些利益的可能获得感即为政治博弈者的利益预期。需要、价值观和政治资源是局中人利益预期的重要变量。如果利益预期为正值,政治博弈者就一定会去做这件事,此为趋利行动;如果预期利益为负值,他就一定会尽可能逃避或抑制去做这件事,此为避害行动。[10]这两种策略行动都是政治博弈者基于利益预期采取的理性行动。第三,政治博弈结果。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博弈结果就不同。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就应该注意政治博弈者利益预期的实现程度和对新的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
三 新型村庄权力结构的实践与政治博弈
当前,国家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迫切要求社会组织承担起乡村治理功能。湖北G市顺应形势,挖掘本地社会组织发展的经验,以行政手段进行推广,在乡村培育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农村社会组织进入村庄权力结构后,各权力主体间展开了博弈,不同村庄产生了不同的治理效果。
(一)社会组织进入村庄权力结构的实践
早在1993年,湖北G市湖村的袁少敏竞选上村支书后,想修村里的那条烂泥巴村道,无人响应。但是他发现村里由老人组成的“红白喜事理事会”在村民中很有影响力。受此启发,袁少敏发动村里“五老”人士,成立“村务理事会”牵头议事,并下设专项协会具体执行,袁少敏将它称作“1+X”自治模式。“1”是村务理事会,由村民推举25名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军人和老模范组成,“X”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的各类专项协会,最终形成村两委议事、村务理事会决事、专项协会办事的工作模式。
湖村的“1+X”自治模式引起了G市政府的注意,G市政府于2014年在全市农村社区推广,采取了以下两个重要步骤:首先,将“1+X”自治模式的推广纳入全市社会治理的总体部署之中。2014年G市市委、市政府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强城乡新型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意见》《孝感市城乡三类新社区建设工作推进方案》《关于全市城乡三类新社区三个“1+X”建设标准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明确将“1+X”自治模式嵌入全市城乡社区建设的总体目标、具体任务、建设标准之中。其次,落地建构“1+X”自治体系。在全市农村社区中推广“理事会+协会”自治模式,组建理事会451个,文明新风、互助自助等协会1736个,投入1000万元支持社会组织购买1500多台设备,扶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在当地政府主导推广中,各村都非常重视,纷纷建立了“1+X”自治体系,如J村村务理事会下设老年人互助活动协会、和事佬协会、路灯协会、安全饮水协会、民主理财协会等。
(二)新型村庄权力结构中的政治博弈
湖北G市在全市农村社区推广“1+X”自治模式后,就在村庄场域内建构起了“国家—村两委—农村社会组织—普通村民”四层权力结构。博弈主体都具有多重理性,每个主体多重理性的综合会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预期利益,促使主体采取特殊的博弈策略。主体的政治博弈决定了村庄权力结构的治理效果。
1.政治博弈主体的特点
当前乡村无治理的状态对农民的生产生活、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合法性等存在严重的负面影响,改善当前农村的治理衰败状况正是国家的理性所在。村两委是连接国家与农民的纽带,既是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制度,由农民选出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又是国家将政策制度法律在农村落实最终实现乡村良治的委托人和依靠者。因角色分化,村两委事实上具有三重理性:作为村庄当家人或村民自治的委托人,村两委需要最大限度保护和争取村庄的共同利益;作为国家治理村庄的委托人,村两委需要具体落实国家的法律政策制度等;村两委干部作为普通农民,也有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需求。
农村社会组织是基层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承担必要社会功能的共同体。理性系统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理性工具,组织的效率源于组织成员的理性。因此,农村社会组织理应最大限度地承担特定的社会功能,维护和实现共同体内部的共同利益,但组织成员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会影响组织理性的实现,特别是当组织成员的理性超越或凌驾于组织理性之上时,农村社会组织就会出现非理性行为。
当前农民处于快速的理性化之中,之前约束农民个体“搭便车”行为的传统力量越来越弱。农民这种理性化之变,实际上是遵循个体主义逻辑的农民个体理性的不断激活、膨胀和遵循集体主义逻辑的农民公共理性的不断抑制、萎缩的综合表现。农民的个体理性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公共理性追求村庄公共利益最大化。个体理性通常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选择维护个人利益,因此它是村庄治理的障碍因素。[11]农民正是在不断综合平衡其个体理性和公共理性的判断中参与到村庄政治博弈中的。
2.新型村庄权力主体间的政治博弈
湖北G市在农村社区创造了“国家—村两委—农村社会组织—普通村民”四层权力结构,四大主体各自依凭其优势资源相互博弈,并且形成了一个博弈链,即国家与村两委博弈、村两委与农村社会组织博弈、农村社会组织与普通村民博弈。博弈链条上的每一个互动环节都会影响到博弈整体结果。
(1)国家与村两委的博弈
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希望农村能够成为实现现代化的稳定器。市县镇对于乡村治理的预期就是不断提供满足农民需求的公共产品,从而化解矛盾,突破农村发展陷阱,改善治理现状,使农村保持良好的秩序。在利益预期推动下,一旦发现实践中有新的治理资源,市县镇就会利用规则的制定权和行政推广权,搞一场乡村治理的“变革”运动。湖北G市市政府就直接将推广“1+X”自治模式纳入改进全市乡村治理的总体部署之中,并以方案、通知和意见等行政命令要求乡镇出面指导或督促村庄建立各种协会。
面对国家绝对的治理权威和推进治理的强大行政力量,村两委的博弈力量很弱。按照村委会组织法,村委会是村民选举出来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只需对村民负责,将村民共同利益的增长作为利益预期,但实际上,在长期的利益磨合中,村两委已经将完成乡镇下达的治理任务当成自己的工作理性。如G市K村村支书说:
“1+X”模式在湖村是适合的,但每个村都这样做就不好了,村情不同,效果就不同。K村根本就没有路灯还要成立路灯协会,说的是先预备着,等以后有了路灯再发挥作用,但还是感觉比较可笑。
可见,村两委在面对上面压下来的任务时,首先是接住并且尽量按要求搞出形式来,即便发现有问题,也只是私下说说而已。村两委在与国家博弈中采取如此策略,主要是因为处于压力型体制的末端。也就是说,继续当村干部的利益预期使村两委干部不大可能代表全村村民与国家进行正面政治博弈。
(2)村两委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博弈
与国家博弈中处于劣势不同,村两委在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博弈中握有主动权。因国家和底层社会的双重赋权,村两委拥有治理村庄的合法性,并掌握如何治理村庄的话语权和具体操作权。但在当前的治理实践中,农村的治理资源不断流失,村两委在具体问题上常常显得无计可施。在这种情境下,村两委维护村庄公共利益的理性需求并不强烈,对于治理村庄的利益预期并不高,大多数村两委只想做一个维持型的村庄当家人。也正因此,村两委在博弈中对社会组织采取了消极态度:首先,牢牢把握对农村社会组织的领导权。农村社会组织要在村两委的指导下开展工作,村两委仍然是村庄治理的核心,并且不允许农村社会组织去动摇这个核心。其次,并不积极想办法鼓励社会组织成员参与村庄治理。正如J村的村干部所说:
协会都没有什么用,只是挂块牌子而已。有些协会成员根本不上心,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来一下,平时有什么事情要处理,无论怎么喊都不来。
农村社会组织的理性是通过承担某项社会治理职能,维护村庄共同利益,使村庄保持良好的秩序。但是社会组织的策略行动不仅受社会组织利益预期的决定,还要受社会组织成员个体利益预期的影响。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村务理事会和各类专项协会大多由“五老”人员组成,在参与村庄治理中这些老同志可以满足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如果他们感觉这些需求的份量要超过所付出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就会配合村两委积极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来;如果他们感觉两种需求的满足是得不偿失的,就找各种借口不参加活动。从某种程度而言,农村社会组织掌握了与村两委博弈的主动权,因为参与村庄治理的利益所得与所失都与村两委关系不大,完全是社会组织成员自身需求和价值观选择的事。那么,村两委与社会组织的博弈就是一件相互没有压力的、社会组织具有更多选择权的博弈。
(3)农村社会组织与普通村民的博弈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村庄治理所拥有的治理资源具有确定性。在“1+X”自治模式中,村务理事会和各专项协会拥有两种治理资源:一是国家和村两委认可的参与村庄治理的正当性。在湖北G市,农村社会组织是由国家和村两委推动建立起来的,自产生之日起就拥有了国家和村两委授予参与村庄治理的权力。二是普通村民的信任与认同。在熟人社会内部,社会组织成员大多是德高望重的“五老”人员,他们熟悉村民的个性特点和村庄内部的情况,在处理村庄事务、调解村民纠纷时能做到情理法的统一。根据利益预期和所拥有的治理资源,农村社会组织在与村民互动中常采用两种策略:一是讲道理讲人情。农村社会组织利用国家和村两委所赋予的治理正当性,可以理直气壮地进入特定场域用法律和地方规则来校正村民的认识,用村庄人情来软化村民的固执,从而化解治理问题;二是“吃亏”策略。在讲道理无效时,社会组织成员常通过让自己吃亏来“逼”村民改正。如湖村环境卫生协会一位成员发现村民乱丢垃圾,多次讲道理无效,他就提着垃圾袋跟在乱丢的村民后面捡。这使村民不好意思再乱扔垃圾了。
在理论上,普通村民是村庄权力的所有者,是村庄最为重要的主体,但村民快速增长的个体理性,使村民常处于分散与无组织状态,在村庄治理中往往成为国家、村两委和村庄社会组织的治理对象。对于农村社会组织的治理措施,普通村民常有两种对应的博弈策略:一是用脚投票。在面对农村社会组织的治理行动时,普通村民会迅速地感知这种治理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利益偏好,然后决定多大程度参与其中。如果发现与自己的利益无关,就会使用“弱者的武器”,冷漠对待,有时会刻意回避。如果发现有增于或无损于自己的利益,就会适当参与治理活动。二是形成民意压力。对于农村社会组织的长期村庄治理活动,普通村民会形成一个总体性感知与评价,以促使农村社会组织调整博弈策略以弥补治理的失败和进一步创新治理策略。
3.政治博弈结果
在湖北G市大力推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实践中,最终各主体利益的实现出现了不同的状况。一种是以湖村为代表的村庄,社会组织发挥了预期作用,各主体基本获得了预期利益。国家实现了将社会组织纳入村庄权力结构使其成为村庄治理重要力量并真正改善乡村治理效果的预期目标。村两委完成了乡镇的工作任务,找到了村庄治理的承接者,提升了村两委的信任度,实现了村庄治理的好转。普通村民享受到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农村社会组织承担了一些村庄治理功能,维护了村庄的公共利益和良好秩序,其成员获得了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另一种是其它大多数村庄,农村社会组织只是从形式上得到了建构,但没有真正发挥公共治理作用,各权力主体的预期利益只是一种概念上的利益。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组织中有些成员会计算“满足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成本——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和人际关系成本。在比较成本收益之后,大多数社会组织成员都不再积极参加村庄治理活动了。正因如此,在大多数推广“1+X”自治模式的村庄中,农村社会组织的治理作用发挥有限。
结 语
当前湖北G市在全市农村社区建构的“国家—村两委—农村社会组织—普通村民”权力结构能否成为村庄治理的稳定结构,关键是看权力结构中各主体在相互的政治博弈中能否实现一定的利益预期,而各主体预期利益的实现程度又要看农村社会组织成员是否仅仅满足于“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精神利益。如果农村社会组织成员满足于精神利益,不计较付出的成本,并积极参与村庄治理,则其他政治博弈主体就能够获得一定的预期利益,这种村庄治理结构就可以长期而稳定地存续下去,国家在农村政治方面所建构的政策就可以存续并发挥良好的制度性作用。
注释:
[1]李志强、王庆华:《“结构—功能”互适性理论:转型期农村创新社会管理研究新解释框架——基于农村社会组织的维度》,《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2]刘鹏:《浅论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的现代化》,《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5期。
[3]吕方:《再造乡土团结: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新公共性”》,《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4]汪锦军:《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政府、村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角色》,《浙江学刊》2008年第5期。
[5]刘宁、黄辉祥:《组织维稳与集体失范:农村社会组织角色冲突分析》,《东南学术》2015年第3期。
[6]谭江蓉、乐章:《社会管理视角下的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基于十省市千户农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农村经济》2012年第10期。
[7]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37页。
[8]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9]金太军:《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
[10]古洪能:《政治博弈论》,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年,第112、145页。
[11]谢迪、吴春梅:《农民理性、村庄治理与农村公共服务效率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省为例》,《农村经济》2015年第6期。
责任编辑 余 茜
作者简介:贺海波,湖北工程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孝感市,432001;包雅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北京市,100010。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农村社会自治能力增长研究——以孝感市为例”(15Q203)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6)03-008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