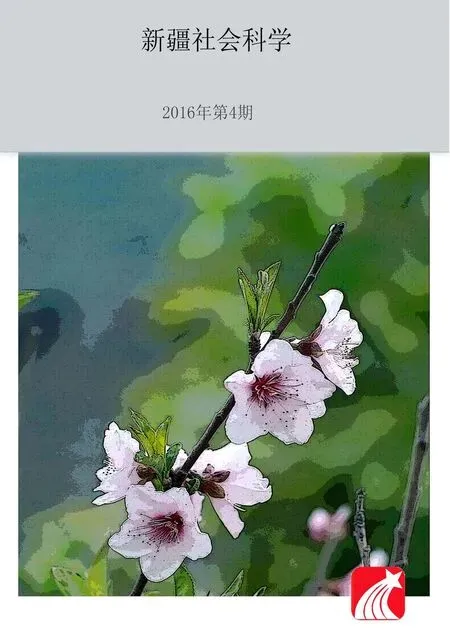论恐怖活动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司法适用
阿不都米吉提·吾买尔 商浩文
论恐怖活动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司法适用
阿不都米吉提·吾买尔 商浩文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的恐怖活动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这不仅有利于我国依法打击日益严峻的恐怖活动犯罪,也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的要求。但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恐怖活动案件范围界定、证明标准、国际司法合作等相关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并深入研究和探索。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恐怖活动犯罪 证明标准 国际合作
一、前言
新《刑事诉讼法》第280条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在笔者看来,确立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恐怖活动的资金是恐怖组织得以生存、发展和从事恐怖活动的基础,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恐怖活动根本无法进行,因此,反恐要取得成功必须遏制恐怖活动的资金。*商浩文:《英国涉恐资产冻结法律制度介述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时代法学》2014年第4期。在恐怖活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的情形下,由于在我国刑事诉讼相关法律中尚未确立缺席审判制度,无法对逃到境外或者是死亡的恐怖活动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裁判。确立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特别是对于那些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有效地斩断恐怖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资金链,消除其再次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经济基础,防止其再次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因而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对于恐怖活动犯罪的防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针对恐怖活动犯罪确立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但是该程序在适用对象、证明标准等方面尚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讨。
二、恐怖活动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
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针对恐怖活动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经定罪的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对于恐怖活动犯罪而言,适用该特别程序的关键之一是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由于在我国相关立法中关于恐怖活动犯罪的界定还是一个盲区,因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困难。在我国刑法体系中,恐怖活动犯罪是一项类罪名,包含若干具体的罪名。虽然在我国有关立法文件和司法文件中经常有“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犯罪”等专门术语的表述,但是立法中尚未有统一、明确、权威的界定,因而正确适用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的特别没收程序,需要我们进一步明确恐怖活动犯罪的范围。在笔者看来,恐怖活动犯罪行为和情节较为复杂多样,很难对其概念作出明确界定。但是,我们可以依据恐怖活动犯罪的特点明确其适用范围,在认定过程中,既要以刑法典中相关犯罪构成为基础,也要结合相关法律中关于 “恐怖活动”等概念作出判断。*杜邈:《恐怖活动犯罪的司法认定》,《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一)恐怖活动犯罪的界定必须以“恐怖活动”的认定为基础
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反恐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第2条对“恐怖活动”进行了界定:“恐怖活动是指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以及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的行为。”我国公安部2012年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明确了“恐怖活动犯罪”是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犯罪,以及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的犯罪。然而,2015年12月27日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修改了恐怖活动的概念,并同时废止《关于加强反恐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那么,现在对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应如何理解?这就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及时予以明确,否则容易造成司法适用中的混乱。
《关于加强反恐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对“恐怖活动”概念的界定侧重对该行为危害性的描述,并没有明确“恐怖活动犯罪”的范围。但是从《反恐怖主义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恐怖活动犯罪一般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通常表现为暴力、破坏、恐吓等直接危害行为,包括了恐怖活动犯罪的组织行为、预备行为、施行行为等,比如,以暴力实施的故意杀人、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等等;一种为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的行为,如资助恐怖活动罪、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以及《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帮助恐怖活动罪,等等。前一种是最为直接的恐怖活动犯罪行为方式,后者则是此种恐怖活动犯罪的帮助行为,因此,恐怖活动犯罪不仅仅包括这些直接的危害行为,还包括依靠人力、资金、犯罪工具等予以实施谋划、准备的行为。纵观我国现行刑法典,只对其中部分恐怖活动行为规定了专门的犯罪,对于其他恐怖活动犯罪则以分裂国家罪、故意杀人罪、爆炸罪等一般刑事罪名予以处罚。对于刑法典中已经有明确规定的恐怖活动犯罪直接适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当无疑义,但是对于没有明确规定为恐怖活动的行为,如以故意杀人形式的恐怖活动犯罪,司法机关需以有关机关认定其为恐怖活动作为依据,进而适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
(二)主观要素应当作为认定“恐怖活动犯罪”的关键
对于我国刑法规定的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由于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条款与《反恐怖主义法》关于“恐怖活动”界定不一致,基于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的原则,那么对于“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条款很难认定。故而无论是专门的《反恐怖主义法》还是刑法典均未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范围作出规定,需要国家立法机关予以明确。笔者认为,应当将主观要素作为认定“恐怖活动犯罪”区别于一般刑事犯罪的关键。
“恐怖活动犯罪”与一般刑事犯罪最为关键的区别是犯罪人主观目的的不同。虽然学术界对于恐怖活动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但我国《反恐怖主义法》第3条对上述犯罪的目的进行了界定,该条款规定:“恐怖主义是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主张和行为”。且《反恐怖主义法》第2条以宣誓性条款规定:“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以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煽动仇恨、煽动歧视、鼓吹暴力等极端主义,消除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由此可见,上述犯罪属于刑法中的目的犯,司法机关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对于其他犯罪行为,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放火等案件除了按照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予以认定外,还应当认真考察犯罪人是否具有特定目的,进而认定是否属于特定种类的犯罪。这样就需要相关主管机关依据相关的组织和人员所提出、宣传或者追求的活动目标或者后果来判断相关活动的性质,进而确定是否属于恐怖活动。*黄风:《金融制裁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第173页。恐怖活动犯罪的直接目的是积极追求侵犯人身、财产等具体法益,其根本目的是制造社会恐慌、危害社会秩序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进而达到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和主张,而这些主观目的是很难为普通的犯罪所能涵盖的。*赵秉志、商浩文:《论我国恐怖活动犯罪刑法制裁体系及其完善》,赵秉志、张军、郎胜主编:《现代刑法学的使命》,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17页。
从我国的反恐局势来看,“三股势力”具有鲜明的宗教狂热、暴力恐怖和民族分裂的特性,往往利用信教群众对宗教的虔诚、少数民族群众对本民族的归属感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此,当前恐怖活动犯罪的主要威胁是以分裂国家、宗教极端思想为犯罪意图的恐怖活动,因而司法实践在具体认定恐怖活动犯罪案件时,除准确认定危害行为的类型外,还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注重从主观上以分裂国家、宗教极端思想为犯罪意图的犯罪来认定恐怖活动犯罪,以凸显相关案件的恐怖主义性质。
三、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
(一)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理论纷争
对于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当采取何种证明标准,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也不甚明确,在学术界对此也有较大争论。目前学术界主要观点有:一是“证据确实、充分,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特别程序,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一般规则的约束,据此,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也要达到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即要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陈卫东:《构建中国特色刑事特别程序》,《中国法学》2011年第6期;郭大磊、吕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问题研究》,《犯罪研究》2014年第2期。二是“优势证据”证明标准,主张采用这一证明标准的学者认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对物而提起的诉讼,本质上不属于刑事程序,而是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没收程序,据此,对此不应该采用刑事诉讼的“证据确实、充分,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而应该采用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证明标准。*万毅:《独立没收程序的证据法难题及其破解》,《法学》2012年第4期;周晓永:《检察机关适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思考》,《人民检察》2013年第6期。三是采用混合证明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没收违法所得程序中存在两种诉讼关系:第一种是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恐怖活动犯罪,这是典型的刑事程序,据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恐怖犯罪的事实应当采用“证据确实、充分,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第二种是在有其他利害关系人主张该财产是其合法所有的情况下,查明拟没收财产的所有权归属的诉讼关系,从性质上来看,这种诉讼关系属于财产权的归属问题,属于典型民事确权争议,其证明标准需要达到“优势证据”程度。*③ 郭旭:《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司法适用与完善》,《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4年第5期。
(二)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基于刑事程序的视角
对于违法所得程序的证明标准,学术界之所以出现以上诸多争论,是因为对违法所得程序的性质定位有不同的认识,因此,在探究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程序证明标准之前应当对该程序的性质予以厘清。笔者认为违法所得程序应当是刑事程序,理由在于:首先,从立法宗旨上看,我国增设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主要目的在于有效惩治和预防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恐怖活动犯罪,尤其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逸或死亡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其违法所得财产予以追缴,从而克服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逸等原因导致的诉讼障碍,保障刑事诉讼目的的顺利实现。其次,从诉讼性质上看,违法所得没收裁判具有惩罚性,有学者认为判断一种程序是民事程序还是刑事程序,主要看该程序所作出的裁判是否具有惩罚性和威胁性,一般民事程序的性质是救济性和补偿性的,而刑事程序的性质是惩罚性和威胁性的,*初殿清:《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性质与案件范围》,《法学杂志》2013年第8期。从违法所得没收裁判的性质上看,其裁决具有明显的惩罚性,甚至有学者认为法院作出的违法所得没收裁定属于量刑环节中的“财产刑”。③再次,从诉讼的程序特点来看,违法所得程序的申请主体是人民检察院,即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追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法所得财产的没收申请;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负责审理;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出庭并负有举证责任;对于人民法院的没收裁定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抗诉。从这些诉讼流程和特点来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不同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程序,而属于刑事程序。
综上所述,无论从立法宗旨、诉讼性质或诉讼程序流程来讲,违法所得程序属于刑事程序,因此,对此不应该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的证据规则,而应当适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即“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另外,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人民法院对恐怖活动犯罪适用违法所得程序时是否要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如果要查明犯罪事实,对其是否要采用“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此,有学者认为为了保障公民的财产权、防止国家权力滥用,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等事项的证明必须达到定罪的证明标准,*吴光升:《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若干检讨》,《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这里的定罪证明标准就是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的 “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笔者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5条第2款的表述,可以得知人民法院在恐怖活动犯罪中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时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等事项进行审查,相应地对它的证明也应当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程度,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事实的审查应当限于程序性审查,而不应当对犯罪事实的实体问题进行审查,理由在于: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未经定罪程序而对与犯罪有关的财产予以没收的特殊程序,该程序的重点不是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而是追缴其与犯罪有关的违法所得财产。如果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进行实体性审查,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逃逸或死亡,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事实的实体性证明极为困难,相关人民法院的法庭审查也会陷入困境,这显然不符合该程序的特性,也有违于该程序的立法宗旨。据此,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对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审查时,检察机关对犯罪事实只进行程序性证明就足够。这里的“程序性证明”指检察机关在法庭上通过出示立案决定书、撤销案件决定书、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等程序性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曾经或正在受到刑事追诉,*万毅:《独立没收程序的证据法难题及其破解》。而现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通缉一年不能到案或已经死亡的事实确实存在即可。
四、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国际合作
(一)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国际司法合作的依据
1.国内法层面的依据
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国际司法合作的国内法依据主要包括《刑事诉讼法》《反恐怖主义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如 《引渡法》《洗钱法》等。具体而言:一是《刑事诉讼法》第17条规定。我国司法机关进行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国际司法合作的主要根据是我国缔结的国际条约,如果没有同我国签订相关刑事司法协议或者没有与我国参加某一个司法协助条约,也应该根据互惠原则进行司法协助。二是《反恐怖主义法》。该法第7章专门就恐怖案件的国际合作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为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国际司法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2.国际法层面的依据
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发展历史看,违法所得没收国际合作的产生是在引渡、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产生之后。*蒋秀兰:《没收国际合作的发展沿革》,《西部法学评论》2011年第4期。目前,世界各国通过联合国有关国际公约、双边国际条约和其他的国际法互惠原则等方式来实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引渡和境外违法所得资产的移交或返还问题。就国际法层面而言,有关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国际司法合作的主要依据:一是国际公约。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公约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依据,我国加入的有关违法所得没收方面的国际公约主要有《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13条对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中对违法所得没收裁定在其他国家的执行情况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该条第1项规定:“缔约国在收到对本公约所涵盖的一项犯罪拥有管辖权的另一缔约国关于没收本公约第12条第1款所述的、位于被请求国领土内的犯罪所得、财产、设备或其他工具的请求后,应在本国国内法律制度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将此种请求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取得没收令并在取得没收令时予以执行;或将请求缔约国领土内的法院根据本公约第12条第1款签发的没收令提交主管当局,以便按请求的范围予以执行,只要该没收令涉及第12条第1款所述的位于被请求缔约国领土内的犯罪所得、财产、设备或其他工具。”《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确立了资助恐怖主义活动的犯罪性质。根据该公约序言的规定,其主要宗旨是增强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并以此断绝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二是区域性公约。如《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该公约作为我国和中亚地区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的重要区域性公约,在维护该地区安全形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该公约在违法所得没收财产的司法合作方面作出了框架性规定,如该公约第8条第1项规定:“基于提供协助的请求,或经一方中央主管机关主动提供信息,各方中央主管机关在本公约范围内,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进行相互协作”。三是双边条约。双边条约主要是指我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协定。我国目前已签订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有49项,引渡条约有36项,*根据外交部条法司2013年统计的数字。其中大多数条约对违法所得财产的追缴和移送方面予以规定,如我国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先后签订了有关刑事司法协助的双边条约,为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司法合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国际司法合作存在的不足及其完善
就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关国际司法合作的内容而言,我国目前与国外进行刑事司法合作的主要方式是代为送达刑事司法文书、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引渡与遣返和其他各类司法协助。*宋英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精解》,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对于刑事案件国际司法合作的重要内容——外国刑事裁判的承认和执行,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法规未作出任何规定。就国际条约而言,国际司法合作的主要途径——双边司法合作相关条约中对民事裁判的相互承认和执行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对刑事裁判的相互承认和执行未作出明确规定。*如我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就民事裁判的相互承认和执行作出了规定,但对刑事裁判的相互承认和执行未作出规定。当恐怖活动犯罪的犯罪所得、犯罪收益和犯罪工具等违法财产在境外的情况下,如果我国司法机关作出的违法所得没收裁定不能得到违法财产所在国的承认和执行,那么这不仅不利于该制度预期目的的实现,也不利于有效打击和预防恐怖活动犯罪。因此,笔者认为为了有效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斩断恐怖活动犯罪的资金链条,我国也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作出承认和执行国外刑事裁判的相关规定,并以此为基础在相关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对各国互相承认和执行刑事裁判予以确认。对国外刑事裁判的承认和执行,部分国家在《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中作出了明确规定,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对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裁判的原则、程序、条件以及一些具体的规则作出规定;德国就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制定了专门法律——《刑事司法协助法》,在该法律中对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裁判的相关条件作出了规定。*黄风:《刑诉法应增加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制度》,《现代法学》2007年第2期。据此,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当借鉴域外经验,在《刑事诉讼法》或者其他相关法律中对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裁判的条件和程序作出规定,为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司法合作奠定基础;另外,为了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司法合作的顺利推进和争取相关国家司法合作的积极性,在具体司法合作时也可以通过确立分享资产制度,确保恐怖活动的犯罪所得、犯罪收益和犯罪工具等违法财产的没收和返还,进而达到进一步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斩断其资金链条的目的。
责任编辑:万小燕
D925.2
A
1009-5330(2016)04-0096-06
阿不都米吉提·吾买尔,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北京 100875)、新疆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新疆乌鲁木齐 830017);商浩文,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 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