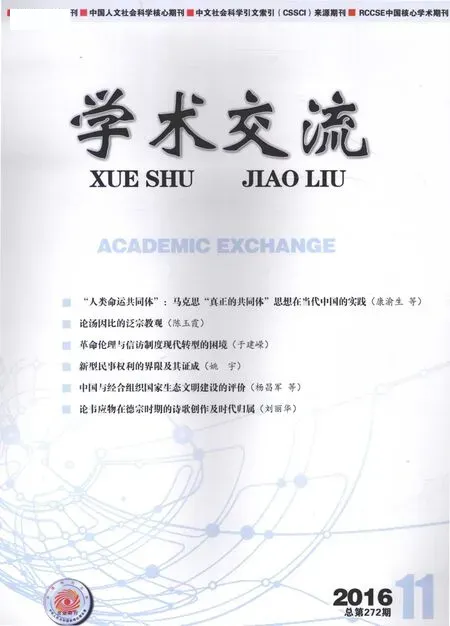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共生的共产主义
朱松苗
(运城学院 中文系,山西 运城 044000;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武汉 430072)
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共生的共产主义
朱松苗
(运城学院 中文系,山西 运城 044000;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武汉 430072)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产主义这个词的确切所指既不是粗鄙的共产主义所理解的共同拥有私有财产或共同进行物质劳动生产,也不是它所理解的共妻,而是共生,即共同生存、共同生成。这是因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来,人及其本质是不断生成的,进而共产主义也是不断生成的——它是通过人的创造性物质生产劳动,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的共在中生成的。一方面,自然、社会的内涵只有在人的世界中才能被完全揭示出来,并显示其意义;另一方面,人也只有在自然、社会中,其本质才得以生成,并且只有通过它们,其本质力量才显现和确证,人的真正的生命才得以不断的出场和实现。因此作为共生的共产主义既是指人的生存、生成,也是指人与自然、社会的共同生存、生成,所以它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诸多矛盾的真正解决。
共生;社会;共产主义
众所周知,共产主义既是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高理想,但是由于粗鄙的共产主义思想的误导,人们很容易误解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内涵。我们通过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共产主义一词自身含义的分析,发现在这个文本中,真正的共产主义并不是粗鄙的共产主义所理解的“共产”和“共妻”,而是作为“共生”的共产主义。
一、被遮蔽的共产主义
根据威廉斯的考察,Communism(共产主义)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Communis,而Communis这个词源自拉丁文com-(意指“一起”)与拉丁文munis(意指“有义务”),或是源自com-与拉丁文unus(意指“一个”)。[1]70这种词源学上的丰富性使得Communis一词具有了多种意味:首先,它意味着Communism(共产主义)一词本身就含有“一起”享“有义务”即共有义务的含义,这在《手稿》中表现为人按照人所当是的内在规定要求去实现自己;其次,它还意味着Communism(共产主义)原本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共同形成的,具体到《手稿》中,这既意味着此种“聚集”不仅具有同一性,而且具有差异性,同时也意味着这种“形成”不是机械、外在的组成,而是自觉、有意识的内在融合。
两种词源学上的解释虽然看似毫不相关,但实际上却共同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前缀com-,即一起、共同之意,而在汉语语境中,“共”和“同”是同义词,《说文解字》解释“共,同也”[2],所以将“共同”简化为“共”是合适的。作为副词,“共”即一起、共同之义;如果衍变为动词,“共”则可以理解为共享、共用或共有。这体现在粗鄙的共产主义的“共产共妻”的表述中。
问题在于,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共”所指向的是“共产共妻”吗?在粗鄙的共产主义看来,所谓“产”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私有财产,二是指物质劳动生产。据此,粗鄙的“共产”也相应具有了两种含义,一是指共同拥有私有财产,二是指共同进行物质劳动生产。但是在《手稿》中我们发现,这种理解很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或否定的内容。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在粗鄙的共产主义看来,“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3]79,而在马克思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所谓“占有”并不是“物质的直接占有”,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81;与之相应,它也不是对作为私有财产的人(妻)的直接地、身体性地占有。所以真正的共产主义不是简单的对实物世界的占有,而粗陋的共产主义却正好相反。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的“共产共妻”不过是人的卑鄙性的体现,因为它实际上来自人的“嫉妒心”和不劳而获的“平均主义”[3]79思想。这种“忌妒”一方面表现为它对于私有财产的否定,也即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3]79;另一方面表现在它由于“忌妒”而产生的对私有财产的平均化上——这与其说是反对私有财产,不如说是想占有别人的私有财产,所以说到底,它“是贪财欲……用另一种方式使自己得到满足的隐蔽形式”[3]79。因此不管是对私有财产的直接的否定——消灭,还是间接的否定——平均化,或者说平均化不了的就直接消灭,实际上都只是其“卑鄙性”的体现。
如果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是劳动的话,那么,由这种“忌妒”所形成的对他人私有财产的占有实际上是占有了他人的劳动,这也是一种异化劳动,而且是一种更为堂而皇之的异化劳动。随着这种“忌妒”的普遍化,它会导致异化劳动的普遍化,即私有财产的普遍化。每个人的劳动成果都被他人占有,所以“工人这个规定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3]79。
其结果是人的差异性被否定,人们只是片面地追求人的同一性,“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抛弃……到处否定人的个性”[3]79,而且这种同一性是“人的力量已经被减少成最小公分母”[4]的那种同一性,即共同贫穷,这不仅仅是指物质上的匮乏,而且是指精神上的贫乏——所以,它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3]80。因此,真正的共产主义强调人的差异性和个性,它虽然强调“共”,但不否定“个性”,这既是因为如果失去了独立的个性,所“共”之物就只有贫穷和“倒退”;同时也在于,如上所述,从字源学上看,共产主义原本是指由独立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共同形成的,“共”原本就是由丰富性的“个性”有机的结合而来的。
正是因为此,物质劳动生产的共同性和工资的平等性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没有可能,甚至会适得其反——所谓的“共同性”可能会扼杀人的个性,所谓的“平等”可能会造就真正的不公。
既然真正的共产主义不是粗鄙的共产主义所理解的“共产共妻”,那么它究竟是“共”什么呢?
二、作为共生的共产主义
(一)何谓共生?
让我们从马克思本人在《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出发:“共产主义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范围内生成的。”[3]81
如果说共产主义就是指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的复归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究竟意味着什么?二是如果共产主义就是“人的复归”的话,为什么这种“复归”又是“生成”的?而在此之前,我们还要追问马克思究竟是如何理解“人的本质”的?在《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是将“人的本质”作为一个预先存在的概念来对待的,因为他在文本中多次提出这个概念,如“劳动对工人来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等等,但是这个屡屡被提及的“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却语焉不详,它只是在与动物的相比较中存在,也就是说它没有具体的内容,只是抽象的存在;另一方面, “人的本质”在《手稿》中又被认为是不断发展即不断生成的——即“人的发展的本质”[3]63。具体而言,它是在人的物质生产劳动中不断发展、生成的,由于人的劳动是不断发展的,所以它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古尔德认为,对于马克思而言,人的本质是一种“自身不断变化的作为这个活动结果的本质”[5]。
这说明,在《手稿》中马克思首先预设了一个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一样的抽象的概念——人的本质,也唯有如此,人才能“复归”这个本质,但这个本质只有在人的物质生产劳动中才能从从抽象变为现实,才能真正将这个概念所具有的潜能全部发掘出来,才能真正地实现它自身,即“人的本质”才能真正地生成出来——所以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3]113。
这样一来,前两个问题便迎刃而解。所谓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实际上是指现实的、实际的占有——这正好符合Actual[6]的本义——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式的占有。后者是人与生俱来的,因为“人”这个称谓本身就将他与动物区分开来,所以这种占有实际上是形式上的占有,只有经过不断的生产劳动实践,前者才能完成。而“人的复归”也不是要复归到抽象的人性中去,而是要复归到具体的、现实的也即“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范围内生成的”的人性中去。
综上所述,对于马克思而言,不仅共产主义的核心内容即人(的本质)是不断生成、不断实现的,而且就连(或者说正是因为此)共产主义自身也是不断“产生”和“生成”的,因为历史的运动既是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3]81,因此鲍·斯拉文认为它是一个“历史过程”[7]。所以真正的共产主义中的“共”在马克思《手稿》中是指向“共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同于粗鄙的共产主义的“共产”,也不同于其“共妻”。那么,何谓共生呢?
它首先是指共同生存。这意味着:第一,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者,他必须与他人、他物共在。这既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含有“共同”“一起”之义,暗示了人的存在状态——人不是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存在,而是共在——存在于“共”中;同时,这也符合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思想,因为他反复强调人是社会的动物。第二,这种共在不同于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共在”,它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共在,而是建立在平等关系上的共在。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在”正好呈现出这种不平等关系,从而造成了人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即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产生,进而造成了人的异化。第三,即便是建立在平等的关系上,这种共在也可能是一种消极的共在,即这种“共在”只具有联合的意味,有可能只是一种外在的联系——肩并肩的关系。原始社会中的人也具有“共在”的特点,即共同生存,但这种“共在”只是一种消极的、迫不得已的共存,是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一起的联合,而不是积极的共存——以人的生成为目的。
所以真正的共生不仅意味着共同生存,更意味着共同生成。这种“共生”是一种内在的联系,是一种融合,即彼此亲密相契、相互补充,也是一种“共与”[8],即共同(相互)给予、相互构造(创造)、彼此生成。正是在此意义上,《手稿》中的“共”不是作为动词出现的,而是作为副词存在的,因为它所“共”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一种状态。故而,“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3]93。因为它只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共”在的状态,不仅共同生存,而且共同生成的生活的存在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人才能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和对人的人性的复归——这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相反,粗鄙的共产主义所理解的“共”——共产共妻,误将“共”作为动词使用,因此就出现了“共”的具体的对象——“产”(财产)和“妻”,并且又将所共之对象只是作为物来占有和利用,而没有将它们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和完成,所以对它们的占有实际上与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性的复归完全无关,相反,它否定了人的人性(个性),增加了人的动物性——即“把妇女当作共同淫欲的虏获物和婢女来对待”[3]80。再一方面,即便“产”在这里是指物质劳动生产,亦即“共”是作为副词使用,这也不符合《手稿》的原意,因为从本质上讲,《手稿》中的共产主义与其说是要追求物质的共同生产,毋宁说是要寻求人的共同生成。所以粗鄙的共产主义还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二)为何共生?
如果说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共生”的话,那么,究竟是谁和谁共生呢?一方很显然是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讨论才有意义,关于另一方,对于马克思而言,就是社会(他人)与自然,因为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就是在与社会(他人)、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生成的,反过来,社会、自然也是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生成的——彼此相互生成。
1.人与社会的共生
“社会”在这里不是指具体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社会,既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史前社会、阶级社会意义上的社会,甚至也不是指我们通常所讲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而是指社会的本性,即合乎“人性的”存在状态——因为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3]81。那么这种“人性”的存在状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根据威廉斯的考察,Society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socius,意指同伴;到18世纪末,society意味着“生命共同体”;到了19世纪,society的其中一个含义为“相互合作”;Society的最后一个明显的用法,是指一个人与其(所属阶级里*这种“阶级”的限定是《手稿》所反对的,因为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手稿》对“国家”的批判实际上是认为这种“深厚情谊”是超阶级的。)伙伴间的深厚情谊[1]446-451。综合以上种种解释,社会的真正、完整含义应该是:有着深厚情谊的同伴由于相互合作所形成的生命共同体。
如果是这样的话,《手稿》中“社会”的完整理解应为社会共生体,即人(性)的共生体,是所有人生存、生成的生命的共生体,故而,它不同于国家、家庭和宗教,“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3]82。因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只是一个“阶级共生体”,具有阶级的局限性;而家庭是一个“血缘共生体”,具有血缘的局限性;宗教是一个“信仰共生体”,具有信仰的局限性——它们都是有限的共生体,甚至是排外的共生体,都是对“人”的一种片面乃至狭隘的理解。而社会共生体是普遍的、相互合作的、情谊深厚的“生命共生体”,是所有人的符合人性的共生体。
所以我们不能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3]84。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不是一种外在、形式上、机械的组成,而是一种内在、本质、有机的生成;不是一个凌驾于个人之上、盘踞于个人之外的抽象的概念,而是人的具体、现实的存在状态。故而个人与社会之间不是对立,而是合作。这种合作也不是外在的联合,而是内在的融合:个人居于社会之中,社会也存在于人之中。因此,人与社会是共同生存、生成的,社会生产人,人也生产社会。而对于《手稿》而言,人与社会的关系又可以具体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社会中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也是一种共同生存、相互生成的关系。
(1)人需要社会(他人)
对于马克思而言,个人之所以是社会存在物,就在于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成为人,不仅人的生产活动,甚至整个人的存在、思想和语言都是在社会中形成的。[3]83而且,这个社会不仅是当下的社会,即人与之直接打交道的社会,这是人的生存、生成的当下资源;同时也包括历史上的社会,“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决不仅仅存在于直接共同的活动和直接共同的享受这种形式中”[3]83,这即是说,人的生存、生成还具有历史的资源,不仅如此,它们甚至是人的存在、思想和语言的更为本源的本源。
这种人与社会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被具体化为人与人的关系。如果说人是在社会中生存、生成的话,这又具体化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生存、生成。这种交往不仅仅只是物质性的交换,更是人性的相互给予、相互塑造和相互补充。个人通过与他人交往,不仅可以得到生存得以继续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人交往,我们可以真正地占有他人已经生成的人的本质(如才能、精神、思想、语言、感觉),“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称为我自己的占有”[3]86,从而促成自身的人的本质的生成,所以这种交往既“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3]82,即这种交往既为己,也为人。
同时,这种“交往”不仅仅只是指与他人的直接的现实的交往,也包括间接的交往,如“科学活动”[3]83,这种活动虽然很少和别人直接联系,但它本身是凝聚了前人和今人智慧结晶的活动,我虽然不直接与之交往,但这种智慧的传承和交流是存在的,我的活动是间接地建立在他人活动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他人的活动,就没有我的活动。
也就是说,只要“我是作为人活动的”,我必然与他人打交道,这个“他人”不仅仅是指我们现实地直接与之打交道的人,而且包括我们不直接与之打交道的现实生活中的他人和历史上的他人。
(2)社会(他人)需要人
同理,对于他人而言,我也是对于他而言的一个他人,所以这种交往不仅生成了自己,而且也生成了他人,是相互生成。与之相应,不仅我需要社会,而且社会也需要我,因为“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3]84,社会不是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存在,它就生成于个人的生成之中。
2.人与自然的共生
同样,人与自然的共生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1)人需要自然
这首先意味着人需要自然界,即人需要物质的自然。因为一方面,人需要自然界提供的能量维持肉体的生存。另一方面,人需要大自然以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实现”在这里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和完成,这需要在改造大自然的人的活动中实现,人的本质力量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包括改造自然的劳动中创造出来的;二是指人的本质力量要得以显现,需要以自然界为中介,即人的本质力量需要对象化,这个对象就包括自然界。其次,这还意味着人需要自然(规律、规则)的指引。这集中地体现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上,因为人们需要自然科学以发现自然的规律,然后利用这些规律来指引、“改造”[3]89人类的生活。
(2)自然需要人
在马克思看来,与人共在的自然界也是不断生成的,是在人的世界中生成的,因为“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形成的”。[3]89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将物的潜能全部发掘出来,从而将物的物性发挥到极致,即使物的物性已经得以实现和显现。所以自然界也需要人,没有人,自然界潜藏的巨大能量无法显现,它的意义和价值也不能实现。
而物的物性在多大程度上被发掘,这要取决于人的本质力量在多大程度上被发掘;反过来,如上所述,人的本质力量在多大程度上被发掘,这又取决于他的对象,即物的物性在多大程度上被发掘。所以人与自然是相互发掘、相互生成的。故而“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3]83,这里的“社会”就是指社会共生体,在这种存在状态中,人与自然的本质才能被完整而彻底地激活——“复活”,进而各自完成自身,而这种完成是以对方的完成为前提的,同时又是对方完成的前提。对于人而言,自然的完成是其完成的前提,反过来说,人的完成本身就意味着自然的完成,反之亦然。正是因为如此,《手稿》认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3]81。
三、共产主义的显现与实现
故而,对于《手稿》中作为真正共产主义的“共”,我们既不能将其理解为“共同”或“大同”——因为这种理解实际上只重视了对com-的翻译,而没有界定清楚这个词在《手稿》中的完整含义,同时也不能将其理解为粗鄙的共产主义意义上的“共产”和“共妻”,而应该将其理解为“共生”。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发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也隐含着巨大的不同:前者强调的是“共”,而后者强调的是“公”;前者强调了人与社会(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只强调了人与社会(人)之间的关系;前者突出了人的个体性,后者则只强调了人的社会性;前者强调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完成,后者则只强调了人的道德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前者是面向未来,后者是复返过去。对于“大同”思想而言,通过礼仪道德的修养就可复返“大道之行”的古代社会;而对于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的实现,主要需要的不是道德的修养,而是现实的劳动。
马克思认为正是劳动生产了人,生产了人对自然、人对社会(他人)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当然这个“劳动”在《手稿》中是有特定含义的,它不同于动物性的自发的活动,也不同于工人的异化劳动,而是一种自由的、有意识的、富有创造性的物质生产活动。正是在其中,共生得以实现。首先,在物质生产劳动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得以共同生存。这意味着,它不仅使人作为个体得以生存下来,而且在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人与大自然之间也从先前敌对的或彼此无关的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了共在的关系。其次,通过创造性劳动,人与人、人与自然共同生成。“劳动不仅改变它所指向的对象,也改变劳动主体自身”[9],也就是说,这种劳动不仅创造和改变了外在的物质世界,而且创造和生成了人的内在的生命和本质力量——人通过劳动创造和改造其对象(他人、大自然)而生成了自己,通过劳动成果确证、显现了自己。
而这种创造、改造或者生成能否实现,还在于它是否遵循了对象的本性,否则,人不仅不会通过自己的对象生成自己,反而会通过它失去自己。“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3]86所以这种建立在遵循对象本性的基础上的对对象的创造和改造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生成,也是对象自身的生成。对于人与自然而言,人需要通过劳动,按照自然的本性来改造自然,这样才会发掘自然的本性,而人通过这种创造性的发掘,同时也发掘了自身的本性,显现了自身的本质力量;对于人与社会而言,他通过劳动,按照社会规律来改造社会,这样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进而推动他人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也推动了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而业已生成的新的人的本质力量,在进一步的对象化劳动中,又会与对象的新的尚未发掘的潜质“相适应”,从而会有更新的生成产生……所以马克思的生成不仅是共同的生成,也是生成性的生成,是在人的创造性、对象性劳动中的生成。
四、结语
综上所述,《手稿》中真正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作为共生的共产主义,它意味着人通过创造性物质生产劳动,在与自然、社会(他人)的共在中生存、生成。一方面,它是指人的生存、生成,即人扬弃私有财产、克服人的异化,从而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复归人的人性,这意味着此种占有和复归是对人(性)的占有,而不仅仅是对物的占有;是对包括感觉、思维、情感、愿望、活动、爱等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而完整的占有,而不是片面而畸形的占有;是向人所当是的本性的有意识的复归,而不是盲目的、混沌的徘徊;是历史性的、现实的复归,而不是思维性的、抽象的推理——所以与其说是占有,不如说是“创造”[10];与其说是复归,不如说是完成。另一方面,它又是指人与自然、社会的共同生存、生成,其结果是人、自然、社会(他人)的相互完成。因此,作为共生的共产主义既是“人的复归”和“生成”,又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1] [美]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59.
[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美]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M].王贵贤,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5.
[5] [美]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M].王虎学,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6.
[6] MARX Karl.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M].Loyd D Easton,Kurt H Guddat,edi.NewYork:Anchor Books,1967:304.
[7] [俄]鲍·斯拉文.被无知侮辱的思想——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当代解读[M].孙凌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50.
[8] [法]让-吕克·南希.共产主义,语词——伦敦会议笔记[C].张志芳,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8),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90.
[9] [匈牙利]乔治·马尔库什.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M].李斌玉,孙建茵,译.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6.
[10] [美]迈克·哈特.共产主义之共者[C] //陆心宇,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8),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82.
〔责任编辑:杜 娟〕
A811;B83
A
1000-8284(2016)11-00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