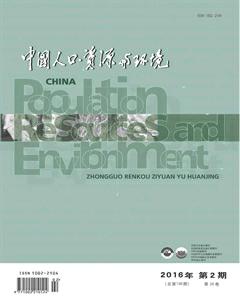贫困地区农民真的从“新农合”中受益了吗
卢洪友 刘丹



摘要:基本公共服务受益均等化要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应有效地保障贫困地区的农民大致均等地享受该服务。本文运用边际受益归宿分析技术,实证测度了2007-2011年中国244个地级市(州)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来探究贫困地区的农民是否真的从新农合中受益。研究发现:第一,与富裕地区相比,贫困地区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更高。2007-2011年,最贫困地区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分别为1.287 8、1.179 3、1.065 9、0.985 7和1.202 7,最富裕地区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分别为0.751 8、0.671 6、0.597 6、0.888 8和0.922 9。第二,从动态角度观察,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新农合边际受益率的差值在逐渐缩小。2007年,最贫困地区和最富裕地区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相差0.536 0,2011年,这一差值缩小为0.279 8。第三,传统的平均受益分析低估了贫困地区的新农合受益水平。以2007年为例,通过平均受益分析得到的最贫困地区的受益份额为24.20%,而边际受益归宿分析结果显示,最贫困地区从整体新农合受益提高中增加的受益份额达到了32.20%,较平均受益份额高出8个百分点,亦即,贫困地区的农民从新农合服务的扩张中可以获得更大的受益,在新农合服务的缩减中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本文的结论表明,国家在新农合中“亲贫”的政策倾向更多地惠及了贫困地区,新农合的受益均等化程度越来越高。为保证贫困地区的农民在更大程度上受益,政府应实施“精准医保扶贫”,加大新农合投入;多元化新农合服务供给渠道,加强地区间协调配合;优化新农合资源配置,完善对地方政府和相关官员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贫困地区新农合的生产效率。
关键词:新农合;边际受益归宿;受益分配;贫困地区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2-0068-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2.009
健康问题是关乎国民生命和生活质量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农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屡见不鲜。据国务院扶贫办最新的摸底调查显示,中国现有的7 000多万贫困农民中,因病致贫的达到42%。为了减轻农民的就医负担,政府在农村医疗保障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体现为由传统的家庭保障到“老农合”,再到“新农合”的转变。
早在1956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就规定,为社员在因公负伤或因公致病时提供实物补助和现金补助。
1959年,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改变了公社时期的资源配置和财产关系,进而改变了农村合作医疗的经济基础,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合作医疗近乎停办。自1990年开始,政府转变工作重点,将增加医疗卫生供给转为提高农民有效需求[1],农村合作医疗开始恢复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农村医疗保障水平,国务院于2002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2003)中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参与并筹资的具有互助共济性质的医疗制度。紧接着,卫生部、民政部等相关部委在一些省市启动了试点。至此,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了由传统合作医疗向新型合作医疗的转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政府向农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要“提高公共服务的共享水平”,这就要求政府一视同仁地向社会成员提供数量大致相同、质量大致相当、方便可及程度大致相近的基本公共服务[2]。只有农民真正从新农合中受益,才能最大化社会效益,实现农民的生存权和保障权。从规范的视角对新农合的受益状况进行笼统的分析并不足以为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对现阶段新农合受益分配状况进行实证测度,主要探讨的问题是:中国地区间的新农合是否遵循了均等化的要求,亦即,贫困地区的农民是否真的从新农合中受益?依据当下中国渐进式改革思路,分析新农合增量的边际受益状况更具现实意义。本文采用边际受益归宿分析技术(Marginal Benefit Incidence,MBI),系统地评估了2007-2011年中国244个市(州)新农合的边际受益状况。研究发现,中国市(州)间新农合边际受益存在显著差异,贫困地区的边际受益水平高于富裕地区,且二者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该结论在跨时期和改变分组中保持了高度稳健性。研究结论为完善新农合制度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
1 文献综述
新农合制度作为一项公共政策,要考量其公平性[3-4],不仅要求投入公平、产出公平,受益更要公平。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投入(产出)视角来研究农村公共服务(包含农村社会保障服务)的均等化。朱信凯和彭廷军[5]利用Logit模型发现,投入总量不足与结构不合理是导致农民参合的逆向选择问题的核心所在。李晓艳[6]利用黑龙江抽样调查数据,对新农合卫生筹资的公平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合作医疗筹资制度并没有实现垂直公平。朱玉春等[7]利用DEA技术从投入-产出视角评估了农村公共服务效率,研究发现农村公共服务效率水平自东向西呈现梯度下降特征。仇晓洁等[8]利用泰尔指数评估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均等化水平,发现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存在严重的区域内不均等。二是评估新农合制度的整体受益状况。汪宏等[9]采用Logistic模型和“四部模型”研究了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受益状况,研究发现合作医疗的受益存在不公平性。颜媛媛等[10]利用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参合有助于农民从就医中获益。程令国和张晔[11]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基础上的差分内差分方法、两部分模型和样本选择模型评估了新农合的经济绩效和健康绩效。发现新农合在改善参合者健康状况的同时,并未明显降低其医疗负担。
在国外,大量文献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受益分配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存在受益不均衡问题,这种不均衡可能是由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中赋予不同群体不同权重导致的[12-14],也可能是由公共服务提供成本存在地区差异引起的[15]。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边际受益归宿分析技术对公共服务的受益分配状况进行实证测度[16]。Lanjouw和Ravallion[13]利用印度农村的截面数据测度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边际受益分配状况,通过观察辖区内公共服务参与率的变动,来估计不同收入人群从公共服务受益范围扩大中获得的受益状况。研究发现农村的义务教育和反贫困制度的边际受益分配具有显著的“亲贫”性。Ajwad[14]、Ajwad和Wodon[17-18]对前者的方法进行了改进,首先在目标辖区内部进行群组划分,通过与本辖区其他群组的比较,测度公共福利在不同群组间的分配。研究结论显示,贫困人群从教育中获得的边际受益高于非贫困人群,但从基础设施的扩张中获得的边际受益却低于非贫困人群。Jalan和Ravallion[19]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阿根廷工作福利计划的边际受益状况进行了分析,发现最贫困地区的边际受益最高。Atemnken和Noula[20]使用边际受益归宿分析方法测度了喀麦隆地区教育服务的边际受益状况,发现初级教育边际受益的性别差异是最小的,且中等收入群体是初级教育最大的边际受益主体,后者与政府反贫困的目标相左。Kruse等[21]使用印尼地级数据分析了公共卫生支出的边际受益归宿,研究发现中央转移支付对地区公共医疗支出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且门诊医疗支出的增加是明显有利于贫困人群的。尽管上述研究大多并未直接涉及到农村医疗服务,但可为之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既有研究或仅从投入(产出)视角对新农合制度进行评估,或从平均效应角度切入,对增量新农合服务的边际受益关注不够。而边际受益归宿分析可以甄别公共服务的真正受益归宿,即谁是增加的公共服务供给的最终受益者,该服务在多大程度上惠及目标人群。本文创造性地将边际受益归宿分析技术应用于新农合制度的边际受益分配研究,以识别新农合服务真正的受益归宿。在中国的分权财政体制下,省一级政府在配置本辖区新农合资源时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探讨省以下的新农合的边际受益分配状况具有积极意义。
2 实证技术与数据处理
本文借鉴了Lanjouw和Ravallion[13]、Ajwad 和Wodon[18]的边际受益归宿分析技术,并稍作改进。选取了2007-2011年中国大陆地区20个省244个地级市州的新农合参合率数据,实证测度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农民的新农合边际受益分配状况。之所以选择31个省(直辖市)中的20个省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剔除的省(直辖市)所辖地级市数量太少或数据质量较差,不符合群组划分的要求。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卫生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
2.1 分析框架
边际受益归宿分析(MBI)是通过截面回归分析,来识别总体受益率上升时各受益主体受益状况的受益归宿测算技术,能够克服面板数据缺乏或时间跨度不长的缺陷。该技术的基本思路是:对省辖区内的市(州)依据一定的标准划分为若干群组,测度省级新农合服务产出增加时,各群组的边际受益率。如果边际受益率大于1,表明省级新农合服务产出的增加导致该群组新农合服务产出以更大比例提高;反之亦然。
边际受益归宿分析的基础是进行群组划分。对选择样本地区的人均GDP和新农合参合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人均GDP越高的地区,新农合参合率也越高。因此,本文按照各市(州)的人均GDP进行分组,如果新农合能更多地惠及贫困地区,则该项制度是公平有效的,反之,则认为其并非公平有效。
2.2 数据处理
从理论上来说,对一个包含10个地级市(州)的省份,最多可以将其划分为5组(一个群组至少包含两个个体)。由于20个省份的群组个数要保持一致,结合各个省份样本的容量,我们将每个省份的地级市(州)按照人均GDP划分为4组。
2.3 实证程序
首先,将xi,q,j定义为归入第i省第q个群组的第j个市(州)的新农合参合率,则第i省第q个群组的新农合参合率的平均值为:
式(9)即为第q个群组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该式的值如果大于1,表明第q个群组从提高的新农合参合率中受益更多,反之,则表明第q个群组从提高的新农合参合率中获益更少。
本文采取似不相关回归技术(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UR)对(10)式进行估计。由于第q群组的平均参合率与省一级的平均参合率相关,而省一级的平均参合率又包含了其他群组参合率的信息,因此(10)式包含的4个方程,其因变量及干扰项是相关的。为消除方程之间的相关性,我们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技术,通过将随机误差项的协方差矩阵行列式最小化,对系统内各方程的系数进行更有效的求解。
3 实证结果
新农合制度自2003年在部分县市开始试点以来,参合人数以年均34%的速度迅速增长[11]120。截至2013年底,全国有2489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农合服务,参合人数达8.02亿人。由于各地新农合制度的实施时间不同,加之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参合农民的受益状况苦乐不均。
表1汇总了中国新农合的平均受益状况(由于篇幅限制,2008年和2010年的数据不在此列出)。我们发现,新农合参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向关系。即,与富裕地区相比,贫困地区的新农合参合率较低。这一事实的背后有着深层的制度原因。一方面,农民参加新农合遵循自愿原则,政府不做强制性要求。贫困地区的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教育水平落后,参保意识薄弱,因此,参保积极性不高。汪宏等[9]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他们发现,与中高收入者相比,即使保费很低,低收入的农民参保意愿仍不强烈。另一方面,新农合实行的是“个人缴费、集体扶持、政府资助”的筹资模式,政府财力对辖区农民参合有着重要影响。研究发现,较高的政府筹资水平对于提高农民参合积极性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22]。贫困地区的农民收入较低,政府在新农合筹资中承担较大比例,但因自身财力有限,在为新农合提供财力支持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推移,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新农合参合率的差值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由2007年的5.51%减少到2011年的1.06%。这表明,与不断提升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日益完善的新农合制度相适应,贫困地区农民的参合积极性愈来愈高。
虽然表1呈现了新农合的平均受益分布状况,但是由于平均受益分布同时包含了前期的存量及当期增量的信息,因此,并不能准确反映增量新农合服务的边际受益的变动。可以看出,对于新农合的平均受益分析具有一定的笼统性。本研究更加关注的是,新农合服务每增加一个单位,各个群组的受益会增加多少?为此,我们采用边际受益归宿分析技术,通过SUR估计方法,对各群组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进行了估计,模型结果见表2和表3。
系数ρ1-ρ3是对群组一到群组三的线性方程的估计系数,ρ4是对非线性回归方程估计得到的系数。所有系数均为正,且都在1%水平下保持显著,表明省级新农合的平均受益率提高时,各个群组的新农合平均受益率也会显著增加。
将各个年份的系数ρ1-ρ4代入(9)式,我们计算出了2007-2011年各个群组新农合的边际受益率(见表3)。表3中的数字代表省级新农合受益增加一个单位,各个群组的新农合受益的增量。
通过比较表3中各年份0-25分位群组与75-100分位群组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我们发现,新农合的边际受益分配具有明显的“亲贫”倾向,即,最贫困地区的边际受益率要高于最富裕地区。例如,2007年,0-25分位群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为1.287 8,而75-100分位群组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为0.751 8,两群组的边际受益率相差0.536 0。从分位均值来看,最贫困地区边际受益率的均值要高于最富裕地区,其中,0-25分位群组5年的均值为1.144 3,75-100分位群组5年的均值为0.766 5。这一现象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国家于2003年在部分省市开始启动新农合试点工作,针对试点地区新农合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在总结先进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卫生部等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2004),指出要“慎重选择试点县(市)”,被选为试点的县(市)要有较好的财政状况,农民要“有基本的支付能力”。由此可见,新农合制度首先是在富裕地区实行,富裕地区的农民最先享受了该服务,而随着试点范围的不断扩大,贫困地区的农民才逐渐从新农合中获益。因此,与富裕地区的农民相比,贫困地区农民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较高。
从动态视角观察,0-25分位群组与75-100分位群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的差距呈逐渐缩小的趋势。2007年,两群组边际受益率的差值为0.536 0,2011年,这一差值缩小为0.279 8。这是因为,随着贫困地区农民参合率的不断上升,其边际受益率逐渐降低。与此同时,观察表3中75-100群组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2007-2009年,富裕地区农民参加新农合的边际受益率呈现递减趋势,在2010年转为上升。在对各地区新农合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时发现,部分省份于2010年在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进行了城乡统一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尝试。由于该制度还在探索阶段,当前的努力主要集中于缩小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筹资标准、报销比例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实践促进了富裕地区农民边际受益水平的提升。综合以上两点原因,贫困地区农民与富裕地区农民参合的边际受益率的差值越来越小,这一现象也反映出新农合的受益均等化程度在不断提高。
此外,我们将新农合平均受益分配与边际受益分配进行对比发现,新农合的边际受益归宿分析具有重要意义。表1给出了各个群组的新农合平均参合几率,以2007年为例,最贫困群组的受益份额为24.20%(96.81%*(1/4))。表3中新农合边际受益归宿分析结果显示,2007年,最贫困群组从整体新农合受益提高中增加的受益份额为32.20%。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受益归宿分析中使用的平均受益率在衡量公共服务增量提供的边际受益方面存在一定的偏差。在上例中,最贫困组的新农合边际受益份额较平均受益份额高出8个百分点。亦即,最贫困地区的农民从新农合服务扩张中可以获得更大的受益,在新农合服务缩减中,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
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我们从改变分组数量和分组依据两个方面,通过隔年抽样的方式评估了2007年、2009年和2011年中国新农合制度的边际受益分配效应,研究结论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和稳健性(见表4)。一方面,我们将每个省份的地级市(州)按照人均GDP划分为3组,对每个群组的边际受益状况进行测度。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民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高于富裕地区,以2007年为例,贫困地区农民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为1.130 6,富裕地区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为0.812 7(见表4)。且二者的差距呈现缩小趋势,2007年,贫困地区农民和富裕地区农民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差值为0.317 9,2011年,这一差值缩小为0.219 5。另一方面,由于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业人口比例不同,我们将每个省份的地级市(州)按照农业人口比例划分为4组,考察不同农业人口比例群组的新农合边际受益情况。研究发现,农业人口比例最低群组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低于农业人口比例最高群组,以2007年为例,农业人口比例最低群组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为0.847 5,农业人口比例最高群组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为1.261 2,且二者差距由2007年的0.413 7缩小为2011年的0.301 2(见表4)。一般而言,农业人口比例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而农业人口比例低的地区较富裕,因此,这一结论亦与最初按照人均GDP分为4组的结论一致。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当下中国有一个经济现象: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落后地区享受了更好的公共服务[23]。在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下,作为农村社会保障重要内容的新农合制度应更多地惠及贫困地区,保障贫困地区享受大致均等的新农合服务。本文利用边际受益归宿分析技术,实证评估了2007-2011年中国244个地级市(州)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研究发现:与富裕地区相比,贫困地区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更高;从动态角度观察,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新农合边际受益率的差值在逐渐缩小;传统的平均受益分析低估了贫困地区的新农合受益水平。本文的结论表明国家在新农合中“亲贫”的政策倾向更多地惠及了贫困地区。为保证贫困地区的农民在更大程度上受益,推动新农合服务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均等化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基于新农合更有利于贫困地区农民的边际受益分配效应,政府应实施“精准医保扶贫”,精确瞄准贫困地区的农民。加大新农合投入,建立新农合筹资水平与医疗费用增长速度及其他相关因素合理挂钩的科学调整机制。在当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通过政府二次分配,提升贫困地区的新农合保障水平,有利于调节收入不公,缩小贫富差距。卢盛峰和卢洪友[24]的研究发现,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既可以直接减贫,又可以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来降低贫困发生率。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财政投入应保持适度水平,否则就可能会引发财政风险、甚至财政危机[25]。
其次,应该注意到,贫困地区新农合边际受益率偏高这一现象反映出这些地区新农合参合率较富裕地区偏低的事实。因此,政府应加强宣传舆论引导,提高农民对新农合的认知度。
多元化新农合服务供给渠道,鼓励企业、志愿组织和慈善团体等社会力量参与新农合服务。
由于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信息优势,因此,在划分政府新农合事权时可将其作为第一层次[26],充分发挥其在新农合中的宏观调控职能,加强地区间新农合服务的协调配合以及新农合医疗卫生资源的整合和共享,增强农村人口在地区间的流动性,以提升新农合整体受益水平。
最后,从新农合的生产角度考虑,应优化配置新农合资源。张宁等[27]认为,通过改善卫生资源利用方式,可以提高健康生产效率。因此,可以通过资源的优化组合,实现农村地区新农合生产的“规模效应”。在资源既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新农合供给标准和质量。此外,还应设计新农合绩效考核指标来完善对地方政府和相关官员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贫困地区新农合的生产效率。
(编辑:田 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王国军.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J].浙江社会科学,2004,(1):141-145.[Wang Guojun. Changes of Chinas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J].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2004,(1):141-145.]
[2]卢洪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及其制度路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9-05(B04).[Lu Hongyou.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Theory and System Path [N]. Chinese Social Science Today,2012-09-05 (B04).]
[3]邓大松,杨红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利益相关主体行为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04,(8):14-16.[Deng Dasong,Yang Hongyan. Behavior Analysis of Stakeholders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J]. Chinese Health Economics,2004,(8):14-16.]
[4]胡善联.卫生领域中政府管制作用的探讨[J].中国卫生经济,2006,(2):10-13.[Hu Shanlian. Discussion on the Regulation Effect of Government in Health Care[J]. Chinese Health Economics,2006,(2):10-13.]
[5]朱信凯,彭廷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逆向选择”问题: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9,(1):79-88.[Zhu Xinkai,Peng Tingjun. The Adverse Selection Problem in NRCM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nalysis[J]. Management World,2009,(1):79-88.]
[6]李晓艳.从健康水平、服务利用和筹资视角看新农合制度公平性:基于黑龙江省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9,(3):96-102.[Li Xiaoyan. Viewing Equity of NRC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and financ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Heilongjiang Province[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2009,(3):96-102.]
[7]朱玉春,唐娟莉,刘春梅.基于DEA方法的中国农村公共服务效率评价[J].软科学,2010,(3):37-43.[Zhu Yuchun,Tang Juanli,Liu Chunmei. Evaluation on Rural Public Service Efficiency Based on DEA in China[J]. Soft Science,2010,(3):37-43.]
[8]仇晓洁,李聪,温振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均等化水平实证研究——基于公共财政视角[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3):70-76.[Qiu Xiaojie,Li Cong,Wen Zhenhua. Empirical Study on Equalization Level of Chinas rural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Based on Public Finance[J]. 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13,(3):70-76.]
[9]汪宏,Yip W,张里程,等.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受益公平性[J].中国卫生经济,2005,(2):16-19.[Wang Hong,Yip W,Zhang Licheng,et al. The Public Benefit Equity of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in China[J]. Chinese Health Economics,2005,(2):16-19.]
[10]颜媛媛,张林秀,罗斯高,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效果分析:来自中国5省101个村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6,(5):64-71.[Yan Yuanyuan,Zhang Linxiu,Luo Sigao,et al.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NRCMS:An Empirical Study on 101 Villages of Five Provinces in China[J]. Chinese Rural Economy,2006,(5):64-71.]
[11]程令国,张晔.“新农合”:经济绩效还是健康绩效?[J].经济研究,2012,(1):120-133.[Cheng Lingguo,Zhang Ye.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Financial Protection or Health Improvement?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12,(1):120-133.]
[12]Shoup C. Rules for Distributing a Free Government Service among Areas of a City[J]. National Tax Journal,1989,42(2):103-122.
[13]Lanjouw P,Ravallion M. Benefit Incidence, Public Reforms and the Time of Program Capture[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9,13(2):257-274.
[14]Ajwad M I. Are Public School in Texas Funded Fairly? An Analysis Using School Campuslevel Data[D]. 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1999.
[15]Hoxby C. The Productivity of Schools and Other local Public Goods Producer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9,74:1-30.
[16]Younger S D. Benefits on the Margin:Observations on Marginal Benefit Incidence[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3,17(1):89-105.
[17]Ajwad M I,Wodon Q. Who Benefits from Increased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at the Local Level? A Marginal Benefit Incidence Analysis for Education and Basic Infrastructure[J]. World Bank Economists Forum,2002,2:155-175.
[18]Ajwad M I,Wodon Q. Do Local Governments Maximize Access Rate to Public Services Across Areas? A Test Based on Marginal Benefit Incidence Analysis[J].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7,47:242-260.
[19]Jalan J,Ravallion M. Estimating the Benefit Incidence of an Antipoverty Program by PropensityScore Matching[J].Journal of Business,2003,21(1):19-30.
[20]Atemnkeng J T,Noula A G. Gender and Increased Access to Schooling in Cameroon:A Marginal Benefit Incidence Analysi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2011,12(1):94-106.
[21]Kruse I,Pradhan M,Sparrow R. Marginal Benefit Incidence of Public Health Spending: Evidence from Indonesian Subnational Data[J].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12,31:147-157.
[22]许朗,吕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状况及参合农民对其的满意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郊县地区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0,(4):63-73.[Xu Lang,Lv Bing. The Operation Situation of NRCMS,the Satisfaction Situation of Participant Farmers and its Factors:Taking Nanjing Suburbs as Example[J].China Rural Survey,2010,(4):63-73.]
[23]卢洪友,陈思霞.谁从增加的财政转移支付中受益: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2,(4):24-32.[Lu Hongyou,Chen Sixia. Who Benefits from Extra Fiscal Transfe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County Data[J].Finance &Trade Economics,2012,(4):24-32.]
[24]卢盛峰,卢洪友.政府救助能够帮助低收入群体走出贫困吗?——基于1989-2009年CHNS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3,39(1):4-16.[Lu Shengfeng,Lu Hongyou.Could Government Assistance Help the Poor to Alleviate Poverty?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NS from 1989 to 2009[J].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13,39(1):4-16.]
[25]叶姗.论社会风险应对中财政责任的限度[J].社会科学,2012,(2):121-131.[Ye Shan. Limitation of Fiscal Liability in Response of Social Risks[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2012,(2):121-131.]
[26]蔡社文.政府间社会保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和国际经验[J].税务研究,2004,(8):24-29.[Cai Shewen.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Intergovernmental Social Security powers and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ies [J].Taxation Research,2004,(8):24-29.]
[27]张宁,胡鞍钢,郑京海.应用DEA方法评测中国各地区健康生产效率[J].经济研究,2006,(7):92-105.[Zhang Ning,Hu Angang,Zheng Jinghai. Us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Approach to Estimate the Health Production Efficiencies in China[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06,(7):92-105.]
Abstract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ervice should effectively ensure farmers from poor areas to enjoy the service more equally, which is required by equalization of benefit from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marginal incidence of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in rural China based on data from 244 prefectures from 2007 to 2011. The results show that,firstly,the poor areas benefit more from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ervices compared with rich areas. From 2007 to 2011, the marginal benefit rates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for the poorest areas were 1.287 8, 1.179 3, 1.065 9, 0.985 7 and 1.202 7, and the marginal benefit rates of the richest regions were 0.751 8, 0.671 6, 0.597 6, 0.888 8 and 0.922 9 respectively. Secondly, the difference of marginal benefit rate between poor areas and rich areas was narrowing. In 2007, the difference of marginal benefit rate between the poorest areas and the richest areas was 0.536 0,and it decreased to 0.279 8 in 2011.Thirdly,conventional methods for assessing benefit incidence underestimate the gains to the poor areas from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Taking 2007 as an example, the average benefit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share going to the poorest areas is 24.20%, while the marginal benefit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oorest areas obtain an 32.20% increase in the total benefit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That is, farmers in poor areas can get more benefits from the expansion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ervice, and lose more through the reduction of the service.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policy of propoor in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benefits the poor areas more, and leads to higher degree of equalization of benefits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In order to ensure farmers in poor areas benefit to a greater extent,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precision medical insuranc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and should diversify supply channels and strengthen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e should also optimiz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improve incentive and constraint mechanism for government and related officials, so as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in poor areas.
Key words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marginal benefit incidence; benefit allocation;poor ar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