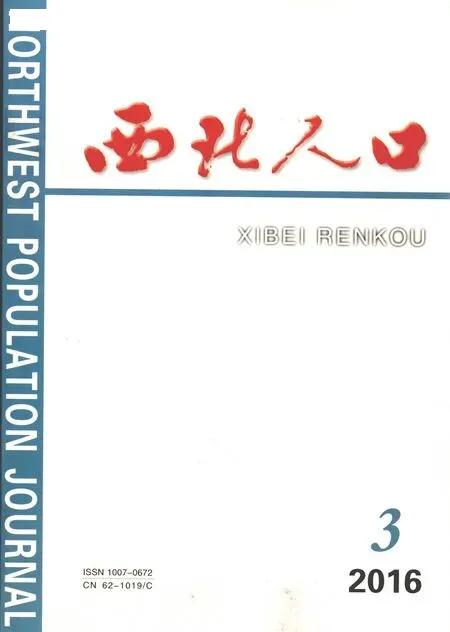后发地区城镇化制度变迁中的困境与取向探析
——以西北民族地区为例
白燕
(新疆兵团党委党校经管教研部,新疆 五家渠 831300)
后发地区城镇化制度变迁中的困境与取向探析
——以西北民族地区为例
白燕
(新疆兵团党委党校经管教研部,新疆五家渠831300)
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结构变迁,也是推动后发地区实现赶超的重要路径和手段。为缩小东西部差距,国家加大对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政策支持。“安居富民”、“定居兴牧”、“撤乡建镇”、“村改居”、“旧城改造”等系列城镇化的制度安排,改善了落后的发展条件、投资环境和生活状况,使西北民族地区发生了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剧烈的社会变迁。但推进中也面临着制度缺失、制度失信、制度偏好、路径依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引起的制度冲突等困境,论文提出了城镇化的制度完善与变迁取向。
后发地区;城镇化制度变迁;困境与取向;西北民族地区
一、引言
后发地区援引“后发国家”的概念,是相对于经济发达的先发地区而言的经济落后区域。西部相对于东中部地区是后发地区,西北民族地区又是西部的落后地区。论文研究范围包括多民族聚居与贫困发生率高的青海、宁夏、新疆、甘肃四个西北省区。发展经济学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结构变迁,因此也被认为是国家推动后发地区实现赶超的重要路径和手段。新制度经济学提出制度是影响经济社会活动最根本的因素。为实现西北民族地区快速赶超,中央政府加大城镇化推进的制度安排。论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变迁中取得的制度绩效及后续推进中面临的制度困境与取向。
制度是城镇化发展的核心要素。制度与二、三产业均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制度障碍对城镇化发展具有明显的刚性,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影响最大的制度障碍(叶裕民,2013)[1]。城镇化本身就是从农村向城市、在工业化推动下的制度变迁过程(刘维奇、焦斌龙,2007)[2]。政府是城镇化制度主要供给者。城镇化制度变迁中,尽管政府作为唯一的制度供给者遇到了困境,但自发性的制度安排取得良好的制度绩效仍需国家的推动。因为自发性的制度安排需要支付较大的预期成本,无法成为制度有效变迁的主力(林毅夫,2004[3]、刘传江,2006[4])。我国城镇化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式。强制性制度变迁是自上而下依靠国家权力实现的变迁,而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市场力量诱导下个人或组织自发实现的变迁(李保江,1994)[5]。以上研究说明制度是影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城镇化的发展与推进涉及政府、市场组织和农民多方利益,是政府正式制度与农民非正式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同一制度在不同区域、不同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绩效。
二、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制度安排的成效评价
为缩小东西部差距,加快西北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国家先后实施两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涉及交通通讯、供排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民生改善的城镇化就成为扶贫脱困、加快发展的重要手段。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进入加快发展时期。2014年,宁夏的城镇化率为53.6%,甘肃为41.7%,青海为49.8%,新疆为46.1%[6],四省区城镇化率比上年增长均在1%以上。“安居富民”、“定居兴牧”、“撤乡建镇”、“村改居”、“旧城改造”等系列城镇化的制度安排,改善了落后的发展条件、投资环境和生活状况,使西北民族地区发生了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剧烈的社会变迁。
(一)冲击了传统观念,转变了思维价值观
农牧经济是自给自足、分散且封闭的经济,其局限性以及浓厚的宗教氛围使人们易满足现状,迷信宗教和权威,而城镇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其高度市场化与开放度对传统农牧经济的封闭自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转变人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社会组织关系以及价值观念。在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在开放竞争的氛围和现代文明环境的熏陶与洗礼下,将会逐渐摆脱落后的心理状态和文化常态,改变“等、靠、要”、“小富即安”满足现状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激发了闯荡市场和勤劳致富的活力和潜能,积极主动学习掌握生产、经营、致富的本领,缩小与现代文明观念、意识上的差距。
(二)改善了生活环境,转变了生活方式
安居富民、棚户区改造、旧城改造、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等城镇化工程的受益群体是农民、完成产业转移的农民工、居住在“城中村”的边缘城市群体以及城市居民。属于提升城镇质量,改善居住环境的就地城镇化模式。“生态移民”、“定居兴牧”工程把农牧民从贫困山区、生态恶化、草场退化、灾害频发的地区相对集中迁移到水土资源相对丰裕、气候条件适宜的定居点、小城镇或城市周边,属异地城镇化模式。改变牧民的传统游牧生活,过上安稳舒适的定居生活。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投入、在原址上重建新房,住房按照水电暖气功能配套的高标准建设,升级改造城镇基础设施,拓宽街道、更新公共设施,改善了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随着人口的集聚与规模的扩大,使农牧民、农民工、边缘群体享受与城镇同等的公共医疗、卫生、教育、娱乐、文化等服务水平,加快少数民族从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普适性的文明生活方式的跨越。
(三)收入日趋多元,转变了生产方式
农牧民在城镇集中居住,不仅为土地流转、农牧业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而且加快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农牧民在迁出地从事简单劳作和放牧生活,种植业和养殖业成为主要收入来源。而聚居到城镇或邻近城镇的定居点,教育培训机会的增多,信息交通的便捷,观念和思维方式随之变化,拓宽就业渠道,收入日趋多元化,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养殖方式由天然草原为主的传统畜牧业向放养与圈养相结合的现代养殖方式转变,农业种植由传统农业向高效现代农业方式转变。家庭剩余劳动力拥有更多的赚钱机会,手工编织、农家乐旅游、观光畜牧业、农牧兼营、商贸服务、建筑工程、工厂务工、外出打工等多样化的生计方式正逐步取代了单一农牧业传统的生产方式。
(四)形成新的社会网络,民族交往频度增加
费孝通认为我国农村存在着社会结构“差序格局”[7]。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从一个向下一个逐渐推下去,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根据私人关系构成的网络,是以家庭为中心,按照家属关系的远近向外扩展关系网。生态移民来自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等不同民族,形成以单一民族和家族血缘关系为主的格局。进入城镇生活,就业方式的多元化、市场化、公共休闲场所、各类文化娱乐活动的开展以及社区混合居住方式,增加了各民族交往接触的机会,打破了家庭界线、家族范畴,扩展族际交往,加深了族际交往的广度与深度,增加各民族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力和宽容度,使血缘之外的业缘关系得到实质性发展,形成了新的社会网络,推动了社会转型与变迁。
(五)实行城镇社区管理,转变了组织管理方式
2012年以来,“撤乡建镇”速度加快以及“村改居”的推行,使农村的管理模式发生了变化。将城市社区治理方式移入农村,撤销村民委员会改建为城市居民委员会,解决传统城乡分治中农村社会管理缺失问题,放大城市辐射效应与延伸区域,提升农村场域中的社会管理和服务效率。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均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但村民委员会相比城市居民委员会其自治性更强,属于松散性管理。“村改居”后,在加强村治的同时,将公共卫生、就业服务、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法律服务、养老服务和公共安全等职能服务回归政府,可以弥补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与服务主体缺失的问题。城镇化包括人口在地理空间的转移、产业转型和市民化的转型三个层面。市民化转型是城镇化转型的高级形式,是对前两个转型的提升。“撤乡建镇”、“村改居”的制度设计通过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和方式的改变加快市民化的转型。让农民不仅实现了身份认同,还随着思维观念、社会关系、休闲方式的变化而增强对社区这一载体的认同与归属,加快农牧民从“非农化—城镇化—市民化”的转变。
三、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推进中的制度困境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和转移,由此引起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非农化的制度变迁过程。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演进过程,同样也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变迁过程。快速城镇化给西北民族地区社会带来巨大变迁的同时,也陷入了社会矛盾凸显、贫困问题突出、文化适应差的困境之中。当前,面临的制度困境表现为五个方面: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引发的制度缺失;制度执行偏差引起的制度失信;形成少数官商受益的制度偏好;强制性制度变迁形成对政府扶持的路径依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引起的制度冲突。
(一)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引起的制度缺失
有效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而组织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掌握技术、知识和学习能力。政府作为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推动者,凭借强有力的权威和资源分配的权力成为远比私人主体、民间力量更为有效的组织,主导了制度变迁的全过程。制度变迁的效率取决于政府组织的有效性,政府组织的有效性又取决于政府政策的适用性以及公务队伍素质、能力与执行力。城镇化推进中存在着制度不配套不连续的问题。牧民定居、生态移民、老城区改造等工程前期投入大、政策很优惠,制度设计倾向于迁出激励,缺少迁入后的长效激励。生态移民迁出原居住地后,技能培训与产业配套未跟上,农牧业不能有效结合,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成为新的城镇贫困群体。在城镇规模扩张中,大量城郊农地被征用,产生大批失地农民。老城区改造中,居民原沿街经营的小生意、烤馕等清真特色食品加工的就业空间与环境丧失,而城镇的农牧产品加工、劳动密集产业以及三产对劳动力的容纳能力均不能承接劳动力的进城就业转移。这在宁夏的西海固地区、青海的海东地区、甘肃的贫困山区、新疆的南疆地区贫困集中度高的区域表现尤为突出。城镇化变迁中缺少产业配套、教育培训、民生改善等系列制度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削弱了制度效力。
(二)制度执行中的偏差引起制度失信
中央政府对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采用同一模式、同一政策、同步推进的方式,缺少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差别化政策。如“两居工程”是普惠性政策,制度设计是以缩小差距、扶贫帮困为行动逻辑,但在实施中,并非最贫困的民族地区和居民是最受益的群体。对不同收入家庭而言,收入条件较好的家庭在享受扶持政策之后有条件盖房和致富,而对于较为贫困的家庭因不具有低息贷款能力,即使有政策支持依旧盖不起房,养不起楼;国家项目更易让财政状况较好、有能力承担项目配套资金的地区所接受,贫困地区会因项目配套和后期运行成本高昂而放弃。
制度传递环节中,因信息透明度低、程序复杂,民众不知情。受素质和能力的制约,基层干部队伍对制度的理解和把握不够,执行时变形走样,制度利益被执行者侵夺,好的制度在基层并未真正落实。如老城区、棚户区改造中,以行政手段强制房屋拆迁,忽视居民利益诉求和民族特色,拆迁方式简单粗暴,补偿措施不到位,随意更改规划、不履行承诺与合同。或前期没有科学规划,各个规划脱节,导致城镇建筑“拆了建、建了拆”,地下管道“挖了填、填了挖”,造成资金的巨大浪费和居民出行的不便。政府以强势推行旧城改造及新城扩区,宜引起干群矛盾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居民文化素质不高,法律意识不强,既缺少自觉学习的动力,又缺乏获取信息的渠道,无法与政府平等谈判,即使有了表达途径也无法纳入政府考量议程,陷入到“理性”的“无知”中。在信息传递不通畅和不对称的条件下,制度很难得到众多目标对象的认同。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不对等、出现偏差,导致制度效力递减,民众对制度失信。
(三)形成少数官商受益的制度偏好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作为理性经济人,地方政府为了谋求晋升提拔机会和个人利益最大化,总是努力符合政绩考核标准。城镇的景观建设、地标工程、高楼大厦相比民众的收入增长、地下管网建设更有利于政绩评价,因此,钢筋水泥下“造城运动”轰轰烈烈。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城镇化发展成效不是由民众进行评价,而是政府作为代理人的自我评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存在差异,中央政府是以后发地区少数民族脱贫致富为目标函数,地方政府则把城镇面貌、政绩考核作为目标函数,为追求政绩,盲目追求城镇化速度,力求自己有限的任期内实现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热衷于建设吸引眼球的地标性工程,盖高楼、拓马路、建广场成为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城镇化成为“物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成为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手段,而不是民众期望与向往的城镇化。地方官员、房地产开发商成为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形成了制度偏好。地方政府在契约执行中具有充分的信息优势,为追求土地财政,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暗箱操作,以低成本征用土地,滋生了寻租腐败现象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城镇化制度变迁的有力推动者。“空城”、“鬼城”的出现就是例证。
(四)强制性制度变迁形成对政府扶持的路径依赖
外生制度有效性取决于与内在演变制度互补性。为加快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只有激发诱致性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形成耦合互动关系时,其交易成本才能最低。我国相关政策、制度的出台源于东部地区的创新与实践,如棚户区、城中村的改造、“村改居”等在东部均有成功的范例与典型经验。东部省区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基础条件较为成熟,有着良好的区位条件、经济实力以及创新活跃的个体组织,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推动下,诱致性制度变迁随之形成。而西北地区经济缓慢、基础薄弱、制度创新不足,具有现代化进程中起步晚、起点低、市场机制导入迟的“迟发展”特征,与东部地区同质化因素少,不具备强制性制度转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条件与土壤,简单嫁接和复制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了城镇景观形态,现代文明的特征越来越鲜明,但因其是外生植入型的制度变迁,缺乏自发动力,植入的新制度与原制度耦合度不高,系统内部未能形成有效的、良性的动力与创新机制,使强制性制度变迁效应被“挤出”,造成经济效率损失与政策效果减弱。这也是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制度变迁中的问题与矛盾远多于东中部地区的重要原因。
强制性制度变迁大大降低城镇化发展中的交易成本,可在较短时期内获得较好的制度绩效,但从长期来看,易陷入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中。道格拉斯·诺思丰富和完善了路径依赖理论[8],路径依赖是指某种制度一旦被选择后,往往会产生出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形成制度惯性,从而使制度退出的难度增大、成本增加。西北民族地区城乡二元矛盾突出,农业结构调整慢,农村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贫困面广。城镇数量少、规模小,非农产业不发达,吸纳非农就业有限。越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交易费用越低,收益递增将会校正对低效率路径的依赖,而在市场竞争不充分的逻辑下,将会强化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固化的体制结构、落后的产业结构构成了城镇化制度变迁的锁定因子,陷入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民众对政府双重依赖的路径中,导致制度低效,阻滞了城镇化进程。
1.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制度的路径依赖。西北民族地区作为后发区域,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继享受了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诸多优惠政策,2010年以后,加大了以新疆为重点的贫困地区民生改善的政策支持力度。城镇化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因此也成为中央政府政策支持的重点。城镇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资金需求量大,而西北民族地区县市乡财政自给率低,基本是“吃饭财政”,收支缺口大,自身财力无法满足城镇的巨大投入,即使有国家项目的支持,但基础设施的配套资金、房屋拆迁补偿费等都需地方财政承担,财政入不敷出,城投债风险巨大。国家政策支持成为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制度变迁的核心动力。陷入“政府单一推动—地方财政负担沉重—依赖国家投入”的“越推越靠”的“路径依赖”之中。
2.民众对政府形成制度的路径依赖。城镇化已成为政府的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而民众受语言障碍、文化素质、劳动技能、习惯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不愿改变现有的生活状态,进城意愿不强,在城镇化制度变迁中仅是被动的服从者和参与者,对“被上楼”“被城镇化”“被逼发展”有着无奈、不满与抵触。缺乏快速适应城镇生活、寻求更广阔发展空间的动力,又缺少在非农产业中生存就业的技能,“等、靠、要”思想严重,靠领取政府低保、各类补贴以及优惠政策而生存,陷入“政府支持—民众参与度低—依赖政府”的“路径依赖”困境之中。
(五)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引起的制度冲突
“制度结构是一个社会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总和。”[9]正式制度是国家或某个组织作了明确规定的、并由行为人的组织予以监督和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制度。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均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指对行为人约束的不成文规定,与正式制度相对应,包括价值信念、风俗习惯、伦理规范、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领域。正式制度是政府或组织意志的体现。当与非正式制度高度一致时,正式制度就能达到既定目标。制度变迁的设定目标与非正式制度距离越近,亲和力越强,其变迁成本就越低。制度目标越容易实行。
城镇化已成为西北民族地区实现后发赶超的正式制度,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并称“四化”发展战略。正式制度是以缩小区域差距、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减少贫困群体、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为组织目标。西北民族地区集聚多个民族,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影响很大。农牧民居住在高山、草原和边远的农村,长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及四季游牧的生活,形成与城镇现代文明生活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思维价值方式。农业家庭耕作、草场放牧与圈栏养殖的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少数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形成了对布局分散、平房大院、住种养一体的居住偏好,留恋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愿进城住楼,楼房狭小的活动空间改变了原有的院内种植、家族聚会、朋友交往的生活方式。对城镇新环境学习和认知能力不足,主观上不愿接受城镇化[10]。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存在差异,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发生矛盾与摩擦,政府与农牧民之间在博弈中时常被锁定在非完全合作状态,导致城镇化制度执行效率不高。
四、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制度完善与变迁取向
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稳步推进城镇化。西北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的背后,涉及农业现代化水平、产业发展、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等正式制度的配套设计,以及观念转变、人际交往、宗教信仰、文化适应等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摩擦协调需要一定的时间,强制性制度变迁激发诱致性制度变迁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居民对制度变迁也有接受和内化的过程,因此,在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制度变迁中更要有历史耐心,要把握节奏和时序,警惕运动式城镇化,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稳步地推进城镇化。
制度安排要考虑区域的差异化。西北民族地区与其它省区的发展基础、区位条件、贫困程度、资源不同,宁夏、青海、甘肃、新疆四省区际、省区内的差异较大,制度安排中不能搞同一的“一刀切”政策,要体现制度的差异化和针对性。对贫困程度不同的地区实施不同的制度安排,充分体现制度的公平性,让所有民众享有同等的制度效应。对贫困程度深的居民,采取住房、贷款、社保等精准扶贫政策。
建立以产业发展为核心的城镇化制度安排,构建人口转移与产业间的联结互动机制。人、产、城是城镇化三要素,其中产是核心,注重发展特色民族产业,培植城镇发展动力。生态移民中要将农牧业有效结合,做精、做深优化传统产业,提升产业效益。在旧城改造中,保留老城区文化特色,对老街环境改造优化后,合理布局小生意、烤馕等清真特色食品加工业。改善投资环境,引入资本与技术,延长产业链,发展农牧产品深加工、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拓展劳动力的就业空间。
重视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影响,减少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摩擦。城镇化制度变迁中,及时了解传递非正式制度状况,将农牧民的意愿、文化分歧、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纳入制度设计的考量范围,慎重实施可能对少数民族人口生活习惯发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努力做到农牧民意愿与正式制度的“激励相容”[11]。建立居民意愿表达机制。政府要加大广播、电视、网络等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拓宽农牧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强对制度政策的认知度。同时要主动作为,及时了解居民需求,通过入户调查、问卷发放、网络投票、微信平台、领导信箱等方式收集居民的意见,将其作为制度供给与决策的重要参考。将原先强制、命令方式改变为逐步诱导,解决就业,转变观念,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
创新制度,完善城镇化相关配套制度。杨小凯提出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制度模仿要远比技术模仿难,而后发优势是以制度创新为逻辑起点的。西北民族地区要不断创新政绩考核机制,建立上级政府评价与群众满意度相结合的评价机制。将公共服务质量与居民收入、就业率等纳入到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体系中。定期对居民满意度调查,纠正“为城镇化而城镇化”的错误政绩观。净化官场生态,改变土地财政格局,切断地方官员与房地产开发之间的利益纽带,减少和杜绝寻租腐败、道德风险的发生。改革户籍制度,放宽落户条件,让转移就业的农牧民落户城镇,逐步纳入城镇住房、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保障范畴,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权益。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第四,创新土地制度。推进集体土地同权、同价入市。规范和引导土地流转,鼓励土地规模化经营。筝
[1]叶裕民.中国流动人口制度障碍的宏观负面效应解析[J].现代城市研究,2013(3):21-25.
[2]刘维奇,焦斌龙.技术变迁与城市化路径[J].珠江经济,2007(10):40-47.
[3]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70-378.
[4]刘传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J].理论月刊,2006(10):23-25.
[5]李保江.城镇化诱致性农业发展的制度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1994,(4):21-24.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14.
[7]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80-95.
[8](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48-49.
[9]卢现祥.论制度变迁中的制度供给过剩问题[J].经济问题,2000,(10):8-11.
[10]辜胜阻,刘传江.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管理[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361-390.
[11]刘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制度变迁的特殊性与优化[J].西部论坛,2013,(1):122-138.
Abstract:Although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northwest minority areas has obtained the phased achievements in recent years,it still needs a long way toward alleviating poverty.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northwest minority areas.By investigation in Gannan state,first,Gannan state was divided into three regions including the farming areas,the mixed pastoral and farming areas and the pastoral areas.Then,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of each area of Gannan state were further analyzed,and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Our goals are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overty problem of Gannan state and also hop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ethnic areas.
Key words:northwest minority areas;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farming areas;mixed pastoral and farming areas;pastoral areas.
Backwardness Area Urbanization Difficulties with the Orientation of Institutional Change:In the Northwest Minority Areas,for Example
BAI Yan
(Xinjiang Corps Party Committee Party School,Wujiaqu Xinjian,831300)
Urbaniz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modernization drive,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path to promote backwardness area achieve tremendous and means.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east and west,and the state of the northwest minority areas urbanization policy support.Settled XingMu“anju enriching people”、“withdraw township building town”、“the home village changed”、“urban renewal”and other series of system arrangement of urbanization,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ckward condition,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living conditions,the northwest minority areas involved in economic,social,cultural and other fields have taken place in dramatic social change.But also face system lack in advance,broken system,system p
,path dependence,formal system and informal system system conflict caused by such trouble,put forward the orientation of urbanization system consummation and change,follow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steadily promoting urbanization.
Backwardness area;urbanization difficulties;with the orientation of institutional change;northwest minority areas
(上接120页)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es of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Northwest Minority Areas:A case study of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WANG Zhen-ya,HAN Xu-feng
(School of Humanities,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Lanzhou Gansu 730070,China)
F299.21
A
1007-0672(2016)03-0121-06
2015-12-02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疆生态移民与城镇化发展研究》(12BMZ042)的阶段性成果。
白燕,女,河南偃师人,新疆兵团党校经管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