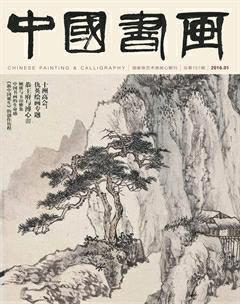从清明节到喜庆日
余辉
自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问世之后。尤其明清以来。画界代代不乏追随者。以“清明上河图”为题材的长卷。宋元明清本可达数百之多,留存至今,分藏于公私之家,遍布在世界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故宫博物院藏,以下简称“宋本”)。代表宋代风俗画的最高艺术成就。可以说,宋本是这类绘画题材的原创本或祖本。其二是明代仇英(款)的《清明上河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以下简称“明本”),代表明代苏州片较高的艺术水平,将该绘画题材的构图形式基本上固定下来,对后世具有一定的范本作用。
本文以两本《清明上河图》的基本内容为视角,研究画家时代背景、绘画观念、审美取向以及创作目的等人文方面的演化问题。
一、以“清明上河”为中心的“街景画”
宋本以北宋汴京城郊和市中心为生活原型。然而,北宋被金朝女真人灭亡后,汴京城遭到劫掠和焚烧,已不复繁华之貌,后因历次黄河泛滥和泥沙淤积,旧城渐渐不复存在。明本的作者乃至后世所有《清明上河图》的作者依旧要表现汴京,但这些画家大多生长于江南。汴京乃被换装成苏州繁华的都市景象和江南风俗等,这是两本《清明上河图》的基本异同。
经历过元末战乱,萧条的江南诸多名城,在明代中期经济重新步入辉煌,苏州成为江南首富之都。经济繁荣在北方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在南方主要集中在江南,更以苏州、南京、松江、杭州等地为重。南北两地许多城市画家来自苏州一带,尽其丹青之艺描绘当时城市的繁荣之景,是这个时期街景画最突出的艺术成就。
这种专事表现城市繁荣的绘画离不开描绘街肆和商贸人群,将两者有机结合为一体,笔者称此类绘画为“街景画”。明清“街景画”是特指17世纪至18世纪生活在城市里的画家作品。萌发于明代中后期,崛起于清代,是城市手工业和商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呈现出社会性的艺术需求。城市画家特指生活在市井之中的职业画家,他们是市民阶层的一部分,熟悉市民生活,有不同程度的文化素养,其写实技巧更为精巧、雅致。城市画家绘画题材以人物为主。亦有山水和花鸟,其中有许多是不为画史所重的佚名艺匠,假借仇英之名作画卖画。他们的绘画动机与当时的社会需求特别是富家的收藏雅好紧密相联,是城市画家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伴随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城市手工业经济和商业经济的发展,给市民画家开拓了市容绘画题材。在明清两朝,“清明上河图”成为一种特有的绘画题材,“街景画”在苏州形成了新的“清明上河图”,画面中由右向左依次画出近郊村野、城外虹桥、城里商肆、御苑龙舟等四大区域。所绘城市大多以苏州代替开封,在御苑之外,所绘河流必须是一条运河一以贯之,上有一座拱桥,下有舟船,两岸街肆鳞次栉比,还绘有城墙、城门和闹市区等场景。明代苏州片《清明上河图》的基本结构来自于宋本,这归之于宋本曾在苏州一带有过长达百年的递藏历史。由于此类绘画所绘之景皆是作者在苏州的生活感受,所有景物和人物几乎苏州化了口经过许多明代工匠画家的传摹,在苏州一带广为流传,明本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本,展示了画家的界画功底和人物画技巧。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要将这两本《清明上河图》所绘地域具体确认到哪条街、哪座城门。还要具体到哪个季节。事实上,汴河上的虹桥有许多座,而画家就绘制了一座。显然,两本的画家是将若干座虹桥的特色集于一体,画中街道、城门等均如此处理。人们习惯于将宋本与南宋孟元老回忆北宋末汴京城的《东京梦华录》进行比对,认为两者是一致的。不过,在《东京梦华录》里记载的各种名店、名街和特指的某个知名建筑物。几乎在宋本里找不到,如当时最有名的“御街”、“十三间楼”、“宣德楼”及其附近的“张家酒店”、“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等,还有“潘楼东街巷”里的“李生菜小儿药铺”、“仇房御药铺”、“刘家药铺”和“看牛楼酒店”等在宋本里亦无踪影。书中提及许多著名的寺观如大相国寺、上清宫等,在宋本中均无处可寻。特别是大相国寺,是东京最热闹的去处,“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宋本中出现的商肆和店铺如“刘家上色沉檀……”、“赵太丞家”、“孙羊店”等在《东京梦华录》中是没有的。宋本中绘制的商肆大多被抽去了店名,如“脚店”、“正店”等,流行的建筑形式如“欢门”和交通工具“太平车”、“平头车”、“串车”等均可见诸于宋本和《东京梦华录》。可以说,宋本和《东京梦华录》的时代气息和所表现的生活景象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细节上,《东京梦华录》具体如实,而宋本则文学化了。店名的真实性必须与街道及其周边环境的真实性统一,宋本作者有意避免实景的真实以免被苛求处处如实,而是对城市生活细节进行高度概括和集中。这种创作手法被明本和清院本所继承。
明本也没有具体描绘苏州某具体区域。这类非实景绘画在艺术上的处理手法是:整体上集中概括,局部中具体写实。
两本《清明上河图》在画面结构上最大的不同是:宋本画到城内的喧嚣处而止。作者张择端另行绘制了表现宫俗的长卷《西湖夺标图》(今佚,见宋本张著跋文),与描绘民俗的《清明上河图》成为姊妹篇,一并进呈宋徽宗。明清本则将画中的这条商贸大道画到尽头,增绘的半段是:面对这条大道的北宋皇家御园金明池(俗称西湖)。那里正举行三月三日龙舟竞渡,皇家每年只在此日允许百姓入园观赏。因此,明清本淡化了清明节的气氛,增添了更多喜庆和享乐的节目,坚持认为宋本有遗缺的学者称此类本子为“清明上河图补全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绘画主题。这些表面上的差异。实际上潜藏着画家的创作观念和绘画目的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等诸多方面的不同。
明本的作者是否见过宋本?比较宋本与明本之间的构图关系、人物的组织结构等,可以推断,明本作者没有见过宋本,明本画家所接触的是当时苏州片中的《清明上河图》。那么,明本和清院本后半段“金明池夺标”的内容和形式来自何处呢?这两本的画家可参照元代王振朋(传)《金明池夺标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样式,图中所绘皆系北宋后期衣冠服饰、宫俗风物等。元代与此相类似的本子有六七本之多,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张择端《西湖争标图》或该图传本的图像样式被元代王振朋及其传人所用,否则,后人无从得知北宋崇宁年间龙舟竞渡的盛况。而明清本中的金明池夺标的构思在不同程度上参照了元代王振朋的传本,并加以改造。
二、创作主题和观念不同
两本《清明上河图》卷都有一个共同的绘画主体,表现开封城内外清明时节的人物活动,尽管明清两朝将开封绘成苏州城的面貌。由于画家的时代、地位、身份不同,同名绘画中表现出不同的创作思想。宋本和明本、清院本观察社会的视角有所不同。如前者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不回避市面上的各种矛盾,而明本反映的是享乐主义,各种供享受和消遣的店铺应有尽有。
1.两个不同的节日场面。两本虽然是同名绘画长卷,但在时空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宋本所画的时间段是学术界通常认为的清明节。空间是汴河两岸从近郊到开封城内的世俗生活,人物大多是围绕着清明节这一天的祭扫、聚会、商贸等活动展开,没有鲜明的喜庆色彩。
明本在时间上免去了清明节这个感伤的日子,上坟祭祀等活动不再出现,场景气氛相当欢乐,甚至出现嫁娶等不可能在清明节出现的大喜之事。全卷变成了一个盛大的商贸佳节和喜庆之日,集中概括了许多佳节的喜庆内容。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这种变异。主要是欣赏者们追求享乐的审美需求,这种需求大大地被商业化了最终导致宋本《清明上河图》的主题发生了重要变化。
2.民本地位之异。在两件《清明上河图》卷里,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官僚活动和在画中的地位,各卷官本位思想的轻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画家所处的地位。
明本画家生活于远离皇城的苏州民间,关注的是市井百姓日常生活。画中官员和百姓服饰没有明显区别,故重在贫富之别。许多明代江南兴起的小手工艺店铺。在明清的本子里一一出现。画中出现了放风筝、童嬉、看戏、娶亲、武术表演、伎乐、木偶戏、舞伎、文人雅集、耍猴等一系列欢乐的场景。在明本和清院本里,汇集更多的是享乐和消费。那条从近郊到城中心的大道几乎成了“欢乐一条街”。
与明本在本质上不同的是,宋本中的一条街汇集的是财富和汗水。从张择端对现实生活的取舍来看,可以判定在创作中没有突出官本位思想。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民本观念,画家并没有刻意地粉饰太平不去重点表现世俗百姓享乐欢快的一面。而是把世俗百姓为生计付出的种种辛劳,包括各种重体力劳动一一诉诸出来。恰恰是他的这种取舍。表明了他不愧是一位具有悲天悯人思想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大师。
宋本决不回避官与民或官与官之间在道路上的矛盾,透过这个表面现象,不难窥探出北宋末潜藏着一定的社会危机。仕宦们个个养尊处优。画中的世俗百姓过的是辛劳忙碌的生活。张择端绘制该图有潜在的政治用意。他是有选择地真实地表现当时街头的社会生活,而不是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去观察社会、罗列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所载录的各种世俗生活,当时的张择端完全可以看到,但是,他并没有将自己所见所闻全部描绘,有的视而不见。如在《东京梦华录》里,录有十座供民间艺人表演的场所——瓦舍,张择端无论平时还是清明节都可以看到许多欢快的街头表演,如在平时,“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小唱:李师师……。嘌唱弟子:张七七……”。当时。在瓦子里常年演出杂剧。傀儡戏有杖头傀儡和悬丝傀儡、小儿相扑、皮影戏等,还有类似今天的相声“说诨话”。“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若在清明节,“都城之哥儿舞女,遍满园亭。低暮而归”。还有杂剧、戏剧、武术、球类、荡秋千、相扑、角抵戏、斗鸡子、踢毬、牵钩(拔河)等在清明节中盛行的民间娱乐活动。北宋开封街头兴盛的娱乐活动是当时风俗画的表现主题,如京师画家汴京人氏高元亨“工画佛道人物,兼长屋木,多状京城市肆车马,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市”,能“尽事物之情”。在宋本里,没有出现街头杂耍的大场景。只简略地描绘了一场小规模的说唱活动。看来,张择端是有意识地回避描绘这种在清明节出现的欢快戏场。
3.矛盾对立之不同。两本《清明上河图》对社会矛盾有着各自不同的立场,这取决于不同的创作目的。宋本讲求人物活动中极其严峻、激烈的矛盾冲突,并且显得十分惊险,特别是虹桥上下表现得尤为突出:来不及放下桅杆的大船即将与虹桥相撞,引得两岸百姓惊呼不已,桥上的轿、马及行人也为争道而发生纠纷形成了立体交叉的综合性矛盾。
这种群体性矛盾在明本里淡化多了。画家们取消了群体性的矛盾冲突,在虹桥上下,基本上是相安无事的人流和车船,偶尔出现的争斗演化成个人之间的矛盾而已。其中明本出现的矛盾频率最低,明本的作者出于商业售卖的需求,以人物之间小的矛盾摩擦为噱头。如以荒唐的打斗来吸引欣赏者的眼球,仅仅是为了活跃画面中的人物气氛而已。
三、城防武备之异同
两本《清明上河图》卷中有无涉及到军事防备方面的内容,直接反映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国力、军力的强盛程度和军民的防犯意识。结合当时不同的政治、军事背景,不难揣摩画中的奥秘。
1.兵马之别。宋代经历了从文武并治到以文治代替武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具体体现就是宋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马匹从多到少的过程。宋仁宗朝翰林学士承旨宋祁奏曰:“今天下军马,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也就是说,宋军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官兵没有马匹。景祐年间(1034-1038),他上奏曰:“天下久平,马益少,臣请多用步兵。”提出他的兵学观念也是主张“损马益步”,即减少骑兵增强步兵。连“先天下人之忧而忧”的参知政事范仲淹也无视军马在战争中的作用,竟然提出了如此观念:“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边人,行之则困中国,然自古骑兵未必为利。”因而在张泽端笔下绘有五十多头牲口,竟然没有一匹像样的战马。倒是来自域外的驼队长驱直入,匹匹精壮。
北宋兵卒的士气也是从强到弱。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政府养育了上百万职业兵,终年只是“饱食安坐以嬉”,以至于每次领口粮都无力负荷,不得不找人替扛。卫兵入宿。自己衣被也同样得由别人持送。在“新党”王安石变法时,“将兵法”得到普遍施行,这一情况得到了改变。士兵受到了一些训练,军队素质有了提高。但在北宋末,“新党”失势,宋军依旧故我,宋本中全城几乎没有任何武备,城外一大宅门口有几个“饱食安坐”的兵卒也显得十分慵懒,画家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戒备状态,恰恰是北宋后期兵卒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宋本里。绘有大小五百五十多人,涉及各行各业,只绘有少数几个兵卒,其中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兵!在该有兵的地方竟无一人把守画家在城郊绘有一砖砌的望火楼,楼下的营房本应“有官屋数间。驻屯军兵五百人,及有救火家事”,遗憾的是,望火楼上无一人观望,楼下更无一兵一卒,数排兵营已被作为商业用房,其军力涣散可见一斑。
2.城防之别。大凡古代城池多有城防功能,城内、城外、明处、暗处必有武备。宋本和明本的城防图像各不相同。分别从宋本的虚设到明本的强化。“虚设”是国势衰弱的表现,“强化”意味着国家的警觉意识。
两图的城墙营造样式因时代不同各呈其貌,这是表面现象的异同,其本质上的不同是每幅图的城防意识不同。宋本城墙上下没有一个守备人员。土墙上面也没有任何城防工事,连射箭的城垛也没有甚至连虚设的城防都没有。在明本和清院本里,一进城门的左侧屋宇是城防机构所在,有重兵把守而在宋本的同样位置,居然是一家商铺,老板正在验货。账房在记账。从画面上看。整个汴京正沉浸在浓厚的商贸气氛,完全是一座不设防的都城。这不是画家张择端的有意设计,而是真实地反映了徽宗朝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力和日趋淡漠的防范意识。同样,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也极少谈及军事防务,仅仅说在外城设有“战棚”而已。仅凭此图,就不难得知为什么北宋汴京会被女真铁骑轻易攻破,北宋的国家危机可见一斑,宋金战争的结局可想而知。最后,在1127年的冬季,金军铁骑冲进了一座座像宋本中不设防的城门:通津门、善利门、朝阳门、宣化门。直到北宋禁城南薰门!
在明本里,画家表现的是明代中后期的苏州城,从军事上看,其城防能力被大大强化了城墙将画面斜分为二,城墙上有专供射箭用的城垛。包括水门在内的两个城门都有一个瓮城,或藏兵,或增加一道防线。一个兵卒持矛伫立在城门内的守备间里。门外竖立了三个标牌:“固守城池”、“盘诘奸细”、“左进右出”。门口的左右两排武器架上插放着刀枪剑戟,墙角还倚靠着四块盾牌。这里还画有明代抗倭战争中特有的长枪类利器,靠着屋檐斜立的两把狼筅,在明代兵书《武备志》《登坛必究》等刊有该兵器的说明或图像:“狼筅古所无也,戚少保于倭战水田中。其为阵四散,不可施蒺藜与拒马木。故以竹支之。使其利刃不得遂入,而我徐有以置之……”这是戚家军为对付蜂拥而上的倭寇而发明的一种竹制或铁制兵器。此外,地上还堆放着三组铁球,说明这里还有重型热兵器——火炮装备。城门外有三个大汉正在注视着进出的人群,有可能是便衣,在宋本和清院本里没有这样的人物。城门的另一侧是水门,它有两道城门,第一道是明门,在城门口。第二道是暗门,在水门的顶端即城墙上有一个漕口,万一有敌欲从水门攻入,可立即放下暗藏的千斤闸,挡住来犯者。水门外有两个兵卒在守卫。
当时进犯苏州城的主要是倭寇,他们一般从太仓的浏河港登陆,袭击太仓、攻掠松江、苏州等城,大肆烧杀掳掠。如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三十三年(1554),倭寇三次袭击苏州。枫桥旁的铁岭关在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1552-1559)度过了倭寇连续八年的惨烈攻击。据明代郑若曾《枫桥险要说》。“奸细”时常出没。如杭州虎跑寺僧徐海,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月,率倭寇分掠苏州、常熟、崇明、湖州、嘉兴,先后为官军所败。细细品味画中城门内外的种种紧张的迹象,不难看出画家记录了为防御倭寇进犯留下深刻的时代烙印。至今,苏州元末始建的盘门、阊门依旧保留下城门和水门。特别是水门上铁闸闸孔和城头上“牛腿炮”依旧如故。
3.习武之别。在宋本和明本里。分别展现了不同的习武态度,即习武活动从无到有的两个历史阶段。宋本除了绘有一个军卒在押运军酒前做了一些拉弓的准备活动外,没有任何表现习武的人物和场面。明本出现了来自民间小规模的骑射活动。这是这两个时期不同的尚武精神决定的。
在宋代“崇文抑武”国策的制约下,画中不太可能出现习武场面,习武活动几乎不被风俗画收入。在现存的宋画里,仅有一两幅与武备有关的绘画。
明本中出现小规模的骑马和射箭活动,习武者衣冠不是制服,其颜色和样式各不相同,显然是民间组织的练武活动。这样的操练与当时民间自发组织的抗倭活动不会没有联系。不过,画中几乎没有观众,说明操练者的社会关注程度还远远不够。
四、风俗民情各不相同
两本《清明上河图》绘制的时间为:宋本绘于12世纪初,明本绘于16世纪。汴京、苏州相隔千里。许多社会风俗因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各有变化,有的共有的风习因画家构思角度不同,各有取舍。
1.衣冠服饰之别。两本《清明上河图》卷人物的衣冠服饰各有不同。毋庸置疑。宋本中各阶层人物的衣冠服饰皆为北宋中后期样式,属于当时人绘当朝事。明本乃系后世者绘前朝(北宋)之事,人物基本上是明代的衣冠服饰,画家在当时难以得知宋代样式,系无奈为之。
2.市井生活之别。在宋本里,较多地体现了北宋社会以生活必需品为主的生产与贸易的密切关系,社会经济处在蒸蒸日上的状态。明末虽然处于社会经济上升时期。但受到明万历以后宫廷极端享乐主义乃至颓废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市井文人中也出现与之相应的生活观念。明本中绘有许多晚明文人喜欢消费的场所,如琴店、书坊、画店、古玩店、瓷器店、肖像馆、扇铺、盆景店等,甚至有妓馆等。
在两本《清明上河图》中,表现市井生活不同之处的突出点还有对妓馆的描绘。在宋代,朝廷决不禁止市井里的色情活动,仅北宋初年的开封城就有一万多家“鬻色户”,甚至有官妓和私妓之分。汴京城里的妓院分布于大街小巷里的酒楼茶肆之中,甚至毫无顾忌地开到衙门口、寺庙外。如在城南朱雀门西过桥即投西大街。“向西去皆妓女馆舍,都人谓之‘院街”。在朱雀门外的“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在大相国寺的南面“即录事巷妓馆。……北即小甜水巷,巷内南食店甚盛,妓馆亦多”。在那里出现了包括名妓李师师在内的各种等级的妓女。
在汴京的酒店,还盛行以妓售酒的营销手段,这是起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的风习,“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令娼女坐肆作乐以蛊之”。这种售酒妓也是陪酒女。多如牛毛。宋本描绘了各类不同档次的酒馆,店内无一妓,没有一处直接描绘这类妓女活动及其场所,从侧面表明了张择端对此类事物的严肃态度,只是在一家豪华的“正店”门口,画上了四盏栀子形状的灯,据韩顺发先生考证,此系栀子灯,是在暗示顾客里面可以“买欢”。这种风习一直传播到南宋临安:“门首红栀子灯上,不以晴雨,必用箬赣盖之,以为记认。”据明代谢肇涮《五杂俎》和张岱《陶庵梦忆》等史料记载,晚明颓废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弥漫朝野,明初禁止“买良为娼”的法律已形同虚设,色情活动已经公开化。明本画中进城后的第一家就画出了“青楼”,在妓馆对面还有春药铺等,春药铺和妓馆分别开在城防关卡的右侧和对门,说明色情业在明代街肆的公开程度。明代宣德年间(1426—1435),朝廷虽然禁止官吏狎妓宿猖。但不久此令渐渐变成一纸空文。生活于城市中的文人,有不少热衷于风流倜傥的狷行,更以惊世骇俗为能事,明末画家陈洪绶“狎妓”韵事在当时文人中相当普遍。
明代文人中流行的纵欲主义思想,与明代思想家李贽鼓吹的“人欲论”有关。袁宏道则干脆放言:要“做世间酒色场中大快活人。”思想解禁最终是导致行为放浪。官宦、富贾和逸士们纷纷蓄养艺妓、登楼狎妓,并引以为快,引以为荣,引以为雅,形成整个社会的时代风尚。
3.园林之别。在宋本里,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园林图像,在当时的文人宅院后面就有精美的园林,如驸马都尉王诜家就建有名为“西园”的后花园,成为文人雅集场所,皇家园囿则更多,张择端没有表现这些园林美景,完全是出于表现市井百姓生活目的而进行了大胆的舍弃。
明本则增加了皇家园囿和贵族园林。比较而言明本的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下层的民间画家,画家去过一些富家私宅的后花园,但缺乏深入观察和体味其中的雅韵,与富家的接触尚欠亲密,画中只出现了一处富家园林。但表现比较牵强,缺乏雅致。明本卷尾皇家水上园林表现更捉襟见肘,缺乏宫廷建筑的基本常识,作为御苑,宫墙上和园中正殿上的琉璃瓦应该是黄色而不应该是绿色,绿色琉璃瓦是皇子们的用房,画家反而把侧殿画成了黄色琉璃瓦。此外。宫廷龙舟乃系皇家重船。操浆者不可能是弱不禁风的仕女。
五、绘画风格之别
首先,宋本很可能系一人所作,明本系画工作坊的产品,有可能是合作。两者艺术基调不尽相同,画家不同时代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不同的艺术追求,最终出现环同的艺术格调。两本具有共同的绘画主题,即表现繁荣的市井生活,明本还增加了皇家游乐活动,这些和绘画风格的形成或取向都有密切关系。
1.艺术格调之别。两本《清明上河图》在绘画创作上具有严格的写实态度。宋本则较多地融入了悲天悯人的气格。明本多一些享乐主义的成分,如描绘想象中的宫苑和喜庆场面等。宋本表现出的艺术格调凝重厚实和沉稳大度,张择端在接受宫廷艺术之后显现出审美多元性,故其艺术内涵之深、意蕴之厚,一般画家难以企及。明本则恰恰相反,成长于世俗社会的画家在稚拙中追求成熟,在变异中力求华艳,确切地说,明本是这类绘画题材在转型阶段中的代表作,它所表现出的探索意识,如汴京怎样变成苏州、如何表现噱头和追新求异、如何续上补绘本等。是俗文化的典型代表。
2.色彩之别。色彩是艺术格调的具体体现,在两件《清明上河图》卷里体现得十分真切。宋本以墨笔为主,稍加花青和淡赭。在色调上显得相当沉郁,甚至有些悲怆之感,十分符合人们在清明时节的悲悯心境。明本借鉴了青绿山水画的用色之法,整个画面亮丽鲜艳,个别地方甚至有些俗艳,这一色彩基调受到明代仇英山水和人物画风的影响,特别是卷尾皇家园林建筑金碧辉煌的色彩,如同给全曲敲击出了最为响亮的尾声。
3.画家的生活基础不同。两本的作者有不尽相同的生活阅历,宋本作者是从民间走向书斋。再从书斋走向宫廷画坛。明本作者长期置身于社会底层,以作画为营生。比较起来,宋本作者张择端对码头生活和漕运活动最为熟悉,甚至包括其中的生活细节,如对桅杆的处理、堤岸的结构、船桥的构造等都符合物体自身结构,特别是驳船因不同的载重量呈现出不同的吃水程度。在明本里。画家严重缺乏水上生活经验,船舶种类较少,几乎雷同,画中运河几乎没有画河堤,河畔基本上没有出现本应有的湿地植物,水浪画得过于汹涌且无虚实变化,将运河画得如同洪水一般,这是画家缺乏水上生活和忽视实地观察所导致的错误。
4.场景透视与人物透视之别。宋本和明本的透视都是散点透视,画家们都没有接触到来自西洋的焦点透视。比较而言,明本的透视结构有一些错乱,如城墙上垛子的透视关系没有处理好,占据了通道等。画家笔下船舶的透视、结构屡屡出错,造型过于概念化,如高高翘起的船尾透视显得十分生硬。船顶上有用竹木编制起来的可折叠的船帆,船与人物的比例显得小一些。
上述诸多内容都是通过画家笔下的线条显现出来的。线条最能体现出画家的艺术个性,宋本的线条简洁坚凝,其界画功底和山水笔墨胜于人物,建筑、舟桥的线条十分精雅,全无板滞之弊,人物造型生动稚拙而富有生活情趣,但人物结构尚欠准确。明本的人物活动颇为生动,线条则显得质朴但趋于简率,建筑、舟桥的线条缺乏描绘细节,生活于市俗之中的民间画家如果过于着意于商业目的。将会失去风俗画所应有的细微之处。
结语
张择端以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意识为宋徽宗绘制是图。画家特意表现出一些大的矛盾冲突如船桥之险、桥上的轿子与马匹争道等,象征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还描绘出全城毫无军事防范。希冀徽宗能够看到较为全面的社会现实。北宋官吏利用绘画向皇帝表述民情的手法不止一例。如熙宁七年(1074)是北宋的大灾之年。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借工匠绘制的《流民图》请求宋神宗停止王安石的变法活动。明本的作者基本上以享乐主义的态度绘制该图,以客观加猎奇描绘了当时苏州社会畸形的发展状况和稳固的城防措施,增加了许多噱头,迎合了当地富商们的审美需求。以求获得善价。这就是清明上河图的题材为何从清明节到喜庆日的内在原因。
不同的绘画目的导致艺术基调不同。宋本沉郁凝重,明本异彩浮艳,证实了同一个绘画题材在不同历史条件和艺术背景下,必然呈现各自不同的思想观念以及审美意蕴等。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此而论,两本《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中同名绘画鲜明的演化实例。
责任编辑:欧阳逸川 宋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