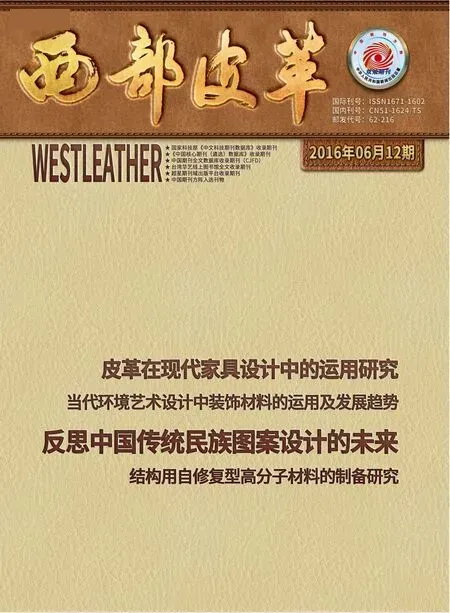罗伟章小说中“刺点”的符号学解读
——以《大河之舞》为例
罗会毅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罗伟章小说中“刺点”的符号学解读
——以《大河之舞》为例
罗会毅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刺点”是符号学中的一个概念。在艺术文本中,“刺点”不仅能够增添文本的艺术魅力,还能刺激读者的阅读欲望、发人深省。罗伟章的长篇小说《大河之舞》围绕“半岛人尚武、排外”这一核心刺点,又制造了“半岛中两个家庭之间的对峙与仇恨”这一“刺点”,并且通过一系列事件与这两个“刺点”搭配和组合,从而拓展了文本的张力,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关键词:刺点;符号学;《大河之舞》
巴尔特在《明室》中提出“Studium”和“Punctum”这一对概念,赵毅衡先生把它们译为“展面”和“刺点”,并对巴尔特的这对概念进行了阐释。赵毅衡先生认为:刺点就是在文本的一个组分上,聚合操作突然拓宽,使这个组分得到浓重投影。[1]赵毅衡先生还举例指出“诗的“练字”,相声中的包袱,戏剧出乎意料的亮点,晚会演出中别出心裁出乎意料的部分都是‘刺点’”。[2]由此类推,小说文本中埋下的伏笔、精心设置的情节、巧妙的艺术表达、深刻的主题揭示都可以称为“刺点”。长篇小说《大河之舞》通过描述川西北罗家坝上的罗疤子与罗建放两个家庭之间的恩怨情仇,展示半岛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接轨过程的复杂状况,展现出多重文化反思。
1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
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自春秋战国以来,大至邦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往来,小到亲朋好友之间的日常生活交往,礼都是备受推崇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对礼的推崇,使无数文人墨客吟诗作文,渐渐地使中国成为屹立于世界的礼仪之邦。随着现代文明的到来,“以‘礼’为中心的传统人际交往模式在当代与以法律、契约为主导的现代交往秩序并存发展”[3]。而与之相对的武力,除了战争年代用来保家卫国之外,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体育技能存在,如相扑、拳击。作者向读者展示的半岛人的世界活生生就是野蛮人的世界,尚武好斗是他们闻名三河流域的“法宝”“他们的脾气是微波炉,插上电就热,火力键一拧,就成高温。他们的交谈方式,不是用嘴而是用拳头。”[4]这是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交谈方式,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尚武好斗”成为半岛人文化的主要基因,而由这一特点衍生出了“排外,不侮辱人,不干苟且之事,行事光明磊落,打架不在于谁有理谁无理,而在于胜负其他的特点”等品质。半岛人的生存交往方式,即便在战乱纷飞的春秋战国也是罕见的,更遑论当今的文明社会。作者描述半岛人的世界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是陌生的,毕竟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崇尚武力的民族不多。“刺点,就是文化‘正常性’的断裂,就是日常状态的破坏,刺点就是艺术文本刺激‘读者式’解读,要求读者介入以求得狂喜的段落。”[5]半岛人尚武好斗的传统这一“刺点”的介入,拉开了大众接受常规阅读的期待视野。
崇尚武力解决问题的半岛人应是英勇无畏、所向披靡的,他们的决斗场面也该是惊心动魄、壮观无比的!但出人意料的是,小说中并没有一场真正的半岛人决斗的场面。小说总共出现过三次“武力”场面。第一次是发生在孩子之间,罗杰和东娃都是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就被对手打倒,对手之间无论是实力还是年龄的差距,都注定了这场角斗的不公平性。第二次是发生在罗疤子与罗建放之间,两人之间的冲突是由于罗杰与东娃的引起的冲突。第三次则是罗建放带着拿着家伙的村民到回龙中学“收复失地”,但村民们并没有动手并且在警员到来之前离散而去。这三次冲突,武力成分一次次减弱。
崇尚武力的民族,怎能不用武力解决问题了呢?这不仅是我们读者的疑问,也是半岛上一直想把罗家坝尚武的传统发扬光大的罗建放的疑惑。罗建放对于罗疤子不敢用刀劈自己的行为看不起他,并指责他不配做半岛人。罗建放带着村民去“收复失地”时,村民“既没有进厨房帮忙,也不在外面压阵!”[6]在他看来,“半岛将要毁了,半岛将不再是半岛人的半岛了!”[7]半岛人不再以武力解决问题,难道真的如陈副镇长所言,“绝大部分半岛人现在都变成文明,不愿意再跟着某些人胡闹了!”[8]此时,读者也会情不自禁去思考:半岛人文明化到底是好是坏?可以说,从文本看来,作者似乎并没有给读者一个明确的答案,反而在论述中时而显现出矛盾的情绪。半岛人排外,尤其是对于政府。20世纪30年代初半岛人当天拒绝接受政府战争后武力安置难民到半岛,把政府吓走后又把难民请回去,好生招待。作者借叙述者之口,这样评价此举“只是一种无效的挣扎,也可能是最后的挣扎。”[9]半岛人看似团结有主见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渐渐被外界社会瓦解同化的苗头。这种苗头便是通过“半岛中罗姓两个家庭之间的对峙与仇恨”这一“刺点”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显现的。
2核心刺点的颠覆是通过分刺点进一步离析与瓦解的
正是通过刺点的层层推进,文本不再是解释和揭示生活的立体结构,而是在传统与现代文明之中,立定一种半岛人的生活图景。罗秀疯子被人强奸怀孕是文本中埋下的一个很大的伏笔。罗疤子的女儿罗秀从三岁开始便患了疯病,不知从哪天起她怀孕了。这样一个只相过一次亲却以失败告终的黄花大闺女怎么可能怀孕?唯一的解释,就是被人强奸。半岛上的人行事一向光明磊落,干偷鸡摸狗之事是为人所不耻的。半岛上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人?随着故事的展开,最后真相大白:竟是一向以“真正的半岛人”自居的罗建放对罗秀做出这等半岛人所不耻的事。
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作者安排罗建放做了许多能够体现他作为半岛人的事情。第一宗便是上面提及的对罗疤子的侮辱。罗建放与罗疤子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文革期间”罗疤子带着众人批斗罗建放的父亲,使得他的父亲遭受众多苦难。罗建放对罗疤子最怀恨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他扇罗建放父亲耳光,“半岛人从不以侮辱的方式对待对手”[10],这是半岛人崇尚武力之外的另一不可侵犯之处,侮辱半岛人比杀了他们还更严重。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罗建放要与罗疤子决斗,但罗疤子未从,罗建放要罗疤子喊出“我是脓包”这样自取取辱的事。第二宗便是上面提到的罗建放带人到回龙中学“收复失地”的事。从这次动员半岛人一同前去发动“武力”之事,半岛人没有积极响应罗建放的号召,而是罗建放用肉去请他们才勉强答应了这一要求。在罗建放看来,这是半岛人的耻辱,以前遇到捍卫半岛人土地这回事,无须请求,云聚响应。在这两件事中,罗建放的儿子东娃也被作者塑造成英勇无畏、血气方刚的少年。换而言之,似乎罗建放才是半岛上的希望,是拯救其他人被外界所同化的最后救命稻草。但出人意料的是,罗建放这一形象刚刚塑造成形,作者却把罗秀被强奸的事安排在他身上,“真正半岛人”的形象轰然倒塌。
如果说,罗建放算不上真正的半岛人,那巴人的精神与灵魂就无人继承了吗?从作者为我们安排的罗杰后来的成长过程与结局,却似乎并不如此。那么罗杰俨然是冉冉升起的巴人形象?
文中的罗杰从小不喜欢与半岛其他人接触,而是整日守护在疯子姐姐罗秀的身边。罗秀难产逝世后,罗杰就一直保护着姐姐的女儿“巴艳”的坟头。到回龙中学读书时,行为举止怪诞,不爱学习,却喜欢上像自己姐姐的夏老师。夏老师因个人私事问题回到故乡重庆后,因各种原因辍学的罗杰也开始了自己浪迹天涯的苦累生活。历经千辛万苦、人事沧桑的罗杰风光满面地回到故乡。在罗杰还没有荣归故里的时候,作者安排了一次考古事件。考古队挖出的M22号墓地墓主背部伤痕累累的白骨与罗杰时不时的背痛不谋而合,罗杰的父母认为被推测为贵族或首领的墓主就是罗杰。这一前一后的安排,罗杰似乎就成了半岛上的伟人。此外,在罗疤子与罗建放父辈两代的较量中,从结局来看,是罗疤子家取胜。罗建放被自己的儿子弯刀劈死,东娃也因杀死父亲被处以死刑,只留下孤苦伶仃的母亲艰难度日。而罗疤子一家却幸福美满地生活于世,罗杰的腰囊鼓鼓更是为他们家赢得了骄傲。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罗疤子一家都是幸福无比的。但出人意料的是,罗杰却不这么认为。罗杰原本以为东娃一死,他就胜利了。但当东娃死之后,他却陷入了迷茫。“他们的较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谁败了?谁胜了?”[11]作者借叙述者之口传递的不仅是罗杰的疑惑,同样也是的疑惑:真正的半岛人是谁?
真正的半岛人是否存在令人疑惑,而真正的半岛文化是否遗存也引人深思。摆手舞是半岛人的特权,几千年来已经沉淀为他们的民族文化。“在文化的不同领域中,文化的‘自我交际’(autoeornmunieation)与‘身份自我追寻’(identiysearch)使得文化语言产生了特殊性”。[12]摆手舞这种肢体语言是半岛人交际交往的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模式,是他们作为半岛人的“文化身份认证”。围绕着摆手舞作者设置了罗秀疯子被强奸、罗建放请大家跳摆手舞、巴艳跳摆手舞三个事件。这三个事件,让人看到的是曾经作为巴人祖先传下来的艺术也不再是那么纯净了,而是掺杂着各种复杂人事。罗秀就是在跳舞的当晚被罗建放奸污的,罗建放请大家跳摆手舞也是为了侮辱罗疤子。罗建放请了所有的人去跳摆手舞,除了罗疤子之外。“你不来,并不能证明你有脸面,恰恰说明你没有脸面,因为祖先传下来的舞蹈你都不敢跳。”[13]而巴艳以非半岛人身份出现跳摆手舞这事,罗建放一声不吭。“按照罗建放的原则,绝不允许一个与半岛不想干的会跳把手舞。”[14]原因在于:罗建放早从巴艳的长相中,看出她就就是自己强奸罗秀所得的亲生女儿。亲情的力量使罗建放这个一向以真正半岛人自称的硬汉形象放弃了矢志不渝的坚守。罗建放乱伦罗秀之事败露后,从罗建放的话语中,读者能够明白:罗建放对罗疤子所做的一切侮辱性事件都是希望罗疤子能够赐自己一死,赎当年那个晚上奸污罗秀的罪。他以各种方式来证明半岛人的英勇,却无济于事。“罗疤子几人,是明明白白地坏规矩,罗建放却做得偷偷摸摸。”[15]
半岛人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与优良品质的渐趋消失,除了半岛人自我内部原因外,也与外部因素的渗透密不可分。外部因素中我们看到“半岛人供他们吃,供他们住,贵客一样招待,直到万源大山平静下来,难民放心大胆地返乡为止。”[16]半岛人是排外的,此举为何?这决不是他们的善良本性使然,而是对当权者的惧怕。 “文革”期间,罗疤子批斗罗建放父亲,是受当时“牛鬼蛇神”的摆布。这外面来的“牛鬼蛇神”破坏了半岛内部的团结。罗建放以“真正的半岛人”自居,按理外面的想法对他应是刀枪不入的。但从罗建放对父亲头上的“地主”帽子耿耿于怀,而当父亲的帽子被摘后,他请半岛人喝酒跳舞庆祝这一前一后的反应来看,并非如此。正如罗疤子所说,“我需要半岛外面的想法,未必罗建放就不需要,为啥外面摘掉了他爹头上那顶早就无关紧要的帽子,他就高兴成那样了!”[17]罗传明是半岛上第一个不靠武力走出半岛的知识分子,是半岛上的第一个“叛徒”,他不仅接受来了外面的知识,也接受了外面人的处事方式。“在他眼里,半岛是血肉之躯,有呼吸,有体温,也有感情,总之不是由‘传统’留下的遗物,而是鲜活的生命,比遗物更珍贵,也更令人痛惜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唯一,这是半岛的全部价值。”[18]罗传明却从不承认这欲加之罪,自己虽不推崇武力,但想法仍是半岛人的想法。而从去恩人罗建放父亲摘“地主”帽子后上坟的方式由以前的偷偷摸摸到现在大白天去的变化,也使罗传明承认自己是被“外面的想法”所控制和摆布的人。罗杰作为半岛上的第一个走出半岛的人,不仅走南闯北的去外面的世界赚过钱,还帮助政府动员半岛人迁出半岛。半岛上的年轻人,他们更是走出半岛,被外面的世界所淹没。“这些年轻人,离开古老的骄傲,跟三河流域的年轻人一样,去了外面的世界。”[19]
尚武、排外、跳摆手舞等半岛人的一些习惯及习俗都渐渐地远去,伴之而去的是半岛人内部的团结,淳朴的民风。但半岛人也获得了知识,获得了与外面世界的接触,而不是处于与世隔绝的荒芜之地。外面的世界对半岛人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引人深思。
总之,《大河之舞》意味深长,这离不开罗伟章在小说中核心刺点与分刺点的恰当设置。小说正是通过刺点的不断“节外生枝”,推动故事意义的发展,在意义的探寻下,反思现代文明的价值景观。从而使小说的主题意蕴得以深化,彰显出作家讲故事的艺术宗旨,拓展了文本叙事的内在张力。
参考文献:
[1]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169.
[2]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169.
[3]赵星植.论礼物的普遍分类:一个符号学分析[J].符号与传媒,2014(1).
[5]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p.169.
[12]马西莫.莱昂著,钱亚旭译.从理论到分析:对文化符号学的反思[J].符号与传媒,2013(2).
[4][6][7][8][9][10][11][13][14][15][16][17][18][19]罗伟章.大河之舞[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p.6.152.155.155.8.66.346.127.272.288.6.127.166.298.
作者简介:罗会毅,男,贵州铜仁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602(2016)12-027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