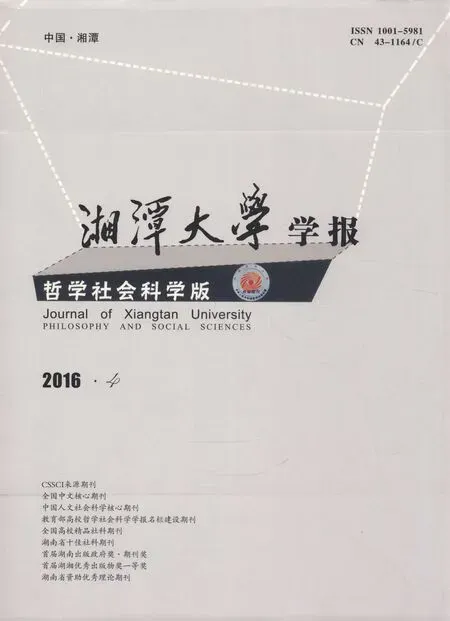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再探析*
李 戈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再探析*
李 戈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如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重要的二级学科已有十年,但作为这一专业领域研究的前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在学界仍然存在不同的解读。分析研究党的历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认识,梳理并评析学界已有观点,并从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四对范畴入手整体性地厘清其科学内涵,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开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其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所取得的每一个伟大成就,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展紧紧相连。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断丰富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这一带有前提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在学界仍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解读。我们迫切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演进历程和学界已有观点的梳理入手,厘清其科学内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认识和演变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无产阶级借以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指出,他的学说“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但对于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规律性认知并不能离开现实的历史而存在,“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153这种理论特质使得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开始就内在地要求将自己同中国的具体现实结合起来。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瞿秋白等在不同场合已经表露出了类似的思想。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曾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2]3他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也曾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3]5瞿秋白也曾指出:“革命的理论永远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为此,“得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4]310在这一时期《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过程中知识分子群体也注意到了将欧洲的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做了中国化的转换,为马克思主义立足中国打下了文本上的基础。但由于此时马克思主义刚刚在中国传播开来,翻译、阐释和启蒙还是其首要任务,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尚不成熟,这些思想萌芽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并未真正融会到革命实践中去。
抗日战争初期,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经历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从正反两方面为党提供了丰富经验。更为现实地与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斗争,也迫切需要党正确回答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等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这段经典论述中,毛泽东深刻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651在这里,毛泽东清晰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适应性结合,这种结合内在地要求我们“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并且赋予这种结合以充分的民族形式。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倡者,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6]335周恩来则指出:“(共产主义)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7]139这些论述一方面肯定了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卓越贡献。另一方面也表明,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以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已经成为全党理论上的共识和自觉地行动。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探讨与传播以及对于中国现实国情的研究,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等,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建构提供了有益参考。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打消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化的顾虑,毛泽东在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修订了相关篇目的措辞,将“中国化”提法删去,代之以“具体化”,但其内涵实质并未发生改变。党在随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遭遇了严重的曲折,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成为曲折产生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邓小平尽管并未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但仍然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8]146“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8]291相较于毛泽东的论述,邓小平保持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进一步凸显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发展这一创新维度。在这之后,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多次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江泽民在论述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历史地位时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9]1900胡锦涛指出:“三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10]796这些论述表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不断总结凝练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主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新的高度。习近平从发展的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11]114为此,“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11]697另一方面着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一维度,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12]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总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者和探索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经历了曲折之后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和应用适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排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干扰,正确处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基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条件,紧扣时代脉搏,创立、发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着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土壤和凝聚民族力量、推动民族复兴的精神宝库的重大意义,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高度。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演变线索,我们可以发现,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问题意识,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经历了从侧重民族化到侧重时代化,再到积极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养分这样一条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的发展路径。
二、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解读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其前提条件是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但在这一问题上,学界存在着诸多不同视角的解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三种解释框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解释框架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分歧,其差异仅仅在于解释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
第一种解释框架是“多重内涵论”,其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多个互相联系的内涵板块所共同构成的概念整体。这种解释框架也是目前学术界解读框架的主流。例如,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为双重内涵,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3]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为三重内涵,即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提升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为理论,植根马克思主义于中国优秀文化之中;[14]17-26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为五重内涵,即“‘立足中国国情’(横向总体)、‘总结中国经验’(纵向历史)、‘汲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过去)、‘反映当代中国实践’(现在)和‘解决中国问题’(目的)”。[15]23也有学者从思想史的视角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置于其概念提出的起点,即1938年前后的历史情境当中去加以考察,基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具体阐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归纳为五重内涵:其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其二,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三,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总结中国历史、整理中国文化;其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中国文化的形式和特点;其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开放、持续的过程。[16]336-338在这其中,三重内涵的解读成为学界的主流共识,2015年修订版的教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三层表述,即“第一,紧密联系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问题;第二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三,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17]4-5即是基于此。
“多重内涵论”的科学之处在于,充分顾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其内部各元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解释框架下,学者们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基于矛盾运动的不同路径进行深入剖析,使得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得到充分的展现。但其不足则在于,多数研究是在“二重内涵说”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学术旨趣进行增添,各个内涵维度之间有简单并列之嫌,导致内涵定义臃肿而无法突出主次元素的差别,也未能很好揭示其内涵构成的历史动态性。
第二种解释框架是“过程论”,其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着重考察这一概念的生成过程、阶段及其源流并从中把握其内涵。实际上,学界早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这三个基本方面,它是一个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18]类似的“结合论”表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入“过程论”当中,因为其关于结合的论述已经内在地包含动态性和开放性的意蕴。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也秉持这一基本思路,学者们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这一宏观背景之下,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出发,分阶段多层次的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基本经验。[19][20]还有学者进一步在抽象层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态生成过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视作“是由对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而言的外生、内生形态的渐次生成、循环演进所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它并不是“一次成型、一成不变的凝固抽象体”。[21]
这一视角针对目前学界主流的“多重内涵”式的解读所欠缺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各要素之间具体历史联系作了有益补充,还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思想史概念的演进历程。但对于历史丰富性的强调也使得这一视角下的理论叙述流于琐碎,难以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要素和精神实质,更有甚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动态性的强调会导致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源与流关系的认识偏差,存在着模糊马克思主义方向的隐患。
第三种解释框架是“层次论”,其特征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沿着特定维度划分为平行的数个层次,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政治与学术、实践与文化的二分。有学者认为,我们通常所讲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政治层面的中国化,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则是指“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中国化,其任务就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22]中国目前的问题在于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已取得重大成果,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却明显滞后。另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相结合”;其二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相结合”,并指出“从文化的认同到实践的契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过程”。[23]
这种“分层”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益角度,但其揭示的仅仅是一个侧面而非全貌,也往往造成作为有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概念被人为割裂开来。例如,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区分为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也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和作为实现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这两重地位之间人为地对立起来,似乎学术和政治可以截然分开并且难以统一。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话语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告诉我们,学术层面的探索可以为政治思想的形成做有益铺垫,[24]政治层面的思想与实践也深刻形塑着学术发展的方向,将两者进行区分而不作统一的理解,难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三、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不断丰富深化的过程,并非一个简单的规定性概念,而是包含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中国现实问题、中国建设实践、中国具体实际、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以及其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等诸多元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体系。目前,学界已有的研究紧紧跟随了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界定,并在此基础上从不同解释框架出发衍生出不同的内涵表述,但这些论述散乱之余也存在各自的不足,要完整统摄这些元素并提出清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需要我们从以下几对范畴入手进行系统梳理。
一是理论与实践的范畴。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最基本的一对范畴,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骨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体系想要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程,就不能停留在远离现实的抽象层面,而必须时刻面向中国的现实问题,运用理论自身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去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理论与实践的有血有肉的联系。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到实践中去,其内在地也要求将实践产生的众多宝贵经验进行提炼,升华为理论,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实践-理论”的运动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了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25]374他所论述的正是这一层意思。全面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就是要将其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互动共进的过程。
二是普遍与特殊的范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之所以成立,其根基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普遍性真理的地位,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就无从谈起。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区分两个问题,“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怎样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26]前一个问题的答案寓于普遍性之中,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普遍性,它一定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则寓于特殊性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也只有通过与中国具体的实际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更进一步,这里的特殊性也拥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横向意义上的特殊性,即民族性;另一个则是纵向意义上的特殊性,即时代性。特殊性的这两层含义,分别对应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民族化和时代化的两大主题。全面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就是既要防止片面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要防止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而落入教条主义的陷阱。
三是主体与客体的范畴。学术界已有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阐述,往往缺乏对这一概念不断演进过程中各元素主、客体地位的论述。在理论层面,主客体范畴的探讨要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谁去“化”谁的问题。例如,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时,学术界一些学者宣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伦理化,其实质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体地位,用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这一错误倾向必须得到遏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的悠久历史积淀和传统文化当然是中国实际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我们必须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这一丰厚的历史遗产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批判性的加以鉴别和吸收。全面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就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和理论自信,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养分,这不仅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带有鲜明的民族特性,也会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迈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
四是内容与形式的范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中国化,也是其承载形式的中国化。内容层面的中国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褪去空洞和抽象,建立起面向中国现实问题、服务中国建设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式层面的中国化,则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通过民族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并通过符合中国实际的制度形式落在实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概念的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即是个中典范。全面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向中国实际,并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以上四对范畴作为经纬线,精确框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本质。在四对范畴的梳理中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表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并将这一结合过程中的实践经验经过提炼加工上升为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形成在内容上民族化和时代化、在形式上富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总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逐渐展开,到毛泽东时正式提出,并在随后经历了不断深化地探索过程。当前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仍存在不同解读,这难免带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理研究中在问题域挖掘和方法论选择上的种种偏差。从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四对范畴入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表述更为清晰,有助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2]李大钊文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李大钊文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瞿秋白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五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周恩来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2]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9-25.
[13]顾海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论要[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1).
[14]张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15]韩庆祥. 从整体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解[C]//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6]丁俊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一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7]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18]陈占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1).
[19]梅荣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肖士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渐次生成及其外生、内生形态的循环演进[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22]许全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区分[J]. 理论前沿,2003(18).
[23]李海荣. 从文化认同到实践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过程[J]. 学术论坛,2002(3).
[24]欧阳奇. 论理论工作者群体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作用——以艾思奇和何干之、陈翰笙、吕振羽、周扬为考察对象[J]. 毛泽东研究,2015(5).
[25]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6]周新城. 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说起[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4).
责任编辑:熊先兰
Re-analysis of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bout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LI Ge
(School of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In October 1938, Mao Zedong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of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on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ix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t has been ten years since the research on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became an important secondary discipline under the Marxism theory as a first level discipline. As the pre-conditional question of this field,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notation of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We need to stud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by the successive leaders of the Party and review the existing academic viewpoints so that we can clarify 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reas,theory and practice, general and special, subject and object, content and form. In summary,these woul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scientific connotation
2016-04-29
李戈(1989-),男,陕西宝鸡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A81
A
1001-5981(2016)04-013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