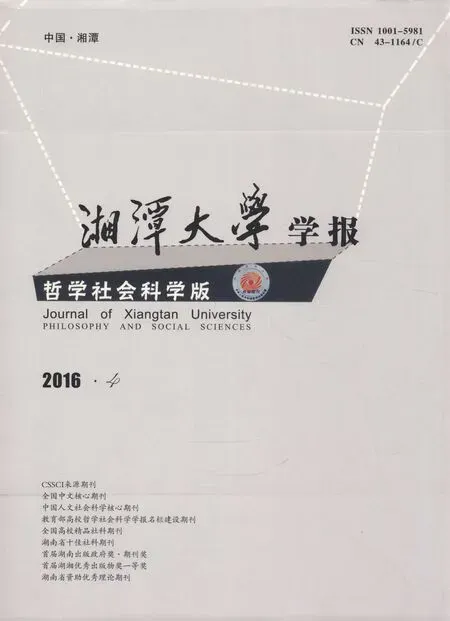柳鸣九的波伏瓦评介及男性化误读*
王 芳
(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女性主义文学/性别研究”专栏(3篇)
柳鸣九的波伏瓦评介及男性化误读*
王 芳
(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堪称“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的柳鸣九,亦是较早研究波伏瓦的学者。他的研究是早期中国波伏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法国文学评论界对波伏瓦的评价和定位。柳鸣九认为:波伏瓦的作品极具史料价值;实现了反抗传统、追求自由的自我形象建构;表明其在与萨特的关系中处从属地位。柳鸣九的波伏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男性中心思维的局限。
柳鸣九的波伏瓦评介;自我形象建构;男性中心思维
柳鸣九以其对法国文学研究的特殊贡献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是三卷本《法国文学史》的主编,翻译、主编外国文学作品及理论,撰写了不少文学评论、随笔,“可谓著译等身”[1]107。柳鸣九是中国法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有“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之称,他为萨特真正意义上进入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及萨特,人们自然联想起波伏瓦,《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正是柳鸣九主编《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10卷本中的作品。柳鸣九对波伏瓦有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价。
柳鸣九曾评价说:“波伏娃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可算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她细腻的女性风格早就得到了法国乃至世界文坛的认可。萨特的确使她的声名更加响亮,但没有萨特,她也一样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她的《第二性》在文坛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她的小说也极有成就……”[2]51柳鸣九评述波伏瓦的文字虽不算多,但着意深刻、言之有物。作为一位资深的法国文学研究者,柳鸣九以法国文学传统为背景,在对法国文学史作出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对波伏瓦作出评价,其研究对文学研究者极具参考价值。柳鸣九指出:《名士风流》、《第二性》和回忆录是波伏瓦那“一大片文字海洋中”“几个突出于水面之上的陆屿顶峰”[3]1,从评述看,柳鸣九对波伏瓦作品中的自传性以及她与萨特特殊的两性关系作了特别关注。因此,本文着眼波伏瓦的回忆录、《名士风流》、《女宾》和《美丽的形象》。
一、波伏瓦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柳鸣九认为,“在20世纪法国文学中,西蒙娜·德·波伏瓦无疑是一个最大的回忆录作家……至今仍然是无人出其右的。”[3]2进而指出:波伏瓦具有“充分而为社会广泛承认的自我价值”,她与萨特这个“第一流大作家”、20世纪思想发展“里程碑”式的人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精神实体”,他们结交了“同时代思想文化界几乎所有的精英”,这“构成了她写回忆录深厚的生活基础”[3]3。除了回忆录,波伏瓦的重要作品,如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名士风流》、其成名作《女宾》,都带有明显的自传性。作品不但记录了20世纪30至70年代法国乃至欧洲的社会历史状况,还介绍了当时的文学与文化动态,呈现了存在主义文学的发展脉络。
波伏瓦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回忆录和《名士风流》中。她在回忆录中追求历史真实性,描述她和精英朋友耳闻目睹的一些重大事件,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广播和报刊报导的重大新闻、民众关注的社会热点、波伏瓦及其群体印象深刻的或极具文化意义的事件。柳鸣九因而称波伏瓦的回忆录为一部“编年史”、“大事纪”[3]7。而发表于1954年的《名士风流》则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三到四年间的社会图景:战后的世态凄凉、国土破败和社会危机。
波伏瓦的作品是当时重要文学事件和精英人物的珍贵记录。她几乎逐年记载了当时法国和欧洲出现的重要电影、戏剧和文学作品,并表达了自己的观感和阅读感受,进而对剧情、演员、作品和作家加以个性化的评说。在一定程度上,她的作品勾勒出“西方文学发展的某种侧影”[3]7。由于波伏瓦和萨特交友广泛,与当时多国的文学艺术领域的杰出人物多有交往,得以在回忆录中记入与他们的交往、见闻和重要活动,对他们的个性也有生动传神的勾画。因存在亲疏好恶和思想立场的差异,勾画中未免“带有相当强烈的主观色彩”,虽难免有失偏颇,但依然不失为一个文坛掌故的“档案库”[3]8。《名士风流》描述了二战结束前后短短三四年间巴黎一群知识精英“在困顿中的自我选择”[4]3。波伏瓦在小说中展现的是她和萨特所处的阶层和社会圈子,他们在战后错综复杂的严峻社会现实中遭遇的困顿、迷茫中的自我选择,他们持有的立场、精神状态与心理历程。在小说主要人物迪布勒伊、亨利、安娜身上融入了萨特、加缪和波伏瓦自己的某些特征、经历和立场,刘易斯则是以美国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为原型,其他许多人物也都有波伏瓦熟悉的人物的影子。
波伏瓦回忆录“最主要的价值还在于它是存在主义文学这一战后最重大的精神现象历史发展的一份最有权威的记载”[3]8。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创建者萨特最亲密的思想交流者和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波伏瓦在回忆录中真实地记录了存在主义创建并被贴上标签后风靡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始末,以及存在主义作品连同他们自己受到的种种评价和所处境遇,波伏瓦在书中还为自己和萨特的作品受到不公正的评价和待遇进行了辩解。柳鸣九对此分析后得出结论:波伏瓦和萨特赞同和支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3]12,他们是“具有一定程度社会主义色彩的存在主义者”[3]16。此外,他们“自我选择”的哲学思想对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发掘主体意识有着积极的意义,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十分盛行。柳鸣九曾在回答《南方都市报》记者关于中国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自由选择思想影响的问题时总结道:“事实上知识界的精英很少有人没有读过萨特,可以说萨特‘自我选择’的哲理曾经守护了一代人的精神摇篮。”[5]281波伏瓦的回忆录为影响如此广泛、深远的哲学和文学的发展轨迹留下了历史记录,无疑是研究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不可多得且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二、反抗传统、追求自由——波伏瓦作品中自我形象的建构
在柳鸣九看来,波伏瓦不但用作品记录了法国乃至欧洲20世纪数十年间的社会历史状况,还通过作品建构了“一个反抗传统、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这个女性形象就是波伏瓦自己。波伏瓦继承了卢梭自我剖析的传统,力求在回忆录中“展现出自己作为一个不平凡女性”的“特殊的女性状态”[3]17。这个女性形象的特殊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以自食其力来赢得独立人格。波伏瓦认为自己是弄清妇女生存状况、摆脱女性依附角色的合适人选。她把写作当成独立自由的标志,在少女时代就将成为名作家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她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学习,取得哲学教师资格证,成为哲学教师,从而摆脱了家庭的教管,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和追求自我发展的自由。
其二,为实现成为名作家的理想而放弃婚姻和生育。为了成为作家,波伏瓦广泛涉猎,努力充实自己,参入社会生活,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并勤于练笔,甚至决心以避免生育的方式来赢得创作所需的时间和自由。柳鸣九认为这是对传统的极大挑战,因为“按照传统观念看来,她这种决心,既牺牲了人性的天伦之乐,又是一种应该加以责难的‘有失天职’”。[3]18
其三,以女性身份取得成功正是对男权社会的叛逆。当存在主义风靡一时,波伏瓦和萨特作为存在主义作家而声名远扬的时候,波伏瓦在“沾沾自喜”中“满怀叛逆情绪的欢乐”[3]18。对此,柳鸣九解释道,“这是一个女人在男性上帝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在只有极少数杰出男性才能问津的精神文化创造的领域里得到了社会承认后所体验的欢乐,它无疑带有一种发泄性与报复性”,有时甚至“骇世惊俗”,当波伏瓦的《第二性》引起众声谩骂时,她“在坏名声中自得其乐”[3]19。波伏瓦从谩骂中反而感受到了成功,体验了与男性平起平坐以及突破传统女性状态的乐趣。
其四,以性开放的态度和生活来反叛传统。柳鸣九认为,也许“波伏瓦反传统的自我个性,主要是体现在她的性爱关系上”[3]20。她与萨特签下情侣协议,过着不排除“偶然爱情”且互不隐瞒的情侣生活。波伏瓦在回忆录中坦承自己的情欲和情人、与萨特的艳遇以及两人各自的情爱经历。这种先锋性的情爱生活,无疑是波伏瓦投向传统式婚姻和爱情的重磅炸弹。柳鸣九对此未作直接的评判,但却对波伏瓦不加遮掩的真诚坦白和真实个性加以赞许。
三、柳鸣九波伏瓦评价的男性中心误读
柳鸣九未对波伏瓦的性开放的观念和作风作出任何褒贬,但对这种完全的性开放表示十分诧异,难以理解。在涉及两性关系的评述中,柳鸣九指出:波伏瓦并未如她的回忆录和《第二性》所想要表现的那样坦然地接受萨特的艳遇,相反,她是被动地接受这种关系并为此深感痛苦。如此一来,波伏瓦意欲树立的反叛、独立形象则难以成立。
柳鸣九进而认为:波伏瓦和萨特契约式的伴侣关系以及他们与奥尔加的“三重奏”关系,均是由萨特提出并主导的,波伏瓦只是被动承受。波伏瓦与奥尔格伦和朗兹曼的热切爱情“相当清楚地表露出了西蒙娜·德·波伏瓦作为萨特契约式的生活伴侣那种冷寂落寞的少妇闺愁”[3]23。“在这一永恒的、深刻的、牢不可破的关系中,西蒙娜·德·波伏瓦无疑是居于从属的地位,但她为了保持这一关系所作出的努力与牺牲,对于一个女性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她为了文学事业却决不与萨特分离”[3]23-24。
纵览柳鸣九关于波伏瓦的评价,他的分析主要建立在波伏瓦的回忆录以及带有自传性的几部作品的基础上,无疑有一定的根据;但作进一步思考,我们不难读出柳鸣九在波伏瓦的性观念及私人生活方面的男性中心误读,这种误读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柳鸣九对波伏瓦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误读首先体现在契约式爱情由谁主导的问题。柳鸣九认为这是由不专情的萨特提出,而波伏瓦只是消极接受。柳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同行评论中不乏类似的看法。如果说波伏瓦的回忆录和带有自传性的作品是柳鸣九的评论根据,我们却能从中得出不同的结论。1925年,17岁的波伏瓦爱上了自己的表兄雅克。波伏瓦的好友埃尔博希望她嫁给雅克或者嫁给其他人,因为按照当时社会的传统观念,女人只能为丈夫献身,而男人过了18岁若还是童男则是“神经病患者”[6]327。波伏瓦表示,这是世俗偏见,她坚持认为:“女人应该像男人一样自由处置自己的肉体”[6]327。埃尔博则认为,社会只尊重已婚妇女;波伏瓦对此的态度却是:“我不在意是否受到尊重,和雅克生活在一起,和同他结婚,对我来讲是合二为一的。”[6]327当波伏瓦看到朋友与推着婴儿车的妻子在一起时,她“热切地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在我的将来中出现”,“两个彼此爱恋着的人的唯一联系应该只有爱情”[6]327。这些表明,她在与萨特成为情侣之前,就十分重视女性的性自由,并且不希望受到婚姻和子女的束缚,而将爱情置于两性关系的中心,认为联系恋人的只有也只能是爱情,至于在一起的形式是同居还是婚姻并无区别。波伏瓦反对男人拥有性自由而女人应坚守贞操的传统偏见,不在乎传统对于女性的道德评判,由此可见,波伏瓦拒绝婚育束缚的思想清晰可辨。后来,萨特对波伏瓦说:“从今以后,我将负责保护你”[6]341,但波伏瓦在与萨特的相处中认识到他“只为写作而活着”,对婚姻“没有一句赞词”[6]343,“他将永远不会成为父亲,他也决不会成为一个已婚者”,他“不受任何占有物的阻碍”,而波伏瓦赞赏“性的超越”,她意识到“除了一点细微的差别外,我发现他(萨特)的人生态度和我的人生态度之间极为相似”[6]344。波伏瓦和萨特对于性自由、婚姻的看法与观念非常接近,而且他们都认同为了文学的理想和人生的信条而放弃婚育。其实,不止波伏瓦和萨特,还有不少作家“视婚姻为爱情、自由、诗情的对立物”[7]4,这其中不乏普希金、拜伦、托尔斯泰这样的大文豪。因而,波伏瓦和萨特在成为情侣后选择了契约式爱情,原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谈不上萨特主导,波伏瓦被动接受。
第二个误读是波伏瓦作为萨特伴侣的“少妇闺愁”。萨特“对女性的友谊很有兴趣”[6]341,一生中情人众多。柳鸣九指出:波伏瓦在回忆录中已表明了这种情况,波伏瓦因此常“陷于嫉妒、空寂、哀怨的心态”[3]22-23。笔者认为,恋爱会使人产生丰富、复杂甚至矛盾的情绪,人人如此,因而波伏瓦在与萨特共同的生活中有时产生失落情绪极为正常,并不值得特别强调。柳鸣九以波伏瓦跟美国作家奥尔格伦恋爱时的心动、投入,分手时的伤心,以及得到朗兹曼爱慕时的感动和重新焕发性爱激情为例来证明波伏瓦在与萨特关系中的失意,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读过《永别的仪式》和《被勾引姑娘的回忆》的读者均有所知,萨特喜欢同女性交往,但对实质意义上的性生活并不感兴趣,他只喜欢交谈、抚摸,且有性虐待倾向。而波伏瓦则生命力旺盛、精力充沛,对性充满尝试欲和冒险精神,这样,“从40年代中期以后,萨特与波伏瓦的关系就更主要地演化为一种文学的、事业的关系。”[8]85在此情形下,波伏瓦先后拥有过与奥尔格伦和朗兹曼的动人爱情,有时还拥有其他情人,甚至还有同性恋的情人,这些事实恰恰说明波伏瓦在处置自己肉体方面的自由,而并非只是拥有落寞闺愁却坚持守护萨特身旁的“良家”少妇。若以波伏瓦在萨特之外找到激情就证明波伏瓦在与萨特的关系中感到寂寥,那么萨特也有许多波伏瓦之外的情人,是否也能说明他在与波伏瓦的关系中感到寂寥呢?事实上,女性的所谓“艳遇”常会被寻以寂寞之名,而男性的“艳遇”则被称之为风流。虽然波伏瓦未曾与萨特成婚,但多数人仍习惯于用解读婚姻的方式来解读他们的这种特殊关系。
进而的误读是关于波伏瓦是否为了萨特而离开深爱的奥尔格伦。波伏瓦虽钟情于奥尔格伦,并自称是他的“妻子”,但二人最终分道扬镳。此种结果表面上看是波伏瓦不能离开萨特,实质上却是“她为了文学事业却决不与萨特分离”。此时的她看重的并非作为情侣的萨特,而是作为文学、思想、政治伙伴的萨特。与奥尔格伦分手的另一个原因是,奥尔格伦希望与她结婚,若婚后随其去美国定居,这对将文学事业作为毕生追求的波伏瓦来说,是绝不能接受的损失,离开巴黎、离开法国,意味着她失去创作的素材、灵感和源泉;若二人定居法国,奥尔格伦的创作则会受损,在此种情况下,身为作家的他们只能割舍、分离。因此,以此来证明波伏瓦在与萨特的情感中处于从属地位并不能成立,而世人却乐于将波伏瓦描述成为了萨特而舍弃奥尔格伦,从而树立她对萨特依赖和妥协的形象。殊不知,这正是传统“男主女从”思想造成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在作祟。
再有的误读是关于“三重奏”的说词。波伏瓦在回忆录和《女宾》中都描写了关于波伏瓦、萨特和他们的学生奥尔加组成的“三重奏”故事。比安卡·朗布兰则在《被勾引姑娘的回忆》中叙述了他们另一段“三重奏”的故事。波伏瓦和萨特的性开放行为——其中包括“三重奏”的生活——首先来自于他们将自由尊为首位的人生原则和信念,他们将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当做一项权利,性自由自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原因出于他们把写作奉为毕生的追求,创作需要丰富的、甚至是不同寻常的人生体验,自传性小说《女宾》引起轰动并取得成功的例子即可为证。萨特在1974年跟波伏瓦的谈话中坦言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作为一个作家,我应该同许多女人有恋爱关系,充满激情,等等。这是我从关于大作家的书中学来的。”[9]341而15岁就立志当一位名作家的波伏瓦,显然也不打算过“循规蹈矩”的生活。20岁时,她就常背着父母在酒吧装成妓女与陌生的顾客喝酒胡闹,或是扮成不良少女与一些小流氓搭讪厮混,并从中得到“冒犯礼仪和权威”[6]272的快乐和满足。波伏瓦与儿时的同学“扎扎”有着非同寻常的姐妹情谊;另外,在她与萨特、奥尔加或比安卡·朗布兰组成的“三重奏”中,不仅萨特与参与其中的第三位女性有情爱关系,波伏瓦也同样分享甚至可以说是更多地分享了这些女性的爱情,比安卡的回忆录可证实这一点。
波伏瓦和萨特从未停止在“三重奏”或其他爱情历险中观察和分析人性,体察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感悟和记录生命存在的哲理。他们的“三重奏”生活带有很强的实验性,甚至有着某种哲学探索的意味。波伏瓦在回忆录中叙述与奥尔加组成的小家庭生活时,除了讲述事件的发展过程,还在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停下笔来描述他们三个人各自的处境、感受、心态和表现,并分析其中的原因。波伏瓦在这种关系中从未“感到自在”,且由于两人关系变成了三人关系,波伏瓦与萨特和奥尔加原本拥有的亲密情谊突然间都被另一个人分享,使得波伏瓦在三人同处时“感到双重的失意”[10]280-281。波伏瓦在此中发现,“奥尔加也处境艰难”[10]281。波伏瓦认为自己“比萨特更招她(奥尔加)喜欢”,但波伏瓦却“坚定地与他(萨特)站在一起”;奥尔加则一面与萨特不断发生争吵,一面又担心因此伤害与波伏瓦的感情,因而在这三人关系中常感“忐忑不安”、“惊慌失措”,甚至“恐惧”[10]283。与此同时,“很难说萨特从整个关系中得到多少超脱”,“奥尔加犹豫不决的转向和摇摆令他心烦意乱”,萨特有时会“大发雷霆”,有时则会“怒火中烧”[10]283。可见,萨特和波伏瓦一样,在“三重奏”中并不轻松。波伏瓦、萨特和奥尔加发现:他们三人“跳着可怕的舞蹈”,但最终却“皮毛未损”[10]284。
波伏瓦在回忆录中写道:“奥尔加迫使我正视一个迄今为止我竭尽全力去回避的事实——他人完全如我一样存在着,同样有着存在的显而易见的理由。”[10]285在“三重奏”生活中,波伏瓦修正了关于自己与萨特关系的看法,从而也修正了关于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看法。她意识到“把自己和另外一个人通过‘我们’这个多义的、过分灵活的词列为同类,这是错误的”,“两人间的和谐总不是先验的‘已知数’,它必须不断被实现。”[10]286他们与奥尔加的共同生活、体验引发和深化了波伏瓦关于“我们”以及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思考,日后也成为《女宾》的主要素材。虽说《女宾》中的主人公确实是以波伏瓦、萨特和奥尔加为原型而塑造的,但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为使小说结构紧凑、情节更符合情理,也为使作品更有深度和力度,波伏瓦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情节的铺陈做了许多艺术化处理。因此,以小说中弗朗索瓦兹的一言一行、所思所想来完全对应波伏瓦的言行和态度是不合理的。归根结底,“三重奏”生活对于波伏瓦及其创作、哲学思考来说应该是十分有益和重要的人生体验。
波伏瓦的“三重奏”生活一开始就具有发展新的人与人关系的试验性质。波伏瓦和萨特共同认为:“人与人的关系,要在不断发现新鲜因素的过程中发展,没有哪种关系可以通过特许或者超越一般而成为一种先验的存在,而我们的关系(指“三重奏”——笔者注)似乎是自己破土而出的。我们早就梦想出现这种情形。”[10]267这段话表明,波伏瓦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哪种关系具有先天的、约定俗成的优越性,那么,当然包括婚姻、异性恋,甚至是两个人的情侣关系,这些都可以被打破和被颠覆,而在“三重奏”生活中,波伏瓦和萨特显然就是这么做的。应该说,“三重奏”以及他们自由甚至有些泛滥的情爱生活,在现实中难免会对一些牵涉其中的人造成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有些甚至留下了一生的阴影,例如比安卡。因此,这种生活方式目前来看并不具备普适性。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武断地将它完全否定。正如波伏瓦指出的那样:人类没有哪一种关系是先验的存在。现在,许多学人已经认识到,被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并不能被证实是唯一和最佳的模式,例如法国在1999年通过的、2000年开始实施的“紧密关系民事协议与同居”法令就是一种创新。由此,PACS(民事伴侣契约)成为“传统婚姻之外的一种新型的二人共同生活模式”[11]48,它在保障同性伴侣和同居伴侣享有类似婚姻中某些权益的同时,又保留当事人在双方关系和其他许多事务上的自主权。PACS反映了社会对“‘松绑婚姻’的需求”,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婚姻模式的思考,并且有学人认为“如果无法在婚姻制度的框架下兼容多层次的二人关系约束机制,PACS就有可能与婚姻长期并存”。[11]48虽然,很难证明波伏瓦与萨特的“契约式伴侣”关系和生活实践与此有直接联系,但社会经济、教育和法律等各方面的发展,以及人在自主权、性别平等意识方面的增强,在婚姻家庭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变化,也必然带来变革或完善二人共同生活模式的需要,因此波伏瓦的新型伴侣生活与PACS之间在本质上有着契合之处。按此也就说明了波伏瓦和萨特的情爱生活理念虽不具备普适性,但仍不失为社会对人类亲密关系模式的有益尝试,就如同并非人人选择PACS制度,但PACS毕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一种的选择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进步。
波伏瓦的自主和反传统意识使她在与萨特成为亲密伴侣前就具有了性自由和抵制婚育的观念,遇见与她志同道合且观念相近的萨特后,他们成为并肩作战的哲学和文学伴侣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正如波伏瓦的养女西尔薇·勒蓬-德·波伏瓦(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所说,波伏瓦不是因为选择了萨特才成为波伏瓦,而是因为她成了波伏瓦才选择了萨特。《战斗的海狸》的主要译者黄荭为了翻译这部波伏瓦评传,大量研读了波伏瓦的各种资料,她也赞同波伏瓦养女的这一观点:“显然,在遇见萨特之前,西蒙娜就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成长为波伏瓦、成长为海狸,她已经形而上地建构了自身的独立自主并严格付诸行动。”[12]154所谓波伏瓦对萨特的从属关系并未经过事实论证,所以我们理应予以客观对待。至于波伏瓦与萨特的关系是否“牢不可破”,他们一生的经历已然说明,虽然这“牢不可破”的关系并不只是情侣那么简单。诚如前文已引柳鸣九所言,“从40年代中期以后,萨特与波伏瓦的关系就更主要地演化为一种文学的、事业的关系”,因此,世人也应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而不能一味地仅用看情侣的眼光来看待、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跳出“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我们或许能从波伏瓦和萨特的人生实践中得到更多有益的启示。
四、结语
柳鸣九是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是为萨特进入中国代办“签证”的人,他对波伏瓦的评价无疑是学界研究波伏瓦的重要参考。针对世人对波伏瓦价值的质疑,柳鸣九曾表示,没有萨特,波伏瓦“也一样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但柳鸣九的波伏瓦研究由于篇幅等种种原因所限,显然也具有某种局限性。我们注意到,柳鸣九几乎所有评论波伏瓦的文章都将其作品的自传性作为研究的中心,在《一份历史文化与自我个性的真实记录——西蒙娜·徳·波伏瓦的四部回忆录》中甚至用了不短的篇幅[8]74-80来阐释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作品的特点及政治倾向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柳鸣九的波伏瓦研究佐证并支持了他关于萨特及20世纪西方文学价值评判方面的观点,或许这也正是他研究波伏瓦的重要目的之一。这样,柳鸣九选择研究的作品和重点就难免会有一些局限性。柳鸣九明确表示了“《第二性》在文坛有特别突出的地位”,而且波伏瓦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她写出了她作为一个杰出的职业妇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代社会里的思想观念、感受体验、精神优越与矛盾苦闷、欢乐与幽怨……”,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第二性》、《名士风流》和《女宾》,它们奠定了波伏瓦在20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不朽地位”[13]486。但遗憾的是,柳鸣九并未就《第二性》以及在他认为的波伏瓦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方面展开研究。造成这种遗憾的不仅有评家的问题,也有历史、社会和自身现实的原因。从评家而言,恐怕与柳鸣九自身的性别意识和婚姻立场不无关系。“对文学中的性别现象研究提倡客观‘中性’,持守‘和而不同’立场”,尽管这是万莲子针对性别诗学研究主体提出的一种“防止自身自然性别偏执的努力取向”[14]42,但它其实适合所有关涉性别现象的研究者。若研究者能用性别包容代替性别偏执,真正认同两性在“差异中的平等与和谐”这个目标,就能理解女性在自身解放道路上的努力和艰难,波伏瓦与萨特在两性关系中“谁主谁从”也就不复成为问题了。
[1]佘协斌.柳鸣九与世界文学[J].当代外国文学,2000(2).
[2]黄燎原.和柳鸣九谈二十世纪法国文学[J].外国文学.1993(3).
[3]柳鸣九.序[M]//西蒙·波娃.闺中淑女——西蒙·波娃回忆录(一).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4]柳鸣九.前言∥西蒙娜·徳·波伏瓦.名士风流.许钧,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5]柳鸣九.《萨特研究》三十年[M]∥柳鸣九谈萨特.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6]西蒙·波娃.闺中淑女——西蒙·波娃回忆录(一) [M].谭健等,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7]宋德发,周颖. 他是“许门的仇敌”——简论普希金的婚姻观[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S1).
[8]柳鸣九.从选择到反抗[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9]西蒙娜·徳·波伏瓦.萨特传[M].黄忠晶,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10]西蒙·波娃.盛年(卷上)——西蒙·波娃回忆录(二)[M].陈欣章等,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11]王薇.法国PACS制度的法律性质简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12]黄荭.三重奏,四重奏,蓝调芝加哥……[J].读书, 2009(6).
[13]柳鸣九.此作中的自传性成分[M]//西蒙娜·德·波伏娃.女宾.周以光,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
[14]万莲子.性别: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责任编辑:万莲姣
LIU Mingjiu’s Evaluation of Simone de Beauvoir and His Masculine Misunderstandings
WANG 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China)
Known as “first person for researches of Jean-Paul Sartre in China”, LIU Mingjiu was also an early expert for studies of Simone de Beauvoir. His research of Beauvoir is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in the early studies on Beauvoir in China. To a certain extent, his criticism represents Beauvoir's evaluation and location in China. LIU Mingjiu believes that Beauvoir's works have greatly high historical value, her works successfully realize the self-image construction of rebelling against tradition and pursuing freedom, but she is subordinate to Sartre. LIU’s comment on Beauvoir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studies of Beauvoir, and however is restricted by male-centered thought at the same time.
LIU Mingjiu’s Evaluation of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lf-image construction; limitation of male-centered thought
2016-03-05
王芳(1976-),女,湖南衡阳人,博士,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女性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波伏瓦在中国的传播与阐释”(项目编号:11YJC752024);湘潭大学课题“波伏瓦在中国的经典化”。
I0-03;I0-02
A
1001-5981(2016)04-01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