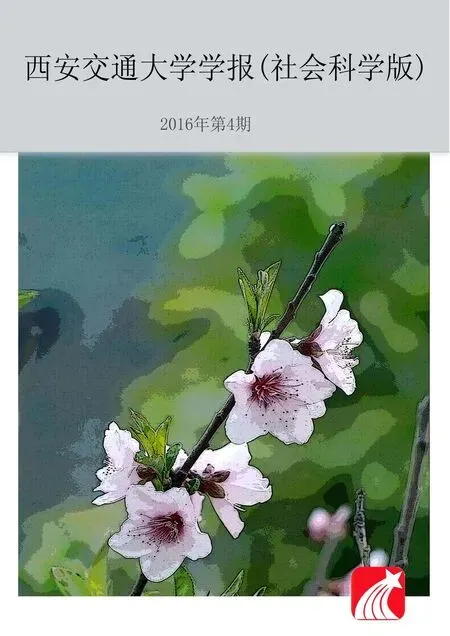国际投资法的社会化趋势探析
王 鹏
(西安交通大学 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国际投资法的社会化趋势探析
王 鹏
(西安交通大学 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阐析国际投资法社会化趋势的规则表现,动力机制及其中的大国问题;认为国际投资协定越来越多包含传统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保护之外的条款,以更多回应外国投资引起的或与外国投资直接相关的社会利益保护事宜;主张国际投资法社会化趋势是国际投资法体系下各利益相关者理性互动的制度反应,国际投资法社会化趋势从抽象规范落实为具体规则仍有赖于处在国际投资法体系中心位置的大国的示范和支持。
国际投资;投资自由化;投资保护;国际投资法体系
本文探讨国际投资法体系内正在发生的社会化趋势。作为促进与保护投资的工具,国际投资协定①相当多的国际投资协定以双边投资协定(BIT)为主要表现形式,同时,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专门投资章节也值得注意。一直以来以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保护为其条款的主要内容。晚近,国际投资协定越来越多地纳入诸多回应或保护东道国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条款,国际投资法正经历“社会化”转向。社会化趋势体现了国际投资法体系在经历了政治驱动和经济驱动的发展轨迹之后,再次震荡调整以回应日益紧迫的社会政策需求。
一、国际投资法简史
国际投资协定脱胎于《友好通商航海协定》(FCN),最早的专门投资协定是1959年签订的德国-巴基斯坦双边投资协定(BIT)。投资协定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作为资本输出国回应发展中国家政治独立后的国有化行为。政治利益是驱动国际投资协定产生的直接动因②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BIT战略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回应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化行为和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关于国家主权的集体行动。关于美国(BIT)战略的简史参见K J Vandevelde, The BIT Program: A Fifteenth Year Appraisal (1992) 86 ASIL Proceedings 532.。投资协定缔约高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对立基本结束。随着华盛顿共识的确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席卷全球,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为吸引外国资本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纷纷与发达国家签订国际投资协定[1]。经济利益是促进投资协定扩散的主要原因。
在投资者不断提起的国际仲裁的影响下,国际投资法体系逐渐脱离缔约国的缔约初衷。投资者在国际投资仲裁庭不断起诉东道国的政府行为,甚至包括一些普遍适用的公共政策行为。国际投资仲裁庭过度拘泥投资协定的字面含义,而导致过于保护投资者的仲裁实践。作为缔约国,主权国家在修订或新签订投资协定中力图扭转这一的制度“偏差”,逐步纳入社会化条款,用以明确东道国的监管权力、投资待遇的例外情形和投资者的义务等。
在经历了政治利益驱动和经济利益驱动发展轨迹后,国际投资法体系进入社会利益驱动的发展阶段,社会利益在国际投资协定中逐渐由幕后走到前台。以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保护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投资协定也有社会利益的影子,多在序言中间接体现,典型表述为“促进国际私人投资的流动有助于促进缔约国经济的发展和缔约国领土内人民福利的提高”。2000年以后,各国签订的投资协定,尤其以2004年美国投资协定范本为代表,多在征收条款中以附件的方式明确排除东道国行使治安权的公共政策行为。新近投资协定则更多地纳入了体现东道国社会利益的条款。2012年,美国范本专门规定了环境和劳工权利条款*US Model BIT 2012, Article 13 Investment and Labor and Article12 Investment and Environment.。在新近发布的欧盟-中国BIT谈判动议中,欧盟希望明确纳入具体的并附有专门争端解决机制的社会利益条款*Motion for a Resolution on the China-EU Negotiations for a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1 October 2013) (hereinafter, Motion for EU-China BIT Negotiation), para.33.,包括治安权例外、劳工和消费者权利、产业政策*Motion for EU-China BIT Negotiation, para.23.、文化多样性*Motion for EU-China BIT Negotiation, para.29.、公司社会责任和遵守东道国法律义务等。
二、国际投资法的社会化趋势
社会嵌入性是国际投资活动的根本特性,决定了跨国投资治理体系的整体机制设计。国际投资法在东道国具有不容忽视的社会效应,既可能促进东道国治理水平的提高,也可能干预东道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国际投资法的负面社会效应是投资法社会化趋势的直接政策目标,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扩散也一定程度构成投资法社会化的条件。
(一)国际投资法的社会效应
1.国际投资的社会嵌入性。国际投资活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嵌入性。受保护的国际投资几乎涵盖所有有价值的资产。投资待遇涵盖但不限于投资者的设立、扩大、经营、转让、处置、利润汇出等行为。投资者权利不仅涉及静态的物权、财产权保护,也涉及动态的契约交易活动,甚至关涉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日常运营活动。投资活动不可避免地与投资所在地的社群利益及活动密切关联,并受东道国一般适用的公共政策的影响。投资活动深深地嵌入到东道国既有的治理监管体系中,触及东道国法律体系的各个层面。
正因投资活动的社会嵌入性,对跨国投资的监管不可避免地与既有的治理和监管体系相关联、相互动、相作用,并进影响东道国的公众利益。所以,国际投资法在东道国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
2.国际投资法的溢出效应。国际投资法的社会效应可能是积极的,对东道国治理具有溢出效应。国际投资法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本理念,强调个体权利保护与市场经济。虽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承认市场失灵时政府(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但其总体上反对政府对市场和经济的不当干预。
国际投资法体系有助于建立产权保护制度、市场秩序和有限政府。国际投资法体系对一些转型国家的国内宪政建构、法律制度完善等方面都有积极的示范和促进作用。国际投资协定义务的国内履行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国内改革的外部激励,可助力东道国国内改革。国际投资法赋予外国投资者直接诉权,投资者以启动国际投资仲裁的方式监督东道国各级政府的行为也有助于东道国中央政府推行改革措施。虽然国际投资法可能对东道国当地救济制度具有效率改善的效应,但在某些情况下,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制度设定也可能对东道国当地救济制度构成替代,从而导致东道国当地治理水平的下降[3]113。
3.国际投资法的挤出效应。国际投资法过于强调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保护,从而干预东道国的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挤出本应实施的公共政策,对东道国监管具有挤出效应。在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下,乌拉圭和澳大利亚香烟包装案*相关案例如Philip Moris v. Uruguay和Philip Moris v. Australia。、德国原子能案*Vattenfall AB and others v.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CSID Case No. ARB/12/12.、阿根廷2001-2002年金融危机应急法系列案*Burke-White, William W., The Argentine Financial Crisis: State Liability under BITs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ICSID System.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140628. See also J. R. Picherack, The Expanding Scope of the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Standard: Have Recent TribunalsGone Too Far, 9 Journal of World Trade and Investment (2008), p. 288.、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环境和劳工标准的系列裁决*Metalclad Corporation v.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ICSID Case No. ARB/97/1 (NAFTA), Award, August 30, 2000; Methanex v. USA, Final Award, 3 August 2005.都表明了投资者-国家仲裁裁决对东道国公共政策的影响。为吸引和保护外资而放弃的其他社会利益的保护,体现了东道国对与投资关联事项的监管存在政策放松或政策迁抑。投资法的挤出效应主要包括两种形式:监管寒蝉效应(Regulatory Chilling Effect)和监管逐底竞争(Regulation Race to Bottom)。
监管寒蝉效应是指东道国政府因投资仲裁而抑制本来应当实施的监管行为或公共政策。投资仲裁本身就构成一种战略威胁。投资者一旦胜诉,东道国必须用本国的财政资产来支付裁决,这意味着东道国的全体国民负担仲裁裁决。对于尚未实施的公共政策和监管行为,东道国政府可能因预见并顾忌投资者可能提起的仲裁而避免或减少使用,而这无疑干扰了东道国政府最佳的公共政策决策。
监管逐底竞争主要表现为一些缔约国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而放松国内监管,如降低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等。在此种宽松的监管体系下,投资者为了营利更可能采取不负责任的运作方式,投资因而可能存在更大的社会负效应。逐底竞争行为有悖于国际投资法通过吸引外国投资以促进缔约国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福祉的政策目的。
(二)国际投资法社会化的政策导向
社会利益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本来就已存在,只不过并未以具体规则的形式呈现。国际投资法的社会化是社会利益的重述,是从手段到目的的回归,而不是重新纳入。
就政策目的而言,对监管寒蝉效应和监管逐底竞争行为的回应无疑是国际投资法社会化的政策目标之一。重申东道国的监管主权是对寒蝉效应的直接回应。随着投资仲裁案例增多,寻求投资者和东道国权利义务的平衡成为缔约国的共识。对东道国监管权力的一般性宣示和具体规则设计有助于仲裁庭在未来的国际投资仲裁中更准确地把握缔约国在投资协定中的缔约意图,平衡投资者权利保护与东道国公共政策。
此外,可持续发展也是国际投资法社会化的政策目标之一。虽然在国际法下,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绝大多数意义上仅是一个政治理念,而不是具体的法律规则,但缔约国对投资协定的预期正从手段转向目的,探寻实现国际投资直接促进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路径。随着资本输入-资本输出国双重身份国家的增多,可持续发展正逐渐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
(三)国际投资法社会化的表现
国际投资法试图通过社会化回应平衡投资者权利和东道国权力,平衡经济政策和其他公共政策,以回应日益增长的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诉求[2]82。从类型上看,社会化条款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重申东道国监管权力,这类条款包括序言和治安权例外,可见于一般例外条款或征收条款的附录。第二类,不得减损条款,多事关环保标准和劳工待遇标准,用以避免缔约国之间为了吸引外资而采取逐底竞争策略。第三类,明确或强调投资者责任和义务,多见于公司社会责任条款和遵守东道国法律义务条款。
1.重申东道国监管权力条款。重申东道国监管权力可以多种的形式体现。2012年美国BIT范本在其前言部分明确提及“愿以与保护健康、安全和环境,促进国际公认劳工权利的原则相一致的方式实现这些(保护投资者权利和促进经济发展等)目标”。由此可见,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与投资保护与促进、促进经济发展等目标处在美国外资监管的同一政策序列。在投资纠纷解决方面,美国也重视国内救济在解决投资纠纷方面的重要性,就直观表述而言,国内救济与国际仲裁的重要性不分上下。
2012年,中日韩签订的投资协定也包含类似的缔约政策目的*中日韩投资协定 前言部分。,在前言部分,虽然传统的创设稳定、有利、透明的投资环境以促进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仍是缔约目标之一,但增进缔约国福利、不降低广泛适用的健康、安全和环境标准、投资者遵守东道国法律以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进步等也是前言中明确肯定的政策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中日韩在投资协定议定书中,缔约方明确将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土地财产纠纷排除在条约前四条范围外*中日韩投资协定议定书,第一条。。此外,在东道国请求的情况下,所有投资纠纷都应首先进行国内行政复议程序*中日韩投资协定,第15条第7款。。更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中国、加拿大签订的投资协定并没有简单地重复投资保护和投资自由化的政策目的,而是在前言中直接纳入了可持续发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进一步认识到需要依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促进投资;希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两国经济合作;特签订此条约。”*中加BIT,前言。
2.不得减损条款。不得减损条款主要包括环境和劳工条款。美国2012年BIT范本“投资与劳工”条款明确提及“缔约双方认识到通过削弱或降低国内劳动法所要求的保护义务来鼓励投资是不恰当的”*美国2012年BIT范本,第13条投资与劳工。。类似的,在“投资与环境”条款中,美国也重申“缔约双方认识到通过削弱或降低国内环境法律所要求的保护义务来鼓励投资是不恰当的”,“本条约不应被解释为阻止缔约方采取、维持或实施除本条以外与本条约相符的措施,只要其认为该措施是确保其境内的投资活动符合环境关切的适当措施”*美国2012年BIT范本,第12条投资与环境。。
3.投资者责任与义务条款。投资者的责任和义务条款主要见于投资定义和业绩要求。业绩要求在投资协定中总体成一种限缩的趋势,多与WTO项下的业绩要求内容类似。投资定义条款往往要求投资者依照东道国当地法律进行投资。关于“遵守东道国当地法律义务”的单独条款,新近条约动向可参见2012年南非BIT范本:“投资者和投资应当尊重东道国关于投资设立、获得、管理、运营和处置的所有法律、法规、行政指南和政策”*南非2012年BIT范本 第11条(Compliance with Domestic Law)。。
理论界也有关于在投资协定中纳入公司社会责任条款的讨论,但尚无条约实践。但挪威*挪威2007年BIT范本 第32条(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和南非*南非2012年BIT范本,第16条(Corporate Governance Standards)。发布的投资条约范本已经纳入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示范性条款。
三、国际投资法社会化的动力机制
国际投资法社会化是表征,隐现的是国际投资法下各利益相关者的理性反应。表面看来,国际投资法的社会化条款是国际投资法理论的异常,然而,通过国际投资法的历史分析可知,社会利益保护和社会福利促进一直是国际投资法体系的目的之一。国际投资法的社会利益重述体现了国际投资法从手段到目的的回归。在制度上层面,国际投资法的社会化体现了利益相关者——尤其是缔约国——试图矫正国际投资法体系的努力。
(一)国际投资法体系的产生机理
国际投资法体系的产生机理在于不同治理机制的制度能力与投资监管的政策需求之间的耦合。国际投资监管的可用治理机制包括私人合同秩序、以国际投资协定为主的条约秩序和东道国国内监管体系。国际投资监管的政策需求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侧重。
1.国际投资治理的机制选择。私人秩序以投资合同为主要形式,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商事仲裁。私人秩序的优势在于纠纷当事人可以单独协商纠纷的解决程序,东道国事前控制较强。私人秩序要求投资者具有较强的谈判地位和能力并且未来合作可以产生较大收益,这无疑局限了私人秩序的作用范围,而且一旦东道国不履约,传统的政治性外交保护可能是最后的保障。
条约秩序以国际投资协定为主要形式,争端解决机制包括国家间仲裁和投资者-国家仲裁。条约秩序的优势在于缔约国通过缔结条约的形式赋予国际仲裁庭对投资纠纷的管辖权。条约秩序出现的前提是缔约国对投资监管事项保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且可落实为可操作的条约规则,同时国际投资仲裁庭的裁决不会过于偏离缔约国的条约意图。条约秩序的缺点在于缔约国事前和过程控制都较弱,在国际投资协定规定较为抽象的情形下,国际仲裁庭的裁量权过大,仲裁裁决很可能有违缔约国缔约意图。
东道国国内法律体系是默示的争端解决体系,以东道国当地的法律体系为基础,是规制东道国公共利益的最佳机制,但投资者对其信任度不高,当地司法救济体系很难成为投资者和投资母国所能接受的争端解决机制。
2.国际投资监管的政策需求。在产生初期,征收条件及补偿标准是跨国投资纠纷的主要形式。所以,确立投资待遇和保护水平及一个去政治化的争端解决机制是最主要的政策需求*范德维尔德(Kenneth J. Vandevelde)认为美国BIT战略在初期有多重目的,首先在意提供一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支持的征收补偿标准;其次,BIT能够通过纳入投资的习惯国际法保护规则,进而提供一套稳定、透明、有利的投资环境;最后,在十分初级的意义上,BIT能够向发展中国家宣示那些受投资者欢迎的法律环境。当然,BIT的首要创新之处在于投资者的国际投资仲裁庭直接诉权。。海外投资利益保护是一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一环,但外交政策也有其他政策追求,动辄因私人投资而卷入外交保护争端对投资母国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政治挑战,尤其是这种外交保护可能影响两国总体的外交大局。一个去政治化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投资保护与监管的最核心政策需求。
随着国际仲裁数量不断增多,国际投资法的挤出效应逐渐显现。当公共政策引起的间接征收成为国际投资争端的主要表现形式时,以直接征收为预设对象的国际投资法在运行中出现了部分偏离缔约国意图的趋向。如何在保护投资的同时为东道国预留必要的政策空间成为投资监管的新政策需求。
(二)国际投资法体系的发生条件
在产生初期,直接征收和大规模国有化是国际投资争端的主要表现形式。一种非政治化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各方的政策需求点,而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是各国关于国际投资有基准性的待遇水平和保护规则。因此,专门性的国际投资协定初现。
国际投资法的出现有效地回应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制度需求。兼具专门化的投资实体待遇和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国际投资法可以有效回应国际投资监管的治理需求*“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公约的签订及ICSID中心的建立对投资者-国家仲裁的扩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根据OECD的一份1660个国际投资协定的调查,到1980年代末,80%以上的国际投资协定都明确包含国际投资仲裁条款。。对于东道国而言,国际投资协定传递了其保护投资的承诺,有利于吸引外资。法律化的争端解决方式也使东道国在投资纠纷解决方面免于遭受大国政治的胁迫。对投资母国而言,国际投资法可为本国海外投资者提供切实的投资保护,将其从数量众多的外交保护纠纷中解放出来,避免因为私人投资者的投资纠纷而影响两国的政治大局。对投资者而言,国际仲裁庭具有较高的中立性和声誉,国际投资法能够有效地降低或确定投资者的海外投资风险,直接起诉东道国政府的国际仲裁庭诉权也使得投资者握有解决投资纠纷的主动权。
(三)国际投资法体系的维持条件
投资者的利己行为放大了国际投资法体系的既有弱点。国际投资协定出现后,投资者可以多种方式规划公司国籍,以获得最优的条约保护水平。加之,20世纪90年代以后直接征收减少,间接征收成为投资纠纷的主要形式,国际投资法的挤出效应增大。为了重申监管主权并预留监管空间,缔约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具体限定例外事项并为设置特别的争端解决程序,即例外事项的具体化和争端解决程序的复杂化,此即国际投资法的第一次系统调整。争端解决程序的复杂化表现为特定的前置程序(行政审查前置或联合决定前置)和过程控制程序(联合解释),体现了不同治理制度的“纵向合作”。
随着跨国投资活动的深入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播,东道国越来越注重国际投资对本国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并在制度上反思既有国际投资保护体系的有效性。这表明国际投资法体系面临从手段到目的、从消极到积极的第二次系统性调整,而此次系统性调整的结果则是国际投资法的社会化。国际投资法的社会化表明国际投资法与东道国法律体系的横向合作普遍化和深入化。同时,国际投资法纵向制度结构将更加复杂,东道国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投资争端解决的介入将更加主动、更加灵活。
不同治理机制的制度能力与国际投资监管的政策需求之间的耦合催生了国际投资法体系的发生。去政治化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政策需求开启国际投资法时代。为东道国预留公共政策空间的第一次系统性调整导致国际投资协定例外事项的具体化和争端解决程序的复杂化。东道国越来越注重国际投资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并在制度上反思既有国际投资保护体系的有效性。国际投资法体系面临从手段到目的、从消极到积极的第二次系统性调整,国际投资法的社会化趋势显现。
(四)国际投资法体系下利益相关者互动模式
缔约国、投资者和仲裁员是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利益相关方在现有制度约束下的理性反应是影响国际投资法体系演进的关键变量。
1.缔约国:体系的设计者和调整者。在条约缔结和修订阶段,缔约国无疑享有绝对的主动权,处在主导地位。在缔约阶段,缔约国无疑处在最佳影响位置,缔约国通过国际条约的形式设立国际投资监管与保护的整体框架。但正式磋商耗费相当的成本和精力,需要多个国家集体行动,因而条约缔结的启动频率较低。在具体仲裁程序中,缔约国一般处在被动地位。此时,作为被诉国,东道国的应诉行为往往围绕具体行政行为展开,少有制度层面的回应。当然,非诉缔约国可以通过递交陈情、与东道国发布联合解释的方式主动参与投资仲裁程序,但这种程序性参与并未改变缔约国在具体仲裁中被动参与的地位。与缔约阶段类似,缔约国在条约再修订阶段处在绝对的主动地位,不同在于缔约国的条约再修订可能比缔约启动的成本低,因为投资条约中可能包含相关程序规定。
国际投资体系改革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各国对国际投资法及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认识和定位不同。缔约国对国际投资法演进方向的倾向因国而异、因时而变,具体选择何种方案取决于本国的核心利益。国内公共利益调整优先于吸引外资需求的国家很可能采取稳妥甚至保守的国际投资法改革策略,例如澳大利亚。区域强国或领袖型国家出于追求本国国际影响力的政策目标很可能采取积极改革方案,参与未来国际投资制度建设。例如美国和欧盟推行的新投资协定政策,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也是构建未来国际投资法律制度框架的契机之一。
2.投资者:制度的消费者。投资者对国际投资法体系的主动影响主要体现在启动投资仲裁的主动权。从投资仲裁的数量来看,投资者启动投资仲裁的态度相当积极。
投资者在条约缔结和修订阶段的主动权较低,少有发言权。个别投资者的利益很难体现在国际投资协定中,但这并不排除组织良好的投资者群体对投资条约设计可能施加的影响。一旦投资协定签订,投资者可以利用全球投资布局和公司结构规划的方式“用脚投票”,在最能保护自身利益的国家设立公司注册地、公司总部或管理中心所在地,以实现最佳的条约保护水平。因此,可以将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和仲裁申请作为衡量一国投资政策的信号之一。
3.仲裁员:系统演进的“黑箱”。仲裁员群体无疑是国际投资法演进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数量较小、相对较为封闭、互动较强的国际投资仲裁员群体自觉不自觉地加强了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政策外部效应,使国际投资仲裁逐步获得了制度的自持性,从而初步形成了发挥治理效应的制度结构[7]。国际投资仲裁特设本质要求仲裁员在裁决时必须充分说理,故而仲裁员大量援引先前判决。在相互援引的过程中,数量较小、互动较强的仲裁员群体逐渐对国际投资协定的核心概念和条款形成了基本的共识[8]。
仲裁庭群体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可识别的分化,不同教育、法律训练和职业背景对仲裁员的推理模式影响较大。具体而言,私法背景仲裁员更可能采取对投资者有利的解释和推理路径;公法背景或政府部门经历的仲裁员则更可能关注缔约国的缔约目的,并采取有利于东道国政府的解释和推理路径。首席仲裁员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影响作用更大。
总体而言,投资者、缔约国和仲裁员对国际投资法体系的制度影响和作用空间存在差异。投资者和缔约国的行为存在一定的规律,而仲裁员群体则充满不确定性,是国际投资法体系演进的黑箱。缔约国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提供国际投资法网络体系的基本框架;私人投资者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规划国籍,并通过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的方式启动国际投资法多维、多向的演化过程;仲裁员通过具体仲裁解释和适用具有制度层面影响的核心概念和程序,进而影响国际投资法体系的演进;在投资者和仲裁员的行为过度偏离了缔约国的缔约意图时,缔约国或通过条约修订或通过联合解释的方式重新矫正国际投资法体系的演进方向。
四、国际投资法社会化趋势中的大国问题
毋庸置疑,大国之间的共识是任何国际法体系形成并维持的必要条件。作为主权国家之间横向分工最为细致、纵向合作最为发达的国际法体系,国际投资法体系仍面临核心的权力问题。国际投资法的出现和系统调整历史无疑体现了这一点,当前国际投资法社会化趋势如何从抽象规范落实为具体规则也有赖于大国的示范和支持。
处在国际投资法体系中心的国家对国际投资法体系影响更大。考虑到跨国投资体系形成的互动关系存在多个维度,投资协定、投资者和仲裁员等是三个可能衡量中心国家的标准。从投资协定的角度来看,一国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的数量无疑是衡量该国在国际投资法体系中作用大小的标准之一*国际投资协定的数量可根据UNCTAD IIA database和World Investment Report年度报告整理。。从投资者的数量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数量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数量也是一个标准*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可参见OECD outflows and inflow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数据。。从仲裁员的供给来看,本国国籍仲裁员的数量和本国(投资者或政府)参与国际投资仲裁的频率也可作为一个衡量标准*仲裁员任命人次数可参见ICSID Statistics定期报告,被告次数搜索ICSID网站。。三个标准在不同领域和不同阶段的权重可能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三个指标上都很有影响的国家一定处在国际投资法体系的中心位置。
总体而言,无论是国际投资协定数量,还是跨国直接投资的数量,还是仲裁员任命人次数,欧盟作为整体都高居首位,其无疑处在国际投资法体系的中心位置。除此之外,美国的数据领先其他国家。就欧美之间的比较而言,美国的制度影响可能更大,因为欧盟正处在一体化过程中,欧盟统一的投资政策仍处在探索阶段。相比之下,中国则处在成长阶段,正在成为中心国家。虽然中国与传统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但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和资本输入输出双重身份的三重角色使中国具备不容忽视的示范效应和影响力。
一般而言,中心大国对国际投资法体系的演进的影响要比处在边缘位置的小国大得多。但是由于国际投资法体系以一种渐进、多维度、试错的方式演化,加之最惠国条款和投资者的国籍规划行为,某些小国的国际投资协定可能被投资者利用而引发体系性变革。例如,意大利投资者针对国债的投资仲裁案件和菲利浦(Philip Morris)烟草公司针对健康法案的仲裁都具有体系层面的震动和影响。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互动使国际投资法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复杂体系(Regime Complex)的特性[4],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国际投资法体系自产生之初就一直处在一种动态的系统演进中。当然,作为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提供者和维持者,大国的共识和支持是任何制度变革或演进的必要条件。
五、结论
国际投资活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嵌入性。投资活动不可避免地与投资所在地的社群利益及活动密切相关,并受东道国一般适用的公共政策的影响。国际投资法在东道国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可能对东道国治理具有溢出效应,也可能对东道国监管具有挤出效应,干预东道国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挤出本应实施的公共政策。
不同治理机制的制度能力与国际投资监管的制度需求之间的耦合催生了国际投资法体系,去政治化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政策需求开启了国际投资法时代。为东道国预留公共政策空间的国际投资法体系第一次系统性调整导致国际投资协定例外事项的具体化和争端解决程序的复杂化。随着跨国投资活动的深入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播,东道国越来越注重国际投资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并在制度上反思既有国际投资保护体系的有效性。国际投资法体系面临从手段到目的、从消极到积极的第二次系统性调整,国际投资法的社会化趋势显现。在条约缔结、执行、修订的不同阶段,投资者、缔约国和仲裁员的制度影响和作用空间存在差异。尽管内部存在分化,投资者和缔约国的行为存在一定的规律,而仲裁员群体则充满不确定性,是国际投资法体系演进的黑箱。作为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提供者和维持者,大国的共识和支持是任何制度变革或演进的必备条件。国际投资法社会化趋势从规范落实为具体规则、从理念转化为具体制度仍有赖于处在国际投资法体系中心的大国的示范和支持。
[1] KENNETH J. VANDEVELDE. A Brief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J]. U.C.-Dav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Policy, 2005(12): 157-194.
[2]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0: Investing in a Low-carbon Economy [M]. Geneva: UN Press, 2011:82.
[3] TOM GINSBURG. International substitutes for domestic institution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governance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2005(25):107-123.
[4] JOOST PAUWELYN. At the Edge of Chaos? Foreign Investment Law a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How It Emerged And How It Can Be Reformed [EB/OL].[2014-01-24]. http://ssrn.com/abstract=2271869.
[5] KENNETH J VANDEVELDE. U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M].Oxford:Orford Clniversity Press 2009:26-27.
[6] JOACHIM POHL, KEKELETSO MASHIGO, ALEXIS NOHEN.“Dispute settlement provisio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A large sample survey[EB/OL].[2014-03-01].http://
[7] SERGIO PUIG. Emergence and Dynamism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CSID, Investor- State Arbit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M]. 44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3(44):531-607.
[8] TEN CATE, M LRENE. The Costs of Consistency: Precedent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J].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2013(51):418-478.
(责任编辑:冯 蓉)
On the Soci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WANG Peng
(School of Law,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China)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system is currently under a turn toward socialization. Transnational investment is highly embedded in the social structural and domestic regulation framework in host state, and therefor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s of great social effect in host state, including Spill-over Effect and Crowding-out Effect. Beyond traditional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provision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corporates more and more socialized provisions to response to the negative social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 host state to social interests and public policy. The soci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reveals the rational interactions of stakeholders, among which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central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system are critical to such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zati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investment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system
2015-01-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FX052);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攻关项目(14JZD022);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YJCZH013)
王鹏(1987- ),男,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D996.4
A
1008-245X(2016)04-008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