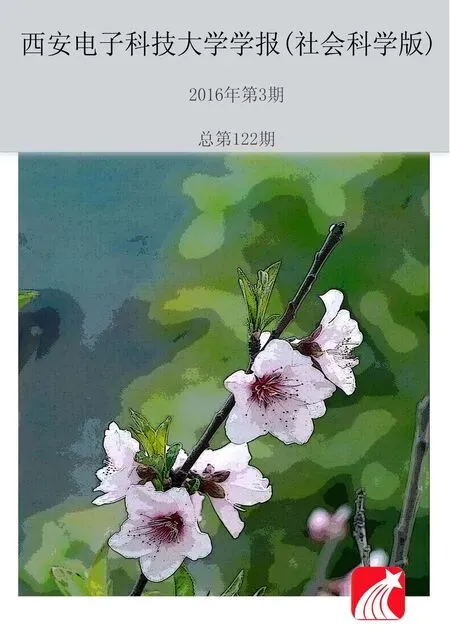当代中国媒介文化生产机制的转换与联动
王敏芝(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传播学
当代中国媒介文化生产机制的转换与联动
王敏芝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从生产机制层面观察,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生产从单一政治主导下的运作转向由政治与市场双重主导下的联动运作机制。这种联动机制直接影响了当代媒介文化生产的生产逻辑的内在扭转与调试更新。在这种复杂联动的生产机制规定下,媒介产品也呈现出意识形态涵化、市场化与政治市场合意等多级样态。
媒介文化;文化生产;机制转换;市场化
媒介文化作为理解当今文化形态的重要切口,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生产层面的具体研究,则是理解和阐释媒介文化的重要环节。生产机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媒介文化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游戏规则”的具体操作和常规实施,并对媒介文化的产品生产与整体面貌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来,媒介文化的生产机制在技术配合与推进下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进行着整体性地转换与调试,也深刻地改变着当代媒介文化的具体形态。
一、“新闻改革”与“体制改造”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国新闻改革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与解放之态,其改革的深度与广度已经广为人知;同时,新闻改革的参与者与研究者们也拥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由于市场机制的许可和引进使得媒介及其相关领域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一系列的变化中关涉到许多环节和因素,如媒介工作者的个人行为、媒介机构的组织行为、媒介机构同社会其他领域的关系等各个方面。
有学者总结90年代新闻改革的三大特点:1.既有新闻体制所包含的基本原则不予改变;2.新闻改革从总体上缺乏清晰完整的目标设置;3.因为第二点的原因,新闻改革体现出非常明显的“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性[1]。所以,新闻改革的发生和进展带着“临场发挥”的行为特征。但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 90年代的新闻改革在缺乏既定目标的情况下能够如火如荼的展开并且受到管理者极大限度的宽容、默许甚至事后的认可与支持?或者可以解释的理由之一是,中国当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本身也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鲜明特征,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并没有现行成功的案例可以模仿,更没有成熟的理论能全面指导,因此这种边改革边探索的特点反映在新闻体制改革领域中,也就表现出“临场发挥”的特征了,换句话说,新闻领域的改革是业务突进之后带动的观念变革。
实际上,我国的新闻改革在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有较为重大的动作,比如对新闻制作和报道一些实践层面的改变,“散文化写作”对教条死板的文风的突破、反对新闻假大空,强调新短多、恢复批评报道等等[2]。这些最初的行为更新,很大程度上促进了90年代传播领域对“信息”、“传播”等概念的理解、以及对新闻“商品属性”的热烈讨论与重新认可。随着十二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确定,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经济发展改革和思想解放的社会氛围愈加浓厚,新闻界的改革浪潮涌动,从管理者到业界实践者体现出一种“合作”或“合谋”的推进模式。
称作“合谋”,是在强调官方管理与新闻实践主体虽各自拥有不同的追求和具体目标、不同的思考新闻改革的角度,但在追求方面却有某些重合之处,或者各自关注的重点领域有重合之处,这是在客观上能形成“合作”的前提。比如政府需要降低财政负担并激发文化产业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而传媒实践者则需要扩大自主权、自谋好出路等等,虽然目标各有所向,但客观上有很多一致之处,因此,也就能一拍即合。其结果是中央财政减负成功、媒介机构逐步商业化。当然,改革行动是在政府管理层和传媒实践主体共同策划协商中进行的,在那些双方利益追求重合之处,改革就进行得非常顺利,如果改革行为违背了基本的新闻原则,这种行为则会遭到限制和规约。
这种“上下协商”的新闻改革实践在客观上造成了90年代以来逐渐加强强度的新闻体制改造。之所以称为体制改造,目的是强调体制层面改革是在一定空间内进行的,并非完全彻底的改变既有体制。从整个新闻改革实践来看,新闻改革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新闻观念的更新和新观念的确立这个层面,比如:首先破除了唯一性的党报观念,确立了国家和人民的新闻观念,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传媒结构;其次突破了传媒唯一性的党性观念,并在确立党性观念核心地位的前提下将传媒事业的党性、人民性、群众性等结合起来;第三,突破了唯一性的媒体指导观念,提出媒体的服务性、趣味性、思想性与指导性相结合的观念[3]。可以说,在新闻改革过程中,传媒观念、传媒功能、传播模式等层面都进行了全面的探索与大胆的实践。但毋庸置疑的是,新闻改革中也有一些不能更改的原则,比如对党性原则、党管媒介的坚持,还包括一些既定的新闻观念和规范:比如政治家办报、政府出资办报、新闻采写要接受各级党委的指导和管理、遵守党的宣传纪律等等。这些不能改变的内容一方面框定了改革的运行空间,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新闻改革的基本基调。
二、市场机制与管控机制的联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在分析90年代以来的中国媒介文化生产模式时使用了一个词,将之称为“完全国有的有限商业运作模式”[4],同时认为媒介文化生产虽然仅仅引入“有限商业运作”,但却在这个限度内将商业运作表现得非常充分,甚至大众媒体经常表现出突破限度的企图和行动来。
为什么是“有限的商业模式”呢,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传媒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我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等重要新闻机构的所有权都为国家所有,并构成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双重定位赋予传媒机构市场追求的合法性和积极性,但政府的管控和规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与完全的市场运作方式不同,除了资本成为对传媒生产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之外,另外两个因素也在控制媒介生产:一是意识形态标准,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标准构建着传媒生产的行为边界;二是中国传媒严格的等级差异,客观上造成传媒资源配置的不平等。
因此,我们可以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探索和建立起来的传媒生产机制称为“控制与市场的联动机制”,一方面是市场化、商品化,另一方面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可以说,相对于单纯的集中控制机制,“联动机制”更为灵活也更能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同时,传媒生产的“联动机制”也更符合“中国模式”的要求。
“中国模式”这个词在各种层面上被使用,但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强调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中国模式”的基本含义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一党执政的核心理念,即绝对不允许一切力量挑战一党执政的核心权力;其二,社会控制系统的独特性,无论是社会行为控制还是意识形态控制都具有中国特色;第三,经济层面的突出特点表现在政府操控下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中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并非同西方国家一样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受到政府宏观调控与影响的市场经济[5]。
当然,“中国模式”的探索和选择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从八十年代真正进入改革开放的十年中,国门刚刚打开之后扑面而来的是各种国际国内新状况。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反省和批判,再加上探索中国未来发展之路的思路和努力,这种思想基础成为之后“中国模式”选择的必要准备;而1989年的重大政治风波和90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所遭遇的危机与挑战,成为形成“中国模式”的决定性环境因素。
中国政府经过历届领导集体的探索与实践,选择并继续进行着“中国模式”主导下的改革和发展路径,这也深刻地影响到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发展样态。在文化建设和发展方面,“中国模式”依然是决定性标准和依据:文化建设既要保障意识形态层面的主导性,为政治稳定做好文化保障;又要达到将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目的。从这个角度观察,文化生产中独特的“控制—市场联动机制”虽然产生诸多矛盾和问题,却又极具合理性和可理解性。
中国媒介文化生产首先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体现“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孟繁华认为,“现代传媒在中国的出现,是被现代化的追求呼唤出来的,它适应了社会政治动员的需要,国家民族的共同体认同……现代传媒推动或支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动向。那些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观念和思想正是通过传媒得以播撒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传媒甚至成了某一时代的象征”[6]。同时,传媒所表现出来的新的话语权力更不能轻视,传媒的话语权力“在其传播过程中如果为民间所认同,它也就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传媒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6]。在政治经济领域广泛施行的“中国模式”的指导下,文化领域的改革也在确保“文化领导权”的前提下开始了引进市场机制并最终走向产业化的更高级发展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传媒文化生产也体现出复杂的样态。经济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给传媒文化生产带来压力也带来了机遇,政策的推进给传媒文化规范的同时也给它“松绑”,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机制不断从外部冲击和改变着媒介文化的基本格局。把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文化产业化的实践与中国追求经济强国和文化强国的目标联系起来,在国内消费文化崛起的环境下,思考文化生产的新型机制是极为迫切的问题。
毫无疑问,当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共同介入媒介机构运作与生产领域的时候,媒介文化的生产机制突破了之前政治力量主导的单一的指令型运作模式。市场机制介入媒介文化运作之后,必然导致媒介运行领域内的机制张力:一方面,媒介生产仍然且必须遵循政治力量的规范和制约,并承担主导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建构功能;同时,市场运营的利益追求和大众文化的广泛需求,不断促使媒介生产在市场化、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在事实上不断调整政治力量的约束。既有的“控制机制”和新的“市场机制”在媒介机构的意识形态导向、产品生产、目标诉求等方面有一致更有冲突和抵牾,这种复杂的联动机制必然会导致媒介管理的调整、媒介体制的改造和媒介生态的变化,或者也可以说,这种复杂的联动机制必然导致一个诸多力量复杂博弈以追求动态平衡的过程。
三、“联动机制”下媒介文化生产的多极化现象
如同上文所分析,当代中国媒介文化生产受到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双重钳制,显示出复杂的机制性张力和空间内的博弈过程。其实,除了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这两种决定媒介生产运行机制的本质性力量之外,还有两种参与性因素也一起构成了传媒生产机制的复杂性,那就是媒介生产的专业因素和审美因素。专业因素主要指在技术构成层面和操作理念层面“专业主义”的影响,而审美因素则是指媒介文化除了作为“商品”所具有的商业价值之外,还必然蕴含着作为“文化”而存在的审美价值或称文化价值。
因此,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生产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单一的政治控制性力量规范下的一体化生产,逐步演化为多种力量参与博弈下的复杂联动式生产模式,其文化生产及其样态也呈现出明显的多极化现象。
(一)媒介生产中的“意识形态隐喻”
当我们将传媒称为“喉舌”的时候,对传媒的立场要求就非常明显了,同时,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论分析,大众传媒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并持续不断地在它的文化文本生产中呈现着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意识形态的传播手段。
媒介文本中的意识形态隐喻与涵化是最重要的手段。当今传媒已经成为制造、传播和强化意识形态的最重要且最有效的渠道,它通过将某种特定的价值体系传递给公众并解释其为可被普遍接受的“自然”,成为意识形态的发散地。意识形态的涵化功能是指让受众在不察觉的情况下接受媒介的意识形态侵略与进攻,相当于沃纳·赛佛林所提出的“教养理论”(cultivation theory):“对大量看电视的观众来说,电视实际上主宰和包容了其他信息、观念和意识的来源。所有接触这些相同消息所产生的效果,就是格伯纳等所称的教养作用,或者说电视起到了教导人们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角色观和共同的价值观的作用”[7]。传媒对意识形态涵化的过程通常需要两个步骤:首先是对生产的文本进行意识形态装扮并最终以媒介产品的形式进入公众关注的视野;其次,涵化的最终效果需要公众的参与和解读,因此,这个最终的效果并非是确定的。
很多典型的媒介事件都能充分地解释这种意识形态涵化的目的性。比如“春晚”:中国中央电视台从1983年开始举办每年除夕夜的“春节联欢晚会”,至今已有33年,这种中国电视生产出的典型而重大的传媒产品甚至被称为中国人的“新民俗”。这台“文化大餐”不仅仅是一个娱乐电视节目,更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在“春晚”的关键词中,除了与新年除夕相关的“团圆”、“祝福”、“欢乐”之外,更有“民族团结”、“中华儿女”、“凝聚力量”、“强国之梦”等等对民族国家理念的强烈追求。
因此,媒介生产从本质上讲生产和传播的是价值观,并且通过价值观经营实现意识形态的霸权统治,这是通过传媒进行社会控制的真正目的。
(二)“资本之手”的产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媒介生产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手段,同时,在资本运作领域赢利为首要目的的逻辑支配下,文化生产越来越向大众文化的方向集中,因为大众文化生产可以大量复制从而极大降低生产成本、大众文化消费旺盛因而交易量大且利润可观。文化生产的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分化的另一结果,是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文化生产主体,即商业性文化生产主体。
这种商业性文化生产机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从事文化生产活动过程中的商业目的,换句话说,这些文化生产主体进行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赢利,因此,这些文化生产机构必然采用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同时,“文化工人在等级森严、有高度劳动分工的‘职业’管理组织中工作”[8],从而能够做到高效率生产、大规模生产和复制生产。但商业性生产主体也存在弱点,比如“每家公司都在试图获得大众市场最多的份额,垄断组织的成员之间竞争激烈,但每一家几乎都没有创新动力。这些公司更倾向于避免与创新联系在一起的风险,乐意生产高度标准化的和同质的产品。只有这些公司失去了对市场的控制而面临日渐增多的竞争压力时,它们才被迫进行创新,利用标准化程度不高的内容来销售它们的产品”[9]。这也很能说明为什么影视生产会产生许多可以预判市场价值的“类型片”,也能说明为什么媒介产品会出现“同质化”,为什么一旦一个产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后会引来一众“跟风”与“模仿”,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生产机构对资本安全性和利润可控性的考量。
媒介文化领域产生了新的生产主体,并遵循和使用市场运作机制进行生产,很大程度上冲击并改变着媒介文化的单一面貌,迅速变得多样化。
(三)政治化与市场化的分殊与合意
由于中国传媒文化生产领域中行政与市场并行的二元机制,其内部的张力与矛盾也并存:政治主导性的“喉舌”要求与传媒市场化的诉求显然存在矛盾,前者以维护意识形态霸权为目的,后者则以单纯的市场原则为导向,如何解决矛盾并缓解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的紧张关系,成为政府、传媒和投资者等各方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政治化生产与市场化生产在生产方式和目标上不尽一致,同时,政治化生产与市场化生产的空间和形态分离既能在某种程度上保障政治化生产的严肃性和可控性,也能够为传媒文化市场化、产业化发展提供相对充分独立的空间。但尽管分殊如此,两种不同样态的媒介文化生产又在现实中呈现出互惠合作的态势。其一,在内容生产方面,政治话语希望能够“寓教于乐”,并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市场化的传播理念和运作方法,从结果上看改变了政治宣传原有的刻板样态而被重新接受。比如《感动中国》,在典型报道备受质疑、充满诟病的环境下,依然能够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的扭转。其二,在格局划分方面,市场化的娱乐话语通过自觉地“不越界”来体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并以此作为条件换取政治许可和支持。
所以,当政治性目标想要借助市场力量达成时,当资本之手表面上迎合意识形态宣传而实则图谋更大的经济回报时,两种力量便能达成暂时的一致进行合作。而合作成功,则能使意识形态教化、娱乐大众、经济回报这三种不同取向的追求都获得实现。
[1] 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3):65.
[2] 童兵.市场经济:中国新闻界的新课题-兼议新闻改革的价值取向及其纠正[J].新闻知识,1993(3):6.
[3] 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92-393.
[4] 李良荣.西方新闻媒体变革20年[J].新闻大学,2000(4):14.
[5] 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M]//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49-150.
[6] 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2.
[7] (美)沃纳•赛佛林.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孟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92.
[8] (英)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M].吴靖,黄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3.
[9] (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M].赵国新,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2:50.
本文推荐专家:
鲍海波,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理论。
李震,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现代诗歌批评与研究。
Transformation and Linkage of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Media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WANG MINZHI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710062,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the oper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media culture production transfers from the single political led mechanism to the linkage opera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dual leadership of politics and the market. This linkage mechanism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e production of media production logic to the intrinsic torsion and update debugging. In this complex linkage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rules, media products also show the ideology acculturation, marketization, and political market combining multi-level patterns.
media culture; culture production; mechanism conversion; marketization
G209
A
1008-472X(2016)03-0109-05
2016-02-16
王敏芝(1976-),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