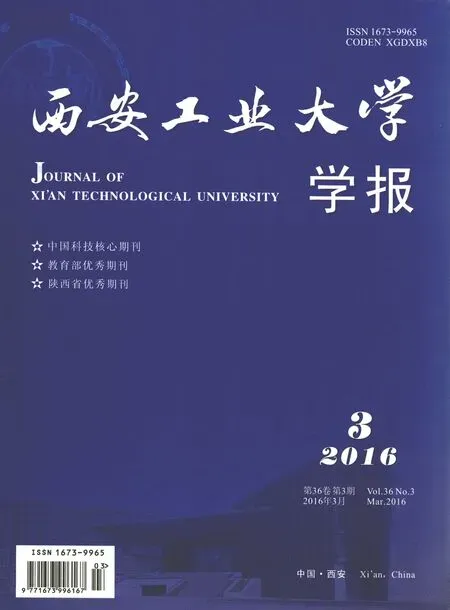抗争政治学视域下的治理秩序与制度选择
梁华平,张 倩
(西安工业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西安 710021)
抗争政治学视域下的治理秩序与制度选择
梁华平,张倩
(西安工业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西安 710021)
摘要:社会治理是一项浩瀚繁杂的系统工程,频发的社会抗争表征着民众与现有体制的裂度,解构着制度的刚性,影响社会稳定,降低政治认同.在社会治理中,制度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在抗争政治学的研究视角下,制度选择在宏观上应考量发展与秩序的问题,在微观上应考量利益、权利和权力的边界问题,在制度存量和增量上应考量其短缺和剩余的问题,而在效益上应考量其成本和收益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抗争;治理秩序;制度选择;抗争政治
制度是组织人类共同生活、规范和约束个体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因此,制度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决定人们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1].他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法律制度等.从政治科学的视角看,对于制度理论的研究历经了旧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①,而新制度主义又有不同的理论形态,如利益代表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规范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等.尽管不同的制度主义派别在制度定义、偏好、变迁、个体与制度间的互动等方面存在明显分歧,但B·盖伊·彼得斯认为,各种制度主义对于制度的理解有共同特征.第一,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和/或政体的结构性特征;第二,制度在一段时间内具有稳定性;第三,制度一定影响个人行为;第四,制度成员中有某种共享的价值和意义[2].虽然制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正如对制度研究的理论形态在不断演化一样,实体制度也在不断发生变迁.
制度变迁的路径不外两种,一是制度的自适应所产生的变迁,制度自我识别环境变化,进而调适以适应变化的环境,著名的“垃圾桶理论”②即是该路径的有力论证;二是制度对外部刺激的反应而非由于内部价值的需要.外部刺激则复杂多样,如规范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危机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根源,危机来自于日益增长的环境条件和需要与制度的规范导向之间的不匹配;而历史制度主义则把制度变迁归结于均衡断裂,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制度处在均衡状态,按其预期发挥功能,但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会发生剧烈变化,在新的制度形成之后又会继续保持均衡和稳定.
从抗争政治学的视角看,社会抗争是影响制度变迁的重要外部刺激因素.抗争政治学的研究起始于西方,已经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甚少.他的代表人物如美国政治学者查尔斯·蒂利、印度社会学者帕萨·查特杰等,以“抗争政治”作为其规范用语.而国内学者于建嵘将之概括为“抗争性政治”.不论如何称谓,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他属政治社会学的学科内容,以底层社会的视角观察底层民众的行为,他并不预设抗争主体行为的合法性,而是一种相对于传统精英政治的一种新的解读方式,他以政治的眼光对底层民众的制度化或反制度化行为进行解读[3].
一定规模的抗争挑战着既有的社会秩序,考验着执政党的社会治理能力,他易于造成治理危机,进而迫使制度做出回应和选择.我国当前处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传统的思想、意识、价值等在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反过来又对现有的秩序形成新的认同和忠诚的要求.同时,近年来伴随各种社会矛盾的增多,人们非制度化的行为反应增加,人们的心理预期发生“异化”,常常会选择体制外的渠道进行利益表达、反映诉求和维护自身权益,这对社会治理产生非常大的挑战.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现代性与稳定性是形影不离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4]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改革目标的要求,即是基于对当前局面的判断而对制度建设提出的要求.面对社会抗争带来的治理危机,制度该如何选择?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大而又现实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1社会抗争:一个理论与实践并存的问题
社会抗争从研究内容上看,交织着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心理学等,从学科发展与分类的视角看,他属于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国内学术界对社会抗争问题的研究可归纳为两方面:①从社会抗争事件出发,在理论上将其概括为“群体性事件”或“群体性突发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等,将其进行特征研究、类型学划分,并提出相应的治理思路或政策建议,如于建嵘的《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肖文涛的《群体性事件与领导干部应对能力建设论析》等文即是此类代表;②借鉴国外社会冲突、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等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美国学者的“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和印度学者的“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③[5],并将其运用到对国内相关社会实践的分析上,如胡庆亮的《抗争政治视阈下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杨爽的《当代中国抗争政治对政治认同的影响分析》和黄冬娅的《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等研究论文即是此种类型.从对近年来关于社会抗争问题研究的文献梳理看,西方的抗争政治理论和研究视角已经被国内学者普遍接受和运用,出现了较多的研究成果,除了研究论文外,也有相关研究著作出版,如《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于建嵘,2010)、《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谢岳,2008)等.所谓抗争政治,他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第二,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6].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是抗争政治行为中的利益相关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定要扮演抗争中的主体方或诉求接受者的角色.最简单的抗争形式是一方对另一方提出自己的要求,但只有当这种需要与权力产生互动时才属于抗争政治的情形.
从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实践看,社会抗争的逻辑起点有三:一是生存伦理受到挑战,即植根于一定社会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受到挑战或生存权利面临重大困境,该社会群体起而抗争;二是依势抗争④易获成效,即弱势群体在实际维权抗争和利益博弈过程中依靠集体力量、社会关怀抑或大众舆论的力量,对诉求对象或第三方抑或是直接的政府部门施加压力,从而实现某种诉求;三是利益、权利、权力之间的边界冲突⑤引致,即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利益、权利、权力等的边界秩序失衡,从而导致社会冲突的发生.以此为逻辑出发点,中国的社会抗争呈现三种类型:一是维权;二是泄愤;三是认同改变.维权即是自身或者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侵害从而通过一定途径采取单独或共同行动来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目的明确、对象清晰;泄愤即是出于对自身或者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侵害或自我所认可的某种价值受到挑战而产生强烈不满,从而采取某种行动发泄不满情绪,该类型一般无明确诉求对象,无明确目的性;认同改变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抗争,他是伴随政治文化的变化,部分社会群体与现有体制的契合度降低、裂度增加,从而采取某种行动进行抗争,该类型的诉求具有价值导向性.国内已有对社会抗争的研究基本是从群体性事件出发,其理论观点带有明显的群体性事件研究的烙印,但从抗争政治学的视角看,群体性事件与抗争政治尽管有重叠,但并不等同.群体性事件的抗争主体为一个群体,抗争政治视角中的抗争主体可以是群体,也可以是个人或机构;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诉求不一定需要与公权力发生互动,而抗争政治下的抗争主体需要与公权力发生互动.
2抗争、秩序与治理
秩序有两种形态,一是制度形态的,一是伦理形态的.他描述的是一种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既可以自然形成,也可以创制获得.在近代以来的工业社会中,秩序基本上是由组织提供的,属于一种创制秩序[7].他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必备条件,尤其在社会复杂化程度非常高的当代社会,对秩序的需求与依赖极其强烈,创制秩序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性要素,是当前存在的社会结构类型的支撑.尽管在后工业化时期,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大大增加,对创制秩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挑战,整个人类社会也都呼唤一种建立在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基础上的自觉秩序,即社会伦理秩序,伦理秩序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在于人际关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也在于人们活动的有效合作,在本质上意味着生活在这种关系和秩序中的人可以合理地、有效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并且能够预见从其他人那里所可能得到的合作,使自己的行动为正确的预期所引导,从而使行动比较主动和自由[8].创制秩序的历史功绩斐然,并且这种秩序下的制度的路径依赖以及带来的人的思维模式及行为模式已经深刻的影响着社会进程.在工业社会前提下的秩序带有明显的控制色彩,他就是为控制的需要而不断进行的制度供给,尽管秩序的存在有其现实合理性和正当性,但依然与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形成一定摩擦和冲突,此种摩擦和冲突对秩序而言有某种程度的积极意义,有利于释放社会压力,可以使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弹性平衡中,也有利于自由的更好实现.正如哈耶克所言,自由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经由那种同时也是自由之规训(The Discipline of Freedom)的文明之规训(The Discipline of Civilization)的进化”造就的.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享有自由,实是因我们对自由的约束所致”[9].
秩序的反面是失序或无序,即组织规则出现了混乱或得不到遵守,制度出现短缺或制度效用降低,进而形成治理危机,社会抗争即是破坏秩序与造成治理危机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从抗争政治学的视角出发,文中所述的社会抗争必须是政府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或者是抗争要求的提出者,或者是抗争要求的接受者等,在抗争行为中具有利益相关性,政府在其中的存在至关重要.从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进程来看,其实质是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制度变迁过程,交叉了权力文化向权利文化的转型发展.在此进程中,利益、权利、权力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社会各主体均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和手段,当然掌握权力的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由此权力与权利的边界模糊甚或交叠,行为习惯与制度规则相互冲突,社会矛盾凸出,非制度化的诉求表达方式增加,社会抗争事件频发.社会抗争的出现从民众与现有体制的关系而言,表明民众与体制之间已产生了一定的裂度,民众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抗争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社会抗争的形式既可以是缓和的,也可以是暴力的;社会抗争的范围可以是区域性的,也可以是全局性的;社会抗争关涉政府的要求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社会抗争对秩序的冲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社会抗争可以是自力抗争,也可以是借力抗争.无论何种形式的抗争,均是对正常社会秩序的挑战,甚至会造成治理危机,从国家层面来讲,就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
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种新的理念,他的兴起源于西方国家福利管理危机的出现,同时也与众多社会组织集团的迅速成长、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等方面密切相关.他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多元主体基于多元目标,运用多样化手段对公共事务进行协同管理的过程和活动[10].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治理过程中不同的利益或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协调的机制的非均衡性和社会快速转型所带来的治理实践的滞后性,社会层面的抗争极易形成治理危机.社会抗争带来的治理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社会抗争影响社会稳定.这里的社会稳定是指一种秩序意义上的稳定,他给予任何一种社会都具有功能上的优先性,没有基本的社会稳定,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正常运转.在现代法治社会,各种法律制度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各种社会活动都在法治的轨道运行,那么制度的基本价值—保障自由秩序—就得以实现.但是,现代社会充满了矛盾、冲突、竞争,利益、权利、权力之间的边界秩序不断被打破,非制度化的利益诉求和表达增加,尤其是大规模群体性的、非理性的、冲击正常社会秩序的或具有破坏力的抗争行为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抗争主体为个体或小规模群体的非对抗性的抗争行为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制度选择漠视或失当,从长远看,也不利于社会稳定.第二,社会抗争降低政治认同,增加体制离心力.政治认同是一种政治态度,是政治合法性的前提,是把社会成员组织在一起的重要凝聚力量,是社会维系和发展的基础.“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着让他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1].这种意愿就是政治认同,他是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所属的政治系统的情感上的归属感或依附感,政治认同本质上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的信任、政治价值的信仰[12].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看,即是民众与体制有较高的契合度,而社会抗争的存在则表明,民众与体制之间的裂度大于契合度.因此,社会抗争表明民众对政治认同度的降低,与体制离心力的增加.第三,社会抗争弱化制度效用,异化利益表达.制度是一种人们有目的建构的存在物,他的基本价值在于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保障社会秩序.而社会抗争的利益诉求和表达往往是非制度化的,由此他破坏了制度存在的价值,弱化了制度的效用.同时,社会抗争也存在一定的潜在利益相关者,如果抗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那么这些利益相关者同样会寻求抗争性的利益表达.社会抗争同样会导致其他社会群体心理预期的异化,在其需要表达诉求或维权的情况下,非制度化的表达将会成为其重要的选项.
3制度选择的逻辑理路
制度选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各种制度的探索、追求、选择和取舍.制度选择与分析政治的方式紧密相关,从政道的角度看,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人民的需求是民主的关键,是关系到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问题.社会抗争是影响制度变迁的重要外部刺激因素,一个社会层出不穷的抗争事件表明民众与体制之间的裂痕,表明制度不能有效回应民众诉求,因此,迫使制度必须做出适应性选择.那么,制度该如何选择呢?
3.1社会与人的发展与秩序的均衡
发展是事物从出生开始的一个进步变化的过程,是事物的不断更新,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秩序”一词在词源学意义上是指人或事物所处的位置,即按一定规则的存在.在一般意义上,秩序有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之分,自然秩序是指遵循自然规律支配的自然界的有序存在状态,而社会秩序是指由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伦理道德、法律制度等规则支配、建构和维系的人类社会存在状态.从政治学视角看,秩序就是各政治主体之间的一种均衡状态,而这种均衡基于基本的政治共识与法律制度.发展与秩序是人类的两大基本追求,两者相依相存,秩序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发展是最终的目标追求.在社会实践中,两者常常相互矛盾,怎样协调发展与秩序就成为对制度设计和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考验.
制度的首要价值是保障秩序,秩序的获取有两种手段,一种是依靠国家机器强制获取,一种是依靠制度科学合理设计获取,而后一种是现代社会制度设计的基本旨要.除了保障秩序,制度的另一重要价值就是推动发展,这里的发展指社会发展,也包含人的发展.社会发展是一个社会的向前运动过程,从纵向看,是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和发展过程;从横向看,是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一个社会各方面整体的运动和发展过程.制度变迁的历史就是人的发展历史,制度的终极价值就是促进人的发展,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人的发展包含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人的发展问题贯穿于马克思制度变革理论价值诉求的始终[13].制度集保障秩序与推动发展这两大问题于一体,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在当前社会,频发的抗争事件冲击社会秩序,考验治理能力,需要制度作出回应,在此情况下,我们应当汲取国内外在此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同时结合错综复杂的国内与国际背景,在制度选择中充分认识到发展与秩序之间的矛盾性,进而探求两者之间的均衡.
3.2利益、权利与权力的边界保障
制度如何选择受制于多种因素,有其基础性的影响因素,如历史传统、民族文化、政治结构、经济因素等,也有其现实性的直接因素,如社会抗争等.从抗争政治的视角出发,利益、权利与权力的边界保障是制度选择的重要基点之一.权利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体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由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的社会成员和特定社会力量主张其利益的法定资格[14];权力是对他人和资源的一种支配力量,马克思.韦伯将其定义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15].尽管在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强调权力来自于权利,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但是在实践的运行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常显现.同时,社会抗争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存在,是部分民众自身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自己所认可的某种社会规范或伦理道德底线受到挑战而采取的一种利益表达方式,在表达诉求过程中有可能冲破利益的边界而挑战权力,同时权力在回应这种抗争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冲破其边界而伤害权利.因此,在制度选择中制约和设置权力边界,保障权利边界,合理整合和划分利益边界是在制度上进行边界秩序构建的重要基点.
3.3制度短缺与制度剩余的研判
制度短缺是指制度供给小于需求而造成的相应社会行为和关系没有规则约束,制度剩余是指制度供给大于需求而造成的制度的边际效益递减、制度多余或无效.不论是制度剩余还是制度短缺,都是一种制度非均衡状态,制度变迁的发生机理就是从非均衡向均衡的发展.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看,由于制度处在不断的变迁过程中,加之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对于一个特定社会来说,非均衡往往是常态,均衡则是短暂的,但这并不能否定制度选择对均衡状态的追求.制度选择包含对各种制度的选择和取舍,在此过程中,必须考量制度短缺与制度剩余问题.对于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或现象,制度短缺抑或剩余的判断和选择是明晰的,由于社会存在的复杂性,在特定问题下运用已有制度还是修订已有制度抑或创设新的制度?制度选择中的制度短缺或剩余问题并不明晰.如我国对腐败问题的治理,已有制度供给充足,但是多年以来,腐败蔓延的势头始终未得到有效控制.正如学者陈景云、杨爱平指出的,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是我国廉政制度建设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廉政建设中出现大量制度剩余,使廉政工作的边际效益递减;另一方面,国家制度建设意义上的宏观制度环境和廉政制度体系却存在明显的制度短缺,影响到反腐倡廉的整体功效[16].社会抗争交织着利益、权利、权力等复杂关系,其大量存在表明制度的非均衡性,制度选择中如何应对,需要对制度的增量和存量状况进行缜密、科学的研判,进而寻求制度供给的均衡.
3.4制度成本与制度收益的评估
制度与普通物质产品和思想产品一样,同时具有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制度成本包括制度创立成本和制度实施成本,制度创立成本包括制度决策成本、制度变迁成本、制度风险成本;制度实施成本指制度运行和维护成本、制度运行的机会成本.制度收益主要包括制度创立、制度运行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各种收益和好处,从宏观看,制度收益在于能体现民众利益、增进社会福祉、保障公平正义.显而易见,制度效益的体现就是其收益大于成本.在当前中国社会,一般的社会抗争未涉及制度层面,在特定情况下,当制度必须做出选择时,制度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就成了关键.制度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他是保障社会秩序的基本要素,制度不能随意创设和废弃,朝令夕改则易损失制度的权威性,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制度创设中的风险成本亦是巨大,尤其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中实施的制度,任何试错都会带来难以预料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同时,理论论证有效的制度在实践运行中的收益亦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往往比理论论证更加复杂多变,因此,评估制度成本与收益是制度选择的关键问题之一.如近年来网络反腐的兴起开辟了反腐败的新通道,但制度的应对较为谨慎,对于这种来自民间的反腐力量进行了选择性的回应,一方面接纳了这种反腐败的新手段,开辟了官方互联网反腐渠道;另一方面对于民间专业反腐网站的建设未接纳.
4结 语
社会治理是一项浩瀚繁杂的系统工程,当前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经济社会等领域深刻变革,社会资源和利益关系不断调整,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社会抗争事件时有发生,对社会治理能力带来极大考验.在社会治理中,制度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人在社会实践中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抽象形式,制度及其变革集中体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博弈和竞争,[13]且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制度也在不断调整、变革和创新.在抗争政治学的研究视角下,制度选择在宏观上应考量发展与秩序的问题,在微观上应考量利益、权利和权力的边界问题,在制度存量和增量上应考量其短缺和剩余的问题,在效益上应考量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的问题.
注 释:
①以美国B·盖伊·彼得斯为代表的制度主义政治研究学者普遍认为,二战前的政治学研究如法律主义、结构主义、整体主义、历史主义和规范分析等属于旧制度主义.二战后这一学术脉络发生了突变,形成了祛除价值,追求科学化的理论与方法诉求、反对规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输入主义的新制度主义.
②该理论为美国政治学者马奇和奥尔森(Cohen,March and Olsen,1972)提出,是指将已有问题的解决方法固定下来,当发觉制度需要调整时,其就有一套可用的反映储备在那里,制度在变迁时常常遵循这种适当性逻辑.
③在以帕萨·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为主的印度底层社会研究群体看来,现代国家在治理的过程中,发展针对不同人口群的治理机制,这个治理机制提供了弱势人口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中创造非主流政治的民主空间.这些人口不是国家的也不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她/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认为非法的,或是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清除的,也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正规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最多不过成为社会精英动员的对象,在权力分配完成后,继续被统治.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为了生存而必须与这两者周旋.在这个周旋过程中,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夺取国家机器,也不在于取得公民社会的领导权,因而开启了一个介于两者之间极为不稳定的暂时空间,称为政治社会.这些来自下层人口的抗争其实是后殖民时期主要的政治活动,只是国家精英不以“政治”来对待他们.
④笔者从抗争政治学的视角对网络反腐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依势抗争”的概念,具体可见《网络反腐的发展逻辑:基于抗争政治学的解释视角》,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12期.
⑤边界冲突的概念是李琼在其《政府管理与边界冲突:社会冲突中的群体、组织和制度分析》(新华出版社,2007)一书中提出的.
参 考 文 献:
[1]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
NORTH D.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Shanghai:Sanlian Publishing House,1994.(in Chinese)
[2]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2版.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
PETERS G.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The New Institutionalism[M].2nd ed.WANG Xiang-min,DUAN Hongwei,Translation.Shanghai: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2011.(in Chinese)
[3]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YU Jianrong.Contentious Politics:Fundamental Issues in Chinese Politial Sociology[M].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1.(in Chinese)
[4]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HUNTUNGTON S.Political Order in the Changing Society[M].WANG Guanhua,LIU Wei,Translation.Shanghai: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2009.(in Chinese)
[5]帕萨·查特杰.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M].田立年,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PARTHA C.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M].TIAN Linian,Translation.Nanning: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7.(in Chinese)
[6]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M].李义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TILLRY C,TAROT S.Contentious Politics[M].LI Yizhong,Translation.Nanjing:Yilin Press,2010.
(in Chinese)
[7]张康之,张乾友.论复杂社会的秩序[J].学海,2010(1):124.
ZHANG Kangzhi,ZHANG Qianyou.On the Order of Complex Society [J].Xuehai,2010(1):124.
(in Chinese)
[8]宋希仁.论伦理秩序[J].伦理学研究,2007(5):1.
SONG Xiren.On Ethical Order [J].Ethics Research,2007(5):1.(in Chinese)
[9]哈耶克,弗里德利希·冯.法律、立法与自由[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HAYEK,VON F .Law,Legislation and Freedom[M].DENG Zhenglai,Translation.Beijing:China Encyclopedia press,2000.(in Chinese)
[10]麻宝斌.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MA Baobin.Public 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M].Beijing: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2013.(in Chinese)
[1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ARISTOTLE .Political Science [M].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96.(in Chinese)
[12]孔德永.政治认同的逻辑[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24.
KONG Deyong.The Logic of Political Identity [J].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2007(1):124.(in Chinese)
[13]龚世星.马克思制度变革理论的价值诉求及其当代启示[J].理论月刊,2014(5):23.
GONG Shixing.The Value Appeal of Marx’s System Reform The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J].Theoretical Monthly,2014(5):23.
(in Chinese)
[14]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WANG Puqu.Basics of Political Science[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6.(in Chinese)
[15]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MILLER D,BOGDANOR V .Blackwell Political Science Encyclopedia [M].DENG Zhenglai,Translation.Beiji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2002.(in Chinese)
[16]陈景云,杨爱平.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我国廉政制度建设的结构性问题[J].学术论坛,2011(12):54.
CHEN Jingyun,YANG Aiping.System Surplus and Shortage of System: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ity System in China[J].Academic Forum,2011(12):54.(in Chinese)
(责任编辑、校对白婕静)
Governance Order and Institution Cho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LIANGHuaping,ZHANGQian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Political Theory,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Xi’an 710021,China)
Abstract:Social governance is a vast,complex and systematic project.Frequent social protests characterize the fracture degree between the masses and the current system,deconstruct the rigidity of the system,affect social stability and reduce political identity.In social governance,institutions play a decisive ro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tentions politics,selecting institutions needs to examine development and order at the macro level,and the boundary of interest,right and power at the mirco level.As for the stock and increment of institutions,their shortage and surplus should be considered.Their cost and benefi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institutions.
Key words:social struggle;governance order;system choice;contentious politics
文献标志码:中图号:C912.63A
文章编号:1673-9965(2016)03-0233-06
作者简介:梁华平(1978-),男,西安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伦理.E-mail:349176857@qq.com.
收稿日期:2015-02-13
DOI:10.16185/j.jxatu.edu.cn.2016.03.011
基金资助:陕西省社科基金(13B025);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研究项目(2013JK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