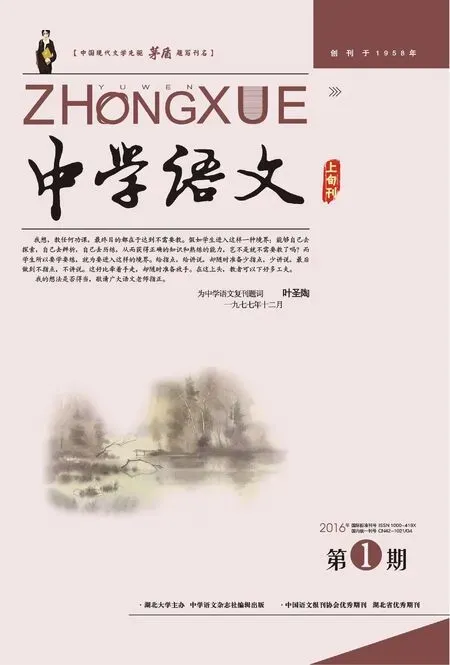《品质》缘何让人怦然心动
沈坤林
《品质》缘何让人怦然心动
沈坤林
初读高尔斯华绥的《品质》,一路下来似乎“感觉平平”,无非是写“我”多次去格斯拉店铺里订做靴子的事情及一些简短的对话,但读至文章的结尾,我们和文中的“我”一起,听到那位“长着英国人面貌的年轻人”说到格斯拉这位能够做“顶好的靴子”的人最终竟至于饿死时,不免怦然心动。
仅仅是格斯拉的死亡、饿死结局本身,让我们心有所动吗?
很少有教师引领学生贴着文本、从文本本身的艺术魅力之角度去探究内在的缘由,我们见到的大量课堂,是教师让学生离开文本去讨论格斯拉的做法是否值得、他应该如何与时俱进之类的问题。于是,作品留给我们的最初感动被忽略了,而作为这一感动背后的艺术特质也被无形地消解了。
笔者以为,从作品欣赏的本体视角看,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探究此文让我们心有所动的内在机理。
1.突破“框架”的震动
我们面对一个作品,脑子里并不是空白的。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文本的相关内容或情景与自己头脑中既有的认识或认识框架(根据框架理论,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以一种类似框架的结构存储在大脑中)相联系,然后作出各种各样的反应。
在《品质》的前面绝大部分,作者通过叙述者“我”,引领我们走出了格斯拉的手艺世界。格斯拉以做靴子这种“手艺”而自豪,从心底里觉得一张无生命的皮革也是“美丽”的;他敬业,尽责,诚信,真正做到质量第一、顾客至上;他为前途忧虑但仍然执着地坚守。在我们走进其手艺世界的同时,也感悟到他的心灵世界之美好。于是,以我们对生活的认识,对整个小说的发展有个预期:这个有着这样“鞋品”和人品的鞋匠,应该有更好的前途;这样的鞋匠,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即使在工业化大潮中,也应该有格斯拉这样的人的一个天地,他们的品质应该被传承下来。
同时,我们似乎跟随“我”与格斯拉交往,并渐渐地认同了“我”的态度与情感,也为格斯拉有“我”这样的顾客而感到高兴,虽然生意日渐清淡,但在这个世界上好歹还有关注格斯拉的人。以我们对生活的一般认识,至少是“好人总有好报”。
想不到,小说的结尾部分来了一个突转,让一个年轻人交代格斯拉的结局,竟然是饿死——这便突破了我们原有的认识框架:重质量、讲信誉的竟然无法生存,竟落得这样的下场!
还有,那位年轻人的情感态度也打破了我们原有的框架。我们与“我”一样,一路下来是同情、怜悯格斯拉的,对他的品质是认同并希望得到传承的;但那位年轻人却只在标榜自己有眼光、公道(“我愿意替他说这句话——在伦敦,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比他更好的靴子”)的同时,只是肯定了格斯拉的“鞋品”,却否定了他的人品(“他是个怪人”)。这又一次与读者的心理期待相冲突,也让人唏嘘不已。
可见,《品质》叙述者“我”在小说的前面部分帮我们“接通”“激活”原有的认识框架,从而产生自己的预期,让我们“能从过去的知识经验中进行预测,引起对有关事物的注意、回忆和推理”①,而在小说的最后,通过框架突破最终与之前引导我们建立的预期截然相反,从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文学效果。
2.叙述“限制”的张力
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对格斯拉饿死结局的震撼,是因为在前面的阅读中没有“心理准备”。如在生活当中,知道一位老者卧病在床多年且去探望过,对其离世的消息不太会有较大的惊讶,而突然听到昨天还见面的一位年轻熟人遭遇飞来横祸而去世的事则往往难以接受。
问题是,我们读《品质》时,对格斯拉饿死的结局为什么没有必要的“心理准备”?
这与作者对叙述者的选择有关,你看,就是叙述者“我”也没有“心理准备”,在小说结尾部分“我”说“但是饿死——”,显然也是表达一种难以置信的意味。
这篇小说选择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而“我”的视角是一个有限视角。“我”只能叙述“我”看到的格斯拉的生活状态。于是,小说的前面部分,写“我”与格斯拉的交往,客观上只是有选择性地“突出”格斯拉的手艺和态度,目的是引导读者将所有关注聚焦于他的品质,从而不知不觉忽视了格斯拉的日常生活,导致格斯拉做靴子此外的生活情节空白。比如,除了身体虚弱又“心里老是想不开”的哥哥之外,其他有无家人?在“我”的“镜头”之外的格斯拉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度过的?饮食起居、日常开销又是怎样的?生了毛病有没有去看医生、有没有人来照顾?等等。这一切空白,事实上悄无声息地铺垫了令人震撼、令人措手不及的“饿死”结局。
可见,人物视角的局限性限制了人物自己的视野,叙述者“我”自己观察不到的视角范围,读者理所当然也无法涉及。读者由于受控于人物有限视角,无从预测故事结局。因此,小说的结尾部分,当年轻人来说出“真相”的时候,惊愕不已的突变结局便让读者惊叹不已。
如果采用全知视角且不加限制来叙述格斯拉的故事,故事还是原来的故事,效果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早已知道格斯拉的日常生活,对饿死的结局便觉得是“自然”的;而如果让全知的叙述者到最后“和盘托出”其日常生活,又让人有“故作神秘”之感。
3.巧用“回叙”的反思
不可忽略的是,对格斯拉饿死结局的怦然心动,隐含着我们掩卷之时的思考——虽然艺术作品不是直接地给读者一些“思想”的,但好的艺术作品总是会促发读者思考的。
《品质》引发读者思考的角度很多,但从艺术的角度说,最重要是叙述本身的反思意味——对格斯拉生存环境、格斯拉品行及其价值等思考,不是简单地揭露或评判,也不是简单地给问题出答案,而是把问题呈现出来,引发更多的人思考。
问题是,这种反思意味,是靠怎样的艺术手段来实现的?
笔者以为,这篇小说的艺术匠心在于采用了回述型叙述的方式。格斯拉的故事,是“我”在若干年后的追叙和回想,这从小说的开头就可以看出:
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哥哥合开一家店,店房有两间打通的铺面,开设在一条横街上——这条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那时,它却是坐落在伦敦西区的一条新式街道。
“这条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可见,格斯拉兄弟的故事,不是发生在现在。现在连那位年轻人的店铺也不见了,因为那条街都“已经不存在了”。
下面的故事,似乎是按故事发生的顺序进行下去的,但叙述者“我”的一些感受与情感显然更多的是立足“现在”对以往进行回望而产生的感受与情感。
比如“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我当然在后来才有这种想法……”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对格斯拉靴子及其灵魂的认识也是回顾中提升的。
比如,在“……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人们不可能时常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所做的靴子非常经穿,一时穿不坏的——他好像把靴子的本质缝到靴子里去了”等叙述中,“迷恋着理想”和“靴子的本质”似乎也不是刚接触格斯拉时的感想,而是在追述中附加了思考。
“选择了什么样的叙述方式,现实就按什么样的方式向我们呈现。”②在叙述“我”与格斯拉的七次交往中,“我”的态度与情感显然有当下的色彩;换言之,是因为格斯拉的“饿死”,照亮了“我”与格斯拉交往的故事,使“我”重新审视以前发生的一切。在回忆中,“我”当初的经历被不断重温,交往的故事及其体验的意义随之深化,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目光,格斯拉的故事超越为一种个体“特例”而有了更具广泛意义的价值乃至社会隐喻:在社会变化过程中,职业及其操守,美德乃至传统,将面临怎样的境况?我们该如何应对?
波兰诗人亚当·扎嘎耶夫斯基有一首诗,题为“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高尔斯华绥的《品质》,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在工业化社会进程中传统手艺的无奈结局,但作者的担当在于,明知这个世界已然残缺,却还是要尝试赞美这个世界。当掩卷而思时,我们自然会为之怦然心动。
参考文献
①刘秀芬:《认知语言学中一组术语的对比分析》,《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②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作者通联:浙江桐乡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