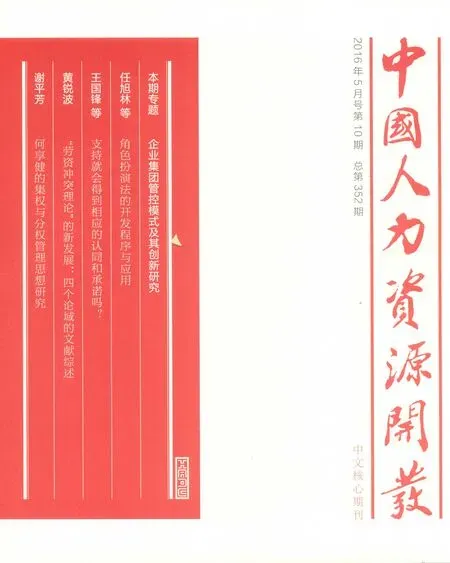互联网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基于美国优步案的新思考
· 韩文
互联网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基于美国优步案的新思考
· 韩文
共享经济不仅催生了众多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也带来了劳动关系形态的新发展,在美国加州的优步案就是二者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不论是在司法领域还是商业实践领域,对优步案的借鉴都应当保持审慎,坚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分析。但在处理此类情况时,不应囿于是否属于“劳动关系”的争议,而应倡导企业与劳动者的平等协商,友好对话,在诉讼外展开良性互动,在法律框架下认定权责,通过市场机制来调整雇员与非雇员的分成比例,从而实现劳动者的自由选择。
劳动关系形态 良性互动 共享经济
正如《共享经济2.0》一书中所说“共享经济在重新分配、利用闲置或过剩资源的同时,对传统的劳动者和资本方的关系也带来挑战”。共享经济的到来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谋生方式?还是预示着其要颠覆企业的雇佣模式?关于优步(Uber)驾驶员与优步网约车平台之间的诉讼引起了各方学界的密切关注。已有学者对其到底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展开论述,认为从劳务关系的角度来认定驾驶员与网约车平台之间的关系似乎更符合实际情况。(彭倩文、曹大友,2016)虽然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对该问题仍无定论,但是在“劳资关系”之外还蕴含着更为深刻的“组织”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公司平台化原本目的是改善资源闲置和人员闲散的现象,而优步司机的请求是否与互联网平台企业“轻资产”理念背道而驰?互联网平台企业对劳动者的控制合理吗?如果在优步案中确立了司机的雇员身份,是否会对我国的同类互联网企业产生影响?共享经济下,互联网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是否需要回归传统的劳资关系的界定?如何实现二者之间良性的互动?笔者试从优步案重新解析,讨论这场“劳资关系”诉讼中容易被忽略的几个问题。
一、优步案初探:雇佣诉讼的域外采风
优步是所谓的预约租车(For Hire Vehicle)服务的提供商,也称为FHV服务公司,这种服务的特征是通过网络提前预约进行乘客和车辆的智能匹配,(周丽霞,2015)实现资源的集约化配置,在我国也有类似如滴滴快的、神舟等网约车服务提供商。优步在美国一直都是法庭上的常客,盖因其进入的本就是一个严监管行业,但其中最令人关注的还是优步司机对优步公司的“同室操戈”。虽然优步声称其既不拥有车辆的所有权,也不雇佣司机为它工作。但是司机们还是对优步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他们的员工身份。他们声称:优步把他们定位为独立的承包商,但是却像雇员那样对待他们。(Brinklow,2015)优步司机认为,他们需要为此准备一台车以及配套的天然气、保险、收费、维修、折旧,还有税金和付给优步的佣金,而“独立承包商”这个身份一开始出现时也并不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但是优步称,即便如此,许多人依旧愿意选择自己做自己的老板和在自由支配的时间里赚点现金(据优步自己的数据,超过一半的司机每周工作量少于16小时)。(Weiner,2015)如果陪审团认定司机属于雇员的话,优步的商业模式将严重动摇。同时,这项裁决也会影响到那些使用独立承包商从洗衣房到食品配送的所有其他的共享经济的初创企业,他们显然都没有为“独立承包商”支付医疗保险的费用。(Huet,2015)优步的竞争对手(Lyft)和Postmates快递公司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坚持认为他们的大部分司机和快递员都享受了独立承包商的自由。(Macmillan,2015)这些公司都依赖于独立的承包商模式,以廉价的劳动力来带动客户群。
2015年6月3日,加州劳动委员会裁定优步司机是雇员而不是独立的承包商,并责令优步赔偿司机相应的报销费用。但是因为优步对这一决定提起了上诉,这一情况将在法庭进行重新审查。所以优步的司机也未收到报销,因为不得不等待诉讼的结果。无独有偶,2015年10月14日,俄勒冈州劳动和工业局在近日发布的咨询意见中称应当认定优步司机是其雇员。
而在此之前,旧金山地方法院的爱德华·陈法官驳回了优步公司请求法庭省略庭审径直作速决判决的动议,根据法院的命令,该案件将由陪审团来裁定。爱德华·陈法官之前表示他并不认为“优步仅仅是一个提供服务的软件平台”。2016年1月,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优步公司推迟审判的请求,该案将于2016年6月在旧金山开庭审理。而其他州也开始启动了类似的诉讼。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两类司机被排除在优步的集体诉讼之外,一种是通过中间公司(例如豪华轿车公司)来优步开专车的司机;另一种是那些签约时用了公司名或假名的司机。法官给出的理由是,他们的情况有别于那些用自己的名字与优步公司直接签约的司机。这两类司机也开始准备他们自己的诉讼。(Lien,2016)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优步案中司机们的代表律师是曾经赢得联邦快递案的律师,在该案中,对于联邦快递的司机到底是雇员还是独立承包商存在争议,堪萨斯最高法院认定司机为雇员。
二、劳动市场弹性化的新发展:共享经济所带来的变革
1.灵活的控制与弹性化的劳动
在美国,对于“雇员”和“独立的承包商”之间的界限其实是十分模糊的,大多数州只能取决于一些变量来判断。只有一些相应的标准:例如工人是按小时付费还是按每单工作付费?由谁提供必要的工作场所和劳动工具?最重要的是,公司对工人的控制是何种程度的直接控制?(Brinklow,2015)虽然在谈论生产要素的控制时司机们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们始终坚持优步公司对自己的直接控制。
笔者认为,优步司机和优步公司之间的“扯皮”是共享经济发展下,劳动市场弹性化发展的全新体现。有人将其视为一种非典型劳动关系,所谓非典型劳动关系(王思闵,2012)包括部分工时的工作、定期性工作(包括临时性、短期性、季节性和特定性工作)、劳务派遣、多重劳动关系等情形。这是一种劳动关系在从属性上的减弱,导致人对组织的依赖越来越弱,而组织对人的需求却越来越强,但是这种需求并不体现在针对个体,而是针对整个人力资源群体而言。依据威廉姆森的观点,如果企业与雇员之间不能建立起专用人力资产的关系,那么企业和雇员之间都不能因此而得到生产上的利益。(威廉姆森,2002)传统雇佣关系中的组织从属性是与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相统一。虽然在互联网平台企业中,人力在外表上更像是彼得·德鲁克笔下所描绘 “可以随意替换的零件”,但同时也因为“人”对“组织”需要的弱化,从而使得“人”成为了企业最为重要的“资源”。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共享经济催生下的灵活就业所造成的。优步等互联网平台企业所采取的控制方式与传统科层制企业的“行政化命令”控制模式有所不同,其控制方式更为灵活,却一样有效。这种灵活的控制方式似乎就是为了应对弹性化劳动而做的准备,然而,二者真的契合吗?
2.劳动关系的中间形态
正如同Rashmi Dyal-Chand 所阐述的那样:“一开始可能不愿意去承认共享经济是一种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但事实上,它的确是。”这是一种看上去不是创建新规则而是破坏市场行为的规则。这样的公司如果不是众多司机的雇主那么就是为众多独立私人运输从业者提供服务的软件开发商。但是,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问题难就难在优步不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种,自此,他们开始将共享经济理解为一种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Chand ,2015)正如同优步没有汽车,阿里巴巴没有库存那样,共享经济下的互联网企业都对“轻资产”运营模式身体力行,这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雇员稀少。美国畅销电视机品牌Vizio只有200名员工,而被Facebook以高价收购的WhatsApp也只有60名不到的员工数量。(The Economist,2015)这种雇佣政策与原本资本主义经济中“做大做强”(成为彼得·德鲁克笔下的通用汽车那样的“大公司”)的理念似乎有些背道而驰。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去重新理解共享经济下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囿于传统的劳资关系界定,那么依旧会落入劳动关系认定的窠臼之中。事实上,越来越模糊的雇佣界限也在暗示劳动关系与非劳动关系二元论的“终结”,由商业实践与共享经济共同型塑的中间形态正悄然到来。传统劳动关系基于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其核心是对劳动力商品的交换。(杨斌等,2014)而依靠平台提供信息、实现利润分成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并不依靠对劳动力商品的交换获取利润,这使得劳动者越来越像独立的市场主体。虽然现阶段因为行业监管与消费者保护等诸多因素导致互联网平台企业需要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这种介于劳动关系与非劳动关系之间的中间形态也必然会伴随着共享经济的壮大而逐渐清晰。
3.公平与合理的重构
共享经济不和谐道出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我们对一些基本概念的误读:这些概念包括“市场”、“商业”、“创业”和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共享经济让许多美国人意识到现在的商业方式仅仅只是商业方式的其中一种而不是唯一。在共享经济兴起之前,企业家通过积累足够数量的私人财产来体现普遍意义上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式成功,但是共享经济完全改变了这种假设。(Chand ,2015)正如同杰里米·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所表达的一个复杂逻辑“资本主义的成功即意味着失败”。其所立论的基础依旧是新技术带来的产品边际成本的减少甚至归“零”。虽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的假设,但是也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可能:“资本主义的时代正逐渐离我们远去”,“一种改变生活方式的新型经济体制应运而生”。共享经济的出现不仅仅是改变了生活和生产,其也在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杰里米·里夫金还举了一个汽车共享的例子:在美国,汽车平均闲置时间为92%,而汽车支出却要占到每个家庭的20%,私家车主通过在RelayRides等网站上注册,将汽车提供给需要的人,出租人可以按小时或实际使用时间定价。这看上去和优步提供的网约车服务有共通之处,唯一不同的是没有提供司机。这些新型的服务方式无疑都是有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杰里米·里夫金认为“所有权正在成为历史”(里夫金,2014)即便共享经济已经或即将带来巨大的改变,但是不论如何,此时此地,我们依旧还是要面对这一问题: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控制行为真的不是雇主行为吗?共享经济的母体不仅催生了优步等互联网平台企业,还唤醒了优步司机的市场意识与维权意识。优步更愿意通过其所设定的规则而不是倚靠雇佣关系来“操纵”司机,但司机们也不可能“屈服”于一个形式上都不能称之为“雇主”的公司。二者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为“控制”与“责任”之间的矛盾。如果将司机认定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那么优步等平台单方面制定的“约束条款”和利润分成也必然面临合理性质疑。这条逻辑是,如果是雇佣关系,这样安排无可厚非,但既然不想成为雇主,那平等市场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必须对等,不能由一方“单边”决策。所以对优步的控制行为与利润分配就必须加以限制。这也是互联网平台企业面临的焦点难题:如何能够在“控制”与“责任”之间、在分配利益与公平对话之间找到平衡。
三、中国语境下的思考
1.针对优步诉讼的“就事论事”原则
被排除在集体诉讼之外的两类司机表明,针对不同情况的司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优步的发言人在一封邮件中坦言:联邦地区法院这么做是为了这一群体进行区分,他们的情况千差万别。(Kendall,2016)而司机们的律师称,优步对司机有着很严格的筛选(Macmillan,2015),根据Benenson Strategy Group 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优步司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专职司机、转型司机、新入司机和兼职司机。(弓长颖,2015)根据这些司机的经验不同,他们在利润分成中的比例自然也不相同。所以,在中国语境下思考优步案,不能陷入“一视同仁”或“人云亦云”的陷阱。
桑斯坦教授曾认真讨论过司法的“最低限度主义”:除非对于论证结果的正当性确有必要,否则就不发表意见。一方面,这是为了避免司法判决的负担和避免错误,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更是基于对不同事实的尊重与区别对待。泮伟江将其解释为“就事论事”,即只解决手头的案件,而不对其他案件做出评价,除非这样做对解决手头的案子来说确实非常必要,且非这样不可。优步案中,法官将两类司机排除在此次集体诉讼之外,认为他们情况有别,即使诉讼也要另行起诉。
2.中国语境下的实践区别
这给予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很多思考。类似于优步的情况同样可以复制到所有的中国网约车平台上,他们的司机如果“揭竿而起”呢?我们以前似乎从未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在平台类电商网站上开店的店主是该电商的雇员吗?而同样的情况还可以推而广之:外卖网站中的每个营业个体可否主张自己是该外卖网站的雇员?根据“最低限度主义”,这些新问题的兴起都不可一概而论,这里就必须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是中国实践的区别。优步的诉讼结束后,不论结果如何都不适宜直接复制到中国实践中来。事实上,就连优步案中司机的代表律师也表示,该案即使做出裁决其效力现在也仅限于加利福尼亚州。在国情差别、制度差别和发展差别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警惕一种盲目的“人云亦云”。
第二,是行业实践的区别。任何判断也不能直接适用于所有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非典型劳动关系和弹性化劳动市场都是伴随着共享经济的成长而成长,它们早已诞生,但是共享经济使其壮大,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在此之前我们似乎从未思考过类似的问题,就是电商平台、外卖平台和网约车平台之间的区别,不论这种区别为何,我们都需要审慎地对待其中的行业差别,以行业健康成长为目标要求。
第三,是个体实践的区别。优步仅仅只是网约车的代表企业,但是网约车的平台多种多样,每种情况都有其特殊性,不可一概而论。并且正如优步一案所展现的情况,每个司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也注意个体差异。在中国,在以神舟专车为代表的“劳务派遣”模式中司机全部来自正规劳务公司,而以滴滴快的为代表的B2C 和 P2P 混合专车模式中司机大多来自私家车主和出租车主(彭倩文、曹大友,2016)。在中国的这些网约车司机中,与美国情况最为类似的就是自由职业的私家车主。针对网约车平台司机类型复杂的现状,采取“一刀切”模式反而使问题更趋复杂化。
3.“E代驾”——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
其实,在我国也并非没有类似案件发生,全国各地发生过多起驾驶员起诉E代驾公司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在已有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劳动关系”的司法认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2、对劳动关系不做认定,进行模糊处理;3、在交通事故责任中认定雇佣关系,对于超出保险理赔范围的损失,由E代驾公司承担对事故中伤者的赔偿。(徐虎,2016)从E代驾案中也可以看出司法实践面对此类问题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是对于“劳动关系”认定的模棱两可,另一方面又是在面对事故时需要企业承担责任。这种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优步案如果复制到中国时将会发生的大部分场景。那就是我们面对此类问题时的踟蹰不决和束手无策。
这种尬尴再一次唤醒了对于互联网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反思,不论是劳动关系也好,合作关系也罢,模糊处理只是化解矛盾的治标之策,而对立也绝非解决问题的治本之法,只有倡导企业组织与劳动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之法才是解决之道。
四、共享经济下互联网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1.企业的社会责任:良性互动的现实必要性
彼得·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中提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认为公司是介于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不可缺少的存在,公司仅仅只是一个雇佣机器吗?它通过雇佣劳动者来完成劳动者与社会的联结?在彼得·德鲁克那里,答案是否定的,公司是一种价值传递机制,通过其将劳动者个人的价值传递给社会,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的逆向反馈,通过公司将社会价值反馈给个人。共享经济的兴起与网约车服务的扩大需要充分注意这种情况,一方面注重新型问题的处理,如网约车的监管、劳动关系的处理等情形。另一方面,由“个人——公司——社会”的结构转变为“个人——社会”直接接入的情形,看似其中少了“公司”这一环,但互联网平台组织更不能“置身事外”,将自己定位为“第三人”或“中间商”的角色。其采取行动进行积极回应本身就具有现实必要性。优步案的启思是,共享经济下的劳动关系可能在形式上有别于传统的劳动关系,但即便不沿用契约式的劳动关系,企业也应该为劳动者提供平等和理性的对话机制,这既是基于和谐劳动关系的需要,同时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
2.市场化解决路径:良性互动的理论可能性
任何市场问题的产生、变化和发展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经济规律,而市场机制往往又是解决此类问题的良方。当重新审视优步案时,我们会发现,在这场劳资关系剑拔弩张的背后,其实质是企业运营成本和相应责任的增加,而这一切完全可以通过一种更为良性、平和的方式来解决。
在我国国内,并不缺乏将专车司机认定为雇员的实例。首汽专车与专车司机之间就是一种劳动关系,约定了底薪、工作的时间与地点,并且承诺缴纳社保,但是在收入分成上与传统专车平台不一样。首先,这与首汽原本的汽车租赁平台是密不可分的。其次,这种劳动关系的解决模式也提供了一种更为良性的解决思路。虽然其他“轻资产”运行的专车平台想要效仿仍不是易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借鉴的,如果一旦确立了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那么自然原本约定的提成比例与上班时间自然要做相应的调整。这其实就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良性互动。确立劳动关系并不意味着企业运营成本的必然增加,而应当将其视为市场环境下不同劳动者的差异化选择。订立劳动关系后,即便是需要在劳工福利方面有所付出,但是依旧可以在工作时间的延长和分配比例的调整上达到平衡。也即是,控制程度与分配比例的差异化选择,将追求弹性化劳动和高分配比例的自由劳动者与雇员区分开来。相比一味否认“劳动关系”的存在,企业采取更为理性的对话方式,在互动中引入市场调节机制,与劳动者平等协商,实现一种良性互动则更为可取。
3.市场与法律框架下的良性互动
彼得·德鲁克认为现代公司最重要的任务也许就是“在公平与尊严,机会均等与社会地位、社会职责之间达到平衡”。实现社会基本信仰并不表示应该服从于个别企业盈利和生存的目标。只有在履行社会职能的同时能够促进其有效生产时,公司才能成为社会的代表性机构。(德鲁克,2006)通过优步案反思互联网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互动,依旧可以发现其中暗含着类似于传统劳资关系中的那种紧张与对立,虽然有实例为认定专车司机为雇员提供了一种市场化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依旧需要面对这种劳动关系的“中间形态”何去何从的困惑。而事实上,承认这种“中间形态”的存在都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实现。现阶段的解决方案只是寻求市场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笔者认为应当遵循两条主线展开,第一是尊重法律,在法律框架下解决问题,展开理性沟通,重构社会责任。第二是相信市场,在市场机制下调节适应,进行良性互动。共享经济下成长起来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既不能忽略自身盈利,也不能忘记劳动者权益,这样才能让其既成为创新的大本营,同时也成就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1.德鲁克著,慕凤丽译:《公司的概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127页。
2.弓长颖:《Uber又给监管出难题,司机到底算员工还是合作伙伴?》,载36Kr网,2015-03-16。
3.里夫金著,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零边际成本社会》,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36-240页。
4.彭倩文、曹大友:《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以滴滴出行为例解析中国情境下互联网约租车平台》,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6年第2期,第96-97页。
5.桑斯坦著, 泮伟江、周武译:《就事论事: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6.威廉姆森著,段毅才、王伟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36页。
7.王思闵:《台湾非典型劳动制度之研究——德国及日本经验之启示》,国立台湾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8-15页。
8.徐虎,《“互联网+”模式下企业与从业者劳动关系》,载《中国工人》,2016年第2期,第60-61页。
9.杨斌、魏亚欣、丛龙峰:《中国劳动关系发展途径探讨——基于劳动关系形态视角的分析》,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年第19期,第97页。
10.周丽霞:《规范国内打车软件市场的思考——基于美国对Uber商业模式监管实践经验借鉴》,载《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7期,第21页。
11. Brinklow A. Year in Preview: What the Uber lawsuit means for workers in the Sharing Economy. SF Weekly, 2015, December 30.
12. Chand R D. Regulating Sharing: The Sharing Economy as an Alternative Capatilist System. Tulane Law Review, 2015,90(2):245-247.
13. Huet E. Juries to decide landmark cases against Uber and Lyft. Forbes, 2015,March 11.
14. Kendall M. Uber's least favorite lawyer strikes again. The Recorder,2016,January 06.
15.Lien T. Uber sued by drivers excluded from class-action lawsuit. Los Angeles Times,2016, January4.
16. Macmillan D. Uber drivers suit granted class-action statu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5, Sept. 1.
17. Weiner J. The hidden costs of being an Uber driver. The Washington Post , 2015,February 20.
18. Reinventing the company. The Economist, 2015, October 24th.
■ 责编/ 孟泉 Tel: 010-88383907 E-mail: mengquan1982@gmail.com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et Platform Enterprises and Labor:The New View Based on The Uber Case
Han Wen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ring Economy not only gave birth to many of the Internet platform enterprises, it also bring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relations, the Uber case in California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embodied . Whether in the field of judicial and commercial practice areas, we should be cautious about Uber case's influence, adhere to analyz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But when dealing with such situations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whether they are "labor relations" in the dispute,but should promote equal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enterprises and workers. We should carry out friendly dialogue and positive interaction outside the case and do the things within the legal framework, through the market mechanism to adjust the proportion of employees and non-employees and the workers achieve the freedom to choose.
Form of Labor Relations; Positive Interaction; Sharing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