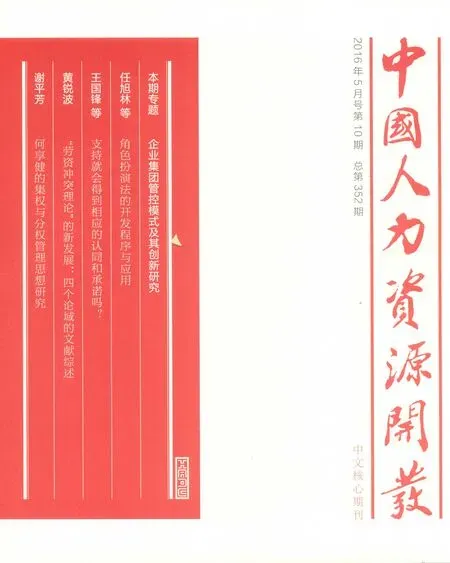“劳资冲突理论”的新发展:四个论域的文献综述——兼议当代中国劳资冲突研究在四个论域的对话
· 黄锐波
“劳资冲突理论”的新发展:四个论域的文献综述——兼议当代中国劳资冲突研究在四个论域的对话
· 黄锐波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调整,资本与劳动对立和冲突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推动了劳资冲突理论在不同论域的新发展。其中,“劳动过程理论”从劳动控制与反抗的角度,阐述了劳资双方在劳动过程中围绕各种因素展开多重博弈;“全球化理论”从资本流通的角度,阐述了劳资冲突的时空转移与跨国联动;“国家理论”从国家维度阐述了国家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策略对劳资冲突的制约和影响;“道义经济学”从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变迁的角度对劳资冲突和劳动反抗作出了的解析。
劳资冲突 劳动过程 全球化 国家策略 道义经济学
劳资冲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之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和冲突,最终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崩溃。然而,马克思的预言并未如期发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调整,资本与劳动对立和冲突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论断所不同,后来的学者们分别在不同的论域中去寻找关于劳资冲突的理论新解释,由此推动了劳资冲突理论的新发展。
本文围绕劳资冲突理论在不同论域的新发展,对相关理论文献进行了综合梳理,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对劳资冲突理论进行总结概括,并针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劳资冲突的理论研究和对话进行评述。
一、劳动控制与反抗:劳资冲突在劳动过程中的多重博弈
沈原曾强烈地批判“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强调要重返“生产中心性”,才能深入了解劳资冲突和工人阶级形成的奥秘(沈原,2007)。一般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是劳动过程理论的经典开端,后经布雷弗曼(Braverman)、布洛维(Burawoy)、托马斯(Thomas)和李静君等人得以丰富和发展。根据马克思的经典论断,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和利润,会采取各种手段对工人这种“活劳动”进行控制,其结果会引发工人的联合反抗进而发展为阶级斗争,最终推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布雷弗曼分析了20世纪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变迁的本质是使工人的“意识”或“观念”(conception)与“执行”(execution)分离开来,资本家通过剥离工人对生产规划的把握,造成了工人的“去技术化”(deskilling);同时生产出一套外在的生产计划与规范体制对工人进行控制,剥夺工人的工艺知识和自主的控制权,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只起到齿轮和杠杆的作用(布雷弗曼,1979)。正是这种劳动的“退化”造成了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如期发生。
布洛维批评布雷弗曼过于强调劳动过程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而忽视了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一书中,他从工人“赶工游戏”出发,阐释了资本主义工厂通过“计件工资制”(让工人加入到“赶工游戏”中来使工人形成内部竞争)、“内部劳动力市场”(通过晋升、轮岗、在岗培训和按资历付报酬等方式给工人在企业内部流动的机会)和“内部国家”(在公司内部建立集体谈判和申诉制度)三种机制重新组织了劳动过程,使工人达成志愿性服从(Voluntary servitude)并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存在一致性,从而有效地消解了劳资冲突与阶级斗争。布洛维进一步通过强迫(coercion)、同意(consent)、专制(despotism)、霸权(hegemony)等概念的构建,认为任何工厂制度都是同意与强迫的组合,当强迫占上风时可称之为专制政体,当同意占上风时则称之为霸权政体。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在新的劳动过程和各种工厂制度中得以不同的塑造(布若威,2008)。在《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一书中,布洛维推进了他的学说,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不仅有经济维度(物品的生产),还存在政治维度(社会关系的生产)和意识形态维度(对这些关系体验的生产)。劳动过程的政治效果和生产的政治规范工具共同构成了一个工厂特有的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在劳动过程中,生产中的关系(relations in production即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即针对剩余价值所发生的剥削关系)之间的斗争就构成了所谓的“生产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布洛维认为,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工厂政体主要是资本家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对工人进行“市场专制控制”;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随着国家力量的介入,工厂政体吸收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发展出了霸权式的劳动控制形式(Burawoy,1985)。
布洛维之后,托马斯和李静君分别引入了性别、公民权等范畴,从劳动过程的微观层面入手,进一步充实、发展了布洛维的学说。托马斯通过对一个使用人力进行收割和另一个使用机器收割的不同公司进行比较,考察了性别和公民权这两种因素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控制的影响。不同的劳动过程对劳动控制的要求各异:人力收割公司如何能以低工资吸引有价值的劳动力而机器收割公司如何保证获得充足的劳动力和稳定的劳动队伍?托马斯发现,人力收割公司是通过雇佣合法和非法移民工人而在市场上激发了劳动力竞争,大量的非法移民由于身份的限制缩小了就业机会空间,并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威胁,造成了他们无法有力地与雇主进行讨价还价,从而成就了雇主对工人的有效控制。而机器收割公司则通过利用女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以及她们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并且通过对工作赋予一定的性别建构(即将操作收割机器建构为“女人的工作”)来分割劳动力市场,促成工作认同,以达到劳动控制的目的(Thomas,1982)。
李静君则通过对香港和深圳两家工厂的比较研究,指出由于深港两地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不同,女工依靠关系网络进入工厂内的性别关系也不同,因而导致“地方专制主义”和“家庭霸权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工厂政体。然而,两种截然不同的工厂政体的发生机制却出现了悖论:香港工厂的中年女工并没有因政府对资本的“不干预”政策和缺乏其他替代性的就业选择机会而走向“地方专制主义”,却因为女工的年龄、家庭角色等的原因发展出“霸权”色彩的工厂政体;而深圳工厂的年轻女工相反也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的制度传统以及“拆分式劳动体制”的存在而走进“霸权政体”,反而因年龄、性别角色等原因而遭遇“工厂专制主义”的对待(Ching Kwan Lee,1998)。
将性别和公民权等范畴带入劳动过程的分析视角,托马斯和李静君试图说明:任何一种工厂政体下,都隐含着根据某种特定的因素来进行劳动控制及规范化的动态权力建构过程。在此基础上,沈原、周潇针对建筑行业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控制的特点,提出了“关系霸权”(沈原、周潇,2007)的概念;任焰、潘毅、汪建华、孟泉等人,还将“劳动过程”中的生产控制延伸至生活层面,用“宿舍劳动体制”(任焰、潘毅,2006)和“生活政治”(汪建华、孟泉,2013)的描述拓展了对劳动过程中劳动控制和劳动反抗形成的观察视野。潘毅、余晓敏进一步将工人反抗性的塑造从生产领域延伸到了消费层面,认为“新生代打工妹”一方面试图通过各种消费行为来改变外表,淡化社会身份差异,实现她们在生产领域无法实现的“自我转型”;另一方面,微薄的收入限制了她们的购买能力,由此带来的社会歧视剥夺了她们平等的“消费公民权”。打工妹的社会身份无法在消费领域获得全面的重建,却最终强化了其次等的生产主体性(潘毅、余晓敏,2008)。
劳动过程理论经历了从马克思的“发端”到布雷弗曼的“退化”再到布洛维的“复兴”过程,再由托马斯、李静君和后来者的不断“充实”:为了在劳动过程中实现劳动控制,围绕性别、公民权、关系、生活、消费等因素所进行的各种“权力建构”和“权力瓦解”,这种“生产的政治”所导致的不同的“生产政体”,工人既可以被“制造同意”、也可以催生“集体抗争”(郭于华,2011);不同的“生产政体”还导致不同的工人联系方式和集体行动的动员方式,由生产控制延伸至生活层面的控制,拓展了工人利用“宿舍劳动体制”和“互联网”(汪建华,2011)来进行集体行动组织和动员的可能性。“劳动过程理论”揭示了劳资双方围绕权力关系的建构,各种“因素”不断被引入到劳动过程中来,资本控制与劳动反抗展开精彩复杂的博弈。正是资本与劳动双方之间在劳动过程中的这种多重互动,使得劳资关系呈现出冲突、缓和与再冲突的反复循环过程。
二、全球化与资本流动:劳资冲突的时空转移与跨国联动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发展而获得确认。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认为,资本在全球流动,致力于构建全球性生产网络,其目的是试图以一种“空间性解决方案”(spatial fix)来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即资本在一定地域空间内“过度积累”的问题(Harvey,2001)。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新的资本积累,资本在新的经济空间中对时间和空间都进行了广泛的重新组织。资本的积累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戴维·哈维将这种变化称为“弹性的积累”,即在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生产和消费模式上都表现出充分的“弹性”(Harvey,1990)(以灵活生产、临时性劳动力使用、国家干预撤离及私有化为特征)。这种新的积累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在过程和结构上都与“福特生产体制”(以大型生产装配线、大型政治组织以及福利型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刚性”完全不同。
资本全球化的这种“弹性”变化,直接导致的就是资本输出国的劳动力市场为了“留住资本”而出现一种工人“向下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新局面,造成国内劳工阶级的进一步分化由此引致劳工运动的危机。对于资本输入国而言,资本在新的“落后地域空间”内,基于这些地区吸引外资的需求和“劳动体制”的宽松,廉价的劳动力得以被使用,由此带来的是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的各种“血汗工厂”普遍林立。资本的这种空间转移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时间概念上的“历史性反动”,激起了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劳工运动,并伴随着“反全球化”的声音与其他社会运动共同进入了“新社会运动”的发展阶段。“反全球化”社会运动中的“行动者”诸如劳工组织、环保主义者、学生、人权组织、宗教组织、女权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社区组织,通过共同的集体行动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正、民主、平等。劳工运动由此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性质,类似“超国家劳工赋权”、“跨国网络支持”、“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及“全球反血汗工厂运动”等,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反抗和劳工赋权的新要素。
贝弗里·J·西尔弗(Beverly J.Silver)在哈维的空间调整(spatial fix)的分析基础上,加入了技术调整(technological fix)、产品调整(product fix)和金融调整(financial fix)分析变量,进一步阐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对劳动控制策略的变化以及对全球劳工运动发展趋势的影响。西尔弗认为,不管资本如何通过各种调整策略来强化对劳工的控制并弱化劳工的团结,试图消解劳资冲突和劳工运动,处于不同国家/地区的工人和工人运动,因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全球政治进程而被彼此联系在一起(西尔弗,2012)。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劳工运动的“个案”之间,会基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通过传播和团结得以构成联系,这种“跨国社会网络的形成”会促成劳工国际主义的新发展。因此,西尔弗认为,21世纪早期的世界各国工人所面临的终极挑战是进行斗争,不仅仅是为了反对工人自身的被剥削和被排斥而斗争,而且也是为了建立一个对利润的追求真正服从于对所有民众生计有所保证的新的国际体制而斗争(西尔弗,2012)。
玛丽·E·加拉格尔将全球化的视角引入对中国的具体分析,她通过对“为什么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治稳定得以在中国并存”这一问题的考察,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具有作为竞争压力、资本主义实验室和为意识形态辩护的三大功能,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国家改革次序选择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多重意义,不仅延缓了中国改革的一系列政治风险,同时为劳资冲突和劳工抗争开辟了广阔的政治行动空间。由外国直接投资所推动的各种劳工立法和劳工保护政策的出台,会对中国的非外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在劳工权利的制度建构形成“竞争压力”,“传染的资本主义”势必会导致“传染的劳工运动和劳工权利在中国的出现”。通过对弱者的不满立法,市场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和基于契约的法律框架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加拉格尔,2010)。
余晓敏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的理论考察,认为全球反血汗工厂/公司守则运动作为关注劳工问题的新社会运动,将代表着全球化背景下劳工维权和劳工赋权的第三条道路(余晓敏,2006)。另外,受玛格丽特·E·凯克(Margaret E. Keck)和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合著的《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一书的影响,中国劳工研究学者黄岩在其著作《全球化与中国劳动政治的转型——来自华南地区的观察》中,基于跨国网络对台兴厂工人抗议的支持和跨国网络对劳工NGO的支持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同样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劳工团结与跨国劳工赋权”抱以厚望(黄岩,2011)。
以全球化为视角凸显跨国劳资冲突的理论言说不胜枚举,对于这种具有“新社会运动”性质的多元主体运动模式,基于时间和空间的发展不平衡性以及其多重的内在矛盾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劳工维权、赋权功能,这些问题自然引发了多层面的争议。劳工国际主义的逻辑不仅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仍然充满未知数。但是,以西尔弗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对于考察劳资冲突的新发展却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一方面,全球化视角下的世界体系论所唤起的劳资冲突和劳工研究复兴是值得期待的;另一方面,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转移而引致的跨国劳工互动,势必将一国或某个地区的工人运动带入到更大范围的受关注和影响视野。面对资本的全球流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弹性”需求,各国劳工阶级一方面既面临日益激烈的“内部竞争”,另一方面又渐渐形成了“反全球化”的新社会运动合力。作为特定劳动体制的主体,国家或地区政府如何去对资本全球化的特性和工人运动的新特点做出有效的回应,这对各国或地区的劳动体制转型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诚然,由经济全球化和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劳资冲突的时空转移,令“世界体系论”者对劳工运动与劳工研究的复兴保持乐观,对跨国劳工联动也寄予厚望。然而,不同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策略,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国家结构形态,其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劳资冲突的时空转移以及跨国劳工联动的反应模式将是不一样的。
三、国家制度与策略:劳资冲突的国家制约与影响
1985年,由彼得·埃文斯等主编的《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一书面世,该书收入了卡茨纳尔逊(Katznelson)从国家角度比较英、美工人阶级形成的著名论文并引起广泛关注,由此兴起了“以国家为中心”来分析工人运动和阶级形成 的理论热潮。
关于国家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奈特尔(Nettle)最早提出“国家性”(stateness)的概念,认为欧洲大陆国家激进的工人运动与“强国家”相关。“在强大国家里更容易出现反制度运动并非是一种巧合”,因为“国家提供了一种方便的去身份化(disidentification)的工具”(即去除工人原有基于地域、族群、宗教等形成的文化身份),反过来却促进了统一政治身份的形成和统一诉求对象的出现。与此相反,“国家性”较弱则是英美两国的工人运动未走上激进化道路的主要原因之一(Nettle,1968)。泽尔博格(Zolberg)也认为,在权力高度集中化的地方,地区性的矛盾和冲突很可能快速指向政治最高层;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体现为权力明确分散的地方,工人集体行动的目标通常较为狭隘的,一般只指向局部的、相关的部门(Zolberg,1986)。
“国家”作为一个“概念变量”还体现在国家“政体类型”(regime type)的差别上:即自由国家或专制国家。熊彼特指出,由于德国存在着压制性和排斥性(exclusive)的劳动体制,这种专制国家的暴力使用迫使德国工人运动采用激进化的方式,走上与国家对抗的道路;而英国的工人运动则由于自由国家的存在,从而走上较为温和的政治发展道路(Schumpeter,1950)。李普赛特也认为,造成工人阶级政治模式差别的决定性因素是:工人阶级面临的是专制的还是自由的国家,国家对工人阶级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压制越大,时间越长,工人就越可能对革命的学说做出正面的回应(Lipset,1983)。
卡茨纳尔逊进一步分析了同是“自由国家”的英国和美国的工人运动也存在差别,强调公民普选权实施时间及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差别,是英美两国工人阶级形成模式存在较大差异的关键原因。美国联邦制的国家体制以及选举权的较早实施,使得美国工人在阶级形成的初期,阶级政治让位于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而英国单一制的国家体制及选举权的普及较晚,使得英国工人将选举政治和阶级政治融为一体,并且指向国家的核心机关——立法议会。英美两国的国家组织形式、宪政及公共政策,对两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内涵以及对两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卡茨纳尔逊,2009)。
维多莉亚·哈特姆(Victoria Hattam)更详细地阐释了英美两国工人运动的分殊在于两国司法体系的差异上,他认为,英、美两国的司法律体系都曾采用刑事共谋条款(Criminal Conspiracy)对工人活动进行管制。经过英、美两国工人的斗争,两国均通过了反共谋起诉的立法。然而,由于英美两国的立法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存在着很大差别,导致了后来两国的工人运动出现分殊。英国由于议会立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法院认同并延续了议会的权威,对相关的立法作了有利于工人的司法解释,因此,英国工人诉诸议会立法来实现工人的权利和利益。而在美国,反共谋法中附加规定,工人行动不能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造成“威胁”。虽然有反共谋立法,但工人及工会仍经常遭到共谋起诉(Hattam,1992)。这主要与美国三权分立下,司法机构强调其独立性以及法院在处理劳资冲突中具有特殊的权威传统有关,也与当时联邦法院绝大多数来自共和党的富裕阶层的法官的保守立场关联。19世纪末,诸多有利于工人的立法也被联邦法院宣布违宪而废除。因此,美国工人和劳联不得已而放弃政治斗争和立法斗争,最终走上了“商业工会主义”和“自愿主义”的道路模式(Hattam,1993)。
为了阐述国家维度的影响,蒂利(Tilly)、麦克亚当(McAdam)和塔罗(Tarrow)等人还用“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来描述政治过程与集体行动之间的互动原理。“抗争政治”理论认为,一定的制度结构塑造了策略的行动;运动的组织者并不是在一个真空中选择其目标、策略和手段;政治环境设定了运动的因由、塑造了运动的议题主张和行动策略;政体中的特定的组织形式和行动者的结构位置,使得某些动员策略更为有效,或者更有吸引力(刘春荣,2012)。诸如政权的开放性程度和政党的意识形态、公共政策和精英联盟、制度中的积极分子、精英分化、决策过程、政治的空间管制能力、镇压意图和更为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能力等等,均构成了影响集体行动策略选择和发展走向的“政治机会结构”。黄冬娅从“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角度出发,将国家区分为三个概念层次:即“稳定的政治结构”(包括国家性质、国家创建和国家政治制度)、“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包括国家渗透能力、战略和策略)和“变化的政治背景”(包括封闭政体的开放、政治联盟的稳定性、政治支持存在与否、政治精英的分裂和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这三个层次上的各种要素都对社会抗争的兴起、形式和结果以及对抗争主体的身份认同和行动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黄冬娅,2012)。
“国家视角”这一理论传统已被学者带入到中国劳资冲突的分析中来。例如,陈峰从中国的国家政体类型出发,认为国家政体类型是解释为何中国在经历了3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后仍未出现经典意义上的工人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政体类型的特殊性,以及由此衍生的国家与工人关系的特殊结构和劳动控制机制,显然比其他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能更有效地遏制工人运动的发展(陈峰,2009)。
郑广怀在分析伤残农民工维权时,认为维权不是简单的赋予权力的过程,还受制度运作实践的影响,主要源于地方政府部门通过制度运作中的不良变通和连接制造制度性障碍,使得一种“有意”安排的制度不匹配得以出现,从而使伤残工人陷入维权的困局(郑广怀,2005)。郑还进一步通过对国家与劳工关系的考察,提出了“安抚型国家”的概念,通过三个方面来阐述国家对劳资冲突的治理策略:一是“模糊利益冲突”,即国家维持现状,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而非推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二是“言行分离”,即国家更多采用政策实践来解决问题,而非按照公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本身(政策文本)来解决问题;三是“点面结合”,即国家在整体上对劳工进行“精神安抚”(意识形态宣传),在个别问题上进行“物质安抚”(如对坚持维权的农民工给予补偿)(郑广怀,2010)。
程秀英通过考察两组国有正式工人和长期临时工人分别如何通过街头抗议、集体上访和法律仲裁等不同斗争路线之间的穿梭,实现与国家代理人之间的互动。她发现两类工人在斗争过程中获得了不同的象征性满足而非物质上的让步,他们的满足方式的差异是国家代理人根据两类工人不同的历史轨迹和社会身份所做出的有差别的策略性回应与引导的结果。分化的工人同地方国家代理人之间的互动体现了一种“消散式遏制”,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未能实现抗争可能带来的阶级认同,却丧失了最初的激进动力与挑战性,逐步屈服于国家的和平驯化过程(程秀英,2012)。
在“策略——关系”的“国家”概念视野中,国家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面目”,这对于观察分析“国家角色”与劳资冲突之间的多重互动和影响极具理论启示。
四、“道义经济学”:劳资冲突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变迁分析视角
一般认为,“道义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是美国著名学者斯科特的伟大发明,他对东南亚农民在市场资本主义冲击下的反叛原因给出了别具一格的解释:对农民的日益严重的剥削很可能是反叛的必要原因,但远不是充分原因……事实上,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由剥削引致反叛的可能性最小。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与精英以互惠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才是造成农民抗议的主要原因。农民拿起武器的目的,更经常的不是为了打倒精英,而是强迫他们履行其道德义务(斯科特,2001)。
其实早在1971年,汤普森就发表了《18世纪民众的道义经济学》一文,认为民众在粮食骚动中的抗议基于一定的传统权利与习惯,而这些传统的权利与习惯主要源于都铎时期的家长制市场规则:粮食应运往市场交易;让穷人在商人批量购买粮食前优先廉价购买;严惩倒买倒卖、囤积居奇行为等。可以说,这一切构成了贫民的道义经济学。对这些传统权利与习惯的伤害,如同实际的剥夺一样,是粮食骚动的直接动因(汤普森,2002)。
“道义经济学”的分析被广泛地引入到对转型中国的劳动关系变迁及劳资冲突的解释中来。以20世纪90年代所有制改革为背景,围绕“国企工人和农民工”这两条主线,“道义经济学”的解释占据偌大的一席之地。
陈峰认为,中国下岗工人是否会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活动,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生存危机和管理层腐败。虽然生存危机和管理者腐败都是引起工人不满的原因,但二者在促使工人采取抗议行动时所发挥的作用完全不同。生存危机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只有在生存危机存在的情况下,管理者腐败才能诱发工人采取抗议行动(陈峰,2005)。刘爱玉在研究国企改革和工人行动回应时指出,国企改革造成了工人“绝对收入减少、主观收入减少、对目前地位境遇满意指数降低”的“相对剥夺感”形成,被推向市场后的国企工人由于对传统单位组织的“结构性依赖”程度降低,因此,在符合“情景理性”(即行动信心、成本与行动成败考量)的情况下,基于“道义经济学”意义的工人集体抗议行动就会被付诸实践,并且主要发生在文化程度和年龄都偏低的工人群体当中(刘爱玉,2006)。黄岩在分析国企改制过程中工人集体行动时,也认为急剧恶化的生存现实、相对剥夺感的不断强化以及改制中的种种不公正,导致工人的抗争运动越来越激烈,因此需要去探索劳动关系新模式,在政府、资本和劳工三方之间达成新的共识(黄岩,2005)。
游正林认为,国有企业变革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触动职工群众的既得利益的过程。因此,他引入“组织公正”(organizational justice)的概念来分析国企改革过程中职工“不公平感”的诞生和发展。并从执政党意识形态、国有企业的组织特性、企业领导的上任承诺以及政府对改革前景的乐观预测等方面对职工形成的“心理契约”(游正林,2007)与现实情况的落差进行对比,从“结果不公正感、程序不公正感和人际互动不公正感”三个方面出发,认为“组织(企业)层次上的劳资冲突源于应该由雇主(资方或其代理者)负责的雇员的不公正感,把雇员对这种不公正感的行为反应视为劳资冲突的表现形式。”因此,国企工人的集体抗议,实质上是一种具有“道义经济学”意义的“不平则鸣”的行动过程(游正林,2005)。
从工人主体性认知的角度,国企工人的抗议、抗争策略同样体现了一种“道义经济学”意味的“互惠伦理”依赖特征。唐军在分析国企工人的集体行动时候,指出工人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某些行动无疑与现行法律相抵触,但为了赋予自己的激烈行动以合法性(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工人利用了自己在生活世界中磨练出来的智慧,充分借助了职工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和体现正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公有制观念(唐军,2006)。佟新在解释国企工人集体行动的“认知”和归因模式时,认为“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是国企工人集体行动的“话语”选择,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市场经济取向的,但在其运作过程中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依然持续存在,并有效地发挥了其文化动员的作用。这种文化传统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个人权利观念和国家观念,并成为工人解释其生活境况的文化资源。当工人们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活境况的解释与持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相连接时,其集体行动便在充斥着旧意义的话语中创造了新的意义和内涵(佟新,2006)。
在农民工维权抗争的这条线索上,“道义经济学”的分析同样占有相当大的理论分量。例如,李晓非从“道义经济学”的立论出发,认为“生存伦理”和“互惠伦理”构成了新时期农民工集体行动的伦理基础(李晓非、王晓天,2013)。蔡禾等人在分析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时,指出农民工因“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会采取沉默、投诉和付诸集体抗议行动(蔡禾等,2009)。
“道义经济学”体现的是工人、农民或弱势群体的一种无组织、非政治的反抗方式,它是一种基于“生存伦理”的日常反抗。在走向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单位制”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解体,造成了面向传统国企工人和农民的原有“互惠伦理”规则被打破,传统国企下岗工人和流动农民工致力于重新在国家和市场的转型中寻找能够构成“互惠伦理”关系的利益空间,也纷纷采取了各种体现传统“互惠伦理”规则回归的行动策略。在这个过程中,“以死抗争”、“以血还血”(刘建洲,2011)是一种对“互惠伦理”规则和空间完全丧失的绝望表现;而“用脚投票”逃离工厂,表明农民工正本能地通过制造“民工荒”来揭开“权利荒”的现实面目,进而控诉“制度荒”的政治缺失(刘林平等,2012)。
随着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诉求越来越多地从“底线型利益”向“增长型利益”(蔡禾,2010)的转变,消解了“道义经济学”意义上的“生存伦理”基础之后,传统的组织资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否还能构成工人集体行动可依赖的、有效的“弱者武器”?正如汤普森在阐释18世纪英国粮食骚动现象时所说,在每次这种形式的大众直接行动的背后,我们都发现某种具有合法性的权利概念(汤普森,2002)。那么,这些体现“合法性的权利概念”如何在市场和国家中得以构建?新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体制如何向工人提供新的“互惠伦理”体验、并且构成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秩序?这成了后改革时代中国劳动关系转型的一个迷思。
五、总结与讨论
四个论域的理论探讨,揭示了劳资冲突问题不止关乎一厂、一行或是一国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秩序问题,还可能构成全球政治进程的重要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主导下,市场化、工业化伴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中国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全面转型时期。尤其是劳动关系的巨大变迁,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新秩序。因此,中国转型时期的劳动关系和劳资冲突问题研究,自然引致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如何认识中国全面转型中的劳动关系矛盾或劳资冲突问题,关系到发展主义国家战略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诚然,以上四个论域的研讨都分别承载着中外学者在不同学科领域的洞察和提炼,为认识中国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的变迁提供了宝贵的现实素材和理论视角。然而,中国的转型是一个涉及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全面转型过程,国家建构进程、市场发育发展、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以及文化心理变迁,各个层面、各种因素的关系变革都纠缠在一起,使得中国的转型过程呈现出多维、动态变迁的特征,以至于任何一种关于中国劳动关系和劳资冲突的简单认识与论断,都有可能只触及中国转型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某一方面。基于不同的学科或不同的主体立场展开分析,自然会对中国劳动关系的变迁和劳资冲突问题得出不同的论断。只要中国的转型尚未完成,中国的劳动关系变迁和劳资冲突治理模式就仍将没有定论。劳资冲突理论如何穿透不同的学科和论域,并在其他的领域获得新的启示与发展,从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发展作出恰当的理论回应和形成理论共识?这有待于人们去进一步探索和研判。
注 释
①本文中,作者认为,工人阶级形成和工人运动是劳资冲突发展的高级形式。因此,国家维度对工人阶级形成和工人运动模式的影响,也是对劳资冲突的影响。
1.爱德华·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共有的习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艾拉·卡茨纳尔逊(著),方力维等(译):《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国家——从美国视角看19世纪的英格兰》,载彼得·埃文斯等(编):《找回国家》,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49-378页。
3.贝弗里·J·西尔弗(著),张璐(译):《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4.陈峰:《国家、制度与工人阶级的形成》,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165-188页。
5.陈峰:《下岗工人的抗议与道义经济学》,来源:http://www.aisixiang. com/data/6675.html。
6.蔡禾等:《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39-161页。
7.蔡禾:《从“底线型”利益到“增长型”利益——农民工利益诉求的转变与劳资关系秩序》,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9期,第37-45页。
8.程秀英:《消散式遏制:中国劳工政治的比较个案研究》,载《社会》,2012年第5期,第194-216页。
9.郭于华等:《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中国劳资关系转型》,载《二十一世纪评论》,2011年总第124卷,第10-12页。
10.哈里·布雷弗曼(著),方生等(译):《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1.黄冬娅:《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217-238页。
12.黄岩:《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工人集体行动的解释框架——以西北某省X 市 H 纺织公司的一场抗争为例》,载《公共管理学报》,2005年第4期,第52-58页。
13.刘爱玉:《国企变革与下岗失业人员的行动回应》, 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68-74页。
14.刘春荣:《社会运动的政治逻辑:一个文献检讨》,载《集体行动的中国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页。
15.刘建洲:《农民工的抗争行动及其对阶级形成的意义——一个类型学的分析》,载《青年研究》,2011年第1期,第33-42页。
16.刘林平等:《制度短缺与劳工短缺——“民工荒”问题研究》,载刘林平(编):《权益、关系与制度——十年(2001——2011)劳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86页。
17.李晓非、王晓天:《新时期农民工集体行动的伦理基础》,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164-170页。
18.迈克尔·布若威(著),李荣荣(译):《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19.玛丽·E·加拉格尔(著),郁建兴、肖扬东(译):《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0.任焰、潘毅:《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和抗争的另类空间》,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第124-133页。
21.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的两条途径》,载沈原(编):《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55页。
22.沈原、周潇:《“关系霸权”:对建筑工劳动过程的一项研究》,载沈原(编):《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269页。
23.唐军:《生存资源剥夺与传统体制依赖:当代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河南省Z市Z厂兼并事件的个案研究》,载《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174-183页。
24.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59-75页。
25.汪建华:《互联网动员与代工厂工人集体抗争》,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第114-125页。
26.汪建华、孟泉:《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第165-177页。
27.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143-167页。
28.余晓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运动:现象、问题与理论》,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188-214页。
29.游正林:《心理契约与国有企业工人的不公正感——以西厂为例》,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77-82页。
30.游正林:《不平则鸣:关于劳资冲突分析的文献综述》,载《学海》,2005年第4期,第56-61页。
31.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显、刘建(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32.郑广怀:《伤残农民工:无法被赋权的群体》,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99-117。
33.郑广怀:《劳工权益与安抚型国家——以珠江三角洲农民工为例》,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第27-38页。
34.Aristide Zolberg,How many exceptionalism? In Ira Katznelson & Aristide Zolberg(eds.), Working class forma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446-448.
35.Ching Kwan Lee,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36.David Harvey.Spaces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New York:Routledge,2001:315、369.
37.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 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1990:121.
38.Joseph Schumpeter.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Harper& Row,1950:341-343
39.Michael Burawoy,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London:Verso,1985.
40.Nettle P,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20,1968.
41.Robert Thomas,Citizenship and gender in work organization:some considerations for theories of the labor proc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8 Supplement,Marxist inquiries:studies of labor,class,and states,1982:96-106
42.Seymour Martin Lipset. Radicalism or reformism: the sources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3.77(1):1-18
43.Victoria Hattam,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1820-1896.In Sven Steinmo et al.(eds.),Structuring politic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33-166.
44.Victoria Hattam,Labor visions and state power:the origins of business unio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 责编/ 孟泉 Tel: 010-88383907 E-mail: mengquan1982@gmail.com
New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Conflict Theories":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Four Domains of Discourse—— and Related the Convers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abor Conflict Study in the Four Domains of Discourse
Huang Ruibo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Research Institu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adjustment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specific content and form of opposi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the capital and labor, promo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conflict theories. Among them, " Theories of Labor Process " expounds the multigaming of labor conflict in the labor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control and resistance; " Theories of Globalization " expounds the shift of time and space and multinational linkage of labor confli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flows;“Theories of State” expounds the restric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stat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policies in labor conflict from the dimension of the state;"The Moral Economy" has made the analysis of labor conflict and labor resist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change of cultural psychology.
Labor Conflict; Labor Process; Globalization; State Strategy; Moral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