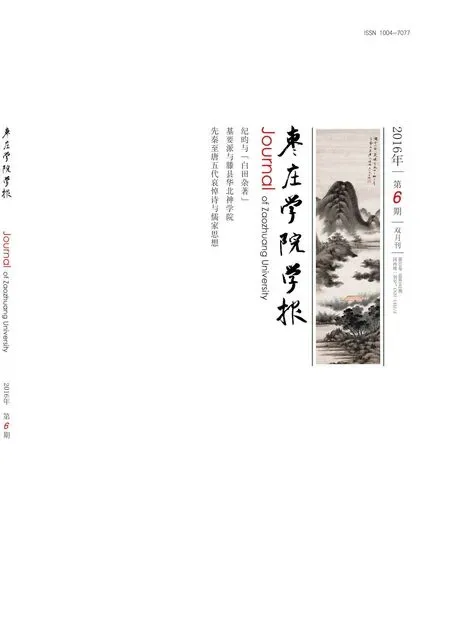关于“钓鱼执法”的法治分析
胡利明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1)
关于“钓鱼执法”的法治分析
胡利明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1)
从法治总体分析启程,经过法治主体、法治程序和法治利益运行,根据证据性和法律性有重点地剖析钓鱼执法的法治问题,运用合法性和道德性衡量其法治和道德价值。为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都带来法治伤害,需要道德和法治合力清除滋生它的土壤空气,熔断其利益体制机制,铲除其利益垃圾,才能培育依法行政的法治新生态、新业态和新常态,才能逐渐形成法治执法的新思维、新观念和新方法,才能打造道德执法的新环境、新平台和新工具,才能形成道德和法治衡量的新视野、新创想和新思考。
钓鱼执法;依法行政;行政执法;行政权力;法治;道德
钓鱼执法是近年来的普遍客观现象,众多性、反复性和持续性是现实表现,政府的业绩考核是行政压力,民众的诉求是民间压力,没有法律规则是制度原因,执法经济是经济驱动器,罚款型行政处罚是追求目标。
其实,钓鱼执法是政府执法的异化方式,表面上是“执法”,实质上是“违法操作”,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主动遵循法定规则、法定程序和法定理念执法,与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背道而驰,造成与善良道德之间的价值冲突。例如:行政理念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行政现实的一种思想认识与价值判断,是包括行政意识、行政信念、行政价值观、行政思想等在内的价值观念体系,是行政过程中所展现的一种深层次行政精神与价值取向[1](P16)。钓鱼执法的具体现象繁多,查处黑车、专车是“典型代表”,打击卖淫嫖娼也“不甘示弱”,其他钓鱼执法现象更是“浩浩荡荡”,诸如此类现象无法列举齐全,限于技术原因不作实质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查阅相关资料。为此,非常有必要既作宏观法治整体分析,又作微观法治具体剖析,还作比法治标准更高的人性道德价值分析。
一、钓鱼执法的法治总体分析
从宏观的依法治国到比较具体的行政授权,钓鱼执法会在每个阶段反向显现不同层次、不同视角和不同思维条件下的法治要素。作法治整体分析钓鱼执法有助于探析法治根源,有助于从法治视角分析,有助于剖析法治要素,有助于借力行政法学理论深入解析法治内涵。
1.依法治国的总体分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的重要抓手和法治思维的具体落实,这要求国家按照预设的法治规范推进治国战略、方针、措施,需要程序规则的密切配合。依法治国的伟大战略部署由来已久,钓鱼执法却在“光明正大”地完成“政治任务”,给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带来特多的消极影响,不仅不能提升依法治国的法治质量,反而成为依法治国的法治路障,进而破坏法治秩序造成法治伤痛。
2.行政法治的总体分析。依法治国是国家社会中最宏观的法治思维,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具体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重点推进依法行政步伐。例如,依法治国的重点是依法行政[2](P15)。钓鱼执法作为行政执法范畴,根本不是依法治国的微观措施,根本不能契合行政法治步伐,根本不是正态运行依法行政,根本不是根源于法治理念,根本不是运行法治思维,与现代法治的“技术要求”还有很大的法律距离。
3.行政权力的总体分析。行政权力有合法来源必须满足法定性要求,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必须符合权力法定原理,原因在于:并非行政机关的一切权力都是合法的,行政权只有经过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来设定才具有合法性,才成为一项合法的“行政权力”;无法定依据行使权力是超越职权[3](P192)。钓鱼执法既不是行政机构的法定权力,又不能表明是合法运行,原因在于没有经过立法机关的授权或直接规定,反而是任性超越法定权限的权力滥用。另外,根据立法授权法定理念[4](P54),钓鱼执法没有经过立法授权,在行政程序方面存在很大的法治问题,与现代法治理念格格不入,不能满足行政权力的法定要求。
4.行政职权的总体分析。依法行政需要行政权力,进而需要行政职权。行政职权是行政主体合法运行行政行为的法定根据,即行政主体拥有合法行政职权是保证合法的前提基础。通过钓鱼途径执法生存法治环境,属于变异行的政职权。根据无法不得行政的行政法原理,行政职权不容任性被非法律性变异,否则既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又不能取得预期的法律效果,还不能符合程序法治的“技术要求”,更不能契合法治行政的“思想路线”。
5.行政授权分析。行政授权是重要的法治和法律问题,行政机关滥授权或不授权行政是非常普遍的客观现象。钓鱼执法由执法人员“牵头”,通常给予经济报酬、奖励或提成,口头或事实上雇佣(滥授权)社会公众,在上述过程中行政机构既不可能出具授权性法律文书,又不可能严格按照正常执法程序执法,还不可能按照授权程序执法,上述行政授权方面的瑕疵不符合法治理念,不同道法治思维,不谋合法治方法,不同轨(向)法治方向,不满足法治行政的技术要求,总体上构成滥用行政权,直接破坏法治程序造成法治伤害,付出不必要的法治代价。
由此可见,钓鱼执法的总体分析是多层次、多角度和多方面的,各有不同的特色、不同的特征和不同的特性。总体上既不能契合依法治国步伐,又不能提升行政法治质量,还不能同步行政权力的法治运行,也不能拥有行政职权的法定要素,更不能满足行政授权的具体要求。尽管这些总体分析不很全面、不很具体和不很完美,但总体勾画了钓鱼执法的法治总体,为法治具体分析定好基调,铺设法治轨道和运行法治思维提供保障。
二、钓鱼执法的法治主体分析
钓鱼执法是行政机构安排的行政活动,由具有执法权的工作人员主导,其他辅助人员协助,甚至以商业交易方式聘请社会公众充当“鱼饵”,诱惑“鱼儿”上钩完成执法任务,行政机构和“鱼饵”都可以获得预期的经济利益,实质上是行政机构运用行政权力兑现经济利益,根本不符合法治规则,根本不符合程序理念,根本不能优化法治质量,根本不能纯洁法治主体。
1.主体定位分析。钓鱼执法作为异化的执法方式,名义主体是政府,法律主体是行政机构,执行主体是执法人员和被聘请的社会人员,被执法的对象是从事特定行业的不特定经营者,甚至还有被引诱误导的无辜者。他们在执法过程中完成权力利益交易,导致执法主体以执法利益为核心导向,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最终失去行政主体的法治性身份发生“逆袭”,即从法治的模仿遵循者沦落为加害者,成为法治过程中的有形障碍。
2.职权法定分析。职权法定是法律上的外观表现,行政机构成为法治主体必须拥有法定职权。其实,职权法定即行政职权法定,是“公共权力法定”的公法基本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化,基本涵义是:任何行政职权的来源与作用都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定依据,否则越权无效,受到法律追究,要承担法律责任,即:行政职权来源于法、行政职权受制于法和越权无效[5](P166~169)。可知,行政职权核心强调职权的宏观法定性,微观强调明确具体的法定根据,行政职权受制于法和越法(权)无效。据此推论,钓鱼执法属于行政执法范畴,难以表明是行政职权范围,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机构可以或应当使用“钓鱼”方式执法,而是行政机构“创造发明”的新手段,将“鱼饵”作为执法工具。这些既没有法定根据,又没有程序指引,更没有法治理念支持,而在“无法”甚至“越法”情形之下任性运行,构成职权非法定即归属于违法。
3.行政强制分析。行政强制既是行政执法的重要方式,又是行政执法的“保障方式”,还是行政机构完成执法的“重要法宝”。根据行政法理,行政强制是法定的行政强制主体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预防和制止违法行为和危害事件发生而实施的强制限制相对人权利的行为[6](P138)。另外,行政强制意指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目的,采取强制措施对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处置的具体行政行为[7](P249)。可知,行政强制的特征或构件主要为:行政主体的法定性、行政目的的公共性、行政对象的特定性、行政效用的有用性(制止或预防)、行政措施的强制性和行政法理的行为性。据此根据上述理论分析钓鱼执法,行政主体的法定性被“掺杂使假”(行政机构没有法律根据聘请“鱼饵”参与执法);行政目的非基于公共性而是追求经济性;行政对象是有选择性的,属于选择性执法;行政效用并不是制止或预防行政违法,而是追求经济利益;行政强制性没有充足的法律、法理根据;行政法理上是不属于行政行为的事实行为。
4.行政职务分析。行政机构成为行政主体,核心要素是行政主体必须具有行政职务保证合法行政行为,即无行政职务无行政权原理。其实,行政主体的职务关系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关系[8](P180)。据此分析钓鱼执法,既不是严格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又不是履行行政职责,而是从事权力利益交换的事实行为,与行政职务有理论差距。
5.行政主体的委托性分析。钓鱼执法是诱惑型的执法方式,其中有相当多的行政强制措施,却不符合《行政强制法》规定,原因在于:《行政强制法》确立了行政强制措施执法人员的资格制度,禁止行政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委托,这种委托制度上的严格性取决于行政强制措施的强制性和即时性,它对公民权益影响较大[9](P271)。事实上,由行政机构委托非执法资格人员共同参与钓鱼执法,导致参与者不能全部拥有执法资格,实质上是行政主体委托行政强制构成违法。
由此可见,钓鱼执法在行政主体层面有诸多违法或不合理之处,主体定位存在重大疑问,职权法定难有根据,行政强制有违法嫌疑,行政职务难以充分根据,行政主体的委托性更是问题重重。钓鱼执法的行政主体存在法治问题,继而分析其程序仍然有花样百出的法治问题。
三、钓鱼执法的法治程序分析
钓鱼执法的最大缺憾是没有可遵循的法治程序,其次是程序没有应有的法律地位,再次是程序被极端异化,程序成为缺位严重的法治障碍。其实,程序是现代法治的独立主体内容,既是独立的法律程序,又是独立的法治价值,还是独立的程序实体,共同为总体公正提供程序支持。
1.程序的本位性分析。程序既是现代法治的发展方向,又是现代程序法治价值理念,更是实体生存之来源和前提。例如:程序是实体之母,或者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10](P7)。其实,钓鱼执法在于程序出了法治问题,根本没有主动遵循法治程序,根本没有树立程序的法治观念,根本没有程序是实体之基础的理念,根本没有程序的独立价值,根本没有程序提升实体的价值精神,共同造成程序本位要素缺位,难以充分满足现代法治的程序要求。
2.诱惑侦查程序分析。钓鱼执法不仅没有主动遵循现代法治程序,而且公然“引进”了诱惑侦查程序,但在法理上存在诸多问题。钓鱼执法是利用“执法圈套”诱惑侦查,引诱相对人按照预设的虚假“诱饵”前行,最终落入“被执法”的圈套,不能在程序法治上产生预期法律效果。执法圈套是诱惑侦查的外观表现,执法效果归于“零”,属于行政程序违法。
3.程序正义分析。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的程序要求和保证社会秩序公正的程序武器。法治不仅要求实质正义,更要求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的法治保障,社会秩序和谐与公正将是“天方夜谭”。现代法律程序所实现的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要求至少应当包括: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和程序公开性。它们反映在现代行政程序中,可分别概括避免偏私、行政参与和行政公开这三项原则[5](P247~248)。据此分析,钓鱼执法无法保持执法程序的中立地位,无法保证程序参与执法,无法保证执法程序公开,无法“预期到达”所对应的避免偏私、行政参与和程序公开的程序正义结果,共同表明程序正义没有“生存空间”。
4.程序性权利分析。程序具有独立的法治价值,程序性权利便应运而生。其实,程序性权利不仅为实体性权利提供实现方式、途径等,而且在权利遭受不法侵害时提供积极有效的救济手段,以实践社会正义[11](P177)。据此,钓鱼执法中难有程序性权利保障,更不用说实现实质性权利,在相对人受到不公正、不合法的侵害时,根本没有积极有效的救济手段,根本没有必要的程序保障,根本没有法治理念的配合,最终无法实现程序正义。
5.程序公正性分析。程序既有正义要求,还是程序性权利,更要完成程序公正的价值任务。所谓程序公正是一种行为过程的公正,是具有一定时空顺序的行为过程的公正。反之,这种行为过程所导致的行为结果之公正为结果公正或实体公正[12](P45)。可见,程序公正体现程序过程性公正,体现特定的时空次序公正,为保证实体公正提供保障。钓鱼执法在程序公正方面做得非常不到位,直接破坏程序公正,违背了基本程序公正原理,突出表现为: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自己做自己的法官,根本不可能涉及程序所追求的公正价值,根本不可能保证公正的实体结果,根本不可能完成程序公正的价值任务。
6.行政禁止补办程序。程序既是公正的保障机制,又是公正的体制程序,更是公正的机制体制学理。行政程序具有即时性、当时性和一次性特征,不得事后补办,否则将构成行政程序违法,此即“行政禁止补办程序”。根据无法即无行政原理类推出无程序即无行政规则,即禁止行政补办程序,即使补办也不能发生预期的法律效力,即制度规则上不认可补办程序,符合现代法治程序的价值要求。
由此可见,钓鱼执法需要程序衡量,程序本位性是总体分析,诱惑侦查是手段程序,程序正义是目标程序,程序性权利是独立目标,程序公正性是追求目标,行政禁止补办程序是保证程序公正的救济型机制。上述程序性分析尽管不可能过于全面具体,但是具有代表性,共同剖析出钓鱼执法的程序非公正因子。
四、钓鱼执法的法治利益分析
行政执法本来是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应当符合现代法治利益标准。钓鱼执法基于执法利益启动之,原始冲动是通过执法过程获取执法性经济利益,必然紧密联系各种利益链条,必然会冲击执法的公正性,必然会影响执法的法治质量。
1.委托利益分析。钓鱼执法成为中国特色的执法方式,利益委托是核心关键,进而根据利益要素产生权力污染。例如,在权力委托关系中,由于各方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角色利益,使最初的意志发生变异,即为“传声污染”:在权力委托关系中,由于参与各方的角色利益渗透而带来的政府权力意志的异化现象[13](P53)。可知,在钓鱼执法过程中,行政机构主动将权力委托给没有执法资格的他方,以获取行政处罚的“证据”,他方当然不可能提供无偿的“义务劳动”,而是需要利益分成。行政机构通过权力外包获取经济利益,他方通过支出“劳动”获取经济分成,双方“利益共赢”完成权钱交易,实质上牺牲了法治利益,破坏了法治秩序,打乱了法治生态。
2.执法经济利益分析。钓鱼执法基于经济利益启动,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完成利益分成是目的,以经济利益作为执法根据的考虑因素,不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为了追求行政罚款方面的经济利益:既有行政机构主导的利益大头,又有“鱼饵”的利益分成,更重要的是将行政权力利益化、市场化和对价化,重创法治的理想秩序状态。其实,“钩头”和“钩子”毕竟不是政府执法人员,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他们有时会瞄准私家车主,通过与执法人员配合并引诱私家车主交易的方式,将私家车当作黑车查处[14](P206)。可知,钓鱼执法完全属于执法经济范畴,“钩头”和“钩子”受聘于行政机构,在经济利益推动下选择性“执法”,本质上不属于法治执法,而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执法手段;执法价值目标不是法治,更不是人民利益,而是人民币利益。
3.美德善行利益分析。美德既是社会的善良追求,又是人性的善良本性,还是法治秩序的原始基因。其实,美德的理论不再像(亚里士多德)“居中”或者像(休谟)“欢快”,而是作为对距离的回应,使行将评判群体效益性的观者变得公正并远而视之[15](P205)。据知,钓鱼执法与美德的标准相差甚远,与美德善行渐行渐远,即美德善行无法运行于钓鱼执法,原因是基于道德非善的行为,与法治善良价值背道而驰。
由此可见,从上述方面反向分析钓鱼执法,诸多方面无法满足法治追求价值,在委托利益过程中权力受到污染,行政机构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与法治标准相距较远,执法经济利益是“罪魁祸首”,美德善行是道德判断标准。
五、钓鱼执法的证据性分析
钓鱼执法中的证据存在诸多的法治难题,法律效力有法治障碍的根本原因在于所取证据的法律效力,证据是行政处罚的事实核心,如果没有被取证的客观事实证据,再完美(善)的法律根据都没有可适用的情形,否则无法完成行政处罚,无法依托执法获取经济利益。
1.利益证据。钓鱼执法基于利益而生,利益证据是突出特征,它难以保证事实准确、证据公正和程序正义,以利益为首要判断标准,公平、公正居其次。利益证据是钓鱼执法的必然结果,钓鱼执法反过来制造更多的利益证据,难以契合现代法治理念,当然不能作为(钓鱼执法)“定罪量刑”的法定证据。
2.诱惑证据。诱惑证据属于制度性“恶”,法治要求摒弃制度性“恶”,即来源于“恶”的证据既不能作为“定罪”的事实根据,又不能作为“量刑”的法律根据,更不能作为法治价值判断标准。其实,诱导型侦查的底线要求是:政府不能为了侦查、追诉的需要而诱导本来无意实施犯罪人的去犯罪[16](P39)。但是,钓鱼执法基于经济利益执法处罚,自制“犯罪工具”并创造“犯罪条件”引诱他人实施“犯罪”,构成“共同犯罪”,跨越了诱导型侦查的法律底线。据此,诱惑途径获取的证据是制度“恶”,既突破了取证的法律底线,又重创了取证的道德准则,更伤害了理性取证的人性情感,理所当然不能成为定案的法定证据,根本不能发生法治效力。
3.毒树之果证据。行政程序的毒树规则比刑事程序宽松,毒树之果是证据效力的排除规则,运用之保证不产生证据效力。原因在于:为保障人民权利,贯彻法治国原则,行政程序应有“毒树果实”之适用,只是在“毒果”证据能力之认定上[17](P99)。可知,钓鱼执法基于毒树之果原理获取的证据,所取之证理应被排除在合法范围之外,不能发生预期的法治效力,以保证法治证据的法律原貌。
4.暴力证据。暴力是法治的天敌,尽管法治社会不能根除暴力,但能在较大范围内减少暴力,这说明法治社会仍然有暴力痕迹,有暴力必然会暴力取证。例如,钓鱼执法是暴力取证的典型代表,属于利益诱惑型的暴力取证。其实,强制力量是通过物理的手段强行对人的身体及生理需求的改变或者惩罚的抑制,而不是通过说服、劝导所形成的内在观念来获得服从的。强制力的基本形式是暴力,暴力是强制力的基础,也是强制产生效力的力量[18](P19)。可知,钓鱼执法通过利益引诱完成暴力取证,其强制力来源于物理外力,既不是法治的说服教育,又不是自愿行为,更不是法治精神上的合法行动。据此,钓鱼执法中运行暴力取证不符合法治理念规则,不能衍生法治因子,不能取得法治效力,不能产生证据效力。
由此可见,有选择性地从利益证据、诱惑证据、毒树之果证据和暴力证据角度相对全面地剖析钓鱼执法中的取证规则,难以契合现代法治步伐,难以符合现代法治理念,难以做到公正、公平、和平和公道取证,难以排除恶性取证,不能获得法治支持的证据效力,不能被作为定案的证据。
六、钓鱼执法的法律性分析
钓鱼执法是被异化的行政行为,既是行政执法范畴,又是事实性的执法行动,更是法律性和事实性交融的产物,所呈现出来的法律性有所变异,与现代法治理念有差异、有距离和有时差。
1.行政执法的法治分析。钓鱼执法总体属于行政执法范畴,但“钓鱼”方式改变了执法的本质属性。其实,行政执法不是简单地落实和执行法律的过程,而是可以看作一个摆正权力与法律、权力与权利关系以及同等看待实体与程序、合法与合理的过程。行政执法的实质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法律根据,受法律规范制约,所强调的是行政机关对法律的敬畏和服从[19](P321)。可知,钓鱼执法既不是真正落实执行法律,又不是主动摆正法律与权力之间关系,还不是正确处理合法、合理和合情的关系,更不能保持对法治的敬畏和服从,而是行政任性行为,扩张了行政权力的适用范围、适用强度和适用方向。
2.法律强制性分析。法律原则上具有强制性,行政行为具有法治强制性,依靠法律强制性运行。其实,行政行为是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状态产生影响的行为,要使这种行为产生的效果处于可靠的、确定的状态,具有权威性,保证秩序的形成和存续,需要法律上的力量作为保障[20](P94)。可知,钓鱼执法依托行政机构,靠权力强制性执法,这不属于法治意义上的法律强制性,与法治强制力有差距。
3.行政欺骗性分析。行政的追求目标是诚信,政府诚信是行政运行的根基。法治政府应该主动遵循诚信原则,法治行政必须按照诚信规则运行,运用诚信思维管理行政机构,行政机构的所有行为不得突破诚信的法治和道德底线。因而,政府行政执法奉行的基本原则是以合法、公开、公正的形式进行,而钓鱼执法完全背离了行政法治原则,以欺骗的方式实施[21](P74)。钓鱼执法公然违背政府诚信公道原则,公然突破诚信的法治底线,公然挑战人性道德底线,公然采取欺骗性方式执法,公然践踏诚信的自然法思维。
由此可见,钓鱼执法既不能完全符合法治意义上的行政执法标准,又难以完全满足法律强制性要求,还是行政欺骗性的事实行为,总体上与法治标准有较大的法律差距,与行政执法的法治要求仍然有距离,其强制力并不是完全根源于法律,而是基于事实行为形成的强制力,背离了行政法治轨道,使用欺骗方式完成“执法任务”,目的不在于法治执法,而是经济执法获取经济利益。
七、钓鱼执法的合法性衡量
钓鱼执法是中国的“客观存在”,经过上述多方面的法治分析发现了不少问题,还需要作合法性衡量评价,尤其是根据不同的标准、从不同视角运行不同思维来共同衡量之,衡量出其是否合法的整体和分项结论,并为后述的道德性衡量奠定法治基础。但是,合法性衡量钓鱼执法前,需要提前预习价值衡量的规则标准,尤其是面对不同层面的衡量尺度,如何去具体衡量有特定的规则。例如,判断行政行为效力逻辑规则:一般情况下用合法性判断;不能合法性判断的情况下用目的性和伦理性判断;在合法性逻辑判断结果或法律规定明显背离行政目的、伦理规则的情况下,用目的性和伦理性矫正判断;当行政目的与伦理规则冲突时,优先适用伦理规则[22](P95)。可知,判断钓鱼执法作为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需要遵循合法性——目的性和伦理性-伦理规则判断的方法路径。据此,笔者率先提出坚持法治(合法性)判断优先,道德性判断紧随其后的创新法治路径。
1.有用性衡量合法。中国有久远的非法治传统,即使强制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非法治习惯做法仍然非常有“市场”,尤其是习惯性地将“有用性”作为衡量合法的重要判断标准。在此借鉴:保安执法的违法性显而易见,从头到尾都找不到合法因子,表面目的上的“有用性”根本不可能成为违法性的“不可抗力”[23](P42)。事实上,法治是良性规则,以是否符合公正、公平的法治价值,是否符合法治诚信原则,是否优化社会秩序,是否符合程序正义,是否满足(不突破)社会道德正义底线为根本判断标准来判断合法与否,与事件的事实“有用性”没有任何关系,甚至相当多具有临时“有用性”的行政行为是公然破坏法治秩序的违法行为。据此可知,保安执法之所以大行其道,最有力的支持根据是“有用性”,而行政机构信赖并大力推行钓鱼执法,除经济利益冲动之外,最能说明理由的是它具有事实上的“有用性”。
2.合法性衡量合法。合法是非常抽象的法治概念,区分合法与否的具体标准诸多,但宏观性的区分标准还相对一致。合法和违法的界定标准主要在于:法律法规要求、法定程序、法定目的、法定权限和法定职责等方面,也就是说,如果完全符合上述标准即合法,否则将是违法[24](P28)。据知钓鱼执法,既在法律法规要求上没有依据,又没有法定程序可言,还没有明确的法定目的,但只有经济目的,更没有法治性的法定权限和对应的法定职责,“行驶”于法治轨道无法满足合法性标准。
3.行政行为的法律构成衡量合法。与钓鱼执法最相近的行政法理论是行政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有合法与违法行政行为之分。合法行政行为指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行政行为,如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遵守权限,符合法定目的等等。违法行政行为指违法法律法规要求的行政行为,如主要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的,滥用职权的,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等等[25](P209)。可知,法律法规的宏观标准在于行政行为合法与否,微观标准在于:证据充分与否、适用法律正确与否、符合法定程序与否、主动遵守法定权限与否、符合法定目的与否,上述客观和微观具体标准都难以表明钓鱼执法合法。
4.合法价值衡量合法。合法性衡量是实践角度的评价判断,合法价值衡量是价值评价判断,两者是法律实践与理论价值的关系。其实,合法是法律事项的重要价值判断标准,肯定性法律评价必须要满足合法价值。合法价值主要是作为衡量性的判断价值,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为基本准则来判断,符合法律规定即为合法,否则即为不合法[26](P306)。据此分析,钓鱼执法在法律价值评价上难以满足合法判断标准,既不能满足法律实践评价,更不能满足法律价值评价,属于没有合法价值的不合法情形。
5.时空公正衡量合法。时空公正是全新原创的法学概念,主要包括准时公正和完整公正范畴,前者是从时间上准时来衡量公正,后者是从完整性方面衡量公正。例如:准时公正衡量合法,不迟到准时到达的公正为“准时公正”[27](P72)。另外,善始善终,完整公正:完整公正是做人为事必须有头有尾、善始善终,才能完成全部公正,不完整的公正其实也是一种不公正[28](P36)。据此分析,钓鱼执法难以完全满足时空公正价值,构成合法有难度,原因在于执法目的是追求执法经济利益,排除对相对人的公正价值,没有满足准时到达的公正,难以企及完整状态下的公正。
6.强制性衡量合法。强制性是法律的重要标志,但不是唯一标志;既是行政措施的保障手段,又是行政行为的核心外观特征。其实,强制性行政只是一种必要的行政手段,而非行政权的内核。为了实现更多的公民自由,行政法必然要通过控制强制性行政的非理性扩张来减少强制与自由的对立[29](P66)。据此分析,行政强制是行政处罚的保障手段,既不是限制适用强制手段,又不是减少强制增加自由,是通过非理性的强制扩张达到“预期目标”。进而分析,钓鱼执法是有强制性的引诱型执法,相对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接受处罚,不符合合法的理想标准,难以达到法治型合法状态。
7.自由权衡量合法。合法是多方面的综合体,自由权可以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钓鱼执法实质上是行使行政管理权,在管理过程中产生行政管理行为,与相对人的自由权有价值冲突。因此,一切不符合自由权实现的管理都不合法,一切不能保障自由权的存在和运行的管理不符合法价值标准,一切以牺牲法自由价值为代价的管理都不符合法治文明,一切为了急功近利以自由为代价换取“立竿见影”效果都不符合法治理念,一切以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忽视合法性的举措都不合法[30](P102)。据此推之,钓鱼执法既直接破坏影响实现自由权,又不能保障合法运行自由权,还不能满足现代法治文明标准,却以牺牲自由权益为代价追求即时效果(执法经济利益),以执行领导意志查处违法行为的“有用性”掩盖行政违法性,与合法还有相当远的法律距离,客观上构成违法。
由此可见,钓鱼执法在法治道路上难以满足合法标准,尽管合法性衡量标准多种多样,但技术上只能选取最重要的“代表”论述之。例如:有用性不能代替合法性,合法性实践不能表明理论上合法,行政行为的法律构成不能表明技术上合法,合法价值不能衡量法律价值合法,时空公正不能提供合法的公正价值,强制性不能表明合法,自由权保障更不能提供合法的法律材料。
八、钓鱼执法的道德性衡量
道德既是法治的原始基础,又是构成合法性的道德基础,还是道德价值精髓。合法性衡量钓鱼执法之后,继续作道德性衡量有助于完善法治整体,有助于夯实合法性根基,有助于提高更严格、更高的衡量标准,有助于用道德价值判断其合法性。钓鱼执法不仅仅在于实践层面的合法与否,而且在于道德层面的合法与否,道德上合法才是真正合法,道德上不合法而事实上合法并不是货真价实的合法。据此,道德性衡量钓鱼执法既有法治实践需要,又有道德规则指引,更有道德价值追求,各方面共同构筑出全方位的合法体系来共同衡量合法性。
1.道德行为衡量。道德既是行为规范,又是行为规则,指引向善良道德方向前行。道德规范主体行为是重要的道德价值,使之有立场、有原则和有方向。其实,道德行为是在一定的道德认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有利于社会或他人的行为,道德行为选择也就是关于道德价值的选择,逻辑指向是求善[31](P213)。据此推论,钓鱼执法丧失道德价值,行政机构主动失守诚信原则,故意引诱相对人违法,通过突破道德底线方式获得处罚“证据”,这些共同表明钓鱼执法表现为道德失范,不仅没有主动遵循道德行为准则,而且主动破坏道德价值规范,构成道德层面的不合法。
2.道德规则衡量。道德行为是具体行动,向道德方向前行还需要类似于法律规范的道德规则指引和规范,但道德要求更为严格。其实,道德规则作为一种关于道德生活的有条理的表述和有约束力的规定,是人们在处理道德问题的长期过程中所总结出来的理智结晶。人们通过对这些情境的多次观察与反复提炼,能够比较稳定地把握其中的关键价值和相关诉求,这些经验做法得到生活群体的认可,被表述为或规定为各种各样的行为规则[32](P245)。据此分析,钓鱼执法没有主动按照道德规则行事,尽管道德规则没有法律强制力,主要靠行为者的道德自律。毕竟道德规则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反复、经常归纳出来的经验法则,具有最高道德效力,但是钓鱼执法的行为者却“视而不见”,难以符合道德规则下的合法。
3.善良价值衡量。道德价值的原则是善良,核心也是善良,善良意志是道德的外观表现,即道德正向追求善良,通常不特定说明解释即表明道德善良,用来衡量特定事项。其实,道德善良既是无条件的义务,又是无条件的善良,更是道德价值合法与否的判断标准。例如,善良意志是单纯出于义务而行动的意志[33]。善良意志就是无条件的善,就是价值判断的最终标准[34](P338)。据此推论,钓鱼执法为了经济目的追求经济效用,不择手段完成“执法任务”,不可能从善良道德出发,不可能具备道德善良价值。从道德价值善良价值方面衡量,钓鱼执法既不可能契合之,又不能追求之,更不能通过执法行为完成“道德任务”,更不可能构成法治合法。
4.道德诚信衡量。道德诚信既是社会运行的基石,又是法治社会的价值基础,更是法治政府的道德准则精髓,这要求政府必须主动讲求诚信。毕竟政府没有诚信,执法者犯法,不仅毒化人们守法的环境,而且它本身以极不道德的手段引导人们的腐化,在这种的社会中,人们即无法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21](P75)。可知,钓鱼执法是行政机构丧失政府诚信的极端表现,既树立了故意违法的“榜样”,又毒化了社会守法的良好风尚,还引导全社会以非诚信方法“为人处事”,进而败坏社会道德风尚,政府诚信形象被污损得“一塌糊涂”。据之,用道德诚信衡量钓鱼执法,无法寻找出任何诚信的影子,无法探寻出法治诚信的基因,无法推论出道德诚信的结论,以道德为基础的诚信价值与之没有任何关系。
5.人性道德衡量。德性是人性道德的集合体,追求人性道德需要保持良好的德性状态,善良优良的道德性是道德的精华浓缩。其实,德性是一种实践理性的自觉,并且拥有一种良知的力量去控制一个人对普遍法则抵抗的倾向,这种力量虽然不能直接地被觉察到,但仍然可以从道德命令中推断出来[35](P82)。据此分析,用人性道德衡量钓鱼执法,既没有体现理性自觉,又没有体现道德良知,更没有善良的道德支持,人性道德与之相差甚远,难以彰显德性合法性。
6.道德命令衡量。道德靠自觉运行,对于遵守道德的主体来说,道德是绝对命令,不需要外在强制力可以自觉完成“道德任务”,甚至比法治强制力更有实效。例如,绝对命令是一项规则,不仅指出而且使得主观上认为是偶然性行为成为必须要做的,因而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主体必须根据此种规则去行动[35](P140)。其实,道德属于自觉类型的道德性规则,核心是绝对命令,既可以主动完成道德义务,又可以保证道德实效,还可以引导道德主体主动履行道德良知,发挥道德善行的价值效用。据此分析,钓鱼执法是行政机构的自我设计的非道德圈套,其实称为恶性道德诱饵不为过,既不能体现道德良知,又不能对道德主体产生积极引导作用,还不能形成社会的善行品德,更不能打造良性的道德规则,对国家社会、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都带来无穷的后患烦恼,这些都根源于“道德绝对命令”的基本原理,进而表明既不符合道德绝对命令的合法标准,又不符合法治的合法标准,还不符合道德理性的合法标准。
7.道德正义衡量。道德原则上是正义,例外是非正义,即道德原则上代表正义并且是对正义的道德追求,这种道德义务建立于自然义务基础之上,自然义务是天生无需他方证实、证明,具有不证自明的原始特色。其实,对正义的道德义务附加在一个自然义务之上,那个自然义务的自然动机就是以一种集体的方式被重新导向的自我利益。正义的义务被集体地重新导向的自我利益中引申出来的一种义务,那种利益就构成我们对正义的自然义务[36](P393~395)。道德正义是建立于自然义务基础之上完成对正义的义务,既是道德正义,又是对正义的自然义务。据此分析,钓鱼执法既不构成道德义务,又不构成对正义的道德追求,更不构成自然义务,反而在权力任性基础之上自我行动,既不能保证追求道德正义,又不能追求自然道德价值,还不能满足正义的法治价值,更不能从道德正义标准满足合法价值。
8.意志自律衡量。道德品质上是善良,行为实质上是自律,外观上是道德意志,意志自律成为道德的核心魄力,通过道德自律主动完成道德义务,取得最高的道德绩效。其实,这种不受个人感性欲望、感官经验支配的行为,就是一个人在按照理性法则要求行为,就是一个人根据内心道德法则的行为。这个行为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强制,而是来自于内心的法,是个人服从自己内心的法,这就是意志自律[34](P341)。据此可知,钓鱼执法是执法官员的主动故意行为,根本不考虑道德价值,根本不考虑道德自律约束,根本不考虑道德诚信规制,根本不考虑道德意志的善良规范,根本不考虑内心道德法则。据其中,核心关键在于没有道德意志自律,没有非成文道德规范约束,让“执法”行为“为所欲为”,既不符合道德规范,又不符合法治合法,更不符合道德合法,是丧失意志自律的道德违法行为。
9.道德恶的反向衡量。运行正向思维剖析了道德的方方面面,钓鱼执法不能符合道德合法标准,不能满足道德价值,不能按照道德规则运行,总体上属于恶性事实。为此,运用道德恶反向衡量钓鱼执法,与正向衡量共同构成道德性衡量整体。其中,道德正向衡量是原则,反向衡量是例外补充。其实,恶是一种客观事实,人们对恶的评价是对这种客观现象的反映。恶的价值属性不仅属于客观事物,而且是从社会关系中逻辑地产生出来的,即恶是在社会道德关系中所具有的消极意义,是对社会道德的要求的违背[37](P18~19)。推论可知,钓鱼执法本质上属于道德恶,属于客观现象、客观事实的客观反映,对道德具有反向影响作用,既破坏社会道德价值,又破损道德秩序,还为道德社会制造恶因子,进而表明本质恶性,加剧了非合法性程度,即运行道德恶衡量之,钓鱼执法没有道德合法的基因。
由此可见,道德性衡量钓鱼执法既是道德理论创新,又是法治思维创新,更是道德法治融合创新,在法治合法性衡量的基础上,继续以更严格的道德标准衡量之,判断衡量是否符合道德价值标准,是否契合道德规则,是否与道德行为同道,是否与道德意志自律同心,是否符合道德善良价值,是否基于道德诚信为之,是否是人性道德的结果,是否主动遵循道德命令,是否追求道德正义,是否与道德恶反向运行。只要符合上述道德标准,满足上述道德价值,契合上述道德规则,追求上述道德目标,以道德善良为核心,实现道德正义,积极向道德原则靠拢,才能完全符合道德合法标准。可是,钓鱼执法无法满足道德的上述技术要求,无法具有独立的善良道德价值,无法在道德基础之上创新法治价值,无法满足道德合法规则。
综上撰述,钓鱼执法的问题多多,法治问题更是“多如牛毛”,只能有代表性选取其中的“代表”重点着墨论之。在此,类比借鉴辅警执法,它既没有法定职权、职责,又没有法定程序可遵循,还没有主体上的合法“名份”,完全是现实社会中针对客观问题所采取的临时措施,根本没有考虑其对法治的负面影响,根本没有契合现代法治理念,根本不能紧跟依法治国步伐,根本没有顾及带给法治的“负面清单”[38](P107)。据此,钓鱼执法同样存在法治伤害,外观症状可能不太明显,但却无法准确估量长远的恶性后果,当时极可能“不痛不痒”,表现为“未发现明显异常”的健康状态,事实上为将来的“法治病症”制造了无数病理基因,如同违背自然规律的控制性人口政策,当时不会感觉到“阵痛”,随着时光的流逝,人口“惨痛”会在不远的将来“光临驾到”,届时后悔是既无用又无效,一切措施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此,钓鱼执法对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都会带来无穷的法治伤害,用道德和法治清除滋生钓鱼执法的土壤空气,熔断钓鱼执法的利益体制机制,铲除钓鱼执法的利益垃圾,才能培育依法行政的法治新生态、新业态和新常态,才能逐渐形成法治执法的新思维、新观念和新方法,才能打造道德执法的新环境、新平台和新工具,才能形成道德和法治衡量的新视野、新创想和新思考。
[1]何颖.行政哲学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1.
[2]叶必丰.行政行为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律解释[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4]胡利明.论立法法修法中的法治理念[J].新疆社科论坛,2015,(6).
[5]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6]朱维究.中国行政法概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7]杨海坤,章志远.中国行政法原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8]杨海坤,章志远.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胡建淼.行政强制法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10](日)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本)[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1]戴剑波.权利正义论——基于法哲学与法社会学立场的权利制度正义理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2]王海明.公正与人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3]张伟.交通“钓鱼执法”研究[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0,(1).
[14]桑本谦.“钓鱼执法”与“后钓鱼执法”的执法困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研究[J].中外法学,2011,(1).
[15](比)米歇尔梅耶著,史忠义译.道德的原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16]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观察[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17]蔡茂寅,李建良,林明锵,周志宏.行政程序法实用[M].台北:新学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6.
[18]周光辉.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19]石佑启,杨治坤,黄新波.论行政体制改革与行政法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0]周汉华主编.行政法学的新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1]范进学.法律与道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2]江必新.行政行为效力判断之基准与规则[J].法学研究,2009,(5).
[23]胡利明.保安执法的违法性考察[J].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1).
[24]胡利明.官员证婚的法律分析[J].中州大学学报,2015,(6).
[25]胡建淼.行政法学(第2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6]胡利明.论房地产区分所有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27]胡利明.法官调查取证制度的合理构建[J].2015,(6).
[28]胡利明.论“三严三实”的法治背景及法治理念[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6,(2).
[29]宋功德.行政法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0]胡利明.自由权和管理权的多维分析[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6,(1).
[31]钱广荣.道德悖论现象研究[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2]李义天.美德伦理学与道德多样性[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33]郑明哲.道德力量的来源[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34]高兆明.伦理学理论与方法(第3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5]戴兆国.明理与敬义:康德道德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6]徐向东.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7]李建华.趋善避恶论:道德价值的逆向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8]胡利明.论辅警执法[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6,(2).
[责任编辑:张昌林]
The Legal Analysis in Fishing Enforcement
HU Li-ming
(School of Law,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From the departure of whole analysis of rule of law,we focused on the analysis of Fishing Enforcement problems of rule of law through operation of the subject,legal procedures and legal interests of the rule of law by legal and moral measure its rule of law and moral values according to evidence and legality.It results in damage of rule of law for society,country and government of rule of law,and it is necessay to to remove breeding its soil and air,to fuse its system and mechanisms of interests,to eradicate its garbage of interests.It is possible to cultivate new ecological, new formats and new normal of rule of law,and to form gradually new thinking, new ideas and new methods of enforcement of rule of law,to create new environment,new platform and new tools of moral enforcement,to form new horizons,new imagination and new thinking of measure of moral and rule of law.
fishing enforcement;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ve ruthority;rule of law;morality
2016-07-15
胡利明(1979-),男,湖北孝感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经济师,主要从事法治理论研究。
D912.1
A
1004-7077(2016)06-00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