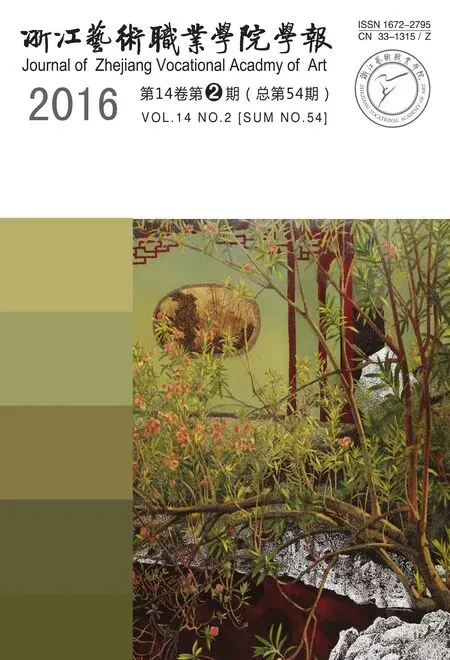作为“标出性”的纪录片本体∗
赵 勇
作为“标出性”的纪录片本体∗
赵 勇
当前纪录片与故事片在创作手法的共用区间越来越大,其体裁区隔的界限却日益模糊。传统的纪录片本体论核心命题,运作概念和实践形式必须经历新的调整。广义叙述学将纪录片和故事片都看作记录演示类媒介,规避了真实与虚构的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纪录电影的风格——非虚构,是一种 “标出性”行为,是作为边缘体裁反抗故事片叙述的有意 “出格”。在当前形势下,纪录片必须从媒介区隔的角度,重新规定本体域范畴。
非虚构;标出性;神圣文本;区隔;述真
一、作为标出性的 “非虚构”
纪录片作为一种电影类型其概念域和实践域的划定从来不是一个系统内部自主性建设的结果。围绕 “非虚构”这一关键性限定语,纪录片规划了自己的几条原则:第一条是关于影像画面的:在场素材的原生摄录,要求摄影机第一时间记录事件流程,不可事后记录,否则为作假 (后面修正为适度搬演事件必须有提示性符号说明);第二条是关于文本功能的:纪录片具有文献性,可用来历史保存,这一点赋予记录一种严肃神圣的文本气质,可以和圣经叙事具有相似的话语权威;第三条关于基本编码语法的:忠实记录是基本创作技巧 (如长镜头美学等),它在立场上与扮演重构技巧相对立。第四条是关于观影效果的:记录片的真实效果可以通过文本外的实证来获得检验,从而满足认知能力的要求。
纪录片的诸多本体论和实践论美学基本都是围绕着上面四条原则展开的。这四条原则的建立都是旨在反对 “虚构”这一文化体裁。在电影内部门类中,故事片和纪录片是影响最大的两大体裁,但是故事片无论在市场规模,电影语言丰富度等方面明显占有优势。虚构性是故事片的基本属性,因此纪录片作为一个比较边缘化的体裁为了获取稳定的存在位置,以抵抗强大的故事片文化模式的侵犯,而采取了一种文化对抗性的方式来自我 “标出”——非虚构。
标出性是语言学的概念,四川大学赵毅衡先生将其引入文化符号学的领域,“当对立的两项不对称,出现次数较少的那一项,就是标出项 (the marked),而对立的使用较多的那一项,就是非标出项”。[1]纪录片的定义和创作具有明显的有意“标出”的先锋意图。纵观电影史,纪录片的确是作为最早出现的类型,但是电影艺术成熟的标志是电影语言的建构,在这一方面,虚构型故事片一直都是起着领军作用的,格里菲斯和前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形成的剪辑语法构成了基础性的影像美学,增强了电影的自由表现力。而纵观纪录片美学理论和实践,会发现其总是处于对立性架构原则之中,比如长镜头美学恰恰是针对好莱坞虚构美学的 “陈词滥调”,反对过度剪辑带来的虚假,破坏了完整真实的被摄体环境。但是虚构型美学作为影视文化的主导性文化,具有异乎寻常的压倒性力量。故事片代表了人类世俗的自由的 “创世”梦想,是一场影像狂欢。而纪录片的严肃气质和 “刻板”语法让人感到冷若冰霜。在 “去魅”的时代,一切神圣文本都将受到挑战。因此在电影市场上,故事片作为虚构型体裁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欢迎,成为通俗文化的典型代表。因此,纪录片日益边缘化,日益避开大众市场,走向精英主义。纪录片一直都在是否跨越虚构手法而左右摇摆犹豫不断,之所以如此,正在于 “虚构手法”在故事片中是主导的因素,具有体裁的规定性。而纪录片需不需要虚构性这个手法就变成了文化立场的对抗的体现,纪录片若获得自身艺术场的合法性,必须不断驱逐任何虚构性语法的介入,在理论和实践上,展开不断的自我检视,维护纯粹的血统。
纪录片对影像文本 “神圣”化,确实维护和提升了电影艺术在精英时代的文化地位,并时刻让电影艺术围绕人类最为本质的物质和精神生存基本问题进行严肃探索和追问。但是在当前泛艺术化时代,传统文化等级秩序获得颠覆,神圣文本失去了被认真审视和对待的外部环境;同时消费美学大肆殖民影像艺术,将影像媒介消解为日常狂欢的碎片文本。拟像时代需要超真的虚构能力,建构更多可复制的虚构文本集合。正是在这个情况下,纪录片的标出性特征——非虚构,就在根本上受到了挑战。纪录片的理论和实践由最初的有意标出,慢慢的开始进行修正性修辞,其向虚构策略大肆借鉴。美国的 《蓝色警戒线》《浩劫》等新纪录片的转向尤其明显:影像那种不可质疑的神圣性开始遭受解构和质疑,在纪录片 “四条”中,违反了三条,原始事件影像阙如;不具有文献性,因为他们是二度引用性文献,影像自身被解构不忠实;扮演和表演手法被使用。只有第四条,实证性获得保证,因为保留着意思逻辑推理和经验现实的参考性。
这个转向具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影像的 “真实”,影像的 “记录”这些传统上纪录片的本体元素受到颠覆,这些本体元素明显是建立在 “非虚构”这一针对故事片语法对立上的标出性风格。传统纪录片的本体论只剩最后一条 “实证效果”。纪录片可以经由文本外的经验真实来鉴定文本的 “真实”性;而虚构型则努力避免被 “现实问责”。纪实型与虚构型体裁的关键区别在于 “媒介区隔框架”。
二、区隔理论——媒介
在广义叙述学看来,纪录片和故事片同属于记录演示类叙述。首先不观是纪录片和故事片,虚构的事件和真实的事件都需要需要在真实空间和时间中具体展开,人物动作和情节变化具有观演的同时性在场感;其次他们都需要被记录在影像媒介上,因此是二度媒介化。之所以指出其共性,恰恰是说明纪录片如果固守媒介真实和素材真实这一立场,是无法说清的——影像作为像似符号,本来就是建立在与实在界的距离之上,真实感永远是幻觉的产物。这样,因为都是影像 “在场”摄制事件素材,所以影像具有纪实性;但因影像符号是对有意义的事件的二次呈现,因此是媒介符号的替代性出场,媒介世界区隔出现实世界,两者世界不同,因此媒介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 “虚构”性再现。影像符号既是纪实性的,又是虚构性的。纪录片的 “非虚构”明显不能作为本体来讨论,正如上文所说,这是其策略性 “标出”的一种姿态。
纪录片与故事片的体裁规定性恰恰是在于媒介的 “显身与否”。
故事片为了建立一个自足的封闭的虚拟世界,比如好莱坞电影,要千方百计区隔出经验世界和故事世界。故事世界的叙述逻辑自成体系,不能也不必要用现实经验来衡量和体验。而纪录片则不同,科恩提出 “纪实型叙述,在文本之外,令需要一个指称层 (reference level)”[2]。她的意思是纪录片的叙述行为,始终指向叙述之外的一种实在。也就是说,记录片是 “与指称有关的”是指称符号,作为符号中介,文本指向现实,纪录片目的是让观众直接将文本延伸跨出到经验真实;而故事片是“符号自指的”,也就是说文本本身就是意图定点的范围,是审美域。比如王兵的纪录片 《铁西区》和王猛的故事片 《钢的琴》题材都是东北失业钢铁工人的生活,反映了中国改革期阵痛的现实。在情感煽动性上,故事片 《钢的琴》要更强,因此它的目的就是要 “最大程度的激动人心”,审美情感是故事片要求。但是 《铁西区》则意在指涉现实尚未解决的下岗工人现状,他们或在纪录片文本世界的外面,而不仅仅是一个表意符号,它触动的更多的是对现实的认知功能,其次才是审美功能。
表现在文本中就是媒介作为叙述框架的在场与否。赵毅衡认为 “区隔框架是一个形态方式,是一种作者与读者都遵循的表意-解释模式”[3]74。故事片作为虚构框架,必须尽量抹除 “人为”痕迹,比如好莱坞叙述强调 “缝合叙事”,“演员不看摄影界”等等规则都是为了保证 “幻觉”产生,以区隔现实世界,以一种 “洞穴观影”的情境,以暂时性逃离现实生活的种种危机。而纪录片则应该有意突出叙事者的性质和影像的在场痕迹。纪录片强调叙事者的实在性身份,比如显示记者和被摄者详细信息 (可作为实证资料);摄影机操作痕迹的说明可以打破幻觉,产生间离效果,引发对 “经验现实”和 “媒介操作环境”的双重检验。《楚门的世界》是一部故事片,这部影片反思了纪录片对媒介 “藏匿”带来的伦理担忧,摄影媒介显身出来才让人对媒介影像那种 “区隔”现实的幻觉产生警惕。这一点恰恰也是对纪录片和故事片关系的巧妙隐喻。在当下一些纪录片中,无论虚构手法怎样使用都不为过,问题在于纪录片创作者是否在文本中留下 “实证性线索”以备观影者按图索骥。纪录片是半文本,它文本完整性有待于观众拼合文本内外来完成,纪录片的品质判断和评价需要 “事后诸葛亮”,这一点和故事片很不一样。
三、述真问题—体裁契约
纪录片是作为一种叙述文本,是个意义结合。符号意义有三个环节,意图意义,文本意义,接收意义,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构成诚信,谎言,虚构关系。
纪录片创作者无意构造一个虚幻的仿真世界,它往往带着更强的现实干预目的,让人相信他所表达的出自其真诚的意图,而纪录片文本内容与实在世界有直接的互为引证的关系,而纪录片观众也应该做好反思和链接现实的准备。这在叙述学中属于述真问题。纪录片必须做出 “诚信”的姿态;而故事片则要做出 “作伪”的暗示。严肃的历史和生活现实的直接反映不容杜撰,然而毕竟纪录片观影者不能事事都亲历现场去求证,所以纪录片创作者必须担保自己所说所言的可靠性。纪录片的体裁就是契约,它裹挟者一系列伴随文本,让观众去识别文本特征。比如纪录片所做的宣传,宣称这是一部纪录片,纪录片创作者显身说法,字幕提供信息,摄影机现实抓拍等典型语言的提示,最可靠的保证就是结尾制作人员的出场——他们不是演员。
“实在与非实在”也是一个重要维度。因为纪录片是半文本,所以它指涉实在世界,观众可以用现实经验来衡量文本逻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从而判断品质价值。
也可以在接受层面,来探索观众的心理意愿,比如观众当愿意接受这是个纪录片文本时,即使该纪录片拍摄粗糙,手段不佳,影像质素不好,但该片的纪录片的价值依然获得承认。诚信/作伪是发送者态度;恰当/不恰当是文本品质;愿接受/不愿接受是接收者态度。本文借用广义叙事学中相关模型来总结纪录片的接受方式——诚意正解型:诚信意图—可信文本—愿意接受。纪录片是诚意正解型,它要求创作者的承诺文本的可信,通过一系列伴随文本显示 (比如暴露媒介,叙事者与作者的合一性等);记录文本具有实证性,纪录片文本要在观影结束后经过时间的广度 (历史长时值)和空间广度 (大规模公共空间讨论)的考验,要在舆论场中生成迟到的文本品质的判断;最后要求纪录片观影者有一定的元语言读解能力,因为纪录片是半文本,需要观影者调动自己的现实经验,知识背景,文化水平等来共同延伸文本创作,“读者也就是作者”。
四、“祈使”结构
纪录片作为一度区隔的符号文本,影像符号具有指涉经验现实的相关性。因此它具有很强的意动功能。因此纪录片具有一种和语言学中祈使语气具有相似的召唤结构。“祈使句与陈述句有着根本的不同:陈述句服从实在的检验,而祈使句则不用——陈述句与祈使句另一个不同之处是陈述句可以变换为疑问句,如某人喝水了吗?某人将要和水,某人总是喝水,与祈使句喝水!则不能转换。”[4]祈使句不求实在验证,重在意动,有劝导功能——这有助于理解纪录片效用。纪录片重点不在于对真实接近的程度,而是以呈现刺点真实,是为了扰乱主流真实的认知规范。纪录片创作者和观众共同遵守体裁的符号指示性,都在试图寻找刺点因素,寻找纪录片文本的社会动能效应。也就是说纪录片影像符号指涉性不仅仅是刺穿文化表象的遮蔽,更具有一种行动邀请性。纪录片不只要完成观影任务,更具有干预社会的结构性功能。它的干预性在于劝导观众观影后要去 “辨别”现实世界,从而在社会学意义上唤起生活世界的变革动力。
纪录片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陈述式向祈使语法的结构转变。强调影像的摹写功能和尊崇真实的态度其实是将纪录片过度拘泥于陈述句式。纪录片不能仅仅是表述 “真实状态”,提供一种关于 “真实异域”的乌托邦:在那里人们发现真理正义被伸张,但世界的澄明性却被牢牢框定在一度区隔的符号系统中。“真实”既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表述性符号的知识系统,又是实践理性介入社会的强力工具。
“意动是人类心灵的基本功能之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首先剔除这一点,他们指出的三功能,是情绪,认知以及意动。”[3]59纪录片具有双重性,使得它区别那些沉溺于二度区隔的虚构电影及其他的艺术文本。纪录片不具有文本自足性,它的价值跨越在认知性和意动性之间。美国新纪录片运动代表人之一的迈克·莫尔,《罗杰和我》编导本人出镜和破产工人历经波折争取权益的斗争过程采取情节化叙事结构,有对人物关系情感变化捕捉和渲染,有精湛的蒙太奇美学语法,这形成了一个具有观赏性的艺术文本;同时作为纪录片体裁的规定性,它最动人的恰恰是纪录片作为社会运动的现实——也就是彼时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衰退下,工人阶级的窘困的现实。迈克·莫尔的动机在片中直接说明: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纪录片创作者主要应该学会社会学方法观察社会的问题动向,而主要不是 “审美”眼光打量世界。迈克·莫尔本身首先是个社会活动家,他制作影片就是表达社会观点,是借此干预现实的一种实践性、操作行为。必须旗帜鲜明地承认,纪录片文本具有工具性,这是第一创造力。文本修辞术很大程度上应该成为一种意动力量,它应突破一度框架真实,将银幕前沉浸于幻影术的静态观众召唤为实在世界的、有思考与行动力的 “社会人”。因此可以这样说,社会学统摄纪录片思维结构,美学附属于社会学是纪录片应该遵循的基本创作原则。混淆这个关系纪录片的命名和范式划定都会出现困难,从而迷失创作方向。
五、问责 “合一”的叙述者
纪录片是纪实型叙述,它承认 “讲述”是“有人物参与的事件,被组合进一个文本中”[3]19。纪录片叙述者与文本的关系是等级制关系,纪录片制作者必须保证文本证据和论证过程的真实以及对叙述修辞术的限定性使用。接受看一部纪录片,就必须认定在信任指数上:制作人第一,文本第二。也就是说影片对真实世界的评价体系牢牢反映出制作主体与文本的控制关系上。这一点与虚构型故事片完全不一样。故事片的叙述者隶属于文本内一个要素,叙事者永远不能跳脱出文本对文本自我进行评价,也就是说故事片叙事者无需对文本真实性担责——文本第一,叙事者第二。等级秩序的差别,其实也就是文本效能的不同,纪录片是功能性文本大于艺术文本,制作人是作为叙述者的 “在场”;故事片是艺术文本的自我完形建构,是实在性叙事者的 “隐身”。
有两种思考方式:论辩式、叙述式。布鲁诺(Jerome Bruner)解释说:“一个好故事,与一个组织良好的论辩,是非常不同的。二者都可以用来说服,但是说服的东西本质上不同:论辩以真相说服我们,叙述以栩栩如生说服我们。”叙述处理的是“人或类似人的意图、行动、变化、后果”[5]。既然纪录片是编导的有意识的叙述行为,而栩栩如生的叙述修辞术又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一点上,如果纪录片痴迷于修辞术,那必将复制虚构型故事片的模式,最终消解自身存在。在贾樟柯 《二十四城记》中,影片体裁无法定义:贾樟柯创作史覆盖纪录片领域和故事片领域,因此无法以制作人身份作为指示性符号;纪录片素材的来源明显无法确证,多重元素混合;文本内外边界区隔模糊,观影主体对体裁识别困难导致无法调取观影经验更无法追踪文本解读方向。需要指出的是某些仿纪录片 《女巫布莱尔》和 《可可西里》。它们尽管很像纪录片,可是文本体裁指出了制作人的身份,前者是美国巫术电影公司,艺匠娱乐公司作为发行人,这两个公司一向是制作和发行小众娱乐作品;而 《可可西里》陆川的创作履历和片尾演职员字幕等体裁性信息作为指示性符号框定了电影文本的虚构属性。所以纪录片作为文本框架外身份的实在性在于:作者要对——文本内的论证逻辑和经验现实素材——呈现和使用要负有问责义务。也就是说纪录片编导必须对自己创作的作品真实性负全责。
创作者不是保证文本的真实性,而是保证文本作为工具指涉现实问题时采取的论证逻辑的合理性。真实观存在着伦理层面,“人为什么不能当别人的道德法官?耶稣讲的好简单:瞎子不能领瞎子的路;如果这样,两个人都会掉进坑里去。”[6]但文本作为工具性论证,必须保障方法论的真实。保证社会调研程序,事件演绎能否经得起求证和检验。在纪录片传播的整个环节而不只是观影环节持续保持问责状态。
传统认识论强调:理性思维认识是感性螺旋提升的结果。德勒兹认为电影能展示人的心智质料,“是一种自动精神机”,[7]通过用哲学分析电影,试图绕过这种线性递进模式:探索影像直接进行逻辑思考的可能性。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各种传播媒介是人身体技能的延伸,在如今已成为现实,人的感性能力在现代媒介中被异乎寻常地放大。可以这样说,当下媒介某种意义上已经开始试图模仿人脑功能并在媒介中延伸。德勒兹意义上的纪录片在未来向度上,电影媒介像人类的大脑一样自由地进行复杂的思维活动,是完全有可能的。纪录片成为新思维论辩术、“方法论”文本。①注:笔者认为,完美的方法论文本指的是以文本以呈现思维路径和逻辑运演为结构,为公共议题服务的文本模型,接近于法国艺术家戈达尔的 “论文”电影。
解构主义让主体退场,解放了文本。在虚构型叙述语境中,多个叙述者竞相争夺叙事主导权和话语优势,主体间性带来了叙述狂欢。高科技影像的发展,让纪录片迷恋超景观异域的营造。但是纪录片不能因此放弃文化领导权:创作者要有主体性意识、要有社会议题意识;既要在价值背景上维护主流文化,又要适度给予 “刺点”性扰乱。纪录片是 “刺点”真实的体裁,它是半文本的,它有艺术符号的可观性,更有文化符号的意动祈使功能;而故事片体裁要求其自身建立文本封闭性的异域幻觉。纪录片应该作为文化体裁的规定性来廓清自我范畴。传统的 “真实论”之争可以就此作罢。但是放弃用真实与否来维护纪录片作为真理言说的权威和严肃性的品格,那么谁来支撑其长久以来的观影信任呢?放弃了真理化身,对纪录片创作者来说,放下义正词严的身段,言说有了很大自由度,比如虚构与纪实只不过是叙述手段:权威性没有了,言说主体的责任担当其实更加重要。以前靠神性——俨然 “真实”的化身使者——现在要靠个人主体,在文本编码、演绎、传播——在整个大文本链中时刻接受对文本真实逻辑的检验和问责。编导既要对文本的创建负责,更要对文本的传播和社会效果负责。在这个意义上,观影的文化契约——“真实”— “记录”的认同机制正式形成。
[1]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81.
[2]Dorrit Cohn.Transparent Mind:Narrative Modes for Presenting Consciousness in Fiction[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3]赵毅衡.广义叙述学 [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4]罗曼雅柯布森.语言学与诗学 [A]//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 [C].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177-178.
[5]JeremyBruner.ActualMinds,PossibleWorlds[M].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13.
[6]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183.
[7]吉尔·德勒兹.时间-影像 [M].黄建宏,译.台湾:远流出版社,2003:649.
(责任编辑:李 宁)
On the Ontology of“the Marked”Documentary
ZHAO Yong
Current documentaries often use the same artistic creation techniques with feature films.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two genres are increasingly blurred.As to the ontology of the traditional documentary,the operation concept and the practice form must experience a new adjustment.The documentaries and feature films are all defined as record-demo media by narratology which avoid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truth and fiction.The style of documentary films,namely non-fiction is“the marked”feature which break the pattern of the narration of feature films.In the current cultural situation,it’s urgent to rename the new category of document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segment.
non-fiction;the marked;sacred texts;medium segment;being and seeming modle
J952
A
2016-05-17
赵勇 (1981— ),男,河北沧州人,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讲师,四川大学文新学院艺术学理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艺术理论与批评研究。(成都 400064)
∗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网络文化发展对小城镇社会生活的影响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PY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