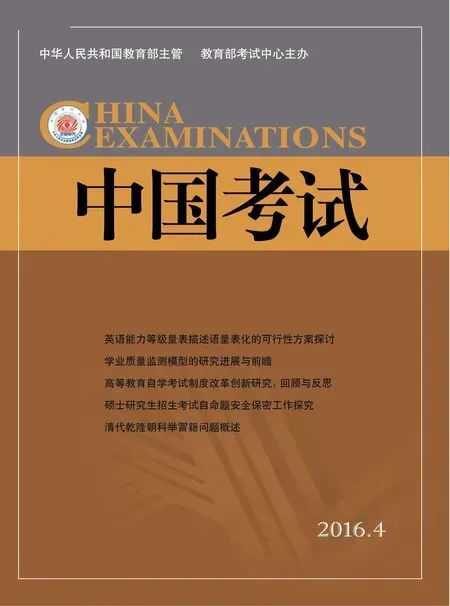清代乾隆朝科举冒籍问题概述
王学深
清代乾隆朝科举冒籍问题概述
王学深
冒籍是中国科举史上一直存在的作弊手法。在清代,冒籍问题以乾隆朝表现得最为突出。乾隆朝冒籍问题原因不同、形式多样,乾隆帝本人也一直对于冒籍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严加防范和惩处。本文以冒籍概念为切入点,具体探讨清代乾隆朝冒籍问题形成的原因、冒籍的种类与形式、冒籍产生的影响以及乾隆朝所采取的稽查冒籍之法等,全方位地展现乾隆朝的冒籍问题。
科举制度;冒籍;高考移民
科举制度从隋朝始至清末终,有着长达1 300年的历史。科举考试作为考试制度,在为国家选举人才的同时,各种作弊手段也层出不穷,冒籍问题就一直相伴科举制度始终。清制规定,士子参加考试,必归于本籍投考,不得越籍赴试。但规定禁而不止,清代以乾隆朝冒籍问题最具有代表性,不仅冒籍问题发生数量多,而且种类繁杂。究其原因,一方面乾隆帝自身重视文教,希图保证科举取士的地域均衡性,尤其是保证南北区域间政治资源和整个官僚集体的平衡;另一方面在于当时国力强盛,有精力纠正弊端,到了道咸之后国势日衰,想纠正冒籍而不能。
随着学界对于科举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冒籍与今天“高考移民”有相似之处,“冒籍”一词也不断出现在学者的著述中。夏卫东(2002)在《论清代分省取士制》[1]一文中论述了“冒籍”问题出现的原因,即分省定额的出现,将冒籍问题延伸,突破了前人仅仅停留于对冒籍问题概述的阶段。王日根和张学立(2005)的《清代科场冒籍与土客冲突》[2]一文,首开专门讨论清代冒籍问题之先河,文中特别针对冒籍引发的土客冲突展开论述,将科举与地方社会史作进一步的结合。
最近几年,学者对于冒籍的关注点由地域冒籍向身份冒籍转变。如曹永宪(2002)《明代徽州盐商的移居与商籍》[3],梁仁志和俞传芳(2005)的《明清侨徽商子弟的教育科举问题》[4],及刘希伟(2010)的《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商籍”考论》[5]均对清代商籍问题有所论述,其中就都提到了冒占“商籍”参加科考的事例。
王洪兵(2010)的《清代顺天科举冒籍问题研究》[6]一文,较前人所述更进一步,将冒籍问题集中于顺天府一地进行讨论。文中集中探讨了顺天冒籍的现象,顺天府对于冒籍的稽查制度,从严格稽查户籍、对廪保的稽查、对冒籍士子的惩戒、对官员的问责及审音的出现论述了顺天府对于冒籍问题的防范措施,更为深入地关注了冒籍问题。
最新的研究当属刘希伟(2012)所著《清代科举冒籍研究》[7]一书。该书从科举制度研究视角入手,不仅追溯了唐至清代科举冒籍发生的问题,而且着重强调了原籍应试原则与变通、冒籍的缘由与社会影响这两方面中官方与士子、土著与移民的互动关系。在“冒籍的理论反思与现实观照”一章,较之前所发表的《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冒籍问题及其现代启示》[8]一文基础上,更加强调冒籍与当代高考移民以及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就地高考问题,并“知古鉴今”,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本文希望展现盛世与科场弊端所存在的张力,通过对于乾隆朝士子冒籍方式与应对方式的系统梳理,尤其是通过对乾隆年间九类科场冒籍种类的讨论,更加深入讨论乾隆时期冒籍问题及其存在的特殊性。
1 冒籍问题产生的原因
清代科举制度在各地区分配入学中式名额,有大、中、小三等之分。从乡试解额来看,总体趋势有所增加,但是乾隆朝应试士子较之以前更多,且乾隆帝注意对于江南地区解额的控制,并不给以江南地区增加大量中额,而对于文风落后之地给予扶持,保证各省士人均等的中式机会,故造成了江南地区一些士子屡试不中,希冀利用地区文化差异作弊,这就直接导致了士子冒籍跨考问题的产生。
清代分省取士制度平衡了各地取士人数,保证了多地域南北平衡发展。为了扶植边远省区人文教育水准的提高,清代对云南、贵州的乡试举额不断增加以避免中举士子一地过多、另一地过少的情况出现。同样因为分省定额制度也引发了士子避难就易的心理,不仅江南士子冒籍云贵、顺天,广东士子冒籍广西,福建士子冒籍台湾应试等,就是在一省之内因各府县竞争水平不同,也往往发生童生同省异府、同府异县的冒籍问题。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学政奏报“福州府之侯官县、闽县、福清县,漳州府之龙溪、漳浦、海澄、南靖、平和等县通同混考十有余年”[9]。
正如夏卫东所说“分省取士制度将考生之间的自由竞争严格限制在本地区之内,造成各地考试的竞争程度不一。南方省份由于文风兴盛,竞争激烈,而北方省份名额虽然不多,但竞争相对容易,大量南方士子冒籍便造成了这一负面效应”[10]。可以说,分省取士成为冒籍多发的重要因素。
2 乾隆朝科举冒籍形式
清代士子冒籍大体上可分为地域类冒籍和身份类冒籍。地域类冒籍主要是士子在非原籍所在地参加考试,进行横向的社会流动,希望到中式率较高的地区参加科举考试,也体现了清政府对于人身控制的进一步放松,人口的地域流动性增强。身份类冒籍部分主要是部分人群希望通过科举转化身份,如一些“贱民”子弟希望参加科举获得功名,以彻底改变地位,因此冒捐冒考事情常有发生。
2.1 地域类冒籍
2.1.1 南方士子冒籍北方
在清代文化呈南强而北弱之势,许多南方士子纷纷冒籍北地科试,其中又以冒籍顺天府大兴、宛平两县最为严重。对于冒籍顺天应试问题其实早有规定,《钦定科场条例》中就有明确规定“顺天乡试南人冒籍北监入试者照冒籍例治罪”[11]。但是禁令禁而不止,乾隆十年(1745)顺天府府丞郑其储奏称“大、宛两县额进生员冒籍居多,冒籍得以入考。由冒同乡在顺天之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为父兄,而冒有籍贯之人借此获利。欲杜冒籍,宜彻底澄清”[12]。对于郑其储奏请,乾隆帝下谕要求冒籍顺天士子以一年为限自己呈首改归,要顺天学政力求“考试时凭文取录,宁缺无滥”[13]。
虽然上至乾隆帝,下至督抚、学政、州县官一再详查,但是冒籍顺天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乾隆二十一年(1756)顺天乡试南方士子冒籍北方问题极为严重,御史范棫士奏称“顺天乡试……南人冒捐北监入试者未除,而本年乡试为尤甚”[14]。根据调查,此榜顺天乡试有李骏等冒籍者31人,乾隆帝要求彻查中式举人籍贯,将所查出分别斥革、改归,31人之父兄有身系职官者均照违令“笞五十、罚俸九个月”[15]。乾隆帝不仅将所查出31人斥革,而且所牵涉的认保、收考之州县官,对于早已中式为官但冒籍之人也一并要求呈报改归,可以说这起冒籍顺天乡试引发的科场弊案直接导致了乾隆帝对于冒籍问题的高度重视。
2.1.2 富庶地域士子冒籍贫省应试
清代浙江、江苏、安徽、福建、广东等省份经济发达,同时带动了当地文教的发展,由于这些地区中额所限,以及所在地区竞争激烈,士子们往往冒籍相对贫困地区参加科考,以求中式。与之相对的如陕甘、云贵、广西、四川、湖广等地相对贫弱,因此成为了冒籍的多发之地。正如广西学政鞠恺所言“惟冒籍之弊最甚,本省府县相邻之人冒考者固有,而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等省之人冒考广西者尤多,大抵或因父兄作幕,或因亲友贸易,诡计影射,混入考试,并无实在田产庐墓。人学之后,仍归故乡,而大比之期复来冒试”[16]。可以看到,冒籍广西者大多是来自经济发达地区,在早年由于广西等地文风凋敝,甚至有开考不足数的时候,这就给冒籍者很大机会,可以冒籍应试。
此外,为了照顾边地的苗民、猺民等,乾隆帝给予他们一定的中额以鼓励地方文教,但不想这一举措也同样被士子所利用。乾隆五十三年(1788)湖南学政钱沣奏称,“溆浦县童生冒考猺籍者甚多,应亟为清厘。已饬辰州府、严督该县按照学册,细查新籍生员。除病故不论外,其现在应试及告给衣顶者必实居猺地。确有户族田庐可凭,取具猺头猺总甘结。日后子孙方准以新籍应试,其余概令改归民籍”[17]。钱沣如此办理,也得到了乾隆帝“得旨,所办颇合”[18]的赞赏。
2.1.3 人口大省士子冒籍小省应试
清朝随着人口的增多,至乾隆末年人口突破3亿大关,但是科举中额并没有相应快速地增加,甚至有所减少,因此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士子中式的几率。这种冒籍问题最为集中体现在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冒籍台湾应试上。据《晋江县志》记载,从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三十年(1765)间,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士子冒籍台湾应试考中秀才者就有王贵、陈名标、唐谦、王克捷、黄帝赉、郭文进、杨对时、张源仁、尤廷对、蔡霞举、张源德等人。其中,王克捷在冒籍诸罗县籍后,获得了生员的功名,后又在福建参加乡试,以台湾诸罗县籍身份考中举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王克捷进京参加会试、殿试,一举考中进士。
除了晋江县外,据统计,在乾隆朝福建泉州府南安县士子冒籍台湾被荐为贡生的有8人,经乡试中举的有6人。福建不仅泉州府的士子纷纷冒籍台湾,其他各府州县如漳州、兴化、福州等地的童生也趋之若鹜。结果导致台湾生员大多是内地冒籍的士子,其中“泉、漳居半,兴、福次之,土著寥寥矣”[19]。据唐赞衰《台阳见闻录》记载:“予查台湾自乾隆癸酉至壬午,凡五科,共额中十名,内惟癸酉科中式谢居仁一名系凤山人,余俱属内地。”[20]
2.1.4 多处跨考
除了以上主要的地域冒籍方式外,两处或多处跨考在乾隆朝也同样严重,即士子既在原籍参加科考,又在所冒籍地方参加科考,以求增大中式几率。如安徽学政戴第元奏称“怀宁、潜山二县疆界毗邻,民居相错,查有童生汪正观、储芬二名任意歧考”[21]。乾隆帝认为此种风气关乎士习,因此在乾隆三年就曾规定“希图两处考试者,此等侥幸之习断不可长,应令地方官逐一确查”[22]。
这种冒考数处情况,在相对边远的地区尤易发生,且一些州县处于几省交界之处,给予冒籍者更是提供了地域上的便利,如陕西学政邱庭漋所奏,“兴安与湖北郧阳府接界,冒籍者颇多”[23]。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川学政陈笙也为清查跨考冒籍之事上奏乾隆帝,陈笙奏报全省有大小州县三十余个,冒籍跨考之事多发于同省异府、同府异县地区,又以府州县学最为集中,每学或一二名、三四名不等。
2.1.5 行政区划混乱引发的冒籍
一些地区因为行政区划原因,导致界限不清,同样引发士子冒籍问题。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广东学政刘星炜奏“肇庆府鹤山县于立县初有广州府民一百零五户,呈请修城入籍奏准应试。此易滋冒籍重考之弊,除已移住鹤山准其应试外,余必有产业呈县注册者准,仍移知原籍以杜重考”[24],广东学政所上奏的目的就是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由于新设县所容易引发的冒籍跨考问题。
同样江苏学政李因培也奏报因阜宁县从山阳、盐城二县分出所引发冒籍混考之弊,其言“阜宁县本由山阳、盐城二县分出,即由山阳、盐城二县各拨文生六、武生四为阜宁学额。其廪增生员,从前并未查明住址,以致所拨之生土著无几,其子弟辗转援引冒籍混考”[25],并要求立刻清查诸生籍贯“其居山阳、盐城者令各归本籍”[26]。乾隆帝用明确行政隶属、严厉稽查冒籍、增补中额等手段防止冒籍发生,并严格各省督抚、学政核查士子籍贯,按照居住满二十年,有田产者方可呈请入籍的规定较为有效地控制了因行政区划变更所导致的冒籍问题。
2.2 身份类冒籍
2.2.1 官员子弟冒籍
清代对官员子弟随同赴任冒籍应试早有禁止。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就有上谕“官员不得在现任地方,令其子弟冒籍,违者革职”[27]。此后乾隆元年(1736)也规定“官员在现任地方,令子弟等冒籍者本生斥革,该员革职”[28],乾隆四十三年(1778)又再次补充“河工各员自通判以上若竟容亲族子弟在该处冒籍者,即照地方官之例办理”[29]。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防止官员子弟因更接近政治资源而纷纷入仕,导致官员队伍内部的不平衡。
虽然乾隆帝对于官员子弟冒籍弊端看得较为清楚,而且严厉禁止冒籍发生,但是一些官员还是利用在异地为官的便利,放任子弟冒籍应试,而这些应试者也甘愿冒着革除功名、停考、牵连为官者的风险去冒籍应试。乾隆二十三年(1758)山东巡抚阿尔泰奏报“莱州任内有即墨童生沈宝篆,原籍浙江,系离任典史沈洪达之子,该府纵令考试,以致人心不服纷纷攻击”[30]。根据阿尔泰的奏报沈宝篆是浙江慈溪县人,在乾隆十八年时沈洪达因计参离任,并于当年启程返回南方老家,但在一段时间后带其子仍来即墨居住而冒籍科试。在县、府试时没有人发现,也没有人认真纠察,到了乡试考试时才有武生胡德辉、增生黄如书二人出名写贴告白。通过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出不仅当地廪保和县、府学官员在稽查冒籍时的懈怠,也反映出官员子弟冒籍的便利性。
2.2.2 冒充商籍应试
清代商业发展迅速,各地商人流动性较大,为了方便商人子弟应试,在直隶、浙江、广东等商业发达之地设有商籍学额,但是一些想走捷径的士子便抓住了商籍管理这个漏洞,纷纷攀附商人关系,冒充商籍应试。浙江学政彭启丰认为“商童应试专以商结为凭,恐招致冒籍假充子侄冒考。致生顶替代倩诸弊,应如所请遇有滥保甲商依律严治”[31]。
虽然有人意识到了冒充商籍应试的问题,但事实上冒充商籍应试问题却在各地不断发生,赵翼就是冒充商籍的典型代表。乾隆十四年(1749),赵翼来到京城以卖文求生,客居于户部尚书尹继善府邸[32],恰好有族人在天津经商做盐业生意,为赵翼提供了冒籍入考的机会,赵翼便“以直隶商籍举乾隆十五年乡试”[33],成功避开了江苏士子的激烈竞争。当时学使叶公煜很赏识赵翼的才华,便没有纠察其冒籍,并拔为乡试第一。冒充商籍之严重一直持续整个乾隆朝,湖北、广东、山东、陕西、山西、顺天、直隶等各地均奏报有冒充商籍案例,可见冒充商籍应试问题是全国性普遍问题,而其引发的结果就是“商学商人子弟日少,而外省假冒日多”[34]。
2.2.3冒充旗籍、民籍、军籍应试
在清代旗籍与民籍有着本质的区别,旗民从政治地位到经济保障都有不同,而在科举考试中旗人单编字号,竞争小而录取率高。因此有些民人为了求得中式便冒籍旗人参加科举,有假托抱养为汉军养子、养孙冒充汉军旗籍者,也有民人出银认某汉军旗籍者为父者。此外,冒占旗籍还有一种形式,即汉军旗籍冒籍满洲旗籍参加科举。乾隆三十三年(1768)顺天府乡试时,有两名镶白旗汉军旗人楚维荣和楚维龄中式举人,但是在核查考卷时发现,两人并没有在卷面注明汉军字样,而是混入满洲名额之内被取中。[35]经过核实,两人确实属于汉军冒籍满洲者,按照律例将二人举人身份黜革。
相反,在清代乾隆朝也存在着旗籍冒充民籍应试的现象。一些投充于旗地的庄头及其亲族拥有旗人身份,但据《大清会典》载:“凡因罪没入或带地投充的庄头亲族均不准应试。”[36]清朝政府为保证田庄内的劳动人手,一般是不许他们“开户”。这些规定将拥有旗籍身份的庄头及其子孙世代固定在田庄之中,而终身没有应试机会,因此这一部分人虽然具有旗籍身份,但往往冒民籍应试。
民人冒占军籍考试者主要是发遣边疆的罪犯的子弟跟随到发配之地,冒充军籍取得在发配地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因地处边远,文风并不兴盛,故而中式率远大于原籍之地。康熙和乾隆二帝对民人入籍地方考试都有严格限制,“各省军籍发遣及安置为民各犯原系罪应迁徙到配所,系彼处编氓。如有嫡属子孙同赴配所情愿考试者,令该犯到配时呈报地方官立案,其非嫡属子孙,虽随行抚养概不许托名混冒”[37]。
2.2.4 隶役、贱民冒籍
贱民冒籍是身份冒籍中最为主要的形式。据清代《大清会典》规定“出身不正,如门子、长随、番役、小马、皂隶、马快、步快、禁卒、仵作、弓兵之子孙、倡优、奴隶、乐户、丐户、疍户、吹手,凡不应应试混入,认保派保互结之五童互相觉察,容隐者五人连坐,廪保黜革治罪”[38]。条例在制度层面将贱民拒绝于科举大门之外,世代无法改变其“低贱”的社会地位。虽然雍正年间废除“匠籍”、乐户等贱民身份,但是需要很长时间才有考试的资格。乾隆三十六年(1771)陕甘学政刘墫就上奏乾隆帝请求准许削籍乐户等应试捐纳,得到奏报后乾隆帝同意所请,让礼部议复刘墫,“凡削籍之乐户、丐户、蛋户、渔户、应以报官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本族亲支皆清白者方准报捐应试”[39]。由此可见,贱民即使开豁之后仍然很难参加科举考试,而优伶、皂隶等贱民阶层更是从法律上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出于改变地位获取平等的心理,贱民冒充良民冒籍应考的事例在乾隆朝时有发生。尤其到了乾隆朝晚期,这种身份冒籍变得异常频繁。乾隆五十六年(1791),根据湖北学政李长森报,在当年汉阳府举行的府试中一名自称汉阳县的童生王烈,本是皂隶王鹏之子,冒籍良民应试,并买通廪生余其瑶、汪大铺为其认保,当即王烈被纠拿,两位作保廪生也一并纠治。[40]乾隆五十八年(1793)安徽盱眙县一位皂隶的孙子参加武科举考试,当即遭到众人反对。两江总督书麟将该县知县降一级调用。[41]
由此两例可以窥见乾隆朝贱民冒籍科举应试现象的全貌,在嘉庆朝这种身份冒籍更加严重,长随、皂隶、伶人等冒籍比比皆是。贱民在封建社会中是被人所鄙视的一个等级群体,无论从业、婚丧嫁娶还是法律地位等都与良民阶层有着较大的区别,为了改变社会地位而冒籍科举也就不足为奇了。
3 科举冒籍问题对乾隆朝的影响
3.1 土客冲突
土客冲突是冒籍所引发问题里最为严重的一项,冒籍士子和当地土著士子形成水火不容的竞争关系。在谢济世的奏折中就强调了“云、贵、川、广人才寥落,冒籍多一人,则土著更少一人”[42]的现实状况。广西学政鞠恺也向乾隆帝上奏曰“嗣因冒籍纷纷,有妨土著”[43]。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广东布政使姚成烈奏报当地土客冲突,由于大量寄籍的士民或者是因为烟户册内仍记录其原有籍贯未改,或者是因为在其籍贯原籍还有一些远祖亲戚及少量田产,这就给了土著生童攻讦寄籍童生“原籍未除,有原籍可归”的口实,造成了土著童生间的群相攻讦。然而当地地方官也并不详细查明寄籍的童生是否确有原籍可归,是否在原籍有嫡系亲属或近祖之田墓、财产,单纯地强令寄籍的童生回赴原籍应试,即使报捐已久贡监生也都取消其资格,一并判回原籍考试,因此也就导致了土客之间彼此争讼不已,此种做法既对当地科场考试无益,又进一步加深了土客之间的矛盾[44]。
以上事例反应出了冒籍者土著生童所攻讦的事实,体现了本地士子和冒籍者的尖锐矛盾。在心理层面上形成了外来人与本地土著的相互抵触的心理,每当客籍童生呈请入籍考试时,虽年限业已相符,土著生童也往往以身家不清相攻讦[45]。这种情况发生很多,而且需要皇帝下旨才能顺利入籍。这种相互攻讦加剧了土客之间的矛盾与心理的隔阂,也成为了影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加深了地域之间的文化分野,从长远看影响了科举自身的发展。
3.2 文风衰退
冒籍对于当地文风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江浙一带的冒籍士子虽然冒籍广西等省考试,但是平常的学习、生活、文化熏陶等都是在江浙家乡所完成的,这一点对于所冒籍地的文化提高没有任何的益处,只会加剧当地土客冲突,并导致土著士子仕进无门。
学政鞠恺在奏折中提到这些冒籍广西的士子都是学问平常之人,虽然当地文风可能不如江南兴盛,但是按照分省定额、就地取才的原则,土著士子还可一心向学,努力读书,逐渐带动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但是当地学校都被冒籍者占据,土著生童希求中式会更为困难,“以国家论秀育才之地为若辈行私舞弊之场,以彼地寡廉鲜耻之徒妨此地向学进身之路,于文教士风所关非细”[46]。亦如乾隆十二年(1747)江西德化县县令钱某在县试时滥收冒籍,有庠士赴督学告发此事,在舆论的压力下钱县令因论去职,新任知县大力整顿了当地冒籍问题,收到了“冒籍彻清,人文蔚起”的效果。
乾隆帝对于跨考冒籍所引发的文风日糜的问题也很看重,常言冒籍等弊端关乎风气人心。除了禁止冒籍跨考外,乾隆帝还从增加本地名额逐渐振兴当地文风的方法入手。他希望振兴文教广收人才,严禁冒籍跨考,“然后学校正而士习端,文教彰而人才盛矣”。乾隆帝之所以大力防止江浙士子冒籍边地,并对边省冒籍之事宽松对待,就是希望边省通过自己培养士子而振兴当地文风,兴文教、广人才,达到平衡科举资源的最终目的。
3.3 腐败滋生
冒籍因属违规之举,故士子常向廪保、县学、府学、乡试考官等送礼,以求核查通过,而考官也乐得收受士子所送之礼,对冒籍士子睁一眼闭一眼,致使冒籍问题日益严重,并催生了腐败。廪生保结士子就多有勒索规礼弊端,正如御史范棫士奏顺天乡试情景一样“南人冒顺天籍学分,由北贝中式者颇多,其中变更姓名弊端百出。本地廪生借此网利,滥行保结”[47]。毛升芳在《冒籍纪实》一文中载“倘法久渐驰,奸人乘间倖冒,而贪贿潜谋者复佐之,将使弊窦更丛,又烦攻讦之劳矣”[48]。因此乾隆帝要求在各童生派保之后,各学政留意核查廪保及童生,防止“私自认识廪保”或者“贿嘱派保”[49]以致滋生弊端。
但是腐败弊端并没有铲除,乾隆四年(1739)署理福建省巡抚布政使王士任奏报,革职发审的漳州府知府王德纯,其曾收受闽县人冒考武童何承玉贿赂,得赃银五百二十两[50]。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所发生的丁泗冒籍案中,廪保就从中渔利,滥保丁泗,以致事发被黜革[51],以上种种均体现了士子冒籍问题引发的负面影响。
4 乾隆朝对于冒籍问题的防范与惩治措施
4.1 廪保制度的延续
廪保制度虽有不足之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范冒籍的作用。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一月,贵州乡试之时就有安顺府学廪保宣文达、赵子英二人揭发清安县童生周家猷、王锡龄、熊澍等冒籍安顺府籍入场考试[52];乾隆四十二年(1777)贵州举行乡试之时,廪保夏繁廪称,“所保童生叶重华细访系隔府冒考之人,即交提调官讯究”[53];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四川乡试时,廪保供出温江县武童李国柱、彭县武童全体和实系冒考[54]。一些廪保虽为士子开了冒籍的方便之门,但是由于清代各朝都注意对廪保制度的不断强化与调整,这项制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冒籍问题,使部分冒籍者无法应试,保证了考试的公平。
4.2 审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审音制度在康熙时期已经初步建立,到了雍正时期,审音制度相对完善,先由县里审音,确定士子资格后,才将身份证明送到府里备案成册。乾隆十年在审音基础上,设立审音御史,并同知县、府丞一同审音,这样三四个人一同审音,且“顺天府属州县及直隶天津府俱照大宛二县之例,于试前审音,并取具廪结存案”[55]。
乾隆帝要求各地审音御史严格审音,杜绝南方士子冒籍顺天的问题。他认为自己百忙之中引见一人都能立刻辨别出其音调籍贯,何况各地审音御史呢?乾隆帝认为冒籍科举出仕“非但政体有关,且筮仕之初,即公然习为欺伪,其于世道人心,所系非浅”[56]。可以说在乾隆年间审音制度已经逐步完善,并在嘉庆和道光两朝得到很好的执行,如嘉庆十二年(1807)朝廷派出御史达德和郑士超二人去贡院会同府丞审音,收到较好的效果。
但审音制度也同样存在着某些弊端,“有些南籍御史对冒籍南人‘审音’不很严格,有些御史不愿意为‘审音’得罪别人,听出了南方口音也故意放行”[57]。当然因为乾隆帝一再强调审音制度的重要性,这种情况少有发生,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音制度的某些缺陷。
4.3 严格的惩罚措施
根据《大清律例》规定“顺天府考试审音之时,究出冒籍情弊,将本生及廪保俱照变乱版籍律仗八十,廪保仍革去衣顶知县教官。如审音不实滥行申送,俱照徇私例交部议处,受财者计赃从重论处”[58]。就乾隆朝来看,对于冒籍的处罚尚属严厉,也起到了防范冒籍的作用。
乾隆二十一年(1756)顺天乡试发生冒籍案,乾隆帝果断处理,要求严行查办,将没有呈首的冒籍者及不严格纠察之官员一同黜革,“岁科考童生冒入大宛等县者、贿保之廪生,及申送之教官、审音收考之州县,俱参革议处”[59],并“暂停南北岁科两试”。乾隆帝认为“此等冒籍生员即永停乡试,亦不为过”[60]。至此对冒籍的考生,形成了黜革功名、仗八十、停乡试等一系列的处罚措施。
在稽查与惩处士子的同时,对于官员的惩处力度也不断加大,一旦发现冒籍者将原送考官、收考官、出结官、学臣、地方官等一并治罪[61],对于顺天乡试冒籍出结之州县官、收考之国子监官严加议处[62],而对于自身为冒籍的官员或者自己子弟冒籍者“本生斥革,该员革职”[63]。对于士子和官员冒籍的惩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慑作用,冒籍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但是随着国势日渐衰落,在乾隆朝以后惩戒机制形同虚设,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5 结语
科举制度发展到乾隆年间已经到了它的式微期,虽然统治者想方设法进行补救,但却无济于事。冒籍问题的发生及难以根治性反映出科举制度自身所存在的漏洞。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人口流动性加大,使得应试士子的籍贯管理成为难点。以乾隆朝为代表,虽然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以整顿科场且起到一定效果,使得天下士子对于冒籍应试有所畏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国力的衰微,冒籍之势已无法遏制,士子冒籍应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体现出科举制度走到末世的悲哀,而新的教育制度也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应运而生。
[1]夏卫东.论清代分省取士制[J].史林,2002(3):47-51.
[2][45]王日根,张学立.清代科场冒籍与土客冲突[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1):69-73.
[3]曹永宪.明代徽州盐商的移居与商籍[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1):32-38.
[4]梁仁志,俞传芳.明清桥寓徽商子弟的教育科举问题[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1):73-76.
[5]刘希伟.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商籍”考论[J].清史研究,2010(3): 83-89.
[6]王洪兵.清代顺天科举冒籍问题研究[J].清史论丛,2010:149-168.
[7]刘希伟.清代科举冒籍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8]刘希伟,刘海峰.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冒籍问题及其现代启示[J].教育研究,2012(1):141-147.
[9]素尔讷.钦定学政全书·卷三十·清厘籍贯[M]//续修四库全书(第8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686.
[10]夏卫东.论清代分省取士制[J].史林,2002(3):47-51.
[11][28][34][35][61][62][63]杜受田,英汇.钦定科场条例·卷三十五·冒籍[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2422,2423,2574,2525,2421,2422,2423.
[12][13]清高宗实录(第12册)·卷二百五十五·乾隆十年十二月癸丑[M].北京:中华书局,1985:297.
[14][47]清高宗实录(第15册)·卷五百二十二·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戊申[M].北京:中华书局,1985:585.
[15]张廷玉.皇朝文献通考·卷五十一·举士[M].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武英殿聚珍本.
[16][30][42][43][44][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嘉时期科举冒籍史料[J].历史档案,2000(4):13-33.
[17][18]清高宗实录(第25册)·卷一千三百六·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乙巳[M].北京:中华书局,1985:589.
[19]陈笃彬,苏黎明.泉州古代科举[M].济南:齐鲁书社,2004:249.
[20]唐赞衮.台阳见闻录·卷下·额定乡试中额[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91.
[21]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四十八辑,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三十日,安徽学政戴第元奏折[M].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289.
[22]素尔讷.钦定学政全书·卷三十·清厘籍贯[M]//续修四库全书(第8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685.
[23]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七十一辑,乾隆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陕西学政邱庭漋奏折[M].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525.
[24]清高宗实录(第15册)·卷五百六·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庚戌[M].北京:中华书局,1985:395.
[25][26]清高宗实录(第15册)·卷五百三十三·乾隆二十二年二月戊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5:726.
[27][37]昆冈,李鸿章.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四〇·礼部贡举·申严禁令[M].光绪二十五年八月石印本.
[29][51]昆冈、李鸿章.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十一·礼部·学校·生童户籍[M].光绪二十五年八月石印本.
[31]清高宗实录(第11册)·卷一百八十四·乾隆八年二月甲午[M].北京:中华书局,1985:375.
[32][33]王钟瀚,校.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5911,5911.
[36]昆冈.钦定大清会典·卷九十四·内务府·会计司[M].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38]昆冈.钦定大清会典·卷三十二·礼部·贡院[M].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39]清高宗实录(第19册)·卷八百八十六·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庚辰[M].北京:中华书局,1985:873.
[4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下)[J].历史档案,2003(1):48-61.
[41]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八[M].清同治十一年湖北谳局辑刊本.
[48]邹锡畴,等.乾隆《遂安县志》卷十·艺文·毛升芳·冒籍纪实[M].清光绪十六年活字本.
[49]昆冈,李鸿章.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八十六·礼部·学校·童试事宜[M].光绪二十五年八月石印本.
[50]清高宗实录(第10册)·卷一百七·乾隆四年十二月壬寅[M].北京:中华书局,1985:603.
[52]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十九辑,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贵州学政李敏行奏折[M].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670-672.
[53]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三十八辑,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十二日,贵州学政刘校之奏折[M].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333.
[54]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四十二辑,乾隆四十三年年四月二十三日,四川学政刘锡嘏奏折[M].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755.
[55]清高宗实录(第14册)·卷四百三十九·乾隆十八年五月甲申[M].北京:中华书局,1985:720.
[56]清高宗实录(第21册)·卷一千三十七·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己丑[M].北京:中华书局,1985:900.
[57](日)平田昌司.清代鸿胪寺正音考[J].中国语文,2000(6):537-544.
[58]李宗昉.钦定大清律例·卷八·户律·户役[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191.
[59]清高宗实录(第15册)·卷五百二十二·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戊申[M].北京:中华书局,1985:585.
[60]清高宗实录(第15册)·卷五百三十·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壬寅[M].北京:中华书局,1985:682.
Study on Maoji i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during Qianlong’s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WANG Xueshen
Maoji was a long-lasting cheating method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ancient China.Maoji reached its zenith in the Qianlong period.It prevailed the whole Qianlong period with various causes and everchanging cheating ways.Although the Emperor Qianlong paid much attention to it and took strict measures to forbid it,whoever conducted this would be bound to be severely punished.This paper traces the concept and history of Maoji,probes its causes and classifications,and investigates its social influences and the specific methods which Emperor Qianlong took to check it,which expounds this social phenomenon by all aspects in the Qianlong period.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Pretend Birthplace to Take Examination;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mmigrants
G405
A
1005-8427(2016)04-0056-9
王学深,男,新加坡国立大学,在读博士(新加坡 138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