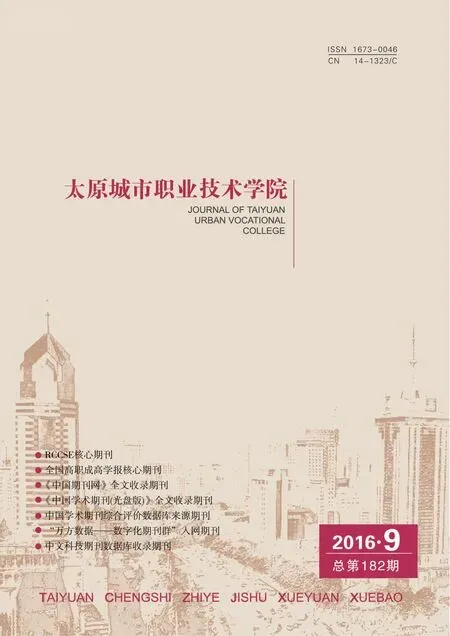论王维诗中的“闲”字
刘子凝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6)
论王维诗中的“闲”字
刘子凝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6)
我国古代诗歌中“闲”字的功用意义在逐步演变,而王维诗中出现过少许的“闲”字,能透露出唐朝一部分直属闲适恬然的诗风。这些“闲”字蕴含多层语意,深刻又富于审美意蕴。且“闲”字包含着王维融通的佛禅理趣,使其诗之“闲”与其人之“闲”相映成趣。
王维;诗歌;“闲”字
一、“闲”字的功用演变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闲”字之功用意义在唐前后出现明显差别。先秦两汉诗歌中的“闲”,多融入儒家匡正修身的思想。诗人往往于内心虚设一个至高至虚的精神高度,强调在自由、平静中寻求“自得”的一种生活状态。魏晋南北朝作为人性觉醒的时期,诗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先秦两汉带来的身困苦恼,精神层面得到较大松绑,情感本体重新独占高地。加之受“玄学”之风的感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开始疏离政权,即便身困也可以让心趋于“闲”的状态。诗人逐渐抛开无法撼动的“修德”、“求志”目的,开始依托一些对象寄情,不再强调绝对的退隐,而是偏向“隐”与“闲居”于朝廷和集市中。也正所谓“身在庙堂之上,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川”,“闲”已经作为一种审美情趣而独特存在。到了唐代,禅宗思想对诗人的人格产生着深刻影响。佛教发展到了唐代,已经消解了繁难的经义、戒律,而是引导诗人将佛理带入日常生活,达到完美的融合境界。唐代时的诗人自身具有的性情也可视为可追求的佛性,以平常之心作为平和圣洁的心境,从而逐渐塑造出“闲身”的审美品格,佛性便成了自身对“闲适”生活审美体验、用世智慧。因而王维诗中的“闲”字,包含丰富的意趣与浓厚的意蕴。
二、“闲”字的语意分析
据笔者略作统计,王维各类诗体中出现“闲”字大约有35次,此语符使用频率虽然不算高,但在诗中有着极丰富的内涵。兹罗列如下:
(一)“闲”为防之意
许慎的《说文解字》析“闲”的造字结构,云:“从门中有木,乃以木拒门也。”而“闲”又为会意字,可推测它表达的是对外力的一种抵抗。《周易·乾·文言》:“闲邪以存其诚。”此“闲”,正是“防”的意思。在唐前的作品,“闲”的此语意运用十分普遍,如陶渊明的《闲情赋》的序言说:“初张恒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定情”“、静情”都是与“闲情”文义互释,都是意在防止浮躁杂乱,摆正心态,清净心灵。此类“闲”字常与“心”组合,或与“坐”、“乘”、“寂”等连用,构成独特的诗歌意象,如《青溪》:“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留别山中温古上人兄并示舍弟缙》:“荆扉但洒扫,乘闲当过拂”。《答张五弟》:“终年无客常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闲”。《戏赠张五弟三首》其一“:窗外鸟声闲,阶前虎心善”。《春日上方即事》“:人北窗桃李下,闲坐但焚香”。诗的意象带有强烈的个性特点,“闲”的防之意能够体现出诗人的风格。正如袁行霈所说:“诗人有没有独特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立了他个人的意象群。”而“闲”字这一意象群带有王维的个性特点,含有某些禅悦之趣。
(二)“闲”字为无事、闲暇之意
(三)“闲”字为清静之意
王维诗中的一部分“闲”字是清静之意,通常出现在一些稀疏、冷清之景里。如《归嵩山作》:“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登裴秀才迪小台》:“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登河北城楼作》:“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这些“闲”字略有寂寥、落寞的意味。王维是个善于交心之人,因而与许多友人建立下深厚的情谊。但由于工作的调动,王维身边的友人不得不频频与其分别,情谊深厚而离情难别,“闲门寂已闭,落日照秋草。”(《赠祖三咏》)送别途间的景色不禁被王维一种失落的情绪所渲染,多了一丝哀伤悲凉的感觉。独自一人也不免生出孤寂的情感,所见之景也变得寥落稀疏,“闲门秋草色,终日无车马。”(《过李楫宅》)“向晚多愁思,闲窗桃李时。”(《晚春归思》)随时日渐久,笃信佛教的他逐渐看淡这些世间的离合常态,于是王维习惯在想念里藏着一抹清浅的惆怅,“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即使感伤仍抹之不去,但王维能用诗中的“闲”字淡化自己昔日孤独抑郁的浓重感。《古尊宿语录》曾云:“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既能澄心观照,便使王维的落寞又逐渐转变为一种恬然,而创造出了空阔、清净的境界。如《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秋色有佳兴,况君池上闲”。《林园即事寄舍弟紞》:“青簟日何长,闲门昼方静”。《沈十四拾遗新竹生读经处同诸公之作》:“闲居日清静,修竹自檀栾”。这些“闲”字都微妙地传达出了诗人复杂的情感意绪。
三、“闲”字蕴含佛理禅思
王维是一个深受佛禅思想影响的诗人,他的诗歌富于禅趣。王维诗歌中造境都透着禅理的意味,清人沈德潜也曾说王维“不用禅语,时得禅理”。王维诗中用的“闲”字直接与禅理有关联。如《饭覆釜山僧》:“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赋得秋日悬清光》:“圆光含万象,碎影入闲流”。《寄崇梵僧》:“落花啼鸟纷纷乱,涧户山窗寂寂闲”。《西方变画赞》说:“心王自在,晚有皆如。”“如”即“空”。佛教认为诸法之体性虚幻不实,是王维自所谓的“法无明相”(《为干和尚<进注仁王经>表》)。即是说万物无实,不能确切地反映,而自在空虚的环境里顺化,有空灵澄明之态。可见,王维在佛教义学中接受了“空”理,以上“闲”字皆体现出超世的境界,渗透佛法的性空之道。王维借助具体的艺术形象道出超尘脱俗的禅意,使得心与天地宽广而闲适。心境与空旷宏大的自然之境早已浑融为一体,心性与清寂浑圆的真如本体无意契合。尤如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致,让人不易察觉,十分耐人寻味。正是达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空非色,即色即空的“悟境”。
王维信佛与他的政途周遭有紧密关联。王维开元九年擢第,又担任了太乐丞一职,不久却受“伶人舞黄狮子”一事所累,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大约开元十五年,又改官淇上。仕途的失志令王维萌生隐遁的念想,于是他便选择从禅师学佛。在开元二十三年春夏间,有幸受丞相张九龄引荐,出为右拾遗,王维的政治抱负又重燃薪火。然而次年张九龄遭罢相、贬谪,李林甫趁势独揽大权,政治日趋黑暗腐败。面对此景,王维甚是失望,他愈发感到心累,在诗中多次透露出黯然隐退的情绪,希望从佛而摆脱尘世的束缚。天宝年间,王维便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在无奈的外在压迫下,王维表现出“不自在”的厌倦感,于是他在诗中寻求闲适,而他追求的“闲”,是参悟自然禅理、静心见性的方式。佛教有“真如缘起”的思想,依照佛性论的观点,众生先天具有真如佛性,却为世俗的“妄念”所隐覆,则不显;若排除“妄念”,则自性可成。所以王维诗中的“闲”字,可以说是他拂尘见性后的顿悟,也使得他在真如佛性里寻得自然万物之真趣。如牡丹花的色彩仿佛能在娴静状态下流动起来,“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红牡丹》)梨花的飘落好似被冷落与草为伍,闲愁而落寞,“闲洒阶边草,轻随箔外风。”(《左掖梨花》)碧波映衬着的月,在澄净的夜空变得清朗闲致,“澄波澹将夕,清月皓方闲。”(《泛前陂》)用“闲”字观照了自然万物的生动之态,获得了“那个常住不灭的本体佛性”,在闲适状态中感受到真如的永恒存在。
[1]庄子.齐物论[M].[晋]郭象,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汉]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2013.
[4]袁行霈.李杜诗歌的风格与意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傅绍良.王维“闲”“空”意趣的禅学再确认[J].文史哲, 2002(3).
I206
A
1673-0046(2016)9-02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