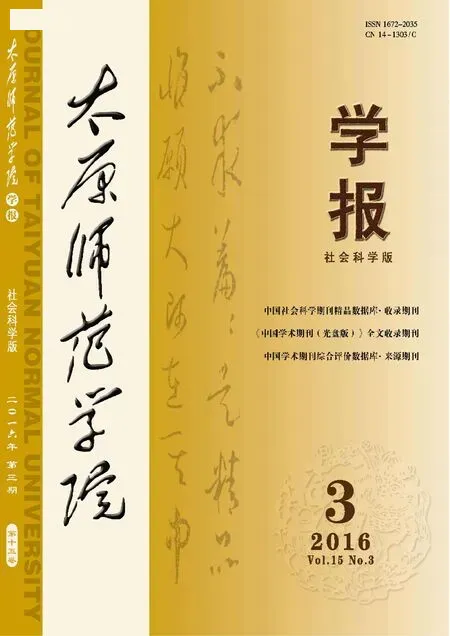论蜀地地理环境对苏轼人格形成的影响
韩 凯
(山西大学 文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文学】
论蜀地地理环境对苏轼人格形成的影响
韩凯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一地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二维度,对当地士子的人格养育往往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蜀地旖旎多姿的山川景物对苏轼“妙赏”风神及故土怀归情结的形成,重儒多气、萧散风流的人文环境对其君子人格、宦隐情结的形成极为重要。
[关键词]蜀地;地理环境;苏轼;人格影响
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作为生存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地士子主体风神养育的巨大影响,可借用苏轼表述江浙自然风光对当地居民影响的诗句“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绿。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儿贩妇皆冰玉”[1]1344来说明。
一、蜀地自然地理环境对苏轼人格形成的影响
苏轼故乡眉州风光旖旎,令人流连,唐人贾岛在《送穆少府知眉州》一诗中评价道:“剑门倚清汉,君昔未曾过。日暮行人少,山深异鸟多。狖啼知峡雨,栈尽到江波。一路白云里,飞泉洒薜萝”[2]181。眉州多秀山佳水,据笔者统计《太平寰宇记》所记,眉山共有多棱山、龙鹤山、鼎鼻山等名山13座,平羌水、洪雅川、鱼凫津等名川13条。[3]钟灵毓秀的蜀地自然环境培育了苏轼以诗意态度品察人生的“妙赏”风神及故土怀归情结,故土山川是其一生难以抹去的眷恋,如他在《寄黎眉州》中写道:“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1]684。
冯友兰先生认为“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底感觉”[4]612,苏轼的“妙赏”表现在以诗意的态度品察外在世界,呈现出与天地合一、与外世和谐的宏大生命境界。受蜀地秀美山川影响而形成的山川风物之赏,构成了苏轼“妙赏”风神的重要一环。其山川之赏,是一种“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5]17的境界,是其物我合一的齐物思想的重要外在表现,如他在《江西一首》中说:“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舟行十里磨九泷,篙声荦确相舂撞”[1]2050。再如其作于宋哲宗元祐元年(笔者按:本文苏轼诗作系年,从清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巴蜀书社1985年版)的《道者院池上作》:
下马逢佳客,携壶傍小池。清风乱荷叶,细雨出鱼儿。井好能冰齿,茶甘不上眉。归途更萧瑟,真个解催诗。[1]1438
此诗以风雨中道者院池景物为妙赏对象,荷叶随风而舞,鱼儿伴雨而出,与天地景物合一的无我之境中,苏轼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
苏轼山川风物之赏中有较多“以静譬动”、“以动譬静”的作品,如作于宋仁宗嘉祐五年的《鳊鱼》首二句:“晓日照江水,游鱼似玉瓶”[1]78,以静态“玉瓶”比况动态“游鱼”,极言江水澄澈。再如作于宋哲宗元祐六年的《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其五)首二句:“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抱山斜”[1]1747,用“抱”字将静态芳草写活,以动譬静,譬喻炼字间显露苏轼对自然万物细致、诗意的体察态度。
蜀地秀美的自然环境是苏轼乡隐情结形成的重要外在因素之一,故土怀归情结时常萦绕在其脑海中,成为其重要的潜意识。宋仁宗嘉祐四年,二十四岁的苏轼随父离眉赴京,刚离眉,已有怀乡作品出现,如《初发嘉州》前四句“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1]6。作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诗作《过岭二首》(其一):
暂著南冠不到头,却随北雁与归休。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丘。当日无人送临贺,至今有庙祀潮州。剑关西望七千里,乘兴真为玉局游。[1]2426
此诗作于苏轼北还过大庾岭时,诗人将乘兴游岭当作成都玉局观之游,登岭遥望故土之关,足见其故土怀归情结。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受蜀地自然环境影响所形成的故土意识,在其仕宦任职中出现了变体,即“心乡”情结。“心乡”便是“此心安处是吾乡”[6]579,反映其坦然达观面对人生失意、随缘而适的旷然风神,如《次韵韶守狄大夫见赠二首》(其一)诗句:“无钱种菜为家业,有病安心是药方”[1]2407。再如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的《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属金山,故作此诗与金山元长老》:
魏王大瓠无人识,种成何翅实五石。不辞破作两大樽,只忧水浅江湖窄。我材□落本无用,虚名惊世终何益。东方先生好自誉,伯夷、子路并为一。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与稷。暮年欲学柳下惠,嗜好酸咸不相入。金山也是不羁人,早岁闻名晚相得。我醉而嬉欲仙去,傍人笑倒山谓实。问我此生何所归,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1]1277-1278
题目点明其“心乡”所在:“蒜山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诗句中多提欲归心乡语义:“问我此生何所归”,“招此无家一房客”。而其欲归心乡的原因,在于仕宦浮沉经历。“我材□落本无用,虚名惊世终何益”,由此可见苏轼“心乡”是其超越功名从困境中解脱的重要途径。
考察苏轼仕宦经历,密州任时所筑超然台、黄州贬所所筑雪堂、颍州任时所筑择胜亭等等,都是“心乡”处所,体现其超越仕宦波折浮沉的“玄心”品质,如苏轼谓超然台“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7]351,谓择胜亭“既濯我缨,亦浣我裳。岂独临水,无适不臧”[7]577,谓雪堂“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8]87。
二、蜀地人文地理环境对苏轼人格的影响
蜀地“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9]2的人文地理环境,使“‘好文雅’成了巴蜀的传统”[10]2,对苏轼人格养育也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依笔者之见,“文雅”很好地概括了蜀地道任精神与风流精神合一的人文环境。
自西汉文翁兴学儒教后,“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11]1191-1192,儒家思想一直是当地士人秉持的主流人生态度。儒家“以道自任”的奋励精神,“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12]38的行事准则,使蜀地士人形成了道任重义的人文传统,如扬雄重义轻利的人生选择:“少而好学……为人简易佚荡……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帘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13]406-407陈子昂直言敢谏的政治气节:“臣闻上有圣君,下得直言,贱臣敢越次冒昧以奏……请为九等税钱以市骡马,差州县富户各为屯主税钱者,以充脚价……臣伏审计便宜,体大非一二状俱尽。陛下若以此奏非虚,或可采者,请勒臣付所司对议得失,然后具条目一一奏闻。”[14]199李白匡扶社稷的雄志:“此乃猛士奋剑之秋,谋臣运筹之日。夫不拯横流,何以彰圣德;不斩巨猾,无以兴神功。”[15]1210这些都与蜀地“刚悍生其方”[3]1461的人文环境有关。
蜀地文化继承发扬儒家道统精神,不觉间滋养了苏轼的君子人格,突出表现在其“以手为口”的笔谏精神。“以手为口”出现于苏轼《游沙湖》:“余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8]13。所谓“以手为口”的笔谏精神,指苏轼在其创作中呈现出的以道自任、针砭时弊、特立高洁、不随时移的骨鲠浩然之气,如宋神宗元丰三年正月所作《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其二):
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1]1030-1031
此诗虽名为题画诗,然由题画起兴,直指王安石新政中“青苗”诸法侵夺民利处,直言对新法不满之情。
再如宋哲宗元祐六年三月所作《和林子中待制》:
两翁留滞各皤然,人笑迂疏老更坚。共把鹅儿一樽酒,相逢卵色五湖天。江边遗爱啼斑白,海上先声入管弦。早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啸老斜川。[1]1763
面对元祐年间党争乱局及其“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宋史·苏轼传》)的政治处境,苏轼并未选择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而是坚守自己的高洁之志,“迂疏老更坚”明言其与旧党执政主流不合作的坚定意向。以“陶潜”自况,“归去”、“老斜川”之愿寄托着其对旧党执政者不务江山社稷而唯事党争内斗的不满之情。
苏轼“以手为口”的笔谏精神,集中体现着儒家君子人格中刚健自砺的一面,“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16]1668,“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16]1669。蜀僧祖秀曾赞美苏轼高尚的政治人格:“夫子之道,为后稷、伊尹,可以致其君于尧、汤。时议将加之于斧钺,而夫子尤讽于典章,海表之迁,如还故乡。”[17]6
论述蜀地人文环境对苏轼人格的影响,风流精神是不容忽视的一维。蜀地士人在“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列眉通衢,平直广衍,夹以槐柳,绿阴翳然”[2]184的自然美景陶冶下,形成了萧散自由的主体风骨及美学追求。寒暑四季,春发冬藏,在蜀人的生活世界里,都可以成为其欢会游赏的对象,“尔乃其俗,迎春送腊,百金之家,千金之公,乾池泄澳,观鱼于江。若其吉日嘉会,期于送春之阴,迎夏之阳……厥女作歌,是以其声呼吟靖领,激呦喝啾,户音六成,行夏低徊,胥徒入冥”[13]35。蜀人旧有“赏梅节”,“亭之上曰芳华楼,前后植梅甚多。故事,腊月赏梅于此”[18]837;有踏青习俗,“眉之东门十数里,有山曰蟆颐,山上有亭榭松竹,山下临大江。每正月人日,士女相与游嬉饮酒于其上,谓之踏青也”[1]161;有蚕市,“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1]162-163。在萧散风神影响下,释、道二教在蜀地极为繁盛,“仙宫佛院,成都颇盛……殿宇廊庑,华丽高敞。观如元天、云台,寺如昭觉、金像、净居、净因、金沙,庙如昭烈,宫如青羊,俱不减两都规模,足供游眺”[9]20。
蜀地浪漫萧散的人文环境使散逸放朗的生命状态成为苏轼仕宦追求目标之一,促成了其宦隐情结的产生。苏轼宦隐情结,是其生命自适渗透作用功名意识的产物,体现苏轼应对仕、隐二端矛盾的自觉调适,反映其新型生活态度,追求“隐吏”境界,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诗句:“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1]341。又如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十一月的《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过旧游》: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更欲洞霄为隐吏,一庵闲地且相留。[1]652
欲为隐吏而“一庵闲地且相留”,体现受功名意识影响的苏轼对生命“闲地”的向往与追求。
隐吏境界首先是志性自然、偷闲疏懒的境界,反映生命萧散风神对功名追求的渗透及改造。如作于宋神宗元丰八年十二月的《次韵答李端叔》:
若人如马亦如班,笑履壶头出玉关。已入西羌度沙碛,又从东海看涛山。识君小异千人里,慰我长思十载间。西省邻居时邂逅,相逢有味是偷闲。[1]1408
此诗作于苏轼以礼部郎中还朝期间,“西省邻居时邂逅”二句,及其同为元丰八年还朝后所作《次韵穆父舍人再赠之什》中的“凤池故事同机务,火急开樽及尚闲”[1]1407,都反映出入直西省后的苏轼内心对闲逸安恬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偷闲”、“及尚闲”反映了苏轼融合功名意识与生命自适的宦隐选择。
其次,隐吏境界是政治自保,全身避害的境界,是苏轼面对仕宦风波自觉应对之策。其作于宋神宗元丰八年十一月二日后《次韵王定国得颍倅二首》(其二):
滔滔四海我知津,每愧先生植杖芸。自少多言晚闻道,从今闭口不论文。滟翻白兽樽中酒,归煮青泥坊底芹。要识老僧无尽处,床头牛蚁不曾闻。[1]1394-1395
阔别京师近十五年的苏轼(笔者按:苏轼自宋神宗熙宁四年七月离京至宋神宗元丰八年十二月抵京,期间虽有熙宁十年短暂还京,因仅止于京郊,未能入都门,故笔者认为其仍在野,非严格意义上还京)面对即将进入的权力中心——西省,并未在此诗中展现出大鹏得以展翅、致君尧舜之志有望实现的欣喜激动之情,反而“自少多言晚闻道,从今闭口不论文”,欲过滟翻樽酒、归煮青芹的官居闲适生活,不难看出苏轼建立在政治自保意识基础上的宦隐追求。
相比自然环境的相对稳定性,区域人文环境往往随着时局变动、思想潮流演变等因素而变化调整。但由于蜀地独特的封闭式的边隅地理位置,加之古代交通不便,前蜀、后蜀政权对文化重视等因素,蜀地保留着前代正脉血液,如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所说:“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7]352蜀地呈现出独特的“孤岛文化”(笔者所言“孤岛文化”,指文化萧条时期,相对封闭的区域由于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保留并传承着前代文化的余脉,该地士子在衰鄙猥颓的时代背景下,独守刚健自砺、风流逸散风骨的独特现象)。受此孤岛文化影响,宋代蜀地文化继续呈现着骨直自砺的道任精神与萧散逸兴的风流精神相融合的特点。
祝尚书指出:“两宋蜀人多直臣、诤臣”[10]523。田锡颇具代表性,直言谏诤、关心国是、建言献策,如他在《上太宗答诏论边事》中写道:“臣之颛愚,岂足上副宸衷;臣之狂直,敢不罄尽鄙怀……若陛下省罢塔庙之费耗,回充军旅之赏给,则孰不革其怨心,孰不致其死力”[19]4-6。田锡对苏轼有直接影响,苏轼曾评其政治风节:“呜呼,田公,古之遗直也……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测之忧,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忧治世而危明主”[7]317。蜀人原先萧散逸兴的风流精神在宋朝延续,“郫邑屋极盛,家家有流水修竹,而杨氏之居为最”[18]837,“江水分流入县,滩声聒耳,以故人家悉有流渠修竹,易成幽趣”[18]840,“蜀中水陆舟车所经,凡有岩石,莫不镌佛像,岂地近西番,前代风气湔染如此”[9]10。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讲,蜀地环境对苏轼人格养育有重要作用。自然环境对其“妙赏”风神及乡隐情结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把握苏轼“以手为口”的笔谏精神、宦隐情结及诗意品味百态生活的成因,蜀地人文环境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另需注意,苏轼之所以形成儒、释、道三家思想融一的境界,与蜀地环境有直接关系,其亲近佛禅态度,早在出蜀前已露端倪,“大峨山者,普贤大士道场,西竺僧所称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第一山也。有苏稽渡,故子瞻读书处”[9]4。
[参考文献]
[1]苏轼(撰),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曹学佺.蜀中名胜记[G]//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3]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冯友兰.论风流[G]//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5]王弼,等(注),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G]//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苏轼.东坡志林[G]//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九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9]何宇度.益部谈资[G]//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0]祝尚书.宋代巴蜀文学通论[M].成都:巴蜀书社,2005.
[11]班固(撰),颜师古(注).前汉书[G]//四部备要(第一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3]扬雄(撰),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4]陈子昂(撰),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5]李白(撰),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G]//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7]释晓莹.云卧纪谈[G]//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二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
[18]范成大.吴船录[G]//宋代日记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19]田锡(撰),罗国威(校点).咸平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8.
【责任编辑张琴】
[收稿日期]2016-01-25
[作者简介]韩凯(1989-),男,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文章编号]1672-2035(2016)03-0060-04[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