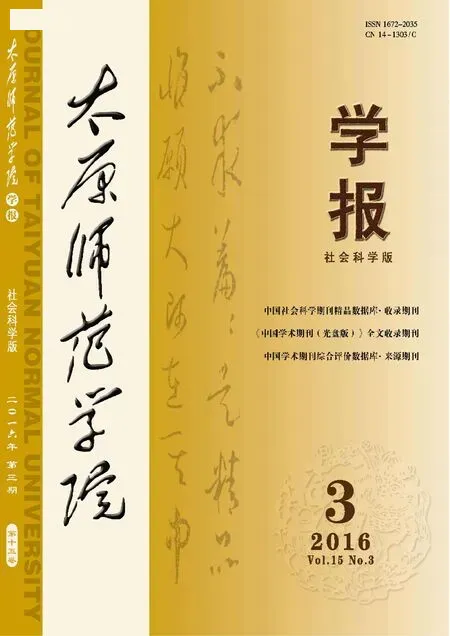“德”之下移:西周铭文中的“德”
王晓玉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文化学】
“德”之下移:西周铭文中的“德”
王晓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现存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周人之“德”经历了一个从天到王再到臣的“下移”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有层级、以“礼”为外在形式的下移过程,为“德”内化为修身的功夫提供了契机。究其原因,“德”之下移既是基于西周确立、稳固政权的需要,也是区分贵族、庶民的政治策略。
[关键词]西周铭文;德;下移;礼
“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德”是周人保有天下,定于一尊的核心观念,在《尚书》、《诗经》等文献中被反复提及。郭沫若先生认为“‘敬德’的思想在周初的几篇文章中就象同一个母题的合奏曲一样,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的确是周人所独有的思想。”[1]355进一步讲,“《周书》和‘周彝’大都是立在帝王的立场上来说话的,故尔那儿的德不仅包含着正心修身的功夫,并且还包含有治国平天下的作用:便是王者努力于人事,不使丧乱有缝隙可乘;天下不生乱子,天命也就时常保存着了。”[1]337这是说“德”在西周时兼顾修身、治国两个方面,颇有宋人所言“内圣外王”的气象。但也有人认为在那个时代,“德”还没有内化为正心修身的功夫。现存的青铜器铭文对“德”也有相当的关注,或许可以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周人之“德”提供一些线索。
一、铭文之“德”释义
现存青铜器铭文中,《大盂鼎》、《班簋》、《史墙盘》三篇较为典型地依次记录了周人之“德”。三者之中《大盂鼎》属于西周早期青铜器,《史墙盘》则为西周中期器,只有《班簋》的情况有些难辨。郭沫若将《班簋》定为成王时器、陈梦家定为康王时器,均在西周早期。也有人认为《班簋》为穆王时器,属于西周中期。故而,三篇铭文诞生的时间顺序大致为《大盂鼎》、《班簋》、《史墙盘》,这也是我们考察的顺序和基础。晚期器铭《叔向父禹篡》、《毛公鼎》等对“德”也有所涉及,意思大略相同。此外,本文所录铭文资料,有些未有定论,辨别不清,故综合参考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陈梦家所著的《西周铜器断代》、秦永龙主编的《西周金文选注》、侯志义主编的《西周金文选编》等书。
首先来看《大盂鼎》:
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乍邦,辟厥匿,匍有四方,畯正厥民,在粤御事,酒无敢酣,有柴烝祀无敢扰,故天翼临。……今我隹即刑廪于玟王正德,若玟王令二三正。今余隹令汝盂召荣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王曰:盂,迺召夹死司戎,敏誎罚讼……易女鬯一卣,冕、衣、市、弓、车、马。……盂用对王休,用乍且南公宝鼎。
以上铭文所表达的意思大概有三层:开篇交代了文王受命于天、武王受天庇佑而克商的功绩;次谈康王效法文王,封官训诰的内容,其中王对《大盂鼎》铭文中的主人公盂有五点希望,即敬而有德、朝夕进谏、勤于参加祭祀、做事情不违背天命、“敏誎罚讼”,也即《康诰》中的“明德慎罚”;最后盂谈作鼎的初衷是为祖先南公作鼎以颂扬王的美德。从“德”观念的角度来看,短短二百多字的《大盂鼎》言明的实际上是周人之“德”的逻辑转换过程:由文王之“德”授命于天到后王继承先王之德,再到王有德,臣子颂之、学之。
《大盂鼎》中虽然讲德、敬德,但对“德”的内涵并没有明确的解释。根据铭文的描述来看,王有承袭自文王的封官之德、告诫之德、赏赐之德。王对盂的训示中也希望盂能“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敏誎罚讼”,显然“德”被周人视为一个有意识想要达成的目标。“敬德”、“秉德”等在《尚书·周书》中也曾反复出现,郭沫若先生认为:“德的客观上的节文,《周书》中说得很少,但德的精神上的推动,是明白地注重在一个‘敬’字上的。”[1]336也就是说“敬”是精神上的功夫,那么这里王所谆谆教诲的“德”是否上升到了精神层面呢?
从文字上来看,王的训示真正可以落实的是讽谏、入宗庙、畏天威、慎罚这些为官之道,更确切地说是政治上的行为,倾向于一种政治诉求,与个人修身还有很大的距离。如果将“求懿德”看作彼时君臣内心的强烈意识,那么,他们的为政举措似乎可以视为“德”之器。问题是这些落实的具体行为的内里是否就是周人念兹在兹的“德”呢?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德”的源头问题,这在《班簋》、《史墙盘》铭文中有所体现:
彝昧天令,故亡,允哉显,惟敬德,亡逌违。(《班簋》)
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上下,迨受万邦(《史墙盘》)
《班簋》记述了毛公讨伐东域凯旋而归这一事件,并认为这场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是敬德,勿违天命。《史墙盘》也道出了“德”之本源在天,并强调上帝降德的同时也送给文王能够辅佐他的重臣,因此他才能匍有四方。也就是说,这两篇铭文中都非常明确地表明“德”不仅是周取代商的重要依据,也是周人历代相传的“保命符”,“德”逐渐与君臣融为一体。关于此,李学勤先生也曾指出《史墙盘》中,“盘铭二百八十四字是文气贯通的整体,前段固然是颂扬历代周王,同时也强调了‘大屏’、‘俊民’、‘左右’即辅佐诸臣的作用,段末更归结于君臣和谐才能得到‘天’的保佑,这就和铭文后段关于史墙各代祖先怎样臣事先王的叙述互相呼应”[2]157。
以上铭文的叙述中,“德”有两个指向,依稀可辨,体现在“德”从天到王再到臣的“下移”过程中。
其一,天之“德”。
这里,我们将天降之“德”称为天之“德”;“德”降于文王,文王便与天合为一体,这种假设为周政权合法性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周建国伊始,急迫地需要为以武力争夺来的天下提供解释,来确保政权的稳定、长久。关于这一点,李山先生早已指出周初诗歌中就有“一道隐形的精神索脉”,“诗篇着意强调周邦获胜的根本原因及胜利本身所具有的含义,乃是由于对‘天命’的膺承时,有一个极其明确的观念意识,那就是,周人并不想将自己的胜利纯粹认定为暴力的成功”。[3]234-235
“德”的提出正是周人为自己寻找合法性依据,重建历史的必然结果。
其二,后天习“德”:人力与“畏天威”的结合。
“德”不光本于天,也可“备”于我,这点在后王、君臣的身上体现出来。后王向先王学习,畏天命、求懿德的同时,他也有义务将“德”传递给身边的人,因为君王也需要有德的大臣辅佐,这正是李学勤先生指出的和谐的君臣关系才能得到“天”的庇佑。铭文中描述王对臣子的训示和时王学习文王之德这类事件,正是“德”下移到历代君臣身上这一过程,更表明了“德”逐步融入到周人的治国理念、政治行为之中。需要注意的是,“德”虽然下移并且靠人的主观努力可以得来,但这个“德”的功用并没变。不论“畏天威”是执政者的政治说辞还是实际行为,都说明“德”作为周王朝的外在约束力的地位已然不可动摇,“德”仍然关乎周人的命运。
二、德与礼:“德”下移的具体方略
天之“德”的唯一功用就是使文王享有四方,究竟什么才是天之“德”,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后王在治理国家时,对于“德”也非生而知之,他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这样本体论意义上的德,或者说一个抽象的“德”,要想下移到更多的人,就必然要形成一套有据可行的规范。
王国维先生说:“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于此。”[4]135“礼”是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的一套完整而严密的行为规范,周公的心血大体在此,它之于周人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礼是否是“德”的承载物呢?郭沫若先生讲:“‘德’字不仅包含主观方面的修养,也有客观方面的规范——后人所谓‘礼’都是包含着的。”[1]336杨向奎先生则认为:“礼既不是德的派生物,也不是‘古代有德者的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下来’……相反,正好是礼的规范行为派生出德的思想体系。德是对礼的修正和补充。”[5]331“周公对原始礼仪有过加工,他以为这种待人敬天的礼以及行礼中的仪容,应当充实德的内容,礼不应当仅是物品的交换,仪也不应当仅是外表的仪容,他把它们伦理化、美化。”[5]332有些情况下,“西周春秋间礼和德的含义是相通的”[5]332。
不论是郭沫若先生还是杨向奎先生,实际上对“礼”与“德”的结合这一点是认同的。上面郭沫若先生已经提到,文献中对于“德”的客观节文讲得很少,但被神秘化的“德”又必须被具体化,才能有迹可循,渗透到“礼”中,恰恰就成为“德”下移的一种最理想的策略。
粗略地来说,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所循之“礼”有所差别。由于考虑和处理的问题不同,每个人所需具备的“德”也不同。通过“礼”即可作出区分,天子修“德”在保有四方,庶民修“德”在家庭和睦,不同的“德”灌注在“礼”中,这样一来,自上而下的“德”是有层级的,在上位者有高于下位的“德”,对下也可以勉励和督促,铭文中正体现了君对臣的督促,“天命”则是对君的最有力的督促。这也就是“道德”团体的一个粗略情况,也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状况。
上面郭沫若先生提到的“德”涉及主观方面的修养,也是一个争论点所在。许多人都认为,当时的“德”并未达到主体自觉的理性修身程度。我们认为“德”的下移过程中,“德”由外而内转化的契机确实已经形成了。
“德”下移的一个策略就是“德”与“礼”的结合,“礼”成为“德”的外在形式之一。它们的结合提示我们,人们对“礼”与“德”的认识是相辅相成的,结合现实的情理来讲,在“礼”的制约中,随着主体认识的加深,人对于“德”的认识会更加深刻,同时“礼”的遵循也将更加自觉,外在的“德”由此有了内化的契机。这样,“德”就更加贴近儒家对修身的探索了。
从铭文中我们也可看出这个契机。《大盂鼎》等铭文感情基调平和或者低沉,远没有建国初期的激情,相反颂扬王“德”、祖先之“德”的意识显露在字里行间,臣对“德”的学习显现为一种勉励的状态。《礼记·祭统》中讲:“夫鼎夫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勉励的背后,也包含着对后世子孙的期许。这些都透露出“德”地位之崇高,需要世代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这个世代相传的追求过程,足以使人们将“德”纳入到内在意识中。
三、“道德”之团体:“德”下移缘由推测
首先,“德”之下移是基于西周确立、稳固政权的需要。
武王立国之初,有一项举措很值得注意。他曾遍访先贤遗迹,分封先贤后人。这一举措一方面宣扬了周人对于贤人的重视,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他们对于政权的担忧。商一日间灭亡的事实历历在目,周人对于兴衰的认识恐怕相当深入且充满恐惧,因为他们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王朝随时可以毁于一旦。正是这种担忧让周人开始重视“德”,继而让“德”下移。
王国维先生尝论: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正在于此。[6]232
许多人对王国维先生使用的“道德”一词颇不以为然,大致认为“道德”过于狭隘,但铭文向我们传达的周人之“德”,明显趋向于上下合于“德”。可见王国维先生对于这个状态把握得相当精准,在现代语境中我们确实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汇来形容。
从王国维先生的论述中来看,周人通过立嫡、庙数、婚姻三个途径,将天下纳入到“德”这个系统中。立嫡制恐怕直接导源于皇室内部,关于分封制,李山先生在《诗经的文化精神》一书中指出“周公的分封直接起因于本族的内乱。”[3]15这样看来,西周建国伊始,担忧不仅来自外部,恐怕更多的是来自于内部。天之“德”虽然足以慑服天下人,却不足以稳定家族内部,故而也只能采用分封的办法。
然在分享既得利益来维护团结的同时,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如何保证诸侯永远臣服王室?王室又如何保护诸侯国的利益?诸侯在封地如何确立权威?也就是说,周天子和诸侯间除去天然的血缘关系,更需要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一种不断加强的认同感。特别是从政权的角度看,不论周人对天命怀疑与否,在大肆宣扬“德”为建国之本、天命所归的同时,“德”已然成了悬在周王室上方的一把双刃剑,成为来自外部的一股强大约束力。若周人无“德”,天命随时可以夺走周人的一切。
质言之,“德”的下移正是基于现实的需要,迫在眉睫。一方面西周政权需要神秘的“德”巩固政权,另一方面他们亟需“德”作为维系周人与诸侯政权的纽带。既然“德”成了周人的终极追求,与诸侯分享“德”的过程中也可获得诸侯对王室的认同,甚至使诸侯自身能够树立权威,“德”的下移何乐而不为呢?
其次,“德”之下移是贵族与庶民间的关系使然,是区分贵族、庶民的政治策略。
铭文中关于“德”的描述,实际上仅存于君臣等贵族之间,并未涉及庶民。王国维先生也曾提到“礼不下庶人”的问题,“有制度、典礼以治,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使有恩以相洽,有义以相分,而国家之基定,争夺之祸泯焉。民之所求者,莫先于此矣。”[4]134“所谓德者,又非徒仁民之谓,必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4]135王国维先生的看法可谓高屋建瓴。周人重视农耕,农耕即是庶民的物质支撑和实际慰藉所在,而君臣和谐、国家稳定正是农耕生活平静、安定的基本保障,故“民之所求,莫先于此”。国家对民的要求,无外乎家庭和睦,故君臣为天下表率,“使民则之”。
君臣又凭借什么成为万民的表率呢?西周初期的贵族不仅在政治体系中有着绝对的权威,也是文化上的精英。当时,王官之学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庶民本没有接触文化知识的可能。李山先生对西周立国之初的“德治”有精辟的看法:“‘德治’之所以为德治,首先在于它自动放弃暴力原则的首要性,而代之以平治天下的承诺。”[3]235
如此说来,周人从文化上着手,构建起一个庶人难以企及的系统将贵族与庶民区分开来,未尝不是一条稳固政权的良策。“德”沟通天人的性质正符合这一功能。因此,“德”之下移于国家、万民有益。
依据对“德”下移原因的推测,我们对于“德”的认识有一个新的提升。首先,西周时,“德”的下移更侧重其政治功用。这种有政治功用的“德”与庶民自身来说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或者说对于庶民没有太多的要求。其次,君臣在政权中各司其职,是有着层级关系的。既然“德”成了维护贵族权威的一个工具,天子、诸侯、卿大夫是有着不同的权威的,他们所要面对和处理的也有所差别,在政治活动中要遵守的“德”显然也是不同的,“德”之下移必然是一个有层级的下移过程。如祭祀敬天的活动中,君主、诸侯、臣子所行祭祀之礼有等级上的差别,“德”的下移也是有层级的下移,身份的差异意味着“德”的差异。
四、结语
质言之,“德”由最初的政权合法性依据逐步成为周人终极的追求。因现实的需要“德”下移的同时内涵也随之丰富,逐步形成一个以“德”为核心的有层级的、圆融的理想政治体系。这个体系成为一段时间内周王朝政权的理论支柱,更成为此后几千年来儒家所极力追求的政权雏形。孔子尝言:“郁郁乎,吾从周”,其心向往之的正是周人之“德”。
[参考文献]
[1]郭沫若.先秦天道观[G]//郭沫若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J].考古学报,1978(2).
[3]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4]王国维.殷商制度考[G]//王国维集(第四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5]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6]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G].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张琴】
On “Virtue” in th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Wares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WANG Xiao-yu
(LiteratureCollege,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Virtue”, as reflected in the existing inscriptions in the bronze wares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moving down from Heaven to the King then to courtiers. This is a process of moving down with many different tiers in the form of ritual,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for the internalization of virtue as a way of cultivating one’s moral character. The reason for the change is that it is required by establishing and stabilizing state power and also an important political strategy to differentiate aristocrats and commoners.
Key words:inscription in the bronze wares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virtue; moving down; ritual
[收稿日期]2015-12-10
[作者简介]王晓玉(1989-),女,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
[文章编号]1672-2035(2016)03-0025-04[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重返“五四”之一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