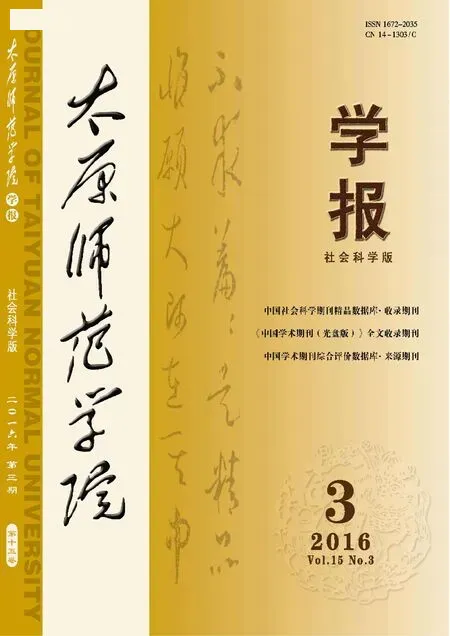自律伦理学的两种可能形态:康德与王阳明
张晓渝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哲学】
自律伦理学的两种可能形态:康德与王阳明
张晓渝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康德和王阳明分别呈现了自律伦理学的两种可能形态,即康德关于“意志自律”的阐发与阳明关于“良知自发”的诠释。如果仅仅是在“自我立法、自我遵守”的意义上谈论“自律”概念,那么二者有着相似的义理结构,这集中体现为其关于道德动机的阐发,即德性作为主体的内在品格逻辑地指向自我成就,因而我们的道德意识中含有一种动力,能够促使我们去实践德性所要求的行动。不过,康德和王阳明分别赋予了自律伦理学两种可能的形态,这种差别根源于二者对自律主体的不同设定。基于中西方异质的情理精神,康德的自律主体有着情理二分的人格组成,阳明的自律主体则是情理合一的存在,其中的关键是二者对“情”的理解。从更广的意义上看,这种设定又逻辑地构成了他们相异伦理学体系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康德;王阳明;自律;动机;行动主体;情理结构
康德首先在伦理学中使用“自律”概念,以阐明道德的本质,其中的关键正是康德对道德动机的说明。因此,人们在谈到“自律”概念时,便通常以康德关于自律的说明为标准,来进行自律伦理学的划分。但他们却忽略了一种情形:康德用以说明道德本质的“自律”概念与康德基于该概念而建构的伦理学体系是两回事。因此,当关涉“自律”概念时,我们自然应当回到康德所澄清的“自律”意义上,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阐发必须严守在康德的伦理学体系中进行。如果说我们仅仅是在前者的意义上观照“自律”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道德动机问题,那么,我们便没有理由否认阳明(甚至整个儒家伦理学的主流)也有如此相似的道德洞识与自律表达,尽管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系统而各有其特殊的问题与关切。基于此,加诸这种比较研究的质疑与批评多出于对上述前提设定的混淆,或是对比较哲学研究本身忌讳的心理,此种自我限制实属不必要。
一、何种自律:相似的义理架构
“自律”作为一个概念最早是出现在政治思想中的。在西方哲学史中,康德首度借境于政治学而将“自律”(Autonomie)的概念引入伦理学中。在政治学中,“自律”的本意为“自治”,意指一个团体或国家为自己制定法律并遵照法律而行动,因而“自律”的概念中含有“自由”与“服从”这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换言之,这一概念中存在着个人自由与共同体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可以说,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正是试图同时给予二者合理的权利表达。对此,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提出了一种有益的尝试,即社会契约,这意谓:共同体的法律是藉由社会契约而体现的“共同意志”,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均将其自身及其全部力量置于“共同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1]48就这一意义而言,每个共同体成员都具有双重身份:作为法律的制定者,他是自由的;作为法律的服从者,他又必须遵守整个共同体的秩序。既然他所必须遵循的法律是由他自己作为立法者制定的,那么尽管他具有服从的义务,但他依然是自由的,因为他并未受到他者意志的限制。
康德借境了卢梭的“自律”模式,并根据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建立的“现象”(Erscheinung)与“物自体”(Ding an sich)的二分结构,提出了“人的双重身份”之说:作为物自体,人从属于理智世界;作为现象,人从属于感性世界。在这一架构中,人一方面以物自体的身份制定道德法则,另一方面以现象的身份服从道德法则,这便是康德意义上的“自律”说明,它的基本涵义最终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获得了明确的澄清。康德说:“作为自己和全部普遍实践理性相协调的最高条件,每个有理性东西的意志的观念都是普遍立法意志的观念。按照这个原则,一切和意志自身普遍立法不一致的准则都要被抛弃,从而,意志并不去简单地服从规律或法律,他之所以服从,由于他自身也是个立法者,正由于这规律,法律是他自己制定的,所以他才必须服从。”[2]51因此,作为道德本质的“自律”概念是行为对意志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便是意志自我立法、自我服从。相反,“如若意志在它准则与自身普遍立法适应性之外,从而,走出自身,而在某一对象的属性中去寻找规定它的规律,就总要产生他律(Heteronomie)。”[2]62这种他律,在康德看来,是由于“一个异己的动因,通过被规定来接受规律的主体的本体,给予意志以规律”[2]66,简言之,决定意志的动力对道德主体而言是“异己”的力量,那么,道德因此就呈现为“被迫”的强制而非“自愿”的追求。
于是按照康德的说法,在道德实践中,道德本质的唯一正确表达是意志自律,而意志自律呈现为道德动机内在于实践主体,更准确地说,是内在于主体的实践理性。这种内在首先是作为一个事实存在于所有人的意识中的,我们能够完全不听任感性动因的召唤,这本身就证明了实践理性是真实存在的。这意味着,实践理性既是义务的根源又是我们服从义务的动机,而自律则意味着在我们的道德意识中已经包含了道德行动的动机。
如果仅仅是在作为一个概念的观照上,阳明无疑有着与康德相似的关于“自律”的表达,在阳明的理论阐发中,它可以被恰当地表述为:道德动机内在于良知,良知本身便足以激发致良知的行动,道德实践相应地表现为道德主体自身理性诉求在德性层面的自我立法并自我遵守的过程。对此,阳明给出了从“心即理”、“致良知”到“知行合一”的完整推论,更完整的来看,这一推论包含着如下三层转化:化“心理相分”为“心即理”;化天理(心)为良知;化良知为良行。
阳明的逻辑起点在于本体论层面“心即理”的架构。当阳明化朱熹的“心理相分”为“心即理”时,他首先实现的便是本体论层面的心体重建。阳明说:“心即性,性即理。”(《传习录上》)[3]17这意味着阳明首先赋予了心以普遍的品格,理内化于心使得理成为了心的题中之义,心相应地包含着理性的品格从而在哲学的意义上为人的存在提供了一种普遍本质的担保。这种本体论层面的先天规定赋予了个体存在以普遍必然的准则和根据,同时也使得理性的规范本身真实地关乎着个体的自我确证和实践挺立,而这又逻辑地对应着本体论向存在论的回归,即由“天理”向“良知”的转换。
事实上,阳明始终拒绝在人的认识活动(知)与实践活动(行)之外讨论本体的存在。阳明说:“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传习录下》)[3]122这种由超验本质向个体存在的回归在阳明的理论中便具体地呈现为其对“良知”的阐发,良知所呈现的意义世界进而明确地构成了阳明心学的核心旨归。
由“天理”向“良知”的转化在阳明的理论中具体地对应着良知由“出于天”到“系于人”的展现。从“系于人”上看,良知首先包含着知识论或认识论的功能,阳明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3]7这意谓良知作为原初的道德意识首先包含认识理的知觉能力,具有知善知恶等理性的分辨。并且,由于阳明预设了“心即理”的基调,因此作为认识对象的道德规范并不是脱离于实践主体的额外附加,并不是由天理所颁布的异己的命令,而是人(心)本身的理性维度作为内在自我所取得的德性形式。简言之,良知所关涉的道德规范不过是人自身所具有的理性诉求在德性层面自我立法的体现,致良知的道德实践亦相应地展现为一个基于主体自律的过程。
就良知作为实有诸己的人格关联着实践的维度而言,这种实践的动力在阳明看来是内在于良知本身的,阳明说:“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传习录上》)[3]7实践的动力即是“良知之发”,“良知之发”实为良知“自发”而非良知“被发”,那么在此,阳明所必须澄清的问题便是“良知如何能够自我发动”?按照阳明的说法,良知之所以能够自我发动基于其“心即理”的基本预设,他解释道:“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传习录中》)[3]51也就是说,阳明所言的心是能够自我立法的道德本心,理因此不再是外在于心的一极,而是本心所制定的道德法则,即所谓“天理”。如此,道德规范作为德性之理的具体展现,便不再是与心割裂的抽象存在,而恰恰是本心(良知)活动力的真实展现,因此理的呼唤本身就承担并反映着良知所具有的能动品格。
更进一步说,致良知的道德实践又逻辑地关联着阳明对“知行合一”的阐发。阳明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3]48在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知行之所以能够“合一”在于它们皆合于“良知”,而“良知”能够统合知行又在于“心即理”的逻辑起点。这里的关键正在于阳明对知行本身所作的实践论而非本体论或知识论的预设,换言之,阳明意义上的“知”与“行”分别指涉的是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那么“知行合一”所试图表达的则是:整个道德实践的动力源泉,即道德行动的动机本身就坐落于实践主体的道德意识中,道德实践亦相应地展现为实践主体自我立法并践履的过程。换言之,道德动机内在于良知,良知本身便足以激发致良知的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阳明才坚称:“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3]25
因此,无论是康德的“意志自律”,还是阳明的“良知自发”,其所表达的内涵无非是:德性作为主体的内在品格逻辑地指向自我成就,因而我们的道德意识中含有一种动力,能够促使我们去实践德性所要求的行动。如果仅仅是在“自我立法、自我遵守”的意义上谈论“自律”概念,那么上述分析已经表明,康德关于“自律”的阐发均见于阳明的学说中,其对应可谓丝丝入扣。道德主体本身就具有实现其法则的能力,就此而言,康德和阳明的义理架构均属于自律形态,而其差别在于二者对自律主体的不同理解,从更广的意义上看,这种架构又逻辑地构成他们相异的伦理学体系的重要一环。
二、谁之自律:相异的自律主体
康德和阳明分别预设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动机承载者:康德强调道德主体的情理二分,阳明强调道德主体的情理合一。
康德的论断我们可以从他关于“动机”和“冲动”的阐发中看出端倪。在康德那里,“动机”(Bewegungsgrund)和“冲动”(Triebfeder)事实上是两个相区别的概念,动机是意志的客观根据,冲动是欲望的主观根据。因此,康德其实并不否认感性欲望和实践理性都能够对行动产生影响,但对康德来说,如果不对欲望与理性在行动中的作用作出区分,那么人势必将降格为自然的存在。当然,这种理论坚持或许也同康德对行动本身的理解有关,在康德看来,一个单纯由情感和欲望所驱动的行为并不能称之为“行动”,行动必然意味着理性对情感和欲望的“再加工”。那么,一个单纯由情感和欲望所提供的动力只能归属于冲动的范畴,而一个通过理性作用于情感和欲望的动力才能被称为动机。只有动机才能表征行动范畴而从属于理性存在,因此,动机事实上涉及的是情感、理性与行动力的关系问题,它的行动主体便是康德所言的“意志”(Wille)。
在康德看来,所有理性存在都自在地作为目的实存,此目的作为意志的客观规定根据表明,意志不仅仅是被动地服从规律,而是按照对规律的表象自行规定行为,即按照原则而行动。康德承认,意志并不必然地全然由理性规定,换言之,意志完全有可能受到感性因素的影响。此时,严格说来,受感性因素左右的意志只能被称为意念(willkur),所谓“意念”指的是人作为经验的、现象界的部分,即“道德法则的服从者”,他可以是受感性驱动而行为。而在康德那里,真正的“意志”则排除了“意念”的部分,专指实践主体作为物自体自身,即“道德法则的制定者”。在康德看来,道德主体应当是后一种意义上的“意志”,此时的意志亦即实践理性本身。因此,一切的情感,以及所有康德称之为偏好的东西,都被排除在了“意志”的根据之外,虽然它们能够对意志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必须基于实践理性的作用。对康德而言,意志的内在张力表征了人作为感性存在与理性存在的内在紧张,这种紧张又因情理二分的基调而变得不可调和。
由于规律见之于行动必然需要理性,因此意志也就是实践理性,即理性的行动能力。当意志的规定根据全然排除了感性的影响,这一意志对其自身而言便是一项法则,它也因此能够被称为是“自我立法”,即自律的。情感尽管并不总是在道德实践中作为理性的一个附带的、消极的要素呈现,但就它毕竟不能成为道德的规范性来源而言,它都难以在康德的动机架构中获得同理性相抗衡的地位。相应地,一个道德实践的主体总是试图以理性的姿态使得责任原则成为其行动的动机,如此,它的行动才真正地具有道德价值,它自身也才真正地同其他自然的存在区别开来。
阳明同样肯定了人性中的情、理成分,不过由于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情理结构,特别是孟子的“四端之心”说,阳明则预设了一个情理合一的道德主体架构。更具体地说,在阳明的系统中,情并未被简单归诸与理相对的形而下范畴。阳明首先对情作出了两种区分,即四端之“情”与七情之“情”,前者属于形而上的层面,而后者属于形而下的层面。就七情而言,阳明说:“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传习录》下)[3]126这意谓他承认七情(自然情感)是人心不可拒斥的要素,但同时,人之“情”不仅指七情之“情”,它同时包括四端之“情”(道德情感)。《传习录》(上卷)云:“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3]17所谓“性之表德”即是“性所表示的内容”。依阳明之见,仁、义、礼、智是“性”所表示的内容,同时,四端之情也是“性”所表示的内容。既然仁、义、礼、智之名是“性”之“已发而有”,那么四端之“情”同样来自于“性”之“已发”,并且与“性”同属于形而上的层面。在这个脉络中,情被提升到了性(理)的层面,纵使四端之“情”被视为“情”,但此“情”并不是与理(性)相分的感性之情,四端之情为本心所发,仁义礼智为本心所立,故心理为一。
在阳明那里(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唯有根据情理合一的主体架构,我们才能充分地了解阳明的“心即理”说,以及由“心即理”、“致良知”到“知行合一”的内在历程所展开的完整系统。也正是这种异质的主体架构,使得阳明的动机观虽然属于自律伦理学的范畴,但在整个体系的表达上却与康德伦理学迥异。
三、结语
正如本文开篇所言,仅从自我立法的意义上理解“自律”概念,那么康德和阳明无疑有着相似的“自律”表达,这体现在他们关于道德动机的架构上。但基于中西方异质的情理精神,他们分别预设了两个不同的动机主体:康德的动机主体有着情、理二分的人格组成,阳明的动机主体则是情、理合一的存在,其中的关键便是二者对“情”的理解。康德和阳明都可以承诺情感包含着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二重向度,在康德那里它体现为敬畏与偏好的分疏,在阳明那里,它体现为四端与七情的差别。
从康德伦理学的逻辑发展以及他的整个哲学体系来看,他认为唯有以“对道德法则的敬畏”为动机来履行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因此康德始终拒斥偏好对道德实践的参与,只承认并接纳敬畏作为沟通其形而上学与经验人类学的桥梁。但问题是,情、理二分的结构注定了情感在本质上是一种与理性异质的要素,既然同属情感的范畴,康德为什么偏偏否定“偏好之情”,而肯定“敬畏之情”呢?并且,对康德来说,如果理性自身是实践的而足以作为道德动机激发行动,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费力地强调道德情感也是道德行动的动机呢?就康德自己的阐发而言,他的确部分地给出了一种道德情感作为动机的可能解释,但是,由于康德自身在情理结构上的二分设定,道德敬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而这又逻辑地决定了康德自律伦理学的内在紧张。
相反,阳明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情理合一的理论基调,这种理论设定以及阳明所给出的系统阐发恰好缓解了康德自律进路的内在紧张,也更容易得到我们的直觉支持。并且,就当前西方道德哲学的最新研究而言,传统意义上的“情感”、“欲望”本身也面临着新的界定与澄清。换言之,我们究竟应当在何种意义上来理解“情感”和“欲望”?与行动相关联的情感是否必然包含理性的作用?欲望是否能否直接成为行动的理由?等等。当然,这涉及道德心理学、规范伦理学与元伦理学的结合,其中可能触及的问题远比我们所能想象以及本文所能呈现的问题复杂得多。
[参考文献]
[1]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
[3]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冯自变】
[收稿日期]2015-11-08
[作者简介]张晓渝(1986-),女,河南商水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博士。
[文章编号]1672-2035(2016)03-0001-04[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