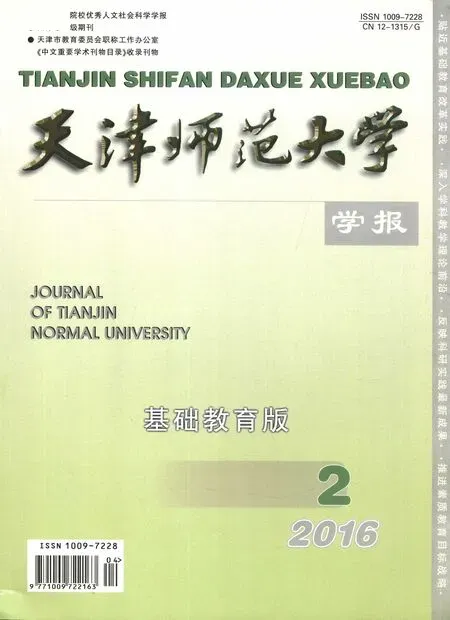演绎推理
——高中生高效历史思维的必要能力
何 睦,杨 蕊,王光明
演绎推理
——高中生高效历史思维的必要能力
何 睦,杨 蕊,王光明
演绎推理是高中历史学习的重要思维工具之一,可以在展示和验证历史规律、检验和更新旧知识、以及建构知识间联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运用演绎推理进行历史学习时,必须尊重历史逻辑,综合多角度结论,才能得到完整准确的历史认识。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使学生养成辩证思维的意识,获得满足课标要求的高效历史思维能力。
高中历史;演绎推理;历史思维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21世纪的社会已经逐渐转变为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的理念也越来越被重视。人们在意识到不断充实知识成为生活第一需要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提高学习效率的有效方法。基础教育普通高中阶段是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繁重的学业负担,掌握高效学习的方法和能力对高中各科学习至关重要。《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后简称“课标”)对高中历史课程性质做了明确说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1](P2)通过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仅只是扩大了历史知识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在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认知活动中,培养历史思维、促进历史思维的发展,进而掌握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然而,不同学科的知识都有其学科思维的特殊性,譬如历史知识不能像理科的公式、定理那样被准确地证明是真或是伪,知识间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如果学生没有理解教材中的知识而仅靠死记硬背,非但没有改变历史教学“知识本位”的倾向,也与历史学科训练思辨能力的特点背道而驰。因此,面对高中历史大量的“知识负担”,探寻一种高效的历史学习思维能力至关重要。
逻辑推理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主要思维工具,是现代科学体系的主要认知手段,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后,就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领域,因此在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高中各科思维能力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按照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逻辑推理可以分为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归纳推理在历史学习中给予较多关注[2-7],而对演绎推理尚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演绎推理的认知机制,对其在高中历史学习中发挥的功用隅之管窥,以探索提升高中生高效历史学习思维的新路径。
一、演绎推理的认知机制
演绎推理是由规律到现象的推理方式,即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方式,其经典形式就是三段论:
M是P;
S是M;
所以,S是P。
具体来说,三段论是由两个含有一个共同项的性质判断作前提,得出一个新的性质判断为结论的演绎推理。结论中的主项叫做小项,用“S”表示;结论中的谓项叫做大项,用“P”表示;两个前提中含有大项“P”的叫做大前提,含有小项“S”的叫做小前提;两个前提中共有的项叫做中项,用“M”表示。简言之,三段论包含三个部分:大前提——已知的一般原理或观念;小前提——具体的认识对象;结论——根据一般原理或观念对具体认识对象作出判断。在历史学的很多情况中,三段论会以省略某一前提的形式出现,比如“抗日战争是正义战争,所以抗日战争一定会获得胜利。”就省略了“正义战争一定会获得胜利”这一大前提。
在认知领域,关于演绎推理的基本观点主要有规则理论、心理模型理论和双机制理论。[8](P137)但目前这三种观点仍处在争论之中,因此不少研究者转而借助脑成像技术以求揭示演绎推理的认知机制。当代脑科学研究发现,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对应脑部活动的不同区域。“归纳推理激活的是双前额最外侧区及右前额背外侧部,而演绎推理激活的主要是右侧枕叶、右侧基底节以及左侧前额皮层。”[9](P42)
规则理论认为,在推理过程中人们使用抽象的、没有内容限制的推理规则来进行有效推理,推理过程是受句法约束的规则加工过程;Goel等人借助PET技术发现,被试在推理过程中激活的主要是负责言语加工的左额叶和颞叶区。[10-11]心理模型理论认为,人们通过构建心理模型来表征已有前提的情况,再通过一系列的模型操作进行推理,这一过程是受语义约束的视觉空间搜索过程;脑研究发现激活的主要是与视觉空间表征相关的顶枕联合区和楔前叶的两侧以及前额叶和前扣带回。[12-13]双机制理论则主张,人可以依据逻辑进行推理,也可以依据经验进行推理,并且人们只有在没有适合的背景知识可供参考的条件下,才会基于形式逻辑结构进行推理[8](P148);Goel等采用FMRI技术发展了推理的双机制理论:人们在现成知识可用时会采用启发式策略,激活的是与语义记忆相关的额—颞叶系统,而没有现成知识可用时,会利用形式逻辑规则,激活与空间信息加工有关的顶叶系统,并且在进行抽象推理时,随着推理难度的增加会伴随激活的增强。[14-15]
尽管脑科学研究对演绎推理的三种不同认知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支持,却仍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值得肯定的是,人的演绎推理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发展而发展的,高中时期是演绎推理达到成熟的关键时期。在一项逻辑推理的测试中,“高中二年级学生的归纳推理能力与大学二年级学生相差无几,但是演绎推理能力远低于大学二年级学生。”[16](P27)也就是说,高中阶段学生负责归纳推理能力的脑区已经发育成熟,而对应演绎推理能力的脑区尚处于快速发育阶段。发展演绎推理能力既是培养高中生历史思维能力的教学任务,也是提高高中生历史学习效率的潜在领域。
二、演绎推理在历史思维中的功用
按照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观点,逻辑推理的两种形式在学习的过程中,分别担负着不同的任务:“走向建立观念的运动就称之为归纳,而走向展现、应用和检验的运动则称之为演绎。”[17](P67)传统上,历史学习的主要任务,是在掌握大量具体史实的基础上,让学生归纳出一种认识历史现象的观念或规律,即主要运用归纳推理的思维方法。譬如,通过归纳拿破仑、克伦威尔、华盛顿、孙中山等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得出时势造英雄的结论;通过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历史,得出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规律;通过巴黎和会等大国主导外交的事例,得出弱国无外交的近代国际法则等。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归纳推理都是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主要手段。相对来说,演绎推理在历史学中则处于边缘和辅助的地位。甚至学界一度有过“在历史学的研习中,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18]的声音。然而,随着高中新课程改革的实施,以及教育学、心理学领域关于青少年逻辑智能发展研究的深入,无论从历史学习本身的需要,还是青少年智力发展的全局出发,都不应忽视演绎推理的作用。
根据高中历史教学的内容和要求,演绎推理对历史思维能力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对规律进行展示和验证
演绎推理在认识方式上的特点是从一般到特殊,由抽象到具体。虽然从史实中总结历史规律是历史学的重要任务,但是对规律的认识并不是学习的终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只有在学生头脑中经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思想等加以展现和验证,才能真正从学生内心萌发情感,产生态度,建构价值体系,这样的历史学习才是有意义的学习。比如,在学习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规律时,会用太平天国运动来反证“农民起义具有阶级局限性,无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这其实就是一组省略小前提的演绎推理,其完整形式为:
农民起义具有阶级局限性,无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运动具有阶级局限性,无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虽然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巅峰,但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并不是分析的目标,而是对历史规律的展示和证明材料。在前提的引导下,太平天国运动的各个具体事实,如领导层的腐化,纲领的空想性等,在思维中都成为了印证“农民阶级局限性”过程中的环节。高中生只有在自己的头脑中经历这种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才能获得内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正是通过演绎推理引发学生认知方式转变的结果。
(二)对旧知识进行检验和更新
如果一个演绎论证被指出其前提会导致结论荒谬或矛盾,就必须对前提进行修正,这在逻辑学中被称为归谬法。[19](P213)在历史学习中,学习者可以利用归谬法,发现旧有知识中的谬误。譬如,学生A在学习过中外各国古代史后,归纳出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奴隶主占有奴隶的人身自由、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继而他以这条知识作为大前提,对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社会进行了如下推理:
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奴隶主占有奴隶的人身自由、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
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社会中奴隶主占有奴隶的人身自由、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
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社会是奴隶社会。
但是学生A很快便发现,任何一本历史书籍都没有将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社会归类于奴隶社会。这是因为美国南方庄园主虽然利用奴隶无偿劳动,但是生产的产品主要作为商品,服务于资本主义形式的社会经济,因此其本质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奴隶制庄园经济。而旧有前提中,仅以生产关系作为对社会性质划分的标准,显然是不周延的。认识到这一点后,学生A重新对自己的社会性质划分标准进行了补充和更新,使得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向前推进了一步。
上述这个例子同时也体现了演绎推理对归纳推理的解弊。演绎推理不是漫无边际的想象,其前提来自于归纳推理的结果。然而除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已知历史规律,历史学习时用以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大多来自于学生在旧有知识之上的归纳总结。但是,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要确保归纳推理的结论为真,就必须做到完全归纳,即对所观察领域内所有对象的归纳,否则结论具有或然性,也就是有可能为真,有可能非真。由于高中接触的历史知识有限,大多数情况无法做到完全归纳推理,往往新出现一个例证就能推翻之前的结论,这使得许多学习中生成的观念并不能完全肯定是否符合历史实在。因此,如果在进行推理的过程中,从某些大前提经有效推导,得出了逻辑矛盾或与经验事实不符的结论,往往可以藉此发现旧知识所存在的谬误,继而进行知识修正和升级。
(三)建构历史知识间的联系,扩大历史认识
在谈论如何对知识进行组织时,杜威指出:“只有演绎才能表明和着重指出事物按逻辑顺序的关系;而只有看到这些关系,学习才不再是碎纸篓。”[17](P78~79)这一特性对于以知识学习为基本内容的历史学尤其重要。如果说学习者以归纳推理建构了基本的历史认识,演绎推理则可以通过对思维的再续风帆,组织起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扩大历史认识的广度,甚至发现某些“隐藏”的知识。而能否达到这一层面,往往成为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差异的体现。例如,让学生列举二战前英国的绥靖政策,这是一道考察点明确的传统归纳题。按照课标的要求,学生只要将一战前的英日同盟、英德协定及两次大战之间的九一八国联调查、承认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慕尼黑协定等教材中直接作为英国绥靖行为出现的相关内容归纳出来就可以了。然而学生B以演绎推理进行思考,从绥靖的内涵出发回顾过去的知识,另外发现19世纪末英国没有立即加入旨在对抗德国的法俄同盟,而是于一战前夕德国明确成为英国利益的主要威胁后,才加入该同盟并形成三国协约,这无异也是绥靖的一个表现。历史学界早有英国存在“绥靖传统”这一说法,虽然在高中阶段只是要求掌握与世界大战直接相关的部分,但学生B通过演绎推理思维显然延伸了对这一问题的历史认识。沿着这一思维的轨迹,学生B很快可以发现英国20世纪初的绥靖行为除了基于时政形势,还有习惯性政策的因素。这样学生B对英国绥靖问题的认识无疑相较他的同学更加全面透彻。
从以上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演绎推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相关性”的发现能力。对此,历史学家沃尔什提出了认识历史的综合法,即“对一个事件,要追溯它和其他事件的内在联系,并从而为它在历史的网络之中定位的方法。”[20](P69)高中生如果要对自己的历史理解进行拓展,则关键在于通过演绎理解历史事件间所固有的特殊关联。只有掌握尽可能多的历史关联,才能进一步扩大历史认识的范围,实现深层次的历史思维。
三、演绎推理在高效历史学习中的合理应用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史学除了具有一般的科学普遍性,同时又具有独特性。因此在应用演绎推理时,必须遵循历史学的学科特点,才能使学生得到正确而有价值的结论,收获良好的学习效果。在高中历史学习的范畴内,特别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尊重历史逻辑,保证学生思维的准确性
要得到正确的结论,推理本身必须符合客观的常识规律。然而,由于时代不同,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与人所共知的常识是不同的。这就会造成有些在常识下成立的推理,在历史中却是站不住脚的。比如著名的关于青铜鼎的用途的错误认识,就可以归为这样一个推论:
用来加热食物的器皿是食器;
考古出土的商代青铜鼎内发现有煮熟的肉;
所以商代青铜鼎是食器。
从推理的结构来看,“用来煮食物的器皿是食器”符合常识,推理前提为真,结论也应为真。然而研究表明,虽然远古陶鼎起源于烹饪器皿,但商代青铜鼎的主要作用已经是祭祀的礼器,而并非食器。部分鼎中发现熟肉的原因是,商代祭礼所使用的祭品须为热食,以示对祖先的尊敬。因此,祭祀时会将事先准备的熟肉投入鼎中加热,以保持祭品的温度。之所以得出了与史实不符的结论,就在于推理过程中忽略了常识与历史的差异。当然类似的不同还有多种情况,诸如各个历史时期对事物评价标准的殊异、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概念名词的流转变迁等方方面面。总之,在进行推理的时候不能想当然,如果没有考虑到历史演进的线索和实态,就会得出扭曲或错误结论,影响历史思维的养成,给学生的学习带来负面影响,更不利于高效率的历史学习。
(二)综合多角度结论,促进学生的全面认识
在演绎推理的规则中,一组前提,只能对应一个结论。然而在历史学中,历史认识往往不是单一的,一个历史事件往往具有多个层面的意义。由于历史认识具有这种多维性和辩证性的特点,这就要求学习者进行多次推理,从多角度地看待某一历史事实,形成高效、全面的历史思维认识。譬如,在学习“九一八事变”时,学生可能首先做出如下推理:
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是民族内部停止争斗,一致对外;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内各派势力逐渐走向停止内战,团结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这一组推理是以民族意识的觉醒为大前提,得到的结论是“九一八事变”对唤醒中国国内民族意识的意义。如果将视角平移,从日本法西斯对外扩张的历史进程来看,则可以进行如下推理:
田中奏折中把占领中国东北作为征服世界战略的第一步;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法西斯按照田中奏折的战略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法西斯按照既定战略展开的侵略活动。
这一组推理以日本法西斯既定的侵略战略为大前提,得到了“九一八事变”并非偶然,而是日本法西斯蓄谋已久的侵略行动的结论。如果再将前提的视角抬高,进行如下推理:
日本法西斯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法西斯走向世界战争的起点;
“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之一。
从日本法西斯在二战扮演的角色为大前提进行推理,就可以超越中日局部战争的视角,认识到“九一八事变”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
以上三组推理的结论,是从不同视角看待“九一八事变”得到的认知。不同角度的结论有利于学生从繁杂的历史知识中梳理出清晰的认识脉络,促进高效历史思维的全面性。可以发现,与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将定理和公式明确地呈现给学生不同,历史学的大前提往往隐藏在知识之中,历史认识来自于对大前提的挖掘和选取。当然这种挖掘和选取不应是随意的,而应依据课标中对历史认识的高度和广度的要求来进行的。
此外,历史学还有一个总的认识原则——史观。我国中学历史的基本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这就要求学生还要具备一分为二的看待和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意识,否则就会造成认识方向的偏颇。譬如,在学习义和团时,如果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角度设置前提,会得到积极的评价:
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反抗外敌入侵的斗争;
所以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
但如果对义和团的认识止步于此,就没有达到高中历史的认识要求。按照辩证唯物史观的原则,还应从另一个角度的前提出发,检视义和团是否具有消极的一面:
滥杀无辜外国人是一种盲目排外行为;
义和团杀死许多无辜外国人;
义和团的举动具有盲目排外性质。
以上两组推理得出的结论看似价值判断截然相反,但实际上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共同建构了对义和团运动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历史认识。
总之,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在运用演绎推理进行历史思维活动时,应该在尊重历史逻辑的基础上,综合多角度多层次的结论来认识历史事实。而多回合推理的过程本身,又促使学生养成了辩证思维的意识,真正达到课标所要求的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1](P2),这是高效历史思维能力构建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四、总结
从课程改革对高中历史学科的定位来看,发展演绎推理已成为高效历史思维能力的内在要求。新课标的一个突出变化是,以能力目标体系代替了以往教学大纲中的知识目标体系。具体到历史学科来说,就是要求学生在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及具备适当的价值判断能力的基础上,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和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关注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的历史命运。”[1](P2)为此,各版新教材均在知识内容方面做了一定程度的简化,许多知识点不再直白地浮于纸上,就是“为历史方法的习得和历史学习能力尤其是历史思维能力的提升”[21]留出空间。这意味着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必须建构一种超越固有知识,主动进行“探究”的意识。否则,即使把书本内容烂熟于胸,也并不能取得理想的学习效果。因此,历史学习过程中必须引进演绎推理参与知识处理。如果没有经过演绎推理的验证,历史概念就无法获得学生的深入理解,三维目标就成了空中楼阁;如果没有演绎推理对归纳的成果进行检验,就无法对习得的知识进行“归谬”,也就丧失了深化理解的机会;如果没有演绎推理进行联系和整合,碎片化的历史知识就无法成为认识的有效材料,历史学习的过程就会沦为死记硬背,历史认识的拓展也将举步维艰。可见,在新的教学目标定位下,演绎推理可以也应是高中历史高效学习中的重要思维工具之一。
当然,强调演绎推理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归纳推理的偏废。历史学是一门高度要求全面逻辑能力的学科。一个好的历史学习者应该具备历史学家般的思维素质,能够以归纳推理进行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梳理,更需要以演绎推理进行历史想象、历史诠释和历史反思。因此,一个完整的历史认识过程是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相互结合,循环扩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应是学习者的主动思维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客观上学生个体间还存在演绎思维能力不平衡的情况。新的心理学研究显示,不同脑优势类型者的演绎推理能力确实存在差异,“左脑优势者更能胜任分析的、逻辑的、理性的演绎推理任务。”但“专业训练的适宜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个体智能的某些缺陷,促进其推理成绩的提升。”[22]也正因此,在历史学习中有意识地增加演绎推理活动,不仅可以促进高中生整体思维水平的提高,也是从根本上实现高中生高效历史思维能力,继而提高历史学科学习效果的重要途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杜兰.历史思维能力初步培养浅谈[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1998(7).
[3]孙楠.中学生历史归纳能力的培养[J].历史教学,1999(4).
[4]何大进.历史教学与逻辑思维[J].历史教学,2001(2).
[5]叶小兵.浅谈历史课堂上学生提出的“意外问题”[J].课程·教材·教法,2007(2).
[6]孙立田,任世江.论历史思维能力分类体系[J].历史教学, 2014(11).
[7]陈志刚.应对高考,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技能[J].历史教学,2015(17).
[8]刘志雅.思维心理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
[9]韩力群,涂序彦.多中枢自协调拟人脑研究及应用[M].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10] Goel,V.,Gold,B.,Kapur,S.,et al.The seats of reason? Animaging study of deductive and inductive reasoning[J].Neuro-Report,1997(5).
[11] Goel,V.,Gold,B.,Kapur,S.,et al.Neuroanatomical Correlates of Human Reasoning [ J].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1998(3).
[12] Knauff,M.,Fangmeier,T.,Ruff,C.C.,et al.Reasoning,models, and images:behavioral measures and cortical activity[J].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2003(4).
[13] Knauff,M.,Mulack,T.,Kassubek,J.,et al.Spatial imagery indeductive reasoning:a functional MRI study [ J].Cognitive Brain Research,2002(13).
[14] Goel,V.Evidence for dual neural pathways for syllogistic reasoning[J].Psychologia,2003(32).
[15]杨群,邱江,张庆林.演绎推理的认知和脑机制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2009,32(3).
[16]朱文彬,赵叔文.高等教育心理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7]杜威.我们如何思维[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18]赵恒烈.历史教育的活力在于开发历史学习的创造性[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6(4).
[19]加里·R·卡比,杰弗里·R·古德帕斯特.思维——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跨学科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0] 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1]李稚勇.历史课唯有求真——论中学历史课的价值追求[J].历史教学,2013(11).
[22]吴欣.三段论推理的影响因素及其脑生理关联性研究[J].心理技术与应用,2013(2).
[责任编辑:陈 浮]
Deductive Inference——the Necessary Ability of Effective Historical Thinking in High School History
HE Mu,YANG Rui,WANG Guangming
Deductive inferen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ols of thinking in high school history learning, which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isplaying and verifying historical law, checking and updating the old knowledge, and building the link between knowledge.We should follow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consider multi-angle conclusions, to get integrated and accurate historical knowledge by deductive inference.We should also help students develop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obtain ability of effective historical thinking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curriculum.
se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 deductive inference, historical thinking
G633.51
A
1009-7228(2016)02-0042-06
10.16826/ j.cnki.1009-7228.2016.02.010
2016-01-20
何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300387)教师教育学院讲师,博士;杨蕊,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学秘书;王光明,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高中生高效学习的心理特征研究”(13YJA190012)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