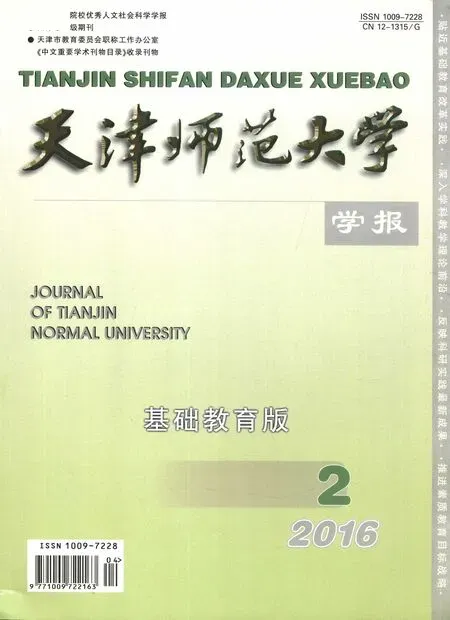论小学语文教材选文“儿童文学化”的缺失
张 璇
论小学语文教材选文“儿童文学化”的缺失
张 璇
儿童文学化,即把儿童文学当作小学语文教育的主要资源。当前小学语文教材选文在“儿童文学化”方面存在着七大缺失:对儿童文学资源利用存在局限性、儿童文学的文体有限、数量不够、质量不高、选文的国际化视野欠缺、选文不符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主题单一。以“儿童本位”的视角探讨小学语文教材选文的选编构想,并提出几点建议。
小学语文;儿童文学化;教材选文;缺失
所谓“儿童文学化”,是指把儿童文学当作小学语文教育的主要资源。王泉根先生认为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这二者的关系是“‘一体两面’之事”;他还着重点出“小学语文儿童文学化是国际语文教育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朱自强先生也认为“小学教育要向前发展,必须走儿童文学化这条路”。儿童文学化,首先是指教材的儿童文学化,而目前小学语文教材选文在“儿童文学化”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缺失。
一、教材“儿童文学化”的历史经验和现状
一直以来,儿童文学和小学语文教材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儿童文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1]:不论是商务印书馆于1919 年8月出版的八册《新体国语教科书》、1922年6月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1922年12月沈百英主编的《儿童文学读本》、1923年6月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还是中华书局在1920年6月推出的《新教育教科书国语读本》、1932年出版的《小学国语读本》,这其中又以193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由叶圣陶主持编写的《开明小学国语读本》表现尤为突出,成为小学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的一个典型实例。[2]后人评论这套课本“形式和内容俱足称后起之秀,材料活泼隽趣,字里行间,流露天真气氛,颇合儿童脾胃。材料亦多不落窠臼,恰到好处。”[3](P151)
身兼语文教育家和儿童文学家两种身份的叶圣陶先生认为:教师在进行国语教育时,要找到“适当的教材”,而“所谓适当的教材”,应该是符合“儿童的夙好”、“富有文学趣味的教材”。历史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途径,随着现代儿童教育理念的逐渐形成,我国教育界也普遍认为“儿童文学可以使人文教育,即健全人格的养成落到实处”,一致主张国语课程应当把儿童文学做中心。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也对儿童文学作品进入教材和课外阅读中的内容及数量有明确的规定。大量儿童文学作品进入小语教材,苏教版、人教版、北师大版这三大教材版本都选取大量的儿童故事和童话,把儿童文学教育作为了语文教育的主体。虽然“儿童文学化”已经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一种必然趋势,但如果从选文的思想性、文学趣味性和语文教育价值观来严格衡量,就会发现我们的教材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儿童文学化”教材。
二、教材选文“儿童文学化”的七大缺失
当前小学语文教材在选文的“儿童文学化”方面存在着七大缺失,具体表现如下:
资源利用的局限性。小学语文教材对儿童文学资源的利用存在着很大的缺憾:第一,缺失民间文学。当前的小学语文教材有一个盲点,即选文中基本上没有选入民间的童谣、儿歌和童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第二,缺失幻想文学。现行的以灌输知识为本的“知识至上”的教育理念使得幻想文学的价值在教材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选文中拟人体童话成为了童话故事的主体,而超人体童话和常人体童话这两类更能激发孩子想象力的作品在教材中却难得一见[4],难怪傅林统认为“幻想童话在国内似乎是斧斤未入的山林”。小学语文教材选文中幻想文学作品的严重缺失,使得很多儿童因无法领会其妙趣,从而导致忽视或影响对儿童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第三,缺失幽默文学。从书中寻求快乐,应该是儿童读书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彭懿认为“一本好的儿童书,应该是幽默迭起的”。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品格,幽默应从小植根于儿童的心灵中。幽默作品在国外许多教材中都受到重视,而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一个重大的失误就是把幽默文学排除在外[5],例如人教版教材选文中表现幽默精神的作品寥寥无几,选文里更多表现和推崇的是克制和忍耐,缺少对快乐精神和幽默文学的推崇。
文类不完整。王泉根教授将儿童文学的文体分为6个方面:一是儿童文学的叙事体,包括儿童小说、成长小说、动物小说、故事;二是儿童文学的散文体,包括艺术散文、少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三是儿童文学的韵文体,包括儿歌(传统儿歌与现代儿歌)、儿童诗歌;四是儿童文学的幻想体,包括童话、寓言、幻想文学;五是儿童文学的科学体,包括儿童科学文艺;六是儿童文学的多媒体,包括图画书、卡通、儿童影视、儿童戏剧、网络儿童文学。[6](P32)根据上述分类,儿童文学按细类有20多种类型,但小学教材选文中儿童文学的文体却很有限。当前教材选文中儿童故事是最多的,童话和儿童散文其次,再次是寓言。与之相比,童谣、儿歌、谜语、语言游戏、笑话、科学小品、儿童戏剧、图画书这些文体的选文数量严重缺失。即使是上面提及的选入篇目比较多的儿童故事、儿童散文和童话这些大类中,选文的文体细类也呈现不均匀状态:儿童故事这类文体中以历史名人故事和生活故事居多,幽默故事、滑稽故事、动物故事严重缺失;童话以拟人童话或知识童话为主,幻想类童话缺失;儿童散文以艺术散文为主,少年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缺失;图文并茂的图画书、卡通缺失。
数量不够。与日本、美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教材相比,当前进入内地教材的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当前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很多选文看似是儿童文学,实际上并不是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被朱自强教授冠名为“教材体”儿童文学,其实是由出版教材的编辑们自己写出来的,其特点是“短小轻薄”,即篇幅短小、人文思想性薄弱。这些作品只是借了儿童文学的外壳,严格来讲是不能称之为儿童文学作品的,难怪有人评论其为“非儿童文学的儿童文学选文”。如果剔除掉这些“教材体”儿童选文后,教材中的选文真正称得上儿童文学作品的为数不多。
质量不高。朱自强教授在《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中指出:“小学语文教材要不要经典,这几乎是一个不容讨论的问题。”当前进入小学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作品整体上质量不高,几乎看不到原汁原味的经典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最有代表性的、公认的优秀儿童文学经典作品没有被选用进教材。现在的小学语文教材里边,二流的、甚至三流的儿童文学作品很多,一流的作品很少。一位有14篇作品入选国内各版本小学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作家曾说过这样的话:“其实,这些课文在我的创作中并不是自己最满意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7]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其次,教材在选文时都不太注重作品的原始状态,大多数的儿童文学选文是改编过的,这种现象在由经典童话改编而成的选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8]以人教版的教材为例,其改编选文比重占课文总数的45%,这种对选文文字和情节的随意删改,使得原文的艺术韵味随着对原文的压缩处理所剩无几,直接导致了让“兼有文学性和审美性的经典变成了一根根不伦不类的鸡肋”[9]的后果。比如,《小蝌蚪找妈妈》,原作1 500多字,是非常精彩的一篇作品,有细腻的心理描写,包括反复4次才形成的认知规律,入选教材后改为500 字,流失掉太多的东西,将“找妈妈”过程中的“找”趣味简单化。再次,“教材体”选文的滥竽充数现象。这种教材体选文因编写模式的“成人化”,导致了作品主题大多充满训诫意味,作为儿童文学特有的趣味性、审美性却严重不足,“没有很好的结构与语言,人物形象的刻画、心理的展示、情感的流露,都是缺乏的。”[10](P207)
国际化视野不够开阔。当前的小学语文教材选文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资源利用存在一定的问题。据统计,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12册选入13个国家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共44篇,约占教材中所有儿童文学选文比重的12%。其中苏联、俄国选入的作品最多,约占总数的40%,美国的作品约占21%,其他9个国家的作品合起来约占39%。以上数据表明各国入选的儿童文学比例不当,甚至严重失调,选文偏重于苏联、俄国、美国,国际化视野不够开阔。此外,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这三大教材中低学段入选的外国作品数量都特别少:人教版1年级教材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一篇也没有涉及,2年级教材中有6篇;苏教版1年级、2年级教材中只有1 篇;北师大版1年级、2年级教材各有1篇。
文体偏离年龄、年级特点。周作人不仅倡导小学语文教科书要用“儿童文学”的编写模式,而且认为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适宜阅读不同文体的儿童读物:“3岁到6岁的儿童读物宜用儿歌,不重意义的韵语;6岁到10岁宜用儿歌、新诗、神怪童话、天然故事等;10岁到15岁,宜用民歌、古诗、传说、写实的故事、寓言、戏曲等。”[11]吴研因的《小学国语国文教学法》和周邦道的《儿童的文学之研究》也都详细地表述了类似的文体组织意见。当前小学语文教材中以儿童故事、儿童诗、童话为主,低学段缺少了儿歌和儿童报告文学两种文体,特别是选编在低年级教材中的儿歌数量太少。高学段儿童故事占有绝对领先地位,虽增加了儿童小说这一体裁,但作品的体裁类型却明显减少。对于寓言这种文体,应该安排在5年级、6年级,而非2年级、3年级。因为要理解寓言,需要具备抽象能力和理性的分析判断能力,因此中高年级寓言文学的入选数量应该随着儿童逻辑思维能力的增强而呈递增趋势,可我们教材中所安排的寓言作品,低年级有6篇,中高年级仅有3篇,恰恰与之相反。
主题缺失。“爱的主题”、“自然的主题”、“顽童的主题”作为儿童文学的三大主题,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前两个主题相对体现得较为充分,体现“顽童的主题”的选文则很少,教材中基本没有涉及像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卡尔松》、卡洛尔的《克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样能表现顽童和探险主题的选文。除此之外,以下主题的选文也较为匮乏:其一,死亡主题的缺失。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主要区别,在于表现主题的方式,而不在于主题的广狭。儿童文学作品也可以承担起死亡教育的功能,诚如美国人所认为的: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用一种自然的、健康的心态来消除儿童由于未知而对死亡产生的恐惧感和神秘感,能帮助他们了解死亡的有关知识,正确处理自己或他人的悲伤情绪,树立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世界上有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表现了“死亡”这个主题,例如《一片叶子落下来》、《獾的礼物》、《爷爷变成了幽灵》、《爷爷有没有穿西装》、《马提与祖父》等,遗憾的是我国小学语文教材几乎没有涉及“死”的主题的选文,这一点很值得教材编写者反思。其二,爱情主题的缺失。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很多表现亲情和友情的文章,但除此之外,是否还应该增加表现另一种美好感情——爱情的文章呢?窦桂梅、胡兰在其文章中提出:“有了这一课,我们的孩子们长大后再去品味爱情,或许就会增加更多的深情与理性”[12],表达了希望通过爱情作品来传递“柔情与感动”、来“演绎语文”。其三,动物主题的缺失。那些真正能表现出丰富、细腻的动物精神世界的文学能够引起少年儿童对于生命、生存、自然等颇具深度意义话题的关注和思考,对儿童的“精神成人”有着其他文学样式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可是在教材中动物文学是缺失的,像西顿、椋鸠十、黑鹤、沈石溪的动物故事都没有被选入。
三、教材选文的几点建议
儿童文学作家严既澄认为:人在小学时期内,“只有儿童文学,是这时期内最不可缺失的精神上的食粮”,“童年时期由谁携手带路,周围世界的哪些东西进入了他的头脑和心灵”会决定一个人的“童年怎样度过”,所以“真正的儿童教育,应当首先注重儿童文学。”儿童文学里面蕴含着很多孩子心灵发展所需的营养,因此在小学语文教材选文内容的编排上,应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用心为儿童提供优秀的、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
对小学语文教材选文的几点建议:其一,选文要突出儿童的情趣。其二,选文要以经典原作呈现。在这方面,日本的小学语文教材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日本小学国语教材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选文基本上都是原文收录,不管文章的篇幅长短,只要选进教材,都会尊重原文。像美国洛贝尔的作品《等信》,全文大概有1 200字,被一字不差地收录在日本小学2年级的教材中。新美南吉的《狐狸阿权》这篇作品有四五千字,也是原封不动地被收录在小学4年级的语文教材中。教材选编不受篇幅限制,就比较容易选入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这对于有意识地培养儿童从小阅读原著的习惯是非常有益的,也有益于培养和提升儿童的审美能力。其三,低年级教材应该多采用一些原版的儿童图画书或绘本儿童书作为选文的一部分。正如约翰·洛威·汤森在《英语儿童文学史纲》里所说的:“最好的儿童文学载体就是儿童绘本读物”。原版的儿童图画书图文并茂,是文字和美术的互相配合,是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结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写得好的绘本儿童书如同是有图画的诗,因此对于小学1年级学生而言,最佳的真实读本应该是儿童文学的绘本。其四,选文的主题和文类要多样化。其五,选文要国际化。其六,各个学段要合理配置文体,并确立文体的份量支配比例。
对小学语文教材提出一些意见,目的不在批判,而在实现更好的教材建构,我们呼唤并期待小学语文教材真正的儿童文学化,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
[1]王林.“儿童文学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J].课程·教材·教法,2006(12).
[2]罗庆云,戴红贤.周作人与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1).
[3]商金林.叶圣陶年谱[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
[4]吴琼.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选编儿童文学主题分析[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5(7).
[5]李山林,朱少先.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选材浅议——以人教版低年级语文教材为例[J].基础教育研究,2010(16).
[6]钟启泉.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皮朝晖.儿童文学与小学教材[J].湖湘语文,2010(8).
[8]沈莹莹,张惠苑.论小学低段语文教材中童话选文的审美缺失——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为例[J].文教资料,2014 (14).
[9]刘艳琳.小学语文教材改选编应遵循怎样的价值——从教育学视角看小学语文教材的改选编行为[J].出版发行研究,2011(6).
[10]朱自强.朱自强小学语文教育与儿童教育讲演录[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
[11]范远波.论民国时期的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材[J].教育学报,2007(6).
[12]窦桂梅,胡兰.语文教育何处寻——我们为什么这样教《牛郎织女》[J].小学教学参考,2007(9).
[责任编辑:况 琳]
ON the lack of“children’s Literature”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xtbook
ZHANG Xuan
Children’s literalization refers to mak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major resources and methods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From the following seven aspects, we can see the lack of children’s literalization in the current primary school textbooks: the utiliz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resources and the literary form is limited, the quantity is not enough, the quality is not good enough, selection of texts is short of international horizon, selection does not meet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ge of students with single themes.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conception, arrangement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xtboo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orientation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Chinese teaching of primary school; children’s literalization;selection of text;lack
G623
A
1009-7228(2016)02-0020-04
10.16826/ j.cnki.1009-7228.2016.02.005
2016-01-28
张璇,天津师范大学(天津300387)初等教育学院讲师,博士。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