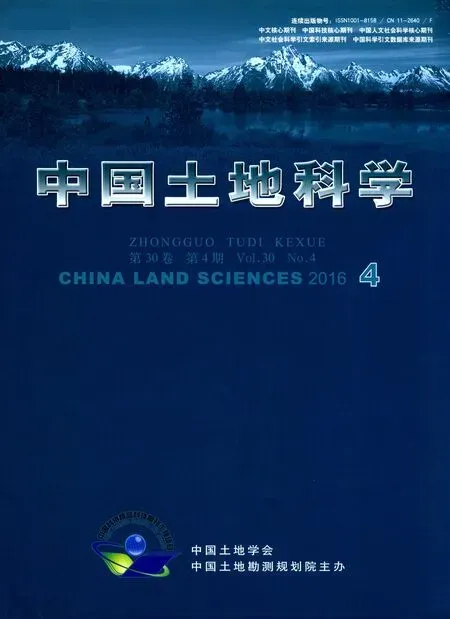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土地权属调整研究
韩立达,王艳西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土地权属调整研究
韩立达,王艳西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研究目的:分析增减挂钩政策中土地权属调整面临的困境,探讨权属调整途径,立足于保障集体和农民合法权益,提出创新和完善增减挂钩政策的建议。研究方法:政策分析法。研究结果: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属调整面临缺乏法律依据、空间约束性强、集中居住区土地性质模糊等困境;集体土地使用权权属调整面临实践与法律脱节、集中居住区土地及房屋产权界定困难等困境。研究结论:在法律层面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流转正名并保障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同等入市”以及建立新型集体经营制度;实践中土地所有权向村集体集中并依法流转、农地使用权以“确权确股不确地”方式交由集体经营、扩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模。
土地管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权属调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土地权属指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他项权利的归属,具体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抵押权、租赁权等各种权利束。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下简称增减挂钩)中的土地权属调整即指项目区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及他项权利的归属主体以及相关权利的重新界定与分配。通过知网全文搜索,笔者仅发现一篇文献对增减挂钩土地权属调整进行研究。杨圆圆等阐述了增减挂钩拆旧区和建新区的土地权属调整方案并总结相关程序[1],但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没有将增减挂钩土地权属调整置于中国现行土地制度框架内考虑,忽视了土地权属调整面临的制度困境和实践困境;二是在其权属调整方案中将建新区土地直接归于国有土地,这直接忽略了建新区土地在集体建设用地范畴内进行调整的可能性。为进一步丰富学界关于此方面现有研究之不足,探讨土地权属调整的途径,进而保障集体和农民的合法权益,本文以增减挂钩项目中拆旧区和建新区(主要指农民集中居住区)土地权属调整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及房屋产权在增减挂钩项目中调整时面临的困境,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 增减挂钩中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属调整面临的困境
在实践中当增减挂钩项目遇到以下几种情况时会面临土地所有权的调整:一是项目涉及多个村民小组或者集中居住区跨村民小组建设时,如A村民小组农民被安置在同村B村民小组的土地上,或者集中居住区同时占用村民小组A和B的土地;二是增减挂钩项目农民集中居住区跨村或跨乡镇建设,这时必然会需要对跨村或者跨镇所占土地进行补偿以及对相应权属进行调整,首先涉及的就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占地集体和被占地集体之间进行权属调整,并由此引出交换、转移、补偿等问题。
1.1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整缺乏法律依据
(1)法律禁止土地所有权转让。在中国现行制度下,法律确认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流转渠道只有土地征收这一种途径,不允许集体土地所有权自由转让。《宪法》第十条和《土地管理法》第二条都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增减挂钩中农民集体之间转移土地所有权的合法性。
(2)不同农民集体间转让土地所有权缺乏依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有三类,组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乡镇农民集体①《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一般来说,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归属沿袭历史现状,但是在拆旧区、建新区涉及以下情况时可能会发生所有权的调整和变更:一是集体土地置换,例如邛崃市平乐镇在农民集中居住新区建设时,遵照“带地入建”的原则,根据本集体经济组织搬迁入住新区的建房户的综合占地面积调出同等地类、面积,补划给被占地集体经济组织,确保被占地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面积不减少,但土地所有权的调整也无章可循;二是通过货币补偿,如成都市青白江区福洪镇先锋村选择跨村建设农民集中安置区,并对被占土地的农户采取年付租金或一次性货币补偿的方式对被占村土地使用权进行补偿,但这也涉及不同村组之间的土地所有权调整问题,由于地随房走,通过货币化补偿获得土地使用权以后,其所有权也必须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目前在一些村范围内的增减挂钩试点通过“撵地”的方式来避免所有权调整,但当跨村建设农民集中居住新区时,通过“撵地”就根本不能实现上述土地所有权调整,且这种做法也未得到国家法律层面的确认和保护,从长期来看更是埋下了农民集体之间土地所有权利益调整的矛盾。
1.2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属调整实践中难以操作
(1)集体土地所有权市场价格缺失。在现有制度下,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不能流转的,实践中也不存在正常的土地所有权市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只能通过土地征收等有限途径转变为国有土地所有权,只存在土地征收价格(涉及所有权的只有土地补偿费)。不同组(村、镇)之间土地所有权调整不管是价值补偿还是实物补偿,都需要基于土地的市场价格,在市场机制无效的情况下,为快速推进项目,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地方政府部门必然会强势介入,完全忽视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补偿。
(2)土地用途差异导致调整补偿标准难以确定。增减挂钩项目集中居住区占地类型复杂,既包括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原宅基地)、农用地(耕地)、乡镇企业用地、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用地,还有可能包括未利用地等,不同用途土地的价值差异悬殊,建设集中居住区后统一变为建设用地,那么涉及土地所有权调整时究竟以哪种土地用途为基准进行调整或补偿就成为决定权属调整成败的重要因素,增减挂钩相关政策也未作出详细规定。实践中的很多做法仅仅是对土地使用权的补偿,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价格的缺失以及被调整土地类别以及用途的复杂性等,集体经济组织之间根本无法确定土地所有权的补偿标准。
(3)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整受空间约束性强。合理的耕作半径是科学布局农村居民点的关键,也是影响农业耕作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2]。即使拆旧区土地所有权法律上可以调整,土地所有权互换(通过“撵地”方式)在临近村民小组还可以实行,一旦不同主体间距离超过耕作半径,那么土地所有权互换这种方式就难以奏效,价值补偿的方式在缺乏市场的情况下也难以规范有效进行。一方面容易形成“飞地”、“插花地”等,不利于土地集中规模经营,集约节约利用拆旧区复垦耕地,发挥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价值补偿方式在缺乏科学评估理论和技术的情况下也存在较大的交易成本。
(4)农民集中居住新区土地所有权处于模糊和维持现状的窘境。实践中跨村的农民集中居住新区安置多个村(组)农民时,在“地随房走”原则下土地所有权事实上已经转移,对这种权属变动进行法律确认就成为保护集体经济组织权益的需要。但是,各地增减挂钩项目实施中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农民集体经济组织都不愿意或者无法确定农民集中居住新区土地所有权的归属,这种模糊和维持现状的做法导致了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土地权属混乱和损害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一方面《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目的才能对集体所有土地进行征收,且国家严控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另一方面增减挂钩政策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复杂博弈的结果[3],因此政府主导下的增减挂钩治理结构就成为一种层级制的治理结构[4],在这种治理结构下增减挂钩项目的重要目的就是获得建设用地结余指标,从而开辟一个独立于年度计划指标严控体系以外的指标来源[5],故地方政府也不会以征地方式来确认农民集中居住新区土地的所有权权属。目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只能是土地使用权,而不能流转土地所有权①《宪法》第十条和《土地管理法》第二条都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此处就是指集体所有土地所有权权属调整。,且政策上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规定也日益细化②参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相关文件。。实践中就出现按征地标准对建新区原农户和集体进行拆迁补偿,但又按集体建设用地来确权,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与茶店镇胜利村增减挂钩项目”,或者某些项目干脆对这部分土地所有权权属调整进行模糊处理或维持权属现状。
2 增减挂钩中土地使用权权属调整面临的困境
现行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二元的,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农用地归集体所有但由农户承包经营;宅基地也属于集体所有但农户享有使用权。因此,使用权权属调整亦是增减挂钩中土地权属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现实矛盾的集中点和敏感区。
2.1土地用途转变导致的困境
(1)权属调整缺乏法律依据。一方面,当拆旧区宅基地经过复垦成为耕地后,宅基地和农用地(耕地)的使用权配置方式在现有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因此一旦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后,就必须对其使用权进行权属调整,但目前法律仅是鼓励将闲置或低效利用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但对随之而来的使用权权属如何调整却未规定。《土地管理法》对此仅表述为“国家鼓励土地整理。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并未规定对复垦后的耕地使用权权属如何调整。若复垦后耕地使用权性质及归属未得到法律确认,其实际使用者会自行寻求土地最佳使用方式,有可能违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出现诸如“农地非农化”等问题。另一方面,农民集中居住建新区所占土地在权属调整方面也存在法律困境,突出表现为当建新区所占土地为承包地时,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户只能在法定承包经营权剩余期限内流转承包土地。就“二轮承包”而言,剩余期限普遍只剩十余年,一旦承包地流转用于修建农民集中居住区,事实上已经类似于“永久性流转”,目前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并未规定,这种法律与实践的矛盾就成为增减挂钩政策的一个制度隐患。产生的一个可预见的后果就是,已经“事实上永久流转承包地”的农户在新一轮土地承包时仍然可以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重新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获得承包地,导致“个人侵占集体利益”,或者说“集体土地成为个人谋利工具”等问题的出现。
(2)权属调整面临效率困境。如何对拆旧区复垦所得新增耕地的权属进行调整在实践中也颇有争议,既有让原农户继续耕种的,也有收归集体的,更有私下进行置换的[6]。在复垦前,土地使用性质为宅基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农民享有使用权;在复垦为耕地以后,土地所有权仍为集体所有,但困难在于使用权如何调整和配置。(1)如果将复垦后新增耕地的使用权分配给农民,除了法律规定缺失以外,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涉及本组的农户众多,其协商、发包的成本高;二是如果分配给家庭经营加重农村土地经营的零碎化,难以发挥规模效益;三是在农业人口非农化、兼业化背景下[7],家庭经营易导致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抛荒;四是由于宅基地复垦要达到耕地质量,需要更长的时间,同时也给集中居住区农户“返家”(回归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提供可能,导致农地非农化。(2)如若将耕地使用权划归集体享有,存在两方面的困境:一是缺乏法律依据,《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农业用地实行承包经营制度①《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同样的规定还见于《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等法律法规。;二是集体难以充分保障农户利益,主要表现在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不合理,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缺乏合理的集体意识形成机制,在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情况下,就会产生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各地虽探索一系列制度安排以搜集民意如成都村民议事会等,但在传统能人治理体制下,往往流于形式,无法实现集体经营的帕累托效率。建新区土地使用权权属调整同样面临效率困境,主要表现为权属调整后各集体所有土地权属相互交错,土地利用外部性加强,权属关系维护成本提高。
2.2集中居住区房屋及其所占土地产权界定存在困境
(1)集中居住区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权属调整与现行法律脱节。增减挂钩项目的重要目标就是通过集中居住,减少农村建设用地面积。因此实践中集中居住新区多为联排或多层住宅,多户共占一块地基,即出现了“多户一‘宅'”现象。传统“一户一宅”管理制度已经不能得到遵行。集中居住区土地性质为集体建设用地而不是传统宅基地,因此如何实现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统一,现有法律也未规定。若新区用地性质仍为宅基地,那农户新增人口或者分户时仍可依法申请新的宅基地,重新扩大农村建设用地规模,与政策初衷背道而驰。同时,国家又明确禁止城镇居民购置农村宅基地,导致新区土地及房屋在产权层面不能与国有土地及房屋同权,导致了集中居住区土地及房屋性质不清,产权不明,不少农民将新区房屋进行出租、买卖,即出现了“小产权房”现象。
(2)集中居住区经营性建设用地法律性质模糊。近来,国家在政策上逐步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积极谋划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同时,在增减挂钩项目实施过程中,一般也允许集体经济组织预留结余建设用地指标的一定比例(如成都市规定不低于5%)用于发展集体经济,这部分土地一般来说是属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范畴,但在目前法律制度下,这部分土地的性质却未得到法律的认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六十条和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严格限制了集体建设用地的用途以及利用方式,尤其是集体建设用地用于经营性用途更是受到极大限制,一方面采用联营、入股等方式需经政府批准;另一方面又明令禁止通过出让、转让和出租方式用于非农建设。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等政策与文件中所提“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相矛盾。实践中也有相当部分集体是通过出让、转让和出租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方式来利用集体建设用地的,因为这种做法为法律所禁止,所以导致这部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法律性质模糊,一些集体经济组织无法真正利用这部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或者即使开发利用这部分土地发展集体经济也因为土地性质模糊无法实现其应有价值,这样既影响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是造成增减挂钩项目资金瓶颈的一个重要原因,如邛崃市平乐镇项目预留5%集体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发展集体经济,但因该镇作为旅游古镇,对建设用地的需求量也比较大,指标无法满足需求,限制了当地发展。
3 创新和完善增减挂钩中土地权属调整方式的对策建议
3.1创新和完善农村土地权属调整的法律法规
(1)在《土地管理法》中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流转正名。中国土地所有权制度分为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国家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具有惟一性,但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并不具有惟一性,因此在逻辑上就存在土地所有权在不同农民集体之间流转的可能性,并且在实践中不同农民集体之间流转土地所有权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不同农民集体通过置换(撵地)、价值补偿等方式调整土地权属。《土地管理法》作为中国土地管理的专项法律,对此种情况却未做任何规定。因此建议补充修改《土地管理法》第二章之内容,增加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流转相关条款,具体内容为:“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可将本集体土地所有权通过出让、转让、置换等方式调整给县级行政区域内其他农民集体。”
(2)建立农用地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互相转变的法律途径。基于中国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以不改变用途为前提,但随着一系列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措施的出台,农村土地流转伴随着用途转变成为常态,如增减挂钩中占用农用地修建集中居住区、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后的流转等。《土地管理法》对于宅基地流转有明文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承包土地流转进行了详细规定,但二者都未对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后使用权如何调整、农用地流转为建设用地如何操作进行规定。法律的缺位必然导致这些土地产权模糊,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与矛盾。因此建议修改《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通过土地综合整治等手段复垦宅基地的,复垦后土地使用权调归集体,或是重新发包或是由集体统一经营;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增加关于农用地流转为建设用地的条款,即“当承包土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需要流转成为建设用地时,可先将承包地调为建设用地,同时将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宅基地使用权)赋予承包权人,而后再允许原承包权人将自己获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给需地方。”
(3)赋权还能,允许集体土地、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六十条和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对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范围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使得增减挂钩项目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农户住宅无法充分发挥其资本属性,严重制约了增减挂钩项目的实践,导致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在产权上不对等[8],增减挂钩项目区集体建设用地产权归属难以有效界定以及不利于农用地流转。建议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精神修改《土地管理法》,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交易。
(4)改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建立新型集体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等规定了农村土地采取实物发包、家庭经营的方式,并严格限制调整承包关系。这就严格限制了农村土地使用权权属关系的调整、赋予土地过多的社会保障功能,严重制约了增减挂钩中通过调整复垦耕地权属关系发挥规模效益、提高农民的收入。因此建议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允许农用地有条件的实行集体经营,即经营权收归集体,农户承包权转为集体经济组织股权,并补充关于按照股份制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规定。
3.2建立合理的土地权属调整方式
(1)土地所有权由组向村集中,村集体之间可进行土地所有权的依法流转。一方面增减挂钩项目中土地所有权进行流转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现实中农村土地所有权以组农民集体所有为主,所有权流转易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零碎化。因此建议在增减挂钩项目实施过程中,若项目仅涉及同一村农民集体,建议采取将土地所有权收归村集体的方式;当项目涉及不同村农民集体时,建议在土地所有权收归村集体的基础之上进行村集体之间土地所有权的权属调整,尽量减少土地所有权零碎化现象的发生。
(2)农用地使用权向集体集中,探索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4年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指出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同时也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也可以确权确股不确地。”建议按照这一思路推进增减挂钩项目区耕地的土地使用权权属调整,具体做法为:统一采取“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方式将耕地折算成相应股份平均分配给本集体有资格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成员;按照股份制公司的方式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这种方式,承包地由农户个体经营转化为集体经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坐实了村农民集体或组农民集体的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地位[9-10]。
(3)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向农户分散,允许房屋及其相应土地使用权有条件流转。对农民集中居住区土地使用权权属进行调整时,建议参照城镇国有土地住宅权属划分做法,土地所有权归集体,但是农户应享有与其房屋相对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向集中居住区农户颁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并同时允许集中居住区农户在符合规划和相关政策的前提下,有条件买卖和出租自有房屋,如当农户拥有两处及两处以上房屋时,可选择将不居住的房屋租售,并以此为契机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11],使农民由“土地发展权的一个名义主体”[12]转变为真正的权利主体。
(4)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作为破解权属调整成本困境的重要途径。高昂的补偿安置成本成为阻碍增减挂钩中土地权属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破解成本困境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拓宽项目收入来源,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不失为一个重要途径,尤其是对于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增减挂钩项目实施以后,当地自然、经济等条件大幅改善,土地增值潜力巨大,若充分开发利用这部分土地,必定会带来巨大收益。因此,建议在实施增减挂钩项目时,符合条件的地区应允许农民集体加大结余的建设用地指标中用于发展集体经济的部分。
(References):
[1] 杨园园,王冬艳,栗振岗,等.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土地权属调整的研究[J] . 中国农学通报,2011,27(32):133 - 137.
[2] 唐丽静,王冬艳,王霖琳. 基于耕作半径合理布局居民点研究——以山东省沂源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区为例[J]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5):59 - 64.
[3] 李元珍. 央地关系视阈下的软政策执行——基于成都市L区土地增减挂钩试点政策的实践分析[J] . 公共管理学报,2013,28 (9):14 - 21,137 - 138.
[4] 顾汉龙,冯淑怡,曲福田. 重庆市两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模式的比较[J] . 中国土地科学,2014,28(9):11 - 16,24.
[5] 谭明智. 严控与激励并存: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脉络及地方实施[J] . 中国社会科学,2014,(7):125 - 142,207.
[6] 韩立达,王静. 创新和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研究——以成都市为例[J] . 农村经济,2014,(10):22 - 26.
[7] 贺雪峰. 城乡统筹路径研究——以成都城乡统筹实践调查为基础[J] . 学习与实践,2013,(2):74 - 86.
[8] 谭静.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的集体土地权益保护[J] . 中国土地科学,2012,26(2):79 - 83.
[9] 张世勇. 村级组织的农地调整实践——对成都市ZQ村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实施过程的考察[J] . 贵州社会科学,2013,(4): 119 - 125.
[10] 汪文雄,钱圣,杨钢桥. PPP模式下农地整理项目前期阶段效率影响机理研究[J] . 资源科学,2013,35(2):341 - 352.
[11] 陈美球,马文娜.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农民利益保障对策研究——基于江西省《“增减挂钩”试点农民利益保障》专题调研[J] . 中国土地科学,2012,26(10):9 - 14.
[12] 顾汉龙,冯淑怡,张志林,等. 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美国土地发展权转移政策的比较研究[J] . 经济地理,2015,35(6):143 - 148,183.
(本文责编:仲济香)
Study on the Readjustments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in “Linkage between Urban-land Taking and Rural-land Giving” (LUTRG) Project
HAN Li-da, WANG Yan-xi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LUTRG policy to guarantee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farmers and collectives by analyzing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land property rights readjustments in LUTRG as well as discussing the way of property right readjustments. The Method used in this paper is policy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readjustments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was difficult, which was induced by lacking legal basis, strong constraint of the space and the ambiguous nature of the land in farmers' concentrated residential areas,etc. Many difficulties also existed in the readjustments of right to use collective land, 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practice and law, the barriers of defining land property rights for farmers' concentrated residential areas, etc. The paper concluded with propositions from two aspects aiming to ameliorate the LUTRG policy: firstly, in terms of law, the circulation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should be allowed, the collective-owned land and the state-owned land should be “equal in rights and prices as well as opportunities to markets” and a new system of collective manage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next, in practice, the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can be given to the village collective and can circulateaccording to law, farmland use rights can be operated by the collective in the form of “giving rights and shares but without defining land owners”, and we also should enlarge the scale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etc.
land administration; linkage between urban-land taking and rural-land giving; land property rights readjustment; 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new collective economy organization
F301.2
A
1001-8158(2016)04-0021-07
10.11994/zgtdkx.20160523.153719
2015-12-28;
2016-03-16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体制机制研究”(15BJY089)。
韩立达(1957-),男,贵州晴隆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房地产经济、环境资源经济等。E-mail: 657688625@qq.com
王艳西(1991-),男,河南濮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管理。E-mail: 98283217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