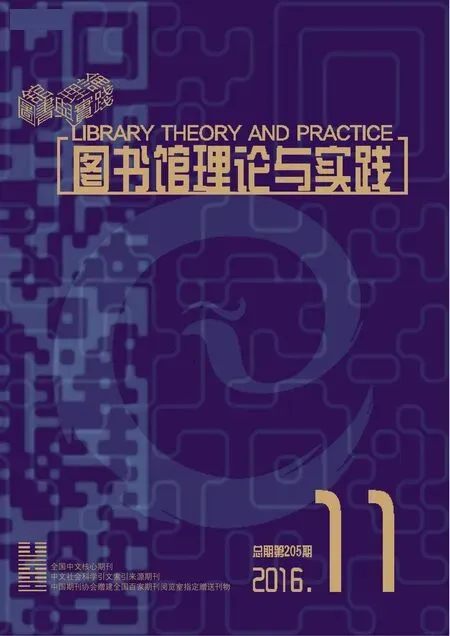方志艺文志“别本单行”例析
——以《蜀中著作记》《福建艺文志》为考察对象
周日蓉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方志艺文志“别本单行”例析
——以《蜀中著作记》《福建艺文志》为考察对象
周日蓉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方志艺文志“单行”的现象,前贤恐未注意到,故未明《蜀中著作记》为《蜀中广记》的一部分,而误以为其流传至今已残缺不全;《清代目录提要》编者未意识到方志艺文志“单行”原因,故疏于查考《福建通志》的刊刻经过,而对《福建艺文志》内容的认识产生了偏差。因此,在地方著述目录的研究中,应注意方志艺文志“单行”的现象及其原因。
方志艺文志;单行;蜀中著作记;福建艺文志
反映某一地区著述情况的目录大体包括两类:一是地方志中的艺文志(以下称“方志艺文志”),二是独立成书的地方著述目录。两者在性质上并无二致,唯有存在方式稍有差别。然而,有些书目看似为独立成书的地方著述目录,实际上是方志艺文志的单行本。
方志艺文志“别本单行”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有因抽印而艺文志有单行本的,此种情况最为常见,如清沈青厓《陕西经籍志》二卷,乃为《陕西通志》卷七十四、七十五《经籍志》改题之单行本。又如丁祖荫《常熟艺文志》为《重修常昭合志》卷十八《艺文志》之单行本。再如,由管庭芬辑、蒋学坚续辑、费寅补辑、管元耀校补的《海昌艺文志》二十四卷(1921年铅印本),为民国《海宁州志稿》卷十二至十六之单行本,其抽印的原因与目的则在于“惟《州志》卷帙繁重,乃抽印单行本,名曰《海昌艺文志》,以广其传”。[1]
有因其他部分亡佚而艺文志残存的,如郑元庆《湖录经籍考》六卷等。现存郑元庆《湖录经籍考》,实为其所纂湖州地方志《湖录》中《经籍考》的集部部分。《湖录》全书屡次付梓未果。郑元庆殁后,《湖录》原稿散出,杨宗嶽、张辂各得其半。嘉庆初,浙江归安人杨知新搜得《湖录》部分残稿,其中就有《经籍考》《金石考》。《经籍考》集部部分后为刘承幹所得,刻入《吴兴丛书》中,题为《湖录经籍考》。
有因修志中辍而艺文志独存者,如辛幹《无锡艺文志长编》等。辛幹《无锡艺文志长编》始撰于1947年春,时值无锡县修志委员会初设,孙靖圻、钱基博、许同莘受聘为总纂。钱基博以旧县志艺文门所录邑献著述,仅载书名,不著解题,其源流得失,不易稽考,为此嘱辛幹仿《四库全书总目》的体例,据无锡县立图书馆所藏乡贤典籍,撰写提要,汇而录之,以备新修县志之用。不久,因经费不足,志局解散,是编遂成单行之本。
有因方志各部分刊刻次序不一,而艺文志单行的,如曹学佺《蜀中著作记》、陈衍《福建艺文志》等。
王欣夫先生在论述“方志艺文志的单行本”时,说道:“方志中的艺文志有别出单行的,必是为了它的内容和体例精善。”[2]可见单行本方志艺文志的价值所在。然而,长期以来,古典目录学研究于方志艺文志“别本单行”这一现象及其原因未加以重视,故而产生了一些“以讹传讹”的问题,对《蜀中著作记》的认识亦即如此。
1 前贤对《蜀中著作记》的认识
《蜀中著作记》十卷,为明代曹学佺所编的《蜀中广记》中的一部分,主要分为经部、史部、子部、内典、地理志部、集部等六部,著录了蜀中人士或宦游蜀中人士所著以及辑刻于蜀中的著作。较早从目录学史的角度,对《蜀中著作记》加以关注的是孙诒让,在《温州经籍志·叙例》中,孙氏云:
《关东风俗》之传,《坟籍》成篇。……方志书目,此其虇蕍,元明旧记,多沿兹作。厥后撰著渐繁,纪载难悉,遂创专志,别帙单行。……地志书目别为专书,不知始于何时。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十,有祁承炬業《两浙著述考》四十六卷、曹学佺《蜀中著作记》十卷。周天锡《慎江文征》三十八载明永嘉姜准《东嘉书目考》,诸书均不传,无由知其体例。[3]
随后,姚名达于《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专设“地方著作目录”一节,在讨论地方著述目录的发展历史时,对《蜀中著作记》作了如下叙述。
姚氏认为《蜀中著作记》是“专撰一书以述一方著作者”,当是受到了孙氏“别为专书”之说的影响。较孙氏进一步的是,姚名达依据《图书馆学季刊》所刊载的四卷,简要说明了《蜀中著作记》的体例。但是,姚氏误以《蜀中著作记》有十二卷之数,与《千顷堂书目》著录为十卷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被称为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第一部以“中国目录学史”命名的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影响甚大,后世目录学史研究著作关于《蜀中著作记》的叙述也大多沿袭此,现选取几家之叙述,摘录如下。
(1)许世瑛《中国目录学史》第十二章第四节《特种目录略述》“地方著作目录”类云:
地方著作目录乃专录一方之人士之著作也。是类目录传者,当推明末曹学佺之《蜀中著作记》为最早。其书凡十二卷,见《千顷堂书目》,已不传,仅残本四卷,见《图书馆学季刊》第三卷。[5]
(2)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第五章第六节“地方文献目录”云:
(3)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第一章第二节《古典目录书的类别》“地方目录”类云:
(4)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第五章四节《地方文献目录》云:
从以上各家所述来看,前贤对《蜀中著作记》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认为《蜀中著作记》是别为专书或独立的地方著述目录,始于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序例》;二是自姚名达之后,认为《蜀中著作记》有十二卷,且依据《图书馆学季刊》所刊载的部分,认为此书只残存了四卷。
2 《蜀中著作记》性质及其存佚情况界说
实际上,曹学佺《蜀中著作记》十卷,完整地保留在其所编纂的《蜀中广记》中。目录学史界对《蜀中著作记》的两点错误认识,当是未明《蜀中著作记》的性质和流传情况,而造成的“以讹传讹”。
《蜀中广记》一百零八卷,为明代曹学佺所编纂的一部重要的四川方志,全书分为十二记:《名胜记》三十卷、《边防记》十卷、《人物记》六卷、《宦游记》四卷、《蜀郡县古今通释》四卷、《风俗记》四卷、《方物记》十二卷、《神仙记》十卷、《高僧记》十卷、《著作记》十卷、《诗话》四卷、《画苑记》四卷。《四库全书总目》入史部地理类杂记之属,并评价云:“搜采宏富,颇不愧《广记》之名。”[9]
曹学佺《蜀中广记》具体的成书时间,文献中并未有确切的记载,《四库全书总目》云:“学佺尝官四川右参政,迁按察使。是书盖成于其时。”[9]大体也是推测之语。实际上,曹学佺在仕蜀之初,便有编纂蜀地方志的打算。万历三十七年(1609),曹学佺任四川右参政。是年,曹学佺致书臧懋循请教编纂《蜀志》一事,臧懋循答复云:“辱谕修《蜀志》事,宦途中弁髦此久矣,得丈任之,诚为千秋盛举。愧仆无他闻见可裨管蠡,所愿效执事者,惟二十一史及《华阳国志》等书不可不研阅耳。”[10]又曹学佺《祭徐鸣卿文》云:“鸣卿每读余诗,辄欲焚其笔研去。今岁观余《蜀中广记》,叹赏以为古今所未有之书。”[11]按,明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二上有《挽徐鸣卿职方》诗,诗歌系年在甲寅年,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而曹学佺于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被罢职离蜀。[12]由此可知,《蜀中广记》的编纂或始于曹学佺仕蜀之初,而完成于万历四十二年之前。
《蜀中广记》内容驳杂、卷帙浩繁,各部分又相对独立,且各部分的刊刻并非一时。国家图书馆藏有明刊本《蜀中广记》九十一卷,有“双鉴楼”、“傅沅叔藏书记”等印记,可知原为傅增湘所藏。今此本与北京大学、天一阁博物馆所藏明刻本补配,影印收录《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五著录云:“(此书)分十二记,其义例不一,字体各殊,《名胜记》《人物记》《宦游记》《边防记》方体字。《郡县古今通释》《风俗记》《方物记》《神仙记》《高僧记》《著作记》《诗话》《画苑》则以楷书上板,疑其撰成非一时,授梓非一地也。”[13]
除了傅增湘先生所举的字体差异外,前人的记载以及明刻本《蜀中广记》各部分版心间差异,亦可以说明《蜀中广记》各部分的刊刻并非一时。例如,明刻本《蜀中广记》中的《蜀中诗话》和《蜀中画苑》虽都为楷书上版,但两者的版式有着细微的差别。《蜀中诗话》版心下记刻工名,如万丙、亨、贤、朱应其等,且页码作“一”“二”等,而《蜀中画苑》版心下记字数,其页码则作“□一”、“□二”等。又徐火脖《重编红雨楼题跋》卷一著录《蜀中画苑》云:“能始宦蜀中四年,初寄余《蜀草》,再寄余《峨眉记》,三寄余《蜀中诗话》,最后寄余《画苑》。……壬子闰月兴公识。”[14]壬子闰月”为“万历四十年(1612)闰十一月”。可知《蜀中诗话》《画苑》在曹学佺蜀中任上便已刊刻,而全书的编纂此时尚未完成。据“三寄”“最后”之语可知,《蜀中诗话》、《画苑》的刊刻时间并非一时。
又《补续全蜀艺文志》卷二十二有魏说《蜀〈著作〉〈方物〉序》,序中云:“能始以独徃之怀,不顾衣冠之忌,方再入蜀,此正忧谗畏讥、咄咄称怪之时,而乃自顾怡然,留心雅事,采拾拈弄,既有《蜀通释》《风俗》《诗苑》(按,当作《诗话》)、《画苑》等录,亡几何,复成《著作》《方物》二种。”[15]据序中“方再入蜀,此正忧谗畏讥、咄咄称怪之时”之语,可知此时曹学佺还在四川任上,又据“复成”一词可知《郡县古今通释》《风俗记》《诗话》《画苑》成书在《方物记》《著作记》之前,且这几个部分成书于曹学佺四川任上。今翻检国图所藏明刻本《蜀中广记》,其中《郡县古今通释》与《诗话》的版式相同,版心下记刻工名,如万丙、亨、贤、朱应其等,页码作“一”“二”;《方物记》与《著作记》的版心下既记字数也记刻工名,且所记刻工名大体一致,如余启、黄金显、高林茂、余明孝、王上义等,页码作“一□”、“□二”。由此可见,《蜀中广记》各部分不仅由不同批的刻工所刻,且刊刻时间也不一致。
另外,《蜀中名胜记》由林茂之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刻于南京,钟惺为之序云:“吾友曹能始,仕蜀颇久,所著有《蜀中广记》。问其目,为《通释》、为《方物》、为《著作》、为《仙》《释》、为《诗话》、为《画苑》、为《宦游》、为《边防》、为《名胜》诸种。……林茂之贫士也,好其书,刻之白门。予序焉。”[16]可知《蜀中广记》的刊刻又非一时一地。
正是因为《蜀中广记》十二记的刊刻次序不一,加之每部分内容又相对独立,故而这十二记以《蜀中广记》为一编流传的同时,也各自单行,清代多家书目既著录了《蜀中广记》,也著录了《蜀中广记》中的某一记。如徐乾学《传是楼书目》著录有《蜀中广记》七十四卷,同时也著录有《神仙记》十卷、《高僧记》十卷、《宦游记》四卷、《边防记》十卷、《画苑》四卷、《蜀郡县古今通释》四卷附《风俗记》四卷、《名胜记》三十卷、《著作记》十卷、《人物记》六卷、《方物记》十二卷。又如阮元《文选楼藏书记》卷六著录《蜀中广记》三十八卷,解题云:“是书记载蜀中郡县、风俗、方物、艺文。”[17]又著录有《蜀中名胜记》三十卷。
同样,《蜀中著作记》流传至今,既有单行,也有保存在《蜀中广记》中的。单行的如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明刻本《蜀中著作记》十卷;又天津图书馆所藏明刻本残存前五卷,已收入《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天津图书馆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版);另外,中山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分别藏有清抄本和民国刘氏远碧楼抄本。[18]保存在《蜀中广记》中的,如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刻本《蜀中广记》九十一卷、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所藏明刻本《蜀中广记》五十四卷,均保存了十卷完整的《蜀中著作记》,且与清华大学和天津图书馆所藏明刻本并无区别。此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蜀中广记》中也有《蜀中著作记》十卷,但与明刻本略有不同,其最大的区别在于,明刻本《蜀中著作记》第五卷卷末有范镇《崇道观道藏记》一文,近六百余字,《四库》本则付之阙如。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著录《蜀中广记》云:“目凡十二:曰名胜,曰边防,曰通释,曰人物,曰方物,曰仙,曰释,曰宦游,曰风俗,曰著作,曰诗话,曰画苑。”[9]并引用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评价《蜀中十志》之语,认为《蜀中广记》“讹舛抵牾,亦时时间出”。[9]王士禛所引的《蜀中十志》,即是《蜀中著作记》。孙诒让在编纂《温州经籍志》时,奉《四库全书总目》为圭皋,并大量援引《四库全书总目》为考证之资,不知何故忽略此条重要信息,误以为《蜀中著作记》已亡佚,后世治目录学史的前贤也未能利用这一信息,而使《蜀中著作记》长期被“误解”,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姚名达等人据《图书馆学季刊》第三卷,认为《蜀中著作记》只残存四卷,其实也是疏于查考所致。《图书馆学季刊》创刊于1925年,1926年3月开始发行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出版至第十一卷第二期,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共出版11卷42期。《图书馆学季刊》刊载《蜀中著作记》实共七卷,分别是第三卷第一、二期刊载了《蜀中著作记》卷一,第三卷第三期刊载了卷二、三、四,第四卷第一期刊载了卷五、六,第五卷第二期刊载了卷七。《图书馆学季刊》并未言其所刊载的《蜀中著作记》为何版本,但从第五卷卷末同样缺少范镇《崇道观道藏记》一文来看,或即是出自文渊阁《四库》本。
综上所述,《蜀中著作记》是《蜀中广记》的一部分,性质上属于方志中的艺文志,非别为专书的地方著述目录,其“独立单行”或“别为专书”,是由于《蜀中广记》各部分刊刻的先后次序不同而造成的。《蜀中著作记》十卷也并未残缺不全,不仅完整地保留在《蜀中广记》中,而且还有多种单行本流传。
3 地方著述目录研究应注意方志艺文志“别本单行”现象
《蜀中著作记》这种在方志艺文志研究中“被误读”并非个例,如陈衍的《福建艺文志》也是如此。
陈衍《福建艺文志》为其所主持编纂《福建通志》中的一部分。陈衍在《福建艺文志》卷首有简要说明,称:“今志福建艺文,凡分四种:一只称艺文志,各书之有解题者,分类录焉;二曰存目,各书之无解题者,分类录焉;三曰板本,凡刻书于福建之书籍,而非本省人著作,亦分类录焉;四曰附录,其书专记福建事,而非本省人著者,亦分类录焉。四种各自为篇第云。”[19]可知,《福建艺文志》分为四部分。然而《清代目录提要》在著录《福建艺文志》时云:“其实,从正文看,只有三种。”[20]又云:“艺文志包括:(1)《福建艺文志》,每类前均有小序,每书都撰有提要;(2)《福建艺文志附录》,收录外省人关于福建的著述;(3)《福建艺文志存目》,但记书名和著者。”[20]可见《清代书目提要》所称“只有三种”,当不包括《板本志》。然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闽蜀浙粤刻书丛考》中,收有《福建板本志》一书,题为佚名撰,考其内容,实则与(民国)《福建通志》中的《板本志》完全一致,即是陈衍《福建艺文志》中的《板本志》。又可见《清代目录提要》所言不确。
既然如此,《清代目录提要》为何称“只有三种”,《闽蜀浙粤刻书丛考》又为何题“佚名”所撰?这需要从《福建通志》的刊刻经过来加以辨析。
陈衍主持编纂的《福建通志》于1921年完成初稿,其刊刻过程十分曲折。现所见《福建通志》的内页有郑孝胥题签,题“壬戌开雕于福州”,可知其刊刻时间始于1922年。然而没过多久,“八阅月而因兵事,才刻百余卷而工停”。[21]2058五年之后,即丁卯年(1927)十月,复刻百余卷,却因资金不足,而尚余三百余卷未刻。1929年,“是岁刻就新通志三百二十余卷,装订九十余本。分类零售,行销各省”[21]2058。这是《福建通志》的第一个版本。
在三百多卷《福建通志》刊成流传后,陈衍继续刊刻其余的卷次。如1930年“补刻列女节烈门”,1936年“刊定艺文志存目”等。[21]2082然而直至1937年7月陈衍去世,《福建通志》全书的刊刻并未全部完成。陈衍去世后,改由魏应麒主持其事。除了补刻陈衍未刻的部分外,魏氏还对《福建通志》做了重新编排,“兹依照《道光志》总目次序,《道光志》所无者,以类相从,编成总目。又新志各门卷目亦未分清,兹以一门为一总卷,附分卷目录于其下”。[22]同时,魏氏还在之前所印的旧书版上,于版心中缝下边添刻了“福建通志/总卷××”字样。现在我们所见到的1938年版的《福建通志》,即是魏氏所改动的版本。
1929年版与1938年版《福建通志》较为显著的区别在于,1938年版的版心中缝下边有“福建通志/总卷××”字样,而1929年版则无。《闽蜀浙粤刻书丛考》中所收的《福建版本志》其版心并无此字样,可知《福建版本志》于1929年便已有刊刻。然而,《艺文志存目》部分于1936年才刊定。由此又可见,《福建艺文志》四部分的刊刻时间并不完全一致。1929年刻印的《福建通志》乃“分类销售”,《福建版本志》因此而单行。另外,由于《福建版本志》不署编撰者姓名,《闽蜀浙粤刻书丛考》不加查考而题“佚名”所撰。
此外,魏氏改动的版本,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魏氏改动的《福建通志》,其“总卷二十五”为“艺文志”(按:后附“艺文志附录”)、“艺文志存目”,“总卷二十七”为“版本志”,中间隔了“总卷二十六”即“金石志”。魏氏重新编排时“以一门为一总卷”,可见在他看来,“艺文志”、“艺文志存目”为一门类,而《版本志》不包括其中。按据上文所引陈衍《福建艺文志》卷首的简要说明可知,《福建艺文志》当为“艺文志”“艺文志存目”“艺文志附录”“板本志”四部分无疑。魏氏的这种改动,误以《版本志》为一门,割裂了《福建艺文志》的完整性。于此同时,后世所流传的单行本《福建艺文志》多不包括《版本志》,如《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目录类》著录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所藏本即是如此。《清代目录提要》编者虽然认识到《福建艺文志》是《福建通志》之“别本单行”,且发现单行本《福建艺文志》与陈衍的介绍存在差异,但未考查《福建通志》原书,而轻易地做出了“只有三种”的判断。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可知,前贤因未正确认识《蜀中著作记》的性质和流传情况,而造成“以讹传讹”的错误;《清代目录提要》编者因未考查《福建艺文志》“单行”的原因,而轻易地做出判断。这既有受条件局限的客观原因,也有疏于查考原书的缘故。因此,在地方著述目录的研究中,一方面要注意方志艺文志“别本单行”的现象及其原因,另一方面要勤于翻检原书,将单行本方志艺文志的研究与原方志的考查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方志艺文志的发展、流传,避免不必要的错误。
[1]管元煦.海昌艺文志跋[M]//管庭芬等《海昌艺文志》卷首.铅印本.民国十年(1921).
[2]王欣夫.文献学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6.
[3](清)孙诒让.温州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1:1.
[4]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29.
[5]许世瑛.中国目录学史[M].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227.
[6]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M].台北:丹青图书有限公司,1986:265.
[7]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M].北京:中华书局,2003:31.
[8]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M].济南:齐鲁书社,1998:189.
[9](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971.
[10](明)臧懋循.答曹能始书[M]//负苞堂文选卷四.臧尔炳刻本.明天启元年(1621).
[11](明)曹学佺.祭徐鸣卿文[M]//曹学佺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713.
[12]陈庆元.曹学佺年表[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75-81.
[13]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M].北京:中华书局,2009:367.
[15](明)魏说.蜀《著作》《方物》序[M]//杜应芳《补续全蜀艺文志》卷二十二《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明)钟惺.蜀中名胜记序[M]//曹学佺.蜀中广记·蜀中名胜记卷首《中华再造善本续编》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17](清)阮元撰;王爱亭,赵嫄点校.文选楼藏书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427.
[18]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史部[M].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975.
[19]陈衍.福建艺文志[M]//福建通志总卷二十五.刻本,1938.
[20]来新夏.清代目录提要[M].济南:齐鲁书社, 1997:421.
[21]陈声暨,等.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M]//陈石遗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0.
[22]魏应麒.编纂后记[M]//(民国)福建通志.刻本,1938.
The Analysisof theOffprintsofYiwen Zhiin LocalChronicles——Taking and asStudy Objects
Zhou Ri-rong
TheoffprintsofYiwen Zhiin localchroniclewasunexpected by former scholars,that’s the reasonwhy they did not realize that“Shu Zhong Zhu Zuo Ji”is partof“Shu Zhong Guang Ji”andmistakenly thought thisbook has beenmutilated.“TheQing Dynasty catalogue”editor did not realize the reason ofoffprintsand failed in investigating the publication of“Fujian Tong Zhi”,which led todeviations in theunderstandingof“Fujian Yiwen Zhi”.Thisarticlesuggests itshould bepaidmoreattention on thephenomenon and thecausesofoffprintsin Yiwen Zhiin localchroniclesresearch.
Yiwen Zhiin LocalChronicles;Offprints;Shu Zhong Zhu Zuo Ji;Fujian YiWen Zhi;
G256
E
1005-8214(2016)11-0104-06
周日蓉(1988-),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典目录学、地方文献。
2016-02-15[责任编辑]王岗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代杜诗学史”(项目编号:15CZW 02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