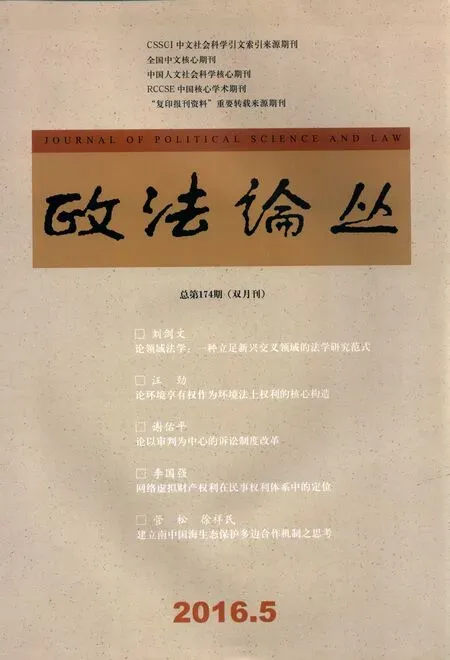微观权力视角下的新媒体与公民社会
蒋 超
(广西大学法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微观权力视角下的新媒体与公民社会
蒋 超
(广西大学法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微观权力是一个以关系为核心的概念,而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社会关系中的强势者。在新媒体不断发达的今天,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记者。新媒体与微观权力之间存在关联。以微观权力作为分析工具对新媒体进行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新媒体为国家治理和公民社会的培育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微观权力 新媒体 公民社会 国家治理
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媒体技术与观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新媒体的诞生和运用迎来了“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新媒体为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如若固守旧有观念与理论,显然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对新媒体的理解和认识显得极为重要,其决定了人们在面对新媒体的时候将采取消极抗拒的态度还是积极接纳的态度。
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进行比较,便能清楚地理解新媒体的内涵和特征。传统媒体与国家权力联系密切,二者往往结成同盟、互为依托。在福柯那里,国家权力被归入宏观权力,与此相对的权力被称作微观权力。微观权力与新媒体之间可能存在某些关联。如果以描述微观权力的方法来分析新媒体,可能为学术研究开拓新的理论空间。
一、以关系为核心的微观权力
福柯试图在距离权力最远的地方定义权力,对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做出区分,用微观权力来表述现代社会中宏观权力概念无法涵盖的那部分权力。微观权力的概念将成为下文研究的工具,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基础性理论的探讨。该部分将采用与宏观权力进行对勘比较的方法来描述和界定微观权力。
(一)宏观权力的界定
霍布斯对权力的论述集中在权力的归属问题上,即权力应该由谁享有、掌权者应当对谁负责。此种权力可以称之为宏观权力,或者压制性的权力,它是一种实质性的存在。在霍布斯对“利维坦”的经典描述中,读者便能够感受到宏观权力的特征:强大而且存在明确的掌控者。“如果要建立这样一种能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权力,以便保障大家能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土地的丰产为生并生活得很满意,那就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1]P131
在霍布斯看来,权力能够转移和让渡,利维坦本身便是宏观权力的拥有者或者载体。在一个既定的政治结构中,存在明确而固定的力量归属,一些人是明确的权力拥有者而其他人则被排除出去。由此观之,宏观权力是一种实质性的力量,其总与占有者、国家机器、暴力和压制等因素相关联。“这种权力从根本上讲,不再是个体之间(主体间性)的对话与沟通,而是一种以‘庇护与臣服’关系作为其第一原理的国家政治权力”。[2]P26
宏观权力往往指涉国家权力或者政府权力,其中承受方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或受压制状态。宏观权力的结构中总是存在着对立的双方,一方的地位明显高于另一方,地位较高的控制者或支配者向地位较低的接受者发号施令。其实现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接受者与支配者之间不会形成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命令的发布方是恒定的,这种角色安排决定了接受者和支配者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无法交换和替代。宏观权力的流向是从支配者到接受者,这种方向性使得宏观权力的转移呈现从一个中心向外辐射的态势。权力占有者的范围极为有限,或者权力总是被垄断,不特定的人很难进入权力中心。在宏观权力的结构中,权力本身和权力主体不可分割。
在这种立场上进行理解,权力具有扩张的本能,时刻都想冲破束缚,一有机会便试图取得吞噬一切的绝对地位。它犹如一头猛兽,一旦其野性被释放,任何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权力扩张和滥用的牺牲品。此外,宏观权力因拥有固定而明确的掌控者,它便具有可交换、可转让的商品属性。现实中的权力寻租、钱权交易的情形,便是权力异化的产物。宏观权力的占有者习惯于发号施令,他们常常会背离设定权力的初衷和目的,从而形成一个日益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官僚。官僚阶层的利益时常背离于社会的公共利益,作为既得利益的拥有者,他们习惯于扮演改革反对者的角色。处于权力压制下的民众往往被塑造成权威主义人格。他们反对和痛恨权威人物对自己的压迫,同时又渴望成为权威人物,获得压迫他人的成就感。弗洛姆在反思大屠杀的过程中,对此提出了经典论述:“权威主义性格的本质就是同时具有施虐和受虐冲动。施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拥有控制另一个人的无限权力,其中多少夹杂着破坏欲;受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把自己完全消解在一个强大权力中,借此分享它的力量与荣耀。”[3]P149
为了驯化宏观权力的野性,人们必须对权力的种类和边界做出界定,同时对权力进行制度化的限制和监督。因此,在现代国家中,权利神圣、权力分立、法治政府以及民主政治的理论被提出和完善,而与其配套的制度架构也被落实下来。
(二)微观权力的界定
宏观权力描述的是存在于政治和国家领域中的权力现象,而米歇尔·福柯认为宏观权力并不足以概括所有的权力形式,因此提出了微观权力的概念。微观权力不是压制性的暴力,其核心也不再是命令和服从,微观权力的实质是一种力量关系,其存在于社会的每个角落。只要存在相对的优势,就存在微观权力。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的阐释所指出的:“现代权力是一种‘关系性’权力,它‘在无数的点上被运用’,具有高度不确定的品质,并且从来都不是某种‘可以获得、抓住或分享’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可供争夺的权力源泉或中心,任何主体也不可能占有它;权力纯粹是一种结构性活动,对它来说,主体只不过是无名的导管或副产品。”[4]P67
与宏观权力相比,微观权力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关系”是它的核心涵义。这种权力没有固定的拥有者,因此,权力的“流动”是多方向的。①虽然任何瞬间都存在着力量对比关系,但是,强势一方与弱势一方的力量对比时刻发生着变化,权力并非长时间掌握在同一个主体手中。福柯断言:“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5]P27
只要存在社会关系的地方就存在微观权力,在该种权力的结构中,不存在固定的支配者和控制者,那么,也就没有所谓的权力中心,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权力个体。当然了,这种权力个体也并非固定不变,何时个体拥有了相对的优势,他便成为拥有微观权力的个体。权力流动的方向只是暂时的,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改变。只要有优势,就有微观权力。福柯认为:“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5]P28
由此可知,宏观权力是一种压制型的权力,而微观权力则是一种沟通型的权力。“福柯把权力视为一种纯粹的结构性活动,打破了宏观权力学里权力的确定性形态”。[6]P56对权力的论说已经不限于政治国家领域,社会领域的权力现象也得到人们的重视。
二、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新媒体
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的区分对应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区分。如果从权力视角来分析媒体,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在该分析模式之下,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和补充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需要媒体提供一定的推动力。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它们都需要承担积极的政治和社会功能。
(一)以宏观权力为特征的传统媒体
诸如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可以被称之为传统媒体。这些媒体往往被牢牢地掌握在执政者手中,同时表达官方的意见和看法。各类报道和文章都要经过当权者的严格审查,报道什么,以及如何报道,甚至是否报道都有严格的指导意见。媒体工作人员的自主能力非常小,当权者喜闻乐见的东西和他们想让社会大众知道的东西才能被传播。信息的流向是固定不变的,即由国家权力中心流向社会大众。信息接收者的意愿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并不重要,当然也是可有可无的。执政者想要达到的结果是:社会大众接收到相同的信息,而且按照“指导意见”进行“思考”。
在传统类型的媒体中,信息的流向是从国家、精英到民众,而且在报道发布之前便已形成了官方的判断,民众没有太多向社会表达观点和异议的渠道。在传统媒体进行传播之前,信息已经被一个政治权力的享有者所审查和裁剪,大众获得的信息往往具有片面性。一般而言,与官方态度相异的意见无法在传统媒体上得到表达。这就导致社会中公开传播的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官方的声音,其他的声音只能于“台面”之下流动。在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之下,人们习惯于将信息和观点置于两种流通领域:“台面上的”与“台面下的”。在不同的场合,人们往往接收和分享不同的信息,有时对于同一件事情也会存在相互矛盾的论说。如此,不诚信和不正直的现象往往而是。
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与权威主义国家联系紧密。在宏观权力的普遍控制之下,新闻媒体和记者往往选择扮演官方机构的“喉舌”角色。官方对他们实施了多种手段的拉拢与控制,其经济利益与官方相关。一旦传统媒体表达出异议者的声音,官方便会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压制。在这种单一模式之下,权力缺少监督,而传统媒体也更易于奉承宏观权力的拥有者。在垄断媒体之下,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源和机会掌握在官方手中,而公民社会也在政府权威的压制之下发育不良。一些所谓的敏感话题被剔除出官方话语体系,一些与政治民主和公共利益相关的事件无法进入公共讨论的空间。长此以往,民众的接受能力愈发脆弱,一旦信息的传播失去官方控制,不满和冲动情绪便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破坏。在此状态之下,民众对信息的甄别能力也可能丧失,一旦出现一些虚假消息或者具有一定风险的消息,整个社会的应对将会显得迟钝不堪。
传统媒体更容易受到权威的影响和干预,进而与国家和执政党结盟。此时,媒体与执政党以及政府之间形成一种依附、臣服的关系。在权威控制下的媒体界,记者与媒体时刻为执政党和政府的利益着想。他们试图制造统一的信息,选择性地报道有利于维护政党合法性的事件,有时甚至篡改事实。在信息来源单一的模式之下,民众被培养成权威的盲目崇拜者,总是以官方设定的目标作为事业或理想。在政府权威与媒体相结合的体制下,不论是记者还是民众,都会产生一种畸形心理,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不但习惯于既存的统治秩序,而且乐于主动维护这种秩序,却从不思考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当压制和驯化扩展到一定深度之后,他们成为了这种秩序的积极拥护者,将自己认同为现存制度的一部分。②
(二)以微观权力为特征的新媒体
不同于宏观权力,微观权力是一种社会权力。现实中确实存在各种力量关系,其核心远离了压制和服从的结构。社会中的个体是微观权力的潜在拥有者,力量的对比关系是这种权力的核心要素。只要有优势,那么,微观权力就存在。新媒体是一种微观权力,它不是由固定的人控制和支配,也没有话语权的中心,有的只是不断流动的“力”。微观权力的运行在一个社会的关系系统中发生,其拥有者是不确定的、分散的和流动的,因此,官方无法全面操纵该关系网络。新媒体的诞生甚至改变了社会的权力结构,原先的权威受到不断的挤压。一个又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应运而生,从根本上动摇了官方对知识和信息的垄断地位。③
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不能容忍旧媒体的垄断地位。民众渴望知悉与政府权力运作过程相关的各类信息,从而实现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多元的新闻媒体更能满足民主社会的需求,新媒体能够克服传统媒体的一些弊端。媒体的市场化使得该行业逐步提升新闻品质,对政府的依赖不断降低。
新媒体,也叫自媒体或者社会媒体,主要指个人能够参与的网络媒体和个人通信工具,具体包括论坛、博客、微博、微信、QQ、Twitter、Facebook等。在网络上,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一个享有话语权的主体,只要拥有了有价值的信息,他就有可能赢得他人的关注。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国家再也无法像控制传统媒体那样控制新媒体,信息可以在免受官方全面审查的条件下进行传播。
新媒体的传播中心是一个又一个匿名的主体,中心并不是永恒的,而是流动和分散的。政治和国家不再是微观权力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力量对比上的新优势者。在微观权力的结构中,没有人是永远的强势者,只存在暂时的力量积聚。同样,在新媒体中,谁掌握了有价值的信息,谁就能够获得大众的关注,此刻他就是信息传播的中心。等到他拥有的信息开始贬值之时,以他为中心聚集起来的力量开始逐渐消散,最终,这个传播的中心将不再是中心。新一轮的信息竞争重新开始。
新媒体的准入具有平民化的特征,不需要太高的官方许可与硬件设备即能参与传播活动。其匿名性使得人们更容易表达出真实的想法,而其自发性则使得社会动员具有灵活性且拥有多元渠道,避免传统媒体的单一组织模式。多元的传播主体使得官方将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者考虑进去,这往往能够帮助官方分散决策风险,实现决策民主。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虽然接受官方的审查,其形式更多是事后审查与事后评价,国家权力无法渗透到信息传播的方方面面。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信息的膨胀,新媒体迅速发展,国家权力再也无力对它进行全面控制,信息不再可能被官方完全垄断。在新媒体被广泛应用的今天,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库,都可以成为一个传播的中心。只要一个人拥有足够的信息,他就可能影响大众的判断。一些不为官方认同或者官方不愿意让社会大众知道的信息,将通过这种方式被大众获知。
在信息分享和传播的过程中,民众越来越广泛地参与政治和社会主题的讨论。新闻活动本身变得富有活力,民众的智慧从各种渠道汇入社会生活领域。同时,新媒体对公共利益的主张和维护可能培养起民众对正义和高尚生活的向往。
诚然,新媒体技术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但是,人们不应该迷信于此。作为一种新技术,新媒体本身的力量极为有限,它仅仅是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其功能的发挥需要一个复杂的环境,包括法律制度、文化传统以及经济需求等。正如陈卫星所言:“也就是说,技术不可以直接生产复杂的事物,比如民主、公共空间或幸福。”[7]P270社会的真正变革始终是一个以人的培养为基础的综合过程,某一方面的进步并不必然引起整体的改良。特别地,一种技术因素的出现并不必然蕴含着政治和伦理意义。新媒体的积极效应更多地在于应用它的人而非技术手段本身。有人不无忧虑地断言:“新媒体提醒我们:信息的数量并不决定公民履行义务的质量。换言之,信息并不宣告民主的到来,而决定民主的实质的并不是新闻或者报纸的数量,而是讲话人和听话人双方为反对不平等待遇而进行的不倦斗争。”[8]P122
三、新媒体与公民社会的培育
在国家——经济——社会三分的框架之下,公民社会的范围不同于国家和市场。俞可平的观点具有典型意义:“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与家庭、企业之间的中间领域,是所有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等‘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以及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9]P158
可以从以下层面理解“公民社会”的概念:为了反抗政府的暴虐,公民社会是一种制衡政府专制的手段;公民社会具有自主和自治的特征,国家干预的范围应当尽量缩小;市民社会的成员以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可以发展一种互动与合作的关系;政府的法治治理模式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正如阿尔伯特·亨特和卡尔·米洛夫斯基的看法:“简而言之,公民社会不仅是非盈利、非官方性质的社会组织的自治部分,而且是该部分与特殊的法律、国家结构以及一种辅助性的公共文化的融合。一个公民社会包括所有这些东西。”[10]P18
新媒体对政治和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特别地,在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机遇之下,新媒体能够而且应当承担一份重要的责任。而公民社会又是国家治理主题下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先前论述的基础上,该部分将要探讨新媒体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有权探索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可否认,传统媒体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不过这种稳定往往会遭遇各种挑战。官方掌握的信息量远远大于社会,向社会进行宣传,说服和塑造社会的权力掌握在传统媒体的手中。但是,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只有一种声音显然是不够的。传统媒体背后的政治中心无法保证自己的选择最优或较优,那么,要求社会大众只能按照官方的标准生活和认知则是危险的。
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新媒体向社会传达各种各样的信息,使得人们能够在诸多的信息中找到有指导意义的内容,并据此选择自己的生活。而传统媒体限制了信息的种类,同时向社会灌输统一的思想,这影响了个体对信息的获取,间接地剥夺了个体对其他(不同于官方倡导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在法律和习俗等规范允许的范围内,每个个体都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国家和政府无权并且没有能力替个体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国家而言,允许个体选择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因为选择意味着责任,如果国家替人们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国家应当对选择的结果承担责任。如此下去,国家将不堪重负。所以,允许个体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选择,能够减轻国家的负担,同时将决策的风险分散化,不至于造成国家和社会的崩溃。
(二)以表达自由防范社会风险
通过新媒体,个人能够将生活中的事件表达出来,不管能否产生社会共鸣,都对个人富有意义。在表达的过程中,个人渴望被关注的愿望得以实现,同时,倾诉本身也是实现主体性的方式。进行表达与分享是个体获得社会认同的途径,又是进行自我反省的形式。也许本来不被人关注的事件,在分享的过程中便被不同的传播者赋予了新的意义。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发表言论,实现表达自由。
在该平台之上,人们必然在乎行为的后果,个人的言行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监督。外界的压力可能促使个体选择谨慎的行为方式,往往,不需要法律的强制就能实现个体的审慎和自控。这种具有自治能力的人自然是公民社会需要的人。
在新媒体的关系网络中,每个个体都是一个潜在的传播中心,只要他拥有足够的信息,那么,他就可以拥有传播信息的微观权力。个体可以随时表达他的观点和看法,当然,这种表达本身并不会对社会造成太多消极的影响,仅仅是一种宣泄的途径而已。在事事都需审查的传统媒体中,这种表达自由是无法想象的。在传统媒体之下,人们过着一种压抑的生活,无法满足公开表达的欲望。因为除了以宏观权力为后盾的传统媒体外,其他人都没有实现表达自由的渠道。
只要是有人存在,就必然会有冲突。此刻,社会往往充斥着不满情绪,这些情绪就像水流,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如果一味压制,那么,水流的表面也许风平浪静,可是水下却已暗流涌动。长期积攒下去的话,这些能量可以摧毁一切阻挡它的堤坝。社会也一样,人们宣泄的欲望只能疏导不能完全压制。如果给予个体公开表达的渠道,那么社会的冲突也会被缓解。
新媒体恰好能够为个体提供一个表达的途径,这个途径在传统媒体中并不存在。每个个体都可以及时地将自己的不满表达出来,而且可以向社会传播各种信息。一旦表达的欲望得到满足,那么破坏性的能量也就无从产生。
(三)国家治理的民主化趋势
现代社会要求善治,而新媒体的成熟、发达关系到政府的善治程度。何为善治呢?“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11]P8这种治理模式要求建立法治政府、民主政府、责任政府和高效政府,新媒体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挑战又提供了机遇。作为公民社会与法治国家进行合作互动的平台,新媒体必将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决策的民主特征将通过新媒体得以展现。民众有权通过该平台实现自己的知情权、监督权和控告权,最终国家政策与政府行动才能赢得民意的拥护。同时,政府的权力得到恰当的限制,在防止权力滥用的前提下,避免不作为和懈怠。在该过程中,公民的政治能力和公共精神得到培养。
善治要求一切政府决策需要向民众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暴力和威胁无法成为政治行动的支撑力量。个体对公共讨论的参与有助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它使得个人喜欢参与政治活动,其观点能够被他人知悉。个体愿意广泛聆听各种观念,养成宽容的习惯。个人将会做出明智的决定,最重要的一点:这种决定在劝说之下而非强制之下做出。④
民主参与为政府决策赢得民意基础,从而实现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互动与合作。新媒体为公民与政府的对话创造了机会,公民的观点和意见更容易被社会听到,更有可能影响官方决策。公民参与政治的程度不断提高,其主体意识也将增强。
现代社会,知识和信息膨胀、专业分工精细,仅凭单个人的知识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每个个体都有其价值,都可能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当然,在国家权力运作的过程中,仅仅依靠官方人员的力量并不足够,如果能够发挥所有社会成员的聪明才智,社会才能一直保持朝气和活力。
新媒体为权力的民主参与提供平台。在传统媒体之下,忌惮于宏观权力,社会大众不敢说真话,往往和官方保持一致的口径。而在网络上,匿名的个人就敢于表达真实的看法,同时也愿意为公共事业出力。这不仅保障了表达者的安全,同时也为宏观权力的运作贡献了力量。仅仅依靠命令和压制来实现宏观权力的运作已经无法想象,沟通和协商才能最终解决冲突。新媒体就为这种沟通提供了一种渠道和机制。
新媒体作为一种交流平台,客观上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创造了条件。公民对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参与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培育,现代国家的治理要求更大程度的民主参与以及社会合作。程序公开、理性协商将有助于社会冲突的解决,而新媒体的繁荣发展能够助益于社会秩序的和谐。
民众参与政府决策的程度关系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政府决策的实施难度。一旦政府的管理方式赢得了社会的认同,那么,公民社会的力量将自然而然地促进国家权力的运作。在该过程中,新媒体发挥了提供沟通平台的作用。各种零散的声音和信息获得表达与传播,去伪存真的效果具有现实可能性。非理性的言论在公开讨论中得到纯化,一旦表达的通道不被阻塞,不满的情绪便不会升级为过激的行为。
(四)对宏观权力的对抗和监督
国家掌握着宏观权力,能够将各种力量动员起来。而这种权力一旦失去束缚,大众的生命和财产会遭遇巨大的威胁。宏观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将它放在铁笼之中才是最安全的选择。新媒体的微观权力成为了对抗宏观权力扩张的一种力量。
政府不应该被视为宏观权力的拥有者,而只应该当作是宏观权力的管理者。“因此,权力不再具有唯一性,不再仅仅是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且是服务于各种各样的目的的”。[12]P95宏观权力只能基于正当目的而使用。只要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新媒体对微观权力的运用不应该受到国家权力的压制。
网民将不易被人重视或者易被掩盖的各种信息提交到网络上,这些信息被其他网民关注并了解之后,在相关信息的中心就会聚集起足够力量,最终引起官方重视,将宏观权力的运行拉上正轨。整个过程无需得到审查和批准,网民就能获取快捷的信息,从而做出反应。
新媒体对官方的监督是间接性的,起初是网民个体的表达,其后是其他网民的关注和参与,包括讨论和争执,最终形成共识性的看法。这是一个力量的积聚过程,等到力量足以引发巨大震动的时候,微观权力便发挥其对抗和监督宏观权力的作用。
不可否认,新媒体的兴起为国家权力的运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同时也为整个官僚系统注入了新活力。大众将不容易被蒙骗和压制,公权力机构只有正当地行使权力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个人的表达自由并非毫无约束,同样,宏观权力的行使也要接受严格的限制。唯有如此,国家和公民社会才能健康运作。
社会大众有权利知悉公权力拥有者的决策和行动,但是仅仅依靠传统媒体显然无法为社会提供足够的信息。有时,大众想要知道一些公权力拥有者不愿意让其知悉的信息,传统媒体的审查者很可能就是这个掌握公权力的主体。如此,大众可能根本无法从传统媒体上获悉相关信息。新媒体自然能够扮演一个揭露者的角色。不然的话,大众生活在卑污的环境中却浑噩不知,那么,国家的善治和公民社会的成熟便不可能实现。国家和政府应当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但是对大众进行欺骗和愚弄则是行不通的。新媒体负载的信息为人们立体地认识社会打开了许多扇窗,这些窗多到任何官方机构都无法全部关闭的程度。新媒体的有序发展为统治者的管理带来了挑战,但同时也为黑暗和腐败关上了许多扇门。
(五)新媒体对公民社会的培育
公民社会本身独立于政府,天生就有防止政府权力不当扩张和滥用的倾向。它往往能够向民众提供较为中立和客观的信息,可能摆脱政府的偏见以及市场主体的自私。其中,诸多的社会组织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它们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新媒体的宣传和动员功能使得公民社会易于获得认同,从而积蓄力量摆脱政府和经济主体的不当干预。一旦新媒体拥有一定的社会力量,它便努力打破既存的话语垄断体系,进而营造一种宽松、多元的公共话语氛围。媒体权力的中心将会不断分散,大学、出版社以及网络参与者都有可能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更加有利于公民意识的养成。在传统媒体之下,大众都是官方言论的被动接受者。就算他们拥有发表和传播信息的意图,也不具有畅通的渠道。长此以往,民众可能成为堕怠而不关心公益的人,自然,公民社会也就不可能形成。新媒体平台上的发声者往往是那些拥有信息且积极传播的人,他们拥有微观权力,信息的流向与该权力的流向一致。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记者。
在新媒体的平台上,个人更有可能跳出自利的圈子走向利他。在参与政治过程和进行信息分享的时候,个人得到了教育。养成积极的性格和热心公益的习惯,是公民意识觉醒的前提条件。新媒体平台上的个人表达具有发展为社会表达的潜力。经过传播、共鸣、发酵和沉淀之后,起初的个案诉求往往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主张。个体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关注他人和社会。
每个公民都有可能通过新媒体参加公共讨论,受到政治教育。人们可能以理性的方式寻求利益的实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政治和公共利益对自己的重要性。一种公共行为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个人的利益,消极逃避和漠然置之并非明智之举。尊重他人的自由就是在保障自身的自由,而尊重他人的权利也在促进自身的权利。
以慈善事业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媒体在培育公民社会上的意义。诚然,考验民族凝聚力的一种场景,便是该民族面对重大灾难时的号召和发动能力。一旦发生重大和危急的情形,如地震、海啸、泥石流、战争等,传统媒体便能发挥出其优势,巨大的舆论和物质力量将被顺利地组织起来。但是,传统媒体也有其功能的局限性。它无法关注到社会的全部细节,同时,其功能的发挥以国家和社会力量的统一安排为依托。新媒体则更能将其关注的焦点遍及任何时刻、任何地点,它引导下的慈善活动范围更广,参与人数更多,更具自发性。慈善活动应当成为常态,只要存在需要帮助的情形或者存在帮助他人的一员,自发的慈善应当立即得到实现。新媒体的自发性与公民社会的自发性相一致,公民社会的培育更加依赖于新媒体。
(六)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
公民社会能够对公权力的运作进行有效监督。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存在对抗关系,不仅如此,二者之间也能形成良性合作关系。一个积极、理性的公民社会是实现政治民主和政府善治的基础。新媒体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机会,这是表达自由的实现。同时,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发声使得个体权利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国家权力相比,个人总是处于弱势地位。一旦个体权利受到威胁或侵犯,他会试图将冲突公开化,以获取社会的力量。个体保护其私人利益的举动,不自觉地、自动地实现了社会力量的联合。该联合发生于政府和市场之外,属于公民社会的领域。
新媒体对政府的管理行为提出了挑战。纯粹的命令与强制已经行不通,要想获得高效而公正的治理效果,政府与社会的良性合作已成为必然要求。若仍将新媒体理解为对抗政府的力量,显然没有扼住时代的脉搏。新媒体能够提供广泛的信息,只要掌握辨别与甄选的方法,国家和市场主体便能顺利获取有用的参考信息。新媒体平台上的沟通行为,也能从一定程度上指导个人的行为,而理性的决策则能最大程度地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
在新媒体出现之后,官方必需与民众进行互动。民众对官方和专家的结论往往能够提出非常专业的调查与论证,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违法的行为会被揭露和批判。在互动中,政府和民众获得学习和进步的机会。新媒体本身也是一个科普与实践的平台,民众自发学习的愿望将会得到满足。公民社会所需要的独立自主、成熟理性的公民将在该平台上得以培育。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对抗与合作共存的模式,二者之间需要相互沟通。信息的拥有者成为微观权力网络上的强势者,该场域淡化了宏观权力的压制性,增强了知识和信息共享中的优势地位。新媒体增加了公民社会的实力,对于其进一步的成熟和发展有所助益。
新媒体应当实行自治原则,切实保障言论自由。但事后审查制度是必要的,一定程度的限制有助于公民意识的培养。自由意味着免于不当束缚,同时自我实现和自主负责。公民社会需要的是独立而负责的主体,当然,新媒体也应当以培养这种主体为目标。相应地,公民社会实施法治原则,人们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新媒体平台上的发言者,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行动,且要为其违法和不当行为负责。该平台既具有私人属性,又包含社会属性。信息的发布和传播都掌握在个体手中,但是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又可以形成一个公共的平台。因此,新媒体的运作关涉到公共利益,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那些伤害公共利益的表达行为,例如违法行为、严重违背道德的行为、人身攻击、谩骂等,应当得到事后处罚。
结论
不同于宏观权力,微观权力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在关系网络中,微观权力时时都在发生流动,它不是一种实体力量,并不存在固定的占有者。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这种关系中的强势者。与此相对应,新媒体具有微观权力的特征,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新闻和信息的发布者与传播者。
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是一种竞争与共赢的关系,当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也是这种关系。传统媒体以宏观权力为后盾,新媒体具有一些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征,它的发达与成熟不会为社会带来颠覆性的震荡,相反,还会对健康社会的形成有所助益。官方应当对新媒体的发展持宽容与合作态度,新媒体对公权力机构的监督并不会损害此类机构的权威。
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个体都渴望表达,传统媒体自然无法满足这种诉求。新媒体的发展将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个体意识的解放使得社会只有一种声音的做法遭到抵制,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看法,并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若仅依赖于简单的“命令——服从”模式,那么,宏观权力可能无法有效运转。
现代社会要求一种善治,在法治政府、民主政府、责任政府和高效政府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新媒体本身的特征使其与公民社会的培育相辅相成。
注释:
① 具体论述参见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② 具体论述参见张建中:《大众媒介与社会转型:墨西哥个案考察》,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41~144页。
③ See James Curran, Media and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55-56.
④ See William A. Galston, Liberal Purposes: Goods, Virtues, and Duties in the Liberal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27.
[1] [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 周尚君.权利概念的法理重释[J].政法论丛,2012,5.
[3] [美]埃利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4]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怀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5] [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 赵鸿燕.关系的网络:微观权力视角下媒体责任探析[J].国际新闻界,2011,12.
[7]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 [法]弗兰西斯·巴尔、杰拉尔·埃梅里.新媒体[M].张学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9] 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转变中的中国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0] Albert Hunter, Carl Milofsky, Pragmatic Liberalism:Constructing a Civil Socie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11] 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2] 张康之.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6.
(责任编辑:张保芬)
New Media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 Power
JiangChao
(Law School of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Micro power is a concept whose core is relationship, and everyone has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the strong in this social relationship. Nowadays, the new media is constantly developed, and everyone gets the chance to become a journalist.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new media and micro power. That adopting micro power as the analysis tool i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research of new media. New media bring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micro power; new media; civil society; the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蒋 超(1975-),男,广西合浦人,法学博士,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
1002—6274(2016)05—025—08
DF0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