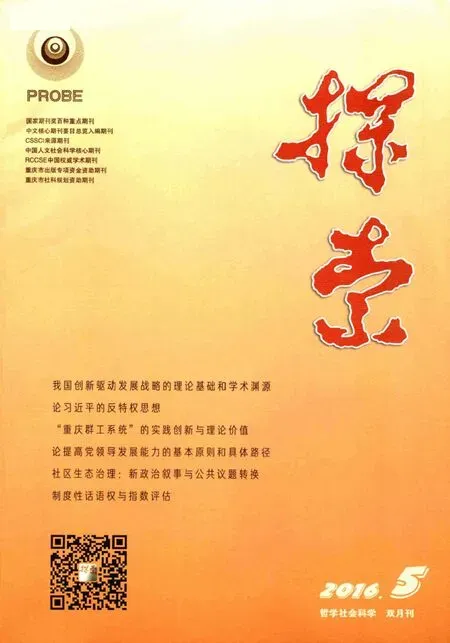网络民粹主义的内涵、张力与特征
刘小龙
(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网络民粹主义是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关于网络民粹主义的内涵、本质与特征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很多学者干脆用“网络空间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来指称网络民粹主义。“在寻求对民粹主义有一个完美恰当的解释的过程中,充满着种种错觉和许多不尽人意的东西,其结果并非总是令人满意的。”[1]2本文尝试厘定网络民粹主义的内涵,剖析网络民粹主义的内在张力,揭示网络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为网络民粹主义相关研究提供一孔之见。
1 现实与虚拟:网络民粹主义的内涵厘定
网络民粹主义在民粹主义的概念前加上了“网络”这一定语,可以考虑在厘定民粹主义概念的基础之上,辨析网络民粹主义与现实民粹主义的关系。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范式:规范性范式和类型学范式。关于“民粹主义”的规范性定义主要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政治类型”和“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三种。“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强调了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如艾伯齐塔和麦克唐奈把民粹主义界定为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断言道德纯洁的、同质化的人民与那些精英和危险的他者之间存在对立关系,描绘后者正在或者试图剥夺人民的权力、价值、富足、认同以及声音。”[2]543从意识形态界定民粹主义的观点,主要强调了其“坚持人民中心、批判精英、强调人民的同质性、主张直接民主、信奉排外主义和宣扬危机意识”等六方面内容[3]35。作为“一种政治类型”的界定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特殊政治领袖的政治控制策略和权力行使方式,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库尔特·韦兰德的界定: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声称“代表”那些感到被国家政治生活排除在外或被边缘化的人民,宣称与特权集团及其特殊利益作斗争,许诺将人民从危机、风险和敌人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以此扩大影响、获得权力和得到支持[4]。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则是一种更为微观的定义方式,关注了民粹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政治风格及其特征,包括“简单直白的语言风格、直截了当的交流风格、极端化思维和对于他者的社会想象”等[3]35。
类型学界定则注重从民粹主义多样形态中进行归类和比较,英国学者玛格丽特·卡诺婉关于民粹主义的分类研究颇具代表性。她概括出“民粹主义者的专制、民粹主义的民主、保守的民粹主义以及政治家的民粹主义”四种基本类型,并得出结论:民粹主义的共同性就是“政治性”,多样化民粹主义类型的共同主题就是“依靠对人民的感召力,不信任精英人士”[5]。从时间维度来划分,先后出现了19世纪后期俄国民粹主义、美国“人民党”民粹主义两种原生形态,横跨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拉丁美洲的经典民粹主义形态,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民粹主义”。
从民粹主义到网络民粹主义的厘定,关键在于对“网络”这一定语及其与民粹主义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网络技术的出现和普及带来了“技术决定论”“社会决定论”和“技术社会互动论”三派观点的争论。“社会决定论”强调网络技术的运用、网络技术的社会变革性影响始终要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过于夸大网络技术社会功能的观点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技术乌托邦”[6]118。“技术决定论”认为,媒体技术发展是人的能力发展全方位的延伸,网络媒体创造了一个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虚拟社会,并在现实生活中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第三种观点认为,网络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要素,它与社会结构性要素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需要从技术和社会双重视角来加以诠释,其内在机制需要深入探讨。
在关于网络民粹主义的界定上,“社会决定论”占据主流,主要有“反映说”“扩展说”和“转移说”等观点。持“反映说”观点的学者认为,“虚拟网络的民粹主义思潮总是现实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反映或观照”[7]。因此不必区分网络民粹主义与现实民粹主义二者之间的概念。“扩展说”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在虚拟空间的扩展和延伸,“是民粹主义在网络传播空间内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一方面是对现实中精英主义的反抗,另一方面是对现实中民粹主义思潮的延伸”[8]。“转移说”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是大众的内心情绪与诉求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宣泄而转移到虚拟空间”,源于“大众凭借网络空间提供的自由表达、讨论机制而掌握了新的话语权”,从而将现实生活中无法现身的民粹主义得以闪现的一种“代偿”“转移”或者“迁移”[9]。
笔者认为,由于网络空间既折射和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和诸多问题,但又具有自己独特的运作规律,“技术社会互动论”的视角可能更为合理。据此,笔者把网络民粹主义界定为:一种强调社会分为人民与精英两大整体对抗阵营的网络话语和网络行为,它推崇整体性、同质化的人民,批判作为人民对立面的社会精英及庇护他们的现行制度,主张政治应当表达人民的普遍意志。这一定义的基本内涵有:其一,网络民粹主义是发生、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一种现象,网络话语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其二,这种网络话语一方面具有崇拜人民的倾向,用美好和积极的话语来描绘人民的形象,另一方面则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作为人民对立面的社会精英,以此来构建人民的光辉形象和敌人的阴暗形象,从而体现指向人民的崇高美好和社会精英的邪恶败坏两极对立的价值诉求。其三,在这种网络话语看来,人民是一个纯洁、美好、同质化的实体,曾经存在着一个人民栖居的澄澈美好的中心地带,但在现实中人民却被社会精英和其他敌对者所剥夺而陷入悲惨的境地。其四,这种话语渲染了一种危机感,纯洁善良的人民处于危险敌人的压迫和剥夺之中,如若人民不采取直接行动加以捍卫,则人民的权力、财富、认同、价值和声音都会遭受危险。其五,这种话语与现实社会的结构性因素直接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现实社会的诸多因素,但网络空间自身的特性使得这种现实因素在话语当中以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
就网络民粹主义与现实民粹主义的关系而言,表现为三个层面:第一,网络民粹主义是现实民粹主义的信息化和网络化,这主要体现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上的一致性。网络民粹主义和现实民粹主义在价值倾向上都推崇人民,反对精英,在思维习惯上都主张二者之间的直接对立,二者矛盾不可调和,都主张坚决彻底的斗争精神。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民粹主义不过是现实民粹主义思潮在网络空间的复制而已。第二,网络民粹主义是对现实民粹主义的拓展和延伸。现实生活中民粹主义的滋生、呈现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限制,网络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些壁垒,从而使得现实生活中无法现身的民粹主义获得表现的机会,拓展了民粹主义的呈现空间,增加了其发生频率,增强了民粹主义的政治能量,如网络舆论的生成,网络围观的实现,网络动员的发起等。第三,就表现形式来说,网络民粹主义是一种全新的民粹主义形式。它凸显了文化民粹主义的影响力,主要以话语的方式呈现,创造了“人肉搜索”、符号性狂欢等新的形态。这种话语性和文化性特征使得网络民粹主义更接近于话语斗争的范畴,更加关注具体议题而缺乏宏观政治规划,在风格上倾向于平淡、平凡的生活政治,而不具有崇高、雄伟的现实政治意蕴,当它需要彰显政治变革能量时往往需要现实政治力量的介入。总之,网络民粹主义一方面可以视为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中的一种新表现,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民粹主义在网络媒介时代发展的一种新形态。
2 以民为粹与为民之粹:网络民粹主义的内在张力
网络民粹主义是一种极为复杂和矛盾的现象,“它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反动的一面;有先进的一面,又有落后的一面。它有民主的内涵,但最终极可能走向专制独裁;它有爱国的情调,但常常导致极端的民族主义;它反对精英政治,但结果经常是个人集权;它貌似激进,但实质上经常代表保守落后的势力。因此,民粹主义对于现代化和社会进步来说,或许是福音,但也很可能是祸害”[10]。对网络民粹主义本质的把握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其中包含的“以民为粹”和“为民之粹”之间内在张力尤其需要关注。
一方面,“以民为粹”是网络民粹主义最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民粹主义“把人民看做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11]102。正是基于这种对人民真理性和道德优越性的信仰,民粹主义者把人民视为自己的神灵,认为“人民”是价值评判的基点和合法性的源泉,也是反抗精英、反对不公和反抗现行制度的主体力量。在功能维度上,“人民”是作为批判精英的批判性、抗争性话语而被建构的,理念上被尊崇的善良、纯洁的人民与现实生活中人民的悲惨境遇和被压迫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种对比恰恰是激发人民起来抗争的动力所在。由此,“以民为粹”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平民主义”,“以民为粹”作为社会底层、草根、大众反抗精英、反抗权威乃至现行制度的话语建构,以一种反抗和否定的姿态提出了人民主权的观念,对社会弱者尤其是边缘群体的权益伸张提出了诉求,直接反抗社会不公、官僚制度和精英宰制。就此意义而言,民粹主义通常代表了社会底层、草根和民众的抗争意识和表达诉求,具有变革的积极意蕴。
另一方面,“为民之粹”始终纠缠着民粹主义,成为民粹主义得以实践的政治形式。“为民之粹”发端于“以民为粹”的价值主张与它的实践可能之间的裂缝。民粹主义视野中的“人民”并不是一个本质属性可以被发现或者利益可以被清晰地代表的实体,而是一种话语的建构,而且其解释权在历史实践中往往成为政治家、行动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相互争夺的对象。也就是说,“人民”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模糊不清的、高度同质化的、整体性的、由话语建构出来的“空的能指”。现实生活中的人民通常以“自发”状态而存在,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在社会权力上通常是软弱无力的,谁来代表人民从来都是一个实践难题。这一难题在所有民粹主义案例中都有体现:俄国民粹主义知识分子遭遇了“向人民学习”还是“教育人民”的困境,美国民粹主义者陷入了“以参与选举来反对代议制度”的悖论,拉美民粹主义者化身为“为民代言”的魅力型领袖同时也是专制型政治领袖。显然,“为民之粹”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甚至有可能滑向集权主义,“以民为粹”提供了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和政治标尺,但在实践中它又容易转化为一种政治的策略和口号,并容易蜕化为精英主义的装饰品,以及掩盖权力斗争和救世主意识的诺言乃至谎言[12]44。由此,民粹主义在理念上倡导“人民”是道德的、高尚的、纯洁的,以此作为依据来反抗精英和现有制度对于人民的蔑视和压迫,从而体现出浓厚的平民主义色彩;在实践上,民粹主义的倡导主体通常是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人民”话语可能成为他们获得权力的一个工具,民粹主义潜伏着精英主义乃至集权主义的种子。
“以民为粹”和“为民之粹”之间复杂、矛盾和暧昧的关系在网络空间中并未被消除,只是被网络权力关系的塑造遮蔽了。一方面,网络空间实现了权力从社会精英向网民的转移,赋予了社会草根、边缘群体以更多的话语权,“以民为粹”在网络空间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建构能量,网络民粹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弱者武器”。网络空间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低成本、跨越地理间隔的、以符号作为表达方式的流动空间,人们的群体聚合大大降低了社会组织的成本[13]15,因而在人民话语下建构起来的“抗拒性”认同得到了充分表达的机会。网民的聚集不是现实社会阶层身份的网络复制,更多是源于共同心态的激发和共同抗争对象的指认,无数分散的对占据霸权地位主流话语的不满,在“人民”的话语下暂时性地集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对抗主流霸权力量的统一战线,在人民的整体性、同质化话语建构中区分了敌我阵营,实现了与社会精英之间的话语对抗。尽管“人民”作为统一战线背后有多样化的诉求,但这种对抗关系却是具有真实社会功能的。并且,正是由于统一战线只是暂时的,因而下一次的凝结和统一战线的构筑才成为可能,网络空间的民粹主义才会反复发生。在原有的由精英控制的传播领地之外另外开辟了一个新的信息场域,科层制让位于扁平化的网络结构,广大网民在虚拟空间中表达民意、反映大众的诉求、追寻社会的公正、维护弱者的权益、反抗精英的压迫,因而构成网络空间中主体的“广大网民”富有正义感、具有道德纯洁性,既是“人民”的现实化身,也是实现“人民”利益、表达人民声音的理想主体。
另一方面,“为民之粹”由自称为人民代言的知识分子、政治人物被置换成为人民代言的“意见领袖”和“网络大V”。“人人平等”“富有正义感的网民”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只是“技术乌托邦”的美丽幻想。政治经济批评学派提醒我们,网络媒体的创造者、掌握者和规则制定者是“微软”“谷歌”“脸谱”“苹果”这些互联网巨头,他们制造了虚幻的技术平等、网民至上的神话,“媒体帝国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工业和驯化思想的利器。“消费文化”“媒体奇观”“眼球经济”的出现可能使网络民粹主义成为媒体集团获得资本利润的工具,其结果不过是强化了精英的利益、资本的逻辑和制度的韧性。网络空间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意见领袖和网络大V,他们以眼球经济、关注度、点击率形成鼓动和消费民粹主义的精英同盟,他们打着“人民”的旗号,声称为人民代言,煽动和刺激着网民的偏激情绪,享受着“皇帝批阅奏章”的快感,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意见领袖与普通网民之间的声望和权势可谓天壤之别,民粹主义仅仅是意见领袖获取名利和社会影响力的工具和策略,“长尾理论”在网络空间依然有效且有可能进一步被强化,因此,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中的另一个面相依然是“为民之粹”。
3 认同与抗争:网络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
网络民粹主义通过划分“我们与他们”“大众与精英”之间的敌我阵营,体现一种认同与抗争同时并存的政治功能,一方面实现网民在人民话语下的聚合、团结和认同,另一方面也建构和指认了作为他者的抗争、否定和批判的对象,话语的建构与解构、话语权的争夺成为网络民粹主义发挥其政治功能的主要方式。通过对网络民粹主义的深入分析,可以概括出基于理性的非理性、表达不满的批判性和有限抗争的话语性三个基本特征。
3.1 基于理性的非理性
从意识形态的维度来看,网络民粹主义作为一种“中心稀薄的”(a thin-centered)的意识形态[3]5,通常以弥散化、“流变性”的方式呈现在网络空间当中,往往依托于一种蔓延甚广的社会心理,表现为一种集体情绪的发酵。“民粹主义其实并不是一种主义,而是一种出自人性本能的朴素的愿望和要求。当这种愿望和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它们就会演化成为一种否定一切的情绪。”[14]社会底层民众在剧烈的社会变化中产生的不适、挫折、伤感、怨愤等朴素情感需要得到表达,“以民为粹”为这种情绪提供了道义上的依据和情感上的寄托,网络空间则提供了便捷的表达渠道和平台。由此,网络民粹主义经常表现为自发性、弥散化、流变性和碎片化的网民态度和大众情感,在常态的情况下潜伏在网络空间当中,而在某个议题的刺激下则以网络舆论的方式集中爆发出来。网络民粹主义缺乏独立的形态和专门的领地,往往与其他社会思潮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并经常借助于其他社会思潮爆发出的巨大的政治能量。
就其呈现方式来看,网络民粹主义总是与亢奋的情绪、道德的感召和精神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并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集体行动逻辑和激进的网络舆论。网络民粹主义往往源于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怨恨和愤怒情绪,并以激进乃至极端的网络舆论表现出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情感、情绪在网络空间中发酵,并具有“自由漂浮”的性质,试图抓住一切可以表达的机会而不去理会真实的冤情究竟来自何处,这就导致了网络空间中仇官、仇富、仇权、仇恨专家和仇恨制度成为一种反复性发作的情感偏向。一种如舍勒所说的“确定样式的价值错觉和与此错觉相应的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占据和主宰了网络大众心理,等待在特定议题的刺激下俘获一个具体的对象,给它贴上标签而施以群情汹涌的围攻。网络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感官的、消费性的情绪聚集,在本质上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价值立场,而是如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精神及其指向未来的、自由的、乌托邦的特色逐渐蜕变为一种纯粹的节日情绪”[15]。事实上,网络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集体情感和社会心理的聚集,这是它在现实社会中显示突出政治能量的一种基本方式。
从根源来说,网络民粹主义的情感发酵、舆论围观来源于社会现实生活,因而网络民粹主义的非理性逻辑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理性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是社会生活中的贫富悬殊、分配不公以及阶层固化等现实因素在网络空间的投射,是现实政治表达渠道不畅的一种替代物。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演进逻辑:从社会因素来看,社会等级制度越强,阶层壁垒越严格,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越难以逾越,网络民粹主义就越丰盛。从政治因素来看,网络民粹主义源于现实政治表达渠道的匮乏,网下政治虚弱的国家是最容易激发网上政治诞生的。一旦现实民主制度无法兑现对人民的承诺,民粹主义就会成为代表危机的产物而登场。同时,对于煽动民粹主义的网络大V来说,他们自觉追寻着、利用着网络民粹主义背后的经济理性:当前的“文化生产包括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创造丰厚利润的工业部门,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约”[16]。对于网络媒体尤其是自媒体而言,如何获取普通民众的青睐,赢得消费者的眼球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主动煽动民粹主义情绪,以人民的符号聚齐尽量多的关注目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造虚假新闻,热衷于报道超出公众心理预期的负面新闻,炒作煽情的故事和意外的丑闻,为点燃大众的怨恨情绪推波助澜,所有这些貌似非理性的行为由冷冰冰的经济理性乃至资本逻辑所主宰和支配。
3.2 表达不满的批判性
欧内斯特·拉克劳指出:民粹主义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理性人逻辑推演的利益诉求的集体爆发,而是“设计出一个有明确敌人的对立冲突,而这是每一个具备有效动员力的政治表述的必要条件”[17],民粹主义的批判性尺度往往通过锁定某个具体的对象而成为现实的力量。在网络空间中,民粹主义通过建构“共同的敌人”的方式来实现广大网民之间的一种抗拒性认同,表现得更为常见、更为频繁。如果说“推崇人民和崇拜人民”为网络民粹主义提供了一个道德制高点并由此触发对于弱者的普遍同情,那么,通过指认作为人民对立面的“敌人”形象并将之具体化,则为网络民粹主义的情绪发泄、情感动员和批判精神找到了现实的靶子。
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网络民粹主义批判矛头所指的对象通常就是社会精英。马克斯·韦伯曾经把社会精英分为“权力”“财富”和“知识”三个领域,分别对应着当权者、富人和知识分子,由此,反对乃至仇恨知识分子、富人和官员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最为典型的三个表征,也是我们在实践中识别民粹主义比较好的切入点。网络空间中信息的海量涌动、信息的沟通共享和信息监控的难以实现,使得理论上任何人的所有信息都可以在网上留下痕迹,而网民通过信息的分享和合作能够形成一张无所不在的监督之网,这种网所要俘获的主要对象就是那些社会精英,包括官员、富人、明星和知识分子等,一旦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出现不当言行而受到公众关注,那么,一场网民发起的人肉搜索运动就在所难免。由此,每一次民粹主义掀起的舆论巨潮当中,“涉贪、涉富、涉权”事件往往容易成为触发民粹主义的诱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知识分子在网络空间中也不被信任,民粹主义“控诉知识精英都已经被市场经济和利益集团收编,尤其对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抵触与憎恶心态”[18]。
网络民粹主义不仅仅体现为对社会精英的否定,而且时常体现为对现行主导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和现行体制的否定和批判[19]2-16。这种否定和批判体现了“大众的反叛”,其根源就是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底层或者大众感受到了不公、挫折、郁闷以及对强势精英阶层的愤怒。正因为如此,希尔斯把民粹主义的产生根源视为社会分为对立的两个阶层,社会精英“在他们所实施的统治过程中,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有民粹主义”[20]100-101。网络虚拟空间提供的就是一种把分散的诉求、情绪和仇恨凝聚起来的“连线力”,网络民粹主义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基于象征符号、类似于舞台剧目演出的一种“表演性聚集”,舞台上前景的集体呈现,是后台脚本、布景和编剧合力作用的结果[21]16-18。对于参与舞台表演的诸多演员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利益诉求,而是在集体性的现场氛围中表达了日常生活中潜在的、分散的、个体化的对于现存制度的失望、不满、挫折感和剥夺感。网络媒体降低了人们积聚起来的交易成本,催生了新的社会互动方式,带来了象征性的聚集,使得以话语构建起来的“简单得可笑”的集体行动得以产生。从而使得种种政治不满、对精英的批判以集体的方式爆发出来,它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力量产生了一定的政治效应。
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说,网络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对现代性的理性化逻辑和代议制民主以及政党政治的不满、批判和否定。正是由于网络民粹主义具有对现代性的批判维度,很多人把网络民粹主义从文化的视角视为“后现代文化”的一种表现,这种认定有简单化的倾向。与把“否定一切”奉为圭臬的虚无主义相比较,网络民粹主义的否定性维度是有限度、有节制的,它没有完全沉溺于破坏的快感、大众的狂欢当中,它有自己建构的维度,它们也没有完全否定国家和现存体制,而只是表达对于现存体制没有能够照顾底层的利益、没有对邪恶的精英们进行有效的控制;对于现代化潮流,它也没有完全否定,而是寻找另外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可以说,网络民粹主义是因现代性而生体现着现代性的逻辑,并因现代性带来的种种不公和缺失而扭曲的一种悲情。在一定程度上,网络民粹主义是从道德意义上用另外一种话语表述了平民大众尤其是社会边缘群体对资本主义理性化发展进程的焦虑和反叛。当然,由于网络民粹主义具有情感性特征,这种情感逻辑一旦形成就很难沿着理性的方向发展,加之网络空间具有空间消灭时间的特性,网络民粹主义有可能发展成为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
3.3 有限抗争的话语性
网络民粹主义主要呈现为符号性的话语,网络空间中话语符号的多样性、通俗性和平民化使得网络空间中的话语削弱了社会精英的信息表达权利,赋予了普通大众以话语表达的权利和机会,从而带来了网络空间中权力关系的变迁。话语表达为网络民粹主义提供了一种现实生活中所无法获得的便利和平台,进而使得网络民粹主义总是在现实与虚拟的复杂互动中得以建构。克莱·舍基强调了网络媒体实现群体性聚合的功能:“一则新闻可以在刹那间由一个地方扩散到全球,而一个群体也可以轻易而迅速地因合宜的事业而被动员起来。”[13]10网络民粹主义通过网民的话语、观点、诉求和主张潜隐在各种网络舆情中,如新闻的标题、事件的报道、故事的讲述以及话语的恶搞、图片的寓意、热点的争论之中。这种分散的、个别化的话语和符号是网络民粹主义的重要呈现方式。这种碎片化、个性化的话语方式并不会保持绝对的平静,而是像波浪一样不断起伏,它们彼此之间会发生聚集和融合,可能会突然在某种议题刺激下形成一股汹涌的浪潮,甚至发生蝴蝶效应,进而掀起巨大的舆论压力。
从根本上来说,网络民粹主义话语代表着一种以话语为载体的微观权力。这种话语权力不仅突破了传统权力自上而下的单向特征,而且其发挥功能的方式也发生了变革,是一种依赖于网民认同从而作用于心灵的权力。卡斯特对此有详细的描述:“新的权力存在于信息的符码中,存在于再现的影像中;围绕着这种新的权力,社会组织起了它的制度,人们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并决定着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权力的部位是人们的心灵。”[22]4他进而分析了网络社会中同时存在着“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三种认同方式,抗拒性认同是由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污名化的位置的行动者所产生的。这就是说网民的聚集不是现实社会阶层身份的网络复制,更多源于共同的心态的激发和共同抗争对象的指认,抗争性是网络民粹主义话语的重要特征。
网络民粹主义“人民”话语的建构赋予了网民一种道义感和崇高感,抽象的“人多势众”也给网民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作为人民对立面的“精英”被打上邪恶的标签,这就赋予了针对精英的谩骂、诅咒乃至人肉搜索以一种宣泄的快感。在“话语建构”中,民粹主义为这种身份认同提供了双重的动力:一方面是作为“人民”的“我们”,另一方面是作为“敌人”的“他们”,因而是最容易构建起认同的一种话语资源。网络空间中无数对占据霸权地位的主流话语的不满在“人民”的话语下暂时性地接合起来,从而形成对抗主流霸权力量的统一战线,在人民的整体性、同质化话语建构中区分我们与他们,实现与社会精英之间的话语对抗。鲍曼对现代性的描绘形象地说明了网络民粹主义话语的产生逻辑:“惟一能够导向回归共同体团结的,并由于这种团结导向或回归一种可靠的栖居地的方式,就是选择一个共同的敌人,针对这一共同的目标,集中力量,共同施暴。”[23]7在无法消除现实生活中产生网络民粹主义根源的前提下,话语性特征降低了网络民粹主义滋生的成本,从而使得现实生活中经常受到监控、监管的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中报复性地爆发出来。
就政治效应来说,正是以话语作为主要形式,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往往由具体社会议题所诱发,这增加了网络民粹主义发生的频次,同时也降低了网络民粹主义对于政治系统冲击的强度,因而网络民粹主义主要属于生活政治的范畴,缺乏宏大政治取向。网络民粹主义的抗争性总是虚弱和有限,民粹主义理性在网络空间的张扬本质上体现着现实政治的虚弱。当然,网络民粹主义的影响也可能会溢出网络空间而走向现实社会,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呈现的网络民粹主义与现实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M].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DANIELE A,DUNCAN M.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8.
[3]MATTHIJS R,GEGOREN H.A Populist Zeitgeist?The Impact of Populism on Parties,Media and the Public in Western Europe[M].Oosterhout:Almanakker,2013.
[4]KURT W.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J].Comparative Politcis,2001(1):1-22.
[5]MARGARET C.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J].Political Studies,2006(4):544-552.
[6]MATTEW H.The Math of Digital Democrac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7]陈龙,陈伟球.网络民粹主义传播的政治潜能[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297-301.
[8]陶文昭.互联网上的民粹主义思潮[J].探索与争鸣,2009(5):46-49.
[9]沈丹丹.网络空间的民粹主义分析[D].上海:复旦大学,2012.
[10]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J].战略与管理,1997(1):88-96.
[11]尼·别尔嘉也夫.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12]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3]克莱·舍基.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M].胡泳,沈满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14]吴若增.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J].炎黄春秋,2015(5):40-43.
[15]陈龙.文化民粹主义与“看”的方式变革[J].学习与探索,2009(4):205-208.
[16]刘晓红.共处·对抗·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49-53.
[17]斯拉沃热·齐泽克,查日新.抵御民粹主义诱惑(下)[J].国外理论动态,2007(10):77-82.
[18]唐小兵.底层与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J].南风窗,2008(3):86-88.
[19]MARGARET C.Trust the People!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J].Political Studies,1999(1):2-16.
[20]EDWARD S.The Torment of Secracy:The Background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Security Policies[M].New York:Free Press,1956.
[21]PAOLO G.Tweets and the Streets:Soci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Activism[M].London:Pluto Press,2012.
[22]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3]齐格蒙·鲍曼.寻找政治[M].洪涛,周顺,郭台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