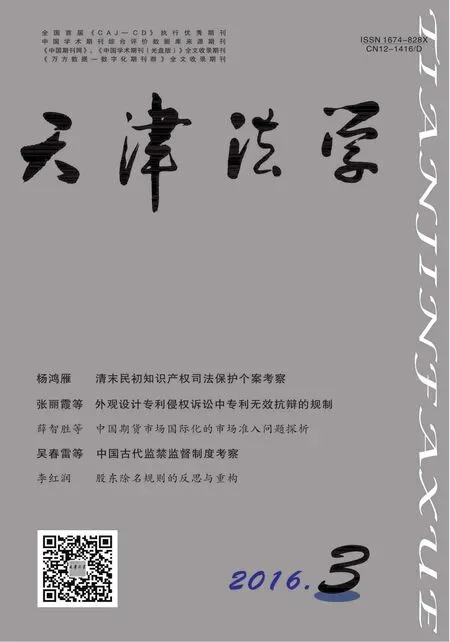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界分——以司法判决为中心的分析
冉克平,丁超俊
(华中科技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学术热点·
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界分——以司法判决为中心的分析
冉克平,丁超俊
(华中科技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界限应当泾渭分明。制度层面上,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权利属性、客体以及保护方式等都存在着不同,单纯从隐私权角度来保障个人信息权显然不足以达到救济权利的目的,个人信息权的设立具有理论基础以及在立法例上皆有参考;价值层面上,隐私权立足于保护人格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而个人信息权是基于个人的信息自决权。从法经济学角度考虑,笼统规范二者,司法效益的价值发挥欠佳,保护个人信息权能够对人格权形成更为充分的保护。民法典在进行体系设计时,可以考虑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此二者分别做出细致的规范,两者明确区分的模式,利于形成更为合理的人格权体系。
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界分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种隐私充斥网络,有观点认为“隐私已死”。的确,隐私的内容正在逐渐的减少。而由于信息社会的推动,个人信息不断传输到网络空间,可以说个人信息的范畴正在不断扩张。以保护隐私权的方式来保护不断扩张的个人信息,并不能够达到保护权利的目的,两者的冲突就显现出来了。
对于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关系,学术界与实务界存在纷争,主要有如下观点:理论界中,主张二者区分说与交叉说的观点值得研究。区分说,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从内容上看,隐私与个人信息有一部分的重合,而从整体的角度来讲,个人信息的范畴大大超过了隐私信息。因此,应将个人信息权单独加以规定,不能将其置于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之中[1]。交叉说,以张新宝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二者所指向的对象存在交叉关系,有的隐私应当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而有的则不然。个人信息一旦涉及私人生活的敏感之处则属于隐私的范畴,但是有的个人信息由于公开的程度比较高则不再属于隐私的范围[2]。
实务界的通行做法是通过保护隐私权的方式对个人信息的权利进行救济。当然,实务部门也并非千篇一律通过此种方法进行权利的救济,如通过名誉权、一般人格权等方式进行救济,对此下文有详细论述。
从前述的总结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关系争议较大,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司法实务部门虽然以“隐私权的方式来保护个人信息权利”为通行的做法,但实务部门也存在其他的法律救济路径。主张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为包含关系以及二者交叉关系的观点并未考虑法律的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信息社会尤其应当将二者进行区分。因此,笔者认为区分说更为合理,并试从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界分的必然性与可能性以及区分保护二者的经济意义进行分析,以期为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略尽绵薄之力。
二、个人信息权独立的必然性分析
(一)概念区分
博登海默教授认为:“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3]。梁慧星教授强调:“因为法律的概念性,决定了法律思维就是运用法律概念进行的思维”[4]。因此,我们要析清“隐私”与“个人信息”概念,这样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问题。
“隐私权”这一概念正式在法律上提出,要追溯至Warren和Brandeis于1890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The Right to Privacy一文。王利明教授认为隐私权是指个体对于私人生活的秘密以及私人生活的安宁所应享有的人格权[5]。张新宝教授认为自然人对于自身的生活安宁以及私人信息的秘密性受到法律保护,是一种不被非法干扰、搜集以及利用等的人格权,且权利主体有权决定自我的私生活他人是否可以介入,并具有对个人隐私是否公开以及公开的范围及程度的权利[6]。
“隐私”强调了私人领域的不可干涉和不可窥视性。“私”突出了其内容的非社会性与私密性,隐私与个人的人格尊严紧密结合。对于个人信息的概念并无统一的认识,可供参考的是欧盟的《资料保护指令》,其将个人信息界定为:“指与确定或可确定的自然人(‘资料当事人’)相关的任何信息。可确定的人是指可直接或间接地,特别是通过参考身份识别编号,或根据其身体、生理、心理、经济、文化或社会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具体因素,确定其身份的人”[7]。
笔者认为应将“个人信息”定义为:“自然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婚姻状况、家庭状况、教育背景、工作履历、健康信息、财务状况等任何单独或与其他信息比对即可识别特定的个人客观信息”[8]。需要突出的是个人信息的社会性以及客观性。个人信息与隐私相比,其与人格尊严的紧密程度不高。
隐私的内容一旦被公开后其不再具有隐私的属性,而个人信息被公开或者利用后其仍属于个人信息,不存在性质的改变。从上述阐释来看,隐私与个人信息所指的是不同的客体。因此,从概念区分的角度而言,二者的界分是有必要的。
(二)权利保障上的必然要求
从权利保护的时点来看,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侧重于“事后”阶段的救济,即只有当个人隐私被“揭露”时该权利才会得到保护,并且主要是通过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进行救济。而个人信息权受到侵犯的时间点包括从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应用这个完整的过程,即“事前”与“事后”两个阶段。
私法上,我国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主要是基于侵权法的路径进行救济的。实务中对于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大体都是通过保护“隐私权”的方式进行救济,往往是扩大“隐私”的含义以保护“个人信息”,以致于“隐私”与“个人信息”含义含混不清,现行法之下的这种处理是否妥当呢?王利明教授给出了答案,为了维持体系上的平衡以及不与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发生矛盾与冲突,我们不能通过扩张隐私权的内容来达到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目的[9]。
现行法之下的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法律中有明文规定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刑法对于个人或者单位窃取或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进行刑罚处罚,专门规定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第2款增设的罪名),我们应当注意到在司法审判实务中都是对犯罪分子进行惩戒,但并未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4条规定:“消费者享有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通过这两部法律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利存在着一定缺陷:一是保护的范围有限,刑法对行为后果的危害程度等要求较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限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其范围较小;二是通过上述路径对权利的救济并不彻底,刑法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却止步于对被害者损失的赔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仅是对商家作出限制而他人通过手段侵权则救济途径只能是通过“隐私权”或“名誉权”来进行保护;三是公法的保护途径与私法的救济路径并不能够“殊途同归”。刑法所保护的对象更多的是从社会的层面而言,由于个人信息权利体现的是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以及财产关系,因而个人信息权利的救济应当体现于私法上的保护。
也有观点认为通过司法解释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对此,有专家指出:“应看到隐私权所保护的与个人信息所保护的是不同的价值指向。在大数据时代之下,个人信息成为一种极有价值的信息资源。现行法之中,并未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作出规范以及未对信息权利人的权利内容作出明确的规定。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希望司法解释对个人信息及其合理使用作出恰当的规范是难以令人满意的”[10]。
(三)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目前的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表现形式来看,主要包括:对个人网络活动的侵犯,例如监视、分析个人活动以及对邮箱内邮件内容的窃取与篡改。对个人网络痕迹的搜集与追踪,如聊天记录等网络痕迹搜集、在硬盘植入cookies、购物网络痕迹的搜集以及搜索引擎搜索个人网络痕迹等。对个人网络空间的侵入,如侵入个人主页、QQ空间、微博好友圈等。
互联网时代,用户随机登陆一个网站,如果继续浏览或者下载相关文件时,就需要填写个人的信息,并且通过邮箱或手机验证后方可继续操作,稍后各种垃圾邮件或者短信蜂拥而至。一些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时也需要填写大量的个人信息,在此之后出售答案、辅导班推销以及考后改分的诈骗信息或者电话也是接踵而至。“个人信息”虽然被要求填写,但用户并不希望它们被陌生人掌握。
通过侵权法来保障个人信息的权利显得过于消极,因为侵权法救济的方式是被动的、事后的,不利于权利主体维护自身的权利,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并不能达到“亡羊补牢”的效果。采取侵权责任法保护个人信息权的一个前提是“发生实际的损害后果”,来衡量这样一个“后果”并非易事。并且在信息时代,单靠隐私权进行“单兵作战”,对市场以及网络秩序的规制都是不明晰的。个人信息所体现出的价值已经远超人们的预估,商业利用的手段多样化,而保护隐私权的“被动”手段似乎不足以克服个人信息被侵犯、盗用的问题。随着社会公开与透明的程度越来越高,隐私的范围在缩小,而个人信息的范围在扩大,同时个人信息的数量也在急剧膨胀,以隐私权狭窄的保护方式来保障公民个人信息权,难免“力不从心”,因此区分二者的意义就不同一般了。
三、二者区分的可能性分析
(一)理论基础
学术界与实务界对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关系存在分歧:一包含说,就该说内又包含两种认识和看法。其一是隐私权包含个人信息,杨立新教授认为:“个人信息所保护的对象也就是隐私权所保护的内容,所以个人信息就是隐私的一个方面”[11]。王泽鉴教授认为:“从权利的核心角度来看,隐私权的核心包括私权利和自主权利。其中的自主权利是指自己有权利决定形成何种私人范围的生活,隐私权所保护的除了私人生活不受干涉之外,还有信息的自主,也就是自我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公开有关自身的数据,就是通常所说信息隐私”[12]。其二是个人信息包含隐私权,实务部门有法官认为:“公民的个人信息应指那些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判断出该公民个人的、与身份有关的信息。因而隐私应当包含在个人信息之中”[13]。二区分说,除前述王利明教授如此主张外,学界有不少学者也如此主张,郭明瑞教授认为:“在信息化时代隐私权的内容随之而发展,网络信息权成为了一种新的独立的权利”[14]。石佳友教授认为:“从权利的保护角度而言,民法典中的隐私权并不能够满足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而个人信息权利是一种与隐私权所不同的独立的一项人格权”[15]。三是交叉说,实务部门有法官认为:“从概念上讲,并不是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的范畴,也非所有的隐私都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此二者在概念上是存在交叉的”[16]。
追本溯源,从哲学基础的角度来思考二者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隐私权的哲学基础是人格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个人信息受保护的权利则是立足于个人信息自决权”[17]。有学者主张对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区分应从身份的可识别角度来思考,这个角度来看“隐私”与“个人信息”似乎永远存在重合部分。如果从客观性以及社会性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则两者越辨越明。隐私强调的是“私”,隐私的内容更多的包含了社会的主观道德评价;个人信息就类似于姓名一样的代号,仅仅是大众认知、识别某人的客观情况,并不存在道德评价。从社会性的角度出发,“隐私”应当是远离大众视野的,且禁止知悉的群体宣扬。而个人信息则是被部分人所知悉,社会交互行为所必须了解的内容。
有学者从法哲学的角度对个人信息权的合理性作出论证[18],该学者从劳动论(主要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上更加侧重后者,强调个人对其附属物享有的自然权利)、人格论(从人格与个人信息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二者关系紧密,人格利用与外界的作用进行发展,保护个人信息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授予个人信息使用权进行展开,实质上来讲是保护个人信息中的人格)、激励论(该论人为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不仅是确认个人的利益而且对其他利益主体进行保护)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个人信息保护权具有物质的正当性和阶级的正当性)对个人信息权存在的合理性作出分析。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学界、实务界对于个人信息的研究近年来程上升趋势。即便我们承认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内容存在一部分的重合,但是从实质上来讲隐私所反映的信息是不愿意向外界透露的或者是个人敏感的信息,隐私重在保护人们的私密空间。而个人信息的内容则关注于身份的识别上,也就是通过该信息可以将该主体与其他主体区别开。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区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并非不可能。
(二)体系上的建构
大数据时代,隐私权主要体现为对人格尊严的保护,而个人信息权不仅对人格尊严进行保护还包括对财产利益的救济。个人信息权一方面表现出精神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其财产性。而保护个人信息财产权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因此,有学者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单纯地将个人信息的保护置于人格权或者财产权的保护之下是存在问题的。通过人格权来规制个人信息权利中的人格利益,而通过财产权来规范个人信息权利中的财产利益,这样二者可以相得益彰,那么对于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就更加周全[19]。
有学者可能认为既然个人信息权已经包括了个人的姓名以及肖像,那么立法上再安排姓名权、肖像权的意义体现在何处?应当认识到,姓名权保护的是公民的姓名,也即“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冒用”。肖像权是公民对自己的肖像所体现的人格利益的一种人格权,即“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曝露个人信息当然离不开姓名或者肖像,但此时姓名或者肖像已经成为识别身份的一种辅助性的“信息”,应当与“姓名权”以及“肖像权”区分开来。保护个人信息权,并不是肆意扩张个人信息的内涵而“侵蚀”其他具体人格权。
(三)立法例上的借鉴
美国法上,《1974年隐私权法》是该国首次对个人信息隐私权进行规定。“美国对于个人信息隐私保护是采取个别立法的方式,仅针对各公私领域的特定行业中的特定问题和不同需求,推出个别法案以保护个人隐私”[20]。
德国法是采取区分原则的,《德国民法典》中并未规定个人信息的权利,而在民法典之外单独制定《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其主要保护的权利包括:请求告知权、个人资料更正权、个人资料封锁权、个人资料删除权[21]。
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已经涵盖了个人信息的权利(信息意思)。学说与立法并非必须具有一致性。台湾地区早在1995年就制定了《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2010年修改通过了《个人资料保护法》,并于2012年10月实施[22]。学术上学者并不认为隐私与个人信息相分离,但是在立法上承认了个人信息(资料)这项权利。
上述国家和地区在立法上都承认了个人信息权。从立法例上来说为我国提供参考,我国在法律中应承认个人信息权,并应当认识到个人信息权也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权,将其纳入人格权法的体系中。我国的《民法典·人格权法编专家建议稿》在第5章中专门规定了“个人信息权”,其涵盖对信息自决权的保护、对基因信息的保护以及合理利用等情形。这样就可以避免任意扩张隐私权的内涵而破坏法律的体系,也可以解决现行法下对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不充分的问题。
(四)司法路径剖析
“上诉人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朱烨隐私权纠纷案”[23](以下简称“百度公司侵权案”)中二审法院裁判认为“网络用户的网络活动轨迹及上网偏好,具有隐私属性,但这种网络活动轨迹及上网偏好一旦与网络用户身份相分离,便无法确定具体的信息归属主体,不再属于个人信息范畴。”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网络活动及上网偏好是否值得法律保护?网络轨迹能否与身份分离?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在网络空间的活动是值得法律的保护,因为网络空间也具有私密性,是私人生活的延伸部分,同时也涵盖大量个人信息。第二个问题主要焦点在能否识别“信息主体归属”上。“数据”在普通人眼里无非是一长串的字符,但在专业人士的眼中就不同了,经过大数据技术处理之后,就可以通过该数据追踪以及查找到用户个体了[24]。在刑事案件中,诸多网络警察通过网络痕迹可以追踪犯罪嫌疑人。运用类推思维,个人的网上浏览痕迹是不能与用户身份相脱离的。
私法上,除前述法院通行做法外,笔者总结司法部门对于侵犯个人信息权利的往往会通过其他三种方式对被害人的权利进行救济:
1.通过保护名誉权的方式对个人信息权利进行保护。根据民通意见第140条:“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现行法之下并未规定“个人信息权”而笼统由隐私权进行救济,一旦散布某人信息使得隐私的内容与个人结合并且对个人造成极大精神痛苦,则可以通过救济名誉权对其隐私或者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思考的路径,但这种做法甚似“王顾左右而言他”,并未真正面对问题。
2.在电商如火如荼发展之下,有法院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个人信息进行直接保护[25]。如前文所述,法律中明文规定保护“个人信息”的屈指可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是其一。该法第14条的规定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值得称赞,但是该法所保护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3.通过一般人格权对个人信息权利进行救济。“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信息传播速度快、影响力大、覆盖面广,保证个人信息的隐秘、安全和正当合理使用已经成为维护个人生活领域安宁、保持个人良好生活环境的重要手段,因此公民的个人信息应当属于一般人格权的范畴,受到法律保护。个人信息除传统的姓名、家庭住址、工作情况外,还应包括手机号码等其他所有专属于本人并可将本人与他人识别开来的信息总和。因此,手机号码作为个人信息应属于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26]。有法院在对透露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案件并未用“隐私权”一词,也仅是使用“含有相当隐私”对侵权行为进行了叙述,在对该案定性时法院的表述是“对赵某某民事权益的侵害”[27]。也并未用“隐私权”字眼,可以见得该法院对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是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是存有不同意见的。
从上述司法实务部门的处理方式来看,现在法院通行做法是通过保护隐私权的方式对个人信息权利进行救济。那么,也有法院试图破解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困局,而通过“一般人格权”的角度进行权利的救济。
四、二者区分保护的经济意义分析
(一)司法过程的经济分析
司法过程是以法院为中心来展开的。实质上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进行一项民事审判活动法院所支付的成本是否相一致。司法效益是指司法机关在解决社会纠纷时带给当事人的收益和维护社会法律秩序稳定所取得的效果。司法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社会法律秩序,但是物质利益由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而丧失,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司法效益是一种负效益。虽然司法效益是一种负效益,但是我们仍然不可小觑其作用。为了避免法律的虚无主义“司法效益的衡量是以法律能否及时、准确地恢复当事人之间权利平衡,以及用最低的人、财、物消耗满足人们的有效权利救济为标准”[28]。
我们不难看出,法院在审理侵犯隐私权等类似案件时所耗费的成本大体相当。但是司法效益是否能够恰如其分地恢复当事人之间的平衡?隐私的内容一经公开即对被害人造成损失,而个人信息的反复利用价值尚存,若将二者笼统进行保护,司法效益的价值则不能有效发挥。
(二)守法行为的经济分析
对于侵犯隐私权以及个人信息的权利案件,司法实务部门在处理赔偿问题时做法大体如下:在“王菲诉张乐奕侵犯名誉权案”中,原告诉请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最终得到支持的是3000元。在“赵建胜与江苏概念传媒有限公司、狄霄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中,原告诉请赔偿精神抚慰金20000元,最终得到支持的是3000元。在“陈锐与陈晓慧名誉权纠纷案”中,原告诉请精神抚慰金500000元,最终得到法院支持的数额仅为5000元。从上述案件中来看,被害人所获得的赔偿非常有限。
美国学者盖多·卡拉布雷西认为:“在一般威慑之下,事故成本主要包括如下方面:一是具有市场价值的物品,此即财产损害的范畴;二是身体伤害;三是疼痛和痛苦及感情损害;四是管理的费用;五是归因于交易的修正”[29]。从侵权者的角度来看,其散布隐私与公布他人信息可能目的不同:散布隐私意欲使他人受到伤害,以期满足“炒作”或者贬损他人之目的。而公布他人信息,一则往往与侵犯他人隐私相结合,通过公布的信息主体与隐私内容相结合,二则是出卖他人信息,以期获取经济价值。而侵权者所受到的惩罚无异于删帖、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以及其他程序费用。众所周知“覆水难收”,隐私一旦泄露就不再是秘密,对被害者的伤害可想而知。从侵权者的成本而言,若伤害某人,通过泄露隐私的方式,所支付的违法成本较低。如上述的案件中,对法人组织所要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仅为三千元。从受害人的角度来看,在进行权利的救济时除了时间成本的投入外,还包括一些律师费、公证费等费用,律师费并不能得到支持,公证费在有些案件中法院也仅是支持一部分。这样一来,所投入的成本与最终收到的守法效益并不对等。因此很多受害者选择沉默。隐私的内容可能被海量的信息覆盖,但是个人信息与自身息息相关,其被再次利用的可能性极大。如果被害者选择缄默,那么埋下的隐患就更多。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 [2001]7号虽未直接列举隐私权属于受保护的范围,但侵犯隐私权仍然可以适用之,根据该解释第8条区分了侵权后果的严重程度,即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侵权人需要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以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侵权人除上述责任外还可根据请求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隐私权受侵犯以精神受损害程度来衡量,单纯认定“造成实际损害后果”较为抽象,那么我们可以援引上述的司法解释第10条,虽然该条是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倒推”的方式来确定是否构成导致精神损害,如“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以及侵权人的获利情况”等。现行法之下,笔者试图通过这样的理解,扩大对受害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
百度公司侵权案中百度公司上诉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默许同意”,即用户没有明确拒绝就推定其同意。部分学者认为对于“告知与许可”方式是保护隐私权或者个人信息权的一种很好方式。换言之,数据的搜集者必须告知个人,他们搜集哪些数据、作何用途,也必须在收集工作开始之前就告知网络用户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制度安排未免小看了一些网络数据公司,数据的价值大多展现在二级用途上,但是在收集数据时对此并未有所考虑,那么单纯依靠“告知与许可”机制就不能再达到预期的管理目的了。
五、结语——人格权法的立法必要性
随着网络在我们生活中的普及,公民的隐私不经意间就会曝露于网络,个人信息也随时会被窥视,人格权受侵犯的风险大大增加,权利的维护与秩序的规范都离不开法律的导向。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已是迫在眉睫,“上诉人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朱烨隐私权纠纷案”在网络上被称为“cookie技术与隐私权纠纷第一案”,对于“第一案”的界定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保护自己的隐私权,网民已经开始觉醒。隐私权所涉及的内容大抵是涉及个人痛楚的,因而对其传播将会对个人造成极大的伤害,法律对这样的行为应设“禁地”,禁止他人涉足,且隐私的内容一经公开后就不再具有隐私的属性了。而个人信息具有客观性与身份性,并且表现出一定的财产属性,其被公布后具有多次使用的可能。大数据时代,信息只有流通才具有价值,倘若对个人信息如同保护隐私一样,那么作用是适得其反的。因此,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非不能触碰的“禁地”。
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但是法院的判决依旧能给行业带去指引。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司法解释,《立法法》承认并肯定了司法解释的作用与地位。不得否认的是它们为法律更好地适应社会贡献了一些力量,但法律不能单纯依靠司法解释维系其生命力,从而去解决新的社会问题。法院如果角色定位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在法理上说不通,那么就对立法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现代人权观念引导人们重新思索人格权,权利的保障离不开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格权法的制定正充分体现《宪法》第33条的价值与意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学界对此进行各种研讨。在总则编之外单独制定“人格权法”编在学界的呼声很高,“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30]。人格权法立法的目的并非为了限制或者说遏制技术的发展。相反,它的目的是要在个人权利的维护与技术进步的冲突中寻找平衡。一来禁止网络技术对人格权的侵犯,二来限制人格权所保护内容的随意扩张。人格权法的制定不单单具有宣誓的意义,也同时是我国立法工作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保障公民权利的一种体现。
[1]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2,(6):68-75.
[2]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J].中国法学,2015,(3):38-59.
[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504.
[4]梁慧星.怎样进行法律思维[N].法制日报,2013-05-08(09).
[5][30]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67.
[6]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12.
[7]欧盟资料保护指令.转引自孔令杰.个人资料隐私的法律保护[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345.
[8]洪林海.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4.
[9][26]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J].现代法学,2013,(4):62-72.
[10]杨临萍,姚辉,姜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J].法律适用,2012,(12): 22-28.
[11][27]杨立新.公民个人电子信息保护的法理基础[J].法律适用,2013,(8):2-8.
[12]王泽鉴.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隐私权篇(中)[J].比较法研究,2009,(1):1-20.
[13]“侵犯公民人格权犯罪问题”课题组.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司法认定[J].政治与法律,2012,(11): 149-154.
[14]郭明瑞.人格、身份与人格权、人身权之关系——兼论人身权的发展[J].法学论坛,2014,(1):5-10.
[15][17]石佳友.网络环境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2,(6):85-96.
[16]陈晓东,凌巍.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的现实困境及出路[J].法律适用,2013,(8):23-29.
[18]张莉.个人信息权的法哲学论纲[J].河北法学,2010,(2):136-139.
[19]李延舜.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及其限制[J].法学论坛,2015,(3):43-53.
[20]高圣平.比较法视野下人格权的发展——以美国隐私权为例[J].法商研究,2012,(1):32-37.
[21][28]齐爱民.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法国际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71-73.
[22]张红.一项新的宪法上基本权利——人格权[J].法商研究,2012,(1):38-42.
[23](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96.
[24][29]冯玉军.法经济学范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458-459.
[25](美)盖多·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法律与经济的分析[M].毕竞悦,陈敏,宋小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6-191.
Differentiation of the Privacy Right an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Analysis on the Judicial Decision as a Core
RAN Ke-ping,DING Chao-jun
(Law School,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The boundary between righ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should be quite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There are som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etween the privacy right an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uch as the aspects of the right attribute,the object and the way of protection.Protecti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simply from the angle of the right of privacy is clearly not enough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elief right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 ha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legislation examples for reference.In the value aspect of the legal system,the privacy right protects the human dignity and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but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 protects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and Economics,normalizing the two sides in broad generality impairs the judicial efficiency.Advocati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 can protect the personality right sufficiently.When designing the framework of the Civil Code,it would be better to make the law of personality right as a separate part of Civil Code,develop circumstantial norms for both sides and draw a clear line between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and the privacy rights,to contribute a more reasonable system of the personality right.
the privacy right;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differentiation
D913
A
1674-828X(2016)03-0038-07
2016-04-11
2015年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人格权上财产利益保护的立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AD020。
冉克平,男,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民法学研究;
丁超俊,男,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2014级法律硕士,主要从事民法学研究。
(责任编辑:杜爱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