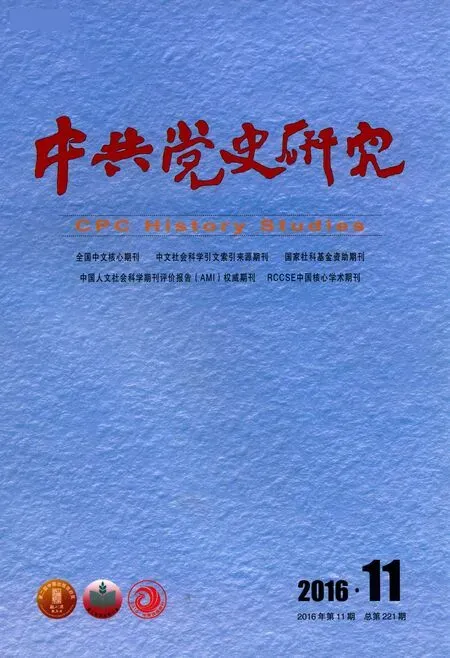中共党史论文论点摘编
中共党史论文论点摘编
一个可能的思想来源:李大钊“活的历史”与伍德布里奇《从历史到哲学》的对比分析
姚 正 平
1924年,李大钊在《史学要论》里所提出的“活的历史”概念以及其他一些颇具前瞻性的历史认识论观点,长期为学术界高度推崇,但这些观点源自何处,却甚少得到关注。实际上,李大钊的这些史学观念很有可能来自1921年1月《史地丛刊》所刊登的美国哲学家伍德布里奇《从历史到哲学》一文。该文明确区分历史本身和历史著述的概念,认为历史本身是活的,因而对历史的解读亦是活的,历史注定要被不断重写,且这种解读的真实性是趋向进步的。这些历史认识论方面的卓识在稍晚出版的李大钊《史学要论》里都有明确体现。更重要的是,二者不仅观点基本一致,而且所举证的例子、表述的语句、使用的概念、论证中出现的矛盾甚至文末结尾的方式等都十分相似。如二者在论述历史需要不断被重写这一重要观点时,表述的语句基本一致,且都列举了“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和英国著名希腊史学家格罗特对希腊史描述的例子;对于“历史”的定义,二者也基本一致,而李大钊对于“活的历史”一词的运用和对“活的历史事实”的阐述都明显直接受启于伍德布里奇;强调历史会不断被重写与坚信完备的历史著述终将写就,这两个看似无论如何也无法调和的观点,也被二人同时接受并加以论述,这缘于二人拥有共同的理论预设,即历史虽总要被改写,但这种改写大致来说趋于进步,也更加趋向接近历史真实;二者都在文末提出两种作史的方法作为结尾。可见,李大钊在历史认识论问题上的深刻洞见,实际上都可能源于这篇文章。这些史学理论问题在国内十分超前,即使在当时的欧美学术界,恰与当时盛行的相对主义思潮多有一致,亦是相当前沿的。《从历史到哲学》一文的翻译者何炳松以及缪风林等人亦较李大钊更早关注到这些在近代史学理论中相当重要的问题,后经李大钊的吸收与改编,共同在史学理论方面推动了近代中国史学学科化的发展。(吴志军摘自《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4期,全文约10000字)
胡绳理性主义思想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捍卫理性与自由
韩 爱 叶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胡绳积极响应“新启蒙运动”,于1935年至1948年间撰写了大量文章,参加了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各种论战,逐步形成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的写作风格。针对冯友兰将理性分为道德理性和理智理性以及道德高于理智的主张,胡绳指出任何道德律令都必须接受理智的审查,方可进入理性之境地,而不是相反;理性的道德维度和理智维度不仅是统一的,而且都需要置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等各种语境下加以理解。针对当时思想文化界对胡适的两极化评价,胡绳认为应该从历史主义的视角,辩证批判胡适的启蒙思想,在高度肯定胡适关于呼唤人们过一种“理性的生活”和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之认识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胡适启蒙思想的不彻底性,进而主张应该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来观察和分析现实,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胡绳还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的启蒙运动史,重新评价了戊戌维新和新文化运动的积极作用与不足之处,指出当时的“新启蒙运动”要继承“五四”精神,继续提倡民主和科学,但个性解放不应局限于少数人,而应是绝大多数人民在共同生活中发展个性。基于此,胡绳指出,今天我们要继承“五四”,就必须要超越“五四”,超越才能真正继承。“民主与科学”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民主事业(政治和经济的民主)、科学事业(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二是民主与科学精神,包含反迷信、反神权、反专制、反盲从、反武断等。“五四”所提倡的主要是民主与科学精神,立足于“破”,而现在要超越“五四”,重视“立”新事物,建设民主与科学的事业。总之,胡绳在这一时期的著述,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捍卫了理性与自由的精神,正确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精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的理性主义品格。(吴志军摘自《理论月刊》2016年第3期,全文约8000字)
五四新文化运动喊错口号批错对象了吗?
商 昌 宝
从9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撰文指出,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儒表法里”的根本性结构,“五四”启蒙运动“批儒不批法”的选择并未抓住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文明发展和文化近代化过程的误解,这一情势甚至与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逻辑关联。但是,若想真正理解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缘由,就必须重返民国初年的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民国成立之初便遭遇内忧外患的困境,共和政体无法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对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等方面的控制力都很弱,“民国不如大清”“今不如昔”的论调急速蔓延,政治复辟和文化复古的呼声此起彼伏,并直接导致袁世凯和张勋等两次复辟逆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者才有针对性地喊出“民主”(这里的民主更多地指向“由民做主”、主权在民这一内涵)的口号以应对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君主;喊出“科学”的口号以应对定孔教为国教这种带有“罢黜百家,独尊一术”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和复古思潮。故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恰如其分、针砭时弊地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政情和文化基因,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阻击和对抗破坏民主共和的政举和国人根深蒂固的专制文化传统。类似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儒不批法”的论断并非基于基本史实,而是从现实中国的结果向前倒推历史发展的轨迹,带有明显的主观臆测和历史决定论的色彩,脱离开历史语境的历史解读注定会走向偏颇。事实上,要回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主潮是什么,要探求新文化人为何喊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以及反儒不反法,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耐心翻看当年的第一手文献。如在《新青年》1915年至1917年的3卷18号里,批判文化复古和政治复辟以及讨论国体和政体的文章,可谓期期可见、目不暇接。此外,还可以参看《东方杂志》《甲寅》《不忍》《国民公报》《亚细亚日报》《申报》《民国日报》等。如果全景式地充分阅读这些文献,就不会出现以宏观思想史脱离具体历史语境地去阐释微观的具体问题那样的错误了。(吴志军摘自《东岳论丛》2016年第8期,全文约9000字)
新旧之间:建国初期上海国营鱼市场经纪人制度的改革
刘 亚 娟
上海鱼市场执全国渔业交易之牛耳,关系国计民生。作为鱼市场的“经纪人”,鱼行存在已逾百年。经纪人制度尽管弊病颇多,但其借助产品交易和利益分配的习惯,已然牢固地镶嵌在渔业交易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着力于促成上海鱼市场的国营化,经纪人制度被认定为“封建残余”,成为众矢之的。在改革经纪人制度的过程中,新政权通过现款交易、取消外佣、配备经售员等步骤,并有效利用旧行会之间的矛盾,借力用力,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逐步废止了经纪人制度。这一过程所体现的缓进的改造原则也给予被改造一方以活动空间,使其能够不断调整策略并加以适应。鱼商业公会一度以新民主主义政策为保护伞,为经纪人制度的留存奔走,鱼行代表在新政权的话语中为自己寻求合法性,鱼市场职工则基于个人利益而不时制造意外,甚至以激烈举动打乱原计划,从而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因此,上海鱼市场经纪人制度的改革可被视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新政权与旧制度互动的一个历史缩影,从侧面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度变迁进程中新旧杂糅的历史特点。(吴志军摘自《史林》2016年第2期,全文约17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