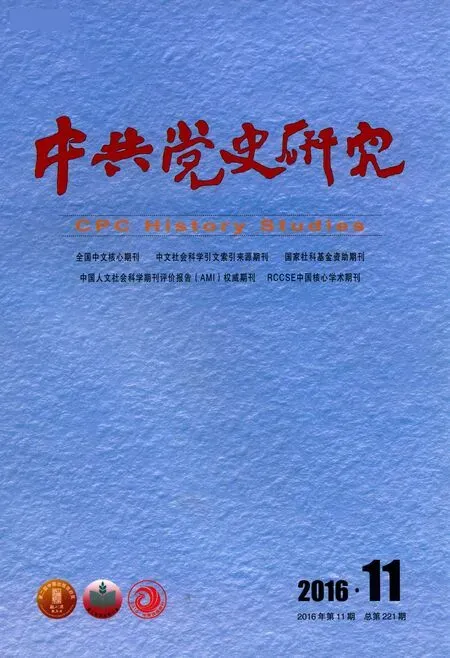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
李 金 铮
·理论与方法·
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
李 金 铮
在《向“新革命史”转型》一文的基础上,本文对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作出进一步阐释。新革命史不是一个新领域,其研究对象与传统革命史几乎无异,只是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审视中共革命史,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概念和理论。其方法主要包括五个方面: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从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共革命史,以及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已包罗殆尽,而应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所有能够进一步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皆可视之为“新革命史”。
传统革命史观;新革命史;视野
拙作《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发表后,引起了学界较大的反响。很多学者在《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清华大学学报》《史学月刊》《重庆社会科学》《党史研究与教学》《中国农史》《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等学术报刊上撰文,对此文给予了积极评价和殷切鼓励。“新革命史”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和方法,已被不少中国革命史和党史学者所运用,这给笔者增添了许多信心。不过,仍有一些同行对此不甚了了,多次问笔者几个同样的问题,如什么是“新革命史”、传统革命史研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如何开展“新革命史”研究等。有的学者还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建议。黄正林认为,“新革命史”需要突破的不仅仅是“政策—效果”模式,而是应对传统革命史研究的史观、方法、视野、资料以及书写方式等进行全方位的反思*黄正林:《近代中国乡村经济史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评李金铮的〈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中国农史》2015年第2期。。把增强也指出,“新革命史”研究理念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如除从乡村社会史的层面反映中共革命的艰难与复杂之外,有没有其他释读中共革命史的视角?如何构建多元化的研究路径方能更好更全面地解读中共革命史的全部内容?*把增强:《中国近代乡村史治史的新门径——从李金铮〈传统与变迁〉所见》,《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以上建议都促使笔者进一步思考相关问题。必须承认,任何学术理念、方法从酝酿、产生到成熟,都有一个艰难而反复的蜕变过程,“新革命史”也当作如是观。笔者不拟过多重复已发表过的言论,只想在既有的基础之上,对“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做进一步申述。
首先,需要界定两个概念,什么是中国革命史?什么是“新革命史”?
在20世纪人类社会的演进之河中,革命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风景”之一。就中国而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反帝反封建、独立解放、自由民主和现代化而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斗争,包括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中共革命等,都可称之为中国革命史。考虑到历史的连续性,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属于革命史的范畴,或可称为中国革命的后半场。*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仍是中共革命的延续,这点与王奇生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参见王奇生:《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中国当代史的“革命史”意义》,《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革命影响乃至决定了20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大势,反思革命、研究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学术论题。笔者侧重研究的是中共革命史,近年所提倡的“新革命史”的研究对象也主要指的是中共革命史,但更多是战争年代的革命史。它既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近代中国系列革命中带有结局性的革命,并与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总之是中共一切历史的基础。
如果说要给“新革命史”做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大概可以这样表述:“新革命史”是回归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概念和理论*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回到历史现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语境下,考察人们是如何想、如何做的。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传统革命史观最大的问题,就是凸显了政治、党派、主义、阶级和革命史本身,而忽略了其他面相,“新革命史”就是试图改进这种史观的一种视角和方法*近些年来,一些学者针对传统革命史观之弊,提出以“现代化范式”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笔者以为,“现代化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革命史观的缺陷,有其进步意义,但不能不说,它仍然是一种线性史观,未能脱离“目的论”的逻辑,并遮蔽了中国近代史的许多丰富面相。本文所提倡的“新革命史”理念和方法,虽然主要适用于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但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可能具有某种启发意义。。笔者以为,若想维护和建立中共革命史的合法性,仅仅靠喊口号、靠增加外力的影响是很难达到的,甚至在一定情况下还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研究者完全可以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获得使人信服的权威性力量,这是今天党史研究、革命史研究头等重要的任务。笔者坚决反对没有任何研究基础的极端“妖魔化”言论,但也不要将在认真研究基础上所揭示出来的“问题”简单理解为影响了党的形象,而是应该视之为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更重要的是,这些难题往往是传统社会留给革命的,而非革命本身产生的。中共正是发现和解决了这些难题,才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并真正彰显了革命之光辉。也不要将“新革命史”误解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更不能说革命史本身有什么问题,其研究对象与传统革命史没什么两样,只是视角和方法发生了变化*革命史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因任何人的喜恶而发生变化。但如何描述革命史,如何解释革命史,则因视角和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如果用一个比喻,“山还是那座山,风景依旧”,但美丽的风景需要发现,我们要有发现风景和欣赏风景的眼睛。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在学术史的谱系中,反思不是苛责前人,而是避免事后重陷已有之误;变化不是造反,不是“革命”,不是终结,而是改良,是扬弃,是超越。迈出传统革命史学之门,目标仍是回到原本魅力无穷的革命史之家*譬如传统革命史观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就依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此为众所周知,无需强调和重复。笔者所主张的“新革命史”理念和方法,更多的是针对传统革命史观之弊而言,并不否定其具有解释力的部分。。针对传统革命史存在的具体问题,“新革命史”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即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从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共革命以及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这一看法,较之《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一文则有明显的拓宽和深化。
一、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
传统革命史观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笔者曾概括的“政策—效果”模式,也可以说是“两头”模式,还可以称之为“三部曲”思维,即中共政权的政策演变,农民接受并获得了利益,最终是革命斗争、革命建设积极性的提高。本来,这种宏大构架、宏大叙事的方法是无可指责的,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无不追求对宏大问题的解释。但如果将中共革命史笼罩在这样一个模式之下,一场艰难的、曲折的、复杂的革命就变得简单化了。
所谓“复杂”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由广大农民参加的革命中,革命领导者、中共政权与乡村社会、农民群众之间,原本存在着相当复杂的互动关系。对于中共领袖和中共政权而言,要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非常不容易的。要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一系列建设,也会遭遇诸多困境,甚至可以形容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面对以上问题,中共总是要想办法克服和解决。而对农民群众而言,共产党是陌生的党,中共政权是陌生的政权,他们对共产党及其政权的了解以及建立联系的过程,同样不是一拍即合的,他们对革命有过犹疑、挣扎和痛苦。
然而,在传统革命史观的宏大构架之下,我们很少见到鲜活的、艰难的、复杂的革命过程,中共政权与乡村社会、与广大民众之间俨然成了单向的“控制”和“被控制”、“挥手”和“跟随”的关系。共产党的领导策略与农民的革命认同之间,呈现为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变成了举手之劳,变成了万能的神话,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革命领导者和中共政权的正确性、权威性。问题是,“高大全”式的超人就能抬高共产党革命的形象吗?恰恰相反,笔者以为它极大地贬抑了共产党的作用。因为谁也不会认为简单的革命是可敬的,这应该是不难理解的道理。
那么,如何改变以上这种“两头”模式的“政策—效果”模式,还原和反映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农民群众的复杂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尝试采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和方法。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不是西方学术视野中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而是指来自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权力与来自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二者之间既有融合与转换,也有排斥与冲突,或者说是相互排斥、融合乃至转换的“合力”,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历史面相。这一视角愈益成为分析国家、地区和民间社会亦即自身“空间”关系的一个有效路径。而这一理论工具恰恰与中共革命的进程是颇相契合的。回顾自清末民初以降的历史可知,政府向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呈不断加深的趋势。不过,只有中共领导的革命才真正深入而彻底地控制了乡村。甚至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像共产党那样,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如此巨大规模的革命性改造。正因为此,上层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频繁和密切得多。这一历史实际为国家和社会互动关系的方法提供了用武之地。
兹以抗战时期中共华北根据地的钱粮征收为例,来说明传统方法之弊以及国家与社会互动方法的作用。钱粮征收为中共革命生存和发展的财政命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传统革命史观的著述中,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如上所说的“政策—效果”的“两头”模式。譬如,影响颇大的权威著作《华北抗日根据地史》,应该说已经与传统党史撰述有了不小区别,但即便如此,这一思维模式仍然清晰可见。无论是合理负担还是统一累进税的实行,都是在叙述完共产党的政策、办法之后就是结果:“华北抗日根据地由于实行了合理负担政策,整顿了财政,使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减轻……抗日经费来源保持了稳定并能逐年增加。合理负担调动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华北抗日根据地推行统累税的负担政策后,克服了财政上的紊乱现象,使人民的负担更加合理。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不仅从人力上保障抗日战争的需要,同时通过财力分配,在调节各阶层人民的收入,为建立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奠定了基础”*魏宏运、左志远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128—132、215—219页。。如果在战争时期将以上描述作为政治宣传的话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则丢失了太多的东西。
此类著作最大的问题,就是钱粮征收的过程没有了。后人难以看到钱粮是如何征收的,尤其看不到农民、地主和富农等阶级对征收政策的反应,看不到他们与根据地政权之间的关系。而借助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便可以发现,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地主、富农,他们对共产党的钱粮征收,就像对待历史上的钱粮征收一样,一般不会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尤其是贫苦农民,经济条件差,收入水平低,生活已极艰难,多拿出一点钱粮都可能影响其生存。所以,为了少纳钱粮,古已有之的隐瞒“黑地”现象,到根据地时期仍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加。也正因为此,中共政权始终进行着反“黑地”的斗争。*相关文件如中共冀中六地委:《关于深入减租查租及开展控诉复仇运动的思想领导与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2月),《河北减租减息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4—415页;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传达与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决定》(1946年7月),《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等等。另外,不同地区在钱粮分配时的讨价还价,农民尤其是地主、富农抵制缴纳钱粮的现象,同样不是个例。在钱粮征收过程中,中共政权恰恰就是要解决这些难题的。但如何解决的历史细节,恰恰为传统革命史学所遮蔽了。
传统革命史学之所以遮蔽这些现象,恐怕主要是因为它不利于革命政策所产生的正面效应的解释。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回避。相反,恰恰是这些现象,才让我们真正理解中共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和中共革命的伟大光辉。如果不显示解决这一难题的复杂性,革命之不易又从何说起?
二、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
传统革命史观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革命史书写中很少出现基层社会的运行和普通民众的身影。我们一直宣传,中国革命是一场中共领导的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传统革命史著述中的一幕幕则是由革命志士、领袖人物、上层政权和革命策略构成的,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似乎无足轻重。
当然,这并非革命史才有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史学都存在的现象。在传统史观之下,绝大多数历史著述都是帝王将相史、英雄豪杰史、知识精英史,反映的都是有关民族和国家的宏大叙事与必然趋势,而很少展现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角色与作用,“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序”第8—9、13—14页;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14—15页。。不过,近年来,其他历史研究领域已经比较关注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而中共革命史还相差甚远。即便谈到普通民众,中共革命史也主要是从整体或集体而言的。问题是,整体或集体能够代表个体的命运吗?“集体生活是生活在组成这个集体的一些个人的行为中。我们想象不出不靠某些个人的行为而有所作为的集体。所以要认识整个的集体,就得从个人行为的分析着手”*〔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夏道平译:《人的行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43页。。因此,未来的新革命史研究尤其需要从人性的视角出发,反映人的情感和需求。
要想改变这一忽视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特别强调挖掘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资源,以突出其主体性和能动性。进一步说,不能将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视为完全被动的角色,而是有意识地站在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立场上,从人性视角、从人的情感和需求出发,来考察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这一视角与前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方法有密切关系,但又有所超越。近年来,无论是新政治史还是新社会史、新文化史,都强调从宏观历史转向地方性的微观历史,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强调从边缘、弱势、下层的立场出发,重新思考多元发展的历史过程。以上新史学的方法与新革命史所倡导的理念是完全契合的,颇值得革命史学者关注、学习和借鉴。当然,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并非与宏大叙事存在着二元对立的冲突。恰恰相反,通过发掘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完全可以深化对革命史之宏大问题的认识。
兹以1946年至1949年国共决战时期的农民参军为例,来表明研究理念转变的重要性。在中共革命史中,农民参军与上述钱粮征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传统革命史观之下,无论是官方史书还是一些学者的论著,都将农民参军与土地改革之间视为存在着必然的内在关系。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经过土改运动,到1948年秋,在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以后,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92、99、170、240—242页。至于各省市县的地方党史著作,几乎也是千篇一律,如出一辙。如果将这一观点与战争年代中共政权的表述相对照,就可以发现,二者是极其相似的。比如,1947年9月,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只有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才能战胜蒋介石。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群众自动参战,人力、财力、物力是无穷的。*《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4—395页。与上述钱粮征收一样,如果将之置于战争语境,作为动员农民的宣传手段是可以理解的,但进入历史学之门,挖掘历史过程、寻求历史真相便永远应当是第一位的。
事实到底如何呢?如果土地改革与农民参军之间真的存在如此紧密的必然联系,那么共产党征兵或农民参军应该是一个易如反掌的问题。因为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的农民的数量毕竟比征兵数量多得多。如在冀鲁豫边区,到1949年8月,除了少数新区之外,约有70%的村庄和近1000万农民得到了土地。而此前该边区一共发起过五次大参军运动,结果有14万青壮年农民参军。*王传忠主编:《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86、735页。按照传统革命史观的逻辑,14万与1000万相比,应该是一个微不足道且很容易完成的数字。
然而,发动农民参军谈何容易,否则,共产党屡屡颁布动员农民参军的指示,批评地方征兵不力,就不可理解了。其实,如果从农民个体和人性视角来看,则不难发现参军动机绝非铁板一块。有的农民的确是因为土地改革的“报恩”和“保卫胜利果实”而自愿参军的,这点与历史上其他政权包括国民党政权不同,不过,也经过了中共的“感恩”和“保卫果实”的说“理”工作。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情况的比例是非常之低的。相反,不少农民不仅不领土改的情,反而以逃跑、装病、自残等方式,对参军进行了躲避和抵制。即便有一些农民,虽然也是自愿参军,但主要是为了获得各种私利的行为。更有一部分农民是被迫参军的,连朱德都承认有一半战士是被迫来的。所以,笔者认为“理”“利”“力”的合力,才是促使农民参军的真相。*李金铮:《农民参军与中共土地改革关系考(1946—1949)》,“文明与革命:跨学科视野下的土地改革运动”国际学术研讨会(重庆大学高等研究院主办),2015年8月。
但在传统革命史观之下,为了凸显革命政策的正面效果,更多地关注了农民获得土地后自愿参军的光辉一面,而对自利参军和被迫参军的一面忽略了。其实,如果改换一种理解方式,即不管农民是出于何种目的参加革命的,都是中共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就完全没有遮掩的必要了。何况,即便是自利参军和被迫参军的农民,经过中共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改造,也逐渐变成了坚强的革命战士,这恰恰是共产党远比历史上其他政权和政党厉害的地方,也是共产党革命不易之体现。以往传统革命史强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无道理,但除此以外,也应该关注共产党与自己所依靠的同盟军的“斗争”。
三、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
传统革命史著述的第三个问题,是对共产党革命之前的乡村史缺乏深入了解和研究,从而影响了对中共革命史的合理解释。中共革命根据地是在乡村建立、发展和壮大的,革命的核心在乡村,革命队伍无论是革命领袖和革命干部还是普通士兵和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也来自乡村。就此而言,中共革命史无不带有浓厚的“乡土中国”特色,因此可以被视为乡村史的一部分。更具体一点说,共产党革命之前的传统乡村,无论是生态环境、基层政权还是农民意识、民间习俗,无论家族、家庭、阶级阶层、土地分配关系、人地比例关系还是农业经营方式、手工业生产、民间金融、市场贸易、赋税征收等,都极大地制约着中共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影响着中共革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但不能不说,以往传统革命史观指导之下的论著,几乎都限于单一的革命史、党史领域,就革命史论革命史或就党史论党史,比较缺少纵向的时间维度或者说历史的惯性、连续性,结果,中共革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共革命的理论、实践以及出现的某些问题,中共革命与基层社会和农民群众的关系,农民参加革命的心态和行为,以及革命领袖、革命干部的思想和行为等,似乎都变得难以理解。
没有传统社会,没有传统乡村,何来中共革命?笔者认为,应将中共革命史纳入大乡村史的视野来考察。其实,乡村史并无所谓大小之分,只是由于以往中共革命史学界缺乏乡村史视角,笔者才提出大乡村史的说法。大乡村史的基本涵义,就是在乡村地域所发生的一切都应纳入乡村史范畴。当然,将革命史纳入乡村史之中,并不意味着以乡村史替代革命史,而是它有助于我们从乡村史的视角来考察中共革命史上的诸多问题。
反过来讲,如果将乡村史纳入中共革命史的范畴,同样可以增强我们对乡村史的理解。上述传统乡村史的许多问题,既制约和影响着中共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也是中共革命进程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对革命进程中的这些问题有深入了解,也势必会加深对中国乡村史的认识,乡村史上的一些问题由此变得容易理解。也就是说,革命史与乡村史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乡村史学界也存在着与革命史一样的问题,绝大多数乡村史学者都不曾深入了解和研究革命史,乡村史与革命史似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老死不相往来,结果自然不利于乡村史的解释。
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民间借贷问题为例,大概可以说明革命史与乡村史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参见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4—114页;《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6—194页;《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在以往的革命史表述之下,中共根据地、解放区对传统民间借贷进行了改造,革命的减息和废债政策一以贯之、所向披靡,解决了长期困扰在农民头上的高利贷剥削。正因为此,减息废债政策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不过,当我们爬梳具体的历史资料就会发现,如果真如传统著述所描述的情形,就会有两个现象难以理解。第一,农民对共产党的民间借贷政策也表示过不理解乃至不满。的确,农民曾因为高利贷剥削的减轻乃至废除而欢呼雀跃,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以后再进行借贷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出借钱粮有被视为剥削并被划为地主、富农或高利贷者的危险,有余钱余粮者不再敢借给其他人。结果,农民遇到青黄不接或其他变故需要借贷调剂时,却没有了以往的来源渠道。于是,他们由减轻借贷剥削的愉悦,变为借不到债的痛苦,甚至对中共政权产生了埋怨。在山东根据地,借贷困难成为“今天广大农民群众最感痛苦的事,也是广大农民群众最切望的事”*《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大众日报》1942年5月25日。。在晋绥边区,临县上西坡村的农民说:“没有放债的了”,“死水一池,可是受治了”*群一:《必须活跃农村借贷关系》,《晋绥日报》1946年9月28日。。在晋冀鲁豫边区,黎城县南堡农会主席说:“以前困难还能借当(指战前),现在出大利也闹不来,真把人憋死了。”*《黎城二区村干部集会讨论开展信用借贷》,《新华日报》(太行版)1947年4月25日。可见,减息废债政策的推行,并非像以往所说的那般简单和顺利。第二,中共领袖、中共政权对民间借贷政策进行了调整,自1942年后开始实行借贷利率自由议定的办法,而不是像传统革命史论著中所描述的那样,完全是减息废债政策。具体地说,就是1942年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以及同年2月颁布的《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对旧债、新债采取分别对待的策略,旧债仍旧实行减息政策,新债则借贷双方自由议定利率。抗战胜利后,无论是1946年颁布的“五四指示”,还是1947年颁布的土地法大纲,对新债利率仍继续沿用自由议定的政策。当然,在革命氛围愈益激烈之下,新债利率能否做到完全自由,仍是中共政权面临的一道难题。
但以往的很多革命史论著为了表明革命策略的正面价值,忽略了以上两个矛盾现象。其实,这种遮掩同样是没有必要的。只要对传统乡村史有所了解和研究就知道,在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中,借贷调剂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民间借贷乃至高利贷的调剂,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有时是很难进行的,也不一定变得更好。农民对中共减息废债之后借债停滞的埋怨,恰恰就是传统乡村社会农民的正常反应。中共政权对借贷政策的调整,也不过是反映了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农民的客观需求罢了,革命与传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反过来说,从中共对民间借贷政策的调整,是否也会对传统乡村社会尤其是民间借贷关系的研究有所启发呢?回答是肯定的。由此进一步证明,农家经济、农民生活与民间借贷包括高利贷具有密切的内在关系。与此同时,共产党对传统借贷的革命,也反映了传统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是不容否认的。否则,革命就完全变成了无源之水。
四、从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共革命
传统革命史观的第四个问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革命缺乏了解和研究。除了少数著述关注中共革命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对于中共革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外革命的比较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在中共革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系的研究中,沈志华的《若即若离:战后中朝两党关系的初步形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是除苏联之外,难得一见的成果。。这一状况既影响了对中共革命的解释,也很难凸显中共革命应有的特色。
其实,在中共革命的年代,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中国发生了革命。20世纪是一个风云激荡的革命的世纪,“震撼全球的绝大多数革命运动发生于因国际因素而起变化的落后的农民社会”*〔美〕拉尔夫·撒克斯顿著,冯崇义译:《1931—1945年冀鲁豫边区的民众起义和共产党政权》,《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600页。。在这个世纪的前半叶,中国正处于革命历史的舞台之上,属于全球落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又以中共领导广大民众取得全国政权的历史性事件最为灿烂夺目。正因为此,不能将中共革命仅仅理解为在中国发生的一场革命,还要将其作为世界民族革命的一员。中共革命既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其意义不能完全限于中国历史,而是世界民族革命的一个典范。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和塞尔登以中共抗日战争为例指出:“这段历史,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是重要的,对一切试图了解以‘中国革命’而闻名的这一重要运动的人,对一切试图理解出人意料地发生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非工业化农业社会的这场本世纪震撼世界的革命的人,都是极其重要的。”*〔美〕弗里德曼、塞尔登著:《抗日战争最广阔的基础——华北根据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日的成功经验》,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87页。不过,以往传统革命史学者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更多只就中共革命谈中共革命,难以看到中共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革命的联系和区别。
要想改变这种单一的论域,可以借鉴近些年来声势勃勃的全球史视野。全球史观的核心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处于联系、交往和互动的状态之中*刘新成:《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全球史评论》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8页。。与前述国家和社会互动关系的内部视角不同,全球史视野侧重于外部关系。立足于这一视野,可以尝试从两个角度对中共革命进行考察。
第一,中共革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系。这些国家既包括与中共革命具有密切关系的苏联,也包括日本、美国、欧洲以及朝鲜、越南、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既包括支持过中共革命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反对中共革命的国家和地区。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共革命产生了哪些影响,反过来中共革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尤其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革命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构成了世界性的革命?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将中共革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革命进行比较,以凸显其特点。比如关于革命的背景与革命的结果之间的关系,中共革命就有自己的特性。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劳苦大众,都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也有共产党组织,这点与中共革命几乎相同,但革命获得成功的则很少。在几乎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中共革命却获得了胜利,表明其确有特别之处。*〔美〕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535—536页。又如战争与革命的关系,也别有意味。在战争期间,一般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十分便于从战时民族主义中获益,二战中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等都是如此。但在中国则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形。抗战爆发后,在日本侵略造成的“战时无政府状态”中,得益者不是处于统治地位、受国际承认的国民党,而是处于敌后游击区的共产党。也就是说,从外国侵略和被侵略国家民族主义兴起这个角度,无法解释抗战时期中共革命的发展。共产党之所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主要不是日本侵略导致的农民民族主义的加强,而是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的社会经济政策。*〔美〕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536页;〔美〕马克·塞尔登著,冯崇义译:《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610—611页。再如革命的武装组织,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武装组织所取得的经验,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越南、阿尔及利亚、古巴、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安哥拉、柬埔寨、萨尔瓦多、秘鲁等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美〕弗里德曼、塞尔登著:《抗日战争最广阔的基础——华北根据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日的成功经验》,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90页。。诸此种种情况都表明,全球史视野能够更加彰显中共革命的独特性和世界价值。
当然,从这一视角进行研究,所要求的知识结构较高,研究难度是很大的。
五、开拓新的研究视点
传统革命史观的第五个问题,是论题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当然,这些方面的继续研究仍是重要的,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缺乏新的研究视点,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揭示中共革命的丰富面相。
新的视点包括以下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之诸方面:话语、符号、象征、形象、想象、认同、身份、记忆、心态、时间、空间、仪式、生态、日常生活、惯习、节日、身体、服饰、影像、阅读等。这些视点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政治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的启发。其中,有的可能是后来的名词、概念,但作为现象,早就存在于革命进程之中,只是为以往传统革命史论著所忽视罢了,甚至可以说不曾有这个意识,因而成为“沉睡”中的问题。相比之下,其他历史领域对此已经有了较多关注。可以相信,考索以上每一个视点或者每一个“碎片”,都可以增加中共革命史的分析角度,进而丰富相关内容,深化历史认识。基于此,笔者尝试提出如下问题。
在话语、概念方面,如“中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人民”“大众”“自由”“民主”“平等”“富强”“革命”“解放”“共和”“道德”“封建”“阶级”“五四”“敌人”“帝国主义”“半殖民地”“汉奸”等,在中共革命进程中是如何建构和演变的?话语、概念的演变与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关系如何?话语实践对中共革命产生了什么影响?*显然,其中一些话语和概念恰恰成为传统革命史观和宏大结论的理论源泉。
在想象、形象方面,共产党以及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各种力量,如国民党、日军、伪政权以及美国、苏联等强国之间是如何相互认识、形塑乃至想象的?共产党的领袖形象在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力量中是怎样形成和演变的?这些认识和想象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进而如何影响了领袖的行为?除了领袖人物,普通民众如农民、工人、女性以及地主的形象,又是如何变化的,相互之间的关系若何?
在历史记忆方面,共产党如何将中华民族历史、民族英雄史、农民战争史、近代以来的革命史,经过加工并运用于革命的宣传和动员之中?历史记忆与革命需求有无冲突,如有,冲突是如何解决的?民众的传统历史记忆和党派、政府的记忆宣传,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新的民族集体记忆对革命产生了哪些影响?*这里所谓历史记忆与今天对历史现象的“记忆史”研究不同,它主要指革命进程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
在新名词方面,“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扩红”“长征”“两面政权”“堡垒户”“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边币”“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等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它们所反映的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含义如何?
在心态方面,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等参加中共革命的初衷是什么?这些初衷与共产党的宣传是什么关系?面对日本侵略,普通民众以及共产党的革命干部有何反应?有一些人屈服于日寇和日伪政权当了汉奸、伪军,其初始动机又是什么?在革命政权实施的策略和措施中,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是如何反应的,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在生态方面,自然环境与革命政权、革命策略等是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就是自然生态环境对革命政权的策略、手段和行为有何制约?反过来,革命政权的策略、手段和行为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在日常生活方面,革命根据地之内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日常生活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关系如何?在这其中,士兵的日常生活尤其值得关注。士兵并不总是处于打仗状态,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包括婚姻、疾病、衣食住行、闲暇娱乐等。
在象征物方面,服饰、旗帜、徽章、图像、标语、纪念碑、遗址等是如何被革命政权作为一种力量运用的,对这一时期的革命认同和政权认同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象征物如何体现了革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关系,如何体现了政治与社会的新旧交替?
在身体方面,革命政权是如何渗透、发动、改造和利用民众的身体的?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的身体包括物质的身体和精神的身体,在革命年代的反应和行动是怎样的?身体的变化隐含了怎样的权力关系、社会观念和历史特性?这种变化对革命的影响如何?
在阅读方面,无论是革命政权的政策文件还是报纸杂志、文学作品等,是如何形成、生产和发行的?有哪些传播渠道和网络?哪些人群(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成分等)在阅读?尤其是普通民众是如何阅读、接受或抵制的?反过来,这些阅读对政权、作者、报刊以及革命进程又有哪些影响?
上述视点在革命史领域大都还是相对陌生的面孔。笔者除了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一文*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也没有太多涉猎,但相信这些所谓历史“碎片”必将是今后革命史研究中非常令人兴奋和期待的视阈。
以上五个方面,只是针对传统革命史观之弊而提出的。它决不意味着完全了、结束了,我们应对之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所有能够进一步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皆可视之为新革命史。*随着新革命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在史料挖掘、问题意识等方面也会有所不同,此为应有之义,恕不赘述。这些变化,除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和历史时间的特质之外,大多都与相关学科方法的应用有关。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擦亮发现问题的眼睛,增添分析问题的翅膀。历史学本身难以“生产”理论。综观当今史学,除了一般的史实考证以外,凡属专深的研究仅凭自己的资源,很难解决所有问题,或者说几无不依赖相关学科的支撑。这是我们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的事情。当然,我们仅仅是将它们作为“雇工”而使用,而不是任其变为“东家”控制我们。即便吸纳了外来智慧,仍应强调历史学包括革命史领域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应有发现革命史独特概念乃至理论的雄心,并使它们成为相关学科的知识资源。
有的学者也许带着怀疑的眼光问,新革命史不能停留于理念和方法,有无研究范例可以借鉴?笔者只能说,始生之物,其形必丑。新革命史研究远未蔚为大观,不过也有了比较成功的论著,如何高潮的《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的分析》(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台湾学者黄金麟的《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丸田孝志的《革命的仪礼——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民俗》(日本汲古书院,2013年)以及齐小林的《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等。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在笔者看来,这些著作都可以被视为符合“新革命史”理念和方法的作品。当然,其他学者也发表了一系列符合“新革命史”意味的学术论文①仅举战争年代中共革命史研究之例,如〔美〕周锡瑞著,冯崇义译:《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535—546页;刘昶:《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1945》,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2—137页;郭于华:《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杨念群主编:《新史学》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05—526页;张佩国:《山东“老区”土地改革与农民日常生活》,《二十一世纪》2003年4月号;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31—292页;韩晓莉:《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黄道炫:《洗脸——1946 年至1948 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Chang Liu,Peasants and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Rural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and the Yangze Delta,1850—1949, U K: Routledge , 2007,pp.1-258;李里峰:《“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黄正林:《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岳谦厚、黄欣:《“郭四颗事件”与“反封先锋”的构建》,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7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70页;孙江:《文本中的虚构——关于“黎城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之阅读》,《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王奇生:《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王奇生主编:《新史学》第7辑,中华书局,2013年,第61—114页;黄文治:《“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阶级革命——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22—1932)》,《开放时代》2013年第4期;杨豪:《象征的革命与革命的象征:以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中的仪式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李军全:《肖像政治:1937—1949年中共节庆中的领导人像》,《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等等。。笔者对土地改革农民心态、中共民间借贷政策以及农民何以参加革命、农民参军与土地改革关系的研究,也都是“新革命史”研究的具体实践②参见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农民参军与中共土地改革关系考(1946—1949)》,“文明与革命:跨学科视野下的土地改革运动”国际学术研讨会(重庆大学高等研究院主办),2015年8月。。当然,以上学者不能说都明显具有了新革命史的自觉意识。
最后,笔者还想强调的是,所谓“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不仅限于中共革命史,也可用之于近代以来的其他革命史直至当代中国史领域。这倒不是笔者有什么雄心,而是理念和方法本身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本文作者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 吴志军)
The Re-discussion on the Idea and Method of the “New Revolutionary History”
Li Jinzheng
Based on the article ofTransformationtothe“NewRevolutionaryHistory”, this paper further explains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the new revolutionary history. New revolutionary history is not a new field, and its research object is almost the same as the traditional revolutionary history. It just tries to use new ideas and methods to re-examine the CPC’s revolution history in order to reveal the difficulty, twist and complexity of the CPC’s revolution, and then put forward a set of concepts and theories which conform to the reality of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The methods mainly include five aspects, using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 emphasizing the subjectivity of grassroots society and ordinary people, combin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history and the rural history, studying the CPC’s revolution history from the global history perspective, and exploring the new points of view. Of cours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everything has included, and we should hold an open and tolerant attitude that all the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which can be able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evolution history research, can be regarded as the “new revolutionary history”.
K03;K061
A
1003-3815(2016)-11-00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