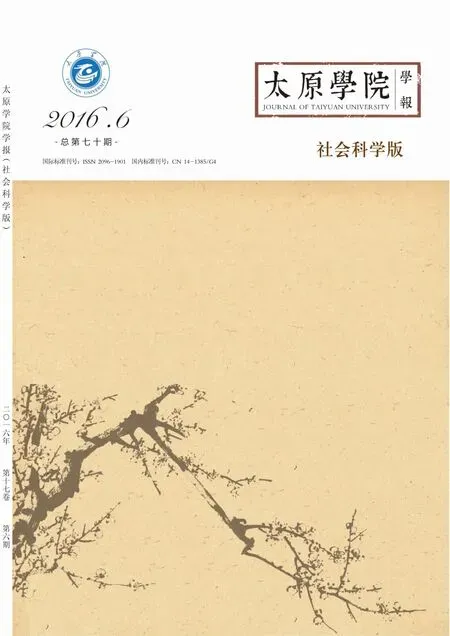《超人》的精神分析学细读
——兼谈《沉沦》与《狂人日记》
管 冠 生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超人》的精神分析学细读
——兼谈《沉沦》与《狂人日记》
管 冠 生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超人》文本与精神分析学说有着内在的联系。他的梦的隐意只有通过精神分析理论才能挖掘出来:母亲是何彬性爱的对象,但“父亲”压抑着这一欲望,何彬乃将性冲动升华为对圣洁母爱的皈依。冰心“爱的哲学”的重大缺陷便是忽略“父亲”形象,不能认识到爱是一种统治关系,人与人之间不只是互相牵连,而且存在各种斗争。对爱做出深刻省思的是狂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叙事始于对中国人事的精神分析。
超人;何彬;爱的哲学;父亲;《狂人日记》
学术界普遍认为,《超人》表现了冰心的“爱的哲学”,和鲁迅文本的深刻与多义比较起来,迄今不多的对《超人》文本的阐释仍然停留在字面理解的“爱的哲学”范围内。本文将参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在与鲁迅、郁达夫的比较视野中,重新理解《超人》及其“爱的哲学”。
一
《超人》何彬是一个冷酷的青年,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他说:
“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下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而且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程姥姥听着虽然不很明白,却也懂得一半,便笑道:“要这样,活在世上有什么意思?死了,灭了,岂不更好,何必穿衣吃饭?”他微笑道:“这样,岂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不如行云流水似的,随他去就完了。”
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我们受到来自三方面的痛苦的威胁:(1)来自我们的肉体;(2)来自外部世界;(3)来自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来自与他人关系方面的痛苦也许比任何其他痛苦更严重”,而避免它的“最便利的保护措施是自动离群索居”[1]76。看来,何彬就是这样一个主动离群索免受痛苦的人。
何彬的话该如何理解呢?程姥姥的话表达了两个意思:(1)活着没意思;(2)最好是死灭。她“懂得一半”,这一半就是第(1)个意思,是对何彬所说“世界是虚空的”之理解。何彬不同意程姥姥的第(2)个意思,人生最好的存在方式是“行云流水似的,随他去”,这该如何理解呢?何彬前面说“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下假面具,便各自散了”,这意味着在台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文明的、亲密的;下了台,方露出为己为我之真面目、自私自利之本能。唯有“台下”才表现出了心理之真实与真实之心理。所谓“行云流水似的,随他去”,即随着本能,自然地、真实地生活。
台上/台下之区分,类似于弗洛伊德表层心理学/深层心理学之区分。弗洛伊德把他提出的无意识学说称为深层心理学,透过人的精神生活的表层,去揭示人的全部精神生活的基础与动力。弗洛伊德以冰山为喻,人的全部精神生活好似坐落在大海里的冰山,浮出海面的仅是一小部分山体(意识领域),海洋下面的巨大山体才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更广阔的部分。这是弗洛伊德的第一个心灵模型——地形学模型,以意识的不同层次作为基础。何彬所言“人生是无意识的”是一句精神分析理论的真理。精神分析把一切心理的东西首先看作是无意识的,或者说“精神分析的第一个令人不快的命题是: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至于意识的心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2]8(越过翻译用语的不同,这里把“无意识”和“潜意识”视为同义的)。但与弗洛伊德不同,何彬及“爱的哲学”并未深入“台下”做继续的探究,而是止于台上/台下之对立,得出人生虚伪之观感而已(“爱的哲学”本无多少哲学气息与思想深度)。远离虚伪的途径,就目前来看,便是离群索居。
“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何彬因此思想意识而炼成超人。冰心的另一篇小说《烦闷》做了更深层的描述与解释。《烦闷》中的“他”抑郁烦躁,看透了社会人生,写了篇短文《青年人的危机》:
青年人一步一步的走进社会,他逐渐的看破“社会之谜”。使他平日对于社会的钦慕敬礼,渐渐的云消雾灭,渐渐的看不起人。
社会上的一切现象,原是只可远观的。青年人当初太看得起社会,自己想象的兴味,也太浓厚;到了如今,他只有悲观,只有冷笑。他心烦意乱,似乎要往自杀的道上走。
原来一切都只是这般如此,说破不值一钱。
他当初以为好的,以为百蹴不能至的,原来也只是如此。——这时他无有了敬礼的标准,无有了希望的目的;只剩他自己独往独来,孤寂凄凉的在这虚伪痛苦的世界中翻转。
他由看不起人,渐渐的没了他“爱”的本能,渐渐的和人类绝了来往;视一切友谊,若有若无,可有可无。
看来,何彬和“他”皆认为世界虚空、社会悲观,从而炼成了超人、“和人类绝了来往”,最根本的是他们隐埋了自己爱的本能。爱有多种表现形式,如父母之爱,性爱,朋友之爱,对祖国的爱,对人类的爱,等等。精神分析的看法是,“爱”这个词所指的东西的核心,就是以性结合为目的的性爱,那些爱的多种表现形式“是同样的本能冲动的表现:在两性之间的关系中,这些冲动迫切地趋向性的结合,但在其他场合中,它们离开了这一目标,或者避免实现这一目标,尽管它们总是保持着它们原初的本性,足以使得它们的身份成为可认识的”[3]89-90,而何彬们及“爱的哲学”选择的突破口或最终的依靠则是“母爱”。
二
何彬是如何想到母爱的?因黑夜里的呻吟:
这一夜他忽然醒了。听得对面楼下凄惨的呻吟着,这痛苦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在这沉寂的黑夜里只管颤动。他虽然毫不动心,却也搅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从窗纱外泻将进来,他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极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直到天明,才微微的合一合眼。
呻吟的声音,渐渐的轻了,月儿也渐渐的缺了。何彬还是朦朦胧胧的——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竭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
何彬听到“对面楼下凄惨的呻吟着……在这沉寂的黑夜里只管颤动”,无论如何让他不得安眠。他“忍受”了六晚上,第七天问起程姥姥,得知是十二岁的孩子禄儿摔伤了腿而发出的呻吟。可是,男女交合时不也会发出让黑夜颤动的呻吟吗?何彬因暗夜里的呻吟而想到母亲,有性的欲望吗?这种问题初看上去是不道德、无耻的,但何彬后来做梦梦到了母亲,“十几年来隐藏起来的爱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脸上;十几年来不见点滴的泪儿,也珍珠般散落了下来”,爱的神情为什么要隐藏十几年呢?“所有被忘掉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些痛苦的经历。就患者的人格标准而言,这些经历或者是可惊的,或者是痛苦的,或者是羞耻的”[4]35。于是某些刻意忘掉的东西在那个梦中重现了。
何彬先付钱为禄儿治好了腿。呻吟声住了,他恢复了常态,“至人无梦”地睡着,并冷冷地拒绝禄儿的感谢。当他要买绳子的时候,“他踌躇着四围看了一看,一个仆人都没有,便唤:‘禄儿,你替我买几根绳子来。’”看来,何彬是固执地拒绝禄儿进入他的意识之中,拒绝这个“深夜的病人”重现,拒绝深夜的呻吟,拒绝某种事物在场。然而,禄儿还是出现了。何彬做了一个梦:
微微的风,吹扬着他额前的短发,吹干了他头上的汗珠,也渐渐的将他扇进梦里去。
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几堆的黑影。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了。
慈爱的母亲,满天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不想了,——烦闷……闷……
黑影漫上屋顶去,什么都看不见了,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了。
风大了,那壁厢放起光明。繁星历乱的飞舞进来。星光中间,缓缓的走进一个白衣的妇女,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着额前。走近了,清香随将过来;渐渐的俯下身来看着,静穆不动的看着,——目光里充满了爱。
神经一时都麻木了!起来罢,不能,这是摇篮里,呀!母亲,——慈爱的母亲。
母亲呵!我要起来坐在你的怀里,你抱我起来坐在你的怀里。
母亲呵!我们只是互相牵连,永远不互相遗弃。
渐渐的向后退了,目光仍旧充满了爱。模糊了,星落如雨,横飞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母亲呵,别走,别走!……”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国产业链条的整合分析和升级管理使得产业结构和整体组织逐渐完善高效,在资源的优化和科学配置上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不同的产业之间可以通过彼此的沟通实现共同协作,产业生产的分配和格局越来越科学合理,集成建筑产品在经营管理上逐渐形成了开发设计、生产运输、运营管理的一体化发展。建筑产业的集成化生产发展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从而增加建筑企业的经济收益。
十几年来隐藏起来的爱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脸上;十几年来不见点滴的泪儿,也珍珠般散落了下来。
梦的形成可以有两种方式引起:“一方面,或者是通常受压抑的本能冲动(潜意识的欲望)在睡眠中达到了足以被自我感受的强度;另一方面,或者是醒时遗留的驱力——附有全部冲突着的冲动前意识思想链条——在睡眠中得到了来自潜意识因素的强化”。 禄儿的呻吟声曾搅得何彬一夜睡不着,使他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他虽极力摒绝这些念头,“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何彬这个梦的形成自然受了这种醒时遗留的驱力的影响,此外可有某种受压抑的本能冲动表现了出来?这种本能冲动是何彬做梦前后未能认识到的。“梦中的回忆比醒时的回忆要有多得多的内涵,梦所恢复的记忆是梦者已遗忘的,也是他醒时难以重现的”,这是弗洛伊德界定的梦的四个特征之一。其他三个特征包括:梦无限制地运用语言符号,其意义绝大多数不为梦者所知;梦中的回忆常常重现梦者幼年的印象,据此可以尝试去重新建构梦者的早期生活;梦使用的某些材料与生俱来,先于任何个人的经验,而受着祖先的影响[5]300。通过下面对何彬这个梦的解析,我们发现它非常符合上述特征。我不认为这是冰心在创作时有意为之,而是无意识的,作者并不完全清楚她所创造的何彬的这个梦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恰恰说明了文学评论的必要性与有用性。
首先,梦中的这个白衣妇女为什么要“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着额前”?何彬的梦为什么要以这两个动作来描述这个妇女呢?它从这个妇女的下半身开始。如果说“撩起裙子”,是因为裙子长,担心走路不便利,那么这个妇女为什么不双手撩着裙子,却又用左手按着额前?她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面目完全呈现出来?妇女走近,俯下身来,看着何彬——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动作表现了性欲的气氛,富含性的意味。这个妇女是何彬性爱的对象,何彬不想承认、不愿意看到她是自己的母亲!
“神经一时都麻木了”,这表示一种让人迷醉的快感。“起来罢”,本意是生殖器勃起,但“不能”,为什么?原来在梦中,何彬把自己倒退回了摇篮时代,把自己重又变回了一个无能的婴儿。这时候,这个白衣妇女,“呀!”,忽然变成了他的母亲,“慈爱的母亲”。不可以生殖器勃起来对待母亲!可是,男孩的第一个性欲对象就是他的母亲,他得学会把对母亲的爱欲压抑住、转移开去,否则便有导致乱伦的危险。但,对母亲的爱欲不会完全彻底地消失,满足恋母情结的最安全的方式或许就是自己躺在摇篮里,尽情接受母亲的触摸与爱抚。“我要起来坐在你的怀里”,但何彬自己已不能起来,他处于性无能状态,完全丧失了任何主动性,转而恳求母亲“你抱我起来坐在你的怀里”,“爱欲渴望着接触,因为它力求使自我和被爱的对象成为一体,消除它们之间所有的空间障碍”[6]256,母亲却离他而去了。在梦中,何彬以倒退回婴儿状态的方式获得母亲的关注,仅仅是关注(“目光里充满了爱”)还不够,他渴望与母亲拥抱抚摸,“永远不互相遗弃”,但存在一种力量使他的伎俩、他的欲望不能最终得逞或满足。
这就是超我,以良心、理想、羞耻感、罪恶感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强大的支配性力量,父亲是它的生物学起源。冰心“爱的哲学”的形象代言人,可以是母亲,可以是儿童,但从来不是父亲,自始至终没有出现父亲的身影。这并不意味着“父亲”的消失,而是他早已嵌入了何彬的内心之中,对何彬的精神生活施加着后者并未自觉到的影响,压抑着何彬对母亲的潜在欲望。即便何彬逃遁到摇篮里,他也未能摆脱“父亲”的监视。
这里出现的问题是:超我在群体与社会中体现为秩序、权威与道德,然而前面引述过,青年人一步步走进社会,逐渐看破“社会之谜”,“无有了敬礼的标准”,只有悲观冷笑,做起了超人,超我似乎瓦解了。其实没有,至少何彬没有。“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受;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但“书架上却堆满了书”,何彬上班回来便闷在屋里看书——书,文明教化的载体,就是一个伴随他左右的“父亲”。他从没接到别人的信,也从不给人写信,超我的力量并未显现。在这个梦之后,他给禄儿留下了一封信,信中承认他的“罪恶”,承认他是“冒罪丛过的”,从前认为世界是虚空,并拒绝爱与怜悯、拒绝宇宙和人生等,皆是错误的。超人并未能摆脱超我,但他选择了忽略,选择了洁身自好,选择了“随他去”,而忘记了斗争。
三
然而,在这封信中,何彬同时承认了“人生是无意识的”也是错误的。这恰恰表明了何彬的认识及“爱的哲学”的重大缺陷。
就何彬与禄儿的牵连来说,他给禄儿钱,原本不是为了爱,而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初衷,不想听到黑夜里的呻吟,使他睡不着觉。禄儿却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先生的恩德”,他的好意又使得何彬梦到了自己的母亲,颠覆了此前对人生与社会的看法。因此,禄儿“拯救”了他,成了他一生的债主,他背负着无法偿还的债务——“我是空无所有的,更没有东西配送给你”,只好用月亮作篮、星儿作花编制一个抽象的花篮送给禄儿,虽然后者并不理解这个礼物到底是什么。
在冰心“爱的哲学”里,母亲或者儿童往往以和平而强大的力量扭转了某个成人思想的转变。《烦闷》中的“他”最终也是从母爱和孩子中得到了安慰:“光影以内,只有母亲的温柔的爱,和孩子天真极乐的睡眠。他站住了,凝望道,‘人生只要他一辈子是如此!’这时他一天的愁烦,都驱出心头,却涌作爱感之泪,聚在眼底”。在另一篇小说《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中,青年凌瑜接触到社会上各种令人愤激苦恼的事情,悲观绝望,来到海边要自杀,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正在沙滩上玩耍(用沙堆起一座小城,插着国旗),凌瑜帮他们采花,他们告诉他:“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乐,请你自己去找罢!不要走那一条黑暗悲惨的道路”,在凌瑜听来如云端天乐,两个孩子如同天使。凌瑜跪在沙滩上,泪流满面,接受了这一神启。无疑,何彬凌瑜们的转变方式是和平的、纯真的,转变后的状态是积极、美好的,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一个本质事实:爱是一种统治,一种权力关系,它演变为一场自我对自我的斗争。这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虽互相牵连,但这种关系实质上是不平等的。面对同一个所爱的女人,父亲和儿子的地位与力量是不平等的,儿子要屈服,要同父亲认同;何彬与程姥姥、禄儿相比,有着更多的金钱和更好的社会地位,因而表现出了更大的主动性。并且,在“爱的哲学”里,母亲或孩子就仿佛是神,对成年人施加着魔术般的支配力量。如果说超我的本来面目是父亲,那么在“爱的哲学”里它被置换成了温柔的母亲或天真的孩子,但都行使着同样的功能。
在冰心“爱的哲学”中,母爱与童年是不再被质疑与分析的所在,它们是人生最后的希望与依赖。然而,不能透视、不敢正视“爱的哲学”所内藏着的真相,我们就不可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真正合理而美好的关系。何彬们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互相牵连,这是客观的事实;如果就此止步,那么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联就是它的理想和典范。但其中被压抑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揭示、释放出来,以母爱的神圣与儿童的天真取消了继续的审思,就等于取消了向前发展进步的可能性。弗洛伊德“实在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总以为兄弟姐妹永远是相亲相爱的,因为,每个人事实上都曾有过对其兄姐的敌意,而且我们常能证明出这种疏远实来自童年期的心理,并且有些还持续迄今”[7]156;黑格尔则认为孩子的天真是无价值的和短命的,“这种无知的天真也许会可笑地被认作理想并渴望回到这种状态去”[8]81。抽象的爱让我们无知,理性的审思则让我们清醒。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首先重要的事实不是互相牵连,而是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因此,在罗尔斯的正义论框架中,在基本自由面前,人与人皆平等的分配与享有,是正义的两个原则中的第一个原则,优先的原则。理性地、全面地解决不平等问题(这需要持续不懈的斗争)而不是依靠某种类型的爱才是社会谋求转变与发展进步的良性标志。
四
何彬的超人境界在五四文学世界中并非个例。郁达夫的“零余者”(以《沉沦》为例)和鲁迅的“独异个人”(以《狂人日记》为例)可视为超人的异姓兄弟。说他们是兄弟,因为他们面孔相似;说他们异姓,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精神特质。
《沉沦》开始这样写道: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
同何彬相似,“零余者”亦与世人不容,过着独来独往的生活。但,超人绝口不谈性,零余者则窥浴、听淫、手淫、找侍女,备尝性的苦闷,备受自卑感与神经症的折磨。像超人把性升华为神圣的母爱一样,零余者也有自己的母亲——祖国母亲,他说“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罢”,蹈海自杀时,零余者希望祖国快富起来,强起来。超人领悟到人与人之间是互相牵连的,零余者则在异国他乡的失意中痛感到个体命运与祖国命运是紧密联系的。前者的爱是母性的、和平的、可以推而广之的,后者的爱则明显带着对第三者(“无情的岛国”)的仇恨与报复。因此,超人获得新生,而零余者因无能而自杀。无论如何,超人和零余者皆(不得不)止步于某种伦理之爱,对爱做出深刻省思的是狂人。
在三兄弟当中,狂人年纪最长(日记第一节明确写着“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零余者二十一岁,超人是个“冷心肠的青年”),感受更为深刻:不仅仅是自己与周围的人不相容,那些人(包括孩子)还要害了自己。超人晚上睡不着,想“慈爱的母亲,满天的繁星,院子里的花”,零余者躺在被窝里遭受“始祖传来的苦闷”,狂人则在进行深入的研究: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他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历史叙述如同弗洛伊德所揭示的梦的结构:历史叙述的显意是仁义道德,隐意则是“人吃人”,即人阉割人、人统治人。男上女下的交合,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则是“人吃人”的典型与原型。历来的解读与评论皆重视狂人的这个发现,但就狂人来说,让他震惊的并不是这个人吃人的发现,而是在爱的名义下,大哥竟然在吃他:
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狂人一口气用了四个感叹句,虽然它们表达的意思大同小异,但它们的并置让人直观地感受到这个发现对狂人的情感与思想的冲击力度!先前的发现仿佛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哥哥吃兄弟的发现则让狂人彻底明白所谓的爱实质上是一种暴力统治。狂人在日记中并未提及生物学父亲,“大哥正管着家务”,这意味着狂人的生物学父亲已经死了,但大哥行使着“父亲”超我的功能。狂人跟这个“父亲”做斗争,跟超我暴力做斗争,不想退回到母爱当中(因为这样虽然安全,但付出的代价太大——阉割自己的主体性与主动性),而是要脱胎换骨做“真的人”:“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尽管狂人的斗争失败了,“救救孩子”的呼声是多么无力,但与超人退回到母爱的怀抱(即退回到过去)、零余者空洞地说祖国快富强起来(即寄希望于将来)不同,狂人立足于历史反思与爱的批判,他是三兄弟中活得最痛苦的。
上世纪四十年代,有人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五四以来的种种解放运动,根本意义就在要灭杀数千年来的超我的权威。反而观之,也就是要给阿物以空前的宣泄机会”,“人家花费了数百年的工夫,解放阿物,解放个性,现在正好开始建设新超我,加紧群体的组织。我们却要同一时间内,两者并行,一面赶造强有力的个人,一面赶造强有力的社会与国家。这两个目标,最容易冲突不过,但平行推进,并不是不可能的”[9]108-9。受此观点启发,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就始于对中国人事的精神分析。超人的梦回母爱,零余者的性变态与祖国之爱,狂人的历史反思与爱的批判,这三种不同工作其实是互补的,它们合力共同致力于重塑自然、理性、美好、强大的中国人与中国形象!
[1]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C]//弗洛伊德.论文明.徐洋,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C]//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熊哲宏,匡春英,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4]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M].张霁明,卓如飞,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5]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C]//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葛鲁佳,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6]弗洛伊德.抑制症状与焦虑[C]//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杨韶刚,高申春,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7]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赖其万,符传孝,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8]黑格尔.精神哲学[M].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望沧.阿物超我与中国文化[C]//吴立昌.精神分析狂潮:弗洛伊德在中国.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姚晓黎]
Interpret “Superman” with Psychoanalytic Theory——Understanding of “Depravity” and “A Madman’s Diary”
GUAN Guan-s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Taishan University,Taian 271000,China)
Bingxin’ s novel Superman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nly in this theory can we get the latent dream-thought of He Bin’s dream. Mother is He Bin’s sexual object, but “Father” represses this desire. The grave fault in Bing Xian’s philosophy of love is to ignore the image of “Father”, she can not realize that the so-called love is a dominating relationship containing all kinds of struggles. It is A Madman’s Diary that did some love-reflection. In some sens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egan with analyzing Chinese human affairs by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Superman;He Bin;philosophy of love;father; A Madman’s Diary
2016-08-29
管冠生(1977-),男,山东诸城人,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文学考古与文学游戏。
2096-1901(2016)06-0043-05
I206.6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