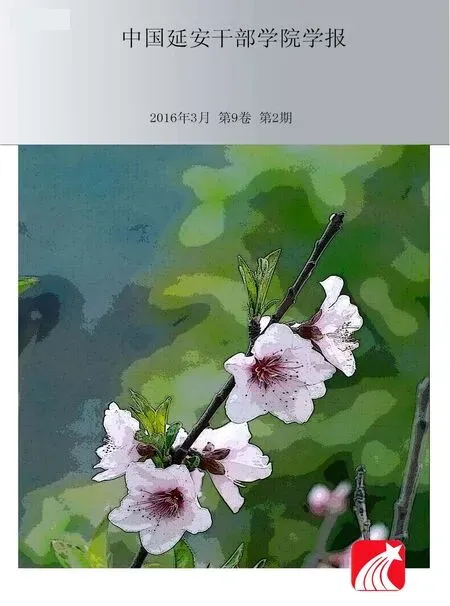革命与象征:中国共产党旗帜符号的历史演变
胡国胜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革命与象征:中国共产党旗帜符号的历史演变
胡国胜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摘要】中国共产党旗帜符号发展形成于民主革命时期,经历了建党初期的萌芽与曲折、土地革命时期的恢复与彰显、抗日战争时期的消解与重构、解放战争时期的形成与引领,最终形成了反映中国革命道路、引领中国发展的象征符号,在引领革命道路、教育革命群众、彰显革命象征、传播革命理念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诠释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革命; 象征; 中国共产党; 旗帜符号
旗帜,泛指悬挂在杆上的布,旗面通常绘有各种图案,具有象征性和标志性,用于宣传、装饰、传递讯息和区分功能。国家、政党、地区、军队、社会团体、政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等通常都有自己的旗帜。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众进行革命过程中所使用的旗帜是为了引领反帝反封建这一民主革命任务的前提下形成发展起来的象征性革命符号,处处体现其革命性与象征性相统一的历史特征。因而,在引领革命道路、教育革命群众、区分革命组织、彰显革命象征、传播革命理念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符号,经历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从简单模仿到质朴创制,从简单制作到统一制式,最终根据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发展要求,形成了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旗帜符号,诠释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一、建党初期中共旗帜符号的萌芽与曲折
中共“一大”并没有规定统一标准的党旗党徽。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而,共产国际的旗帜符号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效仿的对象,“镰刀锤子”自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旗帜符号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中共也并未对自己党旗的使用和制作作出规定。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深入,中共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时,革命实践必然需要革命旗帜的引领。1922年10月,开滦五矿工人在中共北京区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中共唐山地委的领导下,在罗章龙、王尽美、邓培组成的3人小组统一组织下,举行了同盟大罢工,这次罢工历时25天,共有3万多矿工参加,其规模仅次于当时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192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一次罢工斗争。这次罢工所用的旗帜用煤矿工人所用的劳动工具“轮镐”和“铁锤”的实物形态组合而成,简单质朴,直接体现出煤矿工人的革命运动。同样,早期的农民革命运动也是如此。1923年春,在彭湃的亲自发动组织下,高潭区农民协会在高潭水口乡蔚起山房正式成立。高潭区农民协会和各乡农会都备有会旗,农会每逢召开会议或有集体行动,必以会旗为标识。该旗制作于1923年,棉布质地。因旗中间饰有“犁”,故又称“犁头”旗。该旗长109.5厘米、宽76厘米,鲜红色。中间的“犁”用黄色棉布裁制好,再缝在红旗上,“犁”高39厘米、宽82厘米。旗的一边缝有白色布质套筒,用于套穿旗杆。这体现中共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
此后,在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呈现出了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潮,人们再次受到革命的洗礼。但在国共合作大背景下,中共旗帜符号则没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征,多了国民党的符号特征。1924年2月,《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中提出:“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1]225因而,使得中共旗帜符号形式上趋同于国民党的旗帜符号,这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中共旗帜符号的特性。如1925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农民协会和自卫军第一次打出了“犁头太阳旗”,即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加一“犁头”。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2]4此时,革命成为社会发展的潮流,成为人们活动的目标,人们热衷于此。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2]19这里所用的旗帜是指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所使用的旗帜符号,即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1927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信》中就提到:“不仅湖南一省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发生坚强的信仰,全国各地的工农,定要遥瞻国民革命的旗帜,认识国民党的党徽,为他们自由之标志。他们必定自己起来向国民政府之敌作战!”[3]171这都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中共旗帜的符号特征。
这种景象并未持续多久,随着国共两党的决裂,中共则开始探索考虑使用自己的旗帜符号。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正式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由于为了团结广大国民党左派人士,中共仍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打着国民党的旗帜进行起义。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提道:“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应该“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小资产阶级也必定在红旗领导之下。[4]211-212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并对此作了回答。1927年8月21日,中央常委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关于暴动之方式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因为“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形成了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暴动,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3]335-336
从中央的八月决议案中可以看出,中央仍然坚持八七会议的决议案,并未放弃使用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但此事在党内则引起了广泛争议。贺龙在与李维汉谈道,“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李维汉在回忆中也提道,应抛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5]176。
1927年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指出:“最近几月的经验(包括南昌军队中的暴动与两湖广东革命的农民暴动的爆发)指示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3]369这个决议案正式取消了使用左派国民党的旗帜符号,提出了使用苏维埃旗帜符号的决议。
到了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指出:“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6]261至此,经历了曲折的革命探索,中共正式举起了苏维埃大旗。特别是广州起义,举起了苏维埃旗帜。虽然其存在的时间极其短暂,但其意义却很深远,“暴动一开始之后,革命的兵士就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等的徽章完全抛在街上,换上红领带。同时劳动民众将全城的青天白日旗——白色恐怖的象征,一概撕掉,都竖起镰刀斧头红色旗,张贴工农革命的标语。”[7]20
1928年1月22日,《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中指出:“广州暴动失败,表面上革命又受一挫折,但是实际上苏维埃的红旗,却极广泛的散布到中国——从广州到满洲,从上海到四川——广大的工农贫民兵士之中。”[7]86“苏维埃的旗帜,他是联合全国革命潮流的象征,确定革命深入的性质。”[7]87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因在起义失败后继续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而受到责难;毛泽东在发动秋收起义时只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广州起义要求建立城市苏维埃或称公社——所有这些举动都标志着越来越强调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领导。[8]24
建党初期及国民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于刚成立,又面对具体不同的革命实践,革命领导组织也未统一,因而,在革命实践中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旗帜符号,且简单质朴,反映早期中共革命实践的探索历程。即使在武装反抗国民党残酷镇压、打响中共武装斗争开始的南昌起义时,还举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这种举“旗”不定的表现,直到此后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才结束,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才真正使用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旗帜符号。
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旗帜符号的恢复与彰显
旗帜符号的标志象征,“可以成为树立革命理想、保持团结、忠诚、区别于他人、唤起革命意识、形成革命观念的极其有效的手段”[9]60。“镰刀锤子”组合中的镰刀代表农民、锤子代表工人,代表着革命的阶级基础,整个组合象征工农联盟。而工农联盟的意义就是为了完成社会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镰刀锤子”来到中国以后,由于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性,党旗由各级党组织模仿联共(布)党旗的式样自己制作,具体规格式样不尽相同,从而使得“镰刀锤子”经历了复杂演变过程。同时,军旗和苏维埃政府的旗帜符号也借用“镰刀锤子”的符号象征来表达中共革命理念和主张。
中共旗帜符号源于革命实践,因而,最多使用的应是革命军队旗帜。军旗是军队荣誉、勇敢和统一指挥的象征。1927年9月初,为筹备秋收起义,刚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奉命研制了起义的旗帜。旗幅为红色,象征革命;中央为白色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角星内嵌交叉镰刀斧头,象征工农联盟;旗杆一侧的旗幅为白布条竖写“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9月11日,中国工农革命军高举这面旗子,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镰刀斧头”旗,是中国共产党正式亮出的第一面红军军旗。在起义军由江西向湖南平江、浏阳挺进之间,有感于秋收起义翻天覆地的意义,毛泽东提笔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词中有句“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的表述,毛泽东所提的“镰刀斧头”旗指的就是这面旗子。何长工在回忆秋收起义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时是这样说的:“由我负责设计并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鲜艳的红旗中间一枚大五角星,星中是镰刀和斧头的图案,紧靠旗杆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空白,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十分威武、漂亮。”[10]81在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旗帜上有镰刀斧头的党徽以及番号,表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区别于苏联红军军旗的地方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旗帜以斧头代表工人,没用锤子,之所以这样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当时工业化现状和工人阶级队伍现状远不如苏联的认识相关。中国的实际是,代表传统手工业者——木匠形象的‘斧头’,比代表产业工人——钳工、钣金工、锻工等形象的‘锤头’,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同时,‘斧头’相比‘锤头’更具有力度,体现出对中国革命艰辛的认识”[11]11。其红色旗帜也成为红军称谓的来源,颜色对于直观宣传具有重要意义,它的任务是“补充内容并从感情上对内容加以充实。若所选择的颜色与内容不匹配,便会产生不协调,不利于理解”[12]140。这样的旗帜让人一眼就看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队。此外,“镰刀斧头”表述上也是象征性与革命性的结合,如“‘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这副对联,生动概括了大巴山下翻天覆地、如火如荼的斗争情景。”[13]275这里的镰刀和斧头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割断旧乾坤,劈开新世界则表达革命的成功。
1927年11月的黄麻起义,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由于起义的主力军是农民,因而,其使用的旗帜符号是由镰刀、斧头和农民以牛拉犁耕地图组成。突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农联盟的党,更是代表着广大农民利益的党。从这个朴实形象的旗帜符号我们可以看出具体革命环境和实践决定了旗帜的具体符号形式。对此,为了加强对军旗符号使用的统一,1930年4月,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的通知》,规定了红军军旗的规格、斧头样式和刃锋的方向。白色五角星内为黑色交叉的镰刀铁锤,与旗杆相连的右侧镶有白底黑字的布条。旗面上方自左至右有时还缀上“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字样。
1931年3月,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又颁布了《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红军旗帜印信式样》,使得红军军旗符号式样发生了变化,即镰刀斧头改为金黄色镰刀铁锤,五角星由白色改为金黄色,单独置于旗内左上角,以旗颜色区分部队属性等。同时还规定了授旗的范围和各级军旗规格。如中央军委为5.6×4,集团军为5×3.6,军为4.4×3.2,团为3.8×2.8,营连为3.2×2.4(以上均为市尺)。这使得各级军旗都有了自己的标准,这也是红军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表现。此外,《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红军军旗印信式样》也为区分军旗与苏维埃政府、群众团体提供了参照标准,使得苏区内旗帜符号使用混乱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一苏大”后,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即席讲话,我们甚至连国歌、国旗、国徽都来不及制定出来。这没有什么关系,孩子都生出来了,还怕取不出名字?没有国歌就唱《国际歌》,没有国旗就暂时打红军的军旗嘛。从而,红军军旗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国旗。直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的颁布才告结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国旗作出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规定所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锤子与镰刀,架谷穗于地球下河两旁,地球之上及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写‘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呵!’”,“国旗为红色旗上加国徽”[14]132,这就形成和使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国旗符号。此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有陆军旗、海军旗、商业旗的列项,但无具体规定。
任何符号都有本身的内涵意义与延伸意义,一面国旗、一个V型字,或其他政治符号本身是一种符码,而这种符码的价值会因不同的使用情境、观众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发生变化。[15]22-23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战火之中,使得“国旗”的样式很不统一。从一些历史照片或当年的历史场景来看,各革命根据地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最多的就是1930年版军旗和1931年版军旗。“国旗”的图案,一种是在旗面正中置一个大五角星,星中有一镰刀斧头图案,类似于何长工设计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一种是把五角星置于旗面左上方,把镰刀斧头图案置于旗帜中央。这两种样式,在许多场合也是红军、地方武装等军事组织的军旗样式。根据“一苏大”会场的布置,我们可以看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使用的国旗是第二种国旗,即1931年版军旗。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属的各省政府的旗帜,多数在旗杆上署写了本级政府的名称,基本样式同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也有不同的,如福建省平和县苏维埃政府的旗帜在旗面的右下角标记有“C.C.P.”这一中国共产党英文字母的缩写符号。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对国旗军旗设计要求作出规定:“国徽: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之上为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则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地球形为白色底子,轮廓经纬线为蓝色,地球上的镰刀锤子为黑色,五角星为黄色。”“国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加国徽于其上。旗柄为白色。”这基本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中规定一样。而军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中为黄色的交叉镰刀与锤子,右角为黄色的五角星。旗柄为白色。”然则,由于“二苏大”正值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五次疯狂围剿之时,无暇贯彻执行“二苏大”通过的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后来因红军被迫战略转移而流产。从当时发行的报纸可以看出,红军主要还是使用着1931年版军旗作为主要旗帜使用。比如在长征途中,刘伯承司令员与彝族沽鸡族(又做沽基、果基、古鸡)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并赠送小叶丹一面用红色锦缎作旗面,右上方缀一颗五角星,中间是镰刀斧头标志的“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佳话。
整个土地革命时期,虽然中共旗帜符号不尽统一,但基本围绕“镰刀锤子”这一符号象征而展开,此时中共旗帜符号的苏俄特征较为明显,但从“镰刀锤子”到“镰刀斧头”的演变来看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革命道路的中国特色。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旗帜符号的消解与重构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指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16]158这是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的重大让步,中共不惜把自己“屈尊”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区,放弃了苏维埃的旗帜符号,同时还把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红军番号撤销,但中共并未放弃其符号内质。“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不能放弃工农主要成份与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而要继续保障之。”[16]160-1611937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中则提出:“新的形势更要求我党同志迅速的澈底的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以适合于目前的新环境。过去的武装斗争的方式,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方式,现在必须转变到和平民主的斗争方式。”“我们还要懂得如何在旧形式中灌输新内容,旧躯壳中注入新生命。这种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的研究学习与创造,今天成为展开党的全部工作的需要关键。”[16]203有意思的是,一边是要保证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性,一边正是按照国共两党合作要求对中共旗帜符号进行形式上的改变。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郑重提出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17]844-845这必然要对中共旗帜符号进行彻底的形式改变。虽然中共旗帜符号作出了巨大的形式变更,有的甚至使用了国民党的旗帜符号,如军旗军徽、边区政府旗帜等,但并未改变中共的本质。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进行了第二次合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而在旗帜符号使用上也做了较大调整,清一色使用了体现国民党符号象征的青天白日旗。据廖汉生回忆,抗战初期的军队改编时,广大官兵真要摘下红军帽戴上国民党的帽子时,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跟国民党军队作战。在我们的眼里,红星是革命的象征,那‘青天白日’的白帽花则是反动派的标志,我们与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却要同戴一顶帽子,总觉得有些别扭。”[18]193这充分反映了“红星”这个象征符号已深入到广大士兵心灵之中。
最为明显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红军改编时,广大红军战士是坚决支持的。“可是,要从红军战士头上取下那顶十年来一直给予大家以最大希望、最大鼓舞的红五星军帽的时候,思想感情总转不过弯来。因而,当第一次颁发国民党军队的灰军帽、灰军服时,大家都很激愤,把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狠狠摔到地下,声泪俱下地叫嚷起来:‘让我戴这玩艺儿,我不干,我不当白军。’”[19]84-85王震最终说服了大家,千言万语归结一句话:“为了团结抗日,我们暂时外边白,心里红,红星永远铭刻在心上。”[19]85由此可见,这反映了旗帜符号在变动时所引起受众的群体抵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很多人以此认为中共将会在抗日的洪流之下逐渐消解变成一个民族革命的政党,其所主张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等都会被消解。王明甚至主张“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听从国民党的指挥和安排。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名称,很多人也主张改名,其中不乏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党内也存在类似议论。毛泽东曾在七大作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有人说我们党要改改名称才好,他们说我们的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毛泽东认为,“一切问题并不在乎名称,你叫保守党也好,什么党也好,他们还是叫你红党。”“我们党的名称还是不要改。我们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20]324-3251938年10月12日—14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16]659这为中国共产党建构和使用自己旗帜符号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
旗帜符号形式的改变只是一种革命策略,关键的是在抗日的大环境下如何建构自己的旗帜符号来引领未来革命前途。中国共产党是在民族主义这一大旗帜下独立自主地建构自己的旗帜符号。即使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和抗日大旗之下,八路军的活动也遮盖不住中共一贯政策和主张,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八路军区别于其它的国民革命军。1937年1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八路军应带符号,从新规定证章,凡无此据者,应一律取缔,并将规定报阎及通报友军及地方行政机关,出布告发表谈话登报。”[16]400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抗日潮流之下,中共也担心其所领导的八路军被趋同了,也设法在本身已经相同的番号上作出区别,在旗帜符号形式的共性中寻找个性,避免被老百姓同等看待。
抗日战争时期,虽说军旗应与南京国民政府所规定的军旗要一致,且在各种重要场合下还得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党旗则是一例外。在边区和解放区,党旗的悬挂是不受国共合作影响的。因而,中共党旗在边区、解放区就显得尤为凸出。194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制作中国共产党党旗样式的决定,指出:“中共党旗样式:长宽为三与二之比,左上角是斧头镰刀,无五角星。”会议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作一批标准党旗,分发各主要机关。于是,第一批中国共产党标准党旗在延安诞生了。中共七大召开前夕,大会筹委会收到各地代表的许多来信,建议中国共产党的党旗要体现出民族化的特色。为此,大会筹委会发出了征集党旗图样的通知。在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收到了二百多幅党旗图样,设计图案各色各样,分别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征,洋溢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战斗精神。这230幅党旗图样在七大召开期间还进行展览。由于特殊时期,这些符号图样虽未被采用,但为中共旗帜符号的发展历史增添了一笔重要精神财富。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会场布置得庄严神圣,主席台顶端镶刻“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字样,正中是毛泽东朱德的侧面像,两旁悬挂着六面中国共产党党旗,金光闪闪的“镰刀斧头”和红缨旗杆映照得四壁生辉,充满了隆重、热烈的气氛。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在全国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中国共产党党旗。党旗从不同方面体现出了党的性质、纲领和前途,充满着鲜明的民族气质和战斗精神。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通过自己政治生态的政治定位,通过旗帜符号形式的转换,取得了革命的主动权。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旗帜符号的形成与引领
国共和谈失败后,国民党发动了全面进攻,此时各地解放军的军旗符号又呈现出混乱局面,有的使用红军时的军旗符号,有的使用党旗符号替代,还有的甚至打出了印有毛泽东肖像的旗帜符号。这种混乱使用旗帜符号也由于革命形势急剧变化,使得中共还没来得及去思考统一党内军内以及各解放区旗帜问题。直到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军旗的决议》中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24]171红五星加“八一”字样的设计有其说法的。对此,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规定了军旗及军徽的样式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21]330“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为镶有金黄色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21]332同时,对军旗军徽的制作大小尺寸及用法都作了具体规定。
在国旗的使用和设计上也渗透着中共的革命理念。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21]58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毛泽东对五星红旗的意义作了十分经典的解读。他指出,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面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现在我国人民所包括的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每颗小星各有一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原封不动将革命时期起核心作用的革命党或革命团体使用的旗帜,定为国旗或国徽并不多见,而且所有的革命不可能采用一种固定的旗帜。但革命成功后成立的政府对正式的国旗大多采用固定的象征革命意义与正当性的图案、色彩。”[9]58
解放战争时期所使用的党旗也具有中共自身特色,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场上悬挂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左上角是镰刀锤子,中间写“中国共产党”字样,这又明显不同于中共七大时使用的党旗。尽管延安时期已对党旗的设计样式标准作出规定,但由于革命战争环境变化莫测使得党旗符号在不同时空环境里出现不同的制作式样。1949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旗问题的通知》指出:“中共党旗过去无正式规定,现正在拟制中;在未颁布前各地不要自行公布党旗格式尺寸及解释”,“群众自行悬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或锤镰旗或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者,均听便。但误挂苏联国旗者,应善意劝止,免滋误会与造谣”。1949年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入党仪式所用党旗尺寸的规定》:“暂规定(宽)八十厘米,横一百二十厘米之红旗,左上角的中间为黄色镰刀、锤头,其直径为三十厘米。党旗旗杆左套为白色,宽为六点五厘米,亦即旗面横长十八分之一强。旗杆样式与矛头与军旗制法相同。”中央宣传部在同年10月11日曾函复军委总政治部“同意在党旗未统一规定前按暂行规定之样式试用”。1951年6月17日,《中央关于纪念党的三十周年时党旗的式样的规定》指出:“在党中央未正式规定出党旗的统一式样以前,在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时,各地可按旧例,一律采用红旗加镰刀锤头,不必在旗上加中国共产党等字。”[22]245195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党旗问题的通知》正式规定了“左上角缀以黄色镰锤的红旗,旗上不另加中国共产党字样或其他记号”。这在一定意义上规范了党旗的使用和制作,此后随做了几次修饰,但大样没有变化,中国共产党一直使用这样的党旗。解放战争时期,军旗、国旗和党旗的最终确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开始走向成熟。
中共旗帜符号无论如何变化,有一个符号始终存在,那就是颜色。另一重要符号就是“镰刀锤子”与五角星的组合,成为中共旗帜符号变化的主要表现,直到解放战争才最终尘埃落定。旗帜的颜色和旗面的符号是旗帜彰显政治象征力量、引领政治发展的标识。中共旗帜符号的旗面一直都是红色,红色也是革命的一个重要象征,“有些象征总和一定的颜色联系在一起”,如中共党旗、八一军旗、五星红旗,“经验证明,如果改变颜色,这些象征便会失去感情的特征,因为这是由社会公认的感知规范所决定的,在这些规范中,象征和颜色形成固定不变的联系”[12]140。红色背景下的“镰刀锤子”党旗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具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因而,在中共旗帜符号中最重要的符号要算是“镰刀锤子”这一标志。“镰刀锤子”是党在经历各种革命磨难而发展成为充满极强烈感情的政治象征。象征着工农联盟的“镰刀锤子”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符号,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核心标志。除了一些简单朴素的革命旗帜如早期农民协会的“犁头旗”没有“镰刀锤子”的标志外,“镰刀锤子”在大部分中共旗帜中得到了不同演示,这反映了在中国革命活动中处处留下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轨迹,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无论在什么革命环境中始终代表着最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旗帜符号,但只有当旗帜符号发挥作用时,才能推动群众前进,旗帜符号所包含的感情就会向着共同的目标倾泻。因而,从土地革命时期的“镰刀”加“斧头”的军旗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加“地球”加“镰刀锤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再到解放战争时期“镰刀锤子”的党旗、象征中共的“红五星”和象征红军开始的“八一”组合的人民解放军军旗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这一具体旗帜符号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旗帜符号的不同变化,无论是简单质朴的旗帜,还是其后规范化的国旗、军旗和党旗,“镰刀锤子”始终成为其发展的引领方向。五星红旗国旗和“八一”军旗的确定、“镰刀锤子”党旗的回归,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符号的普遍性与中国革命具体环境的特殊性相结合的曲折发展历程,并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熟。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6]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8]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9] 中野实.革命[M].于小薇,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10]何长工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11]刘中刚.军旗史话[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
[12]列·沃伊塔西克.政治宣传心理学[M].邓本中、钱树德,译.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1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14]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5]彭芸.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6.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7]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8]廖汉生回忆录[M].北京:八一出版社,1993.
[19]王震传: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20]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M].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1]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25]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卷[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刘滢】
Revolution and Symbol: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a Symbol of Banner
HU Guosheng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status as a symbol of banner formed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which had undergone stages of embryo and setback in early days of its establishment, recovery and prominence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and formation and leadership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Liberation War, and finally established its status as a symbol of banner that lead the path of China’s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symbol played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role in lead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path, educating the revolutionary masses, manifesting the revolutionary symbol, spreading the revolutionary ideas, which displayed the special nature and complexity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road.
Key Words:revolution; symbol;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ymbol of banner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2—0078—0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政治符号’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14BDJ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国胜,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
【收稿日期】2016-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