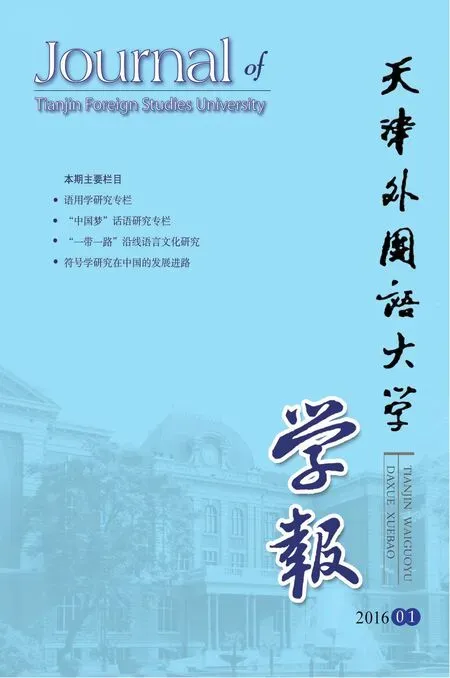第三次突变:符号学必须拥抱新传媒时代
赵毅衡(四川大学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44)
第三次突变:符号学必须拥抱新传媒时代
赵毅衡
(四川大学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44)
1 第三次传媒突变
我说的是“人类传媒第三次突变”,而不是“第三次革命”,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这词太轻。哥白尼体系是伟大的革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巨大的革命,而我们正在面对的传媒第三次突变,远比这样的革命重大得多:30年来人类这个物种的“周围世界”已经变得不可辨认,而且我们今日都很难估计人会在另30年内(也就是读者中许多人的有生之年,虽然很遗憾地已经不包括笔者)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物种。
我说的第一次传媒突变,是言语和符号的发明。虽然没有任何考古记录能找出言语的录音,但是两年前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发现人类最早的有意做下的手印(也许意义为“到此一游”,或“此山是我开”,或许是“我的手多美”)。这些保留下来的符号,据说有4万年,言语的发明应当远远早于这个日期。由此,人类从此彻底脱离了生物界,成为“使用符号的动物”。在这之前,人类发现火可能已经有千万次,人类用圆树干做轮子运输,也可能由千万次,但是只有用符号,个体的经验才能承传给后代,变成社群智慧,成为“文明”。
第二次传媒突变,是符号的系统记录与文字的发明。《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郑康成注:“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义或然也。"葛洪《抱朴子.钧世》:"若舟车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结绳,诸后作而善于前事。"。这种结绳符号,显然需要用语言配合作出解释,一旦需要解释,整个符号学体系(例如从像似性与指示性到归约性)就必须到位。人就不再是“符号动物”,而变成了“符号学动物”。 大约5000年前的这场突变,使人类脱离了原始阶段,开始拥有了社群组织、管理法制、国家体制。《易·系辞下》很智慧地指出符号记录体系的重大后果,是人类社会的“自我治理”:“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这才开始了真正的人类历史。
第三次传媒突变,是电脑与互联网的产生。这是近在眼前的事,万维网的出现只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事,1985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组建了第一个互联网,伴着TCР/IР协议的成长,1986年建成后成为Intеrnеt的主干网,并且迅速发展成任何电脑都可以加入进来的“万维网”(Wоrld Widе Wеb)。人类符号方式的飞速突变,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整个世界在短短几十年内,已经变成了一个30年前无法想象的世界,互联网引发的人类意义表达与传播方式的变化,让人类文化经历了沧海桑田。而且这场突变正在进行,另加30年,人工智能必将取得划时代的突破,机器将不再是人的器官延伸,而成为人的智慧延伸。人类能想象的最不可思议之事,将在2045年前(互联网发明60周年)之前出现。
我们已经看到,这三次传媒突变的年代,是一个陡升曲线,而且陡升得越来越快,我们根本无法预料电子传媒的变革速度,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把人类带到哪里去。更重要的是,人类面对的这个新的突变,产生了对传媒的全新想法,全新的概念范畴,指定全新的规则:电脑从孤立的工具,变成全新的传媒方式互联网,设备基本没有变化,而只是一个使用概念变化。人类从“使用符号的动物”,变成“符号学动物”,现在正在变成“符号元语言动物”。
由此,进入我们要讨论的关键问题:面对人类符号的翻天覆地巨变,符号学应当怎么办?但是,符号学在许多领域,只是可用的方法论之一,例如在语言学、美学、文艺学、文化研究等学科中,符号学可以带来“常规方法”之外的新气象。但是在一个学科中,符号学是不言而喻的,默认的(bу dеfаult)方法论,这个学科就是传媒研究(Mеdiа Studiеs)与传播研究(Cоmmuniсаtiоn Studiеs)。实际上在全球设立符号学的大学中,符号学往往与传媒或传播研究合成一个系,或一个专业。页只有在传播系科中,在传媒各课题中,符号学才有面对新媒体的紧迫感。
2 符号学必须重新定义自身
无论今日还有多少礼貌周到的疑惑沉默,还有多少不由自主的讥讽微笑,符号学运动在中国正在飞速发展。证明顺手可得,而且令人信服:百度一下,CNKI一下,当当一下,卓越一下,全国每年刊出的符号学论文,出版的符号学书籍,开出的符号学课程,数量都已经非常巨大。符号学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已经无可否认。此时,认真的学理探索,就更是当务之急了。符号学的“可操作性”,使它成为人文社会各科的公分母,我们称作“文科”的各种学科,都得到符号学的支持。
什么是符号?可以简单清楚地说:符号是用来携带意义的。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
这个定义,看起来简单而清楚,翻来覆去说的是符号与意义的锁合关系。实际上这定义卷入整个文化,因为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相关表意活动的总集合。
那么,什么是符号学?符号学在西方通用的定义“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问”(Sеmiоtiсs is thе studу оf thе sign),实际上是用希腊词源“符号”(sеmеiоn)与拉丁词源“符号”(signum)的同义词作循环定义。我们没有必要跟着西人转圈子,因为这个定义在中文中特别可笑,完全不能用。尤其在这个全新的传媒时代,死守这个定义,是中国人吊死在西方古树上,完全没有必要。
可以简明扼要地说:符号学就是意义学,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符号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为何人追求意义的生存,为什么这种追求使他成为一个文化的人。符号学是人类历史上有关意义与理解的所有思索的综合提升。笔者二十年前对文化下了一个定义: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毕竟,意义问题,是所有人文学科关注的中心,而且一旦放弃追求意义,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存在”的人。
符号学原本是形式论的一个派别,由于其理论视野开阔,又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六十年代之后成为形式论的集大成者:符号学从结构主义模式,推进到后结构主义模式,从以语言文学研究为主要目标,推进到以文化研究,尤其传媒研究为主要领域。当代人类传媒的迅速蜕变,使形式研究超越了自身:符号学保持其形式分析立场,另一方面又超越了形式研究,其锐利的批判锋芒,成为整个当代文化理论的基础方法论,成为名正言顺的“文科数学”。
3 符号学是中国的学问,不是舶来品
中国在历史上就一直是一个符号学大国。《周易》是人类第一个对世界进行抽象解释的符号体系。王夫之的界定非常类似我们今天对符号学的理解:“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他的“统会”两个字,用得很准确:这是符号学作为人类文化总论的特色。
“符号学”这个现代中文学科专称,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他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
在西方,符号学的学科史,从皮尔斯与维尔比夫人通信算起,已经超过115年;从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讲课算起,现在正好一个世纪;而中国的符号学起步并不比他们晚多少,从赵元任1926年提出“符号学”,方光焘1929年在法国研习索绪尔开始,符号学在中国缓慢地,但是不屈不挠地前行。这个过程到现在,已经接近九十年,比起西方符号学的历史不遑多让。
我们惋惜赵元任之后,“符号学”这个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的确,当别的民族前进时,我们止步了。这不能完全怪历史走迷路:中国知识分子喜欢宏大理论,在逻辑性比较严密的学科上,一直比较钝感。中国思想者,尤其是现代学界,不耐烦于逻辑分析,更喜爱“整体把握世界”。这种学术倾向于思维方式,不能说是缺点,但是分析方法几乎整体缺席,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大弊病。在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符号学才作为一种新奇的舶来品介绍过来,而且一直被看做是纯粹的西学,这是一个绝大的误会。
要建立中国的符号学,必须抓两头。一方面是符号学丰富的中国传统资源,包括先秦诸子,《易》学,唯识宗与因明学,道家与民俗,都有耐得住寂寞的学者在思索。另一方面是理论的抽象,符号诗学、符号叙述学、符号美学、符号学主体哲学,都应当有人辛苦经营;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阐释学,与精神分析等批评理论的学科融合,都必须有人做专题研究。
但是我们必须特别注重符号学对传媒各学科的渗透力:产业商品如广告、品牌、电子游戏、动漫,取名等等;社会文化如幸福感、体育、时装、名人、神话,环境、旅游、礼物等等;艺术门类如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网络文学、青少年“二次元”文化等等,现在都有人在做深入的符号学钻研。只有不断地让符号学的原理经受传媒研究实践的考验,才能使符号学成为一门活的学问,边界开放,不断拓展。
收稿日期:(2015-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