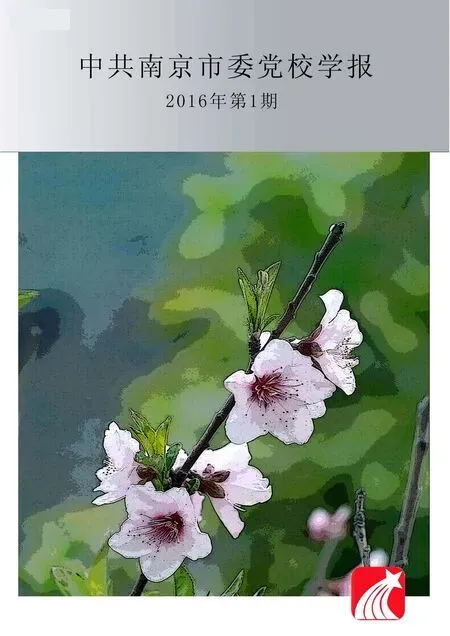西方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主要策略
杨 威 曾志洁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西方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主要策略
杨 威 曾志洁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西方国家在世界舞台上争取国际话语权主要依靠强制性的军事策略、诱惑性的经济策略和具有柔性的软实力策略。军事策略是利用其强制性外交、战争、联盟等手段直接迫使他国听命于本国,站在本国立场上维护本国利益。经济策略则是借助于援助、贿赂、制裁等方式增加或减少他国经济利益,从而诱使其放弃自己的话语权,听命于国。借助于军事策略和经济策略所获得的国际话语权只是被动的、短期的;通过公众外交、价值观渗透以及国际议程设置等方式取得国际话语权的软实力策略才是主动的、长期的。
西方国家;国际话语权;策略;软实力;价值观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世界政治犹如一盘三维棋局,要想赢得这盘棋局就得同时在水平和垂直空间里落子”。[1]在奈看来,三维棋局的上层棋盘是传统的国家间军事较量,中层棋盘是经济力量的角逐,下层棋盘则是国家间的软实力比拼。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当今时代,军事较量、经济角逐、软实力比拼逐渐以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形式出现。世界舞台上,谁掌握了国际话语权,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和发言权。
国际话语权,简单来讲“就是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2]它也是“主权国家通过正式外交、媒体传播、民间交流等渠道,将蕴含一定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话语渗透到国际社会中,使其他国家自愿接受并认同的能力”。[3]在国际对话中,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一方利用话语权优势,“按自己的利益和标准以及按自己的‘话语’定义国际事务、事件,制订国际游戏规则并对事务的是非曲直按自己的利益和逻辑作解释、评议和裁决,从而获得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权”,[4]以便实现该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当前,西方国家在国际话语权上占据着强势地位,美国甚至拥有话语霸权。
纵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历程,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策略主要不外乎这三个方面:军事策略——强制性外交、战争、结盟;经济策略——援助、贿赂、制裁;软实力策略——公共外交、价值观渗透、国际议程设置。
一、西方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军事策略
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来掌握世界政治与安全问题的话语权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最为传统也是最为常见的做法。其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西方国家借用威胁、武力、结盟等手段直接取得某些政治与安全问题的话语权。在实际争夺和霸占话语权的过程中,这些手段则表现为强制性外交、战争、结盟等形式。
(一)利用强制性外交获取话语主导权
“强制外交”这个词最初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亚历山大.乔治于70年代初提出。在他看来,“强制外交就是指使用威胁和/或有限武力,来说服其他行为主体停止和/或清除已进行的某个行为”。[5]由于乔治所提理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美国学者对“强制外交”进行了补充,即“一国通过威胁适用武力和/或实际使用有限武力,影响另一国的决策,促使其做某事——停止正在进行的行动,或消除已经采取的行动,或从事强制国所期望的其他行动。”[6]基于此,强制性外交,作为西方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军事策略之一,是指使用威胁和/或有限武力来强迫他国认同自己的话语内容,承认自己的话语主导权,以此获取对具体事务的定义权、评价权和裁决权。
海湾战争是强制性外交获得国际话语权的典型案例之一,当时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行介入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冲突之中,使得战争形势由“一场以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战争为开端的海湾战争,变成了伊拉克和西方之间的战争。”[7]西方国家的胜利为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赢得了相应的国际话语权,如中东区域安全问题的发言权和石油的议价权等。在当前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美国为了赢得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仍然采用强制性外交来处理少数“忤逆”国家。
(二)发动战争直接强夺国际话语权
战争,作为最为传统的军事手段,是解决争端、冲突最直接和最快捷的方式。但基于战争本身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越来越少的国家选择采用战争来实现其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甚或是国际话语权。不过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西方国家依然会采取战争的形式来取得国际话语。
究其本质,在话语权的争夺中,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某些国家为了取得某些事务的裁判权和议价权,不惜利用武力侵犯他国,直至他国在此事务上听命于本国。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取得国际话语权,美国之所以能取得话语霸权,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其战争策略。两次世界大战尽管不是美国发动的,但是美国作为战胜国取得了对国际秩序议定的话语权;冷战的胜利,更加奠定了美式价值观的全球地位。
(三)借联盟共享话语主导权
地区、国家和组织进行联盟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周边的安宁和稳定。但是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得联盟已经超越了军事战略的内涵,变成了一个经济词汇。在某些涉及地缘政治及国际经济事务中,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盟无疑是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不二选择。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中,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就采取联盟的手段。而联盟的内在逻辑也就是通过与他国达成某种合作关系,建立某种固定的组织,共享对某些事务的评判权。
例如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是美国与西欧、北美主要发达国家为实现防卫协作而建立的一个国际军事集团组织。它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和常规部队,是西方重要的军事力量,也是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军事上实现战略同盟的标志。同时它也是马歇尔计划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和发展,是美国得以控制英国和法国为首的欧盟的防务体系,是美国世界超级大国领导地位的标志。北约的形成对于美国的国际话语霸权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强制性外交、战争、联盟作为西方获取国际话语权的传统军事策略的三大主要手段,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今世界,日益淡出世界舞台,取而代之的更多的是经济策略、软实力策略。
二、西方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经济策略
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实力是一种特殊的权力。美国学者米德认为经济实力是一种“粘性权力(sticky power)”,“这种权力由一系列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构成,这些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吸引其他人喜欢美国的影响,然后接受美国影响。”[8]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是采取援助、贿赂和制裁等多种经济手段取得国际话语权。
(一)假借援助之名
通常情况下,国际经济援助是指有关国家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赠与和提供的优惠贷款。实际上,国际经济援助是长期国际资本流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双边援助和多边援助。援助形式的多样化是基于援助背后的根本目的,如国家利益的实现、意识形态的传播、国际话语权的获得等,而借用经济援助来获取国际话语权是西方国家的传统策略。
19世纪,英国为了重建全球经济秩序,获取全球经济秩序的发言权,将美国拉入英国制定的经济秩序之中,英国伦敦金融市场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促进美国工业的发展。20世纪中叶,美国欲控制西欧的政治和经济格局,获得对西欧的政治经济的话语权也即控制权,对被二次世界战争破坏了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即马歇尔计划。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在此期间,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为获取对台湾岛屿的控制权以及获得对中国事务的发言权,“截至1965年6月,美国对台军援总价值为23.8亿美元,经援总价值为15亿美元。”[9]其中经济援助包括化肥、技术以及资金援助。美国还用此种援助方式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了对日本的控制权。
(二)施以国际贿赂
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中,基于对行为本身的动机进行探讨,获取国际话语权的贿赂手段易于与经济援助相混淆。相比于经济援助,贿赂一般是指商业贿赂,即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商品或者购买商品,提供服务或者接受服务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涉及到国家与国家之间,贿赂则被认为是国家间为争取某一经济利益或者某一事务的裁判权而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贿赂本身所具有的不正当性使得国家间的贿赂行为具体的表现为跨国的国有企业之间的贿赂行为。尽管几乎每个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反海外贿赂法,但是不到万不得已情况之下,西方国家对于自身企业的贿赂行为是不会进行检举的,因为贿赂行为本身为自己获得了实际利益,并且该国政府还获得了对具体经济事务的话语权。据《人民日报》报道,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西门子公司以支付回扣等贿赂方式取得项目竞标,涉及联合国伊拉克“石油换食品”、委内瑞拉铁路、孟加拉国移动电话网络、以色列发电站等项目的参与权,[10]使得德国获得了对这些国家具体事务的话语权。国际贿赂的实质就是部分国家为了获得国际话语权借用财物或其他手段对他国进行贿赂,尽管贿赂行为的不正当性,部分西方国家依然借助此种行为来获得国际话语权。
(三)实行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在经济学中是指一国或数国对破坏国际义务、条约和协定的国家在经济上采取的惩罚性措施。一般而言,常见的方式包括:实施贸易禁运、中断经济合作、切断经济或技术援助。在维护本土技术和本土贸易当中,经济制裁是最为常见的手段。同样,西方国家为取得某些技术、领域等话语的主导权,也会经常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禁运、中断经济合作等经济制裁行为。
以美国为获取通信技术的控制权为例。为获得通信技术的发言权,美国多次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制裁。‘朗讯中国贿赂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为获取通信技术控制权和话语权的案例。2003年8月,沙特Silki-La-Silki国家电信公司向纽约联邦法院递交起诉书,指控朗讯及瑞士的ACEC公司在1995年至2002年期间,向沙特前邮政电话电报部长行贿了价值1500万元到2100万元的现金和礼物。作为回报,电报部长做出很多有利于朗讯的决策,从而使朗讯在沙特无线通信市场上赚取了数十亿美元。迫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的强大压力,朗讯开始在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开始内部审计,调查结果显示,仅有朗讯中国涉嫌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的腐败行为。2004年4月6日,朗讯总部解雇了其中国区包括总裁、首席运营官、财务经理和运营经理在内的4名高级管理员。并且在随后4月22日的中美商贸会上,中国同意无限期推迟WAPI的强制执行,并且同意在关于本国采取何种第三代移动技术标准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即允许运营商自行选择3G标准,这意味着信息产业部松动了对CDMA450的管制。而在此之前,我国对美国的CDMA450颁布过两条封杀令。[11]明显的可以看出美国这一制裁的行为背后,主要是想扩大朗讯在中国通信市场的份额,想要利用CDMA450技术控制中国的3G网络,并获得中国3G网络的话语权。一方面美国通过经济制裁获得了某些事务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经济制裁来维护自己已经获得的国际话语权。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西方国家日益逐渐减少了采取经济制裁来获取国际话语权的策略。尤其是美国,在自由贸易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被制裁国家在被美国给与制裁后选择与其他国家进行进出口贸易,使得美国丧失就某些事务进行评判的权力;同时由于大多数贸易并非政府行为,而是民间行为,对于大多数被美国称为“Rogue states”的国家并不十分关心自己国家民间的贸易行为,美国的国际裁定对其不产生任何影响。[12]
援助、贿赂、制裁作为西方获取国际话语权的经济策略,三者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在西方国家假借对他国施以经济援助并未夺得国际事务的话语主导权时,西方国家就会借助贿赂政策对他国政府及其高管进行贿赂以期获得对具体事物的裁判权。在此应注意的是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变为贿赂。当援助和贿赂都不能使其获得国际话语权时,西方国家则会采取经济制裁,迫使他国接受所提议题,从而获得国际话语权。显而易见,通过采用经济策略所获得国际话语权是一种具有诱惑性的、被动的、短时的权力。
三、西方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软实力策略
如果把军事实力比作大棒,经济实力比作胡萝卜,那么软实力就是“自由女神像”。“软实力”这个词最初由约瑟夫.奈提出,主要是指一种吸引人的力量。[13]区别于军事策略的强制性,经济策略的诱惑性,软实力策略则更多的是借助于世界各国自身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取得国际话语权。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这种依靠软实力来抢夺话语权的策略主要以争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控制权的形式展现出来。在这场持久的意识形态争夺赛中,西方国家主要借助公共外交、价值观渗透、国际议程设置等路径试图掌控国际话语权。
(一)公共外交
按照2000年美国官方解释,公共外交指的是“通过国际交流、国际信息项目、媒体、民意调查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等,了解、获悉情况和影响国外公众,扩大美国政府、公民与国外民众的对话,减少他国民众对美国的错误观念,提高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进美国国家外交方式。”可见,公共外交在西方掌握国际话语权的策略当中是一种迂回前进的手段。其策略就是借助公共外交中的双向互动向国外公众传递本国资讯,宣传外交政策、交流思想传播国家观念,引导外国舆论,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赢得外国公众对该国政策或行为的了解、理解乃至支持,努力在国外民众中培育起一种对本国友好的政治生态,再藉此由外国民众去影响外国政府于我有利的政策的产出,进而切实提升本国的国际话语权。
当前西方公共外交的活动方式多种多样,如信息活动、文化和教育交流、国际广播、各类基金会和思想库、民意调查、网络交际、NGO、MNC、网络、图书馆和多媒体中心、展览、语言培训、书籍出版、人才交流、媒体外交等等。以美国的人才交流为例,“迄今为止,全世界有200多个现任和卸任的国家元首及1500多名部长级的官员在年轻的时候都曾参加过美国国务院负责的‘国际访问者计划’项目。”[14]就中国而言,参加此项目的人都是经过美方精心挑选,且被选人主要是中国的社会精英和舆论领袖。美国如此为之,目的不言而喻。借用社会精英和舆论领袖们的口和笔,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向中国民众介绍美国历史、美国文化、美国生活方式等,促使民众在了解美国过程中不自觉的认同了西式“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进而使得民众以西式观念审视本国政筞从而影响本国决策。
此外,二战刚刚结束时,为加强美国文化在日本的迅速传播,美国的民间基金组织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向日本东京大学提供大量资金,帮助日本政府在东京建立文化馆。文化馆一来是美国教授来日进行文化交流时的场地,二来也是日本青年学者学习西方文化的主要场所。文化馆表面看起来似乎有利于日本学者认识世界以及日本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但实质上,美国创造此文化馆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将本国文化、价值观念输入到日本,一方面为其驻军日本提供合法性的支撑,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自身控制日本的军事、经济、政治等问题的话语权。冷战期间,为了加强对东欧国家的文化影响,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在布达佩斯建立了一个美国之家,并且提供了一个拥有图书馆和戏院的设备完善的文体中心。美国驻匈牙利的大使马克.帕尔梅还提议,应该在每个东欧国家的首都设英国之家、西德之家或西方其他国家的家。文化之间的交流为美国、西欧国家之间的结盟奠定了基础。可见,日本的西化、东欧的回归都是与公共外交离不开的。
当前,美欧等西方国家依靠公共外交来夺取国际话语权呈现三大特征:全面化、本土化、西化。全面化主要在于在其文化传播过程中,关注的对象不再是单一群体,而是由儿童、青少年、青年、成年等既包括一般民众又包括知识分子的多层次群体;另外其组织形式也越来越多样,不仅包采取政府主导的国家间文化交流,还包括非政府主导的民间文化交流等多种形式。本土化则是体现在文化交流中,不再直接向外国民众输出西方文化和思想,而是将西方文化与其他国家的语言特点、生活方式等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吸引、同化外国民众。西化可以说既是公共外交的特点又是公共外交的目的,使交流对象认同西方的文化,并促进其思想和行为的西化。
(二)价值观渗透
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和平演变”使得红色苏维埃政权垮台。和平演变的实质也就是价值观渗透。当前随着商品的世界流动以及互联网的快速传播,西式“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已经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西式价值观的广泛渗透为西方国家在道德、意识形态等方面赢得了国际话语权。从20世纪至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直以“人权”问题指责中国,而他们指责的标准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权价值观。
价值观渗透策略区别于公共外交策略,其对象直接为外国民众,而作用手段则是输出文化产品和互联网。通过文化产品来渗透价值观,以美国为例,在文化产品的制作上,“据统计,美国控制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多达30万小时,在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美国输出的节目往往占到60%-70%,有时甚至占到80%以上,而耐人寻味的是,美国自己的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却仅占1%-2%。”[15]在文化产品输出方面,美国的顺差可谓惊人,但却鲜有国家与其计较文化顺差现象。另外,就影视作品而言,美国更是占尽优势,“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球电影发行网的国家,虽然其电影产量只达到世界的6%-7%。但却占世界电影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16]美国电影、电视剧具有新奇、亲切和有趣的魅力元素,让看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认同了它的价值观。如《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美国经典电影,在无形中使受众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这就是“美国梦”的内涵。美国产业之所以能进行有效的价值观渗透在于:它将民主话语和市场机制结合,实现了主流价值观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巧妙整合。通过市场机制,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实现了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整编’,让普通民众在消费文化之际,浑然不觉地接纳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等核心价值观。
利用互联网来进行价值观渗透,是西方国家在当前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最主要的手段。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计算机的国家,其计算机技术、互联网以及物联网水平处在世界顶尖水平。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甚至垄断了当今国际互联网核心部位的控制权。西方领先的计算机技术为其西式价值观的渗透开创了良好的平台。美国的两大网络巨头谷歌和微软公司,打着“网络自由”的旗号,收集和窥探各种有利于本国的信息数据,主导着网络话语权。另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些社交平台逐渐兴起,Facebook ,Twitter上活跃着数十亿不分民族、不分阶层、不分国籍的网民,他们在网络中不知不觉地接受着西式价值观的影响。西方国家还通过各种方式培植意识形态的“代理人”或“意见领袖”,在网络上为西式价值观代言,从而实现话语控制甚至政治动员的目的。“阿拉伯之春”的发生,背后就有西方国家利用社交网络进行价值渗透和政治策动的“黑手”。
在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赛中,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渗透呈现多元化、渗透性、宗教性的特征。多元化是就西方的价值观的内容而言的,西方对外输出的价值观不仅仅只是包含政治层面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还包括一些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渗透性则是就价值观输出方式而言的,这是不言而喻的。诚然,美国经常公开指责他国没有人权,但是其价值观的主要传播方式还是渗透性的、隐性的。如借助FACEBOOK或推特发一些美国故事或者向他国免费转让有关歌颂美国著作的版权。宗教性,主要是美式价值观在他国的塑造方式,借用新教或天主教,对他人进行“洗礼”,帮助他人重塑价值观。正是通过这种巧妙而隐蔽的价值观渗透,使得一部分他国民众对西式价值观逐渐产生认同,从而在“人心”层面获得话语主导权。
(三)国际议程设置
较之于公共外交和价值观渗透等间接手段来获取国际话语权,国际议程设置则是直接根据具体的国家利益来制定特定的话语内容,并利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媒体来制造国际舆论,从而获得对具体事务的评议权和审判权,也即话语权。可见,谁掌握了国际政治议程设置,谁就赢得了国际话语权。
作为一个传播学概念,议程设置内在的包括公众议程和媒介议程。就二者关系而言,正如马克思韦尔.麦库姆斯所说,媒介议程为公众提供了显要性的线索,“使得公众可以根据这些显要性的线索去组织他们自己的议程,并决定哪些是重要的议题。时间长了,新闻报道中强调的议题就成为公众认为最重要的议题。新闻媒介的议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公众议程。换句话说,新闻媒介议程设置了公众议程。”[17]国际议程设置也内在包含了这两个方面,但是区别于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国际议程设置指的是“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某一国家就国际交往过程中与他国存在的某几个问题领域或某几个国家就他们关心的几个国际问题领域,按照他们对本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向其他国家设置对话的议题以取得议题的话语权和行动的主导权。”[18]国际议程设置一方面通过国家主体来设置议题,另外一方面通过媒介议程来设置相关议题,使其具有显要性,并进入到国内外民众议程之中,使之成为国内外民众的关注、思考甚至是采取行动的重点。
西方国家是如何借助国际议程设置取得国际话语权的呢?当前西方国家强大的国际议程设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国际文化议程设置和国际政治议程设置。西方国际文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制在于: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塑造他者偏好的标准或制度议程设置”的能力;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掌握了信息革命的定义权。前者是一种极具隐蔽性的文化上的损人利己能力。资本主义通过文化殖民重新塑造他者的偏好标准和制度议程,用自身的文化逻辑去替代他者的文化逻辑,将他者文化置身于自身的区域轨道。这种置换话语的“语法”策略,能够产生釜底抽薪的效果,它摧毁了他者文化的正当性基础,使其就范于西方价值观的“文化殖民”。后者伴随着的是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信息革命的滚滚车轮,在信息革命中,西方国家始终掌握着规则的定义权。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的倡导者声称,国际信息系统的维持加深了发展的不平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在信息技术的硬件和软件方面都严重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
区别于国际文化议程设置,西方国际政治议程则是借助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媒体对特定问题进行大力宣传,制造舆论并引导舆论。西方国际政治议程设置的平台——美国有线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法国24小时”国际新闻台、日本的NHK世界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这些平台在新闻的发射转播、业务构成、人力资源、落地覆盖、技术保障等方面远远领先于第三世界国家。凭借此种能力,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事务上一直拥有着内含发言权、评判权的话语霸权。当然,国际政治议程设置能力是与国家的支持、专业化的技术团对以及明确的价值观分不开的。“今日俄罗斯”就是走出话语困境,拥有自己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典型代表之一。[19]
四、西方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策略的启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庞大的经济总量,采取在军事上打压、经济上诱惑以及文化上吸引等策略,在国际话语权的角逐中逐渐掌握了话语主导权。利用所获得的国际话语权,西方国家一方面实现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另外一方面,借助国际话语的主导权制造舆论遏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认清西方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策略,对于中国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是打好根基。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意志的综合体现,其背后则是综合国力的支撑。打好根基就是要不断提高包含军事、经济、软实力等在内的综合国力。军事上,以维护自身安全为目的不断进行装备的创新研发。经济上,科学、协调、绿色、共享、开放发展,实现经济总量的稳增长。软实力上,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结合当前的文化形式,借助各种传播平台,让国内外民众能够听到中国声音,感受中国魅力。
二是抓住对象。国际话语权作为一种话语权力,是话语双方的一场权力博弈。要想在博弈中取胜,就得抓住博弈的对手。了解博弈国家的偏好习性,掌握对方的需求情况,根据博弈国家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策略。
三是建好平台。建立良好的、多层次的话语平台是赢得国际话语权关键性的一步。除了官方搭建的国家之间文化交流平台,还可以发展民间团体组织、NGO组织以及志愿者组织等进行非官方对话平台。通常情况下,非官方平台的在传递价值观方面的效果要优于官方组织。此外官方平台也可以建立针对不同国家的多层次的对话机制,尽可能在对话中,让其他国家了解自己,认同自己,从而获得话语的主导权。
四是“软硬兼施”。软硬兼施是指在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中要善于灵活使用各种策略。针对不同的话语对象、话语内容采取不同的策略。西方国家在获取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并不是单一使用一种策略,而是两种或三种同时进行。如美国为获得世界人权的话语的主导权,不仅利用软实力策略攻占互联网为人权话题造势,而且在对外贸易中,拒绝与违反人权的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并对它认为违反人权的国家出兵进军。
总而言之,要改变中国在世界国际话语权领域里的不利局面,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必须认清西方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策略与实质,同时探索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路径和方法,使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力量的国际话语体系赢得世界更多国家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1][13]约瑟夫.奈.软实力[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 7、10.
[2][4]梁凯音.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3).
[3]王啸.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6).
[5][6]钱春泰, 美国与强制外交理论[J].美国研究,2006(3).
[7]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1999,281.
[8]Water Russell Mead . America’s Sticky Power[J].Foreign Policy ,No.141(Mar.-Apr.2004),46-53.
[9]杜继东.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J].广东社会科学,2011(3).
[10]西方发达国家是跨国行贿重灾区[N]〗.人民日报,2014-12-04.
[11]赵波.陷阱:中国企业案例启示录[M].珠海出版社,2005.
[12]Pascal Boniface . Reflection on America as a world power : a European view[J].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Vol.29.No.3(Spring.2000),pp 5-15.
[14][15][16]张国庆.美国为什么总是赢得主动的话语权[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42、128、129.
[17]马克思韦尔.麦库姆斯. 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 郭镇之徐培喜译[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8]赵长峰、左祥云. 国际政治中的议程设置浅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6).
[19]程曼丽.如何进入国际传播的主阵地———以“今日俄罗斯(RT)”电视台为例[J].新闻与写作,2013(6).
(责任编辑:育 东)
本文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托课题《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增强国际话语权研究》(13&WT003)、“教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阶段性成果。
2015-12-10
杨威(1979-),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珞珈青年学者。曾志洁(1991-),女,湖北鄂州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
D815
A
1672-1071(2016)01-00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