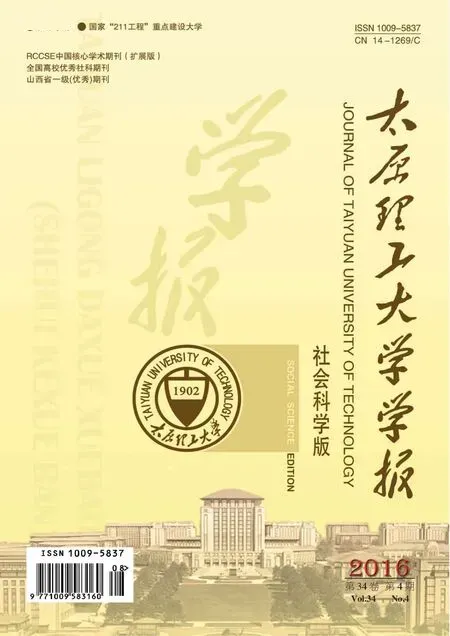论税务和解的适用范围
赵 群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论税务和解的适用范围
赵 群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关于税务和解的适用范围限于复议阶段,这符合税务争议纠纷解决的现实情形。税务和解的标的是法律授权下的行政处分权,法律仅将行政处分权限于行政裁量,忽略了做出行政处分前的事实认定,因为其中可能出现“事实不明”的情况,行政机关对此也有选择的余地,因此“事实不明”也可被纳入和解范围;法律运用偏向于法定职权,应当遵循职权法定原则,“法律不明”不适宜纳入税务和解;税务和解涉及对行政权的处分,须对其适用范围严格限制。
税务和解;行政处分权;事实不明;行政裁量
传统行政法在依法行政、公权不得自行处分的理念下禁止税务和解。“因税法是强行法,不允许由当事人的意思来左右纳税义务的内容以及履行方法,所以在税法上不允许有私法上的和解。”[1]近年来基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2],“协商民主论”[3],“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等理论,学界对税务和解有所接纳,税务和解的法律界定[4]、功能、正当性[5]及其与行政公权不得处分的关系得到了充分阐明,但是税务和解的适用范围这一核心命题却未得到重视,故本文将以此为视角展开论述。
一、税务和解适用的阶段:执法、复议抑或是诉讼
界定税务和解的适用范围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税务和解的适用阶段。税务执法阶段中税务机关的主要任务是认定课税事实、确定应纳税额,税务复议阶段中复议机关的职权是审查税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税务诉讼阶段则是司法机关审查税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因三个阶段作用的对象不同,导致税务和解的适用范围有所区别。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上位法《行政复议法》并未规定行政和解,但是下位法《行政复议法实施细则》却对行政和解做出了明确规定,部门规章《税务行政复议规则》(2010)还专章规定了税务和解,作为税收基本法的《税收征管法》则有意将税务和解纳入税务争议解决机制中,体现为《税收征收管理法征求意见稿(草案)》[6],规定了复议阶段的和解。从行政诉讼相关法律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1989)明确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而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2014)则有条件地承认了行政调解*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第60条规定。,对于却未承认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自行达成的和解。上述规定意味着在立法层面税务和解的适用范围限于复议阶段,并未扩展至执法、诉讼阶段。学界对税务和解的探讨集中在税务复议阶段,对于税务执法、税务行政诉讼阶段可否适用税务和解目前尚存有讨论的空间。
税务执法和解、税务复议和解、税务诉讼和解三者的差异仅在于不同的适用阶段,和解的标的在本质上并无差别。立法在税务和解上将三者区别对待是因为税务案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运行机理和权利义务配置。虽然税收债权债务说在税法理念范围得到普及,但是在税收征纳实践中税收行政公权总是处于较强的地位,例如立法赋予了其准司法性质的强制执行权、私法性质的优先权、代位权、撤销权等。另一方面,纳税人应有权利因法律的不完善导致其相对弱势。如果在税务执法程序中引入税务和解制度,则会加剧行政权的扩张和纳税人权利义务的萎缩。故而,在税务执法阶段不宜引入税务和解。但是,在征纳双方权利义务配置相平衡且有独立的第三方对税务和解进行监督时,则可以考虑将其纳入税务执法程序。
据统计,极少的税务案件能够进入司法审查程序[7],这在客观上导致税务行政职权难以接受司法的监督,立法者即使有心在税务行政诉讼中引入税务和解,在诉讼阶段也是鲜有机会适用。传统的行政诉讼是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但是现代行政诉讼已经将裁量性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最为明显的是法院对“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的审查。税务和解应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行使,包括行政裁量行为。
同很多国家一样,我国对税务案件的争议处理被控制在行政程序内部[8-9],复议机关与执法机关通常不是同一机关,复议机关的第三方特征使得税务和解的有效监督成为一种可能,所以,立法将税务和解制度设置在复议阶段是符合现实的。
二、税务和解的标的——行政处分权
和解,本为民法概念,指当事人约定互相让步,以终止争执或防止争执发生的契约[10]。在行政法中,和解合同是纠纷当事人通过相互让步来消除合理判断中的事实或者法律问题的不确定状态[11],以协议所适用的事实或法律来约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而达成的契约[12]。民事和解与行政和解是以双方的处分权为基础而达成的。在民事关系中,双方可自由处分私权,但是在税务行政关系中,税务机关不得直接对法定职权随意处分,税务机关的处分权限于认定基础事实、选择法律适用和行使自由裁量权等。在遵循税收法定、租税平等原则下,税务和解的适用范围更是限于行政和解范围之一部。
德国税务实践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通过缔结“事实认定协议”解决争议,事实认定协议是征纳双方就课税要件事实如何认定达成合意,并有受其拘束之法效意思之合意行为[13]。德国税法上的和解契约是针对基础课税事实要件而达成的,主要出于稽征经济的考虑。税收征纳乃为“大量行政”,税务机关不可能事无巨细的查阅纳税人全部的会计凭证据以认定课税事实,虽然自主申报、诚实推定、推计课税等制度减轻了课税基础事实认定的困难,但是课税基础事实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能完全确定,直接放弃认定会给国库造成损失,翔实认定又有违稽征经济,为平衡两者,实务中常达成“事实认定协议”。但是,税务和解协议能否适用于“法律问题的不确定”则有存疑,依据德国联邦财务法院的解释,税务和解协议基本上只适用课税要件事实认定的争议,不得用于化解法律上的争议,这包括适用何种法律、适用法律之后发生何种法律效果。针对个案中法律应如何适用或是因法律之适用应该发生何种法律效果,则没有允许协议之余地[13]。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也规定了行政和解,和解被界定为事实和解,指事实是否符合法定构成要件具有不确定性时双方相互让步而达成的契约,这一界定与德国法上的“事实认定协议”具有一致性。在实践中,事实和解运用最多的也是稽征机关与纳税人以排除课税基础事实的不确定性而成立的诉讼外及诉讼上的和解[13]。
从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税务和解的适用范围看,正是基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阶段中的不明状态,税务和解才得以适用。应税事实的准确认定和税法规范的正确适用,是税务机关据以做出合理的征税决定的两大基础[14]。当这两者存疑时,税务机关的征税决定就存在不合法的嫌疑。
达成“事实认定协议”的根源在于税收征纳程序中课税事实无法以全貌的方式呈现,和解协议则是课税事实的确定与证明责任的折中。“事实认定协议”只是在证据法上的角度降低了应税事实的证明程度,因其是纳税人与税务机关达成的,在协议约束的情形下,已经构成了纳税人的一种自认。即使如此,对于税务机关而言,和解协议仍植根于税务机关在基础事实认定过程中的处分权限。法律赋予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纳程序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职权,税务和解的对象也是针对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职权,所以税务机关可以在处分权内达成和解协议。
三、税务和解中行政处分权的界定
处分权对税务和解协议的形成至关重要,税务机关的处分权是在行政行为的形式要件(例如管辖权)齐备的情形下就实体部分被赋予的权限,限制形式要件主要是为了防止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在法律形式要件不具备的情形下订立一个不被允许的协议。税务和解中的行政处分权主要是实体上的,例如立法规定税务机关有权选择做出行政行为的方式或法律效果,此时,税务机关可与纳税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达成和解协议,这也说明税务和解的达成是税务机关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做出的,遵循了依法行政,不属于“公权力不得处分”的限制范围。
(一)行政裁量权
税务机关的行政处分权与行政裁量权有交叉之处,但是两者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有观点认为,行政处分权限的范围即为行政裁量权的边界,应将税务和解的范围限于行政裁量权[15]。“和解在行政过程中的运用,实际上就是在法律授权行政机关裁量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运用行政裁量权,从法定的行为方式中选择一种方式(和解),而后通过与相对人协商合意的方式行使行政裁量权的制度。”[16]
行政处分权与行政裁量权两者看似一致,但是在法律运用的层面上却有很大差别。学理上将具体行政行为分类为羁束性行政行为与裁量性行政行为,这种分类不是建立在行政主体对事实的认定是否具有灵活性的基础上的。就事实认定而言,不论裁量行政行为还是羁束行政行为都具有灵活性[17]。税务和解中的“事实认定协议”并不是行使自由裁量权后可达成的行为效果,而是行使职权确定基础课税事实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税务机关判断、认定属于事实确认部分,而行政裁量权的运用则是在法律事实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对法律效果做出的一种选择。故而,无论是羁束性行政行为,还是裁量性行政行为,在事实认定部分具有灵活性的意思是指两者都存在和解的余地。但是行政处分权绝不等同于行政裁量权,行政处分权的外延大于行政裁量权,运用行政裁量权是行政处分权发挥作用的一种方式,故而行政裁量权的行使也应归入税务和解的范围。
与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对税务和解的范围界定不同,我国税务立法与实践试将税务和解的范围扩展至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行政赔偿、行政奖励及其他合理性问题*详见《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40条和《税务行政复议实施细则》第86条的相关规定。,《行政诉讼法》(2014)对行政调解的范围也是做此限定,显示出了我国行政立法对行政处分权的严格控制,并未将基础事实查明不能时的“事实认知协议”纳入税务和解的范围中,而只是将行政处分权的一部分自由裁量权纳入税务和解的范围。
(二)事实不明抑或法律不明
一般来说,税务机关做出纳税决定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事实认定、事实认定的构成要件之适用(要件的认定)、程序的选择、行为的选择(选择何种行政行为及是否做出该行政行为)和时间的选择(即何时做出行政行为)[18]。法律适用是在要件认定完成之后就法律所做出的一种选择,是否可能出现“不明的法律”呢?法律适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属于法律解释的范畴,当事实认定完整,法律适用可能存在以下情形:事实与法律行为模式完全一致,可以直接适用法律;事实与法律规定的行为模式虽有差别,但经一定的解释方法可以将其纳入其中,此时也无适用法律的困惑;法律概念、法律规则的不确定导致税务机关适用法律具有疑义时;事实相对清晰,但是征纳双方对法律的适用产生了极大的争议,典型如应税事实的法律形式与经济实质不一致。
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在税法规则中大量存在,根据事实适用法律时会遇到法律障碍,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模式构建有从“唯一正确答案”标准到“商谈理性”的解释模式。即行政机关在具体化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情形下,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从以前的追求唯一正确答案转变至具有一个“合乎情理或相对正确”的答案区间[19]。只要行政机关在解释不确定概念中的“过程”“因素”及“理由”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可以得到保障,则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这一法律不确定性就可以解决。上述论述阐明了税务机关可就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解释的方法,并未阐明是否允许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就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协商。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属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现代行政法在行政行为做出的过程中强调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权。但是,法律适用特别是法律概念的确定与事实认定具有很大的差别,税收事实的认定需要相对人提供更多的课税基础事实,相对人参与行政效用更强,而且在确定基础事实的过程中,税务机关花费的调查成本更多,还原经济交易事实更为困难,所以,在基础事实不明的情形下,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税务实践允许双方达成税务和解。法律在适用的过程中虽需与事实认定相联系,但主要还是侧重于对法律概念的理解、法律规则的运用,与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直接相关,且直接涉及租税请求权,原则上应当不允许“法律不明”的和解。
当纳税基础事实的法律形式与经济实质不一致时,税法上有法律实质主义与经济实质主义之争。法律实质主义强调,当形式与实质不一致时,必须根据与实质相对应的法律关系,判断其是否符合课税要件,不能脱离真实存在的法律关系而直接按照其经济上的效果或目的,来判断课税要件的存在与否[1]。而经济实质主义强调,税收负担有必要维持其实质的公平,即便法律形式或名义相同,只要其经济的实质有差异,就应做不同的处理[20]。实质课税的争议已经从“事实不确定”“法律不确定”转向了法律适用,此时适用法律的困境不在于事实不明、法律不明,而在于征纳双方就税法适用规则产生了争议。在这种情形下,法律适用相较于事实不明、法律不明而言完全属于税务机关的职权行使,涉及到行政处分权的核心,在税收征纳关系中体现为对课税请求权的直接处分。在此种情形下应当不允许税务机关与纳税人达成和解协议,否则就会出现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以协议的方式处分行政职权。
税务机关行使课税权时,从事实认定到课税决定的做出,历经多个阶段,这些阶段主要分为三种:较为单一的事实认定、较为单一的法律适用、事实与法律交叉重合。三者的区别在于所依据的原始资料的差异,事实认定依据的是客观的纳税资料;法律适用则依靠法律与事实的契合程度;事实与法律的交叉适用将两者都涵盖。税务和解中将行政处分权限于事实和解不是因为“事实不明”与“法律不明”有绝对清晰的界限,而是因为两者有相对侧重的导向,事实认定侧重客观,法律适用倾向于主观,而且“法律不明”可以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尽量弥补。当税务机关难以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弥补规则适用的缺陷时,税务机关也不得不做出一个充满着风险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作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主体,只能依据法律规定做出行政行为,即使因立法缺陷导致适用上的困难,也只能是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对规则进行阐明,不得逾越法律文本的含义,当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就法律适用达成和解协议时,这一协议充斥着滥用法律的倾向。司法机关作为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方,有权对税务机关适用法律的正确与否做出最终的判断。所以,笔者认为,税务机关在做出具体征税决定的过程中,应当将和解协议限定在“事实不明”的情形和法律授权下的行政裁量行为。
四、税务和解中行政处分权的限制因素
税务和解直接涉及财政收入、税收公平,故需要谨慎地设置这一制度,对其适用范围——行政处分权施以必要的限制。
(一)因“事实不明”达成的事实和解协议的限制因素
“事实不明”中“不明”状态应当是客观的不明,而不是主观的不明。一般来说,“事实不明”的客观标准不是以纳税人或税务机关任何一方为标准,税务机关对应税事实的认定应当与税务专业一般人的认识相一致。如果应税事实并未达到“事实不明”而双方和解,属于明显违法,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事实不明”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客观状态的不明,而且对“不明状态”有深度的要求,即“不明状态”应当以税务机关尽职调查为前提。当税务机关尽职调查后,仍不能确定应税事实时,或者经过尽职调查,预见继续调查成本大于可得收益时,可以就“事实不明”部分达成和解协议。若税务机关未经尽职调查就事实部分与纳税人达成和解协议,则属于职权滥用,此种情形下的和解不应当被允许。
(二)因行政裁量达成的税务和解协议的限制因素
自由裁量权的“自由”其实是法律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时采取的一种抽象化的法律技术[21]。现代行政权的核心是行政裁量权,通过行政法控制行政权的关键在于控制行政裁量权不被滥用,规范和控制行政裁量权是行政法最重要的功能[17]。行政裁量权的运用需要符合比例原则。具体来说须符合比例原则的三项子原则:适当性原则——因行政裁量达成的和解须实现税款征收与保障纳税人权利的目的;必要性原则——税务机关应当选择对纳税人权利最小侵害的方法施行税务和解;狭义比例原则——又称“均衡原则”,是指税务和解的实现过程中不应当过度侵害纳税人的权利,尽量实现税款征收与纳税人权利的均衡。
行政裁量权的形式需要结合实际情形才得以达到合理性的标准,如果将行政裁量权赋予的裁量幅度比喻成一个大圈,结合事实认定时的和解余地就是一个小圈,只有在小圈的幅度内,才能够达成和解。但是,因行政裁量权的幅度并没有绝对清晰的界限,裁量权内和解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更为多样,和解达到合理性的标准即可。现行法律也将和解范围限制为合理性的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判断是结合事实的判断,事实判断需要考虑的因素一般包括税务行政处罚中行为的违法程度、造成的实质损害、纳税人的补缴税款的行为等。
五、结语
税务和解得以达成的原因在于税务行政中存在事实不明和行政裁量。现行立法对税务和解的范围限于裁量性行政行为,在实质上缩小了和解的适用范围。税务和解不仅是对法律授权效果下裁量幅度的一种选择,更重要的是对基础事实的处分权,“事实不明”才是税务和解需要着力的点。税务和解的标的在于行政处分权,为防止权力滥用,需要对基础事实不明状态做出进一步的限定,同时立法也需要对自由裁量权的和解范围做出具体情形的限制。虽不能对此做到完全精确,但是可以具体列举的方式将立法本意含在具体法律中,便于执法者理解,不至于税务机关滥用行政裁量权。
[1] [日]金子宏.日本税法[M].战宪斌,郑林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08,102-103.
[2] 陈少英,许峰.税务争议替代性解决机制探析[J].北方法学,2008(5):81-94.
[3] 颜运秋.税务和解的正当性分析[J].法学杂志,2012(8):40-48.
[4] 张成.税务和解的法律界定[J].特区经济,2010(6):232-233.
[5] 陈春,张成.税务和解的法律价值与社会功能分析[J].特区经济,2010(9):262-263.
[6]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EB/OL].[2016-01-09].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501/20150100397930.shtml.
[7] 崔威.中国税务行政诉讼实证研究[J].清华法学,2015(3):135-155.
[8] 方军.英法行政复议及相关法律救济制度述评[EB/OL].(2007-04-18)[2016-01-09].http://www.procedurallaw.cn/zh/node/2639.
[9] 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419.
[10] 王泽鉴.民法概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447-448.
[11]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55-356.
[12] 叶金育.税务和解的法律要义:功能、标的与协议要件[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5):98-103.
[13] 盛子龙.租税法上和解契约与非正式协商[J].中正大学法学集刊,2015(1):116-147.
[14] 叶珊.应税事实依据经济实质认定之稽征规则——基于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12条之1的研究[J].法学家,2010(1):75-84.
[15] 张永忠,张春梅.行政裁量权限缩论——以税收和解适用为例[J].政治与法律,2011(10):31-40.
[16] 周佑勇.行政裁量治理研究——一种功能主义的立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48.
[17]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7,2.
[18] [日]盐野宏.行政法[M].杨建顺,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91.
[19] 尹建国.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模式构建——从“唯一正确答案”标准到“商谈理性”诠释模式[J].法学评论,2010(5):60-69.
[20] 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5.
[21] 靳羽.行政诉讼调解中的公众参与[J].人民司法,2011(5):75-80.
(编辑:李 红)
On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Tax Reconciliation
ZHAO Qun
(SchoolofLaw,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China)
According to China’s cur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the tax reconciliation is limited to the stage of reconsideration, which conforms with the reality of tax dispute settlement. The object of tax reconciliation is the administrative sanction right authorized by law, which restricts it to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and neglects fact-finding before making the administrative sanction. As there may be some “unclear facts”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s can have a choice, “unclear facts” can als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reconciliation scope; application of laws tends to legitimate authority and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statutory power. It is not proper for the situation that “there is no clear law” to be included in the tax reconciliation; tax reconciliation relates to the sanc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which must be strictly limited to the scope of its application.
tax reconciliation; administrative sanction right; the unclear facts;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2016-03-02
武汉大学税法研究中心和黄石地方税务局合作课题“税收管理现代化”(25000568)
赵 群(1990- ),女,湖北石首人,武汉大学硕士生,主要从事经济法、财税法研究。
D922
A
1009-5837(2016)04-0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