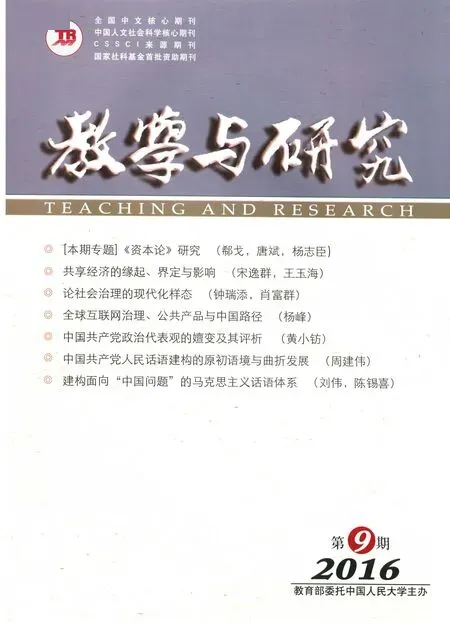全球正义的功利主义分析路径
——以彼得·辛格的理论为例*
高景柱
全球正义的功利主义分析路径
——以彼得·辛格的理论为例*
高景柱
全球正义;功利主义;援助义务;彼得·辛格
功利主义是全球正义理论的一种重要分析路径,彼得·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是其中的代表性理论之一,富裕国家对贫困国家所负有的“援助义务”是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的内核。虽然辛格曾回应了其全球正义理论面临的某些诘难,但是它仍然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中的将“拯救落水儿童的义务”扩展为“援助世界穷人的义务”这一关键论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对人们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他在回应其全球正义理论面临的批判时有时违背了其推崇的“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同时,预设了一种不恰当的责任观,面临着功利主义通常所面临的某些批判。
近年来,全球层面上的贫困、不平等和暴力等问题的加剧,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不少学者从诸多视角出发探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对全球分配正义理论各抒己见。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析路径是采取自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60年代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以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的强烈批判下,功利主义原先所拥有的那种在法学、哲学和政治学等领域所占据的一统天下的态势得以动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功利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毫无影响力的理论。为了回应罗尔斯等人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形态各异的功利主义逐渐在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不断涌现*现代功利主义包括规则功利主义(rule utilitarianism)、结果功利主义(outcome utilitarianism)和制度功利主义(institutional utilitarianism)等,具体研究参见Amartya Sen, “Utilitarianism and Welfarism”,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76, No. 9, 1979, pp. 463-489.。功利主义者既试图通过重新阐释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来应对其所面临的挑战,又试图通过介入堕胎、安乐死和全球贫困等实践伦理学中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来凸显自身的理论优势,将杰里米·边沁等古典功利主义者曾经为社会改革寻求合理的基础这一尝试发扬光大。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1](P1)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辛格的不懈努力下,功利主义成为分析全球正义理论的一种重要分析路径,同时全球正义的功利主义分析路径以及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在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愈发具有影响力。本文首先在简要介绍辛格的功利主义伦理观的基础上,探讨辛格是如何用功利主义来分析全球不平等问题的,然后关注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所面临的批判及其回应,最后分析以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为代表的全球正义的功利主义分析路径的得与失。
一、辛格的功利主义伦理观
在探讨辛格的用于分析其全球正义理论的功利主义伦理观之前,我们应当首先关注辛格对伦理相对主义和伦理主观主义的批判,因为这是辛格的功利主义伦理观的重要起点之一。伦理相对主义意为那些适用于所有人和所有地方的伦理判断是不存在的,伦理判断的客观性或有效性只是相对于社会的文化、传统或实践而言的。辛格曾以性行为和奴隶制为例来探讨伦理相对主义,倘若一种随意的性行为孕育出了无法得到悉心照料的孩子,该性行为就是错误的;倘若采取了有效的避孕手段而不至于怀孕,该性行为就没有什么值得谴责的。在辛格看来,这种相对主义非常浅薄,19世纪开始出现了另一种伦理相对主义,它认为“不仅19世纪欧洲的道德准则不是客观有效的,而且一切道德判断都只不过是在反映其赖以形成的社会习俗。”[2](P5)倘若有两个社会,其中一个社会反对奴隶制,另一个社会为其辩护,依照伦理相对主义,上述两个观点并不冲突,当一个人说奴隶制错误时,他只是在说其所在的社会反对奴隶制;当另一个人声称奴隶制正确时,这个人也只是说其所处的社会赞成奴隶制。显而易见,今天已无人为奴隶制进行公开辩护,伦理相对主义的上述立场是不可被接受的。伦理主观主义声称伦理判断依赖于判断者自身是否持有一种赞同的态度,辛格认为它面临着与伦理相对主义同样的困境。例如,当某人声称对妇女的歧视行为是错误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在言说自己并不赞成歧视妇女,伦理主观主义无法有效解释各种伦理判断之间的分歧。虽然斯蒂文森(C.L.Stevenson)等人所倡导的非粗陋的伦理主观主义可以免受上述反驳,但是伦理主观主义“否认在真实世界中有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伦理事实——就此而论,它们无疑是正确的。可是,我们能否由此推论说,伦理判断可以免受批评,没有必要在伦理中诉求理性或论证,或者,从理性的角度看,任何伦理判断都与其他伦理判断一样好?我不认为可做这种推论。”[2](P8)辛格就探讨了一种理性在伦理决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伦理观,即功利主义的伦理观。
辛格认为自古以来,诸多哲学家就一直在主张伦理行为是那种从普遍的视角看能够被人们接受的行为,这种理念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历久弥新。譬如,依照黑尔的说法,“我们的判断必须是‘可普遍化的’(universalizable),才算是道德的判断。他的意思不是指这些道德判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他指的是,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在不考虑我们扮演的角色的情况下,来描述它们——这也包括在不考虑运用它们是否让我们得利或受损的情况下,来描述它们。”[3](P184)对辛格来说,这意味着我们要过一种合乎伦理的生活,意味着我们在伦理思考的最根本的层面上不能仅仅考虑我们的家人和朋友的利益,也要考虑我们的敌人以及陌生人的利益,功利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伦理观,只不过辛格所认可的功利主义是一种基于利益的功利主义,而不是古典功利主义。依辛格之见,一旦我们认可伦理判断必须源自不偏不倚的视角,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不能因为某种利益是自己的,其重要性就超过了他人的利益的重要性。虽然每个人都有追逐私利的本性,但是一旦我们进行伦理思考时就必须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视角,将对自己利益的关照推广到他人的利益身上,当然,这种不偏不倚的视角并不意味着人们从中得出的伦理判断也必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在进行伦理思考时,不能仅仅因为某种利益是自己的利益,其重要性就要超过他者利益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抉择呢?辛格认为我们在进行伦理判断时,不得不将自己的行动所影响到的所有人或动物的利益都纳入考虑的范围,而不是仅仅考虑自己的私利或者人类的利益:“许多哲学家与其他的作者,在不同的形式下都曾提出对利益的平等考虑这项原则,以作为基本的道德原则;但是他们中间没有几个人看出,这项原则对其他物种与人类一样适用。”[4](P9)也就是说,辛格此时采取了一种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这种原则也是辛格所认可的功利主义伦理观的主要组成部分。
辛格认为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的本质在于“在伦理慎思中,我们要对受我们行为影响的所有对象的类似利益予以同等程度的考虑。这意味着,如果某一可能的行动只影响X和Y,并且如果X的所失要大于Y的所获,那么,最好是不采取这种行动。如果接受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我们就不能说:尽管有以上描述,但由于我们关心Y超过关心X,因此这样行动就好于不这样行动。该原则的真实含义是:被平等考虑的利益不因是谁的利益而有所不同。”[2](P22)辛格接下来还认为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要求人们要不偏不倚地权衡各种利益,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利益”上,而不是放在“谁”的利益上,因此,它成为一种能够为人人平等进行辩护的原则。辛格所推崇的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包括哪些利益呢?辛格认为“人的最重要利益并不受智力差异的影响,这些最重要利益包括:避免痛苦,发展自己的能力,对于食品和住房等基本需求的满足,享有亲密的私人关系,享有不受干涉地追求事业的自由,以及其他许多利益。”[2](P31)在辛格那里,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是平等原则能够唯一获得辩护的基础,它使得我们能够捍卫那种涵盖了人类所有成员的平等形式,无论人们之间存在的差别是什么,同时,虽然人与人之间存在诸多差异,比如人们在财富和国籍等方面是不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是不平等的。虽然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受到了很多哲学家的拥护,但是只有边沁将其适用于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认为动物具有感知能力,能够感受苦乐,因此人类不应残忍地对待动物。[5](P349)辛格继承了边沁的观点,在其《动物解放》中就探讨了如何将功利主义原则应用于动物身上,认为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而且这种平等与人的国籍没有关系。辛格正是将这种作为功利主义伦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用于分析全球正义问题,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以援助义务为内核的全球正义理论
辛格之所以关注全球正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对全球贫困和全球不平等的深刻洞察密切相关:“世界60多亿人口中的大约1/5,或者说大约12亿人,每天靠不到1美元维持生活……在这12亿人中,大约8.26亿人缺少足够的营养,有超过8.5亿的人是文盲。”[6](P78)面对世界上的绝对贫困的赤裸裸的现实,发达国家采取了什么行动呢?发达国家确实进行了某种援助,但是这种援助在辛格看来是远远不够的。那些主张偏好自己同胞的人认为国家的边界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认为人们对其孩子、配偶、爱人、朋友以及同胞负有一种特殊的义务,并认为这一观点是不证自明的,不过辛格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比如针对西季威克等人所说的白人应当优先关注其他白人的利益等观念在当时所具有的吸引力非常类似于我们有义务偏爱自己的家庭和朋友这种观念的直觉吸引力,“但是种族主义观念已经造成了我们这个世纪(指20世纪)的许多最坏的罪行,而且很难看到它们带来了多少好处,它们对补偿所造成的灾难确实是没有什么益处的。……采取一种公正视角表明沿着种族路线的偏私主张,是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加以反对的。”[6](P165)在辛格那里,在目前世界上严重贫富分化的情况下,富裕国家的公民对外国人的义务要超过对同胞的义务。
辛格曾用了一个著名的、在其很多著作中反复提及的有关“拯救落水儿童”的思想实验来反驳上述偏爱同胞的观点。[7](P231)辛格首先确立了人们不会提出异议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由于缺乏食物、住所和医疗保障所遭受的苦难和死亡是坏的;第二,倘若预防某些坏的事情的发生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并不会因而牺牲掉任何具有类似的道德重要性的东西,那么从道德上而言,我们就应该那么做。辛格设想,假如M在经过一个非常浅的池塘的旁边时,发现一个小孩掉进去了,并意识到这个小孩有被淹死的危险。倘若M伸手去拉那个小孩,那个小孩就会得救,虽然这会弄湿M的衣服或者耽误了M的一场演讲;倘若M不施以援手,那个小孩将会被淹死。辛格认为根据上述两个原则,M应该去救那个小孩,对辛格而言,如果我们从一种不偏不倚的视角出发,那么我们就不能因为一个人离我们较远而进行区别对待。有人可能反驳道说当穷人离我们较近时,我们应当优先给予援助,而且可能更好地判断穷人到底需要什么。在辛格看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某种组织或技术就可以直接将援助送到饥民手中,而且可以像援助我们的同胞那样快捷,因此,因为距离的原因而进行的区别对待是不可行的。因此,对辛格而言,倘若预防一些非常坏的事情的发生是人们力所能及范围内的事情,且不会因此牺牲其他任何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从道德上而言,人们应该去做。
在辛格那里,国家的边界并不像其辩护者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根本的道德重要性。辛格还从“拯救落水儿童”这一思想实验推导出富裕国家对贫困国家所负有的援助义务,这一论证也是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的关键论证之一。他认为,一旦我们认真执行“在不牺牲有类似的道德重要性的事情的前提下去阻止恶”这一原则,那么我们的生活和所处的世界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个原则不仅适用于拯救池塘落水儿童的情况,而且还适用于援助绝对贫困者的情况。假设那些表现为饥饿、文盲、无家可归、疾病、较高的婴儿死亡率以及较低的预期寿命的绝对贫困是一种恶;假设减少绝对贫困是富人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事情,而这又不会牺牲道德上具有类似重要性的事情。对辛格来说,上述原则和这两个假设在一起就使得富裕国家对贫困国家负有一种援助义务,如果富国不提供帮助,就是错误的,正如M不去拯救那个落水儿童就是错误的一样。辛格曾用一种更加明确的方式表达了其对援助义务的论证:“前提一:如果我们能够阻止恶,而又不至于牺牲在道德上具有类似重要性的事情,那我们就应该去阻止。前提二:绝对贫穷是恶。前提三:我们能够阻止某些绝对贫穷,而又不至于牺牲在道德上具有类似重要性的任何事情。结论:我们应该阻止某些绝对贫困。”[2](P226)在辛格那里,前提一和前提二较少有争议性,能够被那些持有不同道德立场的人所接受,只是前提三有着较多的争议性,前提三仅仅是在主张阻止某些绝对贫困而又不至于牺牲道德上某些具有类似重要性的东西,它能够避免一个人所能给予的援助对缓解世界贫困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一反驳,因为前提三的关键之处在于一个人所能给予的援助是否能够阻止某些贫穷的发生或恶化,而不是是否能够明显改善世界的贫困状况。因此,依辛格之见,前提三也是可以接受的,辛格就通过上述方式完成了对援助义务的论证,认为我们不能认为人们对其邻居和同胞负有特殊的义务而对外国人没有特殊的义务。
以上我们探讨了辛格是怎样由拯救落水儿童的义务扩展为援助义务的,那么,富裕国家应该对贫困国家援助多少呢?辛格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提出了援助标准。就理论层面的标准而言,辛格继续采取了一种后果主义的思路,他认为“我们给予的捐赠应该一直到边际效用的水平上,也就是说,通过给予更多的捐赠,我将我自己或者那些依赖我的人也几乎遭受同样的苦难这样的水平上。”[7](P241)辛格随后还提及了那些能够预防坏事情发生的强版本和更加温和版本的策略,前者认为我们应该预防坏事情的发生,除非这样做将使得我们牺牲某些在道德上具有类似重要性的东西(something of comparable moral significance),而后者要求我们应该预防坏事情的发生,除非这样做,我们不得不牺牲某些道德上重要的东西(something morally significance),对辛格而言,强版本的策略是一种可行的策略。辛格在实践层面对国家和个人提出了不同的标准,就国家应当提供的援助而言,辛格援引联合国所确立的最低标准,即国民生产总值的0.7%,在辛格看来,这一标准并不高,但是只有瑞典、荷兰、挪威和一些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等少数国家达到了这一标准。[2](P217)就个人应该提供的援助而言,辛格认为一种比较容易实现的目标是“那些在经济上比较宽裕的人大概应该捐赠年收入的5%。”[8](P152)对辛格来说,只要国家和个人的援助达到上述比例,全球贫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缓解。
三、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面临的批判及其回应
依辛格之见,富裕国家对贫困国家负有一种援助义务,倘若富裕国家没有帮助贫困国家,这使得贫困国家中的不少人身处困境甚至极端危险之中,富裕国家就正在做一些错误的事情。正如我们在上文曾指出的那样,辛格将拯救落水儿童的义务扩展为“援助义务”,这一扩展也是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的核心部分,辛格的这一论证是可以接受的吗?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面临着不少批判,辛格进行了回应。
第一,有人认为援助义务是一种慈善的行为,而不是一种义务,这并不纯粹是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所面临的批判,而是很多全球正义理论面临的批判。依照该批评意见,既然援助是一种慈善的行为,倘若一个人进行援助的话,他就应该受到表扬;然而,倘若某人不拥有慈善之心,他也不应该受到任何谴责,他的行为并不是错误的。针对这种批评意见,辛格认为我们应当重新划分慈善与义务之间的界限,传统的划分慈善与义务之间界限的方式使得那些发达国家中的富人的援助行为被视为一种慈善行为,这一划分方式是得不到辩护的。辛格依照功利主义的思维论证道,当一个人购买新衣服的目的不是出于保暖的目的而是出于好看的目的时,这个人并不是在满足一种重要的需要。捐钱能够解决饥荒问题,这个人应当捐款,而不是将其用于购买一件并不是用于保暖的新衣服,否则,就是错误的,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从一种不偏不倚的伦理立场来看,人们应当超越自己的利益来看待问题。[7](P235)显然,辛格的援助义务给人们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第二,个人不提供援助在道德上并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同时援助穷人是政府的责任而非个人的责任。科林·麦金尼(Colin McGinn)是前一种批评意见的代表之一,辛格曾提出了人类应当担负如下两种义务:一种义务是缓解动物的痛苦,停止杀戮,另一种义务是减缓世界上的穷人和饥民的痛苦,麦金尼认为只有前者是可以接受的。为了支持该观点,麦金尼让我们考虑如下两种论证,论证A认为:(1)让动物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在道德上是错误的;(2)我们确实给动物带来了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因此,(3)我们确实在道德方面对动物犯了错误。论证B认为:(1)让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在道德上是错误的;(2)我们确实让人遭受了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因此,(3)对那些正身处痛苦之中的人和那些将死之人来说,我们在道德方面确实犯了错误。在论证A中,动物遭受的痛苦包括吃动物、打猎和活体解剖等等,在论证B中,一些错误的行为包括不捐款帮助世界上的饥民和穷人等等。麦金尼认为论证A是合理的,论证B并不合理。[9](P150)“援助穷人是政府的责任而非个人的责任”这一批评意见认为既然国家的对外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个人就不应从事对外援助,否则,政府会逃避自己的援助义务。辛格认为该观点看起来是在说倘若个人的海外援助越多,政府所承担的援助责任就会越少,然而,这种观点难以获得辩护。相反,倘若个人不进行海外援助,其政府就可能认为公民对帮助其他国家的公民不感兴趣,也会相应地减少海外援助。同时,很多人往往将“这是政府的责任”作为自己不从事任何援助的一个借口,[7](P239)并不会将其作为自己应该非常积极地采取援助行动的理由。正如我们在上文曾提及的那样,很多富国的海外援助总量远远低于联合国所设定的国民生产总值的0.7%,无论个人还是政府,都应提高海外援助的数量。
第三,人们应当优先照顾自己的亲人及同胞,然后才会考虑他国的穷人,而援助义务恰恰违背了这一立场。为什么人们应当对自己的同胞负有特殊的义务?一种观点认为个人与其同胞都参与了某种集体的事业,埃蒙·卡伦(Eamonn Callan)就持有这种立场。[10](P96)辛格回应道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共同体成员之间往往缺乏直接联系,这使得人们与其同胞之间的相互性义务受到削弱,虽然我们很容易理解人们往往将对其同胞的义务置于对他国的公民的义务之前,但是这并不是将对自己的同胞的义务置于他国公民的非常迫切的需要之前的充足理由,“大多数公民生来就是某个国家的成员,而且他们中许多人很少关心国家的价值和传统。有些人也许还拒斥它们。而在富裕国家的边界之外,则有数百万难民极想得到成为这些国家共同体的一部分的机会。没有理由认为,如果我们允许其进入,他们在报答从共同体得到的各种利益时,一定比土生土长的公民做得差。”[6](P171)因此,对辛格来说,人们并不能仅仅以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为由对同胞的特殊义务进行辩护。实际上,辛格对第三点反对意见的回应主要诉诸于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认为毫无疑问人们会有一种优先帮助与自己关系密切之人的利益的本性,但是这并不能使得人们对与自己亲近的人的义务与对他国之人的义务有实质性的差别。
第四,援助义务会促使贫困国家的人口增长过快,进而将会产生更多的穷人。辛格认为依照上述反对意见,最为彻底的解决思路在于采纳战争时期的“筛选”政策:“由于医生太少,无法处理所有的伤员,就只得把伤员分成三类:无医疗救助也有可能存活的,有医疗救助才可能存活的,即使有医疗救助也不大能存活的。只有中间那一类才能获得医疗救助。”[2](P230)筛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最大效率地利用稀缺的医疗资源,对第一类和第三类伤员来说,救助都不必要。依照同样的逻辑,援助义务的对象应该是那些获得援助后能够在食品供应与人口增长方面取得平衡的国家。倘若世界人口持续增长,应该怎么办?筛选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人口不会持续增长,它会因为出生率下降或死亡率上升而受到遏制。对辛格来说,筛选理论所带来的后果非常可怕,只是筛选理论正确地考虑到了援助行为的长远后果,这与辛格的立场较为契合。辛格认为筛选理论的软肋在于其立论基础,没有将结果出现的概率纳入考虑的范围。实际上,人口不会无限增长,当人们贫穷时,繁殖能力确实强,当人们摆脱贫困后,避孕等手段会被广泛使用,人口增长率会慢慢下降。因此,“人口增长不是反对海外援助的理由,……也许这就意味着我们为农村的贫困人口提供农业援助、教育援助或提供避孕措施的服务。”[2](P235)可见,在辛格那里,那种以人口增长为由来反对援助义务这一观点是不合理的。
四、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的得与失
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是一种较为可行的全球正义理论吗?它的得与失何在?首先我们来看看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的积极意义。第一,在辛格的努力下,功利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正义理论的重要分析路径之一。虽然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对功利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功利主义已无人问津。辛格在1972年发表的《饥荒、富裕与道德》一文中正是以功利主义为主要分析工具,建构了一种以援助义务为内核的全球正义理论,并在《实践伦理学》等著作中进一步完善它。正是在其努力下,功利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界公认的全球正义理论的主要分析路径之一。第二,在一个利己主义的时代,辛格倡导了一种不偏不倚的伦理观。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在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时,要求人们过一种伦理生活,伦理生活要求我们不能纯粹关注个人的享乐与满足。第三,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呼吁人们关注世界上的贫困人口,呼吁发达国家及其人民提高对穷国人民的捐赠,倘若那些绝对贫困之人获得的援助能够得到提升,世界贫困无疑会获得极大程度的缓解。
虽然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它仍然会面临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作为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的核心论证之一,辛格由“拯救落水儿童的义务”扩展为“援助世界穷人的义务”会面临着一些困难。譬如,在查尔斯·琼斯(Charles Jones)看来,辛格的拯救落水儿童这一思想实验涉及了个人实现善的义务,比如拯救落水儿童,在大多数情况下,拯救落水儿童是一种义务,即使它可能要义务承担者做出部分牺牲或冒险,但是辛格依照同样的逻辑认为“富裕国家中的人们应该尽力挽救那些贫困国家中的穷人,否则,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这些穷人将会饿死。这种有争议性的思路存在的问题在于它针对的富裕国家中的个人,正是这种特征使得援助义务对人们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这一反对意见具有可信性。”[11](P36)辛格在上述扩展中所采取的论证是一种“类比论证”,类比论证存在的关键问题是被用于类比的双方或多方,是否具有逻辑上的相似性或者事实上的相似性,否则,就不能得出相同或相近的结论,辛格的类比论证就存在这一问题。“拯救落水儿童”和“援助世界上的穷人”这两个事例是不同的,当有人看到一个儿童掉进一个浅浅的池塘时,很多人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救上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会接受辛格所说的援助全球穷人的义务,原因主要在于“拯救落水儿童”和“援助世界上的穷人”是极为不同的:一方面,在前者中,只有一个孩子落水和一个路人经过,救援的对象和实施救援者都是非常明确的,而在后者中,世界上有很多穷人,而且援助全球穷人的责任是一种集体责任;另一方面,在前者中,路人只有伸手,落水儿童必将被救上来,而在后者中,单个人的努力是否能够帮助到全球穷人,是非常令人怀疑的。
其次,辛格在谈到援助义务时所提及的“类似的道德重要性”这一概念非常模糊,对人们提出了一种过高的要求。在麦金尼看来,类似的道德重要性是指遭受的痛苦在类型和数量方面具有相似性。比如M1必须使得自己在做出牺牲时,M1付出的成本少于M1给捐赠对象带来的收益,比如为了减少穷国的某些孩子的痛苦,M1应该使自己的孩子不上大学,不去看电影等。麦金尼认为辛格将要求人们做出上述牺牲,在辛格那里,虽然上大学或看电影都有内在价值,但是它们没有由放弃这些行为所能减缓的痛苦重要。类似的道德重要性致力于拉平世界上的痛苦程度的水平,提出了一种非常强的要求。麦金尼认为该观点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假如M2是一位貌美的女性,受到很多男性喜爱,M2可以轻易满足倾慕其的男性的欲望。M2可以同他们交往以减轻他们的痛苦,比如每天同10个人交往。假设M2能够如此行动,并没有使自己感到痛苦,因此,M2可以如此行动,并没有使自己的福祉降低到相应的程度上。M2愿意这么做吗?M2当然不愿意。[9](P154)当然,辛格可以回应道麦金尼的例子过于极端,其援助义务不需要人们做出如此的牺牲。那么,它要求人们做出何种牺牲呢?辛格认为人们应尽可能地捐助,直到仅仅能够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为止,其中的原因在于“金钱的边际效用递减”假设。[3](P55)该观点可行吗?实际上,它值得商榷,因为边际效用递减这一假设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依照该假设,一个人所拥有的金钱越多,他能从1元钱中获得的满足越少,其所获得的满足少于乞丐从1元钱中获得的满足。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它并不成立,比如某人想购买一台标价5 000元的电脑,他只有4 999元,并不能购买电脑,倘若他又获得1元钱,无疑其需求会获得满足。
再次,辛格在回应其全球正义理论面临的批判时有时违背了他自己推崇的“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比如辛格在回应从人口增长的角度对其援助义务的批评时曾碰到一个麻烦问题:倘若某个穷国已经人口过剩,但是由于宗教或民族方面的理由,它限制避孕措施的使用并拒绝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富裕国家是否在提供援助时,增加一些诸如降低出生率的附加条件呢?在辛格看来,这种强加能够获得辩护。即使如此,辛格认为倘若援助义务没有减少绝对贫困的可能性,“我们就没有义务援助这样的国家,其政府制度的政策会使我们的援助失败。对于这些国家的贫穷公民来讲,这也许显得过于残酷,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但只有最大效率地使用我们的资源,从长远来看,我们才能帮助更多的人。”[2](P236)我们姑且不探讨在提供援助时附带附加条件是否合理,仅仅关注辛格所言的不援助那些不愿意采取措施限制人口增长的贫困国家。实际上,辛格的上述观点违背了其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为什么贫困国家中的公民仅仅因为其政府的不当政策而丧失了获得援助的资格?为什么他们的利益不能获得平等的考虑?这些人往往对政府的政策缺乏发言权,而且可能还受到政府的压制。倘若我们认可辛格的上述立场,我们就等于承认一些人应当对不是由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负责,这不但与人们的道德直觉相悖,而且也有悖于辛格对运气因素的看法。一个人生活在何种政府的统治下,往往并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倘若某个人要对不是因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不利境地负责,显然有失公允。
最后,由于辛格在建构其全球正义理论时采取了非常负有争议性的功利主义分析路径,因此,辛格的理论也面临着功利主义所面临的批判,比如倡导了一种不合理的责任观。正如上述所言,辛格认为富裕国家对贫困国家负有援助义务,倘若富国拒绝提供帮助,它要为穷国中的人所受的痛苦负责。这种责任观是可以接受的吗?我们可以借用威廉斯的思想实验来探讨该问题:吉姆来到南美某个小镇的中心广场上,20个印第安人被捆绑着。上尉向吉姆解释道这些人胡作非为,正等待被处决。然而,由于吉姆是一个外来者,应当受到尊重,上尉给予客人杀死一个印第安人的机会。倘若吉姆接受了该要求,其他印第安人将被释放。否则,所有印第安人将被处死。那些印第安人和围观群众都恳求吉姆接受该“荣耀”。吉姆应当怎么做?依照功利主义的逻辑,吉姆应该接受它。倘若吉姆拒绝了上尉的要求,印第安人的亲戚就可能抱怨吉姆,他们的亲戚本来有机会活下来。吉姆要为印第安人的死负责吗?显然不应该。[12](P108)同样,在辛格的论证中,当一个富人没有将钱捐给一个贫困国家中的穷人时,即使该穷人要承担极大的痛苦,该富人也不应该为该穷人所受的痛苦负责。当然,倘若穷国的贫困是由他国的殖民造成的,那么宗主国应该对穷国的贫困负责。可见,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预设了一种不恰当的责任观,仍然面临着功利主义通常面临的某些批判。
五、结 论
以上对以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为代表的全球正义的功利主义分析路径进行了一种批判性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辛格在批判伦理相对主义和伦理主观主义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功利主义的伦理观,该伦理观倡导从一种不偏不倚的视角出发思考问题,认为虽然每个人都有追逐私利的本性,但是一旦在进行伦理思考时就必须将对自己利益的关照推广到他人的利益身上,即主张一种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第二,辛格将功利主义伦理观用于分析全球正义问题,认为国家的边界并不像某些民族主义者或爱国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根本的道德重要性。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的关键论证是由拯救落水儿童这一思想实验推导出富裕国家对贫困国家所负有的援助义务,援助义务也是其全球正义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第三,虽然辛格回应了其全球正义理论面临的以及可能面临的某些批判,但是其全球正义理论仍然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辛格的由“拯救落水儿童的义务”扩展为“援助世界穷人的义务”这一关键论证不能令人信服;他在回应其全球正义理论面临的批判时有时违背了其一直推崇的“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同时,其全球正义理论预设了一种不恰当的责任观,仍然面临着功利主义所通常面临的某些诘难。
[1] Dale Jamison. Singer and His Practical Ethics Movement[A]. in Dale Jamison (ed.).Singer and His Critics[C].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9.
[2] [美]彼得·辛格. 实践伦理学[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3] [美]彼得·辛格. 生命,如何作答——利己年代的伦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 [美]彼得·辛格. 动物解放[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5] [英]边沁.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美]彼得·辛格. 一个世界——全球化伦理[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7] Peter Singer. 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J].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 No.3, 1972.
[8] Peter Singer.The Life You Can Sav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10.
[9] Colin McGinn. Our Duties to Animals and the Poor[A].in Dale Jamison (ed.).Singer and His Critics[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9.
[10] Eamonn Callan.Creating Citizens: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Liberal Democracy[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11] Charles Jones.Global Justice: Defending Cos-mopolitanis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 Bernard Williams. 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 [A]. in J.J.C.Smart and Bernard Williams(eds). 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C].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责任编辑 刘蔚然]
On the Utilitarianism Approach of Global Justice——A Case Study of Peter Singer’s Theory
Gao Jingzh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Culture,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global justice; utilitarianism; assistance obligation; Peter Singer
Utilitarianism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of global justice, and Peter Singer’s theory of global justice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theories. The assistance obligation of rich countries to poor countries is the core of Singer’s theory of global justic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Singer’s theory. Singer thinks that since we have the obligation of saving the drowning child, we have the obligation of helping poor people in the world. This is a key argument in Singer’s theory of global justice, but it is not convincing. To some rich countries or persons, Singer put forwards some higher requirements, and he has a kind of inappropriate responsibility view.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全球正义理论跟踪研究”(项目号:14CZZ004)和天津市“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高景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副教授(天津 300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