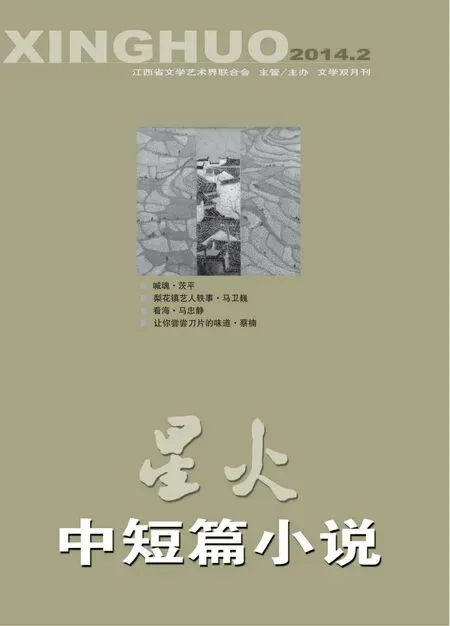日线
○阿贝尔
日线
○阿贝尔

阿贝尔,本名李瑞平。一九八七年开始写作,作品刊发于《天涯》《花城》《大家》《上海文学》《散文》等期刊。出版散文集《隐秘的乡村》《灵山札记》及长篇小说《老屋》。现居四川平武。
艄片子
早年涪江里的筏子很大,由一色的原木扎成。维系原木的是一些铁丝、钉牛和青杠棒。原木都出自岷山丛中的小河沟、火溪沟和王坝楚。我不只是站在河岸上看筏子,也走到泊在河边的筏子上去,从一根木头跳上另一根木头。原木很大,原木和原木之间并不都是紧挨着,有的地方隔着几搾远,中间是蓝蓝的河水。特别是钉牛松动的地方,水面要更宽。
王光朴家门前是停筏子的地方,经常看见停着一边边筏子。王光朴家门前头下去,是赵家浪上,上去一里是锅坨漩。走锅坨漩出来的筏子,或多或少都要带点伤,王光朴家门前那一大片平静的水域是修整的良港。修整需要加换一些青杠棒,而我们这地方盛产青杠树,所以时常有人偷偷砍一些卖给筏子客。
被我忘记了的是筏子上的艄,应该就是舵,前后各有一个,由碗口大的原木做成,固定在一个木架上,活动自如。艄的末梢都做成一个桨的形状,我们叫艄片子,像鱼的尾巴,要的正是鱼尾巴在水中游动的功效。艄是用以掌握筏子航向的东西,下滩时特别管用。
我们家门前便是一个长滩,看筏子下滩是我的家常便饭。缓水里一个人掌艄即可,下滩则要三四个人。前头三四个人,后头三四个人,使劲地扳动着艄片子,喊着号子,吆二喝三地冲进白浪。通常浪子都是很大的,淹没了整架筏子,上头的人只露着上半身。而今记起,筏子上的人像是在滑雪。
滩是一段飞流的水域,英国人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在他的《扁舟过三峡》一书里有过最为详尽的描写。它埋伏着暗礁,稍有大意便可能发生危险。我们家门前的滩上既有暗礁也有明礁,都是石灰石,所以每一架筏子从不敢大意,筏子客抱艄的动作和站姿都显得一丝不苟,表情也颇为严峻。冬季水落石出,筏子搁浅的事情屡见不鲜,而夏秋两季水流丰沛,折断艄片子的事情时有发生。
一架筏子从岩背后下来,要经过柳林子、倒角里、短坑里三个滩,以及笼嘴包、菜包石和锅坨漩三个漩涡,才到王光朴家门前。在这一公里多的水路里,艄片子很少有闲着的时候。掌艄既是一件体力活,也是一件需要整个团队拼命的事。往往是八九架、十几架筏子一路漂流,其阵势完全是在演奏交响乐——滩上的筏子、缓水里的筏子、漩涡里的筏子彼此交替变换,运行在涪江流经我们家门前的这一段乐章里。
至于艄的状态,我还是喜欢它拖在缓水里的样子。懒懒地,在碧蓝的水域里划着,划着,节拍如慢板,艄片子与水的关系不是击节,而是鱼水情。
艄架在岸边的石头上晾晒,也是一种很美的状态。水晒干之后,艄片子雪白,上面的伤痕清晰可见,让人想起打烊的小酒馆和退役的老兵。
放炮
放学的路上总是遇到放炮,不让过。便躲在石墙背后或者核桃树底下,等炮响。沟渠里是乱石窖,房子大的石头都有,现在要农业学大寨,把石头炸烂、拉走,改造成庄稼地。沙石裕敢问青石板要粮,沟渠里也敢。
上学路过便看见打炮眼,“嘀咕儿——闹咕儿”响成一片。还有姑娘家在打炮眼,也“嘀咕儿——闹咕儿”,都叫她们“铁姑娘”。她们不只会掌钢钎,也会使二锤,甩开膀子大干。
又吹哨子了——准备点火。刚才吹哨子,才开始装药、装雷管和导火线。三四个人同时点火,每人负责一块石头,点完便跑。我们以为他们会朝我们这边跑,结果他们全跑到杨逢春家门前头去了。他们跑我们也跑,一边跑一边想象石头满天飞的情景,像雁群,砸下来像炸弹。我们离放炮的地方够远了,还跑。
从点炮的人跑完到炮响有一个过程,大约几十秒。这个过程是一片死寂,人们都抬着头望着炮区,炮区上头真有大雁飞。
炮响了。先看见烟子起来,再听见响声。点炮的人在数数,一炮、两炮……五炮,我们也在数数。看见石头随烟子腾起,飞过来,有的砸中了核桃树,有的就落在前面的人脚边。“狗日的敢放抬炮!”有人骂。抬炮是最厉害的,可以把抱大的石头从沟渠里抬到桂香楼。有一回放抬炮,把杨逢春家的瓦屋打得跟漏筛一样。相对巴炮比较安全,药装在石头上面,力是朝下的。放炮数数,是看有没有哑炮,有几个哑炮。有哑炮,得去排除。数绝对不能数错,数错了,哑炮一响,场面会非常地惨。不时听见大人回来摆,某地哑炮又响了,把人炸成了几节子,把一条腿炸飞到了河对面,把肠子炸飞出来挂在了桑树上。
在龙嘴包建石灰厂烧石灰的那几年,我们家门前天天放炮。大河两岸都是水牛大、房子大的石灰石,炸小了才有法运。先是在煮水潭对面的柳林子,然后是菜包石,再后来就到了我们家对面的倒角里。
站在挑水路,可以看见柳林子、菜包石放炮,烟子起来一阵才听见炮响。烟子不像沟渠里放炮的烟子,乳白里带一点青。很多时候放的都是抬炮,石块四溅,有的石块像老鹰要在天上飞很久才掉下来。
有时正在做事情,突然间炮响了,吓一大跳,手里的东西都吓落了。有时人在背静的地方,看不见放炮,炮响过很久了,还把天上的鸟当成飞石去躲。石灰石放抬炮的声音很大,且不只是放一两炮,通常都是放四五炮六七炮,那阵仗如同天垮了下来。
在倒角里放炮之前,没有人通知我们河对面的人要躲起来。起先我们还站在河坎上瓜扯扯地看,直到看见飞石像雁阵一样扑过来,我们才往回跑。要炸的石灰石就在对岸河边,有的是在水里,离我们站的河坎不过百十米。我们看对岸的人打炮眼、装药、点炮、跑炮,看烟子腾起来,接着是天垮下来。后来我们不敢看了,看到点炮便往回跑。跑到石墙根还不行,跑到竹林也不行,一直跑到房子底下。炮响了,飞石落到了石墙外的秧田里,有一块甚至落进了竹林。“好险,幸好跑!”我们在房子底下庆幸,一块飞石突然间落到了房顶上,砸烂了好几匹瓦。以后再放炮,我们便听了大人的话,不仅要往房子底下跑,而且要往镇了楼板的房子底下跑。
日线
胡家坝依山傍水,水的对面是更大、更高的山。出太阳时,日线特别清晰。看日线是一件很销魂的事。尤其是初夏的早晨,山田翠绿,江水青绿,天空碧蓝,日线沾着露水,从天边的陶家山下来,下到梅子坪,下到宝丰,下到沙渠里。如果我是在龙嘴子看驴子,日线七点半就到了我的脚边;如果是在短坑里,便要等到八点左右。
太阳从錾子岩顶上出来,最后照到的便是錾子岩下面的锅坨漩。我站在锅坨漩对面的短坑里看日线从陶家山下来,从我们村后山的梁包上下来,到了龙嘴子,到了大柴林,到了山羊盖,到了挑水路,到了青皮树底下,到了水磨坊,到了我经常睡觉的灰光石……日线落在房背上,落在豇豆架上,落在竹梢,都是金灿灿的;日线在青杠林里移动,在秧田里移动,在江面移动,在石窖和沙滩上移动,带给我的又是不同的感觉。它是一道金环,一条彩线,它投下的完全是錾子岩脑壳上山峰的形状。
有的早晨,我一直站在秧田埂上,等到日线落在脚边。我会很好奇地蹲下去看日线,看日线里的内容——韭菜一样的嫩草,嫩刷把签,又嫩又肥实的水葵,冲动的蚯蚓……它们都沾满露水,湿淋淋的。
初夏每一个晴朗的早晨,我都是在等日线过来,都在目接日线。在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的感觉里,日线里面是一个世界,日线外面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明亮,温暖,美丽;另一个阴暗,湿润,冰冷。日线移过来,阳光照在身上,感觉真的很暖和,手板儿脚板儿因露水过敏而生的红斑和瘙痒也消失了。
我还会依照日线来看时间,免得婆婆拐着脚下河来喊。通常是日线走到我经常睡觉的灰光石,我就该回家吃早饭了。
日落时也会在山林、河滩、田野划出一道日线,与早晨走着大致相同的路径,不同的是这时的日线是收,铺开的是阴影。
火地
砍倒一片原始森林,放一把火烧了,开出来的就是火地。
药地坪是我们生产队开的最大、也是最远的火地。天晴时走到三秦庙,才能看见药地坪。药地坪海拔两千多米,十天有八天都罩在云雾中。
我吃过火地里种的萝卜、包儿白。吃包儿白的时候,大人总会唱:“包儿白(发音be),包又白,包个婆娘莫出息(发音xie)。”如果你刚刚剃了光头,大人唱的时候还会摸着你的光头搔你。
我看过刚刚砍的火地,刚刚烧的火地——就是一块伤疤。我也看过火地里长着萝卜、包儿白和苦荞的景象。苦荞是最好看的,特别是苦荞花开的时候。开花前,苦荞苗也是很好看的。我没有看过火地里种罂粟的样子,罂粟花开的样子。罂粟是火地最适宜种的东西,老一代人摆起时,我会去想象。
药地坪种的包儿白很甜,熬腊肉特别好吃。但大人很少带回家,都是在药地坪熬了吃,所以,药地坪的包儿白对于我们这些小娃娃只是个传说。还有火地里种的一种洋萝卜,有土饽碗那么大,也只是一个传说,在大人的描述里简直就是一种吃了会长生不老的仙果。不是传说,看得见摸得着的,只有药材,晒在簟里,发出难闻的刺鼻的气味。
为了吃包儿白和洋萝卜,我去了一趟药地坪。天不亮出发,擦黑边上才到;要经过两红岩、麻子地、九道拐、董秃子家、箭豁丫、草米岩、马家,过了马家就是万古老林,有磨刀梁、野猪林、红岩上、水溻子。站在磨刀梁或者红岩上看长河湾、看县城、看涪江,都显得很小,涪江九曲八折绕得像猪肠子。
没去药地坪之前,听大人说在药地坪能听到北京的广播,我不信。到了药地坪,果真能听见广播,但不是北京的,是龙安城里的。
偷嘴
满屋、满院、满村都是肉香。我一边闻着肉香一边很不情愿地赶着驴子下河,心里惦记着锅里煮得翻滚的猪头肉、坐凳儿肉、肋巴骨、轩底子和心舌肚。
过年了,省了一冬的好吃好喝都拿了出来。腊肉、花生、核桃,还有头道面蒸的大馍馍(揪了花,点了红膏子)。
翻了房子,捡了亮瓦,打了阳尘,扫了房前屋后的树叶、竹叶,沤起了火灰。
驴子在河坝里找草吃,我心不在焉。“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蚕,九龙十虎十一老鼠”里没有驴,驴子只能在河坝里吃一点随便饭。我有点恨驴子,恨父亲,过年也莫得自由,不让耍。天灰蒙蒙的,飘雪花,想起来还真有一点《白毛女》里“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味道。
没到吃团年饭的时间我就赶着驴子回家了。父亲见了也不责问,显出少有的温和。关好圈门,跑进厨房,鼻子闻到的肉香已不及先前,肉已经煮好,捞在洋瓷盆里,肥肉上的油已经凝固(我们的方言叫“泠到了”)。婆婆正站在案板前面剔骨头。我有些吃力(我们的方言叫“挣挣磕磕”)地揭开锅盖,看见一锅肉汤,里面下了萝卜干、干豇豆或海带,正翻江倒海地煮着,上面浮澜澜的一层油。我去案板上抓骨头,婆婆没像往常在我脑壳上啪一巴掌,反倒帮我选了块肉多的。
我喜欢偷嘴。刚起锅的腊肉,切在红松木的菜凳上,半肥半瘦,红白分明,抓一片塞到嘴里,嚼着,油水从嘴角流出来,那感觉没说的。
过年允许我们犯一点错误,所以我们时不时便跑进厨房偷嘴,开始是一根骨头,接着是两片肥肉,再下来就是一个盐铲铲或者一块肋巴骨,胆子大的干脆拿一芽肝子或一个心子。婆婆看见了也不管,只是说:“偷嘴都偷饱了,正当端到桌子上又不xia了!”
吃团年饭之前,我们都跑出去看父亲放雷管。洁白的引线,铜黄的雷管,让我们兴奋不已。父亲一颗一颗点燃,扔到挖了萝卜的空地里。响声震天,泥土四溅。
肉端上桌子,我们果真不xia了,这个碗里叉几筷子,那个盘子里叉几筷子,就下桌了。
我就偷嘴打过一个比喻:偷嘴是结婚前的感觉,而上了桌子是婚后的感觉——名正言顺了,也不饿了。
广播
每家每户的房子上都挂着个用油漆涂红的木箱箱。木箱箱正面开着个圆洞,上面绷着布,从圆洞里发出声音。
广播由公社广播站管,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也自办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著名的节目是早上六点半到七点的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自办节目主要是公社书记讲话和播通知。
我们家的广播箱箱挂在楼口上,红色已经变成黑色,积满了油垢和灰尘,沾着蛛丝和竹叶。我经常从木梯爬上去听,听着听着就伸手去摸,摸到的总是一把污垢。污垢也是广播传播的内容,但在我们听来却是昂扬悦耳的。
有一根铁丝把各家各户的广播串在一起,翻桅坪到竹林盖,最后归入公社广播站。我经常在桅杆坪看见那根铁丝,觉得它好神奇。我不知道它也是一根管子,向我们传输着可以改变一个人思想观念的东西。
每一次广播响之前,总有一阵铮铮铮的电流声,强烈刺耳,但我们不觉得刺耳,反倒觉得是一种福音,会带来好消息。铮铮铮,现在可以把它想象成破冰的声音。好消息只有一种,就是通知晚上有电影:《闪闪的红星》《渡江侦查记》或者《奇袭》。张连国故意把“闪闪的红星”说成“你嫂嫂的红星”。有人问起晚上放什么电影,王生喜最爱说的是“雨淋猪”。
广播箱箱在楼口挂了七八年,没有人逗它,有时候不响了,我就爬上去摇几下。几摇几摇它又响了。有时候,隔壁把木梯借走了,我就找一根竹棍夺。
我最喜欢广播在不该响的时候响,特别是下午,大多是通知晚上有电影。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们家的广播响了,我以为还是通知有电影——又闹地震又涨水,好久没看电影了,结果听见的是奏哀乐,一直在奏哀乐,最后听懂了一个成语:永垂不朽。这之前的四月五日,我在这个木头箱箱里听过北京市市长吴德的讲话。
在广播里听得最多的是广播剧《白毛女》。早晨在唱,中午在唱,晚上还在唱。开始是杨白劳的声音,喜悦的声音——我想象得到,过年了,给喜儿买了红头绳,正在往头上扎。接着是喜儿在唱,也是喜悦的声音——爹爹买了红头绳正在给她扎,穷人家的孩子也喜欢过年。可是,怎么转眼的工夫就哭了?我不过是去后门外帮婆婆抱了几根柴。到底发生了什么?杨白劳的声音突然变得悲伤、悲凉、悲惨、悲愤……喜儿也哭了,喜儿的声音突然变得悲伤欲绝又孤独无助……我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但一定发生了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做作业,在撕玉米,在离核桃,甚至是在挨打,没有专心听,结果听见的就是这样完全不同的场面……王大春回来了,喜儿又变得欢天喜地了,音乐和歌声也变得欢天喜地了,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
有一天放学,跟任九胜去桂香楼捡废电池,看见了那根串着我们家广播箱箱的铁丝。循着铁丝,我们找到了公社广播站——两间砖房,就在何聋子家早晚门市部坎上。隔着玻璃,我们看见了一个男人播广播的侧影——原来声音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背篼
背篼是我们用来背东西的。背玉米,背麦子,背粪,背柴,背草,背猪草,背石头,背沙,背泥巴,背桑叶,背娃娃,背簸箕,背樱桃,背菜,背米,背肉……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好几个背篼,也有好几种背篼。大人背大背篼,小娃娃背小背篼,女人背夹背,男人背垮拉子背篼。
夹背是用细篾精编而成的,专门用来背米、背面的。精编而成,没有缝隙,米面不会漏出来。
垮拉子背篼就是特大号,装满东西只有男人才背得动。一般的背篼都是稀眼背篼,留的孔(我们的方言叫洞洞)很大。
有专门编织的背孩子的背篼,里面靠后编有一个座位供孩子坐。
我们那里盛产尺竹和筋竹,房前屋后都是竹林。我们一般用尺竹编稀眼背篼,用筋竹编夹背。很少有年轻人会编背篼。做活路歇气的时候,总是看见上了年纪的人在编背篼。他们开会的时候也编,夏天乘凉、冬天烤火的时候也在编。编背篼的时候,不时会把篾条弄得噼啪响。编背篼也是一种手艺。胡山林编背篼编得好,在生产队很有名。一个人背着一个背篼走过,人们一眼就能认出这个背篼是谁编的。
有的人特别爱惜自己的背篼,比如一些小娃娃、女娃娃,在背系上缠一些碎花布条作为装饰,回家就把背篼藏起来,不肯借给外人,大人要借就哭,就睡在地上打滚儿。大人就说,小背篼是他的命根子。
一个背篼都有两根背系。背系一般都用碎布条或麻绳编成,也有用谷草的,也有用拖拉机、柴油机上的传输带的,还有用铁丝的。背系爱断,背系突然断了,就会把背篼里的东西倒在地上。背篼里背的要是米面,那就很糟糕。要是背重物的时候,特别是背重物走过悬崖峭壁的时候,背系突然断了,那就特危险,东西倒了不说,人很容易失去平衡栽下悬崖。所以,上老林的头天晚上,都要把背系检查一遍。很多背系都是断了接起的,背系上有明显的接头。
背篼里装一背在高山上扯的猪草很好看。各种叶子的,有的还带着花,颜色特别美。背篼里装带壳的青玉米也很好看,装满了还插一边,再挨挨密密地插满,冒冒的,像一朵向日葵。
最好看的是装一背划子柴,一种叫白雪子的棒柴,或者划开的桦子木,高出背篼三分之二,装成一把扇子。一个人背一背这样的划子柴走在山道上,几个人一人背一背这样的划子柴走在山道上,十几个人一人背一背这样的划子柴走在山道上,该是一道怎样的风景?他们都带着拐耙子,累了就扎一拐,把一背柴都歇在拐耙子上,扎拐的同时还要扯起喉咙吼一声:“嗨哟!幺妹儿!”那爽感,就像这一拐是扎在幺妹儿身上。背柴的背篼,底下都用细铁丝绑了一根木棍,便于扎拐的时候掌手。
民国时候的人,背一背划子柴一路走一路还唱:
龙安下来岩(发音ai)对岩,
婆娘女子穿草鞋;
出门一坡山歌子,
进门一背划子柴。
背着空背篼上坡,走累了把背篼放下来倒扣起坐。把背篼放倒坐最舒服,背篼的大头朝前,应该就是我们最早的沙发。
当年我们平武县有一个背篼剧团,在全国都出名,就是背着背篼到处演出。背篼在路上背东西,演出时当椅子。
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在他的《扁舟过三峡》一书里,对我们四川的背篼有过这样的记录:
背篼是具有峡谷地区特点的工具,是中国苦力那根不朽的扁担的较为舒服的替代品。背篼是略呈锥形的篮子,篮口宽阔,用竹篾编出,很整齐,肩上的背系也用竹篾制成,其整体对背部较合身舒服,负重至250英磅也不至于十分劳累。大多数人也用来背孩子,将孩子直立着装在里面,温暖而舒适。
立德描述的,是他一八八三年在我们四川看见的背篼。
泠雨天
泠雨就是连续下了几天的雨——不包括春雨和秋雨。我们把下泠雨的季节叫泠雨天,通常都是在立秋过后。雨一下就是三四天甚至更长。一九七六年的泠雨从八月十六日晚地震后开始,一直下到九月九日。泠雨不是白雨,也不是暴雨,但下得最大的时候也有暴雨的气势。泠雨一霎一霎,像是永远不会停。“一霎一霎,石头泡垮”,是我们对泠雨的评价与感受。
下泠雨的时候,房子长霉了,铺盖长霉了,水捞柴长霉了,人长霉了……整个世界都长霉了,连火柴都擦不燃。雨一霎一霎,天天如此。刚才屋檐水已经小了,滴滴答答,一会儿又拉伸了,唰唰唰,甚至霹雳嘭隆。屋檐水像瀑布从前后檐倾泻下来,包围了整栋木屋。屋檐水的水幕很美,在柔和的天光里,很像是上天拿雨水和瓦沟、屋檐做成的一个艺术。
檐沟里有我们接雨水的水桶。屋檐水流进水桶是不一样的声音——水桶里的水不一样深度是不一样的声音。水桶里水满了,溢出来了,又是另一种声音。我们把洋瓷盆伸过去,放在走路的石梯上,又是别样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会随着雨量的变化而变化。包括屋里的滴漏,水桶、木盆、碗、盅盅,各是各的声音。说是滴漏,雨下大了的时候,也是水帘。
泠雨天睡觉,把自己关在罩子里,听泥窗外面的雨声。雨小的时候,听雨落在樱桃树上和竹梢上的声音,雨大的时候听屋檐水拉伸的声音。雨小的时候也听滴漏声,滴漏就在床面前,滴答——滴答——嘀当——,洋瓷盆的盆沿发出袅袅颤音。你会觉得每一个滴漏都是一口钟。
屋檐下面是关满雨水的院坝。雨水退去,院坝里满是青苔。人畜一踩又是泥泞。院坝边上便是树林,四窝尺竹长成了一大片。竹林里堆着一堆堆水捞柴。有人还在不断地背了柴走进来,倒在柴山上。
泠雨天也是涨水天。水涨得小的时候,我就戴了斗篷去山羊盖钓鱼、哽鱼;水涨得大的时候,我就去龙嘴子捞柴。洪水淹了山羊盖下面的路,我就走山羊盖上面。有的时候水涨得不大也不小,就我一个人扛了柴网去到龙嘴子。水看着看着上涨,很吓人的,我不断地往后退。
泠雨把什么都泡涨了,河坝里的鹅卵石也显得比平常大很多。泠雨把山也泡涨、泡垮了,我们家房后头突然多出的一股山泉,正好解决了全队的吃水。
下泠雨没法去推磨、打米,米面吃完了,只有去园子里摘豇豆、挖洋芋回来熬了吃。顿顿吃豇豆熬洋芋。也掰了嫩玉米回来在手磨上推水粑粑吃。一九七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我们吃水粑粑吃得都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