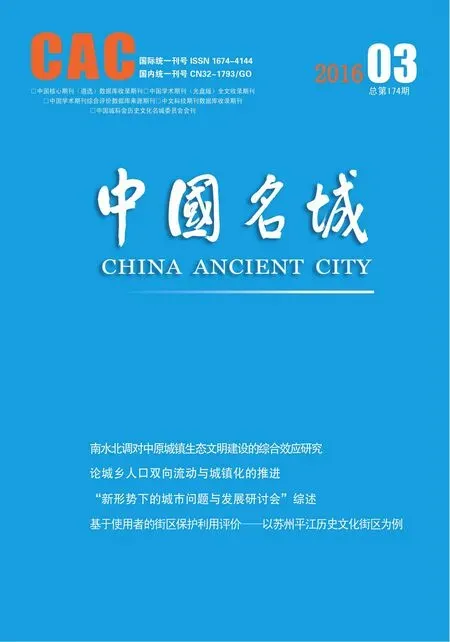城市地名变迁与社会记忆的建构
——基于《紫堤村志》的分析
韦 谢
城市地名变迁与社会记忆的建构
——基于《紫堤村志》的分析
韦 谢
社会记忆不但具有天然的社会整合的功能,还随着时代的变迁被不断地建构,这种建构并不仅仅局限在Barry Schwar所研究的历史人物形象的记忆方面,也涵盖了仪式、历史事件、地名等。历史地名以及地名中蕴含的古老传说,是乡村社会记忆和社区认同的重要内容,构成了延绵的非正式地方史。地名嬗变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空间地理上的演变更替,也隐含着政治与经济变迁的社会背景,政权更替时期的地名命名更是凸显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基于对清朝乡村志《紫堤村志》和《闲话紫堤村志》的材料分析,从历史地名的延续、更替与消失这一切入点,来描述在城市大规模重建背景下乡村社会记忆及地方史的建构与断裂过程。
地名;地方史;社会记忆;社会建构
引言
地方志,即“一地之自然与社会”,是地方历史的重要文字载体,也是宏观史书之外的重要史料。在浩如烟海的地方志文献中,乡村志相对而言较为少见,但乡村生活又是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的研究文献《紫堤村志》即是描述乡规民俗的的典范,书中记载了大量清朝时期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与人文遗存。《紫堤村志》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由汪叟否编撰,道光末年侯云若续修《紫堤村志》,之后由沈心卿以汪叟否编撰的《紫堤村志》为原本参阅侯云岩续修《紫堤村志》时所采集的资料,增修《紫堤村志》成稿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30多年后,张启南抄录增修《紫堤村志》,于民国八年(1919年)刻印成《紫堤村志》,流传于世。这本难得的江南名村志在文革期间差点被破四旧的造反派付之一炬,幸而辗转至诸翟村人朱墨钧先生的手中,才得以保留至今。朱墨钧深感本村志书的重要历史价值,通过实地考察了一百多年前的志书中记载的村落、桥梁、河流以及人文遗址,修订了原书中的一些错误,由此写成了白话文版的紫堤村志,名为《闲话紫堤村志》。笔者拜访了朱墨钧,获得了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口述史材料。本文即是从这些资料基础中孕育而生,谨以地名这一细微切入口,从社会记忆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地名变更中折射出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大背景。
1 地名中的传说:社会记忆的延续
《紫堤村志》自草创到增修成书,历时近一个半世纪。书中详细记载了自元末至清康熙年间500余年的村事村史,在地理状貌中,《村志》引《大清一统志·广舆记》,略述诸翟分属两郡三邑之建置、方里、疆界等目后,对《村巷》、《水道》、《疏浚》叙述特详。依据《一统志广舆记》(明代)及《松江府志》、《嘉定县志》记载:紫堤村村址原属苏州府,以前是昆山县的。到了宋代朝廷从昆山等县划出一块地方成立嘉定县后,它就从属于嘉定县临江乡(后来改为依仁乡)。紫堤村村西原属苏州府秀州华亭县,直至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县升格为松江府(原华亭县地区仍称华亭县),紫堤村村东南便从属松江府华亭县北亭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松江府奏请朝廷增设了上海县,那自然而然属于松江府上海县。明代松江府辖下又建立了青浦县,诸堤村村西划归于松江府青浦县北亭乡(朱墨钧,2007)。“诸翟”这个镇在乾隆时已被朝廷正式命名,并被镌刻在巡检司衙门前的石牌上,现在修志仍称“紫堤村”是为了遵循旧志,前后连贯而已。2000年,诸翟镇与原来的华漕镇、纪王镇合并,建立了新的华漕镇。虹桥机场落户华漕,使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观之,紫堤村历经诸翟镇,再到华漕镇,最终淹没在虹桥商务区的经济开发浪潮中。
在《村巷》和《桥梁》两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地名桥名的历史及当地著名人物传说,桥文化研究,包括建代、形制、质材、建造、经济价值、交通意义、战略价值等多种层面,其中桥名亦属不可或缺之项,它反映着一定历史时期中社会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沈渭滨,2007)。古代地名桥名的命名类型多样,有以人名姓氏冠之的,有取祥瑞意义命名的,也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取名。这些地理上的名字,像一个个历史中的知识符号的序列,串联起当地的社会史与社群记忆。
从历史渊源上考量,上海简称“申”是因为战国时期楚国黄歇被楚考烈王封为春申君后,其封地亦于考烈王十五年(前249年)从淮北迁往江南,并领有上海西部地区,他命人开凿疏浚的大江,便名“黄浦”、“黄歇浦”,或称“申浦”、“春申浦”,亦名“申江”、“春申江”,即今黄浦江。而“申”、“歇浦”、“申江”等名也就成了上海的别称。至于上海华亭的由来,更是早自春秋时期昊国君主梦寿(前585年一前561年)曾“筑华亭于其国之东、松江之南,以为停留宿会之处”,故名华亭,而唐天宝十年(751年)定名的华亭县名也源之于此。阂行镇,是为明嘉靖年间山东人阂其卜居之处。在古代,由于封建宗法制度的维系,人口的聚居地名大都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姓氏来命名(张鸿奎,1995)。这在《紫堤村志》中有诸多记载,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诸翟村了,村名即指诸、翟两户大姓家族。大家族势力的影响在地名上还有很多例证,如秦家桥 ,为字字号一图(属上海县),位于蟠龙港、张占浦处。这户秦家大有来头,始祖秦君瑞官拜南宋龙图阁学士观。秦家后代的厅堂上高悬”为善最乐堂”匾额,其墨宝出自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手迹。
《紫堤村志》里面颇为有名的一号人物是元末明初的造反将领钱鹤皋,有风水先生认定他们家附近的大涞浦有龙脉之象,他曾经在战乱的元末招兵买马,连下七城,最终为朱元璋所破。但民间传闻的龙脉之说仍让朱元璋很是担心,便急忙派人把大涞浦给填埋了。这一段历史表征在很多地名都有当年战争岁月的影子,比如村落王湖桥,这个王,不是姓王的王,而是大王的王。元末的钱鹤皋,将自己所居的村庄前的那条唐家浜改名王湖,湖上的石桥更名王湖桥,村随桥名。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古老的地名不仅仅具有指示方位之功能,也是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
在大家族姓氏之外的命名法中,还有一种尤为具有乡村伦理的意义,即以桥梁的捐资者姓氏命名。比如黄家桥,相传明初乡绅黄某在捐资购大砖铺道路的同时,一并改建石桥,于是这座桥变被命名为“黄家桥”,以感谢富人的慷慨。这正体现了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所论述的道义小农的伦理观,在另一个道德世界,有一种基于生存经验真实的公正伦理,它帮助其成员团结起来,结成社会团体和价值共同体。对于富人的道德期待与对善举的褒扬,形成了乡村社会非正式的保障力量。通过地名与桥名对这些历史的记录,以及村民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正是在延续和再生产村落的社会记忆与道德传统。作为地方社会成员的表达和社会记忆本身就构成关于地方社会的想像,因而也成为地方性秩序场境的组成部分(张佩国,2004)。研究者的责任不在于指出传说中的事实的对错,而是要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这些记忆所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口述资料和本地人的记述,可能更深刻地反映了乡村历史的事实和内在脉络。
2 地名变迁:国家话语与社会记忆的重构
社会记忆源于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研究(涂尔干,2006),他认为集体表述影响着个体生活,哈布瓦赫(2002)认为集体记忆是思维对社会产生影响和社会秩序建构的工具。二者都是功能论者,忽视了权力和政治学的观点。Barry Schwartz(1991;1996)的研究说明了,社会记忆不但具有天然的社会整合的功能,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被不断地建构,以帮助当权者来实现某种整合的目的。这种建构并不仅仅局限在Barry Schwartz所研究的历史人物形象的记忆方面,也涵盖了仪式、历史事件、地名等等。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村落的地理空间也会相应调整,在《紫堤村志》记载的五百多年时间里,这种地名的变化是缓慢而细微的。笔者在与朱墨钧先生的访谈中,六十余岁的朱墨钧感慨了近几十年间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把目光放的更广更远一些就可以看到,近百年的上海,经历数次更名换姓的过程。每一次的更名,即是一次历史演变的见证。
早期随着上海开埠,英、法租界拿来大量的欧美国家的人名作路名,这些人物主要是各国驻华公使、驻沪领事、租界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总董或董事以及来华的传教士、商人等。如戈登是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赫德是长期霸占海关的总税务司,哈同是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大地产商,他们的名字被分别命名为“戈登路”(今江宁路)、“赫德路”(今常德路)、“哈同路”(今铜仁路)(郑祖安,1987)。这一命名过程即是殖民话语赤裸裸的入侵过程。后来,这些洋地名在民国政府期间受到了大规模的变更,国民党领导人的名字取而代之。
1943年10月,汪伪市政府发出训令,公布了原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两租界越界筑路区域的路名和应予更名道路的新路名,以欧美人名命名的道路全部更名,代之以中国地名。
随着上海城市更大规模的发展,以及政权的更替,显然在趋向于形成更加整齐的大区域地名。上海建市后的行政划区及“沪东”、“沪北”、“沪西”、“沪南”四个大型区域地名的出现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郑祖安,1987)。这些新的地名体现了新的国家意志与统治阶级的空间治理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又经历了一次大范围的地名变化,把原来的中正路等地名全部更新为与革命战争相关的地名。
国家承担起记忆与遗忘的责任:它的记忆正如国家本身,是理性和选择性的。另一方面,社会根据特定的价值观,最重要的是当这些价值观成为主流时,在与这些价值观的实用关系中去记忆和遗忘(弗朗西斯科·德利奇,2007)。地名变更这一历史过程展示了意识形态在型塑国家形象中的符号实践。通过新的富有革命意义的地名,充分凸显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姿态,并深入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话语实践,在提到地名的同时,即是在反复强调“新中国”这一社会记忆与国家形象,同时抹去旧政权和旧历史的记忆,最终完成社会记忆与国家形象的重构。
那么,是不是仅仅只有城区中的地名受到了影响呢?当然不是。国家政权从建立之初,就开始全方位渗透进乡村社区,并构建起不同于家族认同、社群认同的国家认同。以诸翟镇、华漕镇为例,诸翟镇在解放初设诸翟乡,属上海市新泾区。1956年3月属西郊区。1958年8月划归上海县,10月编属解放人民公社。1959年8月分属纪王、华漕两公社。1961年10月成立诸翟人民公社。1983年4月就社设乡,1993年撤乡建镇。华漕镇位于闵行区西北部。1949年4月设镇,属上海市新泾区。解放后,设华漕办事处,1949年9月设华漕乡。1956年3月属西郊区。1958年8月,属上海县,编属解放人民公社。1959年8月成立华漕人民公社。1984年3月就社设乡。解放人民公社位于上海县西北部。1958年10月设立,由诸翟、华漕、西郊3乡北新泾镇(11月份划入)、宝北乡北部和纪王乡吴淞江以南地区组成。下设9个生产大队和北新泾镇。公社机关设华漕集镇。境域包括现纪王、诸翟、华漕3镇和长宁区的新泾镇和北新泾、程家桥2个街道,以及上海虹桥国际机场1963年后扩建的部分。1959年8月撤销,境域分别划属纪王、华漕、新泾3个民公社(资料来源:《闵行区地名志》)。从以上这段历史资料可以看到,公社和大队成为新的乡村组织形态,国家干预打破了原有的村落自然边界,形成了行政村落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小村落合并到大队之后,就成为了永远的历史地名。
国家试图把“基层社会改造成民族—国家的分子,使原来相对独立的小区人民变成国家的‘政治公民’从而成为国家机体的‘细胞’,执行国家的功能“的过程(董国礼,2001)。”公社制度试图对传统的小区、家族认同加以取消,大队和生产小队的制度是为了使原先的家族和聚落改造为国家统一管理的生产和工作单位。(王铭铭,1997)民族-国家的权力不仅在行政机构上延伸到乡野边界,而且延渗到人们的头脑之中。然而,公社制度的消失亦如社会休克的一瞬间,这些地名已然成为最年轻的历史地名了。今天我们对于人民公社的社会记忆相当模糊,究竟是国家权力的转移?还是国家话语的自然消解?这一段短暂的地名史也构成了被封锁的社会记忆。
3 地名消逝、城市更新与社会失忆
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说:“不同辈分的人虽然以身共处某一个特定场合,但他们可能会在精神和感情上保持着绝缘,可以说,一代人的记忆不可换回地锁闭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心之中。”那么社会记忆如何传承下去呢?他给人们的答案是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身体实践中口述史是重要的社会记忆的重要操演过程,然而在今天的城市发展主义的霸权话语下,市场化力量对古朴的乡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年轻一辈的人大多数会选择去城市工作生活,老一辈的人对于村落的记忆往往没有了传承和倾诉的对象,只能永远停留在自己的脑海中。同时,在城市化向农村扩张运动中,大量农村的土地被征用开发,村落变居民小区、经济开发区等,其速度之迅猛让朱墨钧老先生都惊叹自己根本不认识现在的家乡了。
据《紫堤村志》排列,紫堤村四周计162个村庄,再加紫堤本身这个中心村,共为163个村庄。如今再打开泛黄的蟠龙塘(港)的南北水道图,面对图上星罗棋布的村庄,强烈地感受到势不可挡的历史推动力,人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163个村庄中有从前人丁减少被自然淘汰的,又有建国后因开河筑路而搬迁的,也有公社化时强求“一大二公”强行拆迁的小村庄,还有为改变村貌而合并的。变化最大的莫过于从2007年春开始动工的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就此一项工程就动迁了将近70个自然村。换言之,又有70个自然村完成历史使命,同时永远地从地平线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林立的“爱博家园”(朱墨钧,2007)。通常只在理论上存在着村落共同体完全由社区内部力量自发形构的可能性,实际上国家力量、市场力量总是参与,影响甚至决定村落共同体的边界、机制和功能(毛丹,2010)。相较于政治力量,市场化的改造力量对于村落共同体的分解是致命的,地名的消失同时也意味着村落生命的终结。庆幸的是民间还有关心自己家乡历史的文化人,朱墨钧先生承续了沈葵等修志人的执着认真精神,通过书写历史的方式使乡村社会记忆得以延绵。
[1]Barry Schwartz. Social Change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 Democratization of George Washingt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1.
[2]Barry Schwartz. Memory as a Cultural System: Abraham Lincoln in World War II[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
[3](美国)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董国礼.国家、仪式与社会[J].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1,(秋季).
[5]弗朗西斯科·德利奇.记忆与遗忘的社会建构[J].国外社会科学,2007,(4).
[6](法国)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7]毛丹.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J].社会学研究,2010,(1).
[8](美国)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 程立显,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5.
[9]沈葵.紫堤村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0]沈渭滨.紫堤村志的史料价值[J].史林,2007,(2).
[11](法国)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2]汪祖超.闵行区地名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13]王铭铭.小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14]张鸿奎.移民与上海地名的变迁[J].史林,1995,(3).
[15]张佩国.口述史、社会记忆与乡村社会研究[J].史学月刊,2004,(12).
[16]郑祖安.近代上海城市地名研究[J].史林,1987,(1).
[17]朱墨钧.闲话紫堤村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于向凤
Social memory is effective of naturally social integration. But as we can see, it is continuing built to help the authority for integration and control. A historical toponym and the old legend of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roup’s memory and community identity,which has constructed the local history in folk. The toponym’s evolution means not only the reposition of the geo-space, but also the indication of changes of social background in politics and economies.Basing on “Ziti Chronicles (Ziti Cun Zhi)” and “Chitchat on Ziti (Xianhua Ziti Cun Zhi)” which are written in Qing dynasty,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toponym, and tries to draw a picture on the fracture and rebuild of social memory and local history in the coun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toponym ; local history ; social memory ; s ociety construction
K29
: A
1674-4144(2016)-03- 53(4)
韦谢,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江苏省张家港市较大规模推进村志编纂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