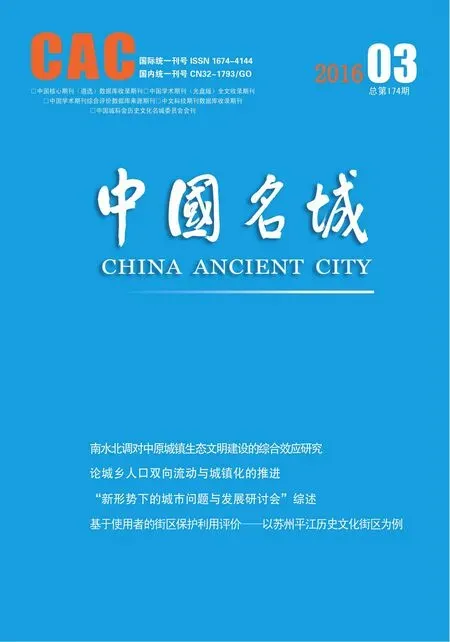论重构中国乡村的文化根柢*
张鸿雁
论重构中国乡村的文化根柢*
张鸿雁
不解决农民的问题,也就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本质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直到现在,好多社会问题都源于还在深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老一代学者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都饱含蕴含着一种个人价值理想与人文精神指向,具体表现为对劳苦大众的人文关怀——上个世纪20、30年代,有一批知识分子、文化人深入到乡村里开展实地研究,也曾试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和农民问题——其解决之道的切入点就是:对农民进行文化启蒙教育。亦如经典作家所论:“以往的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乡愁;原生态文化;城市化;空心村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乡村城市化的过程。然而,现实的经验和城市化事实告诉我们,未来的城市化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所有的人都要到城市里,到大城市去的。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书中讲过这样一句话“未来的城市无底、无形、无边”,社会发展会出现无边界城市和无边界的城市生活方式区域,在空间再生产的意义说,城市生活方式的无边界化是一种必然结果。因为,说到底,城市化就是在传播城市生活方式,传播现代城市文明。
1 保护乡村“原文化”和“源文化”,推进城市文明普及率
关怀乡村主要是关注在乡村能否建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城市文明和现代城市市民的生活体系,让传统乡村中的每个个体获得人性的解放,让每一个人活得有理想、有向上的价值取向。我个人之所以关注乡村、关注乡村的“空心化”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因为在我30多年的城市问题研究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想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必须减少农民,必须让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或者成为农业工人,而其根本的方法之一就是积极推进科学的、适合本地情况的乡村城市化。同时在研究中还看到,目前推进的乡村城市化不仅存在理论与认识上的误区,而且还存在着实践与操作上的错误,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建设不仅难以推动,而且还在走偏,甚至出现某种“建设性破坏”的现象。事实上,合理的新型城镇化在把传统农民变成市民的同时,也应该创造现代新型的城镇科技农业;在“原农业地带”创造城镇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要创造新的城市社会关系体和区域现代性——“城市性”,包括城市市民关系中的契约精神、民主精神、利他主义倾向等,这就需要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乡村城镇化也是在创造新的“地域生产力格局”,建设传统农业社会的“财富积累中心精神”以及个人价值创造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精神。我认为,要让这些“城市性”的要素结晶成为农民的一种文化认知,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进一步说,在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化的今天,如何能在中国原来的农业地带进行有效的城市文明传播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也是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需要解决的重要“短板问题”。
作为一个城市化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学者,必须关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全过程及发展阶段的关键性问题,这也是一个学者职业精神的体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讲过的:“近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的历史”。全球近代城市化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马克思的观点。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在关注乡村问题表现人文关怀、人文情愫和学者的责任的时候,还应该有时代的表达——担当。一个学者在担当现实与历史责任的同时,还需要直接参与乡村文化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这才具有时代性,并把一般的责任担当转化为具体行动。我当过知识青年,下过乡,当过农民,20岁当农村生产队长,东北农村里所有活儿都做过,还当过林业工人和建筑工人。应该说是十分了解农民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繁重,也更了解农民没有文化知识的苦痛生活事实。我认为,不能让传统农民仅仅在原来土地上以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继续没有改变且贫困地生活下去,而要在“原农业地带”创造一种“城镇人”的市民生活方式,正如李克强总理讲过的:城市化就是让农民人进城里,过上与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
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社会精英群体重返乡村去参与乡村的规划建设和治理工作。因专业的要求,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开展了多项、多元的乡村治理、乡村规划设计、乡村文化与旅游策划和传统古村落的“精准保护”工作,也就是参与乡村的具体治理与保护建设工作。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经济较发达国家就有很多知识分子走到乡村去,参与乡村的改造、参与乡村的重建和新文化创造运动。特别是要类比提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20世纪20、30年代)晏阳初等学者在中国开展平民教育,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晏阳初认为:“中国大患主要是民众的“贫、愚、弱、私这‘四大病’”,他创造农民学校等,也是基于这一思想——要改变落后的中国,必须改变“少文化缺知识”的农民。但是,那个时代战火连年,日本侵略逼近,注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实现改变农民贫困生活的愿望,更不可能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而今天,中国处在一个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可以创新的时代,为社会学者介入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有能力、有理论、有科学的方法来改变传统乡村落后的状况、改变农民落后的生产方式、改变农民落后的生活方式。可以建构让农民从“活着”走向“生活着”的,有文化价值追求的生活方式范畴。这里强调“生活着”……意指是个体人生终极价值追求的市民社会。要想达到此目的,必须在保护乡愁的基础上,去重构乡村的“文化根柢”、重构乡村文化的新文化形态。在这方面,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等有成功的案例,如日本古川町的社区治理模式等。一些大学教授、研究者和城市建筑与规划工程师在乡村一做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如台湾的宜兰就有日本学者在那里搞规划设计,并参与地方治理长达十七年。在中国浙江德清莫干山一带,正兴起的“洋家乐”是乡村城镇生活方式化的一种发展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城市精英下乡推广城市文明的一种成功案例。目前,在中国已经出现大批城市精英重返乡村的热潮,在传统乡村里——在深山里建构新型的城市生活方式、类城市生活的空间体系及要素——包括新型的咖啡馆、新型的客栈、新型的书院、新的产业模式等,关键的是,还带来去新型的城市市民生活体系和新的人生价值取向、新的就业模式等,也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中,可以看到已经具有显性化的“四种乡村文化重构与治理模式”:一种是浙江德清的“洋家乐模式”。一些外国人和上海、杭州等城市里的文化人、学者和新一代“文青”,主动下乡建设乡村,在乡村经营发展;一种是浙江“安吉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已经创造了完整的建设经验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和村民共同参与的建设模式,表现十分充分;一种是我本人参与策划的“南京高淳桠溪国际慢城模式”,以“福民富民”为核心,以农民就地城市化为外在特点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方式的创新模式;第四种是安徽黟县的“碧山文化模式”,即通过老宅基地的流转创造一种新型区域旅游和保护乡愁的宅基地流转模式。当下,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及安徽等省市城市里一些有文化、有学历、有经营头脑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有投资能力“文化资本家”到那里,在乡村重构一种乡村的新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同时,还在不自觉地重构地域文化和地方文化,如乡村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书院就是一例,其意义非常深远!
让农民变成市民是城市化的根本目的之一,但这不是一朝一夕或一蹴而就的事情,一定是一个漫长的教育和习得的过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不让农民进城,就永远没有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证明了这一点,城市只是达官显贵为主的居住地,农民没有成为市民的机会。而中世纪的欧洲与此相反,逃亡到城镇里的农奴过了101天就有可能成为市民,所以马克思曾说: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是由逃亡的农奴建造的。改变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的路径大体有二:一方面是让农民先到城里来,参与城市建设,接受城市文明,获得城市生活感受;另一方面是城里人到乡村去,唤起乡村,培育乡村的文化自觉,创造“城镇型农业”和特色村镇,推进乡村的城市文明建设运动,即创造乡村发展的新型内在“文化动力因”。过去,好多人以为“都市农业”、“城镇农业”是农民种了田,生产了农副产品给城里人吃就是“都市农业”。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理解,所谓“都市农业”“城镇农业”就是“都市人农业”,是“城市人”经营、管理、耕作的农业,是有文化的人去农村建构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发展空间,创造出“城市人农业”、城镇人农业或者“工程师、科技工作者农业”。一些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以色列、日本甚至韩国等都在强调“都市农业”“城镇农业”,让文化人、学者 、工程师、技术人员来农村,建立科技型农业生产体系和农副产品的商品价值链,美国的“精准农业”就是非常典型的依靠高学历、高学位的人和高科技来经营耕作的高新技术农业。
要真正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就必须解决现实中国发展的“短板问题”,显然,中国的“短板问题”之一就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当下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农村的“空心村”问题以及相应的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空心村”现象集中代表并反映了农村的现状。这些被闲置的“空心村”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而且使一些农村区域呈现经济和文化大面积双重沦陷的情况,那些断壁残垣述说着一种衰败和痛苦的乡愁。因此说,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急需文化的整治和精准的重建型治理。不得不说,新型城镇化在外在形式上,除了我们看到的发达地区城市化带来城市文明及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之外,还要看到有些地方城乡“二元结构”还在深化。在中国的大地上,形成两道风景线:一面是鳞次栉比高楼大厦构成的繁华城市,一面是空寂无人落后衰败的乡村。特别是那些衰败的乡村,不仅经济发展上成为欠发达地区,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也成为低俗文化的滋生地,如有学者称之为“大面积文化坍塌”。因此,我们必须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责任必须把农民带进现代社会、带进现代文明。
2 重构乡村文化的人文情愫与时代要求的创新
和晏阳初和梁漱溟等老一辈学者亲自参与乡村治理相比,以及同发达国家的社会精英重返乡村、重构乡村相比,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文化重构,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
首先,情怀都是一样的,时代背景和工作内容是不一样的。比如,在高淳桠溪国际慢城的规划与策划中,我们在规划与策划文案中提出一年内农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政府与农民的共同努力,根据规划要求按期实现了“福民富民”的目标。在湖北的一个贫困县,我们提出“药旅联动战略”,在政府直接推动下做到家喻户晓,全县都被动员了起来,三年左右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生深刻变化。与此同时,我们也提出很多新的观念来改变当地人的文化认知模式,给全县的干部上课,教育农民,培训村长,使当地的干部群体获得了充分的理解。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和差异就是:一个更多的强调文化知识教育,一个是在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更多地是直接为农民谋福。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我们确实缺少了一些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上个世纪,那样艰苦的20、30年代,一大批文人学者受西方文化启蒙教育的影响直接来到艰苦的农村是十分不易的。他们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多数中国人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大量的文盲农民找不到生活的价值取向,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民的问题,解决农民问题首先要让农民有知识文化。我们和那个时代区别是社会环境、责任和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就关注农民教育问题这一点来说人文情怀是一样的,因为当代的中国农民仍然属于弱势群体,需要人文关怀,而人文关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底色。当下的中国仍然有大量的文盲存在,我在《“社会精准治理”理论模式创新》一文中指出,如江苏省已经是经济文化较发达省份了,仍然还有三百多万文盲,南京这样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还有二十多万文盲人口,江苏尚且如此,如若推论全国,文盲群体总量应该是很庞大的。如果一个正在推进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还存有这样庞大的文盲群体,是很难使整个国家进入现代性发展的体系之中的。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性“社会短板”问题,必须通过“社会精准治理”和“精准扶贫”来解决。
其次,深入乡村田野调查的方法基本是一样的,但达到目的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深入到每家每户,精准调查,精准统计,以便达到“精准规划和精准治理”的目的。我们曾经在湖北蕲春做田野调查,一万个自然村我们都进行了统计。走遍了所有的十五个乡镇,500个行政村,也对很多自然村进行了一家一户的入户调研,询问他们人在哪儿、老年人有几个、房子有多大、居住在哪里、就业收入情况、宅基地情况及流转情况等,即用“嵌入性”的方法进入农村,到社会底层去了解农民。在江苏苏北洪泽的龟山村,也基本上是一个空心村,共有100户人家,我们对每一户进行了详细的摸底调查,包括房屋的年代、有否古迹、经济来源、房屋年代,进行了全面造册,应该说做到这程度是很不容易的。之所以说我们和老一辈社会学家比,进入乡村目的和目标是不一样的,其主要差别是:老一辈社会学家在那个动乱年代是希望唤醒和启蒙农民来改变中国;而我们是直接通过教育、规划、改造、保护和科学建设来改变农村和农民,使农民成为市民,使乡愁得以留存。现实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实力的增加使得我们有条件、有能力直接对乡村进行保护规划并进行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建设,包括直接引导农民创业和就业,创造“产城一体”的新型乡村空间体系。现在的中国农民,多数是有一定文化的。我们希望让他们尽快转化为市民,以多样化、多渠道的方式成为城镇市民。其中鼓励他们回乡主动参与重构现代乡村文明、创造新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包括建构现代性的乡村文化——“集体良知”。
第三,教育和启蒙农民的目的是一样,但唤起农民“文化自觉”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试图创造从费孝通先生的“乡村文化自觉”,进而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城镇文化自觉”。我们在江苏北部、浙江、湖北和安徽等地开展的许多乡村实践,都是首先要培训农民包括一些乡镇干部,让他们懂得、理解如何建构乡村的特色文化、乡村的“地点精神”,保护乡村的乡愁文化和集体记忆。在一些农村地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好多行政村的村长年龄比较大,我们曾经专门对一些行政村的村长进行相关培训,他们有很多人不懂电脑,也不会看地图,引导他们挖掘自己乡村的特色文化,让他们了解乡村变革的意义,获得新知识。如淘宝村文化、乡村旅游文化、农副产品特色品牌化文化、农村电商文化、休闲农业文化、“产城一体”的知识及乡村旅游产业文化的价值链等。很多乡村的农副产品往往是田头交易,利润少,劳动强度大。我们强调把引导农民成为新一代“农业工人”,并以此为价值取向。孟德拉斯在他的《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最发达的国家,农业从业人员基本上分成三部分人:一是农场主——相当于中型企业经理;二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自我雇佣”型的农业生产者——相当于典型的中产阶级;三是被雇佣的农业机械的科技人员—相当于技术工人。虽然,这种情况与中国的现实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这是改变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并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第四,我们身份是相同的——都是以学者和教育者的身份嵌入乡村的,但是对乡村文化重构的技术手段、方式和主要工作内容是不同的。我们运用大数据的理论、地理模型的理论、现代网络管理理论、智慧旅游等理论与方法,对农村的文化、历史和相关资源进行梳理、整理和创新,并且通过整合优秀的乡村文化使之转化为“城镇文化资本”,进而行成保护、开发和文化再生产的全过程。比如可以进行乡村农副产品的营销推广,直接进行相关农业产业类型和价值链的建构、直接进行产业模式和赢利模式的规划、策划等,我们规划设计过农业科技产业园、食品科技产业园、村镇旅游规划、一村一品开发、乡村旅游节等,切切实实地改变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状况并达到预设效果。鲁迅曾言要唤醒中国的“文化根柢”,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挖掘农村的乡愁文化的。另外,我们以学者身份“嵌入性”的进入乡村是有很多优势的,如可以通过我们以学术研究视角挖掘各种文献资料,找到当地人不知道的历史资料、本地故事、本地传承口碑文化等。有时候,我们做出的一些成果拿出来的时候,许多当地人甚至相关部门的管理者都很惊讶,有的成果可以填补地方文化的空白。我的体会是,在这样的现代性意义上的农村文化保护和改革建设中,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如果能够深入下去,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之所以愿意以回望的视角关注乡村文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体制等原因,很多地方领导干部不可能长时间扎根农村,一般三五年任期后就要走人或升官。回想当年巴黎市长奥斯曼,规划建设巴黎整整十八年,160多年前建构了巴黎的整体空间,现在巴黎的空间样态还是160多年前的形态。所以,中国的学者在乡村建构方面遇到的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有时候很多规划、设计与策划想法很难实现,主要是县市包括乡镇换官换届,很多建设规划往往半途而废。
此外,重构乡村的社会与文化生活空间必须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即保护那些该保护的,拆掉那些不值得保留的、落后的、有落后传统的、甚至肮脏龌龊的村落。在保护乡村文化的认知方面,国内很多知识分子都在呼吁保护乡村文化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对现存的乡村村落加以区分和分类。我们现在做的乡村文化保护与重构,有一整套成功的经验,包括一整套可行的方法、程序,而且是规范而有效的,即用城市社会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城乡规划学的理论、区域经济理论、旅游经济产业规划理论、“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及产业经济理论等方面的知识,进行综合的跨学科的规划与策划,特别是我们强调通过特色文化乡村的建设,在农村建构一种就业和创业机制与文化土壤。我们认为,建设特色文化村镇是中国乡村发展的切入点。全世界有50多万个小城镇,发达国家60%都有特色文化和特色产业,而中国还不到20%。缺乏文化特色就必然缺乏就业机制,缺乏就业机制是中国一些农村凋敝的主要原因。在一些经济发展较落后地区的一些乡镇、村落,几乎无业可就。没有就业机制,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的。所以,给农民创造创业、就业的机会,是回归乡村建设、回望乡村的核心和关键点,而要解决此类问题,必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走都市农业的道路,给农民以新生的文化土壤和机会。这其中的规定动作之一就是:必须把那些有特色传统的乡愁文化保留问题放在首位。我今年排出“精准保护”传统乡村,也是首次提出对优秀传统村落进行“精准保护”的概念。我们必须强调并清醒的认识到:有些落后的乡村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是不值得保留的。在原农业地带的大范围区域内,应该有新型的科技农业、现代型农业、智慧型农业、大数据农业、精准农业、设施农业、创意农业、观赏农业和传统村落形态等多样化新型农业形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变乡村的本质并保留好乡愁。
3 “乡村精准治理”是乡村文化重构的方略之一
当下,一边是中国的城镇化的高速发展; 一边是一些传统农村深陷在旧文化的泥潭中。据有关资料说,山东省目前还有八万个自然村,百分之二三十是空心村;江苏省这样现代化发达的地区,竟然有十多万个自然村,如果全国有百分之十左右的村落是空心村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庞大的空心村数字,也是一个巨大的任务和问题。从一些相对欠发达地区来看,乡村文化重构的步伐是非常艰难的,中国是一个多梯度发展的国家,区域发展是多样化的、多类型的,用一种方法、一种政策、一种理念都解决不了中国乡村的问题。如果说有城乡有鸿沟的话,用卡斯特的话说:现代社会就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信息占有量差异所建构的鸿沟。我在上《城市社会学》课的时候,经常给学生放晏阳初当年在乡村进行平民教育的片子,每次看后都很感动。他们在最初开办农民学校的时候,环境和生活条件非常差,最多时有几百个学者怀着一种热情和理想来到这里,但是,那时的国情条件及农村的工作环境特别艰苦,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来。后来因各种原因加之日本的侵略,没有能够实现学者的理想。即使是现在,到乡村重新扎根也是不容易的,正如开篇所说,必须有一种人文情怀,必须有一种社会责任和一种理想。
在深入乡村、规划乡村,参与治理乡村的过程中,多学科的运用是十分必要的,必须打通规划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旅游学、文化学及农学等多元知识边界,才能有效地进行乡村规划和建设,这实际上需要一个由多学科成员组成的团队才行。在全球城市化的发展中,我们重新看到了城乡在空间上的地理差别和变革,看到城市空间再生产的理论与变迁,看到了发达国家城乡之间差别发生的质变:就像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所看到的那样:“即便是一个人住在森林里、一个家庭住在农业地带并经营农业,但是他们也不是农民”。即使住在很小的城镇里面,也是“城市人”,是市民,因为他们享受的是城市文明,他们以特有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实践着城市市民社会的生活。
从另一个方面说,是否能够把乡村的文化和乡愁记忆保护好,这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关注乡愁的关键所在。在这里,我个人认为并强调:重构乡村文化,不能简单地、单纯地依靠农民来重构的,一定是社会文化精英来引导农民重构,如果农民能够重构农村新文化的话,那么传统农村就不会有几千年来不变传统落后的文化了,重构乡村是城市文明对乡村的接替与侵入,因为全球的城市化和中国城市社会的来临,已经达到了可以普及城市文明的程度。
在这个意义上,再一次强调:重构乡村文化不是保护落后。我曾经讲过,1949年时中国有近六百多万个自然村,当时中国(1949年)有4亿人,到现在我们有近14亿人,也就是说有10亿左右的人口是1949年以后出生的。而且,从1848年鸦片战争以来,百年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外强侵略,很多美丽的乡村被毁于战火,到1949年后“传统美丽乡村”所剩无几,在数量上本来就不多,而且好多美丽乡村经历几场运动又被人为地破坏了。从理论与现实的意义上看,那些能够值得我们记忆的特殊空间、有真正的传统乡愁和人文集体记忆的村落,即像乌镇、周庄那样的村庄本来就不多,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因某种原因又不能进行传统村落文化格局的建设,大量的自然村——即仅以居住功能为主的村落多数是解放后建立的,进一步说,仅仅是能够居住的空间而已,而不是具有典型历史文化特质和“地点精神”的文化空间。因此,解决乡村文化重构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让大多数乡村人成为有文化的人、成为城市文明体系下有“市民意识”的人,才能够出现乡村的文化复兴,如果有那么一天,如美国、法国和德国那样,在乡村里生活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高学历群体、高级白领和各种工程师……,这样的乡村社会才能真正以重构城市文明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文化自觉。
我们不能保留落后的乡村文化,而要保留先进的、与城市文明相匹配的、值得记忆的中国根底文化和乡愁,就像发达国家的乡村里住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一样,而是农业工人,如以色列、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是这样,是有文化的人在农村经营。所以说,那些小乡村,过去叫小镇,能够保留下来的应该是城镇人、城市人,就像我们做的“桠溪国际慢城”那样,大学生、有文化的人回来了,可以成为乡村的主人;现在浙江德清的“洋家乐”也是这样,是研究生、博士去建构乡村的生活,就如我国国家领导人去的英国乡村喝啤酒一样,严格说,那里农业地带,并不传统意义上的村落,在那些农业地带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现代人、有文化、有知识的农业工人。
我曾经到意大利去参观一个小镇,感觉非常亲切,调查了两个企业,一个企业有170年的历史,一个企业有140年的历史。人们都把住在某个小镇里看成是一种荣耀、一种世家传承的文化价值指向,这个小镇不是传统的农民在生活而是城市的市民生活,但是却永久地保存了这里的乡愁记忆。实际上,发达国家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不是把农民留在那里就叫留住乡愁,而是要把那些文化、文脉和集体记忆保存好,并让他们过上现代文明生活才能够真正保护好乡愁。现在也有些争议,很多人,包括一些作家、文艺人呼喊中国乡村都没有了,他们理解的是把农民留在那里就可以了,甚至有的教授也是这样理解的,可是,让他们回到农村生活,他们又不愿意回去!这才是现代版的叶公好龙!乡村里是什么呢?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里谈到在乡村里董事长就是农业经营者,打工的是高级白领,中层管理者和工作者是股东,企业是农业的托拉斯。那么,乡村的乡愁通过什么来建构呢?就是尽可能把所有的乡村文化特色化、差异化,而不能再出现“万村一面”的现象。欧美的一些传统小镇,有的卖巧克力、有的卖旧报纸、有卖老爷车的、有卖书的、有特色餐饮的等等,特色产业不一定就是工业,更多的是文化和文化产业,是历史甚至典型的怀旧产业和消费。所以,我们强调的乡村保护就是保护原文化、原生态、原住民、原习俗、原风貌和原地点精神,但是,这里——传统乡村必须有就业。我们必须从这个多元创新的意义上理解乡村建设,真正的乡愁才可能保留,乡村建设才能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有资料说美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住在中小城镇里,在洛杉矶周边有八十多个村镇构成一个地域城镇生存体系,小城镇是最能够体现美国的生活方式的地方,小城镇,不是落后的农村,而是景观优美、设施齐全的“生活共同体”,去过美国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但是,在中国,很多落后的村落不仅生活方式不完全,而且污染还较为严重,主要有四种:一是河水和饮用水污染;二是生活垃圾污染;三是农药污染;四是乡镇工业污染。特别是落后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是造成各种各样疾病频发原因之一,几乎每个省都有一些比我们想象还落后的地方。这些落后村落的贫困、污染、陋习等地方性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变,一定会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阻力。另外,还有文化和伦理上的问题,如经常看到某媒体说,高速公路上运输橘子的车或运输其他物品的车翻了,很多农民一起不去抢救人而是去抢货物,这种落后的集体文化行为,就是传统乡村脱离现代城市文明的一种结果,也是在空间上远离文明的结果之一。如果说要想改变农民,必须让农民成为有“契约精神”的、有基本道德伦理的市民社会的成员。如果要让一些落后地方的农民有利他主义文化倾向,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具有由现代文化认知所构成的“集体良知”。在那些传统乡村,因为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加上缺乏文化教育,很难形成有人文主义内涵的群体认知,这样的群体在某种意义上说,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文化和情操都很难建构,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些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说,真的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解决底层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的文化缺失问题。
传统乡村的文化重构,主要是寻找那些优秀的村落空间、优秀的地点精神,寻找那些值得传承的、向上的优秀集体记忆来进行重构。有时候我们很着急,因为有很多人认为把农民留在乡村就可以了,可是他们不知道,当下,好多传统的乡村里连下水道也没有,化粪池也没有,晴天还很好,一到阴雨天污水甚至流到井里、流到河流里……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多。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现代科技、现代文明、现代城镇系统和现代科技农业把小城镇、传统村落纳入大中城市的网状地域结构中来,像上海、苏州、无锡的郊区那样,让城市文明普及到乡村,这样,乡愁的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农民的现代生活空间体系才能成建构起来。我们在湖北蕲春统计了近一万个自然村的情况,其十户以下的自然村占百分之四十,很多自然村只有几户人家,这种极度分散的自然村很难形成“集约型”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如果他们是农场的管理者,或者是机械化和智能化农业的耕作者,即使居住在再分散也还是“城市人”,他们通过现代交通、私人交通工具、现代网络和现代工作方式与外界联系。在中国一些落后的村落,特别是那些空心村,虽然房子坍塌了,农民亦弃之不顾,但是房子的宅基地产权还在原农民手中,农民到城市里打工之后,又往往会在乡镇里、县城里或是大城市郊区购房,收入较高者又重新回到村里在交通好的地方再盖房子,因此,一户多基、一户多宅的现象在一些地区比较普遍。如果不解决此类问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是有很大阻力的。我们反复强调,传统乡村文化重构的本质就是让农民市民化,让他们受教育、有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和“集体良知”,像费孝通当年讲的,在乡村底层建构“文化自觉”。所以我们更强调从“乡村文化自觉”到“城市文化自觉”的转化,这也是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4 从乡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整合与社会融合
现在要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现代交通结构的改变,如地铁、高铁和私家车交通把地域城市的地形结构框架都拉开了,东京到大阪之间八百多公里是没有传统乡村的。在美国五大湖地区和三大城市群地域都是城镇连绵区,换句话说,有时在美国开车是看不到农田的,四周都是森林;一些大城市在飞机上也是一眼望不到边,未来的城市乡村差别将会越来越小的。我们当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也提过“消灭三大差别”,其中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差别。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城乡、城郊差异的界线已经模糊不清了。
差别在哪里呢?怎么消灭呢?如在乘坐欧洲之星,在沿路看到的小城镇和居住点,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是和中国村落不一样的“农村”,小镇里有咖啡厅、小酒吧、有现代生活设施、有就业体系、有世代传承的家族企业。即使是农业生产,在农田看到的也都使用农业机器的操作者,他们操作电脑、多类型农业机械,甚至用直升机管理农业。原农业地带的小镇里的“农民”穿着也与城市里人没有差别。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意涵的核心意义就是让城乡的分野的界限不十分清楚。中国古代是城乡有别的,在先秦的文献中对城市和农村的区别称为“国野之别”,城里人叫“国人”,农村人叫“野人”;还有一种分法是“都”“鄙”之别,城市里人称为“都市人”“都人士”,乡村人称为“鄙人”,后来“鄙人”一词演化为中国人日常用语的谦称。值得关注的是西方现代地理学还有“三地带理论”,也描述了城乡分野的变化。现在城市和乡村的发展过程必然表现一种发展规律——城市无边无界。未来,在城乡之间,特别是在生活方式上城乡分野的鸿沟会逐渐缩小。
“原农业地带”这一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大城市区域中的一些小镇和村落,会散散落落地形成一个有机性的区域空间,在休斯顿就是这样,有的住在森林里、有的住在湖边,有的住在山里……去哪都要开车,住在农业地带怎么就说是农村人呢?这个概念就需要改变。另外的含义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个人住在不同的空间里享受和实践着现代文明,如前述,主要是通过“交通方式”“交往方式”“通讯方式”、“工作方式”和“消费方式”形成的“城市 生活方式”的变革,形成城市文明的高普及率,住在那里都是市民。我在1986年一次苏州学术会议上提出迟早有那么一天,苏州和上海要连在一起,很多人不同意我的想法。当时还年轻,在会上和一位领导争论起来。现在的苏州和上海基本连在一起了,所以我现在还要说:迟早有一天,上海、苏州、无锡、常州要连在一起,成为大都市“连统区”或称为“大都市联合统计区”,这种趋势不是靠政策就可以阻挡的,因为它是通过公共交通、市场关系和土地级差、网络化梯度社会结构等因素决定所形成的差序化社会空间格局的必然结果。再用丹尼尔·贝尔的话来完整表述就是城市“无底、无形、无边”,当下,网络社会形成的“自媒体”文化和经济,更能够说明这种现代性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这种无边无界特征的现代性意义。
所以,也可以这样说,现代技术改变了城市空间结构,现代生活方式改变了城市社会结构体系,这是一种必然趋势,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注意对传统村落文化的强保护和精准保护。在现代技术手段广泛应用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对传统村落进行更精准的保存,让它更有原汁原味的文化特质。我们对龟山村这个传统村落规划,就是把握了“原”和“源”的文化价值取向,即原住民、原民俗、原生态、原生活方式、原记忆,特别是表现“原地点精神”文化创新的,包括“文化源头”和“文化源流”的保护。在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保留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思想取向,这也是要反复强调的:保护乡愁不能保留落后,制定保护规划时,一定建立政府、专家、市民和农民共同参与的选择机制。现实的情况时,需要有一批文化精英挺身而出,走向社会、走向基层,提出主张,进行自我建构的同时建构乡村社会的文化,这个时代应该是要到来的。
那么,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在哪呢?首先,从身份讲,农民要成为市民,从这一点上说,在哪都可以。其次,从空间上讲,农民应该在城镇生活体系内,中小城镇应该成为大中城市的区域网状结构化的组成部分。第三是,从分类上讲,可以城市里,也可以在原农业地带,但更希望有更多的农民成为就地城市化的市民。
5 保护好以往的乡愁,建构好未来的乡村集体记忆
人类社会的城市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在1848年时的城市化率是10.9%,美国也只是10.6%左右。可是过了100年,即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化率仍然是10.%左右,而美国已经接近70%,也就是说在1848到1949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没有任何发展。 这一百年,正是中国积贫积弱,烽火连年,战乱频仍,灾害不已的100年,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段时间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过程,早在1850年英国的城市化率就已经达到50%,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完成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社会一直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这也是当代中国城市化任重道远的原因之一。
直到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只有17.8%,改革开放后形成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局面,2000年城市化率是30.1%,2010年达到50%,这一年也是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的一年。到了今天,即2016年的中国,城市化率已经接近57%,这个过程正好反映了全球近代城市化的发展规律,也即25年左右城市化人口翻一番。我们需要认识的是,城市化率只有达到50%的时候,社会才真正进入城市社会的发展进程,我把他称之为城市社会的来临。可以看到,假如按照近代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每25年翻一番这一规律发展的话,就中国目前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左右的情况看,(虽然还有水分,城市户籍人口可能占40%到45%左右),如果25年左右中国城市人口翻一番的话,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将如何发展呢?很显然,未来25年左右,中国也将会全部完成城市化发展的过程。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如果真正达到80%左右也就等于完成了城市化。这其中有一个经常被人们忽视的一个理论,即“城市文明普及率”理论——如果城市化率是10%的话,只有30%的人可以享受城市文明;如果有30%城市人口,就会有50%的人享受城市文明; 如果有50%的城市化率,就会有70%的人享受城市文明;如果城市化率达到75%或80%的话,就会有90%以上的人享受城市文明,也就等于完成了城市化这一过程。不言而喻,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到城市里生活,最终是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普及所表现的城市性与现代性。进一步解剖还可以看到,如果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的水平上,城乡人口的流动就基本停滞了,或者流动规模变得很小了,流动方式也被改变了,主要体现在城市(镇)之间的人口流动,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及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已经证实了这个结果。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角看,如果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时,在一般情况下(不出现巨大的社会动荡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发展会进入较高速发展的状态,中国以往的城市化已经证明这一点。如果城市率达到80%以上的话,城市化就基本完成了,那时的人口红利会真正失去,中国房地产市场也会出现质的改变。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1850年英国首次完成了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社会变迁,并在这一年并创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届世博会。无独有偶,160年后的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也第一次达到了50%的水平。这一年,上海也举办了世博会,也是人类历史上第41届世界博览会。这些相似的历史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城市化率达到50%的时候,表明社会财富已经集聚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城市经济到了可以反哺农村的水平。农村的基础建设、农村的环境改造、农村的空间规划,特别是农村的文化模式和产业模式都可以得到城市经济的直接反哺和辐射。我们已经看到,大城市的郊区农业、发达城市的县属农业发展的都比较好,其原因就在这里。也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概念:城市是地域生产力的集中表现形式,凡是经济繁荣的地区,也必然都是城市繁荣的地区,反之,亦然。上海、北京、深圳和苏州的农业、农村发展都比较好,也是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一个结果。实际上,深圳和上海是中国最早可以宣布没有农民的城市,深圳已经宣布了,上海虽然还没宣布,但已经是没有传统意义上农民的城市。
记住乡愁、表达乡愁、保护好乡愁,只有现代化建构的过程中,社会整体财富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否则,在外不能抵御列强侵略,内不能创新发展,游民四起,哀鸿遍野的时代,民众温饱都不能解决,面对大好河山,只能抱残守缺,望眼东流水而束手无策,近百年来的中国,无数乡村在列强的炮火下,多成为断壁残垣……我研究城市近四十年,十分清楚城市的内在价值: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城市是社会发展动力、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创新地、城市是人才集聚的高地,城市是人类的财富中心……等等。所以说,50%的城市化率,至少表明了社会财富增长进入了快车道,可以对农村文化进行保护、重建和文化反哺,可以对农村进行现代文明和与现代经济上的血液输入。回过头审视现实,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发达地区的美丽乡村建设大都比落后地区要强,比如浙江和江苏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政府不仅可以补贴大量资金,村民的文化自觉也比较普遍。相反,一个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城市政府则很难对乡村建设有较好的补贴,村民因缺乏文化知识而缺乏文化自觉。
推进城镇化就是推进现代化,现代化的结果就是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所谓现代性,换句话也就是城市性。乡村文化重构不是保护落后而是保护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在本质上是要重构乡村的现代性——城市性。让乡村人有市民社会契约精神意义上的价值取向,有自我生存能力、自我改变贫穷的能力和应有的社会保障。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农业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是不能明确划分的,往往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城市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人们的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是可以明确分离的,而且闲暇时间具有某种法律保证,这也传统意义上划分城市生活方式和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的特点之一。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词意上加以区分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如农民的生产我们一般称之为“劳动”,而城市人的劳动我们一般称之为“工作”。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想象,传统农村变成现代城市生活的聚点、现代生活的小镇应该是什么样?其实发达国家已经有标杆和样板。比如发达国家的工程师小镇、白领小镇、特色经济小镇和特色家族企业小镇等,这样的“原农业地带”的小城镇和居住点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延伸,有人称之为“逆城市化现象”,而我称之为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深化现象。
如果有机会应该去莫干山或者安吉的乡村看一下,或者到南京高淳桠溪国际慢城的大山村去看一下,传统落后的小镇、小村已经直接跨入国际的视野、跨入国际生活的范畴,那里的一些城市里人、那里的本地人、那里外出打工回来的人,正在实践着乡村城市化的过程,正在创造山村里的城市生活方式。无论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收入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来农民和一般的城市居民。正如孟德拉斯所说:那样的乡村里,农民的房子比城里人的房子大、农民的冰箱也比城里人的冰箱大。但他们已不是传统农民,他们在敲响传统农业的丧钟。这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国面临着传统农业的终结的考验。
最后,我们要重复讲这样一句话,要想保护好农民、要想农民生活的好,就必须减少农民,就必须让他们成为城市生活方式中的一员——市民;要想保护好美丽乡村的“乡愁”,必须推进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走城市化发展道路,反过来才有能力保护好正在消亡的村落、乡愁和乡村的“集体记忆”。
[1][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铦,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吴相湘.晏阳初传.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
[4]张鸿雁.“社会精准治理”理论模式创新.[J]探索与争鸣2016,(01).
[5][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6]张鸿雁,房冠辛.传统村落“精准保护与开发一体化”模式创新研究——特色文化村落保护规划与建设成功案例解析[J],中国名城,2016,(1).
[7][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视角[M].周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张鸿雁.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创新[J].社会学研究,2013,(3).
[9]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高永青
Does 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farmers, but also can 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China has been a country since ancient times to agriculture. Until now, a lot of social problems are derived from the deepening of urban and rural structure two. An older generation of scholar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 are full of contains a point to a personal value ideal and the humanistic spirit,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is on the toiling masses of humane care --the last century 20, 30 years, a group of intellectuals, cultural deep into rural development field studies, also think fundamentally solve problem of poverty in China and farmers,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olution:to farmers for cultural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As the classical writer said, "the former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and the problem is to transform the world.".
Nostalgia ; original culture ; urbanization ; hollow village
C912
:A
1674-4144(2016)-03- 04(10)
张鸿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名城》杂志主编。
张鸿雁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特色文化城市研究(12&ZD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