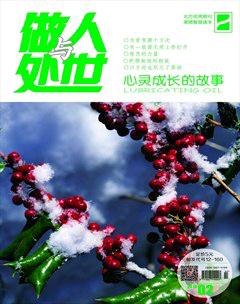有一扇窗无须上帝打开
刘悦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这句话强调了眼睛对于一个人心灵表达的重要性,然而它默许的,或者是不言自明的,即心灵窗口很重要这一事实。眼是心之窗固然不假,我想说的是,窗是屋之眼。一间房屋要是没了窗,它就是一堆砖头木料,死气沉沉;有了窗子则迥然不同,顿时神气活现,灵动起来。这就好比画龙点睛,未经点睛的龙只是血肉的堆积,点睛之后,霎时间气韵生动,顾盼自雄。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的这句诗细腻温馨,寄托了许多美好愿望。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欣赏起来绝不可以落足于灯火明亮的窗内,这是审美上的失败。驻足静谧悄然的夜风中,慢慢踱步走近,看着窗纸上一男一女共执一剪,在跳动的烛火灯影里剪着烛花,明明灭灭间令人充满无限遐思。观赏的位置由外而内,由远及近,无尽黑夜渐渐聚拢于一室幽窗。
与此相反,杜甫用另一种方式写道:“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倚窗而望,满眼尽是峻岭白雪,直达幽幽天际,气势非凡,闭目细品转而微觉陋室生辉,灵台澄澈清明。此一回,我们的视线由内而外,由近及远,推演到无休止的境地。
“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在这一句诗中,站在窗内窗外观赏似乎都不恰当,那只好寄情于芭蕉——我就是芭蕉,芭蕉就是我。浸润了阳光和雨露,惬意地舒展枝叶爬上纱窗,给屋内的人留一道倩影,为屋外的人摆一道清阴。平素爱听《蕉窗夜雨》,雨滴斑驳错杂,或急或缓打着蕉叶,遂而心神扑散开来,随着雨滴飞溅在玻璃窗上,再静静流泻,一层漫着一层,轻柔温润,娴静安然。窗,既可以看出来,又可以看进去;既可以从上瞧,也可以在下望,一进一出,一上一下,异彩纷呈。
在屋子里,从远处望去,始觉壁上有窗;稍近,觉窗中有景;再近,窗隐而景盈。这就像人生一样,小的时候,知道有个玩具叫做生活,充满好奇;长大一些,发现很多人的生活很精彩,不由得定睛凝视;终于步入社会,恍然明白自己每一天都在拼命生活,逐渐融入其中而不自知。每个人都有一扇窗,也许是实体的,也许是内心的。主人通过窗子向外看称之为观赏,其他人通过窗子向内看叫做窥视。实体的窗子被窥视,主人不悦,某种秘密泄露了,私生活被曝光了,引起纠纷不断;内心的窗子被窥视,主人更不悦,仿佛安全感丧失殆尽,继而惶惑犹疑,不知如何自处。人们之所以对窗子小心翼翼,敏感脆弱,大概是因为窗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不想要多得一分,也不情愿少了半点,就像黑洞的入口处,内外是两个世界,一不小心,必然双双崩塌。
在唐代,比较常见的窗是直棂窗,富贵之家用得起窗纸,贫寒农家用不起,雨雪寒天,只好用茅草、破布毡子挡一挡,权解一时之急,古代学子寒窗苦读,也就来自这里。“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幸运的,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寒门学子,屡试不第,更加穷困潦倒。要说简陋不堪,不能不提一提石屋和茅草屋的窗子,仅留有一个孔洞,用来警戒瞭望,除此别无它饰。就算这样,这个孔洞也属于窗子,可见,窗不但是实体上的一种构造,同时也是心理上的需要。在人类社会中,窗是人类自我的延伸,渴望交流,需要获得,哪怕只是一缕微不足道的光亮。
窗的外延不在少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在朱熹眼中,书是他看世界的窗,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推而广之,对个人而言,眼睛看到影像,耳朵听到声音,嘴巴尝到食物,鼻子闻到气味,身体感到触碰,种种信息,都有窗的影射。
对于世界,有人冷眼旁观,是非不管;有人古道热肠,悲慨万端。一双眼睛固然是一个人看世界的窗口,同时又何尝不是世界看自己的窗口,这扇开得小小的窗,看不得多少世界,世界却把我们看得一清二楚,躲闪逃避都是徒然。那仅剩空壳的蝉,被东风吹来,又被西风吹去;那沾人的雾露,一边云气低垂,一边烟霭交接;那破土的幼芽,满心坚定执着,又满身风悲雨苦。所以很多时候无须妄自尊大,也无须趾高气扬,我们当满怀虔诚,恭恭敬敬地卷起窗帘的一角,用心去体悟感受。
(编辑/张金余)